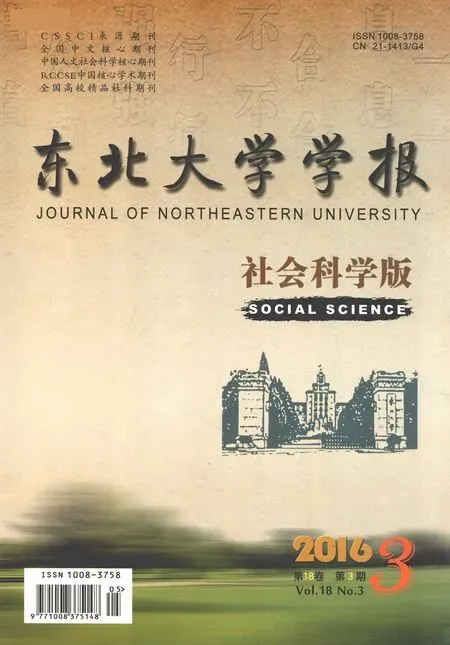中国外商投资影响对外投资的地区差异及门槛效应
2016-06-13李洪英李京文刘文丽
李洪英, 李京文, 刘文丽
(1. 北京工业大学 经管学院, 北京 100124; 2. 河北科技大学 经管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18)
中国外商投资影响对外投资的地区差异及门槛效应
李洪英1,2, 李京文1, 刘文丽1
(1. 北京工业大学 经管学院, 北京100124; 2. 河北科技大学 经管学院, 河北 石家庄050018)
摘要:以2003—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计量方程验证了IFDI对OFDI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运用门槛模型发现IFDI对OFDI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且影响因素IFDI规模、人均GDP和人均出口都具有双重门槛。研究结果表明:IFDI对OFDI的影响作用,以全国数据为样本并不明显,而以区域数据为样本则表现为差异性较大的促进作用,且中部地区作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小。运用双重门槛模型发现只有当IFDI规模、人均出口适中,人均GDP较高时,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才会最大。据此提出了有利于中国“引进来”促进“走出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 地区差异; 门槛效应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出了具有特色的开放型道路,实施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截止到2014年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国和第三对外投资国。当前中国的国际投资面临着新的形势:一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IFDI)进入了2.0时代。外商直接投资受中国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及环境污染限制等影响,其投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二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进入了新的时期,其流量已经接近并且未来几年肯定会超越外商直接投资。中国资金充裕了,企业走了出去,我们未来将如何对待外资,外资是否还有作用?三是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与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频繁进行,理清外商投资与对外投资的关系至关重要。四是我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国家战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未来如何调整使其更加协调发展很值得关注。因此,要回答和理清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层次地探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是否受外商直接投资影响,若存在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具有区域差异性及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二、 文献综述
关于IFDI对OFDI的影响,国内外研究成果较少。在理论上,尹应凯(2002)认为IFDI是OFDI的重要基础,发展中国家吸收IFDI可以解决“储蓄、外汇双缺口”瓶颈,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和竞争效应能够促进本土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1]。Dunning(1981)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阐述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净OFDI的关系,从逻辑上认为吸收IFDI可以提高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加速其OFDI的发展[2]。关于IFDI影响OFDI的机制,陈涛涛等(2015)认为IFDI通过直接影响、溢出效应、竞争效应、示范效应等影响目标国特定产业的产业环境,而受到影响的该环境培育了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对外投资所有权优势,从而促进了OFDI的发展[3]。在实证上,对于中国IFDI与OFDI的关系研究多是采用时间序列的协整分析技术。万丽娟等(2007)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4];陈涛涛等(2011)通过实证得出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不明显[5];肖光恩(2010)利用协整技术认为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在不同时期具有动态波动差异性[6];李洪英(2015)得出1982—2013年中国IFDI和OFDI的数据结构发生了变化,其存在三个阶段的协整关系[7]的结论。IFDI影响OFDI的实证结果差异很大,其原因可能是东道国其他因素存在一定的门槛影响了IFDI向OFDI的传导。I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促进本土企业对外投资所有权优势的形成,已为大家所共识。余泳泽(2012)证实了IFDI的技术外溢存在IFDI规模、潜在市场规模等门槛条件[8]。即当IFDI规模和潜在市场规模适宜时,其技术外溢明显,而伴随两者逐渐增大,其技术溢出效应反而会不断减弱。此外,Goh等(2013)认为出口规模的大小或许能够影响IFDI对OFDI的作用[9]。因为IFDI可以带来出口的增加,但是出口对OFDI的影响不确定,有可能是互补或替代关系。
从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一是现有的研究多是采用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由于中国实施对外开放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时间较短,其可获取的样本较少,不能很好地反映出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二是现有研究多是分析IFDI和OFDI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没有深入探讨IFDI对OFDI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及其产生的原因。三是现有研究多是关注IFDI技术外溢的门槛效应,没有进一步考虑IFDI影响OFDI是否也存在门槛效应。因此,本文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IFDI对OFDI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性和门槛效应。
三、 IFDI影响OFDI的地区差异
1. 模型设定
IFDI影响OFDI能力形成的现有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建立在Dunning 的IDP理论之上。本文也是依据此模型进行拓展和转换。在IDP模型中,人均净对外投资为一国人均对外投资额与该国人均利用外商投资额的差值。本模型为了探讨IFDI对OFDI的影响作用,把净对外投资拆分为IFDI和OFDI两部分,其中OFDI作为被解释变量,IFDI作为解释变量。Dunning等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需要较长时间的资本转化、技术外溢等才能增强东道国的所有权优势,提高其对外投资能力。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规模存量的积累[10-11]。因此,本文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IDP模型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保留在模型中,但由于国家不再统计,本文用人均GDP(GDPP)代替作为控制变量。此外,Dunning等(2015)认为国际贸易介于吸引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中间,对国际投资影响较大,而出口可以为东道国积累资本国际化的经验,进而提高了东道国对外投资的能力[10-12]。因此,引入人均出口(EXP)作为控制变量。最终的模型设定如下:
lnOFDI=α0+β1lnIFDI+β2lnGDPP+
(1)
式中,OFDI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IFDI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GDP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EXP为人均出口,μ为随机扰动项。为了降低异方差和异常项对模型数据平稳性的影响,采用了对所有变量取对数的方法。
2. 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用于分析中国IFDI影响OFDI的地区差异性。根据中国的经济特征、地理区位,以及参照西部大开发的划分,选取了中国31个省区市,并划分为东、中、西3大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陕西、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区市。数据时间选取2003—2013年,IFDI对OFDI的影响主要来自量的累积作用,因此选取这两个变量的存量。OFDI数据来源于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IFDI数据来源于2004—2014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各省区市的人均GDP、出口额和人口总数均来自于2004—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模型的估计采用Stata 13.0完成。
3. 实证结果
表1给出了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的实证结果及Hausman检验。

表1 模型的实证结果
注: ① FE表示固定效应模型,统计量为F值,括号内数值为对应回归系数的t值;RE表示随机效应模型,统计量为Z值,括号内数值为对应回归系数的z值。
② *、**、***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
从表1中可以看出,全国样本和东部地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表现较优,中、西部地区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表现较优。从全国样本来看,人均GDP系数为3.650 8且非常显著,与IDP理论完全相符,但是人均出口和IFDI系数均为负,且均不显著,说明IFDI和人均出口对OFDI为不明显的抑制作用。从3大区域来看,IFDI对OFDI影响的地区差异较大。中部地区IFDI的系数为0.354 6,且在10%水平上显著,而东部、西部地区IFDI的系数都不显著,分别为0.192 1和0.079 1。3个地区人均GDP系数都为正数且在1%水平上非常显著,东部地区系数为4.585 1,高于西部的3.397 9和中部的3.622 5,表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对OFDI的促进作用高于中、西部地区。人均出口系数只有在东部地区显著,中、西部均不显著,其中东部和西部对OFDI成负向影响,而中部人均出口对OFDI成正向作用,表明人均出口过大或过小对OFDI的形成具有抑制的作用。
由上面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中国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总体并不明显,这与陈涛涛、潘文卿、陈晓研究中国IFDI促进OFDI的结论一致[5]。这个实证结果好像与中国实际现状相矛盾,但是从东部、中部、西部区域角度,我们发现IFDI对OFDI的影响地区差异很大,且都表现为强弱不同的促进作用,其中中部作用最大。这说明了IFDI对OFDI的直接影响不明显,更多是间接影响。如IFDI进入中国,直接影响了产品市场、资源市场、金融市场、产业环境及投资政策的的变化,而中国的这些变化能够直接影响到本土企业OFDI的形成。IFDI对OFDI影响的地区差异性,其原因理论上可以假设为区域内其他因素影响了IFDI向OFDI传导的通达性所致。因此,需要进一步验证不同规模水平的其他因素,是否能够导致IFDI和OFDI两者作用具有显著差异性。
四、 IFDI促进OFDI形成的门槛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国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揭示区域间影响作用差异性的原因,本文引入了面板门槛模型。该模型用来检测IFDI规模、人均GDP和人均出口是否存在门槛效应使得IFDI对OFDI的影响明显不同。
1. 面板门槛模型
门槛分析起源于1978年Tong提出的门限自回归模型,这是一种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在经济领域广泛应用。后经发展应用于面板数据,特别是Hansen提出了采用“自体抽样法”检验计算统计量的渐进分布,判断门槛效应的显著性,使得面板门槛模型更加准确。本文采用Hansen的面板门槛回归方法[13]。选取lnIFDI、lnGDPP和lnEXP为门槛变量,并且考虑到这3个变量影响OFDI与IFDI的关系可能存在多个门槛值,所以分别建立如下的3个多重门槛模型。
lnOFDIit=α0+α1lnGDPPit+α2lnEXPPit+β1lnIFDIit·I(lnIFDIit≤γ1)+β2lnIFDIit·
(2)
lnOFDIit=α0+α1lnEXPit+β1lnIFDIit·I(lnGDPPit≤γ1)+β2lnIFDIit·
(3)
lnOFDIit=α0+α1lnGDPPit+β1lnIFDIit·I(lnEXPit≤γ1)+β2lnIFDIit·
(4)
其中,i=1,2,…,N,表示不同的省市;t=1,2,…,T,表示时间。I(·)为指标函数,γ1<γ2<…<γn为n个不同水平门槛值。
本文运用Stata 13.0软件通过稳健性面板门槛估计方法,对2003—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全部样本进行检验,以期发现门槛效应的存在。其中门槛值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设置网格300个,并进行500次的“自抽样法”重复估计。
2. 门槛模型选择
表2分别给出了3个门槛变量单一门槛、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F统计量。从表2中可以发现,门槛变量lnIFDI在1%水平下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极其显著,三重门槛不显著。鉴于双重门槛模型的F统计值较大,其自抽样门槛检验P值更低,变量lnIFDI选取双重门槛模型。门槛变量lnGDPP单一门槛在5%水平上显著,双重门槛在1%水平上极其显著,三重门槛不显著,选取双重门槛模型。门槛变量lnEXP在10%水平上单一门槛和三重门槛都不显著,而双重门槛在1%水平上极其显著,选取双重门槛模型。此外,表2在双重门槛模型下给出了3个变量的门槛估计值及其95%的置信区间。lnIFDI、lnGDPP、lnEXP的两个门槛估计值分别为11.731和15.62、9.384和10.253、5.719和8.001。

双
3. 面板门槛实证分析
表3列出了人均GDP、人均对外出口及IFDI规模的双门槛模型估计结果。IFDI规模双门槛模型中,所有变量参数估计在1%水平上非常显著,IFDI规模对OFDI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IFDI低于门槛值12.436 8亿人民币时,IFDI每增加1个单位,将会带动OFDI增加0.386个单位;当IFDI规模处于12.436 8亿人民币和607.686 8亿人民币之间时,1个单位IFDI的增加将会带来OFDI增加0.620个单位;当IFDI规模跨过607.686 8亿人民币时,IFDI促进OFDI的作用具有下降的趋势,其系数从0.620降低为0.543。在人均GDP双门槛模型中,变量lnEXP在5%水平上显著,与人均GDP门槛区间相对应的3个lnIFDI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伴随人均GDP的增加,IFDI促进OFDI能力逐渐增强。当人均GDP小于11 896.51元人民币时,每增加1个单位IFDI,可以促进0.867个单位OFDI的增加;当人均GDP跨越这门槛且低于28 367.52元人民币时,IFDI对OFDI的促进系数变为了1.013;当人均GDP超过28 367.52元人民币时,IFDI带动OFDI的系数增加为1.124。在人均出口双门槛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参数估计在1%水平上非常显著。随着人均出口规模的增加,IFDI具有对OFDI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呈先增加后下降趋势。当人均出口规模小于304.60元人民币时,每增加1个单位IFDI可以促进0.986个单位OFDI的增加;当人均出口规模超过这个门槛值且小于2 983.94人民币时, IFDI对 OFDI的促进系数增加为1.055;当人均出口超过第二个门槛值2 983.94元人民币时,IFDI对OFDI的促进系数减弱为0.909。

表3 门槛模型系数估计结果
注: 括号内为门槛值,GDPP、EXP单位为元,IFDI单位为亿元。
表4列出了中国2004年和2013年31个省区市3个门槛变量分布,它们进一步反映出人均GDP、人均出口、IFDI规模所产生的门槛效应与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间IFDI推动OFDI的差异性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在IFDI规模门槛效应中,2004年只有西部的贵州、云南等6省处于第一个门槛之下;东部大部分、中部全部和西部绝大部分的22个省区市处于两门槛值中间;只有东部江苏、山东、广东3省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经过10年发展,到2013年IFDI规模的阶段分布变化不大,只有东部的天津、上海从第二阶段跨入了第三阶段,其他省区市基本上没有变化。总体而言,从2004年到2013年31个省区市IFDI规模分布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球形状,绝大部分省区市集中在第二阶段,IFDI促进OFDI的作用较第一、三阶段都强。这些说明我国的IFDI促进OFDI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但未来随着跨过第二个门槛省区市的增加,IFDI对OFDI的促进强度逐渐降低。人均GDP门槛效应中,2004年IFDI促进OFDI的作用整体较弱,因为中、西部地区及东部地区河北、广西和海南都处于第一个门槛之下;只有东部地区的天津、辽宁等7省区市处于两个门槛中间,北京和上海两地超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到2013年所有省区市的人均GDP都已经跨越了第一个门槛值,随着人均GDP的增加,IFDI促进OFDI的作用逐渐增强。跨越第二个门槛值的省区市也由2004年的两个增加到11个,IFDI 对OFDI的推动效应也在增强。人均出口门槛效应中,2004年只有西部的四川、贵州等5省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东部的北京、辽宁等7省区市跨越了第二门槛;其余的19个省区市如河北、上海等都处于两门槛之间。2013年处于第二阶段的省区市数量保持不变仍为19个,只是第一阶段的江西、湖南、四川、贵州跨过门槛值进入了第二阶段,而第二阶段的青海滑落到第一阶段,上海、山东、重庆从第二阶段跨入了第三阶段。总体而言,随着人均出口的增加,IFDI促进OFDI的作用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二阶段。

表4 门槛值及数据分布
通过门槛模型的检验分析,我们发现IFDI促进OFDI存在门槛效应,即它们两者的关系受IFDI规模、人均GDP及人均出口门槛值影响。在IFDI规模门槛效应中,随着IFDI规模的增加,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先增加后降低。由于东道国形成对外投资能力的大小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大小密切相关,而外商投资技术外溢又与IFDI规模相关,该结论与余泳泽(2012)探讨IFDI规模与外商技术外溢门槛效应的结论完全一致[8]。在经济发展初期大量引入IFDI,解决了国内建设资金不足及技术落后的问题,IFDI不仅为东道国积累了大量资本,而且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了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间接促进了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随着IFDI流入规模的增加,当东道国众多跨国企业资本充足、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且已具备对外投资能力时,IFDI促进OFDI形成的资金优势和技术优势则逐渐下降。在人均GDP门槛效应中,经济发展水平越高,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越大。这与Dunning(1981)的国际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所隐含的结论相一致,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增加[2]。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对外开放度和技术水平较高,非常有利于IFDI技术资本效应的吸收,使得该地区形成对外投资能力的速度较快。在人均出口门槛效应中,随着跨越门槛值的增加,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先增强后减弱。IFDI的增加势必会持续增加人均出口的规模。陈洁、蓝振风(2013)认为出口是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先导,当某商品的出口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企业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运输和生产成本会选择在商品销售国进行投资生产,从而出口会促进OFDI的增加,两者表现为互补性[14],此时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增强。当出口跨越门槛值以后,由于市场的有限性,若某种商品出口规模继续增加,势必会降低该商品对外投资的增速,甚至将来会减少对外投资,使得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由互补性逐渐转为替代性,进而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减弱。
五、 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2003—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首先验证了中国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尽管全国样本不支持这一结论,但使用区域样本检测出了促进效应,并且东部、中部、西部中促进作用大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其中中部促进作用最大。其次,使用门槛模型进一步探索了IFDI促进OFDI地区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发现IFDI促进OFDI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IFDI规模、人均GDP及人均对外出口的影响。IFDI规模存在两个门槛,随着逐级跨越门槛,其对OFDI的促进作用先是持续增加,后呈下降趋势。当前,只有东部极少数省区市超过了第二个门槛,IFDI的促进作用减弱;东部、西部绝大部分及中部全部都处于IFDI高速促进OFDI的第一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人均GDP存在双门槛效应,其门槛规律为人均GDP越高,中国IFDI促进OFDI的作用越大。2013年,中国东部地区除了河北、海南外都高于第二个门槛值,其I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其他地区处于两门槛值之间,IFDI的促进作用较大。人均对外出口也存在双门槛效应,伴随其规模的增加,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呈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目前,东部9省和重庆市跨越了第二门槛,其IFDI的促进作用变小;中部全部和西部绝大部分省区市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 IFDI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的甘肃、青海没有跨越第一个门槛值,IFDI的促进作用较大。
IFDI规模、人均GDP和人均出口的门槛值,对于“引进来”促进“走出去”及完善、调整两者相协调的国家战略具有如下启示:①根据人均GDP门槛效应,利用东部地区经济水平较高和基础环境较好的优势,重点吸引高质量外资,侧重于科技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最大可能地发挥外商投资对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②运用外商投资规模的门槛效应,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加大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规模,特别是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西部地区对外投资可实现快速增加。③把握对外出口的门槛效应,重点提高东部地区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中西部注重出口规模的增加,实现中国对外投资的持续发展[15-23]。
参考文献:
[1] 尹应凯. 试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互动关系[J]. 国际贸易问题, 2002(1):36-39.
[2] Dunning J H.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al Approach[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81,117(1):30-64.
[3] 陈涛涛,陈晓. 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机制——机制分析框架的初步构建[J]. 国际经济合作, 2015(5):4-11.
[4] 万丽娟,彭小兵,李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宏观绩效的实证[J].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30(5):143-149.
[5] 陈涛涛,潘文卿,陈晓. 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研究[J]. 国际经济合作, 2011(5):4-13.
[6] 肖光恩.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相互促进?——基于UNCTAD 1982—2007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J]. 珞珈管理评论, 2010(1):106-113.
[7] 李洪英. 中国对外投资与外商投资变结构协整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8):104-111.
[8] 余泳泽. FDI技术外溢是否存在“门槛条件”——来自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门限回归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8):49-63.
[9] Goh S K, Wong K N, Tham S Y. Trade Linkages of Inward and Outward FDI: Evidence from Malaysia[J]. Economic Modelling, 2013,35:224-230.
[10] Dunning J H,Kim C S,Lin J D. Incorporating Trade Into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A Case Study of Korea and Taiwan[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1,29(2):145-154.
[11] 杨校美. 吸引外资能促进对外投资吗——基于新兴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分析[J]. 南方经济, 2015(8):63-76.
[12] 潘文卿,陈晓,陈涛涛,等. 吸引外资影响对外投资吗?——基于全球层面数据的研究[J]. 经济学报, 2015(3):18-40.
[13] Hansen B E. 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estination[J]. Econometrica, 2000,68(3):575-603.
[14] 陈洁,蓝振峰. 我国直接对外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关系实证分析[J]. 商场现代化, 2013(15):41-42.
[15] 朱华. 关于“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关系的理论思考[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9(1):5-7,11.
[16] 吴频,王红霞. 中国双向国际投资对策[J]. 中国金融, 2015(3):37-39.
[17] Apergis 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ward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utward: Evidence from Panel Unit Root and Cointegration Tests with a Certain Number of Structural Changes[J]. Global Economy Journal, 2008,8(1):1-12
[18] Huber F. Forecasting Exchange Rates Using Multivariate Threshold Models[J]. The B.E.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16,16(1):193-210.
[19] Prat S B S. The Effects of Global Excess Liquidity on Emerging Stock Market Returns: Evidence from a Panel Threshold Model[J]. Economic Modelling, 2015,52:26-34.
[20] 常亮,连玉君,安苑. 银行授信影响了企业的现金持有管理行为吗?——基于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J].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14(6):64-74.
[21] 刘敏,曹衷阳.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居民相对消费水平视角[J]. 工业技术经济, 2011(12):134-142.
[22] 叶初升,闫斌. 新常态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事实、大逻辑与理论启示[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5):82-89.
[23] 余官胜,杨文.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决定因素——基于投资规模的实证研究[J]. 经济经纬, 2015(4):61-66.
(责任编辑: 王薇)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Threshold Effect of IFDI on OFDI in China
LI Hong-ying1,2, LI Jing-wen1, LIU Wen-li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18, China)
Abstract: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IFDI on OFDI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3 in China. The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f IFDI on OFDI was found based on the threshold model. Moreover, IFDI scale, per capita GDP and per capita export all have a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IFDI on OFDI was not remarkable based on the total samples, but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romoting effects of IFDI on OFDI based on the samples of eastern,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middle region exerts the biggest effect followed by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 double threshold model,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IFDI on OFDI was the strongest in condition of medium-sized IFDI scale, medium-sized per capita export and higher per capita GDP. According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which may promote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gional difference; threshold effect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3.004
收稿日期:2015-10-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273021);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9132001); 北京市教委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SZ201510005002)。
作者简介:李洪英(1979- ),男,河北故城人,北京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河北科技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对外投资研究; 李京文(1933- ),男,广西陆川人,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数量经济研究; 刘文丽(1973- ),女,辽宁沈阳人,北京工业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财政投资研究。
中图分类号:F 83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6)03-024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