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太文学的
——李浩读札
2016-06-06黄德海
黄德海
文学的,太文学的
——李浩读札
黄德海
1
试图跟上李浩这样一个热情、诚恳、勤奋的阅读者,本就是一件极难的事,更何况,他的阅读路线在不断变化,系谱也不停改写——你哪里会追得上一个不断转向的人了?然而,不管李浩的系谱如何浩繁,他自己的解说如何精密雄辩,你在阅读中总是会怀疑,他的小说,是不是缺了点什么?
那么,用李浩熟悉的比喻,我们不妨在他庞大的系谱旁树起一面镜子,来照一照,看这系谱有什么秘密。这镜子,大概跟李浩的“魔镜”相似,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比如,这面镜子就先行拥有了李浩的另一方师承,即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面向,甚或西方某些古典的面向,它要以自己清晰的存在,对李浩的西方系谱进行“格义”——《高僧传》卷四《竺法雅传》:“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
2
《镜子里的父亲》“飞走的粗布褥单”章,姑姑随褥单上升而去。叙述者承认:“《百年孤独》,第十二章,马尔克斯笔下俏姑娘雷梅苔丝的离开也是如此,我将她的情节借用过来,形成互文,有意给我的姑姑制造幻美……不止如此,不止这一次,之前和之后我都还有诸多的化用,它们来自于马特·斯特兰德,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拉什迪,巴尔加斯·略萨,君特·格拉斯,王小波,杨显惠,卡尔维诺,赫拉巴尔,鲁迅,罗素,钱理群,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熟悉李浩的人当然知道,这就是他前述师承的展开。这个名单当然不够全面,即使从这本长篇里,你也会较为容易地辨认出柏拉图,《圣经》,浮士德,卡夫卡,舒尔茨,博尔赫斯……
学过中国书画的李浩当然会确认,先要摹写得像,然后才有变形和改造。摹写是学艺,变形和改造则是为了撕开这些优秀作品的缝隙,从而填塞进属于李浩自己的发现。在上述名单之后不远,李浩写道:“要有光……在没有光,光亮显得不够或者光亮过于炫目的时候,要有火,要让火焰燃烧,成为另一个变动的核心,和有光与没光的世界对抗……我四叔就是这样做的,从他很小的时候。”《圣经》中上帝自觉的开辟气魄(光),渐渐向人间的创造过渡(火),然后调子继续降低,落实到四叔的具体行动。不易觉察中,“要有光”在随后的叙事中出现,全然消去了神圣的色彩,变为艰难年代玩火的自发顽劣(反抗?),最终由卑微的偷盗取代。如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撑着阳伞来到人间,李浩把从《圣经》里盗取的光,凭技艺遮挡,用于自己的创世——艰难的,琐碎的,无奈的创世。或许,这就是小说的创世之秘?
化用必有其来源,也幻化出诸种可能。然而,有来源就必有限制,不化除来源,来自天廷的普罗米修斯就难免会被宙斯送上悬崖。《庄子·寓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野心勃勃地要“尽可能地触及人与上帝的那层关系”的李浩,已经有了他庞大的“有自也而可”,因而化除来源的“有自也而不可”尤其显得重要。在小说里优游创世的的他,是不是需要逆向回返到人间的创造,进而体认到圣经的开辟气魄呢?到那时,忍饥挨饿、偷盗成性的四叔,是不是能在某种意义上化除艰难,得到更为体贴的安慰,并进而给予写作者本人更大的安顿力量呢?
3
李浩说:“我的写作,从来都不只依附于一个完全的‘个人’呈现,我更愿意和我的阅读者一起反思、打量我写下的这个个人,从这个人的身上找到我们共通的影子。”这么说的李浩,在小说中摒弃人物身上的典型特征,也不以鲜活地勾勒出人物为能事,甚至,他不止一次强调:“模糊叙事是我的有意。”李浩企图在这个模糊里,含纳更多的可能,更多的不确定,更多的存在,更多的发现,甚而至于人性更广阔浩瀚的内容。
康德说过,“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或许是因为对人身上共通的影子的体察,李浩的小说里,没有任何笔直的东西——小说里的人物——主要是“父亲”,多的是专横,怯懦,自私,虚荣,盲从,告密,以失败者自居……所有在现代以来出现过的人性难题,都聚合在李浩复数的“父亲”身上,并由此勾连起“爷爷”和“我”——“父亲的一部分来自于我的姥爷,他是一个非常老实有些木讷笨拙的农民”,“在我的小说中,父亲连接着我个人的血脉,他也是我,交集着我对自己的爱恨,对世界的爱恨”。
李浩小说里的人物,几乎都有这种因复合而来的模糊,在模糊里有着时代的面影,社会的样态。深入以观,你会对这模糊有些微的遗憾,因为所有的爱恨,都因模糊而带着点冷漠,与人世和人心,略微有点隔离,少了点动人的东西。当然,李浩说过,他写小说并不是为了打动人,而是为了会心,似乎冷漠也是有意而为——我不确定是否如此,只觉得,复合在一个具体人身上的“所有人”,理想状态是,合起来是一个具体的人,活灵活现,穿衣吃饭;仔细琢磨,却七凹八凸,百手千头,每一个凹凸,每一个头手,都又是一个具体的人,也照样担水耕田。
对我来说,好的共通性,便如帝释天之宝珠:“网之一一结皆附宝珠,其数无量,一一宝珠皆映现自他一切宝珠之影,又一一影中亦皆映现自他一切宝珠之影,如是宝珠无限交错反映,重重影现,互显互隐,重重无尽。”一散为一切,一切归于一,当我们见到那重重帝网,宝珠无尽,便自不会有两歧的模糊和清晰,会心和动人——它们在帝网结处,交相辉映。
4
李浩的模糊,却并非因为他的小说忽视细节,相反,李浩的细节,我倒觉得是我称谓意义上的细节——比通常所谓的细节多出一点什么。李浩善于把一个细节展开,停顿,议论,思考,比对,解说,仿佛不如此,蕴含在普通称谓的细节中的能量就不能提取出来,给不出一个全息的世界景象。
还是《镜子里的父亲》,饥饿中的二伯患了肺炎,弥留之际终于喝上一碗粥,却病体不支,全吐了出来。奶奶起身准备打扫,一旁的姑姑却把二伯吐出的“米和汤,以及一些黄黄绿绿的不明液体,都舔了一遍”,直到踪迹全无。即便只看这细节,李浩写饥饿的能力,也可以得到赞许。而在二伯吐出之后,姑姑舔食之前,李浩有一段很长的饶舌——我所谓多出的一点什么:“之后的细节颇让我感到犹豫,是否把它落在纸上……涉及我的姑姑,隐身人,娇小,柔弱,一个女孩儿,习惯在暗处躲藏,喜欢一些透明的、易碎的事物……镜子里的细节会让她……要不要写出来……在我父亲的简史之中这段文字无关宏旨,也许可以忽略,但,这个细节……是不是可以交给镍币决定,一元和牡丹的一面代表讲述,而另一面,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1992则表示我可以使用橡皮,把这段细节抹去……抛掷的结果,是一元和牡丹战胜,那我说吧,简略,零度,打扮一下,尽可能减少这一细节的污渍感。”
现代小说不是嗜好人性黑暗和悲惨事件?为什么娴于这一系谱的李浩写到姑姑的舔食如此犹豫?写出来还要“简略,零度,打扮一下”?这个看起来多余的饶舌比直接写出多了点什么?——多了点对柔弱女性的心疼,多了点对人心暗面挖掘的审慎,多了点体谅和同情,多了点,对,小说的美德:因为小说不只是发掘人性黑暗的竞技场。
可是——讨厌的可是又来了。即便李浩的饶舌避免了小说对人心暗面探测的肆心,可仍然把一个细节折为两橛,虽让人看到了小说写作者的谨慎和宽厚,却也因说明而让细节失去了一击而中的力量,未能轻采毛发而深极骨髓。我想起南泉普愿的话:“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有力的细节,不用旁逸斜出,就在这一株花上隐含所有的花,隐含所有对此花的关爱,怜悯,痛疼,爱惜,时人见此,如对梦寐;而在看见的这一刻,此花也不再能够拆解,而是显现为这一株具体的花,天然灵动,娇艳欲滴,动人心魄。
5
米兰·昆德拉是李浩引用最多的作家之一,其中一句,引述更多:“小说的智慧不同于哲学的智慧,小说不是从理论精神而是从幽默的精神中诞生的。”李浩自己也写过《幽默ABC》——那就来谈李浩的幽默。
按之李浩的性情,验之李浩的小说,他即使写到目不识丁的人,也会用上一种特别的大腔圣调,叙事中带出他特有的庄重。这样的叙事方式,几乎很难有放松的时刻,更难以容纳幽默和反讽。在惯常该使用反讽、展示幽默的地方,李浩出现的往往是憨笑或反思(当然,李浩并不缺乏反讽的能力),难道他无意中背叛了自己信赖的昆德拉的嘱托?
《乡村诗人札记》里,“我”讨厌陈傻子,因此希望他倒霉。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想象“陈傻子戴着高帽游街,脖子上挂着一双破球鞋——就挂豆子的那双。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发现有谁的鞋会比豆子的那双更臭,陈傻子挂上这双鞋,他肯定就不想喘气了,从村东游到村西,不喘气的陈傻子就被憋死啦”。这是较为典型的李浩式的幽默,或者,不能称其为幽默,因为通常的幽默作用于机智(wit),而李浩的笑意里有一种拙朴。这样的拙朴,也不能说是天真,嗯,或者说,是一种经思考却不世故的天真之气,一种宅心仁厚的人才有的气息。在这个意义上,李浩不是忘记了昆德拉的嘱托,而是结合自身的朴厚性情,写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幽默——就像写姑姑的舔食,内中也含着他的宽厚,那是属于他自己的,特有的不忍。
在前面对李浩说“但是”的地方,让我来给昆德拉一个——小说真的是从幽默的精神中诞生的?昆德拉说这句话的时候,举的全是欧洲近代以来的例子,他可能忘记了,欧洲的小说,另有一个更远的源头,那就是古希腊。公元二世纪的希腊作家郎戈斯在他(后世也称为小说的)《达夫尼斯和赫洛亚》的“卷头语”中就表示,他写这作品的目的就是施教,教育人们认识灵魂与爱欲的关系。这样的说明,显然不是来自什么幽默,而是源于严肃。当昆德拉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与菲尔丁、斯特恩、歌德、拉克洛对立起来的时候,他大概迷醉于自己的幽默精神,忘记了在某种意义上,以上诸位一起拉开了相对主义的大幕;也没有区分,小说中所有人都有被理解的权利,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好——在他们之前,早有“每种技艺和探究……都以某种好为目的”的训诫。即使不区分这其中的高下,一个以小说为志业的人,还是知道这另一个更远的源头为好。
扯远了,还是回到幽默。在我看来,最好的幽默该是一种不得不然,一种因太过认真而来的不得不然。就像善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的庄子,他不是喜欢如此,当然也不是因为什么荒诞精神或幽默精神,而是“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所有来自幽默精神的幽默,我几乎要说,都不太值得关注。
6
“镜子在我的写作中的确是一个‘核心意象’,它是我对文学的部分理解,我把文学看成是放置在我侧面的镜子,我愿意用一种夸张、幻想、彼岸、左右相反的方式将自我‘照见’……”没错,李浩深爱镜子意象,集其大成的《镜子里的父亲》,更是在普通的镜子之外,使用了哈哈镜、三棱镜、魔镜,力图以此展示他磅礴的虚构野心。
凭借对这些镜子的不断调整,李浩展示了他出色的小说技艺,把他对社会的洞见,对时代的思考,对小说本身的认知,对未知的发现,对可能性的预见,对世界缺陷和这缺陷的超越……所有他想到的,只能用小说表达的那些,李浩都在尝试着做,也做得用心。
借助镜子,叙述从父亲出生前就开始了。在凝重的叙事中,父亲慢慢长大,阅读者也逐渐意识到,父亲的性格习与性成,却有着各种各样的伸展可能,不会呈现为唯一的形状;在不同的环境下,父亲将呈现出不同的样貌——那个遵循物理时间长大的父亲,如果身经的时代不是如此,他将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人。这个放置在不同镜子中的父亲,虽然一直带着他不可更改的缺点,绝少变动的性情,却让人相信,他会根据环境变化,有各种各样的展开,如同可以生活在平行宇宙之中。而在过往的历史中,父亲却只能如此显示。是的,我要说,李浩居然在一个结结实实的过往中暗示了另外多种可能——他几乎在虚构中创造了现实及其必然后果。
但是,读过李浩小说的人都会承认,镜子中的映像及其创造的现实,对焦老是不太准确,仿佛镜子的某些功能出了问题。或许有人会怀疑李浩的镜子不够明亮,而在我看来,问题出在李浩本身。李浩对镜子充当小说支点的热情,让镜子受到了限制,失去了来去自如的本性,变得粘滞而有所私爱,难免劳神而不够清晰。
写到这里,我约略有些明白了,李浩小说让人觉得缺少的一点东西,竟然是因为他对文学过多的热情。这过多的热情,让李浩成了优秀的小说写作者,却也同时让他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因而只看到镜子里文学的那一面。可那些镜子,那无数面镜子,照出的,可不只是文学世界。如果非得用镜子来结束这篇文章,那么,我想说,用力把这文学的镜子打碎,它的后面,或许另有一面更辽阔的镜子——“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或者,所有的镜子都不过是比方,不妨试着全部打碎?要知道,南泉普愿的那株花,透过迢递的时空,一直就在我们眼前。
(责任编辑:李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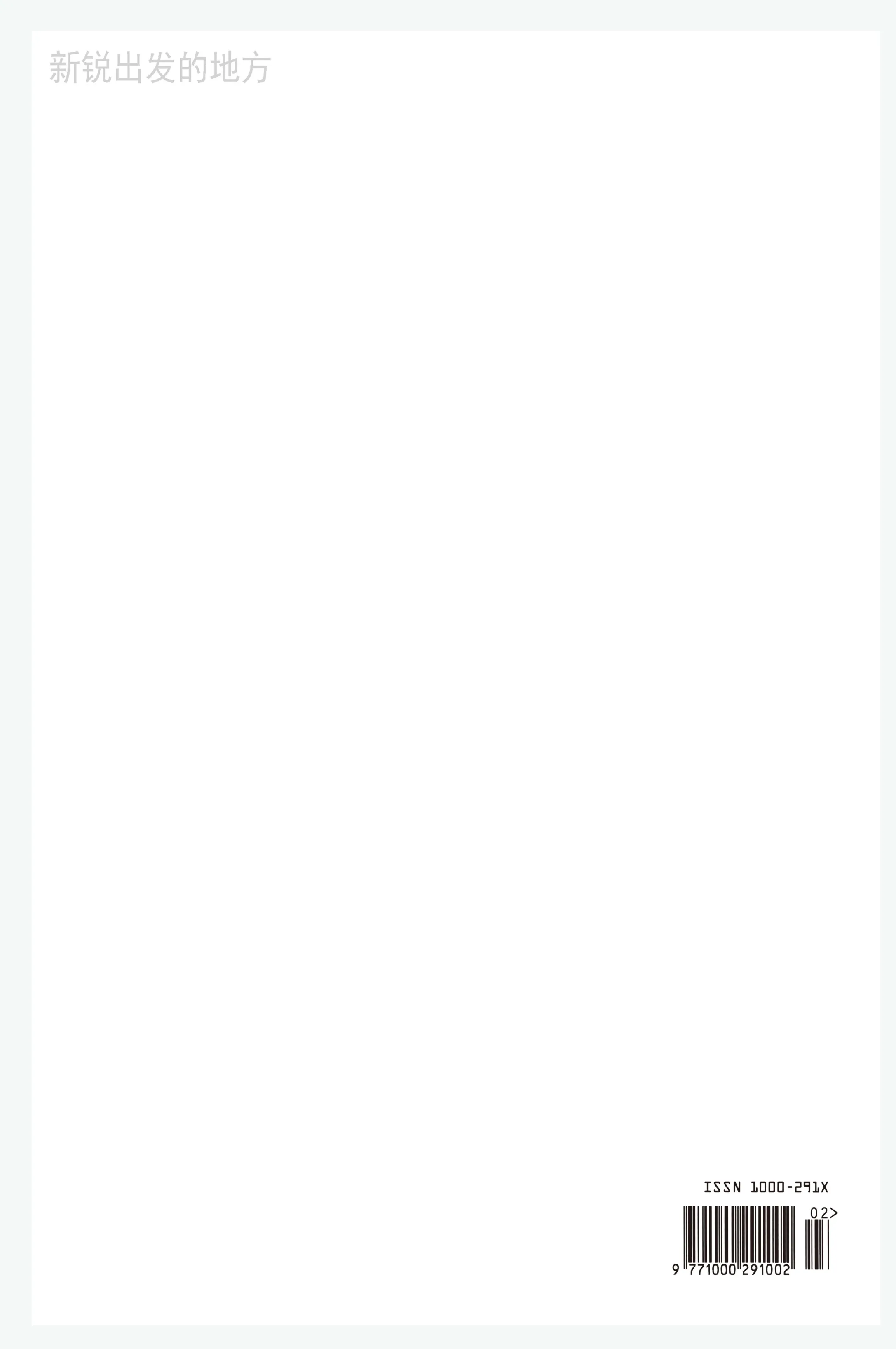
李浩自述师承:“一方面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另一方面,甚至更重的方面,是来自于他们的译笔。”“他们的译笔”,主要指西方现代以来文学作品的翻译。李浩经常在小说中仿写、改造他后一师承中的作品,并写有诸多研探的随笔,以至于生成了一个庞大繁复的李浩文学系谱。在这系谱的每一个点上,李浩几乎都有完善的思考等待着你。不熟知这个系谱,对李浩的阅读将是困难的,因为他早就声称,他的写作就是要面向那“无限的少数”。这些人要有差不多跟他齐平的阅读量,并跟他的系谱大略一致,这才能够领会他作品中的迷藏和博弈游戏,识别出他对系谱中文本的变形、衍生和沉默,并别有会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