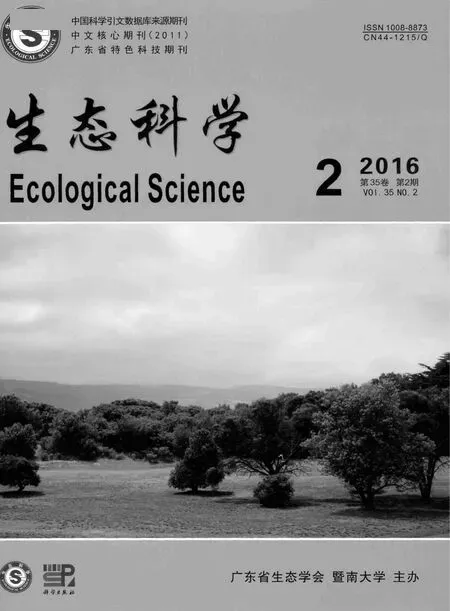土壤溶解性有机质生物降解研究进展
2016-06-05贾华丽郗敏孔范龙李悦乔婷
贾华丽, 郗敏, 孔范龙, 李悦, 乔婷
青岛大学化学化工与环境学院, 山东青岛 266071
土壤溶解性有机质生物降解研究进展
贾华丽, 郗敏*, 孔范龙, 李悦, 乔婷
青岛大学化学化工与环境学院, 山东青岛 266071
贾华丽, 郗敏, 孔范龙, 等. 土壤溶解性有机质生物降解研究进展[J]. 生态科学, 2016, 35(2): 183-188.
JIA Huali, XI Min, KONG Fanlon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biodegradation of soil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J]. Ecological Science, 2016, 35(2): 183-188.
溶解性有机质(DOM)是土壤有机质中最容易被微生物利用的一部分, 是土壤微生物代谢重要的物质和能量来源。DOM的生物降解反映了其稳定性及在物质、能量代谢中的作用, 对土壤的碳循环和大气的温室效应有重要影响。目前, 有关 DOM 生物降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降解过程的表征及其影响因素两大方面, 该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综述。表征指标可以归纳为降解率、降解速率、半衰期等矿化动力学指标和光谱指标两大类; 降解过程直接取决于 DOM分子大小、结构和微生物群落、数量和活性等直接影响因素, 而土层深度、土壤湿度、温度、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pH等间接因素通过影响DOM的组成结构及微生物的性质进而影响DOM的降解过程。在此基础上, 论文指出了目前国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溶解性有机质; 生物降解; 表征指标; 影响因素
1 前言
溶解性有机质(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OM)是由一系列大小、结构不同的分子组成的, 且能通过0.45 μm 微孔滤膜的, 能溶于水的有机物的总称[1],具体包括可溶性有机碳(DOC)、可溶性有机氮(DON)和可溶性有机磷(DOP)等。土壤DOM主要来源于新近凋落物和土壤腐殖质[2], 含量很低, 只有几个到几百个C mg/L, 占土壤总有机质的一小部分, 但却是土壤中最活跃的有机碳库。DOM的生物降解是指土壤微生物对有机化合物的利用[3], 可以减少可溶性有机物的淋失, 避免对地下水的污染[4]。降解过程还可减少土壤中 O2的含量并提供甲烷产生作用和反硝化作用需要的电子, 从而调节土壤温室气体CH4、N2O的产生[5]。此外, 研究DOM的生物降解对了解土壤养分的循环具有重要意义[6]。
为研究不同土壤条件下DOM的生物降解现象,国内外学者从降解过程和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归纳起来, 研究中主要涉及了生物降解过程的表征、降解过程的影响因素两大方面。本文就此对目前有关土壤DOM生物降解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旨在了解不同环境条件下DOM的生物降解机制。
2 DOM生物降解的表征
目前, 有关 DOM生物降解过程的研究主要包括其浓度的动态变化和组成结构的变化, 分别用矿化动力学指标和光谱指标来表征, 其中, 矿化动力学指标包括降解率、降解速率和半衰期等, 光谱指标则主要为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和腐殖化指数。
2.1 矿化动力学指标
矿化动力学指标主要包括降解率、降解速率和半衰期等, 主要用于量化降解过程中溶解性有机碳、氮的变化情况。
2.1.1 降解率和降解速率
DOC的降解率是指培养结束时减少的DOC量占初始 DOC的比率, 即易降解 DOC的百分含量;降解速率则用于描述降解的快慢。通常用双指数衰变模型[7]来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其表达式为:
剩余的溶解性有机碳(%)=(100–b)e–k1t+be–k2t其中,b为稳定DOC的百分含量(%), (100–b)为易降解的百分含量(%),k1为易降解DOC的矿化速率常数(d–1), k2为稳定DOC的矿化速率常数(d–1),t为时间(d)。
学者们对森林、农田等土壤中DOM生物降解所开展的研究中用其表征降解过程中 DOC的浓度变化, DON的降解也同样符合一个双指数的一次衰变模型[6]。研究中DOC、DON降解速率的一般规律为: 培养初期, 易降解部分优先降解, 降解速率较快,随着该组分的不断消耗, 降解速率逐渐减慢[3–4,6,8–10]。降解率则受土壤来源、性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不尽相同, Kiikkiä O 等[11–12]对落叶林和针叶林的研究表明, 森林枯落物层DOC的降解率为25%–32%, 腐殖质层为10%–20%; 而水稻土中DOC的降解率则为30%–70%不等[13–14]。
2.1.2 半衰期
半衰期是指不同组分的浓度经过生物降解反应降低到初始浓度的一半时所消耗的时间。根据DOC不同组分的半衰期不同可将其分为易降解(不稳定)DOC和难降解(稳定)DOC两部分。各组分半衰期的计算方法为[8]:

其中,k1为不稳定DOC的矿化速率常数(d–1),k2为稳定DOC的矿化速率常数(d–1)
Schwesig D[8]、汪景宽[6]、禹洪双[14]等人分别对不同森林、水稻土壤中DOC生物降解的半衰期进行了研究, 发现易降解DOC的半衰期都在1–2天, 而难降解DOC受其结构的影响, 半衰期在几十到几百天不等, 此规律同样适用于DON的降解情况[6]。
2.2 光谱指标
降解过程中, 光谱特征常被用于研究 DOM的组成结构, 其理论基础是不同有机物所含的基团对不同类型和长度的光波具有各自的吸收特性[15]。目前, 用于评价 DOM降解过程的光谱指标主要包括SUVA254, UV260, UV280, E240/E420, E465/E665, E250/E365和腐殖化指数。
280nm处DOM的紫外吸收值(UV280)和腐殖化指数(HIXem)被广泛用于评价DOM的结构复杂程度和分解特性, 一般认为, 值越高其中含有的芳香性化合物越多, 结构越复杂[16–17]。学者们[8, 13–14,]对不同区域 DOM 生物降解的研究指出, 培养过程中, UV280呈先上升, 达到最大值后又下降的趋势, 主要是由于培养前期易降解的组分优先被微生物利用,导致溶液中芳香性物质比例增加, 当易降解组分分解完成后, 芳环物质开始被微生物利用, 从而导致其比例下降。一般情况下, 培养结束时, DOM的腐殖化指数(HIXem)增加[4,15]也表明随着培养的进行,溶液中结构相对复杂的芳香性化合物和难降解组分比例增加。但是, 培养过程中, 高微生物活性可能会引起基质和营养的快速消耗, 导致部分微生物死亡,将容易降解的细胞成分释放到 DOM 溶液中[18], 也会改变UV280和HIXem变化趋势。
此外, 254 nm处的摩尔吸光度(254 nm吸光系数与DOC浓度值比)可示踪DOM的芳香性, 值越大表明有机物越难被分解和利用[19]; 240 nm与420 nm处吸光度的比值(E240/E420)可用来比较不同来源DOM 对紫外光和可见光吸收能力的相对关系[20–21]; 250 nm 与 365 nm处的吸光值之比(E250/E365) 可以较好地反映 DOM的分子状况, E250/E365 越大,则分子质量越小[22]; 260 nm 处的吸光度可表示DOM疏水组分的比例[23]; 465 nm和665 nm处的吸光度之比(E465/E665)可表征DOM的芳香性和腐殖化程度[24–25]。
3 影响因素
DOM 的生物降解主要包括其能否被生物降解(即生物可利用性)以及可被降解部分的降解程度。首先, 作为直接影响因素, DOM的组成结构决定着其生物可利用性; 微生物则主要影响 DOM的降解程度。其次, 土层深度、土壤湿度、温度、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pH等因素又共同作用, 在影响 DOM的组成结构和微生物的基础上间接影响DOM的生物降解。
3.1 直接影响因素
3.1.1 分子大小及结构
分子大小及其结构是影响DOM能否被生物降解的决定性因素, 也是决定 DOM生物降解能力的最本质因素。大部分学者认为, 分子量越小的DOM分子越容易被微生物吸收,优先降解[21,26,27]。例如, Kiikkilä O等[27]研究发现, 分子量<1000 Da的DOM比分子量处于1-10, 10-100及100kDa以上的DOM的降解性和生物可利用性高。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高分子量DOM组分中的多糖可以被细菌快速的矿化, 比低分子量的DOM更能支持微生物的生产[28]。
就 DOM 化学结构对其生物降解的影响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 蛋白质类和糖类物质都比较容易被生物降解, 并且能够在 DOM的降解过程中优先被微生物利用[29–31]; 而具有芳香性结构的腐殖质等的降解能力都很低[29,32–34]。Kalbitz K 等[34]发现, 从森林土壤提取的DOM的生物降解能力与芳香性结构的含量负相关。
3.1.2 微生物
在 DOM的生物降解过程中, 微生物是决定其降解程度的直接影响因素, 主要从数量、活性和种群结构等方面体现。研究表明, 微生物对不同化合物的降解不仅取决于DOM的化学结构, 还与微生物的种群特征有关[35], 而且微生物的影响更为重要[36],因为微生物只对其相应的DOM起作用。Schmerwitz J分别将来自于榉林、云杉林、泥炭地和农田土壤的DOM 溶液接种原位细菌混合液进行降解实验, 发现其生物降解的能力取决于实验所用微生物的类型和来源[18]。Young K C[36]的研究表明, 土著细菌最有利于 DOM的生物降解。此外, 微生物的数量越多,活性越高, 其代谢速率越快, 对DOM的降解速率则越快。
3.2 间接影响因素
3.2.1 土层深度
土层深度作为DOM生物降解的间接影响因素,主要通过影响DOM的含量及稳定性来影响其生物降解。部分学者认为, 土层越深, 降解能力越低[37–38],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深度的增加, 难降解化合物增加。孔范龙等[39]研究了三江平原典型环形湿地土壤DOC剖面分布及储量发现, DOC随土层深度增加而不断减小的原因是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 可供土壤微生物利用的有机质减少。也有学者认为, DOM的生物降解能力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增加[40]。Scott E E[40]通过对6种不同土壤DOM动态变化的研究得出了一个 DOM动态变化的模型: 新输入的高吸附疏水化合物可取代先前吸附的微生物降解副产品-富氮的弱亲水化合物, 这些亲水化合物迁移到深层土壤中, 导致土壤渗滤液的生物降解能力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因此, 以往各研究中关于DOM生物降解随土层深度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 可能是与土壤类型、含水量、温度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有待实验进一步研究证明。
3.2.2 土壤湿度
土壤湿度作为DOM生物降解的主要影响因子之一, 主要通过增加微生物的活性和数量来加快DOM的降解速率。首先, 土壤湿度适度提高, 微生物的活性增强, 研究表明, 土壤湿度在土壤饱和含水量的50%–80%时, 土壤微生物的代谢活动最大[41]。其次, 微生物的数量随土壤湿度的增加而增加, 王君等[42]的多重干湿交替实验结果表明溶解性有机碳在复水后有所减少, 主要是因为复水刺激了微生物的大量繁殖, 使得土壤中的溶解性有机碳短时间内被微生物分解矿化, 以便自身生长繁殖的需要。
3.2.3 温度
温度影响着DOM的组成结构和微生物的活性,不同温度条件下, DOM的生物可利用性和降解速率不同, 进而影响DOM的生物降解过程。Wang H 等[43]研究发现, 升温增加了 DOM 的腐殖化程度,导致其组分中芳香物质含量的增加, 生物可利用性降低, 与Li J[44]、Li M T[45]等的研究一致。von Lützow M[46]研究发现, 稳定碳库比不稳定碳库对温度敏感,因为稳定碳库的降解需要高的活化能。然而, 温度升高, 微生物的活性增强[47–50], 代谢速率加快, 进而加快了对DOM的利用速率, 导致DOM的降解速率加快。因此, 温度升高可增加芳香性物质的含量,抑制 DOM的生物可利用性; 而微生物的活性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从而加速其降解速率。
3.2.4 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
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是指耕作、种植制度和植被覆盖类型的变化, 能够改变土壤理化性质和DOM的来源, 进而影响微生物的活性和DOM的组成结构, 改变DOM的生物降解特性。首先, 土地利用方式不同程度增强了土壤的通透性和疏松程度,改善了微生物分解土壤有机质的环境, 尤其是微生物较易利用的溶解性有机碳[6]。其次,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DOM 的生物有效性不同。Guo Y D等[51]研究了长期复垦对三江平原溶解碳浓度和特征的影响指出, 湿地退化使得DOC腐殖化结构变简单, 生物有效性提高。此外, 植被覆盖的不同, 导致进入土壤的凋落物有所不同, 进而使来源于此的 DOM的生物降解率不同。王春阳等[15]对黄土高原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的生物降解率研究表明, 乔木类(60.8%)> 灌木类(58.6%)>草本类(49.7%)。
土地管理方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施肥, 即外源性营养物质的输入, 可改变DOM的组成结构, 影响其生物降解。禹洪双等[14]对长期不同施肥处理水稻土溶解性有机碳降解特性进行研究指出, 施化肥降低DOC降解率, 而配施秸秆、猪粪等有机肥则显著增加DOC的降解率, 可能是因为施化肥, 尤其施用N、P 养分, 促进了 C、N、P 的平衡周转, 降低了DOC 易降解组分; 而施有机肥显著增加土壤中易降解DOC 含量, 增加了DOC 的降解率。Liu M等[52]研究表明, 外源性 P 的加入使河岸湿地中 DOC的荧光光谱出现蓝移, 主要是由于P的加入使得DOC的分子量和芳香性减小, 生物可利用性增加。
3.2.5 pH
如同其他间接影响因素, pH主要通过影响微生物的数量、活性和DOM的结构进而影响DOM的生物降解, 随着pH的增加, 微生物的数量和活性增强, DOM的生物可利用性增加。研究表明[53], 首先, pH可以改变DOM中芳香性物质的含量, 如低pH可以增加DOM中多酚的含量, 降低其生物可利用性; 其次, 适度提高 pH可增加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和活性,进而加快微生物对DOM的利用速率, 例如, 增加土壤酸度将导致氮矿化作用和呼吸强度提高[2]。因此,适度提高pH有利于DOM的生物降解。
3.2.6 其他
除上述因素外, 土壤质地与结构、营养素、盐分, CO2浓度等都能够影响DOM的生物降解。研究表明, 过量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物影响微生物数量、活性和种群结构[54], 从而影响DOM的生物降解过程。CO2浓度升高可刺激溶解性碳水化合物的产生, 引起微生物生物量的增加,加速微生物对DOC 的吸收利用, 最终导致土壤 DOC 分解速度加快[55]。
4 存在问题和展望
(1)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土壤 DOM 生物降解开展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某一时期不同土壤中DOM生物降解方面, 对于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则较少, 而且在野外自然状态下, 其根本驱动因子并未可知, 因此, 今后的研究工作应该加强不同时期、不同土壤类型、不同土层深度、湿度等各因素对 DOM生物降解相互作用关系及机制的研究, 找出自然状态下影响DOM生物降解的主要因素。
(2)目前对 DOM 生物降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DOC的生物降解方面, 对DON、DOP的研究仅局限于国外少数学者开展的DON、DOP对DOC生物降解影响的研究, 而作为 DOM 的重要组成部分, DON、DOP对土壤N、P循环及DOC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应该加大对DON、DOP生物降解的研究力度。
(3)在全球温室效应的背景下, 土壤作为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溶解性有机质作为土壤微生物最容易利用的基质, 其含量变化与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密切相关,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DOC、DON浓度与温室气体的相关性方面, 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应该将 DOM的生物降解与温室气体的排放联系起来以加深土壤温室气体的产生机制和土壤DOM碳汇的研究。
(4)笔者在 DOM 生物降解的研究实验中发现,浸提土壤DOM的方法, 如: 浸提液、水土比、浸提时间, 接种液的制备、培养方法和接种后溶液的培养都会影响 DOM生物降解的结果, 但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研究方法, 因此应该加大实验力度, 确定统一的研究方法, 为 DOM生物降解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做准备。
[1] LIU Li, SONG Cunyi, YAN Zengguang, et al. Characterizing the release of different composi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soil under acid rain leaching using three-dimensional excitation–emission matrix spectroscopy[J]. Chemosphere, 2009, 77(1): 15–21.
[2] 刘微,王树涛. 土壤中溶解性有机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 土壤通报,2011,42(4):997–1002.
[3] XU Xingkai, LUO Xianbao, JIANG Songhua, et al. Biodegrada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in soil extracts and leachates from a temperate foreststand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ultraviolet absorbance [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12,57(8):912–920
[4] 高忠霞, 周建斌, 王祥,等. 不同培肥处理对土壤溶解性有机碳含量及特性的影响[J]. 土壤学报, 2010, 47 (1): 115–121.
[5] 周江敏, 陈华林, 代静玉. 溶解性有机质在土壤固碳中的意义[J]. 土壤通报, 2012, 42(6): 1508–1514.
[6] 汪景宽, 李丛, 于树等. 不同肥力棕壤溶解性有机碳、氮生物降解特性[J]. 生态学报, 2008, 28(12): 6165–6171.
[7] GREGORICH E G, BEARE M H, STOKLAS U, et al. Biodegradability of soluble organic matter in maizecropped soils[J]. Geoderma, 2003, 113(3): 237–252.
[8] SCHWESIG D, KALBITZ K, MATZNER E. Mineraliza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in mineral soil solution of two forest soils[J]. Journal of Plant Nutrition and Soil Science, 2003, 166(5): 585–593.
[9] HULATT C J, KAARTOKALLIO H, ASMALA E, et al. Bioavailability and radiocarbon age of fluvial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OM) from a northern peatland-dominated catchment: effect of land-use change[J]. Aquatic Sciences, 2014, 76(3) 393–404.
[10] SCHMIDT B H M, KALBITZ K, BRAUN S, et al. Microbial immobilization and mineraliza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nitrogen from forest floors[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11, 43(8): 1742–1745.
[11] KIIKKILA O, KITUNEN V, SMOLANDER A. Degradability of dissolved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nitrogen in relation to tree species[J]. FEMS Microbiology Ecology, 2005, 53(1): 33–40.
[12] KIIKKILA O, KITUNEN V, SMOLANDER A. Dissolved soil organic matter from surface organic horizons under birch and conifers: degradation in relation to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06, 38(4): 737–746.
[13] 焦坤, 李忠佩. 土壤溶解有机质的含量动态及转化特征的研究进展[J]. 土壤, 2006, 37(6): 593–601.
[14] 禹洪双, 刘勤, 陈武荣, 等. 长期不同施肥处理水稻土溶解性有机碳降解特性研究[J]. 土壤通报, 2013, 44(2): 338–342.
[15] 王春阳,周建斌,王祥,等. 黄土高原区不同植物凋落物可溶性有机碳的含量及生物降解特性[J]. 环境科学, 2011, 32(4): 1139–1145.
[16] 康根丽, 杨玉盛, 司友涛, 等. 马尾松与芒萁鲜叶及凋落物水溶性有机物的溶解特征和光谱学特征[J].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 2014, 22(4): 357–366.
[17] 吕茂奎,谢锦升,江淼华, 等. 米槠常绿阔叶次生林和杉木人工林穿透雨和树干径流可溶性有机质浓度和质量的比较[J]. 应用生态学报, 2014, 25(8): 2201–2208.
[18] MARSCHNER B, KALBITZ K. Controls of bioavailability and biodegradability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soils[J]. Geoderma, 2003, 113(3): 211–235.
[19] 雷秋霜,杨秀虹,方志文, 等. 森林新近凋落叶溶出 DOM的性质及其对菲增溶作用的影响[J]. 生态环境学报, 2014, 23(1): 170–177.
[20] 周焱, 傅丽娜, 阮宏华, 等. 武夷山不同海拔土壤水溶性有机物的紫外-可见光谱征[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32(4): 23–27
[21] 杨秀虹, 彭琳婧, 李适宇, 等. 红树植物凋落叶分解对土壤可溶性有机质的影响[J]. 生态环境学报, 2013, 22(6): 924–930.
[22] 谢理, 杨浩, 渠晓霞, 等. 滇池典型陆生和水生植物溶解性有机质组分的光谱分析[J]. 环境科学研究, 2013, 26(1): 72–79.
[23] DILLING J, KAISER K. Estimation of the hydrophobic frac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water samples using UV photometry[J]. Water Research, 2002, 36(20): 5037–5044.
[24] 李璐璐, 江韬, 闫金龙, 等. 三峡库区典型消落带土壤及沉积物中溶解性有机质 (DOM) 的紫外-可见光谱特征[J]. 环境科学, 2014, 35(3): 933–941.
[25] 闫金龙, 江韬, 赵秀兰, 等. 含生物质炭城市污泥堆肥中溶解性有机质的光谱特征[J]. 中国环境科学, 2014, 34(2): 459–465.
[26] AMADO A M, CONTNER J B, SUHETT A L, et al. Contrasting interactions mediate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ecomposition in tropical aquatic ecosystems[J]. AquaticMicrobial Ecology, 2007, 49(1): 25–34.
[27] KIIKKILA O, KITUNEN V, SMOLANDER A.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erived from Norway spruce litter divided into fractions according to molecular size[J]. 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Biology, 2012, 50(1): 109–111.
[28] 蔡明红, 肖宜华, 王峰, 等. 北极孔斯峡湾表层沉积物中溶解有机质的来源与转化历史 [J]. 海洋学报, 2012, 34(6): 102–113.
[29] FELLMAN J B, AMORE D V, HOOD E, et al. Fluoresc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biodegradability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forest and wetland soils from coastal temperate watersheds in southeast Alaska[J]. Biogeochemistry, 2008, 88(2): 169–184.
[30] 郭瑞, 陈同斌, 张悦, 等. 不同污泥处理与处置工艺的碳排放[J]. 环境科学学报, 2011, 31(4): 673–679.
[31] 王定美, 王跃强, 袁浩然, 等. 水热炭化制备污泥生物炭的碳固定[J]. 化工学报, 2013, 64(7): 2625–2632.
[32] 吴丰昌, 王立英, 黎文. 天然有机质及其在地表环境中的重要性[J]. 湖泊科学, 2008, 20(1): 1–12.
[33] 郭卫东, 黄建平, 洪华生, 等. 河口区溶解有机物三维荧光光谱的平行因子分析及其示踪特性[J]. 环境科学,2010, 31(6): 1419–1427.
[34] KALBITZ K, SCHWESIG D, SCHMERWITZ J, et al. Changes in properties of soil-derived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duced by biodegradation[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03, 35(8): 1129–1142.
[35] LEFF L G, MEYER J L. Biological availability of dissolve d organic carbon along the Ogeechee River[J]. Limnology a nd Oceanography, 1991, 36(2): 315–323.
[36] YOUNG K C, DOCHERTY K M, MAURICE P A, et al. Degradation of surface-water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fluences of DOM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icrobial populations[J]. Hydrobiologia, 2005, 539(1): 1–11.
[37] SANDERMAN J, BALDOCK J A, AMUNDSON R.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chemistry and dynamics in contrasting forest and grassland soils[J]. Biogeochemistry, 2008, 89(2): 181-198.
[38] KAISER K, KALBITZ K. Cycling downwards–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soils[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12, 52(4): 29–32.
[39] 孔范龙, 郗敏, 李悦, 等. 三江平原典型环型湿地土壤DOC剖面分布及储量[J]. 水土保持通报, 2013, 33(5): 176–179.
[40] SCOTT E E, ROTHSTEIN D E. The dynamic exchange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percolating through six diverse soils[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14, 69(10): 83–92.
[41] 魏书精, 罗碧珍, 孙龙, 等. 森林生态系统土壤呼吸时空异质性及影响因子研究进展[J]. 生态环境学报, 2013, 22(4): 689–704.
[42] 王君, 宋新山, 王苑. 多重干湿交替对土壤有机碳矿化的影响[J].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3, 36(11): 31–35.
[43] WANG Hang, HOLDEN J, ZHANG Zhijian, et al. Concentration dynamics and biodegradability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wetland soils subjected to experimental warming[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4, 470(10): 907–916.
[44] LI Jianwei, ZIEGLER S, LANE C S, et al. Warming‐ enhanced preferential microbial mineralization of humified boreal forest soil organic matter: Interpretation of soil profiles along a climate transect using laboratory incubations[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Biogeosciences, 2012, 117(G2): 502–504
[45] LI Mingtang, ZHAO Lanpo, ZHANG Jinjing. Effect of temperature, pH and salt on fluorescent quality of water extractable organic matter in black soil[J].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3, 12(7): 1251–1257.
[46] VON LUTZOW M, KOGEL-KNABNER I.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of soil organic matter decomposition—what do we know?[J]. Biology and Fertility of Soils, 2009, 46(1): 1–15.
[47] 高会议, 郭胜利, 刘文兆, 等. 黄土旱塬区冬小麦不同施肥处理的土壤呼吸及土壤碳动态[J]. 生态学报, 2009, 29(5): 2551–2559.
[48] 孔范龙, 郗敏, 吕宪国, 等. 三江平原环型湿地土壤溶解性有机碳的时空变化特征[J]. 土壤学报, 2013, 50(4): 847–852.
[49] 范月君, 侯向阳, 石红霄, 等.气候变暖对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J]. 草业学报, 2012, 21(3): 294–302.
[50] 王玲玲, 孙志高, 牟晓杰, 等. 黄河口滨岸潮滩湿地CO2、CH4和N2O通量特征初步研究[J]. 草业学报, 2011, 20(3): 51–61.
[51] GUO Y D, Lu Y Z, Song Y Y, et al. Concentr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ssolved carbon in the Sanjiang Plain influenced by long-term land reclamation from marsh[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4, 466(1): 777–787.
[52] Liu Meng, Zhang Zhijian, He Qiang, et al. Exogenous phosphorus inputs alter complexity of soil-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in agricultural riparian wetlands[J]. Chemosphere, 2014, 95(1): 572–580.
[53] KEMMITT S J, WRIGHT D, GOULDING K W T, et al. pH regulation of carbon and nitrogen dynamics in two agricultural soils[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06, 38(5): 898–911.
[54] DAI J, BECQUER T, ROUILLER J H, et al. Influence of heavy metals on C and N mineralisation and microbial biomass in Zn-, Pb-, Cu-, and Cd-contaminated soils[J]. Applied Soil Ecology, 2004, 25(2): 99–109.
[55] 李摇玲, 仇少君, 刘京涛. 土壤溶解性有机碳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中的作用[J]. 应用生态学报, 2012, 23(5): 1407–1414.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biodegradation of soil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JIA Huali, XI Min*, KONG Fanlong, LI Yue, QIAO Ting
College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266071,China
DOM as one of the most readily used parts of the soil organic matter is the important material and energy sources for soil microbial metabolism. The biodegradation of DOM reflects its stability and the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metabolism of material and energy,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carbon cycle in soil and greenhouse effect in the atmosphere. Present research on biodegradation of DOM mainly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degradation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Herein, we summarize these two aspects in this paper. The indicators can be conclu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spectral index and mineralization kinetics index, including the rate of degradation, degradation rate and half-life of DOM. The degradation process depends directly on the molecular size and chemical structure of DOM and the community, number and activity of microbe. Meanwhile, the process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depth of soil, soil moisture, temperature, pH, land use and management manner. Given this, we propose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study after summing up the shortcomings of relevant studies.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biodegradation; indicators; influence factors
10.14108/j.cnki.1008-8873.2016.02.027
X144
A
1008-8873(2016)02-183-06
2015-04-21;
2015-06-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101080);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ZR2014DQ028, ZR2015DM004);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技计划资助项目(J12LC04)
贾华丽(1990—), 女, 山东潍坊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湿地变化与环境效应研究, E-mail: 1437960348@qq.com
*通信作者:郗敏, 女,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湿地变化与环境效应研究, E-mail: ximin200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