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馆:历史缘起、命名定位与文化精神
2016-05-31林早
林 早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中国美术馆:历史缘起、命名定位与文化精神
林早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现代意义上的美术馆,尤其是国家美术馆,除了标榜美术馆空间的公共性之外,亦自觉地承担着国家民族文化形象的表征功能。论文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美术馆历史缘起、命名定位、文化精神三个方面的考察,揭示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美术馆的文化定位是如何实现的,其文化形象是如何被塑造的。
关键词:中国美术馆;十大建筑;罗浮;民族形式
若从清末状元张謇1905年于家乡自费筹办的“南通博物苑”算起,中国美术馆的历史已逾百年。严格说起来,美术馆观念并不是从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培育起来的。虽然我们可以举出周代的“春官之职,掌祖庙之收藏”,《春秋·桓公二年》记载的“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汉武帝时的“创置秘阁,以聚图书”,宋徽宗时的《宣和画谱》、《宣和书谱》,清乾隆时的《石渠宝籍》等来说明中国自古代就不缺乏“收藏”的观念。但这正如我们用中国古代文化观念去附和现代文化体系的其他举动一样,这种文化自觉的努力往往只能提供一种“联系”的存在,而产生不了血脉相连的效果。究其原因,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与中国近代所遭遇的西方现代文化体系本就是两种差异很大的文化体系——事实上,“体系”观念,也是西方的。因此,18世纪末,当公共美术馆出现在西方世界并开始标榜政治和美学的胜利时,对中国来说,“美术馆”根本不构成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美术馆与其他许多现代事物一样,它在中国的产生实质上对应着一个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过程。这个“中国化”过程是如此复杂和微妙,联系一下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学”在中国的现代性历程——学界至今仍存在对“美学”学科合法性的置疑声音,我们就不难想像和理解“美术馆”在中国所经历的不断寻求自身定位的过程。在中国,美术馆与博物馆是隶属于两个部门的泾渭分明的文化机构,在推广上两者之间缺少直接的联系、沟通,以至于国内的美术馆事业发展在性质上和经营上遭遇了不小的尴尬。并且,囿于收藏和陈列功能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的美术馆与博物馆还有一个不符合文化逻辑的区分:据此,美术馆主要承担现代艺术品的收藏、陈列、展览、研究工作,而古代艺术品的收藏、陈列、展览、研究则主要是博物馆的工作。比较而言,在西方,Museum这个词既指代博物馆,又指代美术馆,两者之间的区别相对模糊,许多时候视乎具体语境而定。
从文化形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美术馆,尤其是国家美术馆,除了标榜美术馆空间的公共性之外,亦自觉地承担着国家民族文化形象的表征功能。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美术馆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个国庆献礼建筑工程背景下。在特定历史时期复杂而微妙的“中国化”空间中,中国美术馆是怎样定位自身的?其诞生的过程是怎样的?其在创建之初蕴含着怎样的文化精神诉求?于此,我们将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中国美术馆”历史缘起、命名定位、文化精神三个方面的分析来回应上述思考。
一、中国美术馆:历史缘起
一个建筑物的诞生,尤其是一个文献式建筑物(Documentary Architecture)的诞生,往往是由多种决定因素促成的,体现着彼时彼处人们所关注的事物的全部——“从它的外形到内涵,都是一个个被摊开的文本,上面书写着这个国家及城市的记忆、伤痕、想像、遗留的智慧和愚蠢,以及愿景等。”[1]打开中国美术馆建筑这个“文献”,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庆建筑献礼——1950年代“十大建筑”。
“每一座建筑物都是一项建筑任务书的产物,而任务书是根据主持建设的国家和个人的经济条件来制定的。同时也是根据其一般的生活方式、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伴随的风俗习惯来制定的。”[2]中国美术馆,首先是一项政治建筑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国庆工程的产物,这项建筑任务最后具体落实为北京1950年代十大工程,俗称“十大建筑”。
北京1950年代十大建筑,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58年9月5日,中央确定了国庆工程的建设任务。次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召集了京城内外千余名建筑工作者开会并作了关于国庆工程的动员报告。当时的国庆工程计划包括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国家剧院等十几个较大规模的建筑工程,绝大部分的工程都于同年10月下旬开工。1959年10月,其中的十个重点建筑工程——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钓鱼台国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和华侨大厦建成完工。“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建设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智力、财力无与伦比;建筑技术之复杂、施工之艰巨以及所遇到的难题无以复加……‘十大建筑’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由于它的政治意义,设计和施工都是精心进行,利用了被视为禁忌的‘三边’工作法(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和人海战术,终于使之如期完成,这本身就是一个壮举,将一种意志化为共和国10年的纪念碑……由于集中全国的设计和施工精英,出现了在当时条件下最稳健、最优秀的建筑高峰,‘十大建筑’的设计、施工和建筑内容都是当时最高水准。”[3]从建筑工程角度上看,这项建筑规模大小与建筑时间长短成反比并且不乏建筑精品的国庆献礼建筑工程,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可以毫无疑议地被称作“壮举”乃至“奇迹”。
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跃进的产儿》盛赞了“十大建筑”。现在看来,作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壮举”乃至“奇迹”的1950年代十大建筑,与1958年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确实存在着精神气质上的直接联系。虽然大跃进运动那种无节制的英雄主义在中国现代史上饱受诟病,但客观上看,1950年代国庆工程这样的建筑“壮举”也只有在那个全民都处于一种高度亢奋状态,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豪迈的呼风唤雨的情怀和无私的奉献精神,集体意志高度集中的时代背景下才可能成为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1950年代十大建筑无疑是激荡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串凝固的英雄主义旋律最强音。我国的著名建筑设计师,北京1980年代十大建筑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主要设计者柴裴义先生曾经充满感情地谈起北京1950年代十大建筑——“1959年时我还是一名中学生,恰巧有机会到了北京。当我在天安门广场上亲身感受到建筑的宏伟壮观时,也油然而生地产生了一种愿望,当一名建筑师是何等伟大与光荣。可以说1950年代十大工程是我认识建筑并使我为之奋斗一生的启蒙。”[4]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北京人文旅游的介绍中,中国美术馆往往被误当作1950年代“十大建筑”之一。联系到中国美术馆的整个建筑过程以及其建筑功用、建筑风格,发生这样的误会倒也是合理的。客观上,虽然最后落实的1950年代“十大建筑”名单中并不包括中国美术馆,但作为一个一开始便被纳入国庆工程并与“十大建筑”几乎同时动工的建筑项目,中国美术馆在事实层面上确与1950年代“十大建筑”血脉相连。因此,要考察中国美术馆这一建筑实体,将它纳入整个建国十周年国庆工程建筑系统中就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
1958年11月20日是中国美术馆建筑正式动工的日子,当时由于工期紧迫,破土时所选用的是尚未得到周恩来总理批准的清华大学建筑系设计方案。如果当时这个方案得到顺利实施,那么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美术馆将是一个建筑造型为长方型的更具现代感但缺少民族形式的建筑。动工不久,周恩来总理批示,中国美术馆设计要遵循国庆工程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基本设计原则,并特别强调了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特点。时任建筑工程部设计院总工程师、设计并主持中南海改造工程的戴念慈被指定接手中国美术馆的建筑设计工作。这样一来,中国美术馆建筑进一步的施工还来不及展开就必须进行地基回填。如此一挖一填,再加上1959年年初由于建筑高潮导致的钢筋、木材等建筑材料的紧缺和居民建筑的吃紧,中央决定推迟中国美术馆等建筑的施工建设,集中财力、人力、物力于天安门周围的重点工程,同时保证居民建筑问题的解决。因此,1959年2月底,中国美术馆工地进入停工状态,失去了成为建国十周年国庆献礼的机会。国庆之后,由于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对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国庆竣工工程的剩余物资和款项集中到了中国美术馆的建筑工程之中,中国美术馆建筑建设才得以为继。1960年下半年,中国美术馆恢复施工。1962年3月底,一个具有民族风格,气质沉静的中国美术馆显现于北京五四大街。在那个轰轰烈烈搞建设的时代里,这个总面积为17051平方米的国家美术馆从破土、停工到复工、建成,其间经历了4年时间,不可谓不波折。从建筑立项、建筑构想、建筑施工等一系列建筑历程看,中国美术馆工程始终夹裹在五十年代“十大建筑”之中,是国庆工程建筑时期典型的“三边”工作法的产物。[5]
1950年代“十大建筑”作为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具有非常浓烈的政治意义。其产生于建国十周年之际,响应的是完成了“三大改造”之后开始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新中国对自身成熟丰满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形象的迫切需要。因此,十大建筑的建筑功用与其文化象征都牢牢地扣紧了新中国国家意识的主题:人民大会堂对应着国家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个建筑内包含了新旧中国历史两个主题,不仅是承接,同时也是山河换色的对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专馆强调了新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斗争史;北京工人体育馆作为现代国家必备的文体制度体现,在命名上肯定了国家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北京农业展览馆是对中国农业国家地位的肯定和对农民阶级的重视;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对应着国家的民族团结政策;迎宾馆、华侨大厦对应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北京火车站是为共和国公民提供方便的现代交通民用公共设施。我们看到,十大建筑所象征的各种力量和政策,几乎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宪法总纲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甚至是重要的位置。总的来看,整个国庆工程突出了一个摧毁旧社会制度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及广大侨胞和外国友人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可以这样说,1950年代国庆十大工程这些极具政治文化象征意义的建筑物是中国领导人在建国十周年之际发表于新中国国家首都空间的一篇国家意识形态宣言。而中国美术馆的建筑立项也是为塑造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形象服务的,并且它的建立正是为了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形象更加丰满和生动。中国美术馆在当时的建筑停工是中央面对物资紧缺现实进行重点项目选择的结果——既然艺术和艺术家从来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力量,因此当国庆工程面临时间和物资的巨大压力时,放弃中国美术馆建筑工程就成为必然。
二、中国美术馆:命名定位
根据刘曦林对1960年至1966年美术馆旧档案的整理发现,“中国美术馆”馆名的最终确立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
据刘曦林的考证——“大约在1960年第一季度产生的《美术馆建馆方针任务(草案初稿)》中记存了这个方案:一、定名:本馆定名为‘中国美术馆’,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直属事业单位……同年稍晚些产生的《美术馆建馆方针任务(草案)》中说:一、定名:本馆定名为:‘现代美术馆’,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直属事业单位……也许这两个方案都一齐上报文化部,而文化部的批复是“中国美术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60)文厅夏字第683号文件《函复关于美术馆建馆中的一些问题》中说:3.关于美术馆的名称,我部意见:定名为“中国美术馆”较为恰当。此文署‘1960年5月31日’,距1963年6月毛泽东题写馆名时隔3年。其中“夏字”之“夏”指文化部副部长夏衍。”[6]
此外,对于“中国美术馆”馆名的确定还有一个说法——据说是毛泽东在为美术馆题写扁额时,大笔一挥把“中央美术展览馆”改为“中国美术馆”。[7]如果这个突出领袖形象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中国美术馆的馆名确定就经历了一个“中国美术馆”——“现代美术馆”——“中央美术展览馆”——“中国美术馆”的过程。
“这定名的反复所深含的学问是对美术馆性质的探索——对于它的国家性质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对于它的‘现代’性质是有分歧的。如果确有把‘中央美术展览馆’改为‘中国美术馆’之说,则是由展览馆性质向美术博物馆性质的升华。”[6]
的确,作为一个国家美术馆的中国美术馆,在定位上它的国家公共空间性质应该是最没有争议的。但既是如此,为何在定名中间又引入其他的定名方案呢?比较一下其他两个定名——“现代美术馆”和“中央美术展览馆”。“现代”一词界定的是美术馆的时代性,同时也包含了对美术馆收藏、陈列、展览的艺术品在年代上的界定;“中央”一词对应了国家执政党,是从政治上进一步确定了“国家性质”,“展览”一词将收藏、陈列的博物馆功能排除在外,确定并缩小了美术馆的功能。进一步说,“现代美术馆”这个命名的优点在于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但它没有体现出美术馆的“国家性质”,并且这个命名与中国美术馆的建筑风格也不太协调。而“中央美术展览馆”这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名称则从命名上限定并缩小了美术馆的文化意义和功能发展,无疑是三个名称中最不可取的一个。相较而言,还是“中国美术馆”这个命名最能满足“国家公共空间”的功能发展的需要。
在中国美术馆建馆之前,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可以借鉴的建馆、办馆经验。所以建馆之初,对于中国美术馆的定名、定位出现了一种颇为反复和混乱的情况是很自然的事。
“在另一份定馆名为‘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美术馆建馆方针任务草案(初稿)》中,对‘方针任务’作如下表述:本馆系中国美术作品的专业陈列馆,以征集、收藏、研究、陈列、展览我国历代的、特别是五四以来专业的、群众的和少数民族的美术家、民间美术家优秀的美术作品为主……在前述定馆名为‘现代美术馆’的《美术馆建馆方针任务(草案)》中,对‘方针任务’则作出不尽相同的表述:本馆以征集、收藏、陈列、展览我国自‘五四’以来专业的、群众的和少数民族的美术家优秀的美术作品为主要任务。”[6]
从草案中可以看到,“征集、收藏、研究、陈列、展览我国历代的、特别是以五四以来……美术作品”是与“中国美术馆”命名相对应,而“征集、收藏、陈列、展览我国自‘五四’以来……美术作品”则是与“现代美术馆”命名相对应。从逻辑上看,这种对应无疑是合理的。然而,面对古代艺术品收藏缺乏的尴尬和响应时代精神风貌的需要,中国美术馆最终还是在“国家公共性质”之上加上了时代的限定,成为一个以征集、收藏、陈列、展览我国自“五四”以来优秀艺术品的国家现代美术馆。但是与“国家性质”定位不同,“现代性”的定位背景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拥有历代优秀艺术藏品当然是国家美术馆的一种理想状态,但当时的中国先是经历了外辱,后又遭逢内乱,在这种状况下要想完善历代艺术品的收藏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对于当时正陶醉于红色江山的中国来说,具有强烈革命色彩和颠覆意义的“五四”以来的历史更适宜从艺术形象上为我们带来政治和美学的双赢。
当然,仅仅从“国家性质”和“现代性”来对中国美术馆定位只是确定了美术馆的国家地位和藏品的收集、研究范围。客观上看,这还算不上是从美术馆本位出发进行的定位。从美术馆本位出发进行定位,首先要说明的就是美术馆究竟是什么。尤其是在一个几乎谈不上博物馆历史、美术馆历史的国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家性质”和“现代性”的优先明晰,正好印证了公共美术馆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文化价值——“一般而言,公立美术馆成立的背后,可以察觉时代变迁的文化政策导向。”[8]中国美术馆建馆过程所显示出来的凌驾于美术馆本位之上的国家本位意识,并不是世界美术馆历史的特例。日本早期的美术馆建设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早期,想要盖美术馆的,特别是战前想要藉建设近代化机构以迎头赶上西洋先进国家的中央政府,战后则是担负了推动文化建设业务的地方政府,其实并不知道经营一座美术馆,除了盖好硬体建筑之外还需要什么。”[9]既然美术馆主要是应国家彰显国力、健全现代文化机构的需要而生,那么国家本位优先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
但客观上来说,中国美术馆的国家性质、现代性质的确定只是明确了美术馆在国家中的文化任务——用艺术品的收藏、展示、研究传播国家公共文化意识。至于这个文化任务究竟应该怎样去执行,却有赖于从美术馆本位出发对美术馆自身的认识。从美术馆的实践出发,这个定位的焦点集中到了以展览为主的展览馆性质和以陈列为主的博物馆性质上。客观上来说,一个不能提供常设陈列展的国家美术馆是难以实现美术馆将国家公共文化财富向公众进行展示并藉此强化现代国家意识的文化意义。因此,从文化理想上看,美术馆的博物馆性质是毫无争议的。但由于受文革等客观因素的干扰,对美术馆博物馆性质的定性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最终确立。
“1982年8月14日馆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国美术馆的方针任务的报告》,11月16日报艺术局转呈部党组,1983年1月26日文化部批复同意。报告说:中国美术馆自1963年建成投入使用后,确定为国家美术馆,属博物馆性质。故宫博物院收藏、陈列、展览古代美术品。中国美术馆收藏、陈列、展览近现代美术作品。……任务应是:1.收藏、保管、研究我国近现代优秀美术作品(重点放在‘五四’以后)。2.按年代顺序长期陈列近现代优秀美术作品及一些专题美术作品展览……3.进行国内外美术学术交流活动……4.代管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的筹备和征集工作。”[6]
1986年,美术馆的博物馆性质被写进国家条例,这标志着美术馆定位在中国的基本完成——“美术馆是造型艺术的博物馆,是具有收藏美术精品、向群众进行审美教育、组织学术研究、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等多职能的国家美术事业机构。”(《美术馆工作暂行条例》第一章第二条)[10]
至此,中国美术馆的中国国家现代美术博物馆定位得到确立。
三、中国美术馆:文化精神
(一)美术馆的“罗浮”情结
中国美术馆第一任馆长刘开渠为中国美术馆制定的第一条办馆方针是这样的:“中国美术馆不等同于美术展览馆,它的前景应该像法国卢弗尔(罗浮宫)那样的规模”。[6]
事实上,以法国罗浮宫为美术馆的理想原型早在20世纪初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的普遍诉求。稍微留意一下国内对国家美术馆的相关报道,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人的美术馆修辞中,“罗浮”基本上成为了公共美术馆的代名词。这当然与罗浮宫在世界美术馆界的地位分不开。
1793年,自罗浮宫以公共美术馆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它就始终牢牢占据着“世界第一”公共美术馆的地位。这个“第一”既是表明罗浮宫近代史上第一个公共美术馆的地位,也表明罗浮宫以其藏品之丰富、经典成为了后世美术馆意欲仿制和超越的经典模版。①事实上,美国的大都会美术馆和华盛顿国家画廊从规模和藏品数量上已经对罗浮宫“第一”的地位构成了威胁。但从文化渊源上,罗浮宫世界“第一”美术馆的位置仍然是难以动摇的。“罗浮宫是公共美术馆的原型。它最先提出其他国家所仿效的民事仪事。同时也是藉由罗浮宫使得美术馆成为政治上有美德政体的符码。在十九世纪末期,每一个西方国家都有至少一个值得夸耀的公共美术馆。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博物馆的普遍性甚至外溢到了第三世界……”[11]43另外有一点值得特别强调的就是罗浮宫从皇宫到公共美术馆的转型意义——“在一七九三年时的革命政府,抓住了一个戏剧化、一个新共和政体创造的机会,因而将国王收藏的艺术品充公,并将罗浮宫宣布成为一个公共的美术馆……它因此成为一个旧统治结束、新秩序开始的生动象征。革命时给予旧王朝的新意义,是以文字铭刻在由路易十四于十七世纪时所建设的一个贵族艺廊和接待室的阿波罗画廊(Apollo Gallery)。在入口上方是一个革命的布告,宣示一个法兰西博物馆的问世、以及在八月十日开幕以纪念‘暴君崩解的周年纪念日’”。[11]45
集宏大规模与丰富的美学、政治意义为一身的罗浮宫无疑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国家美术馆范本。但如果完全参照作为公共美术馆的罗浮宫的背景和规模,我们似乎有更充分的理由举出“故宫”,而不是新建的一处美术馆建筑作为中国自己的罗浮。事实上,1925年10月10日故宫作为“故宫博物院”对中国广大民众开放这一事件,从国家意识上讲,与罗浮宫的转型是极其相似的。并且,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善的皇家宫殿之一的故宫从建筑规模上讲甚至比罗浮更为气派,但为什么它不能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罗浮”呢?即使是在故宫大量经典藏品并未外流的国民政府时代,国民政府也并未完全采用罗浮宫的陈列、展览机制(故宫博物馆开放了古物、图书、文献等专门展示室),而是在1936年于南京新建、成立了具有公共美术馆意义的“国民美术陈列馆”,陈列、展览包括古代中国书画、现代中国书画、西画、雕塑、金石、陶瓷、铜器、摄影、建筑图形、古代善本图书等。
故宫为什么不能作为中国的“罗浮”?或者说中国为什么陷入一种既需要“罗浮”的建制模式,又拒绝“罗浮”的历史背景的矛盾心态中呢?这需要从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化历程中去寻找答案。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结束了自己的轴心时代,在外力的作用下进入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史。中国文化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大冲击,甚至大分裂。告别轴心时代意味着中国面临了一套新的世界文化结构,而这套文化结构是由西方世界打造的。面对挑战,如何生存?如何应战?张法在“中华性:中国现代性历程的文化解释”一文中给出了两个关键词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在文化转型中的窘境和姿态——“中心化情结”和“赶超”。
“古代中国给予中国现代性历程最大影响的是什么?答曰:中心化情结……中国从此把自己编织进世界历史之中,不是固守中国世界的中心,而是在新的世界中以新的先进/落后,中心/边缘的标准去‘重返中心’。也就是按以西方文化为主流,并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进化阶梯的世界史去进行艰苦的争取民族自强的从落后到先进的斗争……”[12]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对于罗浮的建制模式的需要实是基于以“进步”的西方文化建制为参照系进行中国民族现代文化建制的民族自强心理。这种民族自强心理可以从鲁迅、蔡元培、林风眠、徐悲鸿等文化先贤对于国内美术馆建设的呼吁奔走中得到强有力的见证。林风眠在《美术馆的功用》一文中特别鲜明地表达到:“尽管你们有五千年历史,尽管你们有成千累万足以说明那悠久历史的美术品,但那些东西都在哪里呢……如果在中国的各大都市都有着好的美术馆,使那些以各种目的来到中国的人们毫不费力地看到了我们数千年文化的结晶,毫不费力地看到了我们的历史的表现,谁不相信对于我国的荣誉是有绝大帮助的?”[13]
“从1840年到1894年,中国花了半个世纪多的时间去维护旧的中国世界中的虚幻的中心地位……现在中国决定弃旧图新,必须在一个世界中国图景中去重获生存与光荣……由中心化情结而来的赶超心态,激发出了世界上最伟大最悲壮的雄心,同时也带来了很值得深思的急躁和偏执。”[12]中国的中心化情结催化了中国人的赶超心态,而挟带着强烈中心意识的赶超心态催生了一种因渴望新生而全面否定旧我的文化行动,这即是由中国知识分子发动的否定传统文化的五四运动。了解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待传统文化的这种否定姿态,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对“罗浮”建制背景的拒绝。拒绝故宫成为国家美术馆(国家博物馆),体现的是一种与旧秩序、旧文化彻底决裂,建立新秩序、新文化的文化心态。这同时也尝试解释了为什么故宫博物院从开院以来一直不重视藏品的陈列、展览,因为传统美术工艺品在旧经典文化空间的陈列、展览提供的是一种传统文化经典的体验文本,借着陈列、展览的“仪式感”容易诱发受众的膜拜心理,这是为中国的现代性体验和现代国家体制所不容的。而传统美术工艺品在新的美术馆建筑内的陈列、展览,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去语境的展览,这种去语境本身就是赤裸裸的现代性暗示。
中国现代性历程的文化心理决定了中国人理想中的美术馆——理想上,中国的美术馆一方面应该具备“罗浮”的建制模式,另一方面又必须抽掉“罗浮”的历史背景。这种矛盾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美术馆民族形式的美学呈现中亦可得到印证。
(二)民族形式的审美理想
前面提到,中国美术馆建筑过程颇为波折,一个1.7万平方米的建筑从破土动工到建筑完工共经历了四年的时间,是典型的“三边”工作法的产物。中国美术馆之所以没有赶上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其中一个原因(非主要原因)就是受“三边”工作法所累,在建筑方案没有获批之前就匆匆上马,导致地基回填,贻误了时机。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1955年中央已经展开了全国范围内对“大屋顶”的批判,何以拟作为国庆十周年工程的中国美术馆建筑方案要由一个颇具现代感的长方型盒子最后改为带上“大屋顶”的设计方案呢?并且,“大屋顶”建筑形式还被运用到了最终成为国庆献礼工程的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北京火车站等建筑中。
我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北京火车站和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者杨廷宝在1959年的“建筑艺术座谈会”上谈到:“有人说美术馆在批判大屋顶的复古主义后,为什么又运用了这样浓厚的传统手法……我觉得这个美术馆完全可以运用较浓厚的传统手法,当然这也并不是唯一的手法,还可能有许多别的手法处理,但在当时这个处理手法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当我们还没有找到第二个更好的办法之前,它是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喜爱的。”[14]乍一看,杨廷宝关于在建筑上采用“大屋顶”的相关陈述似乎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当然这也并不是唯一的手法,还可能有许多别的手法处理”。事实上在“大屋顶”饱受批判的背景下,能够用“许多别的手法处理”从逻辑上讲自然是当时建筑设计师们的理想出路。但关键就在于从现实上看“当我们还没有找到第二个更好的办法之前,它是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喜爱的。”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集体意志高度统一的中国,在“大屋顶”饱受批判的背景下,这种建筑形式如何能够出现在共和国国庆献礼的工程建筑设计中?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对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和追求。
中国建筑对自身民族形式的追求,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族固有形式浪潮”开始(代表建筑有上海市政府办公楼、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等),在五十年代初由于“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口号的提出达到了一个高峰。“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这个口号来自苏联。1950年,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在中国推广苏联当时的建筑理论“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1953年初,中国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随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专门到苏联考查了城市建设,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塔什干、新西比等城市,接触了苏联建筑科学院院长莫尔德维诺夫等四十多位建筑界、美术界、哲学界的权威人士。统一追求一种民族形式建筑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市建设得到梁思成的认同和欣赏。回国之后,梁思成撰文大力宣传苏联经验和“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建筑理论,甚至还绘制出了两张中国建筑想象图(图1、图2)——“这两张想像图,一张是一个较小的十字小广场,另一张是一座约三十五层的高楼。在这两张图中,我只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无论房屋大小,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第二,民族形式的取得首先在建筑群和建筑物的总轮廓,其次在墙面和门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韵律,花纹装饰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15]一直以来,梁思成都被当作“大屋顶”的始作俑者,客观上梁思成确实为“大屋顶”建筑提供了权威的理论指导及可行性论证。参看梁思成绘制的中国建筑想像图,再联想一下我们见到的一些“大屋顶”建筑(如图3、图4),不难理解何以梁思成会与中国建筑史上“大屋顶”公案难分难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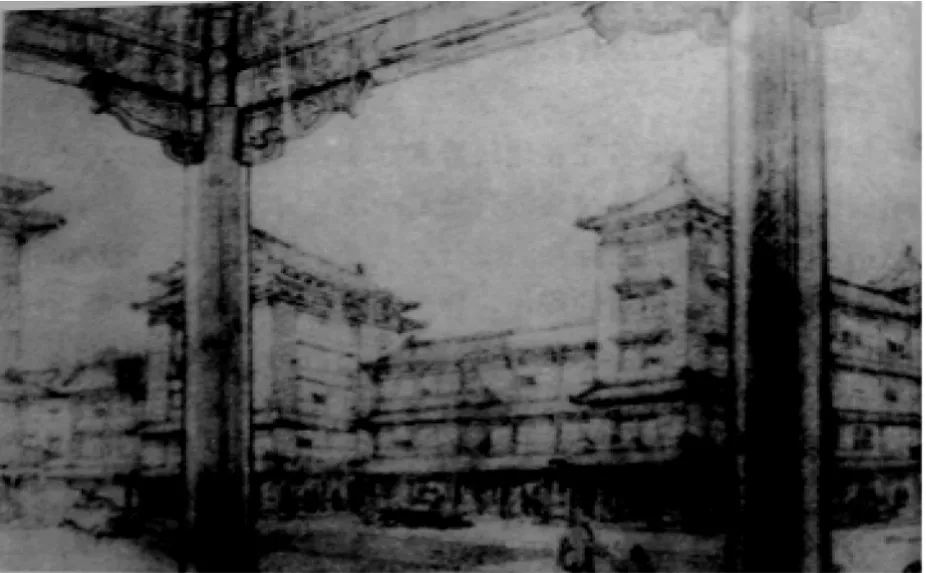
图1 梁思成:未来民族形式建筑的想像图之一

图2 梁思成:未来民族形式建筑的想像图之二

图3 中国美术馆

图4 民族文化宫
其实认真考察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并不简单等于“大屋顶”。“屋顶”只是梁思成所概括的中国建筑九特征之一——“屋顶在中国建筑中素来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的瓦面是弯曲的,已如上面所说……它的壮丽的装饰性也很早就被发现而予以利用了。在其他体系建筑中,屋顶素来是不受重视的部分……但在中国,古代智慧的匠师们很早就发挥了屋顶部分的巨大的装饰性。在诗经里就有‘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句子来歌颂象翼舒展的屋顶和出檐。诗经开了端,两汉以来许多诗词歌赋中就有更多叙述屋子顶部和它的各种装饰的辞句。这证明屋顶不但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并且是我们民族所最骄傲的成就,它的发展成为中国建筑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16]但参照梁思成对中国建筑其余八个特征的论述①其余八个特征分别是:1.个别的建筑物,一般地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下部的台基,中间的房屋本身和上部翼状伸展的屋顶;2.在平面布置上,中国所称为一“所”房子是由若干座这种建筑物以及一些联系性的建筑物,如回廊、抱厦、厢、耳、过厅等等,围绕着一个或若干个庭院或天井建造而成的……;3.这个体系以木材结构为它的主要结构方法;4.斗栱;5.举析、举架;6.大胆地使用朱红作为大建筑物屋身的主要颜色……;7.在木结构中,所有构件交接的部分都大半露出,在它们外表形状上稍稍加工,使成为建筑本身的装修部分;8.在建筑材料中,大量使用有色琉璃砖瓦,尽量利用各色油漆的装饰潜力。木上刻花,石面上作装饰浮雕……,我们不难发现,“屋顶”实是中国建筑特征中最明显、最易于识别的建筑视觉符号,屋顶在塑造中国建筑的轮廓方面具有最显著的效果。因此相应地,在建筑实践中“屋顶”自然成为最方便引用和最容易出效果的建筑视觉符号。这也就不难解释尽管梁思成在“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口号下真正倡导的是善用中国建筑的“文法”和“词汇”,但在急功近利的建筑大潮中所谓的“民族形式”如何最终被简化成为“大屋顶”这个中国建筑“关键词”。
从文化本位的角度看,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几千年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以来,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面临了一个在现代性语境中如何去讲述“中国”的问题,建筑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当传统的中国建筑难以负担和表达中国现代性建筑功能的时候,在学习和推广西方建筑的前提下,对自身“民族形式”的追求自然成为了现代中国建筑最高的审美理想。这个建筑上的最高审美理想实质上是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意识的投影。勿需讳言,许多以“大屋顶”为建筑“关键词”的“民族化”建筑都容易流于一种中西方建筑语言的生硬对接,因而也容易招致追求“形式主义”的罪状。但这种罪状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无法正确理解和处理“民族形式”带来的。事实上,纯粹的建筑范畴内的“民族形式”本身是无辜的。并且进一步来讲,中国要在现代性进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离不开“民族意识”,中国建筑要在现代性进程中讲述“中国”主题就离不开“民族形式”,尤其是在现代中国那些具有历史意义、文化意义、甚至政治意义的标志性建筑物身上。正因为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集体意志高度统一的中国,在“大屋顶”饱受批判的背景下,“大屋顶”造型仍然被允许出现在共和国国庆献礼的工程建筑设计中。这一事实反映出以“大屋顶”为标志的“民族形式”作为一种建筑情结实是中国人浓重的历史感和民族意识在建筑上的体现,这是当时主导了“大屋顶”批判的中央决策层也不得不正视和承认的现代中国建筑最高审美理想。审美理想的实现能赋予一个建筑实体以民族文化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民族文化身份的影响比政治影响更加顽强。
回到“中国美术馆”的主题。在“大屋顶”饱受批判的背景下,中国美术馆的建筑方案仍然从颇具现代感的长方型盒子最终转换为带有“大屋顶”的“民族形式”设计,这反映了现代中国建筑对作为最高审美理想的“民族形式”执着的审美追求,亦说明了当时的中央决策层清楚地意识到了民族文化美学认同对于国家美术馆的重要性。
“斯图尔特·布兰德在他的《如何了解建筑》一书中告诉我们,建筑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建筑随时都在发生改变。有东西加进去,或去掉,特征被修改、移动等等……”[17]1962年至今,中国美术馆分别于1990年、2002年经历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改造装修。其中,2002年的改造装修呈现出中国美术馆为适应新的时代文化发展所进行的文化定位的调节和空间话语的转向。[18]如今,这个存在于中国首都的文献式建筑物将会逐渐交接其历史使命。因为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中心区域内,由法国著名建筑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设计的超大体量、具有新美学风格的中国国家美术馆新馆的开幕正在被中国公众,乃至世界博物馆公众期待着。一个表征着新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中国国家美术馆即将显现,它将创生出新的记忆、伤痕、想象、智慧、愚蠢、愿景等,为后世书写新的美术馆历史。
参考文献:
[1] 南方朔.带着“心”去“闲逛”[A].刘惠媛.缪斯共和国·序言[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2] [意]布鲁诺·赛维.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47.
[3] 邹德侬.50年代国庆十大工程评述[A].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北京十大建筑设计[C].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161.
[4] 李沉.创新:中国建筑师才能走出国门[A].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北京十大建筑设计[C].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198.
[5] 何琳.中国美术馆旧貌换新颜(非出版物)[Z].中国美术馆,2005.
[6] 刘曦林.文案追溯(非出版物)[Z].中国美术馆,2004.
[7] 杨力舟.艺术殿堂珍藏百年精品,文明窗口高扬民族雄风——中国美术馆40年华诞礼赞[A].艺苑摭言[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507.
[8] 候一方,等.台湾的美术馆与艺文空间[M].台北: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17.
[9] [日]并木诚士等.日本现代美术馆学——来自日本美术馆现场的声音[M].台湾: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3:7.
[10] 中国美术年鉴1949—1989[J].桂林:广西美术出版社,1993:1386.
[11] [美]卡若·邓肯.文明化的仪式·公共美术馆之内[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12] 张法.中华性:中国现代性历程的文化解释[J].天津社会科学,2002(04).
[13] 林风眠.美术馆之功用[J].美术观察,2000(04).
[14] 程万里.也谈大屋顶[J].建筑学报,1981(03).
[15] 梁思成.祖国的建筑[A].梁思成文集(四)[C].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56-157.
[16] 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A].王明贤,戴志.中国建筑美学文存[C].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290.
[17] [英]布莱恩·劳森.空间的语言[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212-213.
[18] 林早.中国美术馆:建筑的空间与文化的经验[A].大学与美术馆·作为美术馆的声音(总第四期)[C].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51-70.
Historical Origin,Naming Orientation and Cultural Spirit of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LIN Zao
(College of Humanitie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25)
Abstract:Art museums,especially national art museums,besides boost the publicity in space,they also consciously assume as the symbolic images of na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reveals how the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achieved its cultural orientation in specific historic period and how its cultural image was shaped by investigating its historical origin,naming orientation and cultural spirit in 1960s.
Key words:The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Top Ten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Louvre;national style
作者简介:林早(1979—),女,贵州安顺人,哲学博士,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学。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艺术与公共空间研究”(项目编号:GDBY2010014)。
收稿日期:2016-03-13
DOI:10.15958/ j.cnki.gdxbysb.2016.02.010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6)02-005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