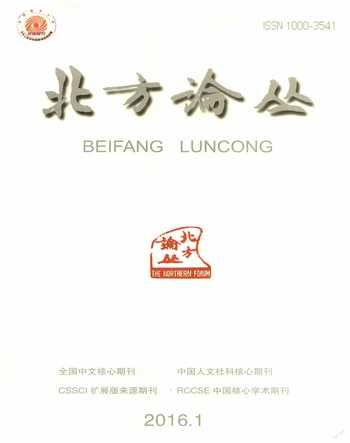《红楼梦》开篇石头故事与太虚幻境的哲学寓意
2016-05-30何跞
何跞
[摘 要]《红楼梦》开篇文本隐含着关于智慧“通灵”的悲剧哲学思想。作者虚构石头境地和太虚幻境,通过寓言故事对哲学命题进行寻根,展现“情”和情之所生的“灵”根,以及智慧“通灵”,也即是智慧觉悟的痛苦,整个带有悲剧的意味和悲观的情调。这个悲剧是因为“情”的现实悖反,也即是“情”与“用”的不能融合,而在寓言故事中它则表征为木石因缘的悲剧过程。以幻境寓意为切入,可以看到其中的“情根”关键,“绛珠”结果,以及宝玉锻炼而生“灵”性,绛珠依石而化“灵”“根”的寓意,解析作者寓于木石“情”“用”悖反与通“灵”悲哀中的悲观哲思。
[关键词]《红楼梦》;开篇;境地;太虚幻境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042-05
《红楼梦》的哲思主体,在其中以寓言形式铺陈出来的虚境故事中得以呈现,作者对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进行了寻根式的探索。《红楼梦》开篇即虚构了石头境地与太虚幻境,它们都是神仙境地,是文中的“虚境”,由僧道送玉一事而联系起来。两者平行共处于故事的“虚境”中,且有千丝万缕微妙的关系。我们可以列举书中关于两境的主要文段,通过理析其中地名人名等的谐音隐喻,剖析其所述事情的微妙联系,并解析作者隐于两事中关于智慧灵性来由的深刻思考。
首先是女娲炼石境地,文中写道: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1](p.7)
其次是西方灵河岸故事,小说通过茫茫大士,也即僧言道出:
那僧笑到:“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1](pp.18-19)
这两段引文中的各种人名、地名、物名等皆有丰富的谐音寓意内容。首先,在地名寓意中,大荒山寓荒唐,无稽崖寓无稽,青埂峰寓情根;太虚幻境寓原始的虚幻之境,西方寓佛家极乐境界,灵河岸寓人的觉悟,三生石寓爱情情缘。其次,人名、物名的寓意中,警幻寓警醒幻情的总领者;赤瑕寓玉小赤、玉有病,神瑛寓神玉,侍者寓为他人操劳者,甘露寓爱心;绛珠寓血泪,离恨天外寓恨天内,蜜青果寓密情迷情,灌愁海水寓灌愁,缠绵不尽之意寓爱情。从上面对两境物事名称喻意的缕析中,我们可进一步深入进行如下分析。
一、幻境寓意
“大荒山”“无稽崖”的地名表明女娲炼石补天剩一块未用事是荒唐无稽之言;石头境地的故事也是作者虚构的,属于总的幻境中的事。“太虚幻境”意谓原始终极的虚幻境地,其中的神瑛、绛珠故事则已然明示其为作者虚构幻境中的事。“警幻仙子”作为太虚幻境的终极总领头目,其人名则表明了其为警醒“幻境”中人事情的终极关键作用,所以为总领。因此,这几个地名人名背后隐寓的意思是:石头境地和太虚幻境都是作者虚构虚幻境地,同属于小说幻境中的“虚境”神话故事,两者本是同性质同体的,只不过作者以小说家的故事话语模式将其拆分为两地两境故事,以虚构情节,好通过小说故事这种艺术语言来隐显作者的思想感情。
在这个大的小说幻境中,太虚幻境是作者所虚构的幻境,用的是小说杜撰笔法;而石头境地中及女娲炼石补天用的则是中国创世神话;西方灵河岸是佛家地名,用的是佛家神话;赤瑕宫中“宫”“侍者”又是道家名目,用的是道家神话。总之,整个虚境故事都是作者叠合套用各家神话,并加入自己的小说家虚构,最后形成的一个新型神话世界,用以辅助其叙事达旨。表面上看,是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提倡佛道空无、清静无为的观念,但实际上他却并没有盲目乖顺佛道的神统权威,而是利用其神话羽翼来构撰自己的关于深挚人情,所谓“痴”情的故事,来探讨人的出路,探讨关于人的终极命运的问题。《红楼梦》作者是一位至情至性的人,也是一位入世很深的人,对人对世界有着深刻的眷恋,而非如佛道出世那样顺从于简单而不负责任的空无清静。当然,他在关于人生的探讨中也参考了佛道思想,但仅仅是参考罗列,而非目的性的弘扬,他的目的还是在于特立独行地用其所擅长的小说笔法对人生人情作充满深情的哲学寻根。
而在各层境地中,主要角色石头被代表佛家道家的僧道由入世的创世神话境地,带入到容纳出世的佛道境地的太虚幻境,再被送入到入世的人间实境,最后又回归到创世神话的石头境地,进行了一个三角的轮回。但结局只是石头境地中顽石凡心的实现,太虚幻境中木石灌溉还泪之账被还清,人间宝黛爱情的悲剧结束,余者还是石头的永恒嗟叹,只不过换了形式,成为《石头记》一书中的文字嗟叹了。这就是作者对人生人情的有穷演绎和无穷探讨。曹雪芹认为,人的本根和终极家园是“情”,但他只是把“情”从生发起演绎了一番,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情”的出路。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出路,那也只能说在于《石头记》一书的文学记载和发泄中。
二、“情根”关键
“青埂峰”“三生石”同是指喻“情”字,并以人情中的爱情作代表。《红楼梦》一书中的“情”不仅仅是男女爱情,而是以男女之间至高无上的纯挚感情为代表,指涉一切真诚执着的人情,也就是其所谓“痴”情。从“三生石上旧精魂”[1](p17)的传统文化含义来看,“三生石”几乎就等于“情根峰”,“情根峰”是对“三生石”的解释性说法。以“情根峰”下石和“三生石”畔草为偶,正好恰对,寓示了木石情缘的自然天成。同时,“情根峰”下的“顽石”与“三生石”本身都是“石”。总之,一“峰”二“石”的叠映复合也提示了两境叠合一体的联系。
青埂峰顽石(具有情根的石头)与赤瑕宫神瑛侍者(赤而有病的神玉)在人间“实境”中合二为一,以宝玉为体,两者本有十分深刻而微妙的联系,它们是叠和同一的。“神玉”是自尊褒美的说法,“顽石”是谦虚讽刺说法,实际二者都是一体的。“赤”比喻赤诚肝胆,没有一点虚伪,所谓“婴儿子”之美好心灵;同时“侍者”身份为他人操心服务的无私精神也喻示了其纯善赤胆的本性。“赤”又与“情根”的必然产物“血泪”之“血”的“赤”红相为映照指喻。“瑕”指玉上的小斑点,脂批所谓“玉有病也”。病有病根,玉的病根即是“情根”。人性的某种性情一旦是天性中所带之根,则往往被世人目为嗜欲、嗜好,目为“病根”。则“赤瑕”所寓指的赤诚真挚的悲情,也是其天生的病根即是“情根”,所以赤瑕宫神瑛侍者与青埂峰顽石是完全重合的两个意象。
上面分析“情根”就是三生石,“情根峰”下顽石也与三生石同体,则赤瑕宫神瑛与三生石则又在本质上相交合,神瑛与三生石两个意象又在意义上完全叠合一体。我们若把神瑛侍者理解为“青埂峰”下顽石,三生石的石头精灵,因“受天地精华”修成个男子形体(同绛珠仙子由草修成女体一样),居住于仙境中的“赤瑕”宫中,也未尝不可。
三、“绛珠”结果
石玉喻情,而珠玉也喻情。黛玉在仙境中为“绛珠”,实际也是“情”的化身。不同于青埂峰顽石与赤瑕宫神瑛“情根”寓意的是,它指喻“血泪”,是情的结果,而且带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绛珠,也就是血泪,说白了还是在喻指愁情。但何以为愁呢?神仙境界中不劳衣食,不忧生死,想去哪就去哪,心有所思,即刻得现,这“绛珠”、“血泪”和这愁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只有两种解释。其一,情与伴之而生的愁是人与人的幻异,即仙道群体所固有的,是有意识的人与仙的一种固有特性,是与生俱来的。其二,愁情的具体产生则是从神仙群体中个体之间而产生,或者从神仙群体与尘世凡人群体之间的关系而产生。从前者看,作者无疑是以“情”为主导和纲领。周汝昌《红楼艺术》第一章言:“《红楼梦》文化之三纲:一曰玉,二曰红,三曰情。” [2](p.8)从后者看,作者解释了“情”在智慧个体之间的具体存在状态,以及他们具体的“情”产生的原因。这里又分两种:一者,是由于仙人之间的相互爱慕,如神瑛的怜惜灌溉,绛珠的“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1](p.18);二者,是由于仙人对尘世中人的悲悯。可见,绛珠和神瑛俱是有情有性的仙人,和人一样会产生爱慕怀恩的感情。
而神瑛绛珠故事的过程,是作者对情之发生与结果的探讨。在神仙境界中,也就是人所向往(或者说幻想)的最善最美的终极出路与宿境中,西方灵河岸的一棵凡草(在它还没有吸收天地精华,修成女体,列入仙班前当然还只能叫作凡草),名字就叫“绛珠”。根据以上分析,绛珠就是愁情,这草其实就是仙界情感和神仙之泪的化身,是神人的爱与悲悯。然后,一个名叫神瑛的仙人见它十分可爱(有情者总是让人怜爱),却要枯萎了(情太甚则悲愁伤身),于是怜惜(也有悦爱之意)此草,每日浇灌,让这株草活了下来,并得以好好生长。这棵绛珠草日后吸取天地精华(有情者是天地之精华,可见作者对“情”的高赞),修成女体(女子是美的象征),列入仙班(与众不同,不同于凡俗)。成仙之后,绛珠仙子的体内装着神瑛的灌溉之水,也就是他的灌溉之情(平白当然不会有灌溉之情,这其中含有神瑛对绛珠的悦爱和怜惜之情),于是自己也就郁结出一断不了之情(所谓“不了”是说缠绵悱恻,深而且痴)。在这红楼主人公“情”之原生的整个过程中,到底是谁先“情”谁,谁是初“情”者呢?从神瑛浇灌绛珠草的事实看,是神瑛“情” 绛珠;然而,加上“绛珠”其名的谐音寓意来看,则是绛珠先已秉“情”,神瑛才会对这秉情之草动情。如果我们接着追问神仙境界中这“绛珠”又是从哪里来的,无疑,它是神仙自己之物,是神仙的“血泪”。神仙境界也有血泪,因此,《红楼梦》里的神仙其实并不是真“仙”,他们也是人,是现实中人幻想出来的一种看似超脱,实则与凡人一样的存在。
似乎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出世也好,神仙也罢,竟然都是虚无缥缈,都是人自己幻造弄出来的。人要解决的那“情”之“血泪”,其实,无论在凡间还是仙界,都不曾被抛除。在神仙世界,“情”与“泪”以看似淡漠的变相出现,其实与大观园里的“情”与“泪”是一样的。“情”与“泪”也不是像作者表面所写的那样,是被拿到神仙境界给化解掉了,反而作者是以神仙世界为贮“情”之所,把一切无法解决的“痴情”与“血泪”归聚到仙界,以木石之属的无知无情和仙道的淡漠超脱来承载“情”与“泪”带给人的巨大负重,并赋以其永恒存在的形态。因为唯有草木石头才会与天地长存,惟有神仙道人才会长生不老,而承载着“情”的“人”却都会老死。
四、宝玉锻炼而生“灵”性
上面分析“青埂峰下顽石”“三生石”“赤瑕宫神瑛侍者”三者同体,且其最根本的特点都在于一个“情”字。“情”是三者共同的“病”根。那么,我们接下来则需讨论这个“情根”是否有最原始的开头。我们发现两条线索:第一是石头境地中所言“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第二是太虚幻境中所言的“西方灵河岸上”。这两句话里都著一个“灵”字。
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顽石中,女娲为何单将这一块弃于“青埂峰”下,而不弃于其他地方,或者说作者为何单用“青埂峰”作为石头被弃之处的地名?显然,作者有所寓意,他是告诉读者:这块顽石之所以被弃,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它可能是有“瑕”“病”,而不能被用来补天,它的“病”就是它的“情根”。后面接着又言:“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其中“自经锻炼之后”一句有歧义,“锻炼”的时间指示不确切,有两种可能:一是“锻炼”开始;二是“锻炼”结束。则整个句子也有两种解释:一是石头自从锻炼开始之后,也即在锻炼的过程中及锻炼结束之后,通灵性;二是石头自从锻炼结束之后,不包括其锻炼的过程,直到被弃后,才通灵性。若采用第一种解释,则整个补天被弃的过程则不是如作者文字表面所写,仅是多出一块这么简单的理由,而是有深层的理由可以解释的:这一块顽石在锻炼的过程中就与别的石头不一样,因锻炼而通灵性,因有灵性而能如人一样达到觉悟的境界而产生了同人一样的意志感情;而经女娲之手被锻炼的石头又与凡人不一样,其所具有的意志感情也超出于凡人,而成为一种极端赤诚纯挚的情志,代表了人所具有的情志的最美好的极端;这个极端在通灵的石头那里就成为它的根,决定其石头物性无生命的不觉悟状态进入到人类智性有生命的觉悟状态,所以,称之为“情根”。但这由通灵觉悟而产生的“情根”因为是人情美好的极端而成为超出于凡人理解“病根”,不能为凡事功利所用,因而被女娲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凡众功利的最高领导者所抛弃。至此,“情根”的最原始来由则被理析清楚。这里,作者并不是否定儒家入世的群体功利观,而是展现了现实中“情”(人情意志之实)与“用”(功利物事之实)的矛盾,同时贯穿了一个“物极必反”的原理,从中推演出情极而悖实用的现实。
那么“西方灵河岸”,则其寓意也有了着落:三生石独处灵河岸边,是三生石的“情根”独基于灵性觉悟的“岸床”。而灵性所生的经历,则作者先在顽石补天一段中隐寓已经交代了。
五、绛珠依石而化“灵”“根”
关于绛珠,它也是基于灵性觉悟的“岸床”所生,且傍具有“情根”的三生石,因而它也和石头一样,是由灵性觉悟到产生情根的过程。而其名字本就喻指“血泪”,“血泪”当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由“情根”而哭泣产生的,它是“情”的结果的物体具态化。因而它依傍三生石而生。可以说,它就是三生石所哭的血泪。再看“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1](p18),是言绛珠(血泪)十分柔弱,若不得神瑛以甘露(爱心)灌溉滋养,则不能“久延岁月”,即会枯萎死亡。这里又含有一个寓意:精神依傍情人所生长的人,还得由情人去维护;由“情”所生之泪痛,还得由“情”去自疗抚慰;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同时,“侍者”作为为他人操劳者的身份,也使神瑛对绛珠的灌溉感情变成大公无私的纯粹本性。这里写出了关于绛珠和神瑛木石之间的整个以爱情为具体的“痴”情的纠葛关系:绛珠就是三生石的泪,神瑛灌溉绛珠相当于三生石的自疗自慰,神瑛若不灌它,则相当于自己的血泪一直自损自伤而终会归于消亡不存在,因而玉石得傍绛珠作为情根宣泄的家园,以灌溉绛珠作为自疗的方式而得以存在;绛珠又傍三生石而生,其性也染有三生石至情的特点,因而它必须依靠石头精灵神瑛的至情灌溉才能存活。总之,二者必须相互依赖而存在,且本为一体,而被离析为两物两对象。这同于一个简单生活的常理:爱情的双方互相纠缠不可分离,是合二为一的一个整体,二者的相互扶持也是出于无私的本性自愿。关于后点,从木石都处灵河岸上,也即都是基灵性觉悟的“岸床”所生,这一点中也可以看出其合二为一的整体性。
再看绛珠后面的经历,它“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又与“灵”性关联,证明其非凡辈。石头在锻炼中产生灵性,绛珠草在灌溉中产生灵性,这也是二者基于灵性觉悟超出于凡俗的相同之处。她修成女体后,“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表面是写其神仙无忧无虑的生活,实际却是说她在离恨天中,以密情为食,以愁绪为水,生活在情、愁、爱、恨的烦扰之中。这又是写两者爱情纠缠之深,在仙界都是如此,因而脂批:“妙极!恩怨不清,西方尙如此,况世之人乎!趣甚警甚!”[1](p.18)后面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是写玉石意欲再入世,以弥补其“无用”之“用”,而绛珠随之,则故事的深层情理便备具了。
绛珠神瑛之事也是实境中宝黛情事的映照。绛珠生于三生石畔,是喻黛玉幼时(具体是六七岁时)进贾府与宝玉相会后,“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的生活。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使其久延岁月,是喻宝玉对黛玉特别的维护、照顾,使黛玉作为被收养者在贾府不致受丝毫委屈,而健康愉快地成长。正如宝玉所言:“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顽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收着等姑娘吃。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了。”(第二十八回)黛玉“后来受天地精华……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则是喻黛玉后来读书识事,由懵懂孩童变为美丽富有才情的姑娘,但却因为感念以前宝玉的情谊而萌生爱情,以不能报答此情为恨,所以,与宝玉不同别人的亲密感情,是她的精神养料,而为此情整天伤愁忧虑则也成为必吞的苦水,成为她常喝的汤药。而神瑛“凡心偶炽”,“欲下凡”则是喻宝玉不安人间功利虚伪的“本分”,与常人异道,厌恶“仕途经济”,坚持自己真善重情的道路理想,而遭遇不被理解被排斥和最后的苦难,相当于神仙的下凡历劫。黛玉欲追随神瑛“下世为人”,则是喻黛玉能理解宝玉,是宝玉的知音,她追随宝玉不喜“仕途经济”的精神理想,正如宝玉所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绛珠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毫无疑问是喻黛玉一生把性命都托付给宝玉,为宝玉一生流泪最终为此而亡。
六、木石“情”“用”悖反与通“灵”悲哀
石头本该补天,却因“情根”而背弃,这是寓意补天之用与情根的背离难合。而石头补天喻儒家入世之“用”,而绛珠喻悲情,现实中的宝黛爱情悲剧,仙境中木石因缘的无果,其实也是寓意“情”与“用”的不能结合。《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里第一回眉批:“妙。自谓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3](p.5)另外,关于“情”与“用”,本文赞同周汝昌先生的观点。周汝昌先生在其所著书《自序》中说:“一个才,一个情,总是密迩相连,竟难离割。《周易》中已有天地人‘三才观念,也有了‘圣人之情见乎辞的提法。”[2](p.1)
神瑛即“顽石”,两者是二元同体的。这“顽石”又自有一番来历:女娲炼石补天剩下的一颗五彩石,被遗弃在大荒山(庄子所谓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无稽崖(喻指虚无缥缈无稽之事)青埂峰(谐音情怀耿耿,难以磨灭)下,其实也就同灵河岸边未成仙之前的那棵“绛珠”凡草一样,也是一颗平凡的会因“无材”被弃而“日夜哀叹”的石头。两者都不是真正无爱无欲,心如止水,“形同槁木”,真的超越了人世。而且“绛珠”喻人之情,“顽石”则喻人之用;既然“绛珠草”修成“绛珠仙子”,“顽石”也同指“神瑛侍者”。其中“侍者”喻国之栋梁,侍于天子和万民,做人民的公仆。两者都臻于至善至美,他们的因缘是喻指人世间“情”与“用”的结合。但是事实上,“用”却无所得用,“情”无所得通;不得用则化而为“顽石”,不得通则化而为“绛珠草”。
“用”是现实所能有的境遇,“情”里面包含了理想;因而“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的不能结合,也即“用”与“情”的不能结合,其实也就是现实与理想的巨大矛盾冲突。同时,除了爱情与理想,“情”里面也包含有因不得“用”而产生的悲哀之情。所以,贯穿此书的木石之缘、瑛珠之份、宝黛之恋的总归虚妄,其实体现了作者对现实人生的一种透析和解悟:理想与爱情总是跟现实相违背,人对理想与爱情的执着追求是没有结果的,悲剧性的,是一种“痴”的举动。但在这种悲哀的透析中,作者却在高度地肯定情以及这种毫无结果的痴情行为。《红楼梦》后面的行文中交代贾宝玉有爱红的毛病,第十九回:“袭人道:‘再不可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还有更要紧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4](p.392)爱红就是爱“绛”,爱“绛”也即爱“珠”,因此,贾宝玉是深味珠泪,深知大悲,深具痴意的人。而薛宝钗爱素斥红,素是礼俗庄重的代表,红则是至情痴情的象征。宝黛爱红,都是痴性之人,因而与宝钗有别。刘万里关注到“薛宝钗对红色加以排拒和隐藏的有趣现象”,并认为:“才子佳人小说《定情人》在谈到爱情标准时有桃红、梨白的说法,宝黛形象即是这一观念的演绎。”[5](p.187)
另外,“无材”谐音“无猜”和“五彩”。“无猜”暗寓纯真的质性和毋庸置疑的才能,书中所言“顽石”“宝玉”“神瑛”都是至真至性的存在。“五彩”则暗寓其外形的俊美。彩同“纹”,“文学”之“文”最初也同“纹”,“五彩”是寓其臻于至美之境,艺术之极境,所谓美质良材,内外俱美。然而,有了“五彩”,往往会不得用,因而也就是凡俗意义上的“无材”了。这里又涉及一个关于艺术与现实的争论。诗化的人生,至美的境界总会为世俗所不容,真正的文人艺术家对凡俗的现实来说往往是无材无用的。这就构成了一种艺术与现实之间的悖谬,一种生活俗常规则与存在真理及人生价值的悖反。这也是《红楼梦》整部作品以反讽为基调,以曲语隐语出之,并且在传播的过程中遭受禁毁,被列为禁书的原因。诗人往往也是痴人,“痴”字里包含人之真性情及理想的“艺术”与现实之用相悖反的深刻哲理。
由上分析可知,总领红楼之旨的正在于一个讲述“情”的“痴”字。而这个“痴”早已经在《红楼梦》虚境里,也是在开篇就托出的起源故事里便早已悄然蕴藏着了。作者以一种无为的视角为遮掩,把实境里的故事冠以仙道之名,赋上出世色彩,做了一次聪明的翻版并暗示了以后的一切的故事。虚实两境里“痴情”的实质没有变,我们也可以说,作者只是用了一些概念性的虚指的地点名词(“太虚幻境”“无稽崖”“青埂峰”“放春山”“灌愁海”“离恨天”),人物名词(如 “绛珠仙草”“神瑛侍者”“顽石”“痴梦大仙”“空空道人”“渺渺大士”),和虚构的故事(无材补天,绛珠还泪),把实境里的痴情痴人和痴事重新叙述了一遍。如果把这些名词词尾舍掉,直接形容词的表述,比如,“虚幻”“无稽”“灌愁”“离恨”“血泪”“痴梦”“空空”“渺渺”等按故事原样连缀起来,这个故事就成了一段寓言而进行哲理性阐发了。由此可见,叙述语气的出世,是入世的变相;虚境与实境都是由“情”字统领着。小说越是趋向出世和“无情”,《红楼梦》后面的故事中越是把人物归导向出世与“破痴”,其实,作者、叙述者、小说中人,甚至读者,就越是被归趋或被导向更深的痴情境地。要不痴,除非他们不再有思想情感,或者说已经真正地消亡或者死亡。梅新林先生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向“生命之美的挽歌的不断超越,最后通过贯穿全书始终的矛盾运动及其之于人类悲剧命运终极指归的深刻辨思而获得了永恒魅力”[6](p.316)。以情为本的文学作品不可能摆脱“情”,也就不可能摆脱“痴”的生存命题。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突出地表现了“情”与“痴”的生存命题及其存在困境。
[参 考 文 献]
[1]曹雪芹. 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M]. 沈阳:沈阳出版社,2005.
[2]周汝昌. 红楼艺术[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浦安迪. 红楼梦批语编全[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曹雪芹.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第十九回[M]. 沈阳:沈阳出版社, 2005.
[5]刘万里. 万红丛中一片雪——薛宝钗对红的排拒与隐藏及其心理透视[J]. 红楼梦学刊,2002(2).
[6]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石头的生命循环与悲剧指归[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作者系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洪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