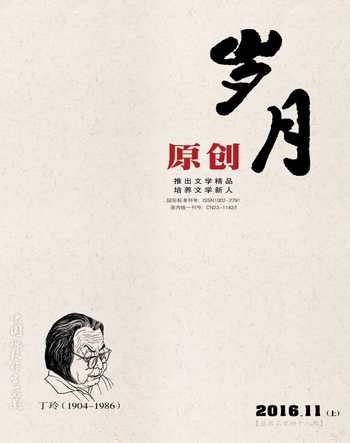路上的修行
2016-05-30洪忠佩
洪忠佩
瑶 湾
一碗茶。一段时光。青花的瓷碗,明前的绿茶,头顶着天光,门前还有潺潺水响,氤氲,散漫,陶然。
在瑶湾念恩堂围着八仙桌喝茶,堂前天井的阳光正好照在窗棂上,透出一种深度的明暗效果。隔扇窗栏雕的图案是《春日》《诗书传家》,冰裂,漫漶,却仿佛留有诵读之声。板壁上挂的条屏笔法虽稚拙,但画境里还有几分水墨意趣。村庄远去的背影,已经消失在苍茫的岁月里,而在不远处的考水、瑶村坦,隐隐约约传来扫墓祭祖的鞭炮声。那噼噼啪啪的声音里,应是血脉在传递吧。瑶湾念恩堂的主人汉龙说,他是考水村的外甥,一家人将去考水黄杜坞为昌翼公扫墓。
“考槃在川,硕人之宽”。考水的村名取义于《诗经·卫风》中。在遥远的年代,考水亦称槃水。而昌翼公呢,是“明经胡氏”的始祖,是他成就考水成了中国“明经胡氏”的发源地。倘若追根溯源,现代著名学者胡适、近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等,他们的祖上都在从考水村走出去的。明经书院、石丘书院、文峰书院、藏书楼、文昌阁、文笔塔,都是对考水村厚重历史文化积淀最好的注解。那四面环山,槃水河绕村而行的古老村庄,始终藏着一个姓氏和一段历史的隐秘,一位名叫胡三的婺源人,因唐末朱温叛乱为唐昭宗李晔保留了一条血脉,这条血脉便是昌翼公……
清明去瑶湾,日子是德馨先生电话约定的,我在出差南昌的途中毫不犹豫答应了。我觉得,清明去村庄无论踏青还是驻留,都是一件有非常意义的事。考水、瑶湾、瑶村坦、樟村,在一条线上。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金灿灿的油菜花还没有退场,石板路、民居、拱桥、路亭、田野、草木、虫豸,还有竹篱笆、社公庙,以及采野菜和锄草的村人,都给了我一路村庄与自然的亲近,以及乡土气息的憧憬与陶醉。瑶村坦在明崇祯间程姓开始建村,樟村在南宋庆元间章姓就从歙县篁墩迁入了,村庄粉墙矗矗,鸳瓦鳞鳞,古朴、安宁,充溢着人间烟火的味道。而瑶湾呢,是对考水、瑶村坦、樟村的连缀与承接。牌楼、民居、文笔塔、池塘、廊桥、路亭,甚至溪岸与护栏,都散落着村庄的往事。从念恩堂厨房飘出的袅袅炊烟里,我感受到了瑶湾的呼吸。
在考水的村史上,村里的明经书院占地有二千五百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大成殿、会讲堂、书斋、塾堂等,不仅能供胡氏子弟读书,也可以满足附近学子求学。明经书院的创建者胡淀与胞弟胡澄,还分别捐田三百亩与六十亩,全部用于兴办义学。书院规定,家族子弟不论贫富,士人不论远近,都可以到明经书院读书求学,书院还提供膳食与住宿。尽管明经书院遭兵火焚毁,后来考水合族重建,最后还是坍塌在岁月之中……荡然无存的只有是时光留下的缺憾吗?有的时候,我在村庄的残基与废墟里,读到的是村庄散佚的一段悼词。
樟村的章氏宗祠前,堆满了一二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木,一根根都是用来修葺祠堂的梁柱。木质的香气,隐逸,干爽,弥漫。即便是新鲜去皮的木头,进入了祠堂,也就有了古意。在祠堂的外墙上,遗存着特殊年月的语录,内墙上还能够勉强看出戏班演出留下的记录,隐约,残缺,像时光的暗喻。祠堂有一半都塌了,而祠堂里的那炷香断过吗?白云悠悠,流水潺潺,鸭子游弋,我心怀敬畏,用手机拍下了章氏宗祠门楼在小溪中斑驳而苍老的倒影。
返回瑶湾,在廊桥前,我想起了诗人庞培写给我的《考水廊桥》:我勉强能看见一头耕牛/至于邻村的新嫁娘/至于远在京城的书生/荣归故里/或牛背上的牧童/我一概没看见//我勉强能够看见油菜花/田野仿佛巨型的染坊/而村口廊桥/像主人家放下的一份聘金/为来年羞红了脸/金灿灿的迎娶……
后 径
“见凤而止,遇凰而住。”这是怎样的一种境遇?
在一千多年前,婺源有一个名为查元修的人果真遇到了。当时,查元修是隐居婺源城西的,一位高人的指点让他经过清华走向了浙源的凤凰山,他的脚步在叠翠的凤凰山下停了下来。查元修当过太常寺太祝,虽然拿着朝廷的俸禄,却只是一个掌管礼乐的官员,他应是无缘也无心于权贵吧。一个追求山水田园的人,他的心境一定明朗而清澈的。不然,他能够在凤凰山下铸炉坦定居下来吗?
一个地方因一个人改变了,那个叫山坑的地方,开始有了凤山的村名。查元修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相中的凤山村竟然会衍生成徽饶古道上一个大村庄。绕着凤凰山的浙水河,流淌着时间的寓言。有人跋山涉水来到凤山安身立命,就有人随着浙水漂泊远去。一个个背影渐行渐远……一抹重墨淡去,文笔、百岁坊都毁了,只有龙天塔、孝义祠、孝善桥、报德桥、西门井,是凤山村山水之外千年镂空的遗存。
村庄的时间,缩在斑驳的屋檐下,躲在祠堂和老屋的暗处。我秋日随查氏的后裔永红兄去凤山村,隐约觉得凤山的千年有一种断裂感。这种感觉,在走村串巷与村里老人的聊天中还是得不到弥补。然而,当我望着凤凰山,以及山下的村舍与农田,不仅感知到了查元修当年忘情于山水的惬意,还感知到了查氏根脉的生长与联结……永红家的祖居“宝德堂”正在修缮,三层楼的老屋,翻修起来工程量大,不仅忙坏了主人,也忙坏了匠人。临街的门面和临河的坊间提醒我,宝德堂的功用除了住家,还是私家酿坊。前有店,后有坊,古法密制,以姓氏为标签,就叫查记酒坊,宛如流水般顺畅。屈指算来,从永红先祖查邦秈雍正年间创立,到他已经是第十一代主酿了。永红如今的家安在上饶,他回乡修缮祖居,应是他怀乡的一种方式吧。
通往麦坞的小径,宛如凤山没有割去的脐带,以山岭的姿势在村庄的后山蜿蜒。那个曾在遥远年月说凤山铸炉坦是一盏灯火的,是一位民间高人,而那位说后径岭是吹火筒的,同样是民间高人。风与火,风是可以助火势的,亦是可以灭火势的,他们个中的玄机只是相互秘而不宣罢了。在卜居的凤山,村庄、后径岭依在,两位高人早已随着风火远去,留给后世的也只有是一段传说的情景和意象。后径岭与后径亭是孪生的,它们互依互存,不离不弃。岭脊上的后径亭从乾隆年间用石块砌起,亭在一次次的修复中还是原来的模样,而嵌入亭壁的碑记已经模糊不清了。岭上岭下,相比以前,跫音是否荒疏了呢?到了岭底,便是进入黄喜坑的路口了,石砌的梅光亭成了起始的标记。遥想当年,凤山的先祖为何把进山的石板路和石亭修建得如此讲究?梅光亭里的一块石碑上刻着明确的答案。原来,黄喜坑不仅有查元修夫人的坟茔,还有高湖山真显大师所创的储秀庵。在凤山,查元修的墓至今仍是一个谜。一个隐士,辞世后连墓冢都不留,他的超然令多少后人自叹弗如。然而,程夫人的墓埋在黄喜坑,黄喜坑乃至后径岭与查元修和凤山就有了隐秘的联系。得道僧人能够相中修身礼佛的地方,无疑是一方福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喜坑是否是凤山人一种精神形式的存在呢?身体的归宿与灵魂的归属,谁又厘得清孰轻孰重?
青山包裹,山坞里曾经刀耕火种的现场,沦为荒芜的田地、茶地。坞边依次是野草、大茅、荆棘和混交林。许是我们惊扰了这里的清净,不时有锦鸡野鸡从草蓬里噗噗地飞出。秋泓一剪,叶落秋风。山涧里的水只有浅浅的一皮,清澈,悠缓。有的地方只有流痕,裸露着石壁的肌理。而低处呢,成了水凼,有绿茵茵的青苔在漂。仔细看,在水里的鹅卵石边还可以看到游弋的小鱼小虾。沿着青石板的小径,发现水坑里有类似鸡血石的石头,惊艳得很。永红脱了鞋袜下到坑里,可惜那“石壁筋”(石英石)上的红只是一种长期水浸的骗局——把石壁筋翻个边,一如山崖遗下的白骨。是什么原因让石壁筋如此红艳呢?这是一路留给我们的谜团。永红在路边摘了一个“牛郎当”(五味子),我和跃明都尝了,酸咪咪的,彻底打开了我们味蕾上的少年记忆。
山岔口的柽籽树(油茶树)疏疏的,有一人多高的样子。柽籽树的树丛中,一位老妪提着一个编织袋在拾柽籽。看得出,柽籽已经下树了,她只是在捡漏。在山里,路遇也是一种缘。没想到的是,她就是储秀庵的庙祝余群英。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还在守着储秀庵,这不正是生活中的修行吗?先前,听凤山村的查传宦老人说过,十多年前村里有四位老妪同修福慧,募捐在废墟原址上重建了储秀庵。我虽然没有见过宁慧媛等其他三位老人,但看到余群英老人躬身的背影,我觉得老人生活在乡村的边缘,她们之所以为建庵去募捐,自己倾囊而出,完全是出自她们一颗慈心,以及内心的信仰。老人们的生活态度决定了她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怎样的拮据或困顿,她们的人生词典里应该不会有“悲哀”、“绝望”这样的词汇。与老人们比照,我们之所以累,是否是我们心中负载和追求的物事太多了呢?
储秀庵面向青山,门前挺立着几棵银杏树和桂花树,边上,还有华佗庙、土地庙、杨令公庙。储秀庵的庵门是锁着的,明代诗人余绍祉为储秀庵撰写的《储秀庵碑记》不见碑影。空谷幽静,没有梵音,没有烟香,只有远远近近不绝的鸟鸣。比鸟鸣更为高远的,还有蓝蓝的天空与悠悠的白云。
在后径岭返村的路上,我问永红,说你知不知道祖上为什么把屋的堂名起为“宝德堂”呢?永红笑了笑说,祖上是做生意的,具体也没听长辈说起过,我猜想是取意“立德为宝”吧。
后径空寂,路上除了我们,应该还有过往的神灵。
山湖之外
高湖山的名字是颇有意思的,湖、山是主体,且与书院古寺重叠在一起,还那么的高耸挺立。蓝天白云之下,山水相依,绿波掩映,高湖书院在赣皖边界的高湖山上曾荡漾怎样的人文气象?高湖寺经年又有过多少善男信女的朝觐?
在没有登临之前,高湖山上的景象对于我只是个谜。尽管,我陆续读过一些有关高湖山的资料,却是想从中找寻或接近一方地理人文的捷径。“晴峦界断半边秋,雾锁山腰白浪浮。无数小峰时出没,湖光万顷点轻鸥。”(《题高湖山》宋·汪铭燕)。在如此绝美的湖光山色中,据说建于湖边的高湖寺在宋代就已备受尊崇,开始成为婺源的佛教圣地了。千百年来,高湖寺的佛在时光深处,启发、关怀以及普度了多少众生呢?
春分的前几天,有好友相邀,便有了高湖山徒步之旅。从浙源虹关转进言坑,沿着清澈的山溪溯行,到山脚的石亭才算得上登临高湖山的起始。向上,一直向上,叠起的山岭依着山势向山上延伸。一路上,既有山水冲毁的路段,也有村民烧炭留下的灰烬;既有圆木搭连的便道,亦有废弃的路亭;既有芜杂的荒草,也有杉林箬叶的遮蔽……这些,像一支支行程中的插曲,有野趣,有抒情,亦有感叹。山岭蜿蜒,绕过山梁,又向着另一座山梁半隐半现地挺进,让人不得不疑惑这样的山岭是否有尽头?
山风,引领林涛,奔放、汹涌。在山风里,登山的同伴脸上都涔着细汗,有的还甚至脱去了外套,但一个个丝毫没有影响登山的进程。徒步,行走,佛缘,岭上的人说一声,岭底的人接一句,有关行走与高湖山高湖寺的话题,也像山岭一样绕来转去。一块风化的石碑竖在山岔口,仔细辨认才知是光绪年间立的路碑:左边,上山往高湖,下岭往庄下;右边,平路往沱川,下岭往察关……我与同伴徒步的山岭,选择的恰是善男信女上山朝觐的山路。转过岔口,上山的路窄了,林也更密了,一拐一转的有十八折,岭上有腐叶,还有苔藓。路边除了针、阔叶林、灌木丛,还长有山竹、荆棘、夹竹桃、狭叶苦丁茶、冲倒山、扑翼草(肺形草)等等。崖中有泉,潺潺而淌,灵动,清冽,一个个都顾不了冰凉,俯身作揖般汲饮。或许是先前的雨雪天气,临近海拔千米的地方,地上与树上还存有积雪,岩石上挂着长长短短的冰凌。此起彼伏的雪水滴落着,嘀嗒之声悦耳,仿佛正在上演一场自然的合奏。雪后的天空湛蓝湛蓝的,是多么的明净。
淡淡的山雾里,高湖山上有一片神启般的高地。绕过杨令公庙,高湖山的陡势一下子缓了,开阔的平地上依次展开土地庙、五贤祠、龙井、高湖书院遗址,以及高湖寺,板壁的,石砌的,瓦棚的,砖墙的,以一条弧线有序地串在一起,古朴、简陋、隐蔽、寥落,藏着一种时光深处的沉静与神秘。从高湖寺、白云庵,到白云古刹,这不仅是高湖山上一个寺庙名字的更替,还是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兴衰的标记。因山而在,我还是喜欢高湖寺的初名。我进入高湖寺的大殿时,有烟香、烛火,有蒲团,却无人打坐、诵经,感受到的是一种难得的安详与清静。高湖寺大殿正中,供奉着“三世佛”(即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殿后便是观音阁,供奉着“西方三圣”(即大势至菩萨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文珠、普贤菩萨。在这充满仪式感和神圣感的地方,大殿里还躺着一块《高湖山供佛香灯田记》的断碑(大明崇祯十年丁丑岁孟秋月吉旦立),标记着寺庙在特定年月特定的公共“消费”来源与规模,让我从中读到了寺庙前经年络绎不绝的信士,还有缭绕飘逸的烟香。
一座古寺,一位守寺的老人,高湖山还有一种禅意在绵延。
记得《婺源县志》上说,高湖山的由来是:“山上有湖,宽六、七亩,四时不涸,故名”。而进山时听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说,约是二三十年前,高湖山上还是有湖的。然而,我在高湖山寻访,却只看到一眼称为“龙井”的水井,那曾经的湖光烟波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说高湖寺前砌起莲池的地方,原是久远的湖心。在干涸的莲池边,我长时间地驻足注目,似是在等待一个失踪者的音讯:那石罅中是否会有水响?那里还会有水奇迹般涌出么?
中午用餐的膳房,原是高湖书院的遗址。板壁房,泥土地,潮潮的,暗暗的,缝隙中透着光影。古寺的庙祝老吴是位热心人,餐桌上有炒白菜、炒红萝卜、炒香干、煮干豆角、煮干碗豆,还有红豆粥与素面。用餐时,我向她问起了高湖山“铁瓦禅林”的来历。相传明代正德年间,僧人明高建高湖寺时,遇大风吹走瓦片,专铸铁瓦防风,后来被人们称为“铁瓦禅林”。庙祝老吴撂下碗筷,还从床底翻出两片遗存的铁瓦。铁瓦平敞,体积有青瓦的四倍左右,虽然锈迹斑斑,却让我开了眼界——几百年的铁瓦,真的是很稀罕了。
在高湖山,通天窍、观云台、狮子石等景观,明代婺源学者余绍祉在《高湖山记》中就已记述。一篇不足八百字的文章,对高湖山的地理人文进行了全面的观照。无论是文字,还是景观,都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以及邂逅优雅的机缘与情致……在“十家之村,不废诵读”的婺源,名声在外的高湖书院也经不住时光的漫漶,遗废在历史的某个年月之中。面对书院遗址,我依然能够想象莘莘学子在高山之上,与日月山水为伴,读书听讲的虔诚,以及一心苦读济世的传奇。很多时候,高湖书院与紫阳书院、福山书院、阆山书院一同被提起。
一株千年的银杏,遭遇雷击,烧毁了躯干,根部又长出了幼株,与一株株的山茶装点着高湖山上的土坦。千年的银杏得到了重生,而湖水消失的边缘,也成了莲池。高湖寺面对迤逦的远山,是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的齐云山。迎面而来的风,凛冽、迅猛,仿佛吹到高湖山的通天窍处又有了回旋。风声里,可否有高湖书院朗朗书声与高湖寺钟磬梵音的记忆?从徒步高湖山到高湖寺,我虽然没有礼佛与布施,而我的叩访,不仅是对山湖之外的寻踪,亦是路上的一种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