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评介
2016-05-23李启军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李启军(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评介
李启军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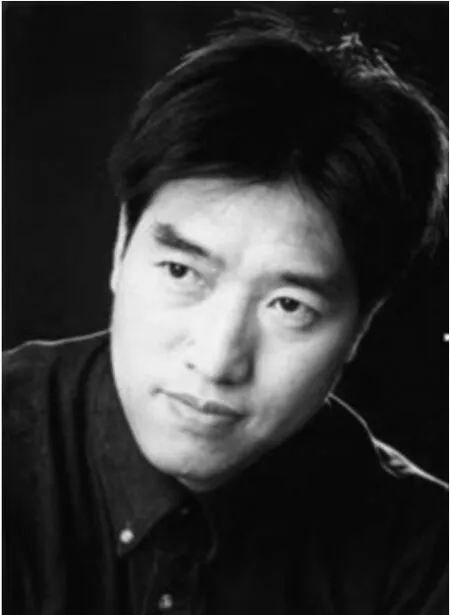
李启军近照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非常令人着迷的思想家。20世纪法国思想界人才荟萃,群星灿烂,罗兰·巴尔特无疑是最亮的思想明星之一。和那些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一样,罗兰·巴尔特属于典型的“跨界学人”,文学批评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符号学家等多种令人称羡的桂冠,罗兰·巴尔特都可以当之无愧地领受。当然,对于传媒研究来说,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最值得国内学人研究和借鉴。
一、罗兰·巴尔特符号学理论的三部重要著作
在汉语学界,近年来罗兰•巴尔特的著作得到大量译介,限于本文的主题——或者,如果我们希望以“短平快”的方式了解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著作的话,笔者认为有三部著作值得提及。
第一部是由怀宇翻译的《罗兰·巴尔特随笔选》。此书选译了巴尔特数部著作的代表性文章,堪称一部“小而全”的巴尔特散文选集。其中《埃菲尔铁塔》一文,翻译者信达雅地传达了巴尔特散文的神韵,阅读此文可以体会罗兰·巴尔特“符号学散文”的特有美感。
第二部著作是《神话:大众文化诠释》。此书是罗兰·巴尔特用符号学理论深入浅出地分析大众文化现象的操练作品。此书的好处在于,它用极为感性的方式,告诉我们如何用符号学分析各类见惯不惊的日常文化现象。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就如同在钻研武林秘籍之前,先看看武打片感受一翻“练武”的力与美,它堪称“符号学”修习的重要入门书。
第三部,也是本文要重点介绍的书,则是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要懂得符号学基本原理,有志者还需在这本“大家小书”上用功。
二、《符号学原理》的基本内容
事实上,《符号学原理》广为流传,在欧美常被作为大学教材使用。应该说在今天,它已经成为一部经典。它也为巴尔特自己的符号学分析实践提供了理论武器。巴尔特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等著作中对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的符号学分析,都是建立在《符号学原理》所阐述的理论基础上的。《符号学原理》的理论总结功能和《神话——大众文化诠释》等著作的符号学分析实践,使巴尔特赢得了“符号学大师”的崇高声望。1977年1月1日,罗兰•巴尔特是以“符号学”获得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头衔的。
简略说来,《符号学原理》主要有如下内容:
首先,它论述了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语言与言语是语言学中的基本概念,与“言语”相对的“语言”是语言之“语”,是语言活动中的制度性、系统性、约定俗成性、规范性、同一性的一面;与“语言”相对的“言语”是语言之“言”,是语言活动中的变异性、过程性、个体性、差异性、丰富性的一面。“语言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二者处在真正的辨证关系中。”[1]就是说先有“言语”行为,然后才有“语言”制度、规则的形成,但是“语言”制度、规则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规范具体的言语行为。
语言的这种“双重结构”正如同符号的“符码”与“信息”的关系,所以成为符号学的一对基本范畴。在这样的结构框架内,巴尔特具体分析了服装的意指系统(具体又分出书写服装系统、照片服装系统、实穿服装系统),膳食的意指系统,汽车、家具的意指系统中的“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同时,提出了与服装、膳食、汽车、家具这些意指系统不同的“复合系统”,“如电影、电视及广告”。但他认为它们的“意义的表达赖于图像、声音和画符的协作,因而要确定这些系统中的语言事实与言语事实的类别,时机还欠成熟”,[1]所以未进一步加以分析。
在归结这个问题时,巴尔特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符号的“契约性”与“任意性”;二是符号学系统不同于语言学系统(只有语言与言语两个层面),而具有三个层面——物质层面、语言层面、实用层面。在一些“言语”匮乏的符号系统中,“语言”需要的是“物质”而不是“言语”,如书写服装系统。这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它论述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不能把符号当成能指。能指层相当于表达层,所指层相当于内容层。巴尔特按照斯多葛派的分析,认为所指既不是“一个事物”,也不是该“事物”的“心理再现”(即概念),而是“可言物”。“因而,只能以一种近乎同语反复的方式在意指活动的过程中定义所指,即:所指是符号的使用者通过符号所指的‘某物’。这样,我们刚好又回到一个纯功能性的定义上:所指是符号的两个相关物之一,唯一使它与能指相区别的地方在于后者乃一中介物。”[1]而由于能指的实体始终是物质的(声音、物品、图像),因而可以据此将符号划分为“口语符号、书写符号、形象符号、动作符号”等。[1]
能指与所指是在意指活动中被联系起来的。只有在一个意指活动中才有能指、所指,才有符号,才有意义的生成。所以意义的生成就是符号的生成。“符号是音响、视象等的一块切面。意指(signification)则可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1]“意指(即semiosis‘符号化过程’)结合的不是单面的存在物,它并不是将两个词项聚拢,因为能指与所指各自既是词项又是关系。”[1]
巴尔特区别了符号的意义与价值。“价值不是意义。索绪尔说,价值来自于‘语言各片段的相互位置’,它甚至比意义还重要:‘一个符号包含的观念或声音物质,并没有比该符号周围的其他符号中的东西更重要。’”[1]用索绪尔的比方来说明的话,就是:把一页纸切分为几片,每一片相对于其他片都有一个价值;而每一片都有相对的正反面,这就是意义。通过切分(分节,历时)而将一个一个符号区分开来,并且使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如同纸片的正反面,共时)一体化而生成意义。
再次,它论述了符号的组合与系统(聚合)。语言各要素间的关系在两个层面展开。一个是组合(syntagme)层面。“组合是符号的一种排列,它具有空间延展性;在分节语言中,这种延展性是线形且不可逆的(即chaine parlee‘言语链’)。”[1]一个是联想(associations)层面,即“在话语(组合层面)之外,彼此之间具有某种共同性的要素在记忆中联系起来,形成由各种关系支配的集合”。[1]在言语链中,各要素实际上以在场(in praesentia)关系相联合。适用于组合的分析活动是切分。与组合层面发生的情况相反,在每个系列中,各要素以不在场(in absentia)的关系相联合。适用于联想层面的分析活动是分类。联想层面,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聚合层面。
根据雅各布森的分析,联想层面或说聚合层面、系统层面属隐喻型话语,组合层面属换喻型话语。在一个具体文本中,如果以隐喻型话语为主,就可称为隐喻型话语,以换喻型话语为主就可称为换喻型话语。俄罗斯抒情诗,浪漫主义及象征主义作品,超现实主义作品,查里·卓别林的电影(淡出淡入的镜头叠合是真正的电影隐喻手法)以替换性联想为主导,属于隐喻范畴。英雄史诗,现实主义流派的叙事,格里菲斯(Griffith)的电影(特写镜头、蒙太奇及视角变换)以组合性联想为主导,属于换喻范畴。
组合层面和聚合层面构成语言和符号的两个轴。巴尔特重点分析了属于聚合轴的各聚合项的二元对应关系,但是,是不是在所有符号系统中聚合项都是二元尚无定论。二元制仅是一种必要而又暂时的分类。巴尔特列举的对应关系——比例式的多边对应、双边对应、等价对应、不等价对应、恒定的对应、可删除的对应,在不同的符号系统中,需要分别对待。例如,交通信号系统、时装系统、影视话语系统中的情况都有所不同。
最后,它论述了符号的外延与内涵。所有意指系统都包含表达层面(plan d’expression,缩为E)和内容层面(plan de contenu,缩为C),意指行为是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R):ERC。如果从这个ERC系统延伸出第二个系统,前者变成后者的一个要素——表达层(能指)或内容层(所指),那么就形成两个既相互包含又彼此分离的意指系统。我们所理解的“话语”本身之所以是有意味的,就是因为它是内涵系统的“内涵指符”,它本身就是能指与所指结合的符号系统。但是一些学者似乎存在着将“话语”简单地理解为符号的能指组合的倾向,这是值得我们认真辨析的。
三、《符号学原理》的价值
关于《符号学原理》的价值,我们在上面已经结合内容有所论述,这里还想特别提出几点:
第一,关于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巴尔特说:“符号学乃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是具体负责话语中大的意义单位的那部分。”[1]这个观点不是对60年代初符号学发展的已有成果的“总结”,而是巴尔特自己的“标新立异”。不管怎么说,这可以引发符号学家们对符号学与语言学关系的深入思考与讨论。有意思的是在阐释学界也存在类似的分歧。加达默尔把阐释限定于语言范围内,哈贝马斯则提出质疑,认为阐释学应该深入到非语言领域。
第二,“世界进入符号系统”的论断值得重视。如果说恩斯特•卡希尔从哲学的层面论证了“人是符号的动物”,那么罗兰·巴尔特则以降服理论的姿态,以一种直觉的方式告诉人们,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符号的世界。符号活动是决定人的本质的活动,而且,我们所能真正进入的世界就是符号系统中的世界,符号系统之外的世界犹如康德的“本体界”,并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衣食住行的一切方面都是符号化的,从语言文字到非语言文字,从资本到实物。符号化的过程就是意义生成的过程。这向我们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中。
第三,元语言的转换与人文科学的发展问题。人文科学从古希腊到现在经历的三次转换正是元语言的转换,就是元语言依次从自然社会本体转到认识主体的主体性,再转到当前的语言学。将来是不是会进一步转到符号学?如此发问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人类从部落化时代进入非部落化时代,现在因大众传媒的作用又重新部落化了。部落化时代正是前语言时代,重新部落化时代也就是超语言的视觉文化时代。如果部落化时代人类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是受非语言的符号制约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想象等到完全重新部落化之后,人类会更重视非语言的符号呢?[2]
四、符号学大师的身后名
罗兰·巴尔特一生多病而忧郁,而且他还受到自身“既不想掩盖,也不想公之于众”的个人性恋取向的困扰。他生前,作为作家和批评家的身份是受到认可的,虽然这种认可以一部分人的反对为条件,但总体来说,还算生活在荣耀之中。罗兰·巴尔特的传记作家路易·让·卡尔维在《结构与符号》一书中写道:“巴尔特的真正教诲: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中。”这位专家作家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中,但我们不会解读这些符号,是“巴尔特让我们对这些符号变得敏感了”。在卡尔维看来,“巴尔特的天才在于他善于摄取周围的理论,用这些理论支持自己的直觉”。[3]显然,这样的天才风格不愁没有读者,同样,也不愁没有持反对意见的“对抗性”阅读者。
但是,生前的成就并不意味着死后的辉煌,
即使人们对辉煌有着不同的理解。卡尔维将萨特和巴尔特这两位同于1980年去世的知名人物作了比较。萨特的去世有5万人参与送葬,而到巴尔特墓地去的只有一小群人。巴尔特不参加游行,不散发传单,总之不“战斗”,但是,巴尔特“却用他那破译社会符号的方法影响了这同一代人”。[3]作为盖棺定论的评价,卡尔维这个结论是靠得住的。
当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罗兰·巴尔特是令人着迷的思想家。当我们以“符号学家”之名为这位20世纪的法国思想大师贴上标签的时候,千万不要仅仅对这位思想家的作品进行简单的“符号化”理解。事实上,巴尔特的迷人之处在于,他的作品以文学化的语言,将哲学、文学、符号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思想有机地融为一体,产生一种富有魅力的“文之悦”(the pleasure of text)阅读体验。
参考文献:
[1] 罗兰·巴尔特(法).符号学原理[M].王东亮,译.三联书店,1999:5,20,34,38-40,46,50-51,3.
[2] 李启军.无意做辩护[J].中国图书评论,2004(6):29-30.
[3] 路易·让·卡尔维(法).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M].车槿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68.
作者简介:李启军(1964—),广西资源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文化与传媒,电影符号学等。
中图分类号:G2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02-001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