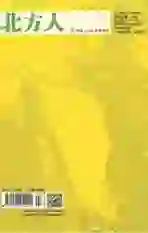精神科医生是如何炼成的
2016-05-14许智博
许智博
再过三个星期,妻子就将分娩,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住院医生付冰冰退掉了在东二环保利剧院后面租的房子,将家搬回了自己去年在通州买的房子。从那里到他工作的安定医院,无论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时间都差不多是之前的三倍,这对于早上7时就要赶到病房的他来说,意味着起床时间要提前好长一截儿。
因为高考志愿上填了“服从调剂”,付冰冰被医学院调进了刚刚成立的精神病学专业。
今年是付冰冰来到安定医院的第五年,明年初他如果通过院里的“第二次大考”,将升为主治医师。
作为中国近两万名精神科医生的一分子,在职业生涯初期,付冰冰也许还尚未像他的前辈们那样,尝尽精神科医生的人生百味。如果说精神病人是这个社会里边缘人群,那么精神科医生在医疗体系中也是对等的弱势群体。他们职业生涯与同行相比枯燥而充满风险,备受偏见,多获得的,是千奇百怪的病人和他们身后的社会万象。
“时间长了会不会得病?”
中国的精神科专业医院的前身大多都是精神病人收容所,在世俗的眼中,这里是“疯子”的聚集地,是“无法理喻”的危险空间。
安定医院的副院长李占江回忆起80年代刚工作时,他经常对陌生人掩饰自己的职业:“很多人知道我是精神科医生,甚至会问我,你们在那里待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得病?”
相比普通人看待这个职业异样的眼光,同行们的偏见可能更让精神科医生们难过。1992年临床专业毕业的姜涛被分配到安定医院时,在北京东城长大的他甚至不知道这座医院地址在哪儿。那时他有时面对大学同窗,也难于启齿自己做了精神科医生:“我们那会儿去北京市卫生局开会,主席台上点名问‘安定医院的来了吗,其他医院的医生们在底下就先会笑成一片。”
除了偏见和歧视,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待遇低同样也是让年轻的医学院学生们“躲避”精神病学专业的客观原因。付冰冰说,“谁都知道,收入上内科不如外科、精神科不如内科。”
做住院医生的第一年最苦,工作从周一到周六,早上8时到病房,名义上晚上10时下班,但写完每天的医嘱、给一些病人开完睡眠药,离开医院一般都10时30分了。晚上11时回到宿舍,洗洗涮涮,12时就得赶紧睡觉。
在安定工作满两年后,付冰冰通过了院里“第一次大考”,有了出门诊的资格。作为国内少数几个拥有三甲资格、惟一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精神专科医院,安定医院的门诊楼连大厅里天天人满为患,偶尔有患者躁狂发作,人们才会躲避、挤让着为他闪出一条路来。二楼的各个诊室门口,站在走廊里、坐长凳上排队候诊的人同样拥挤不堪,为医生送病历的护士也只能抱着牛皮纸的袋子,在人缝儿里侧身扭过。
付冰冰每周出一天抑郁门诊,与另一位同事在十平米的诊室里,平均每人要看50个号。他们将门诊的工作分为两种:为来开药的病人看病叫“刷方子”,为首次就诊的病人看病叫“写白本”。往往,付冰冰正在这边询问着病人的情况,那边就不断有着急的病人推门、探头,一些挂不上号的病人更是会径直而入,要求他给“加个号”。在每个病人4元钱的挂号费里面,医生只获得8角钱的报酬。
更多的工作时间,付冰冰是在住院楼九病区的值班。在那里,七八个年轻的医生“糗”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空间里,一人起身走动,别人就要挪动屁股下的转椅给让出一道缝儿来。像付冰冰这样的“住院医”,每个人要负责10位左右的住院病人。新病人住院当天,他们最短要用40分钟的时间,耐心向家属详细了解病人的既往病史、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再把这些情况逐字敲进电脑,存档进电子病历。有时赶在他值班时一天新来五六个病人,那就连饭都顾不上准时吃,遇到躁狂症状的病人,被抓伤也是常事儿。
与综合类医院不同,安定医院的医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中午不能外出。“因为护士在中午有一轮查房,出现情况需要医生随时处理。”付冰冰做住院医生的第三年时,按照规定去北京另外一家三甲医院内科“转科”,中午时科室主任会经常带着自己部门的人去外面吃饭,“这在安定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医生的情绪
付冰冰所在的九病区曾经有一个被“丈夫”送来治疗的女病人,住院时表现住强烈的“求关注”,每次“丈夫”探视,病情就会好转许多,“丈夫”离开,病情便急转直下。病人的情绪起伏在用药很长一段时间后仍旧没有好转,住院医生们百思不得其解。在一个探视日,一位老专家将“丈夫”单独拉进一间小屋,一番交谈后最后终于让对方放下戒备,将事情和盘托出:原来他与女病人并非真正的夫妻,而是情人关系。他真正的妻子是一名军医,从事建筑行业的他在外地承包工程时与情人产生感情,却因为军婚无法与发妻离婚,情感炽烈的情人最终变成了抑郁症,被他隐瞒关系送到了医院。
不过与病人和家属的沟通也是最让精神科医生们感到“无力”的事情。
在九病区,抑郁症病人的家属一般都属于“高情感表达”(指家属对家庭成员所表达出来的一系列特定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如过分溺爱、关心、关注、介入或过多的批评、指责),对于医生期望很高。九病区的住院医生和护士,都要准备一个讲课的PPT,每逢周二、周五的探视时间,要对探视病人的家属们反复讲解抑郁症治疗的相关知识,让他们改变对待病人的方式。
即便如此,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今年在九病区住院的一个来自农村、在北京上大学的女生,她的母亲对医生的医嘱始终不以为然,一直认为女儿之所以得抑郁症,“就是学上得太多了,就不应该读大学”。母亲的落后的观念不只无助于女儿的康复,甚至会加重她的病情。在第一次出院后不久,她就二次入院,症状从抑郁到抑郁加躁狂。
“每当看到那些对病人不理不管或发脾气的家属,我就特别想吼他们说: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个病人需要照顾吗?”付冰冰说,“我们脱掉白大褂,情感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会同情被父母不管的孩子,也会反感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病人跟我们开玩笑我们也会很高兴,郁闷时大家关起门来发发牢骚。但我们穿上白大褂,职业就要求我们收起情感好恶,眼中只能有病人,一举一动要照顾病人微妙的心理感受。”
而在八病区,许多病人因为病症的严重程度已经无法痊愈,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的家属往往表现麻木,除了病人发病时将其送到医院,便不做其他,甚至对医嘱也不以为然。比如安定医院封闭的住院病区里,明令禁止病人携带一切可以伤人或自戕的东西,但在男病区里,总会有家属在探视时给抽烟的病人悄悄塞上香烟和打火机,一到夜晚,医生总会在厕所里听到噼噼啪啪的点烟声。
“天才与疯子只有一念之隔”,精神科医生也常常因为目睹了太多的天才殒落而感叹惋惜。在付冰冰的记忆里,有一个曾被维也纳音乐学院录取的钢琴天才,因为洁癖和强迫症,总是感觉琴键很脏无法下手去弹,住院的时候,他会一遍又一遍地在厕所里重复着冲马桶、洗手。“如果不得病,他也许又是一个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