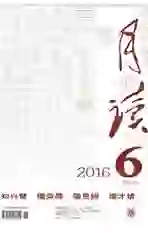东方游吟诗人屈原的浪漫之旅
2016-05-14刘晗
刘晗
2015年端午之际,中国歌唱家龚琳娜在纽约River to River音乐节上首次演唱了由屈原的《九歌》改编而来的三首歌:《云中君》《河伯》和《山鬼》。她将中国传统唱法与西方音乐元素相融合,演绎出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楚辞,可谓别有风味。从古至今,对屈原的评判从未中断过,仅汉代一个时期,从扬雄、班固对其的批判到王逸等人对他的极力推崇,可谓众说纷纭。
近代以来,文学史界对屈原的关注度只增不减:梁启超称“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肯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卓越贡献;郭沫若可谓与屈原惺惺相惜,以“现代屈原”自居,还为此投入数十年工夫,著《屈原研究》,创作历史剧《屈原》;1944年,古典文学研究学家孙次舟教授发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一文,做出了“屈原为同性恋者”的论断,引发一片哗然遭到各方质疑的同时,也得到学者闻一多、朱自清的力挺。进入当代,学界薪火相传,对楚辞文化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从文学、社会学等维度,对屈原的人格、文辞、政治主张做全方位的解读。
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的汤洪所著《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另辟蹊径,将对屈原的研究置于跨文化背景之下,梳理屈辞所涉及的古地理词语,同时借助对先秦汉初典籍与屈辞相关同类地名的考据,挖掘屈原创作心路历程以及文本的内在意蕴。
作为东方的游吟诗人,屈原卓尔不群,将视觉拓展到广袤的西方,屈辞赋比兴巧妙结合,句式灵活多变,以一唱三叹的方式展现其蜿蜒曲折的人生旅程。屈原一生,经历了两次流放,分别为汉北和南方地区,依据《九章·哀郢》的描述,他从郢都出发,顺江而下经过夏首,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离开夏浦,到达陵阳。于是,屈辞中出现了大量现实或者虚构的地名,既有“昆仑”“流沙”“赤水”“西海”等确实存在的域外地望,也有诸如“瑶台”“九天”“九坑”等具有神话意味的地名。作者认为,对屈辞域外地名的探索,既是对屈原浪漫主义游历之旅的地理追踪,同时也应在现实与神话的虚实相间之中,给予地理版图较准确的定位。如《离骚》中有“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余……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据汤洪的考据分析,屈原从苍梧启程到达“昆仑”(今阿拉拉特山)之“悬圃”(比喻神话“昆仑”大山的通天高境,亦与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有某种联系),又从“白水”(代指昆仑)出发抵达西极(大地极西之地),沿途经过阿拉伯沙漠的“流沙”、红海“赤水”、东非大裂谷“不周”,最终抵达大西洋“西海”福田仙境。
不仅如此,《九章·涉江》中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天问》中亦有“昆仑悬圃,其尻安在?”可见,“昆仑”二字以及与其相似的语汇曾多次出现在屈原的语境中,兼有地域与神话等多重含义:楚人之祖先颛顼最早来源于昆仑,《淮南子》《山海经》中就有不少以昆仑为母题的神话,其中一些篇章恰恰出自楚人之手。屈原身处楚地巫文化之中,难免被此种氛围所感染,对原始巫祭文化神秘气息的探究塑造了他超越世俗、独立不迁的人格。也正是出于此,楚地文化赋予他刚正不阿的性格,对于故乡情感之浓烈难以言喻,即便政权沦丧,也不离不弃。作者身陷绝境之际,力求在虚构的神性中寻找答案。“昆仑”是屈原视为神明一般供奉朝拜的对象,在“人神”对话中寻找慰藉,因此,“昆仑”也可视为他诗意的栖息地所在。然而,当信仰遭受危机,思想体系中缺乏一个神的在场,巍峨“昆仑”的意象,则可弥补神在其视觉和想象中的缺失,同时也是终极彼岸的象征,如谶语那般暗示决绝的宿命性结局。
当然,从地理位置或是文化层次上考量,屈原是否真正涉足天山地带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屈原抱有的西域情怀,形成了其独特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流放虽悲怆感伤,也在精神世界的追问和思索中,幻化为笔墨间的浪漫之旅。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从屈辞的地名中发现了域外文化的浓烈气息,这对于我们探求上古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