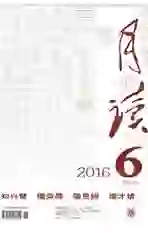中国书的三期变化
2016-05-14金克木
金克木
中国书面貌的三期变化,都由书的生产方法不同而来。这既和社会生产力有关,又和文化的发展同步进行,交互影响。虽可分期,但在后期中前期面貌并未绝迹。这三期是:雕刻时期、抄写时期、印刷时期。
第一时期
第一时期的书是刻出来的。泥版不算书,甲骨和竹简是刻上字的;钟鼎文(青铜器上的文字)是铸出来的,模子上的字和花纹是刻出来的。后来刻在石头上,例如石鼓文和泰山刻石以及石经和许多碑文,到现在也还有刻石碑的。这种雕刻的书一次完成,垂之久远。碑上文字可以拓下来,也可以翻刻,这是以后的事。竹简的书可以装订,把一些“篇”或“册”用皮带捆起来,也可以一遍又一遍刻下去,这才是书的开始。这种刻书情况外国也有。中国傣族现在还在树叶上刻经书,像印度人、缅甸人一样。
这种生产书的情况不仅决定了书的面貌,而且对文化有很大影响。
首先是在文字上,使汉字固定下来,发展起来。因为这种字体将形声符号合一,兼有艺术性,又不占大地方,虽刻起来繁难一点,但这时的书很少再版,只为保存,不为流通,所以好处大于坏处。别的国家刻在石上的文字是拼音的,不以形为主,占的地方也大些。
第二个影响是在文体上。因刻书很麻烦,只有在必要时才用,而且字不能多,必不可少的字才刻上去,这样就出现了书上的文体。这一时期,书面体和口语体分开各自发展。书面体不顾各地音变,可以通行,于是固定下来,发展起来。
第三个影响是在文化上。因为这种书不是为流通的,所以为流通的文化就依靠书以外的途径传播,靠音乐、舞蹈和口头语言。诗歌就是这三者的结合,诗文分家也开始于这一点。礼乐是这种非书本文化的表现,所以有“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和“礼失求诸野”等等说法。由于发展出一种通行口语,诗歌成为不同地区方言之间的交际通讯工具,所以说:“不学诗,无以言。”这一时期中,硬性的沉重的书很少,见得到的人不多,流通范围小,谈不上传播。口头的“书”(乐、舞、诗)是为了当时人交际互通信息,是社会性的。有些口头的书到汉代都变成了写下的书,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口头的书——《乐府》。文化中的这种分化后又合流、合流后又分化的情况在书中也有表现。改了文体也看得出不同层次。
竹木简出现,帛出现,毛笔出现,书的复制和再版容易了,不少口头的书转化为书面的,文章变长,流通范围扩大,发生了传播问题,于是向第二时期过渡。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东周时代,生产和交通大发展,战争和贸易都重用车辆,国家以千乘车、万乘车表示大小。中国广大地区内的不同文化接触频繁,信息传播空前活跃,大统一的要求和趋势日益明显,于是归结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代大统一。大统一的政治出于大统一的经济要求,促进了复杂的文化传播。为了维持当时大统一所必需的金字塔式专制政治系统,必须有相符合的文化传播政策。这就是由荀卿的弟子李斯提出,秦始皇批准实行的一系列文化措施。
第二时期
第二时期的书是抄写的。从秦汉起书写代替雕刻,不但文字由篆变隶,文体由简变繁,而且简册和口头传闻都被大加整理。几乎所有的秦以前文献除金石的以外(甲骨已埋没),都通过汉(代)人之手而传下来。用纸和毛笔较以前用刀镌刻便利,容易复制和传播。到隋唐时文化已大大普及,读书不是算“五车”简册而是要“破万卷”了。从汉代的古籍整理到唐代的“定稿”(石经),书都是传抄的。抄书的影响之广大和复杂一言难尽。例如,书法艺术由晋唐大发展就是一例。
第三时期
第三时期的书是印刷的。晚唐五代,刻板印书兴起。还是刻书,但刻一次就可印刷许多次,与抄写的传播速度不可同日而语。从此书以木板印刷,直到清末的石印和铅印。当然刻石碑和抄书仍然继续,并未断绝。
文化传播工具现代化后又大有变化,书籍文献与前大不相同。文化传播不仅靠文字而且靠声音和形象,极大地扩大了从前的乐舞作用。在现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读书对印刷时期也许还不难了解,对抄写时期就有些模糊,对雕刻时期的情况恐怕会觉得难以捉摸而时常忘怀了。实际上,今天读书,对秦以前文献(除甲骨金石以外)不能不时刻记住汉代的文化“变压器”,对五代以前的文献不能忘了宋代以来木板印刷的改变。忘了从雕刻到抄写又到印刷的变化,至少对于文献的亡逸和流传以及著作体裁的发展就会理解不完全。抄书和印书在文化传播中作用复杂。有的印本书不传(例如清代《闱墨》,即科举考卷),有的抄本书广传(例如小说、戏曲),《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抄而不印。清末民初的石印抄本对于文化传播有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那么多“刀头本子”蝇头小字的小说,吴友如的《点石斋画报》以及《格致书院课艺》《富强斋丛书》。许多碑帖拓本都是石印的。“油印”出现后,各方所受影响,从讲义和文牍到地下刊物,至今未绝。若不注意书的面貌,恐怕难于全面解说文化。
书的生产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刻金石竹木时期,书不多,没有“博览”问题。抄写时期,大概能读一万“卷”纸帛就很“博”了。五代以后,一万册印出的书比一万卷多几倍,很难“博”了。现在又加上外国图书和报刊,数学家也未必能读全各个数学领域的书,其他更不用说了。那么在当今的文化传播条件下,还要像从前那样一本一本地读,只怕是万册未完,头发将白,连杂志也看不过来了。怎么办?也许可以说书在今日已到了又一大变化的前夕,要“博览群书”单用老一套方法恐怕不
行了。
(选自《文化卮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