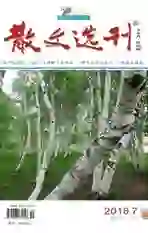老师,感恩有您
2016-05-14田爱祯
田爱祯
老师是我高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他课讲得好,对学生负责。在那动乱年代,就是他那句“吃饭饱腹一餐,学知识受用一生”的告诫拴住了中学生的懵懂。
还是先说那个自命题作文吧。当时,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就用“犁把手”这个题目,写了一个女知青用耕牛学犁地的事。交了作文的第二天自习课时,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打开我的作文,用指头敲着“犁把手”,一脸严肃地问:是抄的吗?有参考吗?真有此事吗?……一连串的问号如同炸在耳边的爆竹,我一下蒙了,傻了,像挨了耳光,脸火辣辣的。难道作文里写了什么错误观点、反动言论?我慌乱地回忆着作文里的字句,双手交替搓着四指。双眼直直地看着老师,连话也不会说了。看见我一问一摇头,满脸的惶恐与迷茫,老师笑了。顺手翻到作文末页,把自己几乎写了一页的批语念了一遍。合上作文,老师又说了十个字:基础不错,好好学,好好写。话语里透出的欣赏与慈爱,如同冬日的阳光,暖了我一生跋涉。
又一节作文课上,老师评讲了“犁把手”。
斗转星移,高考的恢复唤醒了很多人被搁置的梦。而对于我这个“回乡青年”来说,“上大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童话。于是,带着闹着玩(没有任何复习)的心情参加了1977年高考。做梦也没想到,我竟考了238分,远远超过了本省两大名校的录取线。终因报考志愿的“闹着玩”(省内学校一个没报)而滑档。我觉得考而不中太丢人,决计再也不提什么高考的事。就在临近1979年高考的时候,老师从县城传来口信,让我去复习。当时离高考只有两个月,别说我没有这个心气,就是想参加也晚了。看我没行动,老师又接连捎信打电话。我给老师说:“太晚了,人家都复习一年了,我现在再去……”老师说:“复习一年怕啥?现在是混水的多,拿鱼的少。爱祯啊,你如果不参加高考可惜了。”听得出老师的伤感和惋惜,我心里酸酸的。我知道,老师说的什么混水拿鱼是在为我走进考场长力打气,鼓励中掺杂了太多不舍的成分。这哪是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分明是父亲对女儿前途担忧的忐忑和不忍!
不知是为了安慰老师的忐忑,还是自己骨子里的不屈,我终于在复习班已停止讲课的时候,站上了备考的桥头。悬梁刺股的50多天让我背完了政史地三本1000多页的复习资料。就是这“1000多页”让我考过大专录取线(247分)。加上放弃复习的语文(61分)数学(17分),我以325分的成绩名列全县高考(文科)第二名——后来听说那个第一名的考生因其他原因被取消录取资格。尽管报考院校的不理想,但毕竟接通了改写人生的气场。现在想来,不是老师的再三坚持,不知道命运的小船会在哪里搁浅。
转眼间,我毕业了。咋也没想到,见习期刚满,就被组织部门以“选拔”有学历的年轻干部为由调任团县委书记。这在别人眼里如同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在我却是如芒在背、如堕云里雾中的茫然无措。“书记”如同一桌从没见过的宴席,我不知道从哪里动筷,从何处下嘴。工作中的胆怯怵场和周围的明争暗斗像两只无形的大手,把我撕扯得不知所以。面对做事的原则和做人的底线,我不会也不想为平衡周围的争斗违心、盲从。就是这种“不会和不想”成了我性格中的硬伤——加上对某些潜规则的不谙,错过了一次次的与人比肩。每每至此,不免神伤难过,更有朋友为我不平。而老师却说:爱祯,咱不难过。我们只讲耕耘,不讲收获。努力做事、磊落做人是我们的本分……是啊,耕耘在已,收获在天。何必为自己的不可掌控而自虐?可说归说,见了老师,眼泪就是止不住。如同儿时在外受了委屈,见到父母时无需任何掩饰的哭诉放纵。
是的,从考大学那时起,老师在我心中已等同再造——当然,我也成了他牵肠挂肚的“编外”女儿。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疼惜的标准就是竭尽所能供我读书,让我衣食无忧。而老师操心的则是让我学习更多的知识,为走向社会、打点生活储粮备份。上学时一再告诫我:不要因拿到“铁饭碗”而满足“60分”,真才实学既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社会认可的筹码。毕业分配时,老师放下他的“从不求人”,不厌其烦地找教育局领导,推介我的“优点长处”。或许就是老师的“推介”,让我走上了“从政”之路。至于得失,现在已无须答案。但我感恩老师想让我到一个好的发展平台的初衷。
说到感恩,对老师的孝敬如同对待父母一样,是我一生不敢动摇的信仰。“常回家看看”更是我对老师“遵守”的习惯。逢年过节如我不能按老师预想的“女儿回娘家”的时间去看他,他就会打电话问:“家里有啥事?咋没过来?”语气里的嗔怪与不安,说得我心暖暖的。几十年来,不管生活拮据与否,父母有的,老师师母都有,父母没有的,老师师母也有。
我记得,一是二十多年前邀请在城里工作的高中同学给老师庆祝66岁生日。二是前年给不能自理的师母购置轮椅。当老师看到昔日教鞭下的孩子向他深深鞠躬,并祝他“生日快乐”的时候;当看到90多岁的师母为坐上轮椅可以出去“走走”而开心的时候,激动得热泪盈眶,好大会儿都没说出一句话。我知道,老师的“无语凝噎”是既心疼我的“花钱劳神”,更感怀我对他老人家堪比生身的“结草衔环”。正如老师所说,我既没有给过父亲生日的“隆重”,也没有给因摔断股骨头而不能直立行走的母亲购置轮椅——让人心酸与愧疚的是那个叫作 “力所能与力所不能”的说辞。或许就是父母的辞世(十几二十年前)让我备尝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伤怀与遗憾,才更加珍惜我对老师的孝道。
我忽然觉得,我是幸福的。
责任编辑:刘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