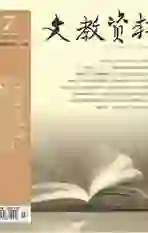治疗与救赎
2016-05-14赵晨
赵晨
爱伦·坡以精巧的叙述手法和瑰奇的想象力而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哥特式恐怖小说更是以出色的氛围渲染和深邃的心理描写而著称,这些都要归因于他那独具一格的美学思想和理念。他认为,应当通过各种逼真的手法“扣住读者的心弦”,进而达到最激动人心的效果。坡着重强调“效果的统一和完整”,要以效果框定作品的内容和模式, 力图使故事中的每一件事、每一细节,甚至是一字一句都为预想的效果服务[1]。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创作者就需要选择合适的题材。在《创作哲学》一文中,坡提出,死亡是最悲郁的主题,而当其与美结合得最紧密的时候最富诗意,因此“美女之死无疑是天下最富诗意的主题。而且同样不可置疑的是,最适合讲述这种主题的人就是一个痛失佳人的多情男子”[2]。许多学者认为,爱伦·坡对这一主题的迷恋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自身经历有关,因为在他一生中曾遭遇过多位女性亲人的死亡,而这些亲人的死亡都是由当时所流行的疾病造成的。
由于对疾病传播缺乏认识和医疗手段的落后,爱伦·坡所生活的19世纪前半叶正是各种疾病肆虐的时代。特别是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作为新兴的工业中心,在城市化急剧发展的同时,人们的居住环境未能及时得到改善,导致各种流行疾病频发,如霍乱、肺结核、流感等。城市成为疾病滋生和蔓延的温床,尤其是在波士顿、费城、纽约等海港城市,数以万计的人口因病死亡。大半生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爱伦·坡不仅对此情况有所目睹,而且是其受害者,他的生母、养母和妻子曾先后死于肺结核,另外还有研究认为爱伦·坡本人可能也是肺结核等疾病的患者。
肺结核也叫痨病,在19世纪被称作“白色瘟疫”,患病者通常面色苍白,身体消瘦,咳嗽阵阵,致死率非常高。然而,这样一种可怕的疾病却被人们赋予浪漫化的想象,“它被认为是一种有启迪作用的、优雅的病。”[3]16桑塔格认为,肺结核所导致的死亡被浪漫派赋予了道德色彩,使死亡得到了美化,因为是一种体面的疾病,是“爱情病的一种变体”,“结核病人是一个被热性‘消耗的人”。[3]20对于艺术家和诗人来说,肺结核被认为是创造力的源泉,同时也被寄予了美的想象。“结核病是艺术家的病”,根据桑塔格的记载,患结核病的梭罗曾写道:“死亡与疾病常常是美丽的,如……痨病产生的热晕”,而拜伦则对友人说:“我宁愿死于痨病”,因为那样会显得美丽。[3]31结核病作为一种美丽、优雅的象征,其隐喻意义在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的诸多作家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作为美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爱伦·坡的一生与结核病也有着令人难以忽视的联系。
在爱伦·坡的幼年时期,其母伊丽莎白·坡就深受肺结核折磨,早早撒手人寰。在1835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坡提到了父母早逝对于自己的影响,并认为父母之爱的缺失是其一生中最沉重的磨难。特别是母爱的困乏,使坡对于年长的女性有较强的亲密感。坡曾倾慕一位同学的母亲简·斯坦纳德,后来将其描写为“我心灵第一个纯理想的爱”,并将其作为《致海伦》一诗的灵感来源。然而,斯坦纳德夫人不久便死于与坡生母相同的疾病——肺结核。后来,非常疼爱坡的养母爱伦夫人和坡所深爱的妻子弗吉尼亚也先后死于肺结核。这些惨痛的经历对坡的心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也影响了他的美学理念。坡成了“最适合讲述这种主题的人”,而“美女之死”这一题材和结核病的影响也在坡的诸多作品中得以体现,如《厄舍府的倒塌》、《贝蕾妮丝》、《莫雷娜》和《丽姬娅》等。在他的这一系列哥特式短篇小说中,《丽姬娅》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篇,后来坡也称此篇为“我写过最好的小说”[4]。
在《丽姬娅》开篇,叙述者“我”回忆与丽姬娅相遇时,竟记不得时间、地点与相遇的过程,甚至连其姓氏都不知晓,这些足以突出丽姬娅形象之完美,以至于其他信息都可以忽略掉了。丽姬娅有着“超越天堂或人间的无双之美——就是土耳其神话中天国玉女的绝世之美”①,虽然“要描绘出她的端庄、她的安详、她的风姿,或是她轻盈袅娜的步态,那我的任何努力都将是徒劳”,但坡还是不吝笔墨,动用了大量篇幅来塑造这位气质脱俗的美丽女子,对她的身材、步态、脸庞、额头、皮肤、头发、鼻子、嘴唇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她“身段颀长,略显纤弱”,有着“轻盈袅娜的步态”,“低低的、甜甜的嗓音说出音乐般的话语”,而“说到她美丽的脸庞,普天下没一个少女能与之相比”;她的额顶“高洁而苍白”,肌肤“象牙般纯净”,天庭“宽阔而恬静”,秀发“乌黑、油亮、浓密而自然卷曲”,有着“优雅的鼻子”和“可爱的嘴”,“那真是天地间登峰造极的杰作”。除此之外,坡还对丽姬娅那无可比拟的眼睛进行了着重描写,“那双眼睛的颜色是纯然的乌黑,眼睛上盖着又黑又长的睫毛。两道略显参差的眉毛也墨黑如黛”,散发着“灿烂的光芒”,甚至在后来患病时还闪烁出一种“太辉煌的火焰”。除了其无与伦比的美貌与气质外,“我”还为丽姬娅广博的学识所折服,甚至认为“没有了丽姬娅,我不过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孩子”,这不难令人联想到爱伦·坡对于女性的依赖心理。而实际上,丽姬娅可以视为爱伦·坡心目中理想女性形象的具体化,否则很难解释为何坡要花费如此篇幅描述丽姬娅之美丽绝伦。
然而,这样一位堪称完美的女性却也逃不过病魔的吞噬,“丽姬娅病了”,她“苍白的手指呈现出透着死亡气息的颜色;哪怕最柔和的一点感情波动,那高洁额顶的缕缕青筋也会激烈地起伏”,“她的声音变得更加柔和”。虽然文中并未明确交代丽姬娅所患为何病症,但从症状表现来看,丽姬娅患的正是肺结核病。这样的安排或许是爱伦·坡有意为之,也许是下意识地把自身经历融入创作之中。在这里,“我”所深深爱慕的丽姬娅仿佛是作者所深爱的诸多逝去亲人的化身。患病的丽姬娅不仅体现出坡所钟情的“美女之死”主题,而且符合浪漫主义文学中对于结核病的想象:苍白、脆弱中蕴含着美丽与优雅,是病态美的化身。垂危之际的丽姬娅要求“我”诵读一首诗歌,读完后“丽姬娅挣扎着站起身来,高高地伸出痉挛的双臂,用微弱的声音呼喊着”“凡无意志薄弱之缺陷者,既不降服于天使,也不屈服于死神”等句,仿佛是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抒发自己对天道不仁、命运不公的愤懑和不屈的抗争。
最终,丽姬娅死去了,正如现实中作者的亲人被结核病所夺去生命一样,故事的叙述者“我”感到悲痛欲绝,远走他乡,流落到英格兰的荒野,与小说的另一位女主人公罗维娜小姐结了婚。不过作者却并没有像对丽姬娅一样对罗维娜的样貌大加笔墨,而是对新房不厌其烦地进行描述,突出其可怖、诡异的氛围,为后来的“借尸还魂”埋下伏笔。“我”对于罗维娜不但没有感情,反而嫌恶起来,同时更加思念丽姬娅,而罗维娜却病了。在描写因病而显得憔悴、孱弱的罗维娜时,作者依然没有交代病因,但从“弥漫在她脸上的那一层死一般的苍白”和“眼睑周围那些微陷的细小血管,一股微弱的、淡淡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红潮正在泛起”等处描写来看,这仍是肺结核的症状。在服用鸦片所产生的兴奋中,主人公“我”所描述的情景亦真亦幻,随着罗维娜的死去,丽姬娅最终得以“复活”,而其重生的证明仍旧是“这双圆圆的、乌黑的、目光热切的眼睛”。
在《丽姬娅》发表后不到十年,爱伦·坡的妻子弗吉尼亚也因肺结核离世,与小说不同,现实中死去的人是无法“还魂”的。坡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两年也离开人世。对于坡而言,残酷的命运令他贫病交加,精神压抑,而所爱的人先后离去,更使他的一生显得孤独而绝望。然而,坡却一再在《丽姬娅》等一系列作品中描写带给他巨大痛苦的肺结核病,重现爱人患病、死亡的悲惨场景,也许正是为了达到他所要追求的艺术效果,通过渲染恐怖、惊悚的气氛,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而且,爱伦·坡对丽姬娅患病直至死亡的描写,与文学中对疾病特别是结核病的浪漫主义审美不谋而合,同时也契合了他所钟爱的主题“美女之死”。
此外,爱伦·坡在《丽姬娅》中对于疾病和死亡的书写可以视为一种自我治疗的手段。尼采认为,悲剧艺术能够帮助人们克服生存的恐惧和虚无,获得生命的超脱,“艺术是人类所了解的人生的最高使命及其正确的超脱活动”[5]。而艺术作品中的恐怖、痛苦和荒诞也有异于日常生活中的恐怖、痛苦和荒诞,它可以在艺术加工下形成一种完美,从而激起人的美感与热情,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和洗礼。许多文学批评家曾指出,悲剧的痛苦具有解救人和净化人的作用;诺思洛普·弗莱在《文学的疗效》一文中提到文学及其他艺术具有的巨大的助人康复作用。他发现,“在文学艺术具有疗效的整个范围内”,“最佳词语按最理想排列就能以许多方式对人体产生作用”,并认为“小说情节能产生一种中和、抵消错乱的力量”[6]。其实,爱伦·坡在创作《丽姬娅》的同时,也是在对自己悲惨而痛苦的人生经历进行审美和诗意的加工和改造,与残酷的现实区分开来,从而抚平内心淤积的哀伤与愤懑,实现情感的慰藉,在艺术的领域里实现自我救赎与治愈。所以,在小说中,爱人丽姬娅在“我”的反复思念中终于复活了。
尽管小说中的“我”并非作者本身,但从“我”对丽姬娅的苦苦思念中,却能感受到作者对于逝去亲人的恋恋不舍。其中不仅寄托了作者对于逝去亲人的哀思,而且体现出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尽管这种愿望实现的场景是那么的可怖。在爱伦·坡笔下,丽姬娅不仅是他那些逝去爱人的化身,更是一种强大而永恒的精神力量。正如小说中所言,“她对死神的顽强抵抗和拼命挣扎之场景决非笔墨所能描绘”。她有着无与伦比的美貌与智慧,象征着能够战胜疾病、超越死亡,永恒存在的美丽。在丽姬娅身上,爱伦·坡实现了与逝去亲人和爱人的团聚,在精神上超越了生与死的界限,实现了自我救赎。同时,通过《丽姬娅》等作品,坡的独特美学风格和理念也得到了充分诠释,实现了艺术上的不朽。
注释:
①文中译文均取自曹明伦译《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一书第307-323页。
参考文献:
[1]朱振武.爱伦·坡的效果美学论略.外国文学评论,2007(03).
[2]爱伦·坡,著.曹明伦,译.爱伦·坡精品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661-674.
[3]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爱伦·坡,著.奎恩,编,曹明伦译.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468.
[5]尼采,著.王岳川,编.周国平,译.尼采文集·悲剧的诞生.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4.
[6]诺思洛普·弗莱.文学的疗效.通俗文学评论,1998(2)西方学者文化研究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