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二题
2016-05-14曾哲
曾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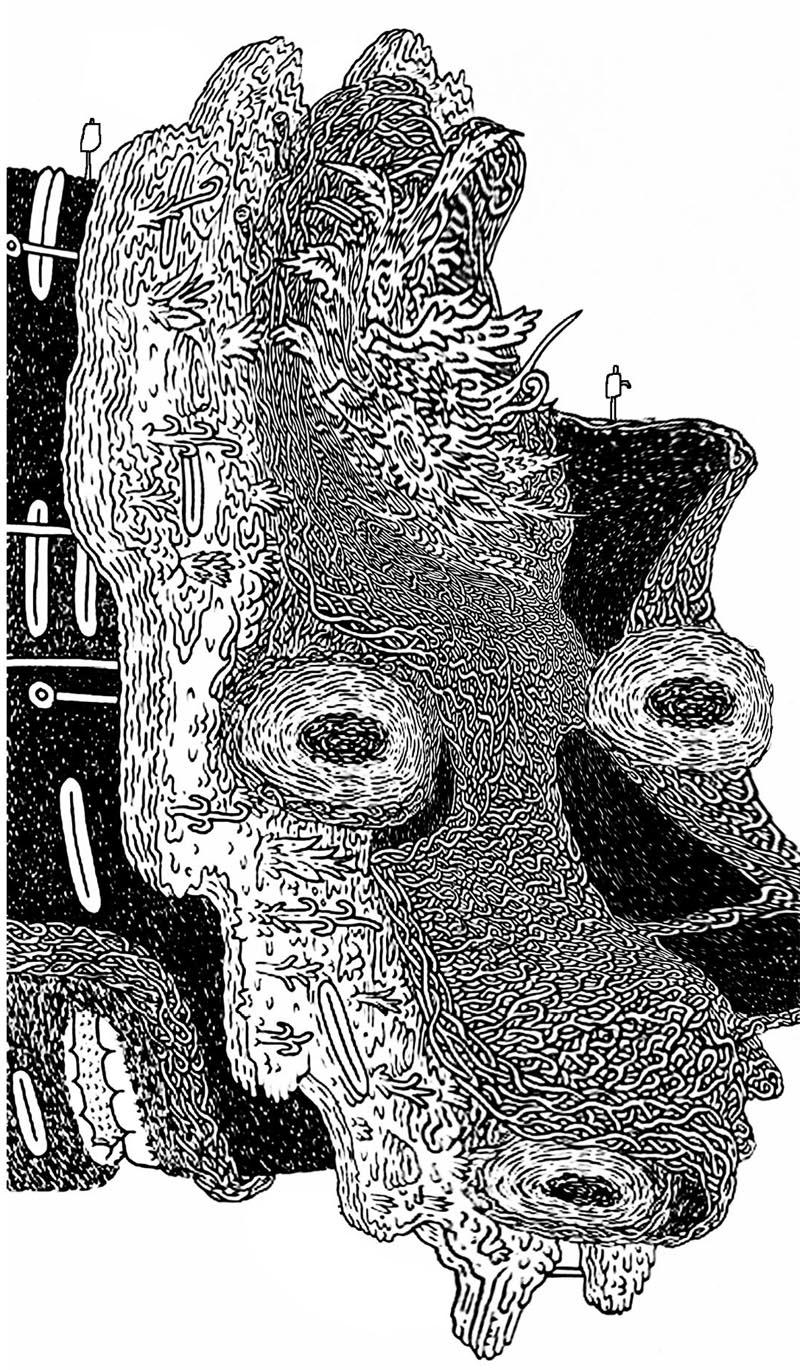
不折不扣之跌倒阳光·江措
我终于被击落,是在一个夜晚。
喜玛拉雅强寒的气流,把这块平坦的石滩,速冻成铁紫色。洁白成群的鸽子,急匆匆地在上边啄食,如同河面上跳动着阳光。眼睛被刺痛,关上窗户。
我借住在歌舞团的宿舍,整个房间只有一扇向南的窗子。糨糊的报纸焦黄干脆,是文革时代的檄羽。朗读铿锵,红潮涌动。过后,屋中骤冷。哆嗦着挑开炉盖,灰烬苍白,龟缩着叹息。昨天在狮泉河滩上走了十来里地,捡来半麻袋弯曲的老根枯枝。一古脑,全塞进去。柴火,仅仅欢呼了十几分钟。刹那的温暖,也是福乐。我常常追寻短暂的愉悦,以陪伴长久的凄凉。
我穿上棉大衣,再裹紧羊皮袄。以此形象,等待车子上路的消息。数日后,一个高兴的清晨,有邮车,三四天可抵达措勤。然后再转另一邮车,同样时间就到日喀则。
喝了碗酥油茶,我急脚急,从河滩上了狮泉河大桥。水中有大块大块的冰凌子,磨蹭着咯吱吱顺流西去。那边一片天地,更加亮丽。爬上车厢,看东天,影壁一样阴沉。直到下午,邮车才颠着一车兜子人(邮件包裹极少)出发了。
我肚子空空,咕咕了一阵安静下来。后车厢里十六人,除我之外都是藏族。十几个人就有七八条枪,短的不算。还有装红外线瞄准器的,漆夜中瞄百十米处的目标极清楚。
车在高山间的谷地草滩里爬行,路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天忽阴忽晴,阳光忽有忽无。
休息时,人们在草滩煮茶。带的还挺齐全,牛粪、锅、碗、青稞面、肉干。我几次想过去要点吃喝,腿脚挪不开步。
转了转,爬上车帮。有个藏族小老头,蜷缩在角落。
吃饱喝足的诸位,收拾好家什,每人从粪火灰中,捡出烤热的卵石焐进怀。上车后再钻进大口袋似的羊皮套中,四角帽捋下来躺倒。那个舒服劲儿,暴风雪都碰不到他们毫毛。
刚开车,藏族小老头呻吟起来。捂着下身,痛苦地团紧四肢。帽子掉下,灰发茬的小脑袋冒着热气。他抬起脸看看车厢里的人看看天。嘴里念叨着什么,一脸的汗水。我挤过去询问。他会汉话:刚才遇到年神了。我不懂:年神?把你弄成这样?他答:刚才去山口屙尿,屙到半截碰上的。我不明白。夺过他手中的皮帽子,给他戴上捂严。他说:受到年神的惩罚啦。年神把风和阳光,吹进了我的鸡巴。哎哟,山口是不能撒尿的。哎哟,疼死我,都想把它割掉。说着一把抓住我腰间的藏刀。我掰开他的手,从屁股下的背囊抽出药包:让我看看,给你选点药。
他比划了粗度和长度说:肿这大!掏不出来。
那么大? 怎么可能? 他见我摇头,挣扎着站起。车上的男男女女,都转过头来挤凑着看。他撩开袍子,脱下羊皮裤。
男人唏嘘,女人吐出舌头。
他的阴茎肿大,好似三岁嘎娃的胳膊,鲜红泛亮。
他服了止痛片,抱膝一个多小时后,全身才松弛,躺倒呜呜地哭泣着。在后来的聊天中,我才知道他是青海察尔汗的牧民。五年前,杀了骗他老婆睡觉的牧场书记。一刀毙命,像宰了一只羊。跑到阿里,在狮泉河以筛沙子为生。有汉名,姓黄。他乡数载记挂老母亲,这次回去探望。
说起命案,他脸上露出凶气。开始因为女人,但后来就完全是男人的事了。又说,女人是河,女人是草滩,女人是阳光,女人是奔腾的血,为女人值……老黄,张望着扬起灰尘的公路。
车子突然刹住。西边不远处有几群黄羊,十几只一堆儿。这畜牲挺怪,见车子停下,它们也愣神不跑了。
一个汉子摘下皮帽,托起半自动步枪,娴熟地打开保险瞄了瞄。乌黑的发辫盘在头上,岩石一样。啪!一声枪响,黄羊群里像掉进炸弹。四散逃命,但很快又聚拢。
没打着。“真臭!”我顺嘴说了一句。
汉子龇着一口白牙,愣着。我赶紧让黄老头翻译:他是不想伤害生灵!放一枪吓唬吓唬。
“球!龟儿子不想。打两只路上可以烧着吃。”黄老头转译过来。那人把枪架在槽帮,用白眼翻着我。黄老头解释:这黄羊被保护的时间太长,繁衍神速。开始和家畜争抢草场,牛羊都没得吃了。政府允许,打一些为了平衡。我得少说话,可不敢惹事。
车停下。啪!汉子又一枪,还是没打着。
我的手痒痒了,忍不住地摇起头来。当年我在五建公司当武装民兵时,百米无依托,五发,打了四十三环。
黄老头向车上的人们一吹我,那汉子把枪递过来。做了个,一枪一只的手势。“擎好吧!” 我接住枪掂掂,品相不错。
车再停时,相距黄羊群也就百十来米,我觉得差不多。那个汉子拍拍驾驶室楼顶,发动机就熄掉火。他又向人们说了一通藏话,大家就都灰着脸看我。我有点不自在。
黄羊一直注视着我们似乎在说:有本事追啊。大有以静制动的丈夫气。殊不知,自己已暴露在残忍黑洞洞的枪口下。
高原上的草滩宁静,只有阳光掉落的声音。
压住气,瞄。给他们露一手。然后搞熟关系,弄碗茶喝分口肉吃。啪!枪一响,我心就凉了。羊儿们,四散奔逃。
好几个人嗤之以鼻,一副嘲笑的面孔。当我沮丧地把枪交出去时,那汉子又推回来。
黄老头告诉我:谁也不能百发百中!他说的。
大度。好!我咬着下唇,冲汉子点点头。黄老头又说:他还有个条件,再打不着,就把你扔下车。卡车好像也这意思,追了一段路停下。我犹豫着想罢手,可缴枪也太丢人啦。
屏住呼吸,啪!这回打中了,我认定。可生灵没有倒下的,四处奔逃。只有我瞄的那只好像被吓傻,一动不动。又没戏,赌输了我下车。正当我跨出腿时,见那只黄羊突然趴在地上。
打到啦!几个人站起喊着。我跳下车,向草滩里跑去。
子弹穿透它的肚子,血水淹没一片枯黄的草,阳光红艳艳。两只不瞑的眼睛怒瞪着我,圆圆的肚子还在喘息。是头大公羊,尖硬双角残缺,想来也是一个好斗者。
我抬头看看,明亮灿烂的公路很远。那辆卡车,小得像个火柴盒子。突然,有远离人间的感觉。想起黄老头的话,这方圆百十公里无人烟。心中一阵恐慌。
有生命远去的脚步,在一寸来高的枯草梢掠过,向缓缓的金色山坡上走去。假如我没打着输了,一个人非死在这不可。
把黄羊连拖带背弄到车前,我已是气喘吁吁。
一路屠杀。几十里过后,车厢尾部已经躺了七只。
这经历说明不了什么,后边的故事才英勇。
我到了拉萨,川藏路塌方一百多公里,无法去成都。一呆就是半个月,串门喝酒睡大觉。烦死啦!友人来劝:去舞厅玩玩吧!不会跳,没兴趣。 散散心,听听歌。我答应,门口见!
晚饭马马虎虎吃过,就去了。约好的哥们儿,过了钟点没来。我只好先进去,选了个离歌台较近的空桌坐下。
舞池里没多少人。我抽着烟,独自想着心事儿。
一首别离情绪浓郁的乐曲,搅得我心里酸楚。琢磨人这条命,片片刻刻都是在被动之中。我从没这么伤感过。
乐曲忧郁,如少女在哭。舞池中的人们拥在一起,步子放慢放慢,摇晃着对方。歌词大意:相见匆匆莫要慌慌分离,高原之路是生命的屋脊。我的心伴你流浪,远方的路茫然凄迷……
歌喉颤抖凄美,像是专门为我唱的。擦去泪水盯住,女歌手年轻的脸,在灯光下洁白秀美。一身牛仔装,特别洒丽。
肯定是因为她漂亮,我虽板着脸,但眼睛一直没离开她。
她唱完一曲之后,我的友人还没来。灯光暗下,彩灯、镭射灯、咣咣咣的音乐,迪斯科曲子,释放出热闹。
女歌手消失了,我只好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中,注视门口。
有人放在我面前一杯咖啡,坐在对面。心中一阵狂喜,是那位洒丽的女歌手。知道有艳遇,就按捺住自己。我诚心拿劲儿,也没谢人家。
姑娘也不好意思搭腔,假装看舞池跳迪的男女。后来可能是觉得不说点儿什么,亏得慌闲得慌:“您是搞艺术的吧!”
“差不多吧!”我还在矜持,但已有点儿喜形于色。想着慢慢来,这只是开始。
“画画的?”“不是!”“摄影?”“不是!”“演员?不是不是,演员没您这气质!”姑娘不够漂亮了。捧人一过,不巴适。
“你是干吗的?”我反问。
“我是歌舞团独唱演员。在这挣点零花钱。我叫江措。”
我有将错就错的感觉。
“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小姑娘求知欲真强。
其实我早想向人家介绍了。
“您看,我猜得多准。北京的作家,一看就不凡,咱们做个朋友行吗?到时我去北京找您玩。”
和这样的姑娘交朋友,尤其是远离故乡孤独的时刻,当然高兴。可我没想到她这么爽快。欲擒故纵,继续沉吟状。
“您不愿和我交朋友? ”江措姑娘把咖啡推到我面前。
“愿意,非常愿意和你交朋友。”我急忙说。怕一个美景像雾,突然逝去。“一会儿我给你留下我家里的电话号码。”想让江措误会我是专业作家。我分析着,选择语言,深入交流,却见她脸色骤变。双睛直勾勾,盯着我的身后。
背后有什么?一只猛兽?江措的脸更加苍白,像刮掉釉子的白瓷坛。我回头,是三个板着脸的小伙子。
待要转身,听到命令:“站起来!”挺严厉,像警察。
服服帖帖很掉份儿,可我还是老老实实站起来。那人凑到我耳边:“你是要和她交朋友吗?”
我踏实了:“就为这点儿破事,这有什么,江措愿意我就可以和她交朋友。”这是人之常理,大义凛然。我牛哄哄刚说完,右屁股蛋子像被马蜂蛰了。看看,是一把刀子扎了进去。
我有些怕,有点火。娘的这叫什么事呵!刀子还不拔出来。
那人长眉大眼的脸又贴近我,从喉咙里挤出话:“你还想跟她交朋友吗?”
我双腿开始抖战,觉得特丢人,可控制不住。再三镇定,看看他边上的另两位,手里也都攥着家什,怒气冲冲面目狰狞。知道此时此刻不能来硬的,一对三不过干。期盼地扫了一眼大门,友人还是没影儿。灯光很暗,乐曲没停,舞池空荡。可要是来软的,姑娘面前也太丢人。再说,高原人,最看不起怂包蛋。
左右为难,我下意识摸出一根儿红梅牌香烟——屁股上想来已是红梅花儿开了。琢磨着这人世间交个朋友,也要付出血的代价,真没道理。嘴里便说:“她愿意,我就可以。你要想和我做朋友,也能考虑考虑!”
我的话没说完,那小子又把匕首扎进去一截。
要是这么下去的话,我的身体和心理会承受不了。但也神了,这一刀虽然扎得更深,但腿却不抖了。我再次牛哄哄拿出火柴点上香烟,就当屁股扎进一根儿刺,做出藐视他们的神态。我记不清当时的香烟抽出烟没有,只是一口一口地抽。
又听到问:“你还想和她交朋友吗?”似乎在说,你再不服软,老子会扎透你的屁股,让刀子从你小肚子前边出来。
没音响了,人们呆愣着不敢动。女人们个个挤到男人的背后,光线亮多了。整个舞厅极其安静,似乎都在等着我的回答。
我绝对不能犯怂掉份儿。“想!”索性豁出去了。脆脆亮亮说完,我开始吞云吐雾。劫数难逃,也得站着死。可脑袋里,却一次次闪着自己挺直的尸体。只想和一个半生不熟的小姑娘交朋友,就要丧命,真不值。可我清楚,眼下不是为了她。
“跟我出来!”那人这一句“出来”坏啦,刀子也出来。我屁股上,有两股热乎乎的东西往下流。一在腿上,一在裆里。
我四下寻摸着,得跑就跑吧。出去这帮家伙一人一刀,还不把俺戳成筛子。
外边比里边亮堂,几米远就是布达拉宫前的大街。回头看看,门口人群挤成了疙瘩。我一边骂着不着调的朋友,一边伺机逃跑。1999年年底的拉萨还是挺紧张的,行人稀少。跑不过他们,近似于定数。没路,也许开步就是路。我正要抬脚,猛听到那小子叫了我一声“大哥!”弯子转得忒快,但是危险过去的信号。我放松下来,右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
“大哥!您是条汉子,我们也真他妈没道理。不打不相识,咱们交个朋友吧! ”
“也要交朋友,我他妈的怎么这么好人缘。”我臭来劲儿了。
另外两位也过来口称大哥,说了请多包涵之类的话。
扎我那小子我就叫他阿扎,我说我这辈子都会记住你。他说:给大哥摆赔罪酒。把江措拉上。三辆摩托车一起发动,五个人到了狮子楼大酒店。
我心里这叫一个气呵!屁股流出的血,已经到了脚腕子上,还在这喝酒?!可也不敢多说,谁知他们这是什么讲究。
三碗青稞酒过后,一人又喝了一碗四川沱牌白酒。阿扎还一个劲儿,让江措姑娘劝我酒。
我再端酒碗,跟他们一一碰了,借了酒劲说:“就这么着吧!情领了,恨记着。我屁股上的血不能再流,我要去医院。”
他们送我到了布达拉宫后面的拉萨人民医院。处理了屁股,又送我回住地——艺术学校。当时我是暂住在人家练钢琴的琴房,也是为了省钱。
他们走后,老师校长都来埋怨我,告诫不要再与他们来往。这些人像北京城里的地痞流氓,在拉萨名气很坏。
养伤的日子,阿扎常来看我,送来许多水果罐头。我以冷眼相对,板住面孔。阿扎这时总是十指插进长长的黑发,闭上眼搔挠一阵,然后说:大哥!你真是不知死!说完,踢开门走了。我大喊:不要再来了!第二天,阿扎还是照来不误。
江措姑娘也常来常往,说她曾在此校读书,很熟。帮我洗衣服、打饭、提热水。我怕流言,每日都早早打发她。她也提出过,让我帮她离开拉萨去外地发展。说不然,会被阿扎纠缠死。
我婉言拒绝,一个流浪汉,哪有这般能力。
江措哭了,像嫩草一样脆弱。父亲是陕西汉人,早逝,和藏族母亲一起生活,相依为命。
我的友人那天大醉,根本就没来舞厅。打电话找他,带我去医院换药。他警示我:拉萨不能再呆,你会丢了性命!
我紧张地告诉自己,要命吧,只有一条呀!上路当然是好事,可川藏线一塌糊涂,怎么过去?先走一截?到林芝也行。
这之后的好些日子,江措姑娘没再来。阿扎,也只来过一次。虎着个脸坐了半分钟,没说一句话就走。
屁股养好了。上路那天,阿扎一人来送我。在拉萨河畔,是个清晨。阿扎一脸的平静后面,隐含着忧伤和沉重。粗壮的手上,执着一串水晶和绿松石的佛珠。告诉我,他也要远行。到西藏的山南去当喇嘛。然后云游雅鲁藏布,一直到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又说,江措姑娘跳了拉萨河,尸体都没找到。
我心沉沉的,沉得没了底。然后又慌恐地感到,自己是个凶手。想起她唱的那首歌,想起那种心的疼。
我俩来到拉萨河畔,水面闪烁的红粼,像一片阳光跌倒在涟漪中。这就是我称之的太阳血,这血是冰凉的,还有一个媚艳的名字——霞。是因为她一次次跌倒,才形成的。我知道这湍急冷美的河水,不久将汇入阳光灿烂的世界屋脊上,那条世人皆知的大江,雅鲁藏布,向东,然后向南。
阿扎挥挥手。
我挥挥手。
不折不扣之冈仁波齐·帛姆
我仅有一次,长头叩拜神山。
发源于冈底斯主峰冈仁波齐西麓的噶尔藏布,在印度河上游的阿里,是帐篷河的意思。在这里,我认识了他们一家。
他们是遥远美丽荒凉的羌塘人,从鲁玛多错湖叩拜而来。在地图上看,有1000来里地。夫妇俩和他们的小女儿帛姆,加之四匹马、两头牦牛。河滩上,孤零零一顶黑牦帐。我习惯了串门的不犹豫,掀了双层羊皮帘进去。
喝完酥油茶,使用了我掌握的全部藏语,包括在青海玉树学会的一点儿康巴土语,再加上比划,告诉他们我的愿望。
帛姆看阿妈,阿妈转着手里的玛尼轮笑着看阿爸。阿爸的大手磨擦了一下脸,把糌粑袋扔到我盘坐的腿前。这是接纳的表达,权威的温和。我的行囊,捆上了马背。
山路像一条弯曲的牛尾巴,四口人的队伍比老牛还慢。开始的几天,阿爸磕头上路一个多小时后,才收拾帐篷捆上牦牛背。我和15岁的帛姆,驱赶着驮队。阿妈转着玛尼轮,在后边慢腾腾跟着。有时找块大石头坐下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走。
山口悬挂着,蓝、黄、绿、红、白,五色经幡,集合着天、地、水、火、土的意识,在路人的头颅上,招摇庇护。
每日出发和歇息的时间全由阿爸掌握,没有规律。路途的长短也没准儿,有时二十来里,有时几里地就歇了。也有一天,风和日丽,天气特好,我们四口人在帐篷里呆到下午。阿爸只管捻着佛珠念经,一点儿没有上路的意思。后来我就和帛姆,去崖口下取冰化水煮茶,吃糌粑。一天天就这么过来,和我想象的一样,在现世和非现世的空间徜徉。喝的水,大都是悬崖洞口垂挂的冰溜子。像漏斗像陀螺,一根根小腿般长短,用黑毛毡子捆裹好。帛姆从来自己背,我只管陪着。到家我抢着砸碎,放到锅里加上砖茶,把粪火烧旺。仅有这么点活干,我得尽情表现。帛姆上过二年级,会一点汉语。她很愿意和我说话,对汉语有强烈的求知欲。
多日后一觉醒来,发现我的藏语已经能和阿爸阿妈交流,甚至可以在康巴博巴和安多的方言里,找出它们的共通之处。有点吹乎。但的确在后来流浪的日子里,方便多了。有位老喇嘛说我,前世是在藏北草原长大的。当然不一定是人,也许是狗,也许是牦牛,也许是虫豸。但我今天是地道的藏汉,这已被高原兄弟姐妹们认同。
“往上走和太阳相会,往上走和雪狮相会,往上走和雄鹰相会。”傍晚,我往火中填着牛粪饼,随口哼出这首古老的民谣。
阿爸掏出鼻烟盒,我赶忙递上刚卷好的莫合烟,用防风的打火机为他点着。他的眼睛盯住翻滚的白烟说:“烟是好东西。”
我想和阿爸聊天,他却不言语了。沉默片刻,有了歌声,苍凉浑厚:黑色的大地用身体衡量过来,白色的云彩用手指清点过来,陡峭的山崖像攀长梯而上,平坦的草原像读经书掀过。
长头叩拜者的朝圣之路,如此轻松。跳跃的酥油灯火,把数平方米的黑牦帐,耀如白昼。
阿爸神色庄重,目光茫然又像凝滞在遥远。他的心思好像不很关注目前的现实,而更着眼在未来的空间。他的怀里,有一座神山。
我几次捕捉过,想知道他目光栖息的风景,却失败了。
帛姆手脚不拾闲,她最大的工程,是去捡牛粪和碎柴。有了这些,我们的帐篷才维持着不息的锅庄和温暖。空闲,还要让我教她汉语。已经学过了火车飞机,再学就是北京中国。她冰雪聪明说:坐着火车飞机,到北京中国。
像往常一样的清晨,刮起小风。帐角和羊皮帘,一劲儿呼打。
帛姆为我系上生牛皮围裙。我跟着阿爸去磕长头。
阿爸迟缓疲倦的步子,拖着沉重的藏靴。地面发出“嚓、嚓”的声响。最后在一块枕石边站定,这是阿爸昨天磕头到这里留下的记号。他合掌如蚌,念了阵子经文,开始跪下,开始匍匐。
阿爸铁黑褶皱的脸,迎向蜿蜒的山路前方。灰白绕在脑后的小辫梢上,一根红布条在飘忽飞扬。精瘦的身躯,起来趴下,趴下起来。我追寻模仿着,他的举手投足和移动。
我双手尽情地前伸,像一个长睡初醒的懒腰。整个身子平匍在地,双手划弧线到腰间站起。然后前迈三步,再磕下去。重复。
开始我感到山体的冰凉,身下常有石子硌得慌。跪下慢,爬起快,吃累得很。再后来,趴下不想站起。五体下的大山有了暖意,眼睛寻摸枯草或碎石看一阵,再起。
几个钟头过去,想来该歇歇,吃吃茶和糌粑。但阿爸严格的动作,标准的节奏,继续,全无停下的意思。
没有温度的太阳坠落,我们叩到一面山坡上。又一个长头磕下抬起身,目光穿过蓝幽幽的山谷。远处雪峰高耸,金辉皑皑。
听到阿爸的念叨:“冈仁波齐、冈仁波齐……”我激动,我们到达啦,我们终于来到了神山的面前。然而,阿爸长跪在那里,闭上了眼睛。面孔安详,破烂的裙摆飞扬。崖头在呼啸,砂石在滚动。
阿爸去世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对于他的身世,我几乎一无所知。他有六十岁吗?和他接触的日子,交流得太少。甚至他唱歌的那天,都没正眼看过我。我也从未捕捉到他的目光。没见过他的喜悦,也没见过他的痛苦,即便是看到了神山。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与磨难艰辛为伍。一种不曾有过的卑微,让我泪水涟涟。
阿妈和帛姆很平静,似乎这是安排好的。
晚上,阿爸还是和我们挤在一顶帐篷下。
佛龛前的酥油灯,照在阿爸用过的木碗上,里边放着青稞炒面和一疙瘩酥油。他的头抵进羊皮袄的领口,像睡着了似的。阿妈坐在他的身边,追着闪动的微光,牵缀牦牛线编织的口袋。
冈底斯的夜,浓浓而又神秘。梦见天神赐给我一匹奇异的坐骑:龙体、狮头、牦牛蹄、青蛇尾。
这个清晨好,寒风小了,阳光暖了。对面薄雪将融的山坡上,有一列上百人的长头队伍蠕动行进。远远望去,像一条橘黄的绸带或一缕长长的云丝,慢慢飘向冈仁波齐的山麓。
我和两个女人把阿爸装进牦牛袋,驮上马背。上路。我代表这个家庭,从阿爸昨日停止呼吸的地方继续,衔接着匍匐叩拜的长头。
对于这家人,我突然有了一种责任感。长头磕得格外严谨。记住阿爸平日每一个细微动作,不敢马虎。在不知不觉中,阿爸温和冷峻的权力移到我的手中。不管她俩方便与否,不顾任何建议和暗示,上路、喝茶、支帐篷,一切我说了算。她们顺从地听任。
那座神奇的山体像块巨大的磁石,每一个长头匍匐,她都含进我的目光。如楔,充满整个大脑。每日到天黑,我才停止。
直至摸到她脚下的祭台;直至那种祥和的气氛令我的指尖发抖;直至献上哈达后抑制不住泪水。
那几天的长头,是在呼吼的寒风和飞雪中完成。阿妈继续摇着玛尼轮,帛姆继续去山野背水烧茶收拾一切。没有疲倦,也不见笑容。山谷寂静,黑云在坡上滚动。
一直和我说话的帛姆要去背水,闭目念经的阿妈说:天快黑啦,将就吧。帛姆答:熬一锅水,睡觉安逸。阿妈说:哦,北京人的习惯。去吧!帛姆回答一声:是!人已经到了帐篷外。
锅庄的粪火快要熄灭了,也不见帛姆的影子。按理,两趟都该回来啦。我穿上皮袄打开手电,出来想往北去,可北面是陡坡。我悉心静听了一阵,就顺着小路走下去,小路分叉三条。我呼喊着帛姆,四面八方寻找。两个多小时后,漆黑的夜色里出现了微弱的哭声。我飞快地冲过去,河岸上,趴着湿淋淋昏死的帛姆。旁边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在抽泣不止。我背一个抱一个,跑回帐篷。阿妈脱光帛姆,裹在我的皮袄里。我连续往锅庄加着牛粪,帐篷里的温度迅速升高。小男孩烤着火,东一句西一句说着经过,大致意思:他原本已经玩够,离开河边准备回家。一个白绒绒的雪人,抱住他就走。帛姆来救,雪人把她摔昏过去。
阿妈送走小男孩回来,帛姆还没醒。鼻息均匀,睡着了一样。
那一夜,我守着帛姆,守着锅庄不让它熄灭。阿妈一直在念经。随着帐篷外的明亮,帛姆睁开了双眼,红扑扑脸好像在笑。她说:从没睡过这么好的觉。我把烤干的衣服递给她穿好。她把皮袄披在我身上。阿妈问:见到雪人了?!帛姆一边做水煮茶一边说:见到啦。两米高,身上热乎乎。我跑得慢,雪人的速度太快,追上就搂住我,我挣扎的能力都没有,后来我就睡着了。
我问:是吓昏的?帛姆说:第一次是有点怕,但这里人都不怕,雪人很友好。阿妈插话:这里雪人多,人们很习惯。
神奇。据说雪人就是野人,是冈仁波齐守护者。尼泊尔王国,有关的记载很多。冈仁波齐是自然的神,是神的自然。
烧好茶时,进来一位藏族汉子。八角帽下的浓眉,像横挂着两条黑牦牛尾巴。“请坐!”我递过去一个木碗问:“你从哪里来?”
“普兰,我叫吉宾。”吉宾又说:今年四月(藏历。公历的六月)树大旗时,在这里结识了一个非常好的札达姑娘。因为她的阿爸在雪山中长大,所以她叫“耶蒂”。是尼泊尔语,雪人的意思。
帛姆昨晚见到耶蒂了。我告诉吉宾。他说:是的。祭祀神山的日子,雪人会在河边深谷巡视。我好奇:我能见到耶蒂吗?他说塔尔钦寺把放倒的经旗杆,换上新经幡重新再树起来,是开庙的日子,也是朝拜圣山冈仁波齐的开始。全年最热闹的一天,人山人海。我的姑娘耶蒂就会来,她要怀孕了我们就结婚,带她到普兰去。
我抓紧和吉宾商量,怎么天葬阿爸。吉宾说,东面万宝山那边有天葬台。这山吉祥,佛祖释迦牟尼曾经走过。他认识山上的喇嘛,但需要钱。我掏出身上的全部,他拿了一百块,说先去联系。临走他嘱咐,让我们迁到东山坡上等。
我们喝了茶吃完糌粑,然后搬迁。
夜色笼罩的塔尔钦寺院一片祥和气氛,诵经和法器声从谷底飘荡起来。冷蓝的空中,不多的几颗星星和着咚咚的鼓点儿闪现。
我们仨偎在羊皮下,一宿无话。帐外的马匹,突突地打着响鼻。附近玛尼石堆上的经幡呼啦啦,似乎在呼唤着什么。
又是一天,太阳快落到西面的度母山时,吉宾带着碎尸喇嘛回来。吉宾说喇嘛会把一切有关事宜安排好,让我放心。还说,天葬时,不用都跟去。但钱还不够,因为阿爸太瘦,一身精骨头,碎开尸体后不够秃鹫吃。要买一些牛肉,天葬时和碎尸骨掺和在一起,才可以保证让秃鹫吃干净。阿妈要拿出一头牛,被我拦住,又给了喇嘛二百块钱。我知道,牲口对未来的母女俩意味着什么。我问够吗?吉宾说:足够,买一头牦牛都够了。
要和母女俩告别了,心里有种不是滋味的滋味。我从行囊里挑出一件崭新的灰茄克写上:扎西德勒!永远的祝福。北京人。交给帛姆,她忧郁地笑了,把夹克紧紧抱在怀里。
我还剩一点儿钱送给阿妈,她不要。拿出半袋莫合烟,她却高兴地接受了。阿妈解开装着阿爸尸体的牦牛口袋,把莫合烟放进去,又从阿爸的怀里掏出盒鼻烟递给我。
铁皮的鼻烟盒上,居然还有温度。我最后看了一眼阿爸,他安详如专心祈祷。
后面发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喇嘛检查完尸体,裹紧袍裙和吉宾说了几句话,过来把钱还给了我。我不知所措。
吉宾说:喇嘛看了阿爸,知道是长头叩拜而来的,很是敬佩。天葬台所有的费用,由寺庙出。看喇嘛,他正冲我点头。
帛姆牵着驮着阿爸的马,阿妈摇着玛尼轮,一行人下了山坡,留下我和吉宾。
我觉得帛姆该回头望望。但她没有。
夜深时,山坡上极冷。阿妈留下的最后一点粪饼,全加入到火中。前胸和脸烤得发烫,后背冰凉。为了预防感冒,我从怀中掏出鼻烟盒,指甲挑出点儿,嗅了就打喷嚏。
吉宾唱起藏歌,说想他的阿妈,想耶蒂了。我俩的后半身,被黑夜吞没了。
我说,再唱,我也想姑娘了。吉宾说,帛姆就是年轻时的阿妈。阿妈年轻时的俊美,在羌塘很出名。又说,帛姆不是阿爸的女儿。脑海里,我努力再现阿妈多皱的面孔,想找出她年轻漂亮的遗留。慢慢那脸,变成了帛姆的脸。想起,一同背负的云和月,一同经历的雪和霜,一同接受的风和日,一同黑牦帐下的夜。虽然是一条不长的道路,但它横越在岁月时空和大山荒凉的路途。有足印,也有心灵的痕迹。
吉宾的家在藏北草原腹地的尼山,是解放军带他出来。读了五年书,又去当了解放军,在扎西冈6000多米的哨卡站岗,三年后复员到了普兰。
山野很静。吉宾时不时抠着腿边上的枯草,扔进火里或者搜索着身上兜里的纸片点燃。八角帽摘下,放在蜷着的腿上。火苗扬起的灰烬,在他盘着如夜一样的黑发上打着旋涡。牙齿真白。
冷,高处不胜寒。我有些后悔,不如和母女俩一起下山。
漆黑的坡下有些异样,似乎刮起小风,从山谷中传来一种乐音,又似冥空中飘来,犹如天籁。是以往岁月的?是未来岁月的?是阿爸的灵魂,从西方的极乐地界飘然而至?我俩息神静听。
愈来愈近,愈来愈近,叮铃铃,叮嚓嚓,嚓叮叮嚓铃铃嚓嚓……和谐优美,茫然而又本质。
篝火忽地炸开火星,风把火苗炭灰扬得老高。火前站定两个衣着白色羊皮袄,健壮的藏族姑娘。脸上涂满羊血,每人牵着一只弯曲大犄角的山羊。羊脖子,坠着铃铛。
当她们给我和吉宾围上哈达时,冰凉的手,才让我释放了紧迫。女人的皓齿,泛着瓷亮。
吉宾兴奋地告诉我:她们在山下碰上阿妈了,知道我们在这里。说宿在山上凉,到她家帐篷去休息。帛姆救的那个小男孩,就是她们的弟弟。我没等吉宾再说话,就兴冲冲踩灭粪火,随她们下山。
天籁,又在夜色里飘荡。嚓叮叮嚓铃铃嚓嚓……
这是一个大得惊人的长方黑牦帐,估摸是一般帐篷的十倍。里边已有二十几个人在喝茶、喝酒。
我先来了碗冰凉的青稞酒。一个老阿妈又送上一碗热茶,再把一块块生肉干丢进嘴里,身上迅速暖和起来。
吉宾和大家交谈热烈,有时和诸位一起看看我。每人都是笑脸。
吉宾说,这些人有那曲的有玉树的也有本地札达的,还有一个尼泊尔人。看一圈,辨不清谁是谁。
我被分到一顶小帐篷里睡下,两个脸上涂血的女人也在。挤在一起很暖很倦,但睡不沉。恍惚之中摸到女人的脸,血还有些黏。
第二天起来时,帐里只有我一人了。太阳还没升起,得过去喝点儿茶,又饿了。
大帐篷门帘边上,一堆羊皮下在蠕动。过去掀开,站起个光腚的小男孩,是我昨天抱回的那个。他撒了泡尿,招呼我进帐篷。他睡过的地方是一片卵石,我摸摸还暖暖的。茶后,全体人员只带上供品。浩浩荡荡,拥向冈仁波齐神山的脚下。
我离开的那天,在人群中找到吉宾时,他身边站着一个大肚子的藏族姑娘。他笑着说,她就是耶蒂,马上回普兰结婚。
我祝福他俩。吉宾告诉我,他碰上那位碎尸喇嘛了。喇嘛说天葬过程很完美。阿爸的头盖骨已开启了一条缝,能插进加玛草茎。
我不知加玛草,但感到阿爸的道行很深。吉宾还说,阿爸的尸体是剃了头的帛姆,走了半天的山路,背到天葬台的。之后,帛姆出家了。阿妈暂住下来,等待转山的日子。
我无力想象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
吉宾扬扬手和我告别,亢亮一句话:结了婚上了鞍子,生了小孩加了鞭子。
这年,也就是1989年11月22日漆黑的凌晨,我站在狮泉河桥北的路口,巧遇喜玛拉雅山上升起的UFO。她美丽泛着黄光的姿态,令我感喟:天长地久,生短人矬。
选自《山东文学》2016年第5期
原刊责编 王利宣
本刊责编 朱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