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 (短篇小说)
2016-05-14乔洪涛
乔洪涛
1
娘第五次逃跑还是没有跑掉,回来后被爹打瘸了一条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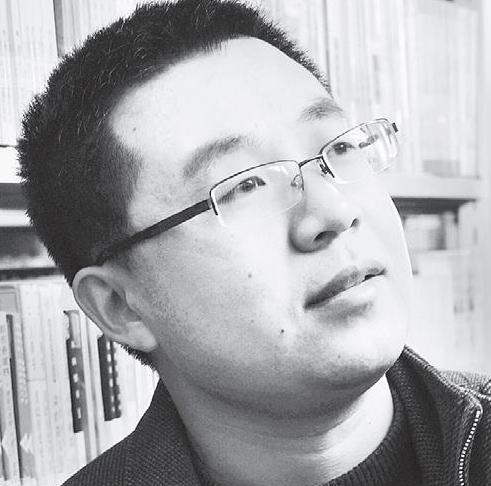
我再让你跑,再让你跑。爹喘着气,哆嗦着,手里的木棍断成了两截。娘躺在地上,披头散发,却一声也不肯哭出来。
这一次,娘躺在床上两个多月才下床。我和妹妹给她端屎端尿,送饭喂汤,爹就坐在八仙桌旁狠狠地抽他的旱烟。这两个多月,娘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从此之后,娘与爹几乎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为娘偷偷掉了好几回眼泪,但我不恨爹,我恨娘。我爹这是为这个家好,他怕娘跑了。我们知道,要是娘真跑了,这个家就散了。其实,在我看来,除了爹没有本事,家里过得有些穷之外,我爹对她不错。我爹把不舍得吃的拿出来给我们娘仨吃,自己不舍得吃一口;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娘仨会一人一身新衣裳,但他自己从不舍得买。除了在娘逃跑这件事上,他打过娘、锁过娘,爹平时几乎从来不发脾气。
你娘跑了,你们就没有娘了。爹对我和妹妹说。
千万把你娘看好了,别让她跑了。爹叮嘱我和妹妹。
我和妹妹点点头,我们想不明白,我们的娘为什么老是要跑,人家的娘怎么就不跑呢。但我和妹妹明白,我们不能让娘跑掉。
我爹说完,竟然趴在那里呜呜地哭起来了。我和妹妹都害怕了,我们心里就恨起了娘。
娘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跑了。这一次是第五次了。
听奶奶说,没生我之前,就跑过两次。生了我之后,抱着我跑过一次。生了妹妹之后,跑过一次。这一次是第五次,还是没有跑掉。要是跑掉了,爹就没有了媳妇,我和妹妹就没有了娘。
前几次,娘几乎都没有跑出山去就被爹和叔叔给捉了回来。捉回来了,叔叔每次要打断娘的腿,都被爹拦下了。这一次,娘跑到了镇上,从镇上坐了班车,跑到了县上,又从县上坐上班车,快要发车的时候,我爹他们赶到把她捉了回来。
差一点儿,我叔叔说,再晚一点,这个熊娘们就跑了。
打断她的腿,看她还能不能跑。我叔叔咬牙切齿地说。
我爹气疯了,抓住她的头发问她还跑不跑。
跑。我娘面无表情地说。
“咔嚓”,我爹折断一根锨把般粗细的小杨树,照着我娘小腿上就敲了过去。我让你跑,我让你跑。我爹真疯了,他一边喊着,一边打,打了得有十几下,我娘躺在地上,抱着她的腿,疼得直哆嗦。
我奶奶从西屋里跑出来,扑上去护着了我娘,不敢再打了,不敢再打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出人命的。我奶奶说。
我奶奶信佛,常年在西屋里敲木鱼,她是个善人。
我和妹妹吓得大哭起来,叔叔把我和妹妹拎到了西屋里去,把门关上了。
搜搜她,搜搜她。我听叔叔说。从窗户里,我们看见,他们把我娘摁在地上,从她腰里掏出来一卷子钱,数一数,有三千元。
娘的 x,怪不得要跑,有钱了啊。叔叔丢掉烟头说。
这些钱我爹不知道,他没想到她身上有这么多钱,他惶惑地看着她,从叔叔手上接过钱来,他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似的。平时钱都是我奶奶和我爹放着,他们把钱藏得紧紧的,娘身上从没超过一百块钱过。娘不需要钱,家里的东西都是爹去买。娘也不需要出去,她的任务就是呆在家里。
娘手里不能有钱。有了钱,她更方便逃跑了。
说说,你这是在哪里弄来的钱?!叔叔用手指着她,面带鄙夷。
娘一声不吭。
大哥,你看看,给你说你还不信,你看看,这个熊娘们咋弄来的钱?她从哪里弄来的钱?你信了吧?!叔叔看着我爹说。
我爹的脸色很难看,他咬着牙,举起棍子,像要敲碎娘的脑壳。奶奶护在娘身上,对着叔叔和爹大声说,你们都给我滚出去。这是我给她的钱!你给她的钱?叔叔瞪大眼,你哪来的钱?你
老糊涂了。滚!奶奶骂道。都滚。娘是当年奶奶托人从外地给爹买回来的,那
时候爷爷还活着,西家借东家借的,好歹凑足了
四千元,托人从南方给买来的。四千元。这笔账还了七八年才还完。我们家里一直过
着穷日子。村上的男人都出去打工,很多都挣了钱发了财。可我爹要在家里看着娘,出不得门,我们家就只靠种几亩山地收入,爹还得供我和妹妹上学,现在日子也过得凄惶。
前些年,我们村上一共买回来四个媳妇,到现在已经跑了两个,喝药死了一个,我娘是剩下的最后一个。
看好你娘,别让她喝了药。晚上的时候,奶奶悄悄告诉我。
2
从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娘说话和别人不一样。我娘说话快,好听,还有些别人听不太懂的蛮语。村上人都称我娘是“南蛮子”。但我娘一般不和别人多说话,其实她和爹也不大说话,娘有时候爱说给我和妹妹听,她还给我们唱歌,她唱: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哟
端端溜溜的照在,
康定溜溜的城哟
她唱起歌来,就像我们山上的百灵叫,真好听。但娘唱着唱着就不唱了,她呆呆地看着山外抹眼泪。我爹有时候也唱两句,他唱的难听,和娘不一样,他去山上放牛,有时候就扯开喉咙喊 ——
人人那个都说哎嗨哎沂蒙山好哦啊哦
沂蒙那个山上哎嗨哎
好风光
好恁娘的头!我娘听见了就撇嘴,说,狼腔鬼叫。娘就把耳朵塞了,关上门,去堂屋里照镜子。娘没事就梳头发,照镜子,她的头发真黑,真长,但每次都能梳下一团来,梳下来她就把它团起来,让我塞到墙缝里去。
娘还说,你们以后想娘了,就到墙缝里找娘的头发。娘说这话的时候,面露凄惶,我们就很害怕,我们害怕娘突然有一天真的不见了,我们就只剩下娘的头发了。
我娘长得漂亮,细细高高的身材,白白的皮肤,笑起来脸上还有个小酒窝,但我娘很少笑。我娘爱干净,每天都把自己收拾得利利落落的。不仅收拾她自己,我和妹妹也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娘很疼我们,她把好吃的都给我们吃。我们塞给她吃,我们说,娘,娘,你也吃。娘这个时候就会笑一下,我们就会觉得瞬间天都亮堂了。娘还给我们做面团子吃,爹去集上买来糯米,她给我们蒸糯米粑粑吃,我们村上可没有谁吃过这东西,他们每天只知道抱着煎饼啃。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好骄傲。
奶奶在西屋里念佛,有时候会出来站一会儿,手里拿着佛珠,看着我们娘仨笑眯眯的。
娘看见奶奶,就会折身进到堂屋里去。娘不喜欢奶奶。
但是娘也算孝顺,每次做了饭,都会给奶奶盛上一碗。奶奶就很知足,还是眯了眼笑,说,阿弥陀佛。
奶奶是个善人,不吃肉,每天都烧香念佛,奶奶总爱摸我的头,让我快快长大。
大郎,大郎。你去集上割二斤肉,给她们娘仨包饺子吃。奶奶说。奶奶不吃肉,但奶奶不阻止我们吃肉。时间长了,奶奶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手绢,从里面找出几块几毛钱来,给爹让爹去买肉,给我们改善一下生活。奶奶也没多少钱,奶奶的钱主要是我姑姑寄给她的。据说我有一个姑姑,在北京工作,每年会寄给奶奶一笔钱。但我从来没见过我这个姑姑,据别人说,我姑姑不是我亲姑姑,是我奶奶替别人抚养的一个女子。那时候我们这里过部队,山里整天枪炮不断地打仗,八路军的女干部在我奶奶家生了娃娃,就走了。这个娃娃就留给了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一直把她抚养到十几岁,后来,人家亲生父母就把她领走了,接到了北京。走了之后我姑姑虽然没再来过,但我姑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她上班挣钱之后,每年都给奶奶寄一点钱来,多的时候,寄过一千块,奶奶就成了我们家最有钱的人。
每次寄来钱,奶奶就看着钱掉眼泪。
我们知道,奶奶想姑姑,她需要钱,但她更希望姑姑能回来看看她。但在我的记忆里,姑姑好像从没回来过。这样说,姑姑也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据说我叔叔有一年去北京找过我姑姑一次,叔叔给姑姑带去了奶奶纳的绣花鞋垫,还背了两包袱煎饼。姑姑在宾馆里给叔叔安排了好吃好喝的住下,还让小轿车拉着叔叔在北京城逛了三天,就是没让叔叔到她家里去一趟。姑姑见了叔叔两面,去的时候见了一面,来的时候,见了一面。其他时间,姑姑很忙,老是要开会,在北京开完,还要到上海开,上海开完,还要到外国开。姑姑据说也是个大官了,她忙得脚不沾地,她没时间陪叔叔,更没有时间来我们这里看奶奶了。
在这个家里,奶奶最当家。什么事都是奶奶说了算,我爹最听奶奶的话了。我叔叔娶了媳妇,分家另过后,我奶奶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过。我叔叔生得五大三粗的,没花多少彩礼就娶了媳妇,还生了一儿一女,后来叔叔出门打工,挣回来不少钱,小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了。叔叔不用在家看着婶子,婶子不用看她也不逃跑。但我爹不行,他离不开家,他必须得看着我娘,否则他前脚出门,我娘后脚就会逃跑了。我奶奶可看不住她,我奶奶是小脚,我娘要跑她可撵不上她。
其实,即使不守着我娘,我爹也出不了门。我爹不仅个子矮,还开山炸瞎了一只眼。村上的人都喊我爹叫“大郎”,大郎,大郎,他们喊。我爹开始气鼓鼓的,后来就不生气了。后来,我奶奶也喊他大郎了,我爹就彻底叫了大郎。好像是梁山泊里武松的哥哥武大郎似的。
我娘每次听到别人喊他“大郎”,就会鄙夷地撇撇嘴,我娘看不上我爹,我爹也实在是配不上我娘。
我爹憨厚实在,只知道干活,个子又矮,家里又穷,三十多了也娶不上媳妇。我们这里群山连绵,一层山叠着一层山,一道梁隔着一道梁,车也不通,船也不通,羊肠小道像抛到天上的麻绳子,曲里拐弯不说,还难走得很。村上很多老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这个村子,更别说去镇上去县上了。也没有哪家的闺女愿意嫁过来,我爹打光棍差不多是命中注定了。
那时候,我爷爷还是村上的支书,看着村上的男青年都娶不上媳妇,一家家穷得揭不开锅,就带领着大家去山崖上开路。他发誓要开出一条宽宽的大路来,路不通,山上种的栗子、核桃、柿子就运不出去,山外的姑娘就走不进来。那时候我爹最积极,他跟着我爷爷风餐露宿,干在山上,住在山上,凿石开路。当然,他最想的是走出去看看女子是啥样的,要是能娶回来一个当媳妇,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但我爷爷和我爹命不好,一次点炮的时候,遇上了哑炮,后来又炸了,我爷爷躲闪不及,炸死了;我爹炸掉了四根手指,炸瞎了一只眼睛。我爹就成了独眼龙,每到阴天的时候,他的那只瞎眼就往下淌眼泪,流眼屎,整个眼睛红红的,很吓人的。我娘最恶心的就是他的眼睛了。
后来,路修完了,可以通到镇上了。我爹残废了。
路通了,山货能卖出去了,山里人也有了一点钱,但还是没有媳妇愿意嫁过来。没人愿意嫁过来,但有人愿意把人卖过来,那就是人贩子。我奶奶就花钱托人给我爹买了个媳妇。
这就是我娘。
我娘刚来的时候,才十七岁。十七岁的我娘,貌美如花,她是被拐卖来的。
我娘有一次给我和妹妹说,她老家那里也是一片一片的大山,那里的山也不比这里的山少,那里的人家也很穷。那里的姑娘也不愿意一辈子就在大山里,都想方设法地想往外走。我娘有一个哥哥,也是三十岁了找不上媳妇。我姥娘姥爷就打算让我娘给我舅舅换亲。我舅舅很疼爱他这个妹妹,不愿意,可是我姥爷姥娘不依。我舅舅就在一天晚上偷偷把我娘送出了山,爬了一夜的山,他们手脚都划破了,终于翻过了大山,走上了一条通往外面的路。我舅舅抓着我娘的手说,妹妹,你走吧,顺着这条大路,走了就别回来了,千万别回头,再也别回来了。
我娘满眼泪水,给我舅舅磕了两个响头,就走了。
她真没有回头,也再没有回家。
她来到镇上,又步行来到了县上。后来,她就遇上了一个人,这个人长得不错,能说会道的,关键是这个人花钱给她买了八个肉包子吃,饿得快死的娘就跟这个人走了。
这个人带着她坐上火车,来到大城市,玩了几天,又坐上火车,把她倒给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又把她倒给了另一个人,后来,娘就被人带到了这群大山里,卖给了爹当媳妇。
娘明白了情况之后,哭了三天,绝食了三天,她自杀过,逃跑过,可是,她都没有死掉,也没有跑掉,她在我们家一待就是十几年快二十年了,她生了我,又生了妹妹,她就成了我们村上的人了。
生了我之后,娘抱着我跑过一次,失败了。再后来,又生了妹妹。娘最疼妹妹了,妹妹长得好看,娘说和她小时候一模一样。妹妹也疼娘,每天挂在娘胳膊弯里,形影不离得像姐妹俩。娘再逃跑就有了牵挂,有很多个夜晚,我都听见娘嘤嘤地哭,一直哭到天色大亮。
爹是个闷葫芦,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除了干活,就知道喝酒。喝多了,就趁着酒劲折磨娘,他个子小,可力气大,他在夜里把床板撞得咚咚响,他喘着粗气,和牛一样重。娘每次都挣扎着,打他,咬他,掐他,后来,娘和爹就瘫倒在床上,一个嘤嘤地哭,一个打着呼噜睡。
奶奶睡不着觉,常年在夜里敲木鱼,每次我爹鼾声响起,她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地念个不停。第二天,她常常会塞给我爹几块钱,让我爹给我娘去买点好吃的。
我和妹妹渐渐长大了,娘也慢慢老了些。
我们就觉得娘不会再跑了。
再说了,我们听说,春天的时候,娘老家那里发生了大地震,姥娘姥爷那个地方震得最厉害,恐怕他们已经都不在了。家都没有了,娘还回去做啥?
那一段时间,娘对着西南方向哭了好几回,她跪在院子里,不停地磕头,不停地哭。后来,就有了娘第五次逃跑。
但娘还是没跑成,不仅没跑成,还被搜出来三千块钱,气得我爹把娘的腿都打折了。
娘成了瘸子,走路一拐一拐的,这次她可真的跑不了了。
我看着娘瘸腿的样子,心里狠狠地疼,像是被蝎子蛰了一般疼。
3
娘疼我们,娘爱我们,我们也爱她,但是,我们也恨她。
那些年,我们家最怕的事就是娘会突然不见了。十几年来,她时刻准备着逃跑,我们则时刻警惕着她逃跑。在娘的一生中,自她十七岁之后,逃跑成了她人生的主题,直到我也到了十七岁、十八岁,考上大学远离了家乡,我才懂得了想家的感觉,想娘的感觉,也才慢慢明白了娘的挣扎、逃跑。我的童年和少年,每天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我害怕娘不说话,我害怕爹打娘,我害怕锁娘的那根铁链子还有那间黑咕隆咚的草房子。我害怕夜晚,我害怕黎明,我害怕白天坐在教室里,放学一回家就不见了我的娘。
我不仅害怕娘突然跑掉、失踪,我还害怕娘会去寻死。
我们村上的妇女,喝农药的、上吊的、跳井的,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两个,我亲眼目睹了红军娘上吊、小国娘跳河而死,我害怕有一天我推门回家,也看到纸幡飘动,我娘躺在灵床上的景象。我害怕娘不要了我们,不要了爹,不要了我,不要了妹妹,独自一个人享福去了。
奶奶、爹还有妹妹,我们都有一样的感觉,几乎每一天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别看奶奶每天敲木鱼,念佛,心像菩萨似的,可奶奶的心从来没有放松过一刻。爹上山下地,出门找钱,奶奶就得好好看护着娘。为此,一辈子省吃俭用,舍不得吃喝用度的奶奶,经常不断地巴结娘,让爹给她买这买那,要是娘笑一下,奶奶就会高兴地一天不停地念“阿弥陀佛”。
我们怕娘丢了。
没娘的日子可咋过呀。
我们村上红林娘,也是从南方买来的,生了红林不久就跑了。红林现在跟着他爹像个乞丐一般,穿得破破烂烂不说,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从未吃到过一顿熨帖饭。
我可不想和红林一样,那样可就惨啦。
那样的话别说我上高中读大学了,恐怕早就放羊放牛,成个小野孩了。
幸亏,我娘没有跑成,也没有狠下心来喝药上吊,我和妹妹才有一个娘喊,才有一个家。所以,她让我们担心受怕,我们恨娘,但我们也爱娘,她一直还给我们一个家。
其实,我们恨娘,还有其他原因。
她让我们一家人在山里抬不起头来。
娘年轻漂亮,爹自然配不上她。后来我看了《水浒传》,我真真切切感到了那里面写的那个故事,就是写的我爹和我娘。我爹就是武大郎,我娘呢,就是潘金莲。
我娘在我们村上应该是最漂亮的,再加上她常年不下地干活,一直白白嫩嫩的,显得很年轻。长长的头发,瘦瘦的腰身,高高的胸脯,笑一下,腮上的小酒窝能把人笑醉。
我们这个山村,一共七八十户人家,因为贫穷,村上光棍就有十几个。这些光棍三十多岁到七八十岁的都有,他们都是一个人吃饱一家人不饿的主。他们穷,也懒,平日里也不想着走出大山去寻个工作,就只在家里干点农活,混个肚里不饿。每年如果手里节余一点,落个千儿八百元的,他们就抽烟喝酒打牌,再就是找女人。
我娘是外地人,和我爹又不般配,我娘的到来,就搅动了整个山村。
从小我就知道,我家厕所后面的石缝外,总是不断有人在那里圪蹴着,等着我娘去厕所里撒尿,看我娘的白屁股。我爹气急了,就拿一把铁锨狂叫着奔出去,要和人拼命。我娘不恼,不怕看,还会看着我爹生气的样子哈哈大笑。后来,我长大了,我就从院子里往外扔石头。有几次,石头就落在了外面的人头上,给他们砸一个血窟窿,他们就不敢了。
我娘不让我爹睡觉。我爹要是和我娘睡一觉,那得像打仗一样。我娘脾气不好。我爹和我娘睡觉,都是我爹喝了酒之后,那时候的我爹才像个男人,天不怕地不怕,把我娘使劲往炕上拖。他撕我娘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把我娘的衣服全剥光,我娘咬他,他就抡起巴掌扇我娘几个耳光。我爹虽然个子小,但我爹有把子力气,他把我娘摁倒在炕上,使劲地用身子顶我娘,顶了一会,我娘就不挣扎了,不挣扎了,我娘就像个面条一样任他糟蹋,就开始叫。我娘叫起来像唱歌,像哭不是哭,声音颤颤的,我爹这个时候就会很兴奋,像一匹野狼一样发出呜呜的声音,把炕弄得啪啪响。好半天,我娘不叫了,我爹也不动了,趴在我娘身上,像一滩烂泥,大口喘粗气。有几次,我家的炕都被他俩弄塌了一个大窟窿。
这个时候,我奶奶就会把我拉进西屋里,使劲敲木鱼,一边念阿弥陀佛,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似笑非笑。
村上不断有野男人跑我家里来和我娘说话。
我娘就看着他们笑,我娘笑起来,真好看。
我娘也和他们说几句,我娘一张口,是南方话,带着点儿普通话,怪好听的,像山里的鸟语。男人们就拿眼直勾勾地看她。
我奶奶拿起拐棍轰鸡,“去哦,去哦——”还把一口浓痰吐在门口,把拐棍摔得啪啪响。
我娘虽然不下地干活,但我娘也不是全都被锁在屋子里。每次跑了之后,锁不了一个月,我爹就会心疼地放开我娘。特别是生了我妹妹之后,看我娘疼爱我妹妹的样子,我爹就放心了些,干脆不锁娘了。
娘就在家里绣绣花,种点辣椒,给妹妹梳个辫子什么的。有时候,娘也会出去,到房前屋后,到门前的小山上走走。
娘一出去,奶奶就给我使眼色,让我跟着她。我不在家的时候,奶奶就让妹妹跟着她,形影不离。有几次,我偷偷跟在娘后面,可是走着走着,娘就跟丢了。跟着娘太无聊,没一点意思。有几次娘发现了,就打发我回家给她拿东西,我一回家,娘就不见了。还有就是,我在路上捉个蚂蚱的功夫,娘就不见了。
我围着山找半天,有时候会看见娘从树丛里钻出来,脸红扑扑的,衣服上还有泥巴。有时候,她会从场院的玉米秸垛里钻出来,衣服上还沾着玉米叶子。娘的头发散开了,脖子里一个血印子。
爹就会闷了头抽烟,抽完烟,喝酒,喝完酒把娘摁在炕上,使劲打娘,折腾娘。
我读完小学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一切,我就开始恨娘。
村上的男人们见了我,总爱让我喊“爹”,“刘天草,喊爹。喊爹。”
我背起书包一口气跑回家里,气得我把奶奶的木鱼都摔坏了。奶奶拾起来继续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有人说,村上的光棍们挣了钱,除了抽烟喝酒,钱都跑到了我娘口袋里。有一次,我也发现,我娘口袋里有一沓子钱,十元钱一张,一大摞。我娘不让我说,给了我一张,就藏起来了。
娘第五次逃跑,被叔叔从口袋里翻出来三千元钱。叔叔就怀疑这些钱是娘不要脸挣来的。
这些龟孙子,我真想杀了他们!爹骂。
我也恨死了娘,可我不能把娘杀了,我偷偷磨快了一把刀,我想把我们村的光棍一个个都宰了。至少把他们的下身割下来喂狗,让他们不再发骚。
该杀的。都该杀。
全杀掉也不可惜。
我有时候也恨爹,我看见他那个熊样我就生气,他只知道生气,我恨他为什么不把我们村的那些野光棍们都杀干净了? !
我十八岁的时候,考上了大学,当我终于要离开家,离开大山,离开娘的时候,我真高兴啊。我真是一刻也不愿意在家里待了。
我被四川的一所大学录取了。
上大学离开家的时候,娘瘸着腿送我出门,她眼里含着泪,把一沓子钱塞给我,我没要,我一把把钱甩在了她面前的泥地上,泥地上砸起了一股白烟。
4
学校坐落在大城市里。第一次走进大城市,大城市真美啊。美是美,可在这座大城市里,我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那些高楼大厦,那些穿着漂亮衣服的同学,让我羡慕,他们好像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我离开家的喜悦很快被想家的念头冲得干干净净。
特别是在夜里,我突然很想家,想娘,想爹,想奶奶,想妹妹,想讨厌了十几年的山山峁峁……我就像一株水土不服的庄稼,病病恹恹,吃不香,睡不着。
我觉得我是病了,我拼了命学习,走出大山,我怎么会这么想家呢?
我竟然特别想我娘。那种想念很强烈,我甚至想逃回家里去。后来,我就明白了娘为什么一次次拼了命也要逃跑了。我很懊悔把钱摔在了娘眼前,我害怕她眼里露出的眼神,我真的害怕极了。
我娘已经腿瘸了,不用担心她逃跑了。但我害怕她死了。
我写信给妹妹,让她好好看着娘,好好疼爱娘,别对娘发脾气,要时刻警惕着娘,别让娘做了傻事。妹妹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在家里和娘作伴,娘最疼她了,她也心疼娘。
妹妹和娘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也白白净净的,黑头发,红嘴唇,笑起来有一个小酒窝。娘不爱笑,妹妹却和她不一样,总是笑笑的,有什么可笑的!
大一下半学期的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是四川的。她家在城市里,她是个城里姑娘。她很活泼,也很爱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喜欢我。我问她,她说她喜欢我像山一样沉稳。她说她不喜欢四川的山,四川的山不是真山,是土山,总是喜欢滑坡,禁不住地震。她向
往北方的山,向往泰山,向往沂蒙山。大气。她说。那是男人的山。我牵着她的手,搂着她的腰,指给她东北方
向看我的故乡,我告诉她那里的山很多,一圈又一圈,一座又一座的,进去了就走不出来。
她高兴地搂着我笑,说,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到你们那大山里去隐居去。种种菜,栽栽花,住石头房子,看北方的大雪,喂鸡,喂狗,还要喂两只猫。
好不好?她仰看着我,等我呼应她。我哭笑不得,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看着怀里的这个姑娘,我不禁想起娘来,想起娘故事里那个遥远的地方。我说,暑假我们去你们这里的山里去看看吧。她说,好啊,那明年你也要带我去你们那里看看。她和我拉钩,我迟疑着伸出手,有些犹豫。大一暑假的时候,我跟着姑娘去了四川的山里。她说她去过那个地方,地震前去过一次,地震后也去过一次,她还去做过志愿者。
一想起那个地方,我心里就痛得慌,但我必须去一次。按照记忆中娘说的那个遥远的镇村的名字,转乘了四次车,到了那里。在我的想象里,那里和我的老家,应该是差不多的模样,一片破破旧旧的。
到了。但没有旧街道,没有旧房子,到处是鳞次栉比的漂亮楼房。
一座座干净的楼房拔地而起,宽阔的马路,成排的女贞树,孩子们在路边草地上放风筝。有风吹过来,凉爽爽的,像娘睡着时呼出的气息。
杨家埠。这就是杨家埠。哦。不知道娘来了认得眼前的这个地方吗?
地震之后,一切都变化了模样。杨家埠村幸存的老人指着一片废墟,唏嘘不已,但语气已经没有意料中的哀伤。
杨阿囡。
二十一年前失踪的小女孩。
杨家的小女儿,有一个小酒窝。活着的都搬了新居了,这一家子,一个也没有了。老人喃喃说。娘当年要是没跑出去,娘会不会也……我不敢再往下想。
远处的山上,树木又绿起来,堰塞湖的湖水,绿得发蓝,一层白云在山顶上缥缈着,仿佛是一带水波,夕阳下金光粼粼。
我点着一支烟,放在废墟前面的泥地上,眼睛里涩涩的,有些疼。娘,我替你回来过了。我心里一阵绞疼,我知道有血埋在这里。我拿手机拍了照。回去的时候,我拿给她看。她就再也不用来这里了,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她第六次逃跑了。
5
妹妹失踪的第二天,娘给我打来了电话。你妹妹丢了。娘哭着说。她说她要到外面看看去,她要看看外面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她要去跟着人家一样挣很多很多钱,傻妮子。娘哽咽着说。她入了传销了。妹妹十七岁了。妹妹也长大了。十七岁的妹妹,怎么会这样和娘一样在大山里一天天呆下去呢。我记起来,娘那时候跑掉的时候也是十七岁。十七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真的很关键。
6
再后来,我老家的大山来了许多外面世界的人。山里人还没有走出去,他们倒是从外面进来了。那些人放着小路不走,却偏要在腰上挂上绳索,去攀岩,走悬崖峭壁。夏天的时候,已经摔死了两个北京人,但这并没有让他们害怕,他们来的人更多了。他们都穿着运动服,戴着鸭舌帽,厚厚的皮手套,墨镜,男的,女的,一群又一群,他们不吃大鱼大肉,偏抢着吃山里的野鸡蛋、野土豆。
他们来了后,就不断地拍照,不断地在山里喊,太美了,太美了。
世外桃源,世外桃源。他们兴奋地喊。
他们翻上了我们当地人从未去过的云蒙峰——挂心橛子。那里据说有妖怪,谁也没有上去过。爹那天在山上目睹了他们攀上顶峰的一刻,他仰着头,看那长长的绳索上,像串着一串蚂蚱。
有一天,我家里也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在我们院子里到处看,看看这,看看那。他们给奶奶拍照,给娘拍照,也给爹拍照。爹躲开了。爹不愿意照相。他们要求在家里吃饭,我爹和我娘愁坏了,家里哪里来过这么多人吃饭?他们说,就吃野菜,吃粗粮,他们看见我们猪圈里喂猪的野菜和红薯,兴奋地说,就吃这,就吃这。吃完了,他们就在我家的草房里土炕上睡觉。土炕上睡不开,他们就把随身带来的帐篷搭起来,在我家院子前的空地上搭起来一溜儿。他们男男女女也不害臊,一对一对的挤在一个帐篷里睡觉,晚上的时候,女人的叫声比我家的绵羊叫得还好听。
娘踮着瘸腿,忙里忙外,脸上露出隐隐约约的酡红色。这是她二十年来,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人,大城市来的人。第二天,他们夸她烧的菜好吃,她的土鸡蛋好吃。临走的时候,他们留下一大把钱给娘,娘不要,他们就硬塞给她,他们说,他们还会来的,不仅他们来,还会带着更多的人来,他们让爹和娘好好盘口大锅,好好养一群鸡和羊,好好垒两个大土炕。
娘从来没见过挣钱这么容易。娘拿着钱,呆愣了一般。
奶奶继续敲她的木鱼,响声更好听了。
我把手机的照片给娘看,娘看了一眼,她愣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继续干她的活去了。
责任编辑 包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