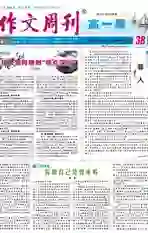重现的西藏
2016-05-09刘馨忆
刘馨忆
在这以前,我听过许多有关西藏的音乐。最早是才旦卓玛的歌,民歌似的唱法中融入了太多欢快明亮的色调,表达的是对新生活的热情赞美,对藏民族最本质的宗教和精神生活未有更多的关注。后来我在西藏听到了真正的民歌。那是在边陲亚东,我因搬运设备而爬上了一座高耸的山峰。在它陡峭的山崖上,我坐在一个突兀的大石头上休息,下面是沟壑深涧,对面群山莽莽,远处的山峰被白云遮蔽,云天相接,一片白茫茫。那辽阔、深远、苍凉,让我几乎不能呼吸。就在那霞云渐退、暮色四合的时候,一阵野性十足的歌声破空而来:
“说给情人的话,已刻在石头上;急风暴雨三千年,花纹也不会变样。”
金属般的歌声打着颤声,像起风时地上卷起的沙柱,螺旋似的翻卷伸延在一片苍茫之上。我感到内心一阵震动,止不住流下了泪水。西藏的民歌为什么大异于别的民族呢?我想,在西藏那辽阔、深远、苍茫和凄美的大背景上,也只有这样野性的抒发,才能让你渺小而实在的生命显示出不朽的卓然存在;让你在尘世与寒冷的风里,把握住生命的温热,让你懂得珍视与热爱。
与才旦卓玛,以及后来的李娜的《青藏高原》相比,西藏的民歌就像未规整过的荒原,是生命自然的表述。《青藏高原》则是长着青稞的土地,有了艺术的修饰。只有《阿姐鼓》是土地上长出的一棵伸向天堂的树,充满神性的暗示。我从未像听《阿姐鼓》那样获得了那般丰富的画面感觉,也未曾有那样对西藏最全面最神似的把握。
低缓的叙述之后,仿佛禁不住内心的触痛,音调经历了漫长的回旋婉转像鹰一样陡然飞升,直插云霄,仿佛脱掉苦难肉身的灵魂,渴望升入天堂。然而,因为太想念酥油茶的浓香,太想念没有阴影的家园,太想念人们整夜燃着酥油灯,保持屋的明亮,太想念处处村落中弥漫的祥和、宁静和怡然,高入天际的吟唱又如缓缓飞行的大鸟,悄悄降落在村落之中,看见家家户户的风铃摇晃并发出悦耳的声音,凝视那一盏盏终夜不熄灭的灯,任月光撒落身旁,心中不禁涌起阵阵的欢欣。于是,歌声舒缓温柔、满怀爱意地抚摸着大地,轻轻地向我述说。于是在这样的夜里,我听见了孩童的嬉戏声,听见了喇嘛在晨曦中的诵经声,高岭上拂过的风声……
我常常听不清她唱的是汉语还是藏文,不知她唱的是什么,但我就像那位感动得泪流满面的西方女孩一样,已完全理解、听懂了她的吟唱。正应了音乐是没有国界的那句老话,所以,《阿姐鼓》才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真正在全球同步发行的中文唱片,在同一时间感动了世界。
这是那位独行的诗人朋友从西藏给我寄来的碟片。他还在我沉迷得只想也随风而散的时候,拨打电话给我,讲那个遥远的然而已切入了我生命的西藏。于是,西藏便在那些黑沉沉的不眠的夜里,在那经久不息的音乐声中,重现在我的心里,重现在时光之中,让我重新把握了那段过去的时光,从而感到了自己确切的存在。在岁月的淘洗之后,当你不幸坠入命运给你的苦难和磨砺之中时,西藏就如一只神鹰,开始高高低低地飞旋在想念者的心里。你的所有苦难,因了这只神鹰的俯瞰的关注与理解的旋舞而化入高原雨季的云彩,也因了黑色的神鹰所寄予的理念与精神的象征而让你得到一种向上的力量。
普鲁斯特说:“唯一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唯一真实的乐园是失去的乐园。”西藏,无疑是我的乐园之一,我像每一个曾经踏上过这片领地的人一样,已把它当成了精神与情感的双重家园而为它魂牵梦绕;也像每一个离去者,有一个精神的结,从离去的那一刻起就总梦想着有一天,能再一次重返这片神奇的土地。然而,无论我们怎样地努力,也永远回不到过去了。天空、草原、道路和岁月一样转瞬即逝,即使我们徒然回到曾经喜爱的地方,我们也不可能重睹它们:因为它们不光是位于空间中,而且是处在时间里。因为重游旧地的人不再是那个曾以自己的热情装点那个地方的少年。我们拥有的是不能忘却的记忆,只期待着在与过去相同的气息里,失去的乐园在我们的生活中显现出来,重新照亮我们的生活。在那些幽闭的日子里,音乐里的西藏给我带来了宁静和幸福。
(选自《重现的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