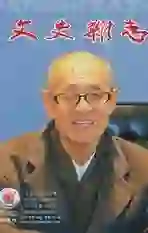蜀族族名含义新探
2016-05-05徐晨
徐晨
摘 要:“蜀”象野蚕之形或象毒虫之形的传统看法缺少有力证据。古代文献以及战国竹简可以证明:“蜀”通独(繁体“獨”),是独的假借字;蜀族的蜀的本义是独立的意思,蜀族是独立于中原文化圈之外的部族。
关键词:蜀即独;蜀族即独族;蜀族族名
对古蜀族“蜀”字的释义,比较普遍的是将其释为蚕。《说文·虫部》释“蜀”:“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段玉裁注:“葵,《尔雅》释文引作桑。《诗》曰:蜎蜎者蜀,蒸在桑野,似作桑为长。《毛传》曰:蜎蜎,蠋貌,桑虫也。《传》言虫,许言蚕者,蜀似蚕也。”《广韵》引此文作蜀,蜀正字,蠋俗字。娟娟,系蠕动曲屈之态。蠋,是蛾蝶类幼虫的统称,这里特指桑中之虫,从而可以得出蜀是桑林中生活的蚕,即蜀蚕相通的结论。由于上述文献的影响,孙冶让的《契文举例》,商承祚的《殷墟对字类编》,叶玉森的《殷契勾沉》以及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解》等都将“蜀”解释为蚕。一些学者认为“蜀族”是古代从事蚕桑的民族,这种解释似乎不能全然令人信服。[1]
其实,蜀、蚕,是有区别的。《韩非子·说林下》:“鳣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渔者持鳣,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为贲、诸。”《淮南子·说林训》:“今鳣之与蛇,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憎异。”高诱注:“人爱鳣与蚕,畏蛇与蠋。”它们皆认为蜀、蚕非一,而蜀(蠋)是一种毒虫。《说文·虫部》释“蜎”:“蜎,肙也,从虫,肙声。”段玉裁注:“小虫也,《毛传》曰:蜎蜎,蠋貌,桑虫也。其引申之义也,今水缸中多此物,俗谓之水蛆,其变为虫。”在殷墟甲骨文中,“蜀”与“蚕”在字形上的区别也很明显,不可混同。
有学者认为,蜀以虫为偏旁,这是商代的统治者对蜀人的一种贱称,说这与历代王朝在少数民族的族称用字都加偏旁“犭”或“虫”,是一致的。[2]细究起来,这种说法也似难成立。从甲骨文看,商代用作方国名和地名者,无一贱称之例。“蜀”在西周曾被视为“四极”之一,《班簋》载:“乍(作)四方亟(极),秉緐(繁)蜀巢。”其中的三极即秉緐巢和蜀一样,并未加“虫”加“犭”,不应视作贱称。周代的中央王权得到极大加强,远非殷商王朝与众方国之间的松散的联盟关系可比,于是华夏自我中心主义思想相应地膨胀起来,“严夷夏之防”,以贱名称呼四夷少数民族的现象开始出现。“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且字不从虫,从虫之蜀始见于西周时期的周原甲文,所以,“蜀”起初并非贱称,到了周代以后才是。[3]
还有一种可能是“蜀”通独(繁体“獨”),是独的假借字。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被发掘,出土竹简804枚,约有13000字,其时代为战国晚期,公元前300年左右。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篇第7号简有:“蜀行,猷口之不可蜀言也。”第54号简有:“蜀凥而乐。”第60号简有:“毋蜀言,蜀凥则习父兄之所乐。”其中的“蜀”,帛本、今本作“獨”。郭店简《老子》甲第21号简:“蜀立不亥。”其中的“蜀”,帛本甲、乙,王本作“獨”。《五行》第16号简:“君子慎其蜀也。”蜀,帛本《五行》第223号简作“獨”。 [4]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得一批战国时期楚国竹简,2001年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2002年出版了《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其中上博简《诗论》第16号简:“《燕燕》之情,以其蜀也。”上博简《中弓》第12号简:“蜀言厌人,难为从正。”蜀言,读为“獨言”。上博简《周易·夬》第38号简:“九晶(三):君子夬夬,蜀行遇雨。”蜀,帛本、今本作“獨”。上博简《君子为礼》第9号简:“蜀智,人所恶也。蜀贵,人所恶也。蜀富,人所恶也。”蜀,读为“獨”。 [5]从对以上楚国的竹简的释读中可以得出,“蜀”是独(繁体“獨”)的假借字,“蜀”有独的意思。
除此之外,《尔雅注疏》卷七释“独”:独者,蜀(蜀亦孤独)。[疏]“独者,蜀”。注“蜀亦孤独”。释曰:“言山之孤独者名蜀。”《方言》卷十二:“一,蜀也,南楚謂之獨。”《山海经》云:“獨山,多金玉美石。”对《管子·形势》篇“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一句,历来解释可谓众说纷纭。其实“抱蜀”就是“抱獨”的意思,而“獨”就是“一”,“一”就是“道”。“抱蜀”就是守住“道”;守住了“道”,便可无为而治,庙堂社稷之政务自然也就会巩固,一切所作所为就会功成名就。[6]
对于中原以炎黄部落为主体的华夏族来说,古蜀国地处偏僻的西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与华夏族截然不同。《文选》左思《蜀都赋》刘渊林注引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引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折权、鱼易、俾明。其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与中原相比,“左言”为语言之异,而“左衽”则为服饰之异。[7]
先秦时期中原王朝往往以右为尊,而一些周边少数民族则以左为尊。《文选·六臣注》载唐吕向曰:“侮食、左言,蛮夷国也。”此为释“左言”之最古者。[7]《礼记·王制》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注:“右学,大学也,在西郊;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礼记·曲礼上》:“献粟者执右契。”郑注:“契,券要也。右为尊。”《礼记·檀弓上》:“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注:“丧尚右,右,阴也。”《正义》:“此即凶事尚右。”《老子》三十一章:“凶事尚右。”“用兵则贵右”注:“贵右者,以丧礼处之也。”《礼记·少仪》:“卒尚右”注:“右阴主杀,卒之行伍以右为上,示有死志。”正义:“卒尚右者,言士卒行伍贵尚于右,右为阴,示其有必死之心。”行伍,排列的行列。现行伍的“向右看齐”,仍应为士卒行伍尚右的残留。[8]
上述“左言”为秦灭蜀前蜀人之言,《汉书·地理志》言:“巴、蜀、广汉本南夷”,是为实录。《蜀王本纪》以及相关典籍,还有《辞源》等的记载都是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出发的,所说的“时人萌椎髣(当为“髻”之讹),左言,不晓文字”是中原华夏族对蜀人的看法。
20世纪30年代的考古发掘,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掘与考古以及对巴蜀历史文化的进一步探究,使许多巴蜀文物重见天日并且得到阐释。有些文物上有巴蜀文字或符号,例如四川新都、郫县张家碾、峨眉符溪出土的铭文戈以及收集的三角形铭文戈等铜戈都系战国时器物,其上铭文成行成句,可以认定为蜀族文字。[9]这些古蜀人的兵器常饰以虎纹,以援脊作为吐出的虎舌……蜀国的兵器演变自有脉络,与中原有别。[10]蜀戈上的铭文无论从文字形体、还是书写方式都与中原的甲骨文不相同,可以看出古蜀人的文字是中原华夏族甲骨文体系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文字,古蜀族是独立于中原文化圈之外的民族。“蜀”应该是中原华夏族对蜀的称谓,不是蜀族人的自称。对古蜀国的文化发展,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说:“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11]
《战国策·秦策一》有:“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伦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李白《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亦可证明古蜀族是独立于中原华夏族之外十分独特的西僻之国,戎狄之长。对于华夏族而言,这个民族是个独立的、独特的部族。
古蜀人崇拜虎,从出土的几件蜀戈来看,其上有虎纹。四川峨眉符溪出土的蜀族虎纹双髻跪人铜戈,虎身和虎尾在胡部,虎头在援末部,大大张开的虎口朝向援锋,紧挨虎口,屈跪着双手双脚被缚的双髻巴人。这个图像表达的可能是蜀虎吞食巴人,以巴人祭虎的图像,象征蜀人战胜巴人的内容。[12]孙华先生说:“巴蜀符号大部分都有虎、羊、心等图形……蜀地也有崇虎的部落。”[13]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金虎和青铜虎,造型生动,说明了古蜀人有崇虎的习俗。这与中原对龙的崇拜截然不同,也说明古蜀国的文化是独立发展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先秦时代,中原王朝判别其他周边国家是否为少数民族的标准,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主要以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为依据。周边国家的风俗、语言、饮食等与中原王朝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国家就会被中原王朝认为是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异族国家。蜀国的左言、左衽等与中原王朝的右衽、右言以及甲骨文为主的文化内涵截然不同。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蜀”与“獨”通假,蜀族族名的含义是獨族,是独立于中原文化圈之外的独特的民族。
注释:
[1]参见钱玉趾.巴族蜀族族名的由来及含义辨析 .[J].当代电大,1990.
[2]参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 .[M].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55.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 .[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36.
[3]参见贾雯鹤.圣山:成都的神话溯源——《山海经》与神话研究之二 .[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
[4]参见刘信芳.楚简帛通假汇释.[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66.
[5]参见蒙默.蜀王本纪·“左言”“左衽”辨释及推论 .[J].文史杂志,2012.
[6]参见朱英贵.释“蜀”.[J].成都大学学报,2011.
[7]参见洪颐煊辑.《蜀王本纪》见所撰《经典集林》卷十四.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录洪辑以入其书之扬雄卷,仅增一条,而又未予说明.
[8]参见张霭堂.古汉语左右尊考释 .[J].玉溪师专学报,1987.
[9]参见钱玉趾.巴蜀文字与神秘文字 .[J].人民日报,1933.
[10]参见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青铜器 .[J].文物出版社,1987.
[11]转见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 .[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15.
[12]参见钱玉趾.巴蜀史与古文字探 .[M].天马出版社,2010.15-16.
[13]孙华.巴蜀符号初论 .[J].四川文物,1984.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