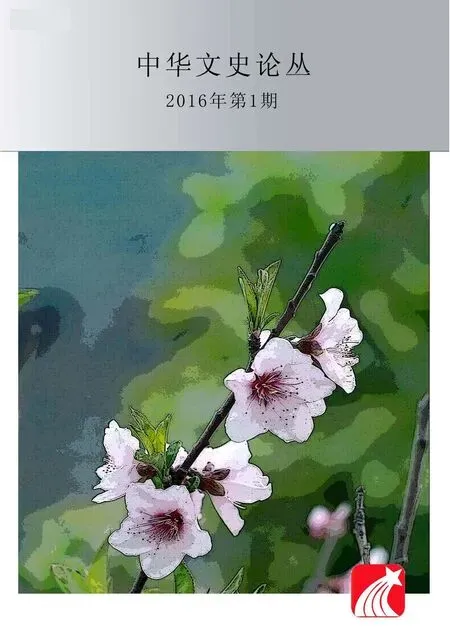再論蒙古進征大理國之緣起及蒙哥與忽必烈間的爭鬥問題——以所謂“斡腹”之謀爲主線
2016-05-04溫海清
再論蒙古進征大理國之緣起及蒙哥與忽必烈間的爭鬥問題
——以所謂“斡腹”之謀爲主線
溫海清
提要: 忽必烈進征大理國向來被描繪成是蒙古對南宋所實施的“斡腹”之謀。然而,依據東、西方史料記載差異可知,蒙古人起初並無以大理“斡腹”而搗襲南宋的深遠圖謀。忽必烈之所以往攻大理,是因面對南宋川蜀地區强固防守力量時不得已而采取的權宜之舉。忽必烈長時間未對南宋展開正面進攻,應是引發蒙哥對他猜忌和不滿的主要緣由。蒙哥御駕親征,以川蜀作爲突破口,而此正是蒙古滅宋所長期奉行的固有戰略;忽必烈實早已意識到此戰略之弊,其被徹底扭轉則要遲至劉整降蒙以後。“斡腹”說很大程度上是南宋西南邊鄙帥臣出於對蒙軍軍事行動的本能警覺的反應,其淵源有自。
關鍵詞: 斡腹之謀大理國西南邊鄙臆說
一問題緣起: 東、西方史料記載的差異
十三世紀中葉,蒙古人緣何要繞道甘川藏區進征位於今天雲南地區的大理國?無論是宋元之際當時代的人們,還是後世的歷史編纂者們,在講述這段歷史時都有一種典型的模式化敍述: 蒙古人當時已有假道藏區先圖大理國而後再迂回包抄以搗襲南宋的戰略遠謀,故而憲宗蒙哥汗命忽必烈遠征大理,即所謂“斡腹之謀”。*“斡腹”之說,當時代即已流行。郝經於1259年評述忽必烈征雲南之舉時稱:“自漢中至於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所謂“示遠之謀”,即“斡腹”之謀的另一種表達,這是蒙元方面有關“斡腹”之說的最早敍述。南宋方面將1220年代以來蒙古軍隊在川蜀及其周邊地帶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均視作爲一種假道“斡腹”之舉,此種說法,俯拾可見;而1257年兀良合台統領軍隊由雲南北上攻宋,則是宋以來人們通常所稱蒙古人存有“斡腹之謀”的主要論說對象。宋元之際有關“斡腹之謀”的此類模式化敍述,自元以降,歷明、清而迄於今,且無論中外,其基本主旨未變。作爲這一傳統敍述框架的堅定維護者,近年來石堅軍發表系列論文,縱論前四汗時期蒙古軍隊之種種“斡腹”圖謀,甚而提出自成吉思汗時代起蒙古就業已形成“斡腹之謀”的對宋總體戰略。石氏對“斡腹”問題的論述,用力頗勤;然因其太過篤信成說,難免有過度闡釋之處。參閱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二《東師議》,《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1),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7年,頁757上—760上。石堅軍已刊系列論文: 《“斡腹”考述》,《內蒙古大學學報》(哲社版)2008年第5期;《蒙古前四汗時期蒙藏關係新探——以“斡腹之謀”爲視角》,《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年第3期;《蒙古與大理關係新探——以“斡腹”之謀爲視角》,《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10年第4期;《蒙哥汗滅宋戰略計畫新探》,《內蒙古大學學報》(哲社版)2010年第4期等。然而,這一廣爲人們所熟知、接受的歷史敍述,是否完全符合當日的歷史實情呢?
我們首先需要仔細檢核涉及此事件相關的主要漢文史料。
據《元史·憲宗紀》載憲宗二年(1252):
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諸王禿兒花、撒(丘)〔立〕征身毒,怯的不花征沒里奚,旭烈征西域素丹諸國。
《元史·世祖紀一》亦載憲宗二年:
夏六月,入覲憲宗於曲先惱兒之地,奉命帥師征雲南。秋七月丙午,禡牙西行。*所謂“諸王禿兒花、撒(丘)〔立〕”,應作“禿兒花撒立”。禿兒花爲蒙古語“質子”意;“撒立”,應指“撒里那顏”,爲人名。屠寄認爲,此人爲質子,“並非諸王”。“諸王”兩字衍。參見《元史》卷二,三,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46,58,校勘記〔六〕,頁55;〔伊朗〕 拉施特(Rashīd al-Dīn)《史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29;屠寄《蒙兀兒史記》,北京,中國書店影印,1984年,頁57下。
上述兩條最爲基本的史料出於“本紀”,應當是官方的正式記錄,其權威性自無需贅言。那麽,“本紀”之外其他相關史料又是如何記述的呢?
據《元史·兀良合台傳》載:
憲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總兵討西南夷烏蠻、白蠻、鬼蠻諸國,以兀良合台總督軍事。*《元史》卷一二一,頁2979。
王惲所撰《大元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廟碑銘》亦載:
歲壬子(1252),時世祖皇帝在潛,奉詔征西南諸夷,命公總督大營軍馬,自旦當嶺入雲南境。*《王惲全集彙校》卷五○,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348。
另,據《元史·董文用傳》載:
癸丑(1253),世祖受命憲宗,自河西征雲南大理。文用與弟文忠從軍,督糧械,贊軍務。
《元史·董文忠傳》亦稱:
歲壬子,入侍世祖潛邸……癸丑,從征南詔。*《元史》卷一四八,頁3495,3501。另據虞集《翰林學士承旨董公(文用)行狀》載:“癸丑,世祖以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853。
再,據《元史·賀仁傑傳》載壬子年(1252):
時世祖以皇太弟受詔征雲南,駐軍六盤山。*《元史》卷一六九《賀仁傑傳》,頁3967。據《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謚忠貞賀公神道碑》載:“歲壬子,憲宗國母弟世祖於秦,受詔征雲南。”參閱查洪德輯校《姚燧集》卷一七,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頁269。本文簡稱此神道碑爲“《賀仁傑神道碑》”。
上述五則史料中所涉及的三位傳主,均爲伴隨忽必烈出征大理國時重要人物。兀良合台是此番進軍大理國的前鋒統帥,其地位僅次於忽必烈;董文忠、賀仁傑兩人則是忽必烈的怯薛宿衛士,隨侍於忽必烈左右。*《元史·賀仁傑傳》載:“仁傑從世祖,南征雲南,北征乃顏,皆著勞績。後與董文忠居中事上,同志協力……”頁3968。有關董文忠作爲怯薛宿衛士隨侍忽必烈並深受其寵幸的記載,參閱《姚燧集》卷一五《董文忠神道碑》,頁229—232。
梳理以上“本紀”、“列傳”、“先廟碑”等記載,我們可以得到兩個非常明確的基本信息: 忽必烈進軍大理國,實乃尊奉憲宗蒙哥汗之成命,此項戰略謀畫應是蒙古大汗及其宗王們所共同議決的;1252年,忽必烈本人還在漠北的時候,就已經領受了這個既定的出征任務。長久以來,人們在談論忽必烈負有“斡腹”之遠謀而受命進征大理國時,應該說都源於上述記載。*此類敍述甚夥,兹按時代,舉數例如次: 《至元辨僞錄》卷四載:“蒙哥皇帝初,壬子春,詔以今上皇帝征吐蕃及花馬、大理等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77),1998年,頁523下。楊慎《南詔野史》上卷云:“是年,南宋理宗壬子淳祐十二年(1252),爲蒙古憲宗之二年七月丙午,太弟忽必烈等奉憲宗命,伐大理,受制專征。”《中國西南文獻叢書》,86册,蘭州大學出版社, 2003年,頁226下。晚近,西人多桑稱:“1252年,忽必烈奉命經略雲南。”《多桑蒙古史》,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70。現當代影響廣泛的蒙元史著作,如《蒙古帝國史》、《元朝史》、《劍橋遼西夏金元史》等,表述主旨與此基本一致,兹不贅述。
然而,倘若我們再細加審讀上述史料,又會發現其中存有些許疑問。如上引《元史·董文用傳》稱:“癸丑,世祖受命憲宗,自河西征雲南大理。”這則記載與其他數則史料的記載存在所指時間與地點上的差異。所謂“癸丑”年受命,與其他史料所記載“壬子”年,有一年的差異。這種年份不一致的記載,其所指涉的真實含義,事實上可以得到比較好的解釋: 壬子年受命,癸丑年正式出征。*關於忽必烈進征雲南的具體時間,參閱方齡貴《忽必烈征大理史事新證——新出元碑〈故大理□□氏躬節仁義道濟大師墓碑銘并序〉考釋》一文的相關考證,《思想戰線》1987年第4期。因此,時間記載差異的問題,或可得其解。
另一方面,若從地點的差異上去加以索解的話,疑問便凸顯了出來。我們可否懷疑忽必烈其實是在“河西”接到出征大理國的命令,而非在“漠北”地區呢?據姚燧撰《賀仁傑神道碑》載:
初,歲壬子,憲宗國母弟世祖,於秦受詔征雲南,禡牙略畔之山。*《姚燧集》卷一七《賀仁傑神道碑》,頁269。原點校者“於秦”後點斷,本文與之微異,但文意一致。另,本文所引凡字下有點者,均爲筆者所加。
此處所謂“於秦受詔征雲南”,非常明確地透露出,忽必烈是在“秦”地(指今陝西地區)接到蒙哥命其出征大理的詔旨,而並非前述諸種史料所稱是在“漠北”地區。《元史·董文用傳》中所稱“河西”之地,與《賀仁傑神道碑》中所謂“秦”地,其所指地域並無太大區別。1253年,忽必烈已在南方,正“駐軍六盤山”。六盤山位於今寧夏、陝西交界處,元代常稱原西夏所屬區域爲“河西”,蒙古人又音訛稱之爲“合申”,源於其地曾屬唐代“河西節度使”轄制。*大蒙古國時期,少林寺蒙漢合璧聖旨碑文的蒙文“Tangγu(t)”,即唐兀惕(指西夏),其漢文對譯原文爲“河西”。另據《元史譯文證補》卷一五《海都補傳》稱:“太祖征西夏,合失生。西夏爲河西地,蒙古稱河西音似合失,轉音爲合申,(轉下頁)( 接上頁) 名以合失,志武功也。合失嗜酒早卒,太宗痛之,自此蒙古人諱言河西,惟稱唐古忒。”河西有廣、狹義之分,狹義於此應指西夏,西夏處黃河之西,故名; 廣義或爲黃河以西之地,誠如前田正名所言,處於塔里木盆地和中原之間的那塊廣闊的區域,均被視作“河西”。以上參閱道布、照那斯圖《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聖旨碑考釋》及《考釋( 續一) 》,《民族語文》1993 年第5、6 期;洪鈞著,田虎《元史譯文證補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211; 前田正名著、陳俊謀譯《河西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 年,頁1。因此,這似乎印證了我們的懷疑,即忽必烈並不是在漠北領受進軍大理國命令的。
那麽,我們該如何理解漢文史料記載中出現的這種牴牾情形呢?漢語文獻中所出現的這種無法協和一致的記載,究竟是一種無意爲之的“疏漏”,還是別有“隱情”?通過比對西方世界的另一部“元史”,即伊朗史家拉施特《史集》的記載,我們或可找到些許答案。
據《史集·成吉思汗的兒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紀》載:
在大忽里勒台召開後的第二年……聖慮開始移注於征服世界上東、西方的遠方各城。首先,由於有許多人要求對邪教徒的不義行爲加以審判,提出自己的控告聽從聖裁,蒙哥合罕便於牛年[1253年],派遣他已經看出臉上有王霸之徵和帝王福份的兄弟旭烈兀汗,前往大食地區討伐邪教徒。虎年[1254年],他又派遣仲弟忽必烈合罕去征服和防守東方諸城,並派出札剌亦兒部落的木華黎國王同他一起去。這些事將詳細記述於他們各人的紀傳中,因爲他們[旭烈兀和忽必烈]都是君主。忽必烈合罕出發後,他從途中派遣急使[奏告說],沿途沒有食物,進軍極爲困難:“若蒙頒降聖旨,我們就到哈剌章地區去。”聖旨准許後,忽必烈合罕就去攻打以罕答合兒之名著稱的地區,洗劫了那裏以後,他回到了蒙哥合罕處。*《史集》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264—265。
又,《史集·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紀》載:
當英君蒙哥合罕即位時,他的京城在斡難-怯綠連地區的哈剌和林境內,安排了國事後,他派自己的兄弟忽必烈合罕前往東方諸城和乞台諸地,而幼弟旭烈兀則被他派往西方和大食地區,有如其本紀中所述。他降旨,命令全部八十萬蒙古和札忽惕軍隊同他[忽必烈合罕]一起前往乞台[漢地],要他們留在該處並征服與乞台接壤的南家思地區。忽必烈[合罕]出發了,但他並未取道直趨南家思,因爲該處的君主已經把途中各地的[一切]食物弄得精光,向那方面進軍很困難,他便向蒙哥合罕派去急使奏告情況,請求允許先征服哈剌章和察罕章地區,爲軍隊取得糧食,然後再向南家思前進。那兩個地區,在漢語中稱作“大理”,意即“大國”,忻都語作“犍陀羅”,我國[伊朗]則稱作“罕答合兒”。……[蒙哥]合罕認可了他的奏告。*《史集》第二卷,頁287—288。
《史集》的上述兩處記載告訴我們: 蒙哥起初是命令忽必烈去“征服和防守東方諸城和乞台諸地”,“留在該處並征服與乞台接壤的南家思地區”,“該處”指中原漢地,而“南家思”即南宋,後者是忽必烈的主要進取目標。若將《史集》與漢文史料記載加以比對,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勾勒出當時真實情狀,並解決前文所指出的牴牾問題: 1252年,忽必烈從蒙哥汗處領受的任務是進取南宋,當年秋天,他便離開漠北南下。*《元史·憲宗紀》載: 壬子“八月,忽必烈次臨洮,命總帥汪田哥以城利州聞,欲爲取蜀之計”。頁46。另參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五《平雲南碑》,《元代珍本文集彙刊》(3),臺北,“中央圖書館”,1970年,頁239—243。1253年,忽必烈在南方展開了一系列活動,*1253年夏秋間,忽必烈曾在六盤山會見八思巴。參閱陳得芝《八思巴初會忽必烈年代考》,《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收入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轉下頁)( 接上頁)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315—332。對南方情形已比較熟悉;他發現直接攻宋難度太大,於是臨時遣急使赴漠北蒙哥處要求更改原計畫,請求先行往攻哈剌章,即大理國,抄略該國以獲取糧食、馬匹等物資後,再行伐宋。忽必烈的這一請求最終獲得蒙哥允准。*學界似已意識到此點,如《元朝史》編撰者認爲:“忽必烈向蒙哥提出先取大理以包抄南宋的計策,並親統大軍南征。”同時,根據《元史·兀良合台傳》的記載,編撰者又進一步認爲,“1258年蒙哥命兀良合台從大理率軍北上,約會師長沙,知征服大理以包抄南宋的計畫確已付之實施。”可見,《元朝史》編撰者潛意識中對此所持的仍是蒙古人早已存有“斡腹”戰略的成說。參閲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80,184注釋二。
於此可見,《元史》的記載顯然有其隱晦不明之處,忽必烈進征大理國的緣由問題應當重新予以檢討。職是之故,重新討論忽必烈進軍雲南的深層緣由問題,成爲本文的一大主題。而通過對東、西方史料中涉及此事件的相關記載的上述解析,我們不僅可以合理地解釋東、西方記載的牴牾,甚至對於《史集》內部的混亂敍述也可以作出合乎情理的解答。如《史集·突厥—蒙古部族志》在述及此事件時,就有一處敍述較籠統,其文云:
他[速別台]的另一個兒子叫兀良合台。在蒙哥合罕時,他曾任大元帥。當蒙哥合罕派遣自己的兄弟忽必烈合罕率領十萬軍隊到合剌章國之時,那支軍隊的統帥即爲兀良合台。蒙哥合罕曾下令讓忽必烈合罕和軍隊全都聽命於兀良合台。那個國家離合罕駐所很遠,約有一年的途程,那裏的氣候又極惡劣、潮濕,因此全軍都生了病。此外,這個國家人煙稠密,軍隊衆多,每天在各個停駐之處都得作戰。由於這兩個原因,那十萬軍隊回來的,還不到二萬。*《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260。另有記載亦稱:“當忽必烈合罕奉蒙哥合罕之命前往那些地區(哈剌章)而他的軍隊正處於饑餓和無衣之時。”參見《史集》第二卷,頁340。
《史集·部族志》此處聲稱蒙哥派遣忽必烈出征大理,這似乎與我們以上所解析的情形有所出入。然而細加揣摩的話,我們認爲拉施特此處所言,與漢文史籍以及《史集》其他幾處的記載,並無實質性衝突。因爲所有這些記載都沒有否認忽必烈出征大理國獲得蒙哥允准的歷史事實。需特別指出的是,《史集》敍述前後並不全然一致的狀況,是史書編撰時經常出現的問題。《史集》“部族志”與“紀”的部分,涉及史料來源以及撰寫時間上的差異;拉施特編撰這麽一部大型歷史著作,肯定有一個助手羣體,關涉遙遠東方中原漢地的歷史問題,出現“瞻前不顧後”的情形,在所難免。*《史集》是伊利汗國官方編修的一部具有世界通史性質的歷史巨著,伊利汗的宮廷裏彙集了來自中國、印度、畏兀兒以及欽察等地各民族學者,他們爲協助拉施特編纂此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史集》有關中國歷史編纂的研究,詳參王一丹《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國史〉研究與文本翻譯》,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年。明乎此,或許就毫無理解上的困擾了。
東、西方兩部“元史”的“本紀”部分,一般認爲其基本主體應均源自元朝實錄,它們之間出現的記載“差異”問題究竟該如何對待,這是個十分繁複的問題。我們對待每一件具體史事都必須作出周全的比勘,方能彌補彼此存在的差異與不足。儘管《史集》記載東方世界的史事多有舛誤,但不應否認它所提供或保留的部分“真實”。此處或可就與本文主旨密切相關的問題,再舉例予以說明。
前引《史集·突厥—蒙古部族志》稱:“蒙哥合罕曾下令讓忽必烈合罕和軍隊全都聽命於兀良合台。”針對這一記載,日本學者堤一昭曾指出,有關兀良合台具有總指揮權的說法是拉施特的誤載。事實上,蒙古第二次西征的時候,拔都擔任統帥,而速不台則實際領軍;所謂兀良合台具有總指揮權的說法,亦當作如是觀。換而言之,忽必烈與兀良合台在遠征雲南的具體權力配置問題上,拉施特對兀良合台所具權力的敍述雖有所誇張,但也談不上有太大的錯誤。特別值得進一步留意的是,漢語文獻中有一則關於兀良合台的矛盾記載。
據《元史·憲宗紀》載憲宗三年:
夏六月,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帥師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又命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兒等國。*《元史》卷三,頁47。
從這則記載可知,兀良合台最初是被指派與旭烈兀一起西征的,而不是隨忽必烈出征大理國。這則矛盾記載,最早引起日本學者志茂碩敏的懷疑,他認爲兀良合台是被轉調出征大理國的,不過未作具體說明。堤一昭則對此解釋說,兀良合台轉調一事未見史料記載,“兀良合台”很可能是指“兀良罕部族男子”,因爲旭烈兀遠征軍中兀良罕部族活躍的異密當中就包括速不台家族成員;然而“能夠決定是兀良合台轉調還是另一個人的史料現在尚未出現”。*參閱志茂碩敏《Ghazan Khan政権の中核群について-Il Khan國史上におけるGhazan Khan政権成立の意義》,載《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1979—18(志茂碩敏《哈贊汗政權的核心群——伊利汗國史上合贊汗政權成立的意義》,載《亞非語言文化研究》1979年第18號);堤一昭《クビライ政権の成立とスベエテイ家》,《東洋史研究》48—1,1989(參閱堤一昭著、張永江譯《忽必烈政權的建立與速不台家族》,《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91年第2期)。倘若我們對於前文所述忽必烈往征大理國乃是一種臨時之舉的歷史事實有清晰認識的話,那麽兀良合台届時轉調問題,雖史無明文記載,但其事實卻是分外明晰的。於此可知,兀良合台的臨時轉調,與忽必烈遠征大理國出於臨時謀畫,可謂兩相互證,契合乃爾。
二“滅南宋”與“征大理”: 蒙哥與忽必烈之間爭鬥問題新解
通過對西方文獻《史集》與東方文獻《元史》等記載差異的比較,我們已可明確一項基本事實: 蒙哥最初委派給忽必烈的任務應是出征南宋而非大理國,所謂蒙古人早已存有先取大理國而後再“斡腹”攻宋的戰略遠謀問題,實際並不成立。倘若重新檢討這一基本事實所呈現的細節,它又促使我們進一步追問: 忽必烈臨陣改變攻宋計畫往征大理國,其背後有無更深層次的緣由?或有論者以爲,出征大理國的最終目標還是爲了滅南宋,其間並不矛盾,那麽這種貌似合乎情理的邏輯背後又究竟隱藏什麽問題?爲何漢文史籍不願直接敍述蒙哥最初下達給忽必烈的任務是進攻南宋而非大理國呢?回答這些疑問,不僅可以進一步印證《史集》有關此歷史事件記載的可靠性問題,而且對於我們究明蒙哥與忽必烈兄弟兩人之間的那場著名的政治鬥爭的具體情狀,以及由此而影響及於當時整個蒙元政局與戰局的走向問題,都顯得尤爲緊要。本文圍繞蒙哥滅南宋的既定戰略規畫與忽必烈臨時往征大理國而回避攻宋的策略之間所凸顯出的差異問題進行探討,以揭示兄弟兩人由此而引發矛盾衝突的關鍵所在。
1252年,蒙哥在漠北指派給忽必烈和旭烈兀的出征任務,肯定曾在蒙古宗王大會(忽里台)上宣佈過,並獲得蒙古宗王們的同意。依據伊朗歷史學家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的記載,蒙哥在登上汗位處理了蒙古諸王的問題之後,便將注意力逐漸轉向蒙古人尚未征服的世界:
首先他遣師出征東方和西方,出征阿剌伯人和非阿剌伯人的國土。東方諸邦和契丹,蠻子、肅良合和唐兀各省,他委付給以聰慧機智而著稱的忽必烈斡兀立。他指派高位的那顏去伴隨他,把駐在那些地區的所有左右翼的異密置於他的統率下。西方諸邦邑,他交給他的另一個兄弟旭烈兀斡兀立,後者以他的剛毅威猛,機警持重,以及馭下有力、功名心切而享譽。
因此在大忽鄰勒塔上,當他已穩居汗位,他的注意力不再顧及那些自私自利者和忌妒者的案子後,他把他的思想轉向征服世界上最遙遠的東方和西方。首先他把忽必烈派往包括契丹在內的東部地區,然後在650/1252—3年着手安排和組織他的另一兄弟旭烈兀的事情,委托他征服西部地方。*〔伊朗〕 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699,724。
所謂“東方諸邦和契丹,蠻子、肅良合和唐兀各省”,很顯然當時蒙哥派遣忽必烈鎮守或出征的地區,並沒有包括哈剌章。不過,另有一則記載則顯示,蒙哥分派給忽必烈的任務中包括了哈剌章在內。據《史集·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旭烈兀汗傳》載:
思考結束後,[蒙哥合罕]派其弟忽必烈合罕到東方的漢地、摩至那、合剌章、唐兀惕、吐蕃、女真、肅良合、高麗諸地區以及漢地、摩至那鄰接的忻都斯坦部分地區去,並派定旭烈兀汗到西方伊朗、敍利亞、密昔兒、魯木、亞美尼亞諸地區去,讓他們倆帶着他們所有的軍隊,擔任他的左右兩翼。*《史集》第三卷,頁29。
然而,《史集》此處提及的地域,很明顯就是忽必烈與旭烈兀後來實際進征所及的區域。這是典型的後世歷史編撰者的一種回溯式敍述,它與壬子年當時的實際情形是有出入的。因此,該記載不足憑信。現有研究業已充分揭示,旭烈兀的主要任務是向西進發,他有三大目標: 打擊裏海南部的“山老”(恐怖組織),迫使阿拉伯哈里發投降,並在解決阿拉伯帝國後繼續向西推進。*Peter Jacks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gol Empir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22, 1978.忽必烈的主要出征任務則在東方,除負責鎮守已經征服的乞台(中原漢地)諸地外,他最大的進取目標自然就是南宋。根據《世界征服者史》的記載,忽必烈與旭烈兀都獲得相同的軍隊配置規模,“從東、西大軍中每十人抽二人”、“並派一位宗王”。*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頁724。
我們知道,蒙哥甫一登位,隨即“命皇弟忽必烈領治蒙古、漢地民戶”,“同母弟惟帝最長且賢,故憲宗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遂南駐爪忽都之地”。*《元史》卷三《憲宗紀》,頁44;卷四《世祖紀一》,頁57。忽必烈可謂備受皇兄信任。蒙哥對於忽必烈的期望自然並不限於鎮守已征服的地區,他對忽必烈進取乃至攻滅南宋抱有極大期望。*據《史集》卷二記載:“蒙哥合罕原來就想征服南家思。忽必烈合罕也有這樣的意圖,尤其是當他的京城設在乞台,鄰近他們[南人]的國土之後。”頁318。而忽必烈自身也有備戰攻南宋的謀畫,這從當時他與謀臣姚樞間的對話中就可窺知一二。據《元史·姚樞傳》載:
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祖既奉詔,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者諸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對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曰:“慮所不及者。”乃以聞,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以圖宋;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元史》卷一五八,頁3712—3713。《元史·姚樞傳》當據《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寫成,姚樞提出於汴、衛等地置經略司、都運司之事,《神道碑》所記甚詳:“公(姚樞)策: ‘……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閫犄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繼饋諸州。”《姚燧集》卷一五,頁218。
忽必烈與姚樞之間的對話,以下兩點值得注意: 首先,所謂“赤老溫山南者,聽世祖總之”,於此可知忽必烈受蒙哥器重與信任之深,這猶若當年木華黎受到成吉思汗的信任那般,賦予經略當地之全權。其二,忽必烈自請惟掌軍事,那麽它的直接指向自然就是經略南宋;所謂欲置經略司、都運司等於汴、衛諸地,就是爲攻宋作準備;換而言之,忽必烈領受任務之初的所作所爲,其目標指向都是爲滅南宋。
從上述忽必烈與姚樞間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窺知忽必烈確在籌畫攻宋。同時,我們還可以找到更多的史料來證明,忽必烈在主政漢地的這段期間內,確實也在爲攻宋作各項準備工作。*詳參周清澍《忽必烈潛藩新政的成效及其歷史意義》,載氏著《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466—494。然而在此期間,我們雖可看到蒙宋之間出現過許多小規模的軍事衝突和對抗,*如《元史》卷一二九《紐璘傳》載:“歲壬子,率陝西西海、鞏昌諸軍攻宋,入蜀。癸丑,與總帥汪田哥立利州。甲寅,攻碉門、黎、雅等城。”頁3144。忽必烈主政漢地期間,宋蒙間此類小規模戰事不少,兹不枚舉。詳參陳世松、匡裕徹等著《宋元戰爭史》,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頁106—125。但幾乎沒有看到忽必烈對南宋采取過正面的或直接的大規模軍事行動。若從壬子年(1252)忽必烈領受出征任務時算起,至1256年蒙哥派遣阿蘭答兒、劉太平等赴陝西、河南等地對其進行鈎考時爲止,在這長達五年的時間裏,他雖擁有漠南漢地全權軍事處置之權,但並未對南宋展開過大的軍事行動,可以說在攻宋問題上無甚大的作爲。
然而也正是在此期間,蒙哥與忽必烈之間關係出現裂痕。鈎考事件意味着彼此間矛盾激化至頂點。以往我們對於蒙哥與忽必烈之間的矛盾問題,多傾向於認爲是由於忽必烈經營漢地有方,聲勢日隆,且因其暗中壯大自己勢力,*《元史·不忽木傳》載:“帝每顧侍臣,稱塞咥旃(指賽典赤)之能,不忽木從容問其故,帝曰: ‘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時未生,誠不知也。’不忽木曰: ‘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以手曰: ‘卿止,朕失言。’”頁3170。是知,忽必烈在南方期間的所作所爲,確有其不光彩處,蒙哥由此產生猜疑,合乎情理。另,美國學者愛爾森曾指出,漢文、波斯文以及亞美尼亞的史料記載均表明,旭烈兀的一舉一動以及他驚人的虜獲數量,都隨時向蒙哥彙報;相反,忽必烈在華北的一系列行爲則具獨立傾向,且蒙哥派遣到華北的大臣如牙老瓦赤、不只兒等人,均與忽必烈不睦。參閱Thomas T. Allsen, Mongol Imperialism: The Policies of the Grand Qan Möngke in China, Russia, and the Islamic Lands, 1251-125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p.50。從而招致蒙哥對他心生嫉妒與猜疑。*參閱陳得芝《忽必烈與蒙哥的一場鬥爭——試論阿蘭答兒勾考的前因後果》,載《蒙元史研究叢稿》,頁360— 373。這一說法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當時姚樞給忽必烈的一番建言,就是一個極爲明顯的證據。據《元史·姚樞傳》載:
丙辰(1256),樞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藍答兒大爲鈎考,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鈎考局。*《元史》卷一五八,頁3713。
蒙哥之所以對忽必烈產生不滿,上述所謂嫉妒與猜疑之說自然成立;然而又不免失之於皮相,且易使人對蒙哥產生一種心胸狹窄的負面印象,這對蒙哥是不公正的。事實上,忽必烈臨時更改攻宋計畫轉而進征大理,且長時間回避正面攻宋,這纔應該是引發蒙哥對他不滿的關鍵緣由所在,而此恰恰是矛盾的核心。那麽,這又有何理據呢?我們可從蒙哥之所以御駕親征南宋的起因、經過及結果諸方面來加以詳細考察。
蒙哥爲何要御駕親征南宋?1256年,他在漠北又一次召集蒙古宗王大會,最爲重要的主題就是再度計議伐宋。*《元史·憲宗紀》載:“六年丙辰春,大風起北方,砂礫飛揚,白日晦冥。帝會諸王、百官於欲兒陌哥都之地。”六月,“諸王亦孫哥、駙馬也速兒等請伐宋”。頁49。《史集》對這次宗王大會的情景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描述:
當時,成吉思汗的一個女婿,亦乞剌思部落的帖里垓說:“南家思國這麽近,並與我們爲敵,我們爲什麽置之不理,拖延着[不去出征彼國]呢?”蒙哥合罕稱贊了這些話,說道:“我們的父兄們,過去的君主們,每一個都建立了功業,攻占過某個地區,在人們中間提高了自己的名聲。我也要親自出征,去攻打南家思。”宗王們一致說:“[陛下身爲]全世界的君主,已有了七個兄弟,爲什麽還要親自去和敵人作戰呢?”他說:“既然我們已經說定,那末再去違反就是不合理、不正確了。”*《史集》第二卷,頁265—266。
這段史料明顯反映出蒙古諸王貴族們對於遲遲沒有對南宋展開進攻已存不滿。面對諸王勳貴的質詢,蒙哥作出御駕親征南宋的決定來加以回應;而對於諸王勳貴們的勸止,他則堅決予以回絕。史料中有關蒙哥決定御駕親征南宋之緣由的這番陳詞,或可作深入解析。
蒙哥之所以選擇御駕親征南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因爲每一位大汗都須獲取武功、提高聲名。然而我們知道,蒙哥之前的三任大汗,成吉思汗建有不世之功,勿遑多論;窩闊台合罕與貴由汗在獲取武功、提高聲名等方面,則可再詳察。
窩闊台曾隨父西征,攻城掠地,已有不小功業。登上汗位後,又隨即御駕親征滅金。據《蒙古秘史》記載,窩闊台曾就欲親征金國之事與察合台商議。當時因金已處弩末之勢,蕩平金國已不凶險,所以察合台並未予以勸止。*《蒙古秘史》載:“斡歌歹皇帝再於兄察阿歹處商量將去。說皇帝父親的見成大位子我坐了。有甚技能。今有金國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爲如何。察阿歹說是。但老營內委付下好人着。我自這裏添與你軍。說來了。遂委付帶弓箭的斡勒答合兒。留守老營。”參閱烏蘭校勘《蒙古秘史》第271節,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382。同時需要指出的是: 其一,蒙古滅金乃遵奉成吉思汗之遺命;*《元史》卷一《太祖紀》載:“臨崩謂左右曰: ‘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頁25。其二,拖雷在滅金時起主導作用,且爲成吉思汗滅金方略的具體執行人。窩闊台將滅金視作自己四大功業之首,稍有名不副實之感。蒙古滅金當年,即太宗六年(1234)秋,“帝在八里里答闌答八思之地,議自將伐宋,國王查老溫請行,遂遣之”。*《元史》卷二《太宗紀》,頁34。可見,窩闊台於滅金之後曾欲親征南宋,然而明顯被强力勸阻,未能成行,具體緣由不明。同時,與窩闊台發動蒙古第二次西征時欲圖親自領軍出征而不得成行的狀況加以比較,滅金次年(1235),蒙古計議再次西征,此次出征又被稱作“長子西征”,它是蒙古帝國世界擴張進程中的一項壯舉。有關蒙古宗王大會議決此次西征的具體情形,《史集》有所描述:
他(指窩闊台)把每個親屬派赴各地,而自己則想親自前往欽察草原。蒙哥合罕儘管猶在青春年華,但由於他的聰明練達,他讓[在場的人們]注意到了合罕的行動,並說道:“我們全體子弟等待命令,準備毫無怨言和奮不顧身地完成頒佈的詔敕,讓合罕能安然享樂、避免出征的艱苦。否則,衆親屬和無數軍隊的異密們又有什麽用呢?”全體在場的人對他的話完全同意,並以此作爲自己必須遵循的決定。*《史集》第二卷,頁59。
由此記載可知,窩闊台欲圖御駕西征的計畫,再度被宗王、大臣們所勸阻,他們的理由是大汗應該“能安然享樂,避免出征的艱苦”,窩闊台只好留駐漠北。以此反觀窩闊台欲御駕親征南宋時因面對的是不可預知的强敵,又被勸止,其具體緣由恐怕亦應與此相仿。
貴由汗此前在蒙古第二次西征時業已取得一定功業,或許是由於在位時間短促,他未能有機會再去獲取個人武功。不過,史籍顯示他曾領軍西行,然而其目的不明,尚談不上是御駕親征以獲取武功的行爲。統觀上述窩闊台合罕、貴由汗的狀況,我們認爲大汗並不一定需要通過御駕親征獲取武功以加强聲望、鞏固地位。因此,蒙哥之所以御駕親征的理由,並未觸及事情的深層問題。*另,據《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孫傳》載,大德五年(1301),曾有大臣動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往征之。”頁3293。所謂“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它確實表明一代之君應開疆拓土以彰顯其休烈,然而它並不是說皇帝需要“御駕親征”以獲取武功,它們之間有所區別。大德五年的這項動議,最終也被大臣哈剌哈孫所制止。
蒙哥在登上汗位以前就已有不小軍功,如第二次西征討伐欽察、斡羅斯諸地,此自不待言。窩闊台御駕征金時,蒙哥亦曾隨軍出征。*《元史》卷二《太宗紀》載: 二年庚寅“秋七月,帝自將南伐,皇弟拖雷、皇侄蒙哥率師從,拔天成等堡”,頁30。可以說,蒙哥的武功是有目共睹的。拔都在推舉蒙哥爲大汗的時候就曾說過: 蒙哥“不止一次率領軍隊到[各]方作戰,並且才智出衆”。*《史集》第二卷,頁237。作爲蒙古的大汗,蒙哥本人也希望自己能如同窩闊台那樣,留駐蒙古本土,享受大汗的尊崇和閑適。據《史集·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旭烈兀汗傳》記載:
[蒙哥]合罕在他的兄弟旭烈兀汗的天性中看出了霸業的徵候,並從他的作爲中知道他的征服者的習慣,他[自作]推斷道:“既然某些國土已在成吉思汗時代征服,某些國土尚未從敵人處收復,而世界上的土地遼闊無比,因此,我讓自己的每個兄弟去開拓邊疆,去完全征服邊地,加以守衛,而我自己[合罕]則住在古老的禹兒惕裏坐鎮中央;無憂無慮地,依靠[他們],我將極幸福地度過歲月,並作出公正裁判。近處的某些敵人領地,我將[親自]率領京城附近的軍隊去征服和解放。”*《史集》第三卷,頁28—29。
倘若將蒙哥此處的言論,與他在1256年蒙古宗王大會上的那番陳詞互相比較,即君主需要建立功業、提高聲名,我們發現它們之間是存有些許矛盾的。矛盾的背後實則反映出,他之所以選擇御駕親征南宋,其實是出於無奈。從蒙哥登上汗位到御駕親征南宋之前,其間長達七年,蒙哥倘有御駕親征南宋的計畫,我們不太能想象他會有如此耐心來忍受這漫長的等待。*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蒙哥是位雷厲風行之人,他對失敗沒有耐心,並且吝惜贊美。《元史·憲宗紀》稱其性格:“剛明雄毅,沉斷而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凡有詔旨,帝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羣臣甚嚴”。頁54。參閱Thomas T. Allsen, Mongol Imperialism: The Policies of the Grand Qan Möngke in China, Russia, and the Islamic Lands, 1251-1259, pp.29-30。相較於此前諸位大汗,如成吉思汗登上大汗之位,次年即抄掠西夏;窩闊台汗甫登汗位即“遂議伐金”,次年又隨即領兵南征金國;而貴由汗則在登上汗位的第二年,便離開蒙古高原外出“西巡”。*《元史》卷二《太宗紀》,頁29;《定宗紀》,頁39。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認爲蒙哥是在等待時機伐宋,他之所以選擇御駕親征南宋,最爲根本的緣由是由於忽必烈前方攻宋不力,因此對其失去了耐心。*1256年蒙哥在計議伐宋宗王大會上的那句回應,即“既然我們已經說定,那末再去違反就是不合理、不正確了”。此乃話中有話,似有指向忽必烈之嫌。1252年,蒙哥交付給忽必烈的既定任務是攻宋,這也是經由宗王大會所議定的;然而,忽必烈臨時選擇往攻大理,且長時間未對南宋展開有效進攻,很明顯已“違反了”“已經說定”的戰略,因此忽必烈在南方的舉動就難免有“不合理、不正確了”之嫌。這點通常被人忽略。
按照史籍描述,蒙哥與忽必烈之間因“鈎考”問題而引起的巨大裂痕,很快就得到修復。然而,忽必烈已無法再取得蒙哥對他的完全信任了。當蒙哥御駕親征南宋的時候,忽必烈則被完全排除在攻宋將帥的名單之列。史書記載說,忽必烈因患腳疾,留在了漠北。*《史集》第二卷載:“在那次會議上,別勒古台那顏奏告說: ‘忽必烈已經出征過一次並且完成了任務,如今他正患腳疾,若蒙降旨,他就可以回家去了。’蒙哥合罕同意了[他所說的]。”“隨後,當蒙哥合罕想要征服南家思時,宣諭道: ‘忽必烈合罕腿有病,他以前已率師遠征,平定作亂地區,今可讓他留在家中靜養。’他[忽必烈]便遵照[蒙哥合罕]旨意,在自己的帳殿中,即在蒙古斯坦的哈剌溫—只敦地方休息。”頁268,288—289。
憲宗八年(1258)春,蒙哥正式率師出征伐宋,其具體經過,史書載之甚詳,無需贅言。這裏需要重點討論的是,與1253年忽必烈采取暫避由川蜀攻宋而選擇往攻大理的戰略相比較,蒙哥此次出征滅宋的戰略謀畫十分明確地直接指向川蜀之地,此兩種戰略之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那麽,蒙古滅宋所奉行的總體戰略究竟是哪一種呢?
1253年,忽必烈曾駐軍六盤山,準備攻宋。六盤山形勢重要,於此地稍偏東而南下入漢中,則可徑直往攻南宋川蜀之地;於此地稍偏西方向而往南挺進,則可進入西蕃諸地,並順勢南下進而往攻大理國。忽必烈對南宋在川陝要地的防守力量以及進取南宋的困難,可以說是有充分估計的。前文所揭《史集》中記載忽必烈來到漢地後,發現“途中各地的[一切]食物弄得精光”,實際就是指南宋采取了堅壁清野的策略,這給蒙古軍隊製造了巨大的障礙。另據《元史·趙阿哥潘傳》載:“歲壬子,世祖以皇弟南征大理,道出臨洮,見而奇之,命攝元帥,城益昌。時宋兵屯兩川,堡栅相望,矢石交擊,歷五年而城始完。”*《元史》卷一二三,頁3029。益昌爲川陝咽喉之地,憲宗“又詔(汪)德臣城益昌,諸戍皆聽節制。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見,乞免益昌賦稅及徭役漕糧,屯田爲長久計,並從之。即命置行部於鞏,立漕司於沔,通販鬻,給饋餉……益昌爲蜀喉襟,蜀人憚其威名,諸郡環視,莫敢出鬥”。*《元史》卷一五五《汪德臣傳》,頁3651。“癸丑,從憲宗至六盤山。商州與宋接境,數爲所侵,命(劉)黑馬守之,宋人斂兵不敢犯。丁巳,入覲,請立成都以圖全蜀,帝從之。成都既立,就命管領新舊軍民小大諸務,賜號也可禿立。”*《元史》卷一四九《劉黑馬傳》,頁3517。上面引文中憲宗顯係忽必烈之誤。蒙古在甘、陝地區最重要的兩支世侯力量,鞏昌汪氏、西京劉氏,都被調集至攻宋前線。從史文記載看來,忽必烈當時在川陝一帶的諸項佈置,以防守爲主,伺機進取。正是由於忽必烈已意識到“蜀道艱險”,且忌憚南宋在川蜀地區的强固防守實力,因此不敢貿然於六盤山之地直接進入川蜀,於是避其鋒芒,選擇先借道西蕃往攻大理而去。
1258年,蒙哥親率大軍南伐,同樣亦駐蹕於六盤山之地。與忽必烈不同的是,蒙哥選擇的是由六盤山偏東南方向下漢中,然後直趨入川蜀以攻宋。忽必烈對蒙哥御駕親征南宋,選擇由川蜀以圖宋的方略,可謂憂心忡忡。有段記載非常重要:
己未,憲宗親征蜀,以圖宋。世祖趨荆、鄂,軍於小濮,召問軍事,公對曰:“蜀道險遠,瘴癘時作,難必有功,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心。”*蘇天爵撰輯《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一《參政商文定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219。
從此段記載可獲知,忽必烈及其身邊謀臣對於蒙哥經由漢中入川蜀而攻宋,抱有很大的擔憂。然而,蒙哥此番主攻川蜀以圖南宋的進軍方略,其實正是蒙古長期以來所奉行的既定滅宋戰略。1252年,蒙哥命忽必烈南下,其進取方向和戰略重點本來也應該是由甘陝而入川蜀,先取川蜀,然後再沿江東下順勢滅宋。不過,忽必烈並未遵循。雖然這一滅宋戰略後來被認爲是失敗的,然而事實上它卻爲蒙古所長期奉行。該滅宋戰略一直持續到至元五年(1268)。當時,南宋降將劉整建議忽必烈攻宋,並提出更改原先以川蜀作爲戰略突破口的滅宋方略,所謂“攻蜀不若攻襄,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可唾手下也”。*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下《襄陽始末》,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306。自此之後,蒙古滅宋的戰略突破口纔得以全面調整過來,以荆襄地區而非川蜀之地,作爲主攻方向。因此就蒙古滅宋的總體戰略而言,所謂由大理“斡腹”而攻宋的深遠戰略圖謀,實難令人信服;而由川蜀作爲突破口以滅南宋,纔是蒙古所一貫奉行的滅宋總體大戰略。
當蒙哥在南方鏖戰的時候,忽必烈仍在北方觀望,後在身邊謀臣的進言之下,他方自請南來伐宋。據《元史·不忽木傳》載:
世祖威名日盛,憲宗將伐宋,命以居守。燕真曰:“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輿遠涉危難之地,殿下以皇弟獨處安全,可乎?”世祖然之,因請從南征。憲宗喜,即分兵命趨鄂州,而自將攻蜀之釣魚山,令阿里不哥居守。*《元史》卷一三○,頁3164。
由於塔察兒統領的中路軍在鄂州前線進展不順,蒙哥最終同意了忽必烈的請求,命他“領一萬精兵與數萬札忽惕人”,*《史集》第二卷,頁289。南下支援。1258年十一月,忽必烈啓程前往鄂州。*《元史》卷四《世祖紀一》載:“歲戊午,冬十一月戊申,禡牙於開平東北,是日啓行。”頁61。次年秋,蒙哥殞命釣魚城。
忽必烈此番南下伐宋,同樣又是無功而返。忽必烈對南宋的忌憚,可以說自從1252年負責經略漢地以來就一直縈繞心間,當時他沒有選擇從六盤山南下川蜀之地直接進攻南宋就是明證。1259年,忽必烈在荆襄前線的時候,見識到南宋江防的嚴整。南宋權臣賈似道以木栅環城,一夜之間即建成,這給忽必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環顧扈從諸臣僚說:“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元史》卷一二六《廉希憲傳》,頁3090。忽必烈身邊的謀臣郝經,更是盛贊南宋邊防力量:“右師滿湖湘,左師溢巴峽。江滸連大屯,淮南擁驍甲。”*《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四《渡江書事》,頁520上—下。當蒙哥殞命合州釣魚城下的凶問傳來,忽必烈對進攻南宋的信心無疑又被澆了一瓢涼水。
忽必烈在奪取汗位最初的幾個年頭裏,因面對北方幼弟阿里不哥爭位問題,蒙古對南宋基本處於戰略相持狀態。1268年,距上次大規模伐宋大約近十年之後,在劉整的建議之下,蒙古攻宋的號角纔再度吹響。遲至至元十一年(1274),當元軍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忽必烈仍不敢掉以輕心,他秘密派人到江西龍虎山問道,在得到肯定預示後,纔下定滅宋的決心。最後,當阿里海牙的軍隊攻下江陵(荆州)時,忽必烈纔長舒道:“東南之勢定矣。”*歐陽玄《江陵王新廟碑》,《圭齋文集》卷九,四部叢刊縮印本,306册,頁76下。忽必烈滅宋經過,詳參白壽彝總主編、陳得芝主編《中國通史·元時期》(13)乙編第六章第三節《南宋的滅亡與江南的統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17。
行文至此,我們再來反觀爲何《元史》以及其他漢文史料有意或無意回避蒙哥要求忽必烈直接進攻南宋的問題,也許就更能明白個中緣由了。值得注意的是,據《元史·世祖紀十二》載,至元二十五年(1288)二月:
庚申,司徒撒里蠻等進讀祖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元史》卷一五,頁308—309。
歷史是由忽必烈及其後裔們所書寫的,對於蒙哥時代的歷史敍述自然也被他們所掌控,有些史實被遮蔽或忽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蒙哥最終死在伐宋的征途上,於蒙古人而言這是一種很大的挫折。忽必烈於此是負有一定責任的。而忽必烈當時未貿然展開大規模攻宋行動,這正是他深具遠見卓識的表現。
與蒙哥急於攻宋相比較,忽必烈暫避攻宋而選擇往攻大理,確係明智之舉。堤一昭對於忽必烈攻下大理之後遽而北返的行動感到十分不解,同時他也十分敏銳地指出蒙哥與忽必烈之間的矛盾正源起於此。他說:“遠征半途而返的忽必烈在其後的三年時間裏,只是往來於漠北的夏營地與冬營地之間,未見有大規模的行動。”“他中途而返的動機何在?我想可以保留更多的想象。蒙哥七年(1257)表面化的蒙哥與忽必烈的不合,可以認爲從這次遠征中途而返就已開始。”*參閱堤一昭《忽必烈政權的建立與速不台家族》。倘若我們對蒙古在“滅南宋”與“征大理”之間的進攻方略變化上加以留意考察的話,蒙哥與忽必烈之間矛盾問題的核心所在,可謂分外明顯。按照《史集》記載,忽必烈攻下大理後即行離開,這與其患有腳疾有關。然而,這恐怕是遁詞。事實上,蒙古主力出征大理只是臨時舉措,忽必烈急於要返回中原,就是要履行其原本早該執行的最爲主要的任務——進擊南宋。另外,蒙軍出征大理,損失十分嚴重,這也是忽必烈迅速抽身北返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緣由。
三“斡腹”源來: 南宋西南邊臣將帥對蒙古軍隊舉動之臆說
在前文對忽必烈未能徑直進攻南宋而臨時改變計畫借道川北藏區往攻大理國的具體歷史關節點進行詳細考論之後,我們對於本文開頭提出的忽必烈最初奉憲宗蒙哥汗之成命,欲由大理而搗襲南宋的所謂“斡腹之謀”成立與否的問題,應該已有了不同於以往的新認識。既然蒙古並非在1252年之初或者在更早的年代裏就已存有所謂“斡腹”大理以攻南宋的深遠圖謀,那麽所謂蒙古欲圖“斡腹”大理進攻南宋的諸種說法又究竟源自於何處呢?若要追究此問題,我們需要在全面梳理宋元時代相關記載的基礎上,纔能明白其來龍去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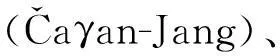
而蒙古人稱雲南爲“哈剌章”,肯定也得諸於其他人羣之口。*《元代雲南史地叢考·金兆梓序》稱:“元人得雲南,一切就蒙古語言諧音(轉下頁)( 接上頁) 迻譯,如‘哈喇章’、‘察罕章’之類,令人不可復究詰。”參閱夏光南《元代雲南史地叢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 年。他們對雲南的最早認知,應源於與藏語人羣有關的羣體,其中最大的可能就是党項羌人或吐蕃人。按照蒙古人所接觸的先後順次,党項人應稍早於吐蕃人。西夏的知識對於蒙古的影響不可謂不大,如“帝師”等概念就十分明顯。*參閱聶鴻音《西夏帝師考辨》,載《文史》2005 年第3輯;鄧如萍《西夏佛典中的翻譯史料》,載《中華文史論叢》2009 年第3期。根據藏文史籍《賢者喜宴》記載,彌藥(西夏人)對於當時自身所處的地理位置曾有一番描述:“東爲漢地,南爲南詔,西爲吐番,北爲霍爾,在此諸國所割據之中心即西夏之國土。”藏文本《賢者喜宴》將“南詔”寫作“’Jang”。*十三世紀以前的藏文文獻中,常用’Jang或lJang(譯音“絳”或“章”)來稱呼雲南地區或當地政權(南詔或大理)。西夏人的四方觀念,與吐蕃政治文化中的“四天子說”應有某種關聯,它顯示出党項文化受吐蕃影響之一斑。此爲任小波博士見告,特此申謝。參閱巴卧·祖拉陳瓦著,黃顥、周潤年譯《賢者喜宴——吐蕃史譯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賢者喜宴》(藏文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頁721。換而言之,蒙古人藉由西夏而得知大理國,其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這同樣也不能排除蒙古人是經由吐蕃人而了解大理國的可能性。蒙藏間發生直接聯繫,一般認爲應遲至1230年代闊端經略吐蕃時纔正式開始,不過蒙藏間更早期的非正式接觸所帶來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意大利藏學家伯戴克認爲,依據蒙古人自身的說法,1206年鐵木真宣佈即大汗位時,蒙藏間就已有接觸和聯繫,不過這在藏文文獻中找不到依據。1207年鐵木真第二次出征西夏以後,蒙藏間或許開始已有所接觸,但也僅局限於川、甘、青等地的藏區邊緣地帶,然而記載也並不十分確切。1236年,窩闊台次子闊端派兵着手經略吐蕃之地,降服甘南地區的幾個藏族部落,蒙藏間的直接接觸或即始於此。此外,斯蒂芬·豪(Haw)、艾騖德(Atwood)等學者新近的研究則傾向於認爲,1203年成吉思汗滅克烈部之後,克烈部王罕之子桑昆等避走西夏諸地,在隨後數年間蒙古人對於甘青藏地區藏人或羌人的接觸和了解應是非常明顯的事實。參閱伯戴克著、張雲譯《中部西藏與蒙古人——元代西藏歷史(增訂本)》,蘭州大學出版社,(轉下頁)( 接上頁) 2010 年; Stephen G. Haw, The Mongol conquest of Tibet, Journal of the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24, 2014,pp 37 49; Christopher Atwood, The FirstMongol Contacts with the Tibetans, 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Roberto Vitali,edited. , Amnye Machen Institute, Dharamshala ( h.P.) , India, 2014,pp. 21 46.蒙古人開始得知大理其國,最早的可能應在1220年代後半期蒙古滅西夏之後;而蒙古與大理間發生直接接觸,則應出現在1235年蒙宋間直接對峙以後。由於尚存很多知識的空白點,蒙古與大理之間的早期關係,我們迄今仍然無法給出明確的年代斷限。*蒙古與大理之間最早的直接接觸,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參《元朝史》(下),頁274。
至今仍常爲人們當作蒙古人早已存有“斡腹”大理以攻宋的證據,源自於成吉思汗時期的所謂郭寶玉建言事:
木華黎引見太祖,問取中原之策,寶玉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元史》卷一四九,頁3521。
此記載之事,實在可疑,不足憑信。郭寶玉當時所指的進擊對象是金而非南宋;而所謂“西南諸藩”,應是指寧甘青川毗連地區的“諸藩”(他們應是藏人或羌人),而非地處西南的大理周邊諸蠻。*詳參前揭斯蒂芬·豪、艾騖德文。另參曾現江《先取西南諸蓄,後圖天下——蒙古對藏彝走廊的軍事征服》,《西藏研究》2005年第4期;《蒙古與大理國早期關係探析》,《貴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與此記載論調幾乎一致的還有波斯文史料,據《史集·也速該把阿禿兒的兒子成吉思汗紀》載:
接着,當他(成吉思汗)征服也在他的疆域內的吐蕃國與唐兀惕國後,想再次出征乞台,將乞台一下子占領並征服乞台的鄰國、離蒙古不遠的哈剌章地區(這一地區,印度人和哈剌章人[自己]都稱做健陀羅,大食人則稱做罕答合兒)。他果斷地決定下了這件大事,但[就在這時][乃蠻]王的兒子古失魯克汗於其父被殺後,逃到了突厥斯坦,與若干蒙古部落、成吉思汗的敵人勾結到了一起,占領了哈剌契丹古兒汗統治下的突厥斯坦。古兒汗去世。這個消息傳到了成吉思汗處,他出征乞台的意圖便減弱了……成吉思汗在狂怒之下忘掉了乞台、至那和哈剌章地區上的事,急忙向突厥斯坦與伊朗地區進軍,在諸子和異密們的協助下征服了[這]兩個地區……在蒙哥罕時代,其弟忽必烈合罕征服了乞台在國內剩下[沒有被征服]的地方……忽必烈合罕在位時占領了[至那]、哈剌章地區及忻都斯坦的一部分。*《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頁83—85。
這則波斯文史料的記載,所涉史實錯誤實在太多。該記載顯示的時間是在1216年,即蒙古第一次西征之前。當時成吉思汗既未征服過吐蕃,他對於哈剌章之地有無具體的了解都令人十分懷疑,怎會想到要去征服哈剌章?另外,早在窩闊台汗時代,乞台諸地早已爲蒙古所征服,又怎會遲至蒙哥時代?而哈剌章諸地被蒙古人所征服,則是蒙哥時代而非忽必烈時代之事。因此,《史集》的此段敍述,可謂謬誤迭現,不能采信。
於蒙元方面的史料記載而言,倘若排除所謂郭寶玉建言事以及《史集·也速該把阿禿兒的兒子成吉思汗紀》的記載,在忽必烈進軍大理國的時候,或者在此之前,實無史料提及蒙古早已存有“斡腹”大理以攻南宋的戰略規畫,亦無漢人謀臣向蒙古人提出此方面的建言。誠如前文所述,蒙哥即位之初,在他分派給忽必烈、旭烈兀出征的國家/地區名單中,並未出現大理國,也就是說,大理國尚未進入蒙古帝國的大征服戰略計畫之內。遲至蒙古攻滅大理國之後,纔有人將此舉阿諛爲是蒙古人的一種戰略遠謀,其最爲典型者就是郝經。郝經於1259年上疏《東師議》,其文云:
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彊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澮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二,頁758上;《元史》卷一五七《郝經傳》,頁3700—3701。郝經所指蒙古人的各種“用奇”之術,包括斡腹之舉、擣虛之計(指1236年闊端入蜀有以攻宋)、示遠之謀,概括而言之,均可視爲“斡腹”謀略。
郝經明顯是在誇飾蒙古軍隊,此自不待言。自郝經之後,在元王朝當代歷史敍述者們的講述中,則很少有人直接將忽必烈出征大理國頌揚爲是一種“斡腹”遠謀。*如元明善所撰《雲南志略序》云:“昔在世祖以帝之貴介弟,帥偏師入西南夷,而伐取之。”虞集《送文子方之雲南序》稱:“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參閱李京撰,王叔武《雲南志略輯校》,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頁64;《虞集全集》,頁529。需特別指出的是,距忽必烈征服大理約半個世紀之後,大元大德年間,程鉅夫受命撰《平雲南碑》,*《元史》卷一七二《程鉅夫傳》載,大德十年,“雲南省臣言: ‘世祖親平雲南,民願刻石點蒼山,以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頁4017。此頌功碑文亦隻字未提所謂“斡腹之謀”的問題。*參閱《程雪樓文集》卷五,頁239—243。
因此,所謂“斡腹之謀”的諸種說辭,在當時代蒙元方面的史料文獻中,幾乎蹤迹難覓。
然而,在宋元之際南宋方面的文獻記載中,“斡腹之謀”的說法,卻接踵頻現,異常流行。*南宋方面有關蒙古“斡腹之謀”議論的文獻記載,曾現江、石堅軍上引諸文皆有所梳理,可資參詳。我們或可按時代先後次序,梳理出南宋方面有關蒙古“斡腹”雲南諸種說法的基本演進線索。
早在蒙古滅西夏時,蒙軍的軍事行動就已驚擾到南宋。南宋理宗寶慶三年(丁亥,1227),蒙軍首次侵擾南宋所轄甘陝南部、四川北部地方,西和州、階州、成州、文州、天水軍等遭蒙軍攻破,此謂“丁亥之變”。*參閱陳高華《早期宋蒙關係和“端平入洛”之役》,載氏著《元史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203—230;陳世松等著《宋元戰爭史》,頁20—22。當時南宋四川制置使張惶失措,“棄階、鳳、成、和、天水五州,畫守內郡”。*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六《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主管沖佑觀虞公墓誌銘》,四部叢刊縮印本,266册,頁623下。此次蒙古入侵事件,給關心南宋西南邊防的臣僚們帶來極大震動。*詳參李曾伯《可齋雜稿》卷二五《丁亥紀蜀百韻》,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79册,頁432上—434上;吴昌裔《論蜀變四事狀》,載《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經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9年,頁1359上—下。當時在四川爲官的吴昌裔已預感到事態的嚴重,他在端平三年(1236)時曾說:“臣十年前聞敵有斡腹之謀,欲借路雲南,圖我南鄙。當時說者皆以爲迂。”*吴昌裔《論湖北蜀西具備疏》,載《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九《禦邊》,頁4403上。吴昌裔所謂“十年前”,正是指丁亥年蒙軍對南宋的侵擾。是知,吴氏當時就對蒙軍用兵意圖持有所謂“斡腹之謀”的猜測。這是南宋方面最早對蒙古軍隊在西南邊鄙地區展開軍事行動而作出“斡腹之謀”的臆測。當時,南宋主要擔憂的是蒙古意圖“斡腹”入蜀。
1234年,金亡之後,蒙宋陷於直接對峙局面。南宋“端平入洛”以失敗收場後,蒙古對南宋開始采取全面的軍事攻伐。南宋對於蒙古軍隊在其邊鄙地區的任何軍事舉動,都顯得異常敏感。1235年春,窩闊台派遣“皇子闊端征秦、鞏,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元史》卷二《太宗紀》,頁34。同年秋,南宋邊防守軍已得諜報: 蒙人“聚兵牧馬,決意南來,一渡河、洛以窺江淮,一由唐、鄧以窺襄漢,一托秦鞏,以窺四川。二(三)道并入”。*《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九《論三邊備禦狀》,頁4398下。1235年秋,袁甫《陳時事疏》云:“臣竊謂今日事勢不當論安危,當論存亡。夫關於國家存亡之最急者,莫急於北邊。秋高馬肥,必謀大舉,傳聞將以三路並進: 阿齊(按赤)台與逆全妻,將自山東窺我淮甸;蘇布特(速不台)將自木波界窺我西蜀;布占(倴盞)將自陝州窺我襄漢。萬一果如所聞,國家何以禦之?”袁甫《蒙齋集》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75册,頁398下。1236年,闊端在征服秦鞏汪世顯部後,蒙軍入成都。*《元史》卷一二一《按竺邇傳》,頁2984。南宋西南邊鄙將領對蒙古此舉深感憂慮,警惕之聲四起。其時,魏了翁就表達了他的遠慮“虜之謀蜀也,先破秦鞏,次降諸蕃”;而監察御史吴昌裔則奏稱,“臣蜀人也,每恨三十年間蜀有危證,而遠不得聞,聞亦不實”,“臣近聞韃虜破階窺文,欲爲斡腹深入之計,又攻打蕃族,徑爲間道取蜀之謀。姦計日深,人危不保”;“又況唐、鄧、均、陸之寇,導之以扣江,秦、鞏、松、維之族,誘之以斡腹,內外受敵,殊可寒心”。*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知安吉州蔣左史重珍》,264册,頁275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經國·論蜀變四事狀》,頁1359上;卷一○○《經國·催王遂入蜀狀》,頁1361上;卷三一○《災祥·論四陰之證狀》,頁4013下。最爲引人矚目的是,吴昌裔於端平三年(1236)底至嘉熙元年(1237)初之間所上的一份奏疏,縱論當時湖北、蜀西局勢,明確指出蒙古有借道雲南欲實施“斡腹之謀”的方略,此即《論湖北蜀西具備疏》。其文略言:
今廟算深長,必能選有威風大臣控扼廣西,如招兵積粟等事,或通湖南,或通廣東,想皆次第施行,算無遺策矣。而臣之愚見,則以爲上流尤所當備。臣十年前聞敵有斡腹之謀,欲借路雲南,圖我南鄙。當時說者皆以爲迂。今聞瀘州安撫司所申密院事稱: 西蜀南蕃蠻王阿永申,敵攻打大理國,並殺死姚州高慶節度,見在大理國內屯駐。四向生蠻,悉皆投拜。烏蒙國都蠻王阿呂申,本蕃鬼婆帶領軍馬往後蕃,見敵兵深入攻打卭部川界分,便破散小雲南國。見敵兵在大理國界分駐紮,言說今冬再回求路,要出漢地。此皆去歲事也。若然,則是小、大雲南悉皆狼狽,迫我後戶矣,詎可不爲關防哉。試將蜀西湖北之與南蠻接者,爲陛下條陳之……臣謂廣西固當備,蜀西之南徼、湖北之南鄙尤當備,蓋廣西猶可諉曰“炎瘴之毒,非彼所宜”,在蜀西、在湖北,則並炎瘴無之矣……辰沅之間,當用史子翬之策,增兵屯鼎澧之間,當臣寮之說,選擇憲守以爲羅鬼國之前拒,使斡腹旋出之師不可得進,則湖北之南鄙,截然如中防之制永矣。*吴昌裔《論湖北蜀西具備疏》,《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九,頁4403上—4404上。對於此奏疏的細緻考辨,參郭正忠《恥堂奏劄與蒙攻雲南——兼涉晚宋一項歲收年代的考辨》,《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
郭正忠認爲,吴氏所言“十年前聞敵有斡腹之謀,欲借路雲南,圖我南鄙”,應是寶慶未年至紹定初(約1227年至1228年間)的傳聞。吴氏此奏疏所言確實大多得自傳聞,而非事實;他所提出的西南邊鄙防備,則深有遠見。南宋當時最直接的擔憂是蜀西、湖北,不過時人也深憂及於大理、廣西諸地。自1236年後,有關蒙古欲迂回大理以“斡腹”南宋的傳聞已日漸盛行。*1245年,方大琮即稱:“七八年前,有韃窺大理之說,或曰隔於泥六七百里,或曰江防僅如許,彼何所憚,而迂回跋涉於瘴潦遐僻之區,是必不然。”其所指應即1237年、1238年蒙古欲圖攻蜀之事。參閱方大琮《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二《廣西蔡帥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89),頁597上—下。己亥(1239)秋,蒙軍在川北一帶遭遇木波國諸番部激烈抵抗,蜀帥陳隆之上報奏稱:蒙古“欲由大渡河直破大理等國,斡腹入寇”。*李鳴復《乞嚴爲廣西之備疏》,載《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八,頁4389下。所謂蒙古借道吐蕃欲攻大理進而“斡腹”南宋的傳言,已逐漸充斥於西南邊鄙帥臣的奏疏中,他們所擔憂的已不止是蒙古“斡腹入蜀”的問題,更爲深憂的是蒙古進攻大理“斡腹”攻宋,因而要求朝廷進一步强化川蜀地區的防守。
1240年代,蒙古與大理之間的直接接觸已日漸增多。四川、廣西以及臨近西南諸蠻的南宋帥臣,紛紛向朝廷上報蒙古欲“斡腹攻廣”的各種動向。蒙古斡腹入寇的傳聞,已甚囂塵上。1240年初,福建路官員方大琮稱,“閩、廣最號僻陋,自去歲已有指爲堂奧者,豈不異哉?元日,趙文仲移師西廣,或謂虜攻南詔,與邕、宜鄰,有買馬驛程,往往不能無震恐”;同年秋,宋人偵知,“南詔復有假道之傳”。*方大琮《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一七《杜尚書杲》,頁522上;杜範《清獻集》卷一○《八月已見劄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75册,頁694上—下。這裏“去歲”指嘉熙三年(1239),“元日”即是次年。1241年,“‘諜報韃謀由交趾趨邕宜,有旨,令帥整飭軍馬,漕積聚錢糧,以俟調發。’時杭相李公初薨,山相獨運。余始識‘斡腹’二字……自辛丑而後,斡腹之說,若緩若急,將信將疑。歲歲如此,至去冬所傳愈響”;“或言虜謀自安南斡腹”,*劉克莊著,辛更儒《劉克莊集箋校》卷一○八《跋趙倅與灝條具斡腹事宜狀》、卷一四一《杜尚書神道碑》,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4486,5627。云云。1243年初,播州安撫使楊文向剛入蜀的南宋守臣余玠進言:“至於保一江以自守,敵去敵來,縱其所之,此爲下策。若夫意外之憂,近年西番部落,爲賊所誘,勢必撓雪外……以并吞蠻部,闞我邕廣,窺我沅靖,則後門斡腹爲患。”*參閱《楊文神道碑銘》,據《宋沿邊宣撫使“播州土司”十五世〈楊文神道碑碑文〉》,載貴州省博物館《貴州高坪“播州土司”楊文等四座墓葬發掘記》,《文物》1974年第1期。另據宋濂《楊氏家傳》云:“下則保江自守,縱敵去來耳。況西番(轉下頁)( 接上頁) 部落,已爲北所誘,勢必撓雪外以圖雲南,由雲南以并吞蠻部,闞邕廣,窺沅靖,則後門斡腹,深可憂也。”《翰苑別集》卷一,《宋濂全集》( 2)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964。
1244年,蒙古與大理於九和發生戰爭,蒙古軍隊“行吐蕃界中,初不經四川地分……直至大理之九和鎮”。*李曾伯《可齋雜稿》卷一七《帥廣條陳五事奏》,頁362上。《南詔野史》稱淳祐四年(1244),“蒙古兵出靈關伐大理”。*楊慎《南詔野史》上卷,頁226上。此次蒙古與大理的戰爭已不再是傳聞,對南宋震動很大,它印證了此前南宋邊鄙守軍對蒙古欲先下大理而後斡腹攻宋的推測。同年,陽枋上書四川制置使余玠,提醒他要“防遏間道”:“萬一敵人知我沿江守備嚴固,計必斡腹。若圖斡腹,必於瀘、敍徑攻田、楊,田、楊萬一不支,則其路可通辰、靖等州,出我之背,以闖朝廷之後戶。宜力諭思、播,深警防度。”*陽枋《字溪集》卷一《上宣諭余樵隱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83册,頁260上。陽氏多次呼籲南宋邊防守軍要注意“斡腹之防”,詳參《字溪集》卷二《上蜀閫余樵隱論時政書玠義夫》、卷六《賀趙守劄》,頁273下,329上。淳祐六年(1246),高斯得有一份《輪對奏劄(六月六日,時爲著作佐郎)》,其中涉及當時西南邊疆軍情:“數年以來,敵攻雲南,傳聞日駭。荆蜀廣右,所奏略同……且臣近者聞諸上流閫幕,以謂大理久已降敵,而朝論方在疑信之間,可爲痛哭!”*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一,叢書集成本,2040册,頁16—17。關於此奏劄年代的詳細辨析,參看郭正忠前揭文。
淳祐四年至淳祐六年之間,李鳴復上《乞嚴爲廣西之備疏》,該奏文稱:
觀賊所向而圖之,最是交廣之憂,不可不慮。……臣向者,己亥之歲,僑寄毗陵。曾聞蜀帥陳隆之具申朝廷,謂韃賊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國,斡腹入寇。密院劄下廣西經略徐清叟,嚴行體探,預作隄防。後來清叟到大理、自杞等國,回報繳申。今可覆視也。近又從邸報見樞密都承旨蔡節奏章,專坐廣西經略蔡范申到事宜,謂邕、宜深爲可慮。與今來牟申之所言,及向來陳隆之所申,大概一同。臣竊惟韃虜向與金爲仇,掃穴犂巢,自燕徙汴,盤旋積歲,竟不能過黃河,以遂其不奪不厭之志。或教之曰:“河之尾,有路可以轉入。”於是,破西夏,逾積石,踐蜀境,竟求以快其欲而後已。今其與我爲鄰也,虔劉我兩淮,洊食我西蜀。所幸天限南北,長江洶湧,不容輕涉。然數年以來,嘗驀過萬州以下之胡灘,透漏黎州以後之大渡河。彼其姦謀詭計,未必不曰“河之尾,有路可以蹙金”。則江之尾,亦必有路可以窺我。*李鳴復《乞嚴爲廣西之備疏》,載《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八,頁4389下—4390上。此奏疏時間在淳祐四年至淳祐六年間,詳參郭正忠前揭文。
是知,蒙古斡腹入寇的傳聞日甚。1246年,劉克莊曾懷疑:“臣每怪韃在草地,哨騎在淮北,斡腹之謀在安南。”*《劉克莊集箋校》卷五二《召對劄子淳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頁2570。淳祐丙午(六年,1246),據李昴英奏劄:
上曰:“如果有奇才,當不拘資格,聞廣中斡腹之傳,如何?”奏云:“臣本欲作一劄,敷陳此事,然事關機密,恐播傳於外。”上曰:“極是極是。”因奏云云。上曰:“已令徐敏子去體探。”奏云:“此事須是純實可托者方可信,若喜功生事者,徒知爲一身功名計,又恐別生事說,則不惟廣西受弊,必欲通廣東之兵財,而兩路俱受其弊矣。”*李峁英《文溪集》卷七《淳祐丙午侍右郎官赴闕奏劄(第二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81册,頁161下。
所謂“廣中斡腹之傳”,乃因蒙古已徑攻大理,其下一個目標自然就直指兩廣地區。*1246年,孫夢觀廷堂輪對時,有“聲言襲我廣右”之語。參閱孫夢觀《雪窗(轉下頁)( 接上頁) 集》卷一《丙午輪對第一劄( 結人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81 册,頁67上。淳祐七年,牟子才上奏稱:“其如淮西諸郡,間被傷殘;蜀西諸屯,時肆蹂踐;遠而至於廣西一路,又有斡腹之憂。”*《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一,頁4031上。
淳祐九年(1249),廣西帥守李曾伯上書朝廷,疏陳禦邊五事,此即《帥廣條陳五事奏》。該奏疏基本主旨有二: 一是結合當時西南時局與地理防禦形勢,分析蒙古意圖間道而出“斡腹”攻宋的各種傳聞與諜報,呼籲南宋朝廷應予重視;二是在此分析基礎上,針對廣右地區的備邊措施提出具體建議。
李曾伯條陳第一事即爲“邊防所急,間諜爲先”。他指出此前對於蒙軍攻大理的資訊“往往得之諸蠻所傳”,其虛實不明,因而要求“重賞招募有能識蠻路、曉蠻語之人”,以獲取準確情報。他在分析各類“斡腹”傳聞與廣右備邊的關聯性問題上指出:
但參之衆論,皆謂虜若自沈黎以西之諸羌透漏南詔,則蜀閫當先知虜;若自思、播一帶之諸蠻透漏沅、靖,則荆閫當先知。其與本司欲自邕、宜以探大理,自融州以探思、播,其去韃境地里委相遼絕,欲望睿慈劄下荆、蜀兩閫,應有探到韃賊動息以時關牒本司,庶幾本司得以隨機應接,極力備禦。
李氏條陳第二事則爲“韃虜謀人之國,多出間道”。他指出各種諜報顯示蒙軍“姦謀不淺”,所謂“但觀淳祐五年以來,節次備錄,所報或傳謀入思、播,以窺沅、靖;或聞取道蕃部,徑趨南詔;或謂吐蕃已得韃賊旗號,爲鄉道入廣。此等之報,不一而足”。他仔細分析了川蜀與廣右間的地理形勢,要求朝廷防備蒙古軍隊間道“斡腹”攻宋:“臣以此推之,則戊申既失利於巖州,又安知不捨巖州之熟路,而取他道?有如蜀帥久在西邊,識戎情於萬里外,其爲廣右深慮如此,夫豈可玩?”*參閱《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八《禦邊》,頁4379上—下;李曾伯《可齋雜稿》卷一七,頁360下。李氏十分明確地指出,川蜀穩定方可安大理,大理安則廣右地區之安全無虞。
李曾伯對當時西南邊備的認識,可謂深具遠見。他對嶺南“斡腹”之防的擔憂十分沉重。*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四《第二辭免奏》稱:“惟嶺當斡腹之防,非臣可養疴之所。”頁631上。後卷五《回宣諭闗閣長二月六日兩次聖旨奏》則云:“臣憤邊患之憑陵,慮斡腹之侵食。”頁655上。在整個1240年代,隨着蒙古與大理之間戰事頻發,南宋西南邊鄙將帥已深刻預感到,蒙古攻下大理之後必將再由此而“斡腹兩廣”,甚至危及福建地區。有論者指出:“1246年是忽必烈平大理前宋人‘斡腹之傳’最頻、‘斡腹之憂’最深、‘斡腹之議’最多、‘斡腹之防’最嚴的一年。”*石堅軍《蒙古與大理關係新探——以“斡腹之謀”爲視角》。
然而需指出的是,吴昌裔、李鳴復、李曾伯等南宋邊鄙帥臣們過去近三十年來所上報的有關蒙古欲斡腹入寇的各類奏聞,事實上並未引起南宋朝廷的重視。淳祐七年(1247)八月,湖南安撫大使陳韡“抵潭州,密奏提刑宋慈所言大理諸蠻事宜”,九月,公言:“斡腹之說,此實過疑。有備無患,自治上策。要之,先事之備,貴於無迹。目下平安,忽爾汲汲軍事,徭侗安南必且疑懼。”*《劉克莊集箋校》卷一四六《忠肅陳觀文神道碑》,頁5775。另據《宋史全文》載,始自寶祐三年(1255)迄於開慶元年(1259)底,有關“斡腹之謀”、“斡腹之報”、“斡腹之傳”、“斡腹一事”、“斡腹支徑”、“蒙古謀斡腹”等內容纔日漸頻繁地出現在理宗與大臣的召對、諭旨中,它已顯示出事態的緊急。*佚名《宋史全文》卷三五《理宗五》、卷三六《理宗六》,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311—2398。另,黃寬重著有《庶無稽遲——宋、蒙廣西戰役(轉下頁)( 接上頁) 的軍情蒐集與傳遞》一文,詳細討論了李曾伯於寶祐五年( 1257) 至景定元年( 1260) 間的各類奏報,其中涉及所謂蒙古斡腹之事甚詳。參閱氏著《政策·對策: 宋代政治史探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 年,頁195—230。1257年,李曾伯離開廣右八年之後,仍大聲呼籲:“竊惟敵人斡腹之事,乃是宗國切身之憂,以邕、宜而觀,視沅、靖尤緊。”*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五《回宣諭令調兵援廣與徐經略商確》,頁636下。換而言之,在此之前,南宋中央朝廷對於蒙古軍隊在西南的各種“斡腹”傳言,其實並沒有采取切實有效的應對措施,一則他們擔心此類傳聞引發恐慌,二則宋人防蒙重點一直集中在川蜀、荆湖、兩淮地區,而非廣右之地。*景定三年(1262),劉克莊對於“斡腹之傳”仍抱有很大的批評和懷疑,他說道:“斡腹之傳且二十載,於是建閫桂林,倚之爲萬里長城,羽檄調精兵良將,分佈要害,又竭廣東楮積錢粟以餉廣西。寇未至則先抽外戍以自衛,寇至則堅閉四壁而不敢出。”《劉克莊集箋校》卷八七《進故事·壬戌七月初六日》,頁3732—3733。
蒙古經略雲南數年後,對當地控制已趨穩定。自憲宗五年(1255)起,兀良合台所統領的軍隊,一面北上攻蜀,一面進擊貴州、雲南等地未下諸蠻。這年年初,南宋左丞相謝方叔上奏朝廷稱,“廣西之傳”不虛,蒙古果有“斡腹之謀”。憲宗七年,兀良合台由雲南北上配合蒙哥攻宋,“斡腹”之勢已明。*據黎崱《安南志略》稱,兀良合台的任務就是“經安南邊邑,取廣西道,會兵攻宋”。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4。南宋邊鄙帥臣對蒙古“斡腹南來”的猜測終成事實: 寶祐六年(1258)五月一日,理宗聖旨提到大理諜報,以及朝廷從湖南制置使處得到據稱蒙哥所言“止隔重山條江,便是南家”的信息。*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六《回奏宣諭》,頁682上。撇開所謂“蒙哥之言”的真實與否不論,或可稍加澄清的是,蒙哥所指稱的地區應是川蜀而非大理,當時滅宋戰略突破口正在川蜀地區;此時蒙軍攻下大理已長達五年之久,形勢早已十分明朗。次年“秋九月,韃靼國憲宗皇帝親帥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斡腹南來,歷邕、桂之境,南至靜江府”。*王瑞來《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卷三《理宗》,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47。而兀良合台所統領的軍隊被稱爲“斡腹之師”,這也是當時或後世談論“斡腹之謀”時最爲主要的論說對象。*《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卷三《理宗》載,己未年十月,“趙葵爲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州,遏廣右斡腹之師”。頁249。元人劉一清《北兵渡江》稱:“開慶己未秋九月,北朝憲宗皇帝親率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因(國)斡腹南來……”《錢塘遺事》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77。逮至1260年,郝經奉命使宋,他曾聲言:“且彼國邇年以來,兩淮殘破,四川陷沒,二廣透漏,江面綻缺……上流在所可以下,江面在所可以渡,斡腹在所可以出。”*《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七《宿州與宋國三省樞密院書》,頁816下。
前文所述宋人自1227年以來有關蒙古軍隊在西南地區吐蕃、川蜀、大理等地的軍情報告,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南宋邊鄙帥臣敏感於蒙古軍隊的行動,進而所作出的一種臆測與聯想。而這種臆測或聯想,一方面本身出自各類“傳聞”;另一方面,南宋文人帥臣們原本喜好談論軍國大事,就邊鄙之事抒陳己見,這無疑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蒙古存有所謂“斡腹之謀”的種種憂慮。李曾伯後來在《歸里謝宣諭奏》中說:“果而連歲值敵大入,以南方素無備之地,當此敵二十年。斡腹之謀,誤國誤民,固所深懼。”*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四,頁634下。
自邊鄙危機日重之後,南宋西南邊防帥臣對於蒙古在西部邊疆地帶(陝西、四川、吐蕃以及雲南地區)的一系列舉動,均視作爲“斡腹”之舉。蒙軍攻秦鞏,南宋憂蜀西;蒙軍入川蜀、攻吐蕃,南宋憂雲南;蒙軍進占雲南,南宋則又深憂廣右、福建諸地。在南宋邊鄙帥臣看來,蒙古軍隊的意圖似乎一覽無遺。南宋人的這種擔憂當然並非多餘,他們之所以深爲關切蒙古軍隊在西南地區的種種舉動並將其稱爲“斡腹”謀略,最讓南宋廣大軍民耿耿於懷的直接緣由是,就在不多年前,蒙軍正是强行假道宋境而“斡腹”滅金,是所謂“殷鑑不遠”!倘若不算太過牽强的話,我們認爲它背後還有更爲深刻的歷史遠因。這就不由令人聯想起漢武帝征西南夷之事。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載: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史記》卷一一六,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993—2994。
這段記載非常清晰地表明漢武帝苦心經營西南夷以圖南越國的戰略,就是先行據有西南之地而後再攻兩廣。*漢武帝開西南夷之事,歷來爲人們所稱道,宋元時代的人們自然也不例外。所謂“漢武開僰道,通西南夷道”,“漢武開僰道,雲南此初程”云云,不甚枚舉。以上參閱《雲南志略輯校·諸夷風俗》,頁86;胡助《純白齋類稿》卷三《賦僰道送蕭存道元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14册,頁567下。雖南宋時代去西漢時代懸隔遼遠,然而當今天再仔細審讀南宋人當時針對蒙古存有所謂“斡腹”之謀的種種隱憂時,我們總會印象深刻地感覺到它們之間所具有的某種歷史關聯。前文所引李曾伯《帥廣條陳五事奏》稱:“廣右之藩籬在邕,邕之藩籬又在兩江,習南方形勢者,素有此論。蓋以右江通大理來路,左江與安南接境,兩江羈縻州峒險隘不一,先朝疆以周索,賴此以控制之故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八《禦邊》,頁4380下—4381上。另外,對前文所提及的南宋末年文人帥臣如吴昌裔、李鳴復、高斯得、陽枋以及魏了翁等對“斡腹”之說的種種言辭,我們總能發現它們與《史記》的這則記載竟如此異曲同工。上述這些帥臣,大多進士出身,無一不是飽學之士,他們不僅“素知南方山川形勢”,對於歷史前轍更是熟稔於胸。他們對《史記·西南夷列傳》的相關記載自然不會陌生,之所以不予明言點破,應是有所違礙,畢竟漢武一統與蒙古來伐之事,勢不可等量齊觀。
通過以上分別對蒙元和南宋方面文獻記載的考察,我們已有充分理由相信,“斡腹”之說很大程度上應源自於南宋西南邊鄙帥臣對蒙軍軍事行動本能警覺反應的一種說辭。而且,元代的人們重新講述所謂“斡腹之謀”這段歷史時,很明顯就是蹈襲前文所述南宋人的那些描述。如宋本稱:“歲己未,憲廟親幸蜀,世祖皇帝以皇弟帥兵渡鄂,將與兀良合台共會江左,宋人號‘斡腹’之師,掎角擣虛,勢急雷電”;盛如梓則云:“憲宗在位,以公(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爲征蠻大元帥,子阿朮佐之統兵,由蜀道征大理、交趾,斡腹湖廣,南方震驚。”吴萊亦云:“金房假道,徒示夾攻;黎、嶲奇兵,竟成斡腹。”*宋本《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三一,四部叢刊縮印本,423册,頁319下;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上,叢書集成本,328册,頁1;吴萊《淵頴集》卷一二《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09册,頁202下。
如果說上文對南宋方面所謂“斡腹”之說出現的歷史過程已大致梳理清楚了的話,那麽接下來我們應該對所謂“斡腹之謀”的結果予以澄清。蒙軍雖然攻滅大理而進占雲南地區,但由此地北上欲圖“斡腹”攻宋的戰略意義並未實現,也沒能取得多少實質性效果。據《兀良氏先廟碑銘》記載,兀良合台領軍北上進擊南宋的主要路線,大致爲橫山寨、老蒼關、貴州、象州、靜江府、辰州、沅州、潭州等地。從雲南北上攻宋,須克服險惡的地理環境障礙,其地山川橫亘,瘴癘之氣肆虐,跨越此等艱難之地理區域,難度可想而知。兀良合台北上進軍的效果並不明顯,甚至容易陷於危險境地。兀良合台的軍隊雖與忽必烈在攻打鄂州時取得了聯繫,然而由於忽必烈急於北上爭奪汗位,蒙古欲圖夾擊南宋的效果自然沒能實現。*參閱堤一昭《忽必烈政權的建立與速不台家族》。明人魏濬就曾評述:“敵性不能南處,隆冬草枯,盛夏蝱出,即當反北。逾蕃部、南詔,必須多歷時月。滇黔之間,岡嶺敧折,敵馬不能長驅,必安據南詔,乃可東向。又得廣交,以窺吴楚,是謂仰攻。敵人狡黠,豈其不諳地利,當時何故發此迂計?謀國之疏,其略可睹。”*魏濬《假道斡腹之謀》,《粤西文載》卷六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466册,頁768上—下。
回到本文開頭所提出的問題上來,即忽必烈進征大理國的目的究竟何在?前文所引《史集》記載,稱是爲了獲取軍糧。然而歷史事實卻表明,忽必烈此番進軍大理國非但沒能達成此目的,損失反而十分慘重。據《賀仁傑神道碑》載:
公由是入備宿衛。經吐蕃曼沱,涉大瀘水,入不毛瘴喘沮澤之鄉,深林盲壑,絶崖狹蹊,馬相縻以顛死,萬里而至大理。歸由來塗,前行者雪深三尺,後至及丈,峻阪踏冰爲梯,衛士多徒行,有遠逾千里外者。比飲至略畔,最諸軍亡失馬,幾四十萬匹。*《姚燧集》卷一七《賀仁傑神道碑》,頁269。
另據《董文忠神道碑》載:“癸丑,從征南詔,其兄平章忠獻公文炳恥不得從,自藁將家僮二百騎追之。大軍深入矣,路經土蕃,戰而後達,纔餘數騎。”*《姚燧集》卷一五《董文忠神道碑》,頁230。前引《史集·突厥—蒙古部族志》稱,當時進征大理國的蒙古軍隊有十個萬戶,而最終僅剩下兩個萬戶。如此巨大的損失,或許正是後來蒙哥要“鈎考”忽必烈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元代史籍對於忽必烈征大理之事始終感覺有所諱言,究其緣由或許亦在此。
忽必烈攻滅大理政權,基本未遇太大抵抗,總共耗時亦不到半年,次年之初即匆匆北返,留下兀良合台繼續在雲南地區征戰。忽必烈滅大理國,雖可視爲一項大功績,*耶律鑄《賢王有雲南之捷》云:“詔出甘泉總六軍,渡瀘深入建元勳。旌旗蟠地慘遮日,金鼓震天寒攪雲。鏖戰折衝貔虎陣,先聲靡拉犬羊羣。中朝詞客椽如筆,擬(一作已)與名王紀所聞。”王禮《羅瀘州子父志節狀》稱:“國家混一南方,自得雲南始,是猶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99册,頁442上;王禮《麟原後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20册,頁539上。然而它的代價卻是十分巨大的。忽必烈時代之所對其攻滅大理國的前因後果未留下詳細的記載,一方面固然是因爲相較其後來滅南宋的不世功業而言,滅大理自然不值得大書特書;但另一方面則正如前文所言,忽必烈進軍大理國本身其實是個得不償失的舉動。他之所以選擇進軍大理國,當時實在是由於征宋遭遇阻難,而後采取變通措施先行進征大理國而已。忽必烈深知,倘若當時便急於攻宋,肯定難有勝果;若遭敗績,於其個人前途而言是極爲不利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蒙古人在征西夏、滅金以及西征過程中,“斡腹”戰術可謂運用嫻熟,屢試不爽。*郝經《三峯山行》詩云:“朔方善爲幹(斡)腹兵,豈肯掠地還攻城?”《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一一,頁572上。這或許與遊牧人羣的圍獵習俗有很大關聯,所謂迂回包抄、夾擊、打圍等等。倘就寬泛意義而言之,無論蒙古入吐蕃,攻川蜀,還是征大理,甚或進軍安南諸地,就其攻宋之客觀大勢上說來,我們或許均可將其解讀成各種“斡腹”之舉。*參閱前揭石堅軍《蒙古與大理關係新探——以“斡腹”之謀爲視角》、《“斡腹”考述》兩文。然而,就忽必烈遠征大理國的事件而言,雖後世史家們經常將此頌揚爲一種典型的“斡腹”壯舉,不過從上文所解析的這段歷史的最初緣起、最終結果以及“斡腹”之說的實際流傳狀況等合而觀之,當日歷史實情似乎並不全然如此。所謂蒙古人早已存有欲先“斡腹”大理而後滅宋的戰略遠謀問題,實在仍需要我們審慎對待。
(本文作者係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Rethinking the So-called “wofu” Strategy: From the Reasons of Kublai’s Expedition on Yunnan and the Struggles between Möngke and Kublai
Wen Haiqing(p.263)
Previous studies almost have always described Kublai’s expedition on Dali Kingdom as part of outflanking strategy of the Mongols to attack the Southern Song, which is called “wofuzhimou” (斡腹之謀,literally “strategy of turning around from interi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historical records, however, reveal that the Mongols did not have such a long-term “wofu” strategy, which is turning around from Dali to defeat the Song. Attacking Chuanshu (川蜀) region (today’s Sichuan and Chongqing area) as breakthrough to defeat the Southern Song was always the strategy of the Mongols. But due to the enhanced defense forces in Chuanshu region, Kublai Khan had to change the strategy to attack the Dali Kingdom instead of Chuanshu region. Because Kublai did not launch a frontal attack on the Song for a relatively long time, the Grand Khan Möngke’s suspicion and resentment to him was triggered. Möngke reacted by personally leading an expedition on the Southern Song, and he still chose to attack Chuanshu region instead of Dali. However, Kublai was deeply aware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this strategy. The whole situation between the Mongols and Southern Song hadn’t been changed until Liu Zheng (劉整)’s surrender to the Mongol authorities. The “wofu” strategy actually was only a speculation from the sensitive generals of the Song, which was based on the Mongolian military activities on their southwestern borders, and it had its own origins in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