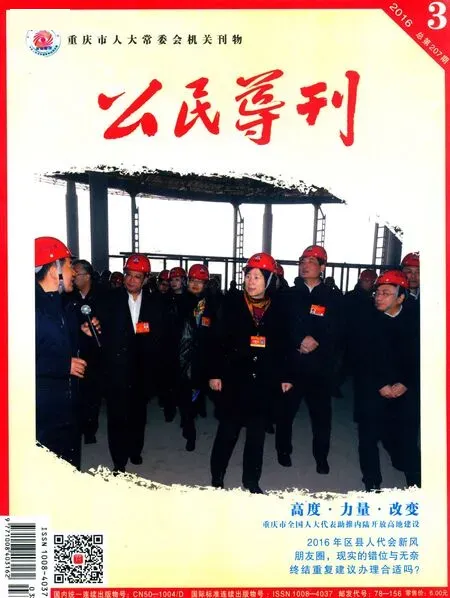人大立法权限须合理平衡民主与效率
2016-04-29阿计
(阿计:著名媒体人,资深人大新闻工作者、中国法学会会员)
国家立法权是立法体制的核心所在,只有清晰划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并构建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才能确保立法同时行进于民主、高效的轨道上。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审议慈善法草案。这是继去年全国人代会审议、通过立法法修正案后,全国人大连续两年行使立法权。
近期已经召开的地方人代会也不时传出立法消息,比如今年广东省人代会就通过了广东省地方立法条例修正案。相对于全国和地方人大常委会频繁立法,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职能由沉寂渐趋活跃,是一个非常鲜明的改革信号。
这一变化潜藏的追问是,究竟哪些立法权应当由人大行使?哪些立法权可以由人大常委会行使?
1982年颁布的现行宪法,构建了统一、分层级、多种类的立法体制,并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进一步明确了纵向的中央与地方之间、横向的人大与政府之间的立法权限,并设定了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订法律的中央专属立法范围,不过,两者之间内向的立法权限并未得以清晰划分。
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全国人大的立法数量不断萎缩,而常委会的立法数量急速递增。
有统计表明,1979年至2009年,全国人大立法占全部立法的比例在第一个十年为33%,第二个十年下降至13%,第三个十年更是骤减至4.2%。自2008年至2015年年底,全国人大仅仅修改了3部法律,同期常委会制订和修改的法律却多达101部。
而在地方立法层面,同样是因为权限划分过于模糊,绝大多数地方性法规都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定,有些省级人大甚至已经十多年没有立法。这些事实表明,人大立法权在很大程度上被虚置,而常委会立法权却有过度膨胀之嫌,这不仅与两者的宪法地位不相称,也削弱了人大对立法全局的主导和调控。
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边界不清,还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越权立法、交叉立法、立法冲突等弊端。
比如,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原则划分是,前者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后者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但由于没有明确界定“基本法律”、“其他法律”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势必导致错位行权等现象,典型者如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三者均属民事基本法律,但前者由全国人大立法,后两者却由常委会制订。
再比如,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可以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不过,由于“部分”、“基本原则”等含义过于抽象概括,也难以控制修法权的失范。
典型者如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1980年制订的婚姻法的修改,其修改、增删的条文数甚至超过了原法律的条文数,并且涉及七大基本制度的改变,这种几近重新立法的修改,事实上很难归入“部分”修改之列。
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活动的失衡状态,从表面看是立法权限划分不清的制度设计不足所致,其实质却是立法民主与立法效率的深刻冲突。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所指出的:“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在现代国家,“主权在民”原则和代议制民主是奠定立法正当性的基石。
在我国的政体框架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相对于其常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行使国家立法权无疑更能体现“主权在民”原则,更符合立法的民主性、正当性逻辑。
但问题在于,按照当下的人大制度设计,全国人大每年仅开一次会,且会期短暂、代表众多,需要承担议政等多项繁重的职能,无论是时间配置、代表素质、参与程度等等,都难以胜任量大面广、高度专业、程序精细的立法任务。
相形之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每两个月开一次会,可以使立法议程处于范围广、常态化的状态,而常委会人数有限、相对专职化等优势,也提高了议事效率和质量。
这是1982年宪法正式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正如彭真所言:“适当扩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方法。”
而历史也证明,常委会广泛而频密的立法有效满足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需求,对构建现代法律体系和推进依法治国功不可没。但同时应当看到,立法权在现实行使中向常委会的过度倾斜,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立法的民意基础,由此引发的越权立法等问题,更是当下法治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目前人大制度的基本架构下,如何既体现全国人大的主导作用,使立法最大程度地反映人民意志,同时又赋予人大常委会足够的立法权限,适应改革和法治的进程,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这就需要合理平衡立法民主和立法效率,更加细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各自的立法权限。
尤其是为了进一步激活全国人大的立法功能,对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普遍性规范意义的基本法律,以及关涉公民权利和民生权益的重要法律,应当坚持由全国人大行使立法权的底线原则,并尽可能厘清应当由其立法的具体事项范围。对于人大常委会对人大立法的修改权,亦应作出更加明确、更具操作性的规范和限制。
与此同时,在人大常委会仍需承担大部分立法的现实语境下,为了有效缓解立法民主与立法效率之间的矛盾,除了进一步动用公民参与等民主立法机制予以民意制约外,还应强化全国人大对常委会立法的监督。
比如,如果常委会对全国人大的立法作出了修改,可以考虑在翌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增设特别议程,由常委会报告修法理由和情况,由代表大会通过批准、备案等程序实施监督,如经审查发现有违宪、违法之处,全国人大可以改变或撤销常委会的不适当立法。
如此,既不延误修法时机,又能确保修法质量。同时,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专门机关,负责日常裁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冲突,并对常委会立法的合宪性、合法性进行即时、动态的审查,以实现对常委会立法的常态化监督,防止越权立法等危险。
国家立法权是立法体制的核心所在,只有清晰划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并构建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才能确保立法同时行进于民主、高效的轨道上。以此为基点,还将促动人大的组织机构、权力配置、议事规则等向更为科学、合理的方向演进。这既是提升法治质量的必然要求,对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亦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