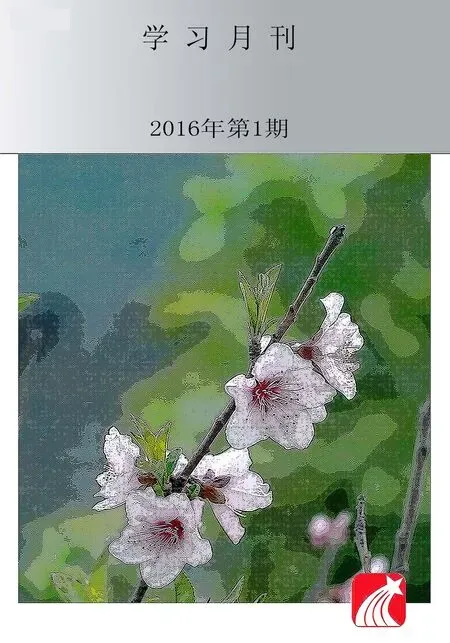据于德
2016-04-25
据于德是孔子立己做人的第二项基本原则。
据,有依据、凭借的意思。据于德,就是以德树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和道是密不可分的,道表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德表示对道认识后按照规则去办事。所谓“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德是源于道的东西,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立志虽要高远,追求天人合一的天道人道,但追求天道人道要从道德的行为开始。换句话说,“志于道”是哲学思想,“据于德”是为人处世的行为,思想是据于道,行为是据于德。儒家强调“人禽之辨”,就是要人明晰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就是德,人丧失了道德就无异于禽兽。故《孟子·滕文公上》讲:“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在人具备生活条件之后,必须伴之以道德教化,并实践伦理规范、道德义务。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德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不依靠外力的特殊的行为规范,属社会意识的范畴。在形式上,它通过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概念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除了法律、行政手段的进一步强化以外,道德是社会稳定发展必不可少的行为规范和调节手段。
我国历史上有对基本道德要求进行高度概括的传统。先秦时期儒家就十分重视道德修养,以后经过历代思想家的继承发挥和不断完善,形成了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道德修养理论。这一理论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认为“物有本末、事有始终”,一切都要从修养个人的品德做起,只有修身才能齐家,然后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早在孔子之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由此形成一种把道德放在首位的文化价值取向。此后,中华伦理道德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中华道德发展的历程表明,以孔孟“五常”为标志,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千年以后,宋代以“八德”为标志,形成了“以家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又过近千年,清末民初,孙中山先生以新“八德”为标志,形成了“以国为本”的伦理道德观。“三个为本”分别成为不同时期道德教化的着重点,反映了不同时代对道德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同时又表明,道德是变化发展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又推动历史的发展进步。
“仁义礼智信”五德(五常),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最具代表性的道德观和核心价值观。汉章帝建初四年以后,“仁义礼智信”五德被确定为整体德目“五常”。五常不仅是五种基础性的“母德”、“基德”,而且形成并高度概括了中华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观念和基本精神。五常中,仁和义是两大根本性的道德元素,可谓总体价值观中的核心价值观。离开了仁义,忠孝礼乐等都失去了意义。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荀子讲:“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白虎通》中说:“君臣以义合,不可则去”,《周易》也讲:“不侍王侯,高尚其事”。可见,仁义相比其他道德要素具有超然性。仁义礼智信五德旨在规范家庭社会的各种伦理关系,这些伦理关系就是《白虎通》说的“三纲六纪”。其中“六纪”即六种伦理关系,即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和朋友,规范了这些关系,社会就能和谐发展,所以陈寅恪先生说“三纲六纪”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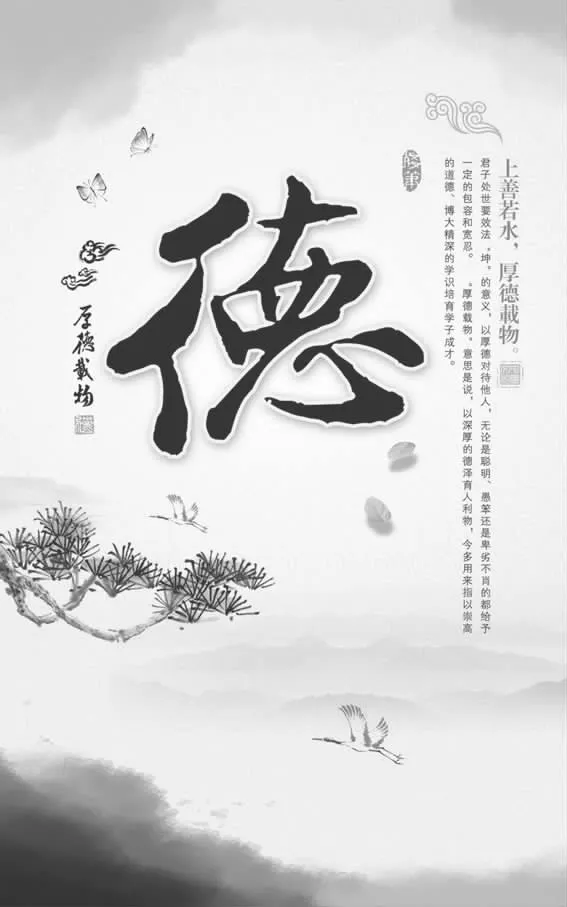
在中国道德观念中具有代表性的德目是通常说的“新老八德”。
“老八德”就是宋人总结的“孝梯忠信礼义廉耻”,它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核心价值和传统美德。其中“孝梯忠信”是孔子仁学的四中体现,孝是对长者的奉养,梯是对兄弟同胞的亲爱,忠是对他人尽心竭力,信是做人做事重诺守信。礼义廉耻这是管子提出的“国之四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从管子的阐述中可知道,礼指的是各种社会规范和秩序,义指的是对国家社会的道德义务,廉指的是坦荡无私公正廉洁,耻指的是对坏事的羞耻之心,“四维”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兴衰存亡。宋代把孝梯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德目合在一起称为八德,又称 “八端”。“八德”在传统社会深入人心,忘记八德就是“忘八端”,忘八端就如同禽兽,不具做人资格。
“老八德“的着眼点是“家”,只有“家固”才能“邦宁”,所以在“家”与“国”的关系上,突出了“孝梯”,并将其置于“忠信”的前面。这八德是宋代对中华道德的新构建和新发展,它一直影响到明清,以致影响到东亚各国。到清末明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康梁等维新派提出以“孝梯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产物。 这“八德”调整了“孝”与“忠”、“家”与“国”的位置,表明民族和国家观念高于家族的观念,既是对古人“教孝即教忠”的继承,也适应了现代“国家至上”的价值观,有利于强化“爱国意识”。“新八德”至今台湾还在奉行,台北市有四条主干道就是以这八德命名的。
通过对新老八德的比较研究,国学界一般认为,还是“孝梯忠信礼义廉耻”更加合理、更具历史渊源,也更能体现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王岐山同志就在一次会上说:“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梯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DNA,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敢挑战这八个字”。我们应该认识到,“八德”这个中华文化的DNA,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务必认真记取、努力践行。
中华传统道德是以人为本的道德,因而它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个基本特点是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孟子讲过两句话,一句是:“所欲有甚于生者”,意为我所要求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人格尊严。另一句是:“所恶有甚于死者”,意为我所厌恶的东西还有比死亡更甚的,这就是丧失人格。坚持人格尊严是双向的,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容他人侮辱;另一方面要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不容侮辱他人人格。第二个基本特点是注重人伦关系。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处在具体的人伦关系之中,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在古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叫“人伦”,所谓人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次序。孟子概括了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五种人伦关系,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和朋友关系。怎样处理这几种关系呢?孟子说要做到“君臣有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传统道德特别重视“天伦”关系,即家庭关系。“父子有亲”就是父慈子孝,“把孝看作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所以“孝梯”在先,“忠信”在后,把“天伦”关系处理好了,才可能处理后其他人伦关系,才可能为国尽忠、对人有信。总之,是要求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仪之道,夫妻之间有内外之别,老少之间有上下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这就是处理好人伦关系的道德遵循和行为准则。
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对于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尚公、入世、仁爱、贵和等道德原则作用尤巨,可视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努力把握。
尚公,也就是重整体的观念。强调整体至上,克己奉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点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在中国传统伦理结构中,为国利民,“兴天下人民之大利”(《墨子·经上》),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是最大的“义”。坚持这一理念,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一切服从这一准则,乃是“仁人志士”的体现。自古以来,关心国家、兴利人民成为了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责任,成为一种不可遏止的忧国忧民情怀。孔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雍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又说君子要“自认以天下之重”,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此后中国的士大夫始终强调“以天下为己任”,从《左传》的“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贾谊的“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到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历代志士仁人的人生信条,也对一般民众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种整体至上的道德文化里,不仅个人对他人、对群体的责任意识始终被置于首位,而且也突出了以小我成就大我,以牺牲个体利益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所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这种整体之上的尚公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强大凝聚力,是中国自古以来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石。
入世,也就是重进取的观念。强调“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宽阔胸襟。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的流变,化育而成中国人的人格精神,表现为相对而生和相互联系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在《易经·易大传》中,最早提出“刚健”学说,“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易经·象传》又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谓天道刚健,君子效法天道,以顽强的奋斗精神来实现自己不息的理想。这与儒家后来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取精神完全一致。儒家强调,修齐治平积极入世不仅是君子人格的体现,更是其实践社会责任的过程。这一思想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时期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族危亡之际更成为激励人们的精神力量。如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无不体现着强烈的感召力量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培育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维护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正是因为自强不息精神的独特价值,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最早就用它来概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
入世作为的另一重要方面是 “厚德载物”的人文情怀,它也是实现刚健自强的现实途径。《易经·象传》中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君子应像大地那样以博大的胸怀,孕育、承载与容纳万物,从而实现其入世有为的理想。
崇德,也就是重品德的观念。中国优秀道德文化重视人的德性品格,重视德性的培养和人格的提升。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都是坚持道德信念不受物质条件的影响。强调明辨义利,主张以理节欲,形成以重视礼义廉耻、奉行孝梯忠信为核心的传统美德体系。尤其是这种崇德尚义的道德追求,通过古代的文明规范体系“礼”,行成了中华民族仁与理互为表里的礼治传统,所以崇德又表现为重礼、重秩序。在传统社会,礼笼罩一切、规定一切,用荀子的话说便是:“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要求人们从饮食、衣服、居室、器用、车马直到待人接物,都要符合礼的规定。于是,法度称为“礼法”,治理成为“礼治”。由于“礼者,人之规范”,是社会秩序的总称,因而它又往往具有法的含义。中国传统社会实际上就是“礼治”的社会,中国文化实际上也是“礼乐”文化。人们循礼与否,不仅是判别文明与野蛮、文雅与粗俗、君子与小人、有德与无德的标准,而且是判别人是否安分守法的标准,这样崇德与重礼的结合,使“人人纳入规范之中”。
贵和,也就是重和谐的观念。“德莫大于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因此贵和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重要精神。贵和精神表现在诸多方面,在国际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在国家治理上,主张“政通人和”,在人际关系上,主张和衷共济,在家庭关系上,主张“家和万事兴”,就是在经营之道上,也是主张“和气生财”。中国人始终认为,祥和之气最可贵、最美好。为了实现人际和社会的和谐,传统文化崇推崇仁爱兼利的原则,孔子以仁作为道德的核心内容,同时将“爱人”作为仁的根本要求,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博施济众”。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因而倡导“爱人若爱其身”。中国的贵和精神不仅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也表现在“任物”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视生态伦理,倡导“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概括了道德修养的完整体系,以供我们遵循,同时还为我们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道德修养方法,诸如“立志”、“学习”、“克己”、“内省”、“去私”、“实践”、“慎独”等等,值得我们认真效法。我们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段时间以来“道德无用论”、“道德代价论”等观点引起广泛争论,但道德滑坡的教训给我们上了深刻的道德教育课。虽然道德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道德作为社会关系强有力的调节器,那么,这个社会就连正常的生活也难以保障。我们需要以法治国建立一个法治社会,也需要以德治国建立一个道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