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学汉语
2016-04-21白乐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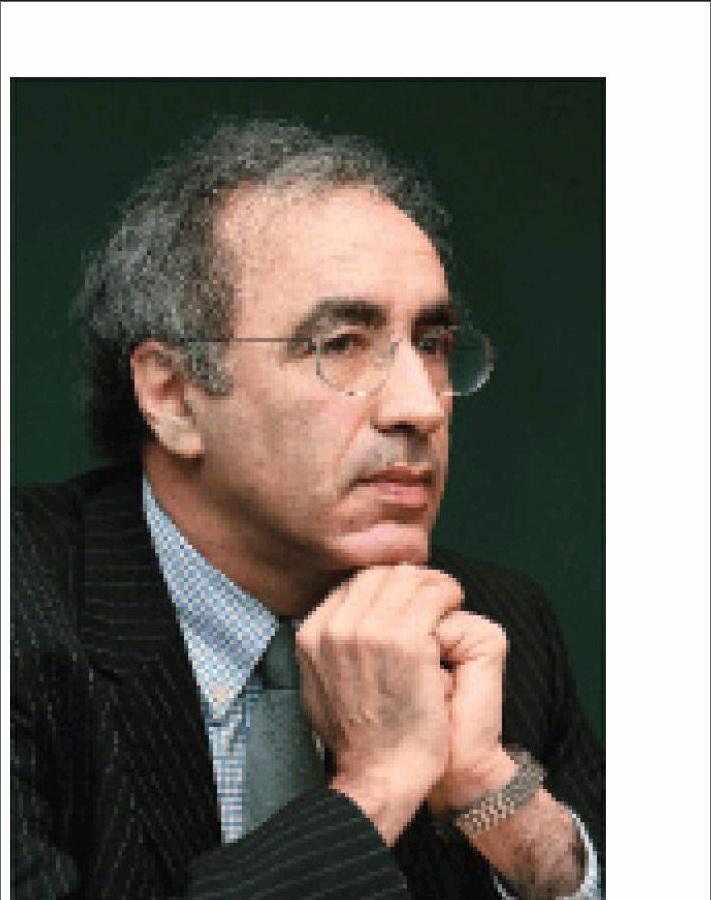


在世界汉语教学界,白乐桑先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全欧第一位汉语教学法博士生导师、法国汉语教师协会创始人及首任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但是,在他身上,你看不到这些“官衔”的影子或光环。他言谈是那么平和,待人是那么亲切,衣着是那么朴实。如果只听声音而不看人的话,就像是同一位普通的中国学者交谈。如果只看人不听声音的话,就是面对着一位普通的法国学者。但是,在平和之下,我感受到了白乐桑教授思想的深邃、知识的广博和追求的坚韧。他告诉我,他原本是学哲学的,理性思维是他的长项。此言不虚,思维的缜密和逻辑的严谨,贯穿着他讲述的始终,恰恰是他如数家珍似的道出的那一件件小事,铺就了他人生的成长之路。
几十年来,我经常被问及“为什么学汉语”,而我找到的答案就是:“我学习汉语就是为了有一天,人们问我,您为什么学习汉语。”
有的人追求相近、熟悉,倾向于走向熟路,也有人一直追求踏上陌生的、别人没有走过的陆地,向往发现疏远的境界、新的视野。
“黑脚”的好奇天性
当自己在汉语教学与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有了不小名气的时候,我也不得不开始对自己进行反思,特别是思考在我一生中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学汉语?你觉得汉语四声调难学吗?我走上汉语之路的因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从个人角度说,我儿时有哪些因素能促使我后来选择了汉语?这些因素对我选择汉语和学好汉语甚至起了一些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用法文说,我就是出生在“黑脚”(pieds-noirs)家庭,是一个“黑脚”,对不同的文化有着好奇的和探索的天性。
一般来讲,对于“黑脚”的来历有这样一种解释:法军19世纪3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登陆的时候,士兵穿的是皮鞋,而当地的阿拉伯人是光脚走路。据说就是根据这个小小的细节,从法国本土过去的法国人被称为“黑脚”,意思是穿皮鞋的。
我的爷爷、奶奶、爸爸都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爸爸从事过不少职业,还特别爱好唱歌,不是一般的爱好,特别爱好,而且他的嗓音是非常好的。我为什么指出这一点呢?也是为了回答经常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中文的声调那么难学,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常常想起我的父亲。
我既是一个法国人,又不是一个正统的法国人。我现在分析,这些因素可能是决定20年以后就开始主修一种莫名其妙的、最遥远的语言文字,那就是汉语。
1950年,我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奥兰省(Oran)第二大城市西迪贝勒阿巴斯。
1962年,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我跟随绝大多数的“黑脚”离开阿尔及利亚,回到了法国本土。
1968年,我进入巴黎第八大学,主修哲学。
入学的第一年我就知道有一个中文系,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踏上了汉语之路。
当时,在我快结束哲学系一年级学业的时候,校方发了一个通知,说从下一年开始,所有学生必须同时主修两个专业。于是,我就去注册西班牙语系,开始一年级的课。但两三个星期后我做出了一个完全改变我一生的选择:放弃西班牙语,改去中文系注册。
放弃西班牙语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对于我来说太容易。是中文系秘书办公室门上的“中文系”3个字吸引了我。对我来说,这3个汉字太有魅力了,是它们改变了我的一生。
于是,我去中文系敲门。进去之后,秘书问:“你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哲学系的,学校不是要我们主修第二个专业吗,我想学一点点中文行不行。他比较幽默地回答:“欢迎,但这个专业的学生少得可怜,只有6个同学,加上你就7个了。他们已经上了两三个星期的汉语课了。”我说:“那好吧。”就这样,我开始走上汉语学习之路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就被汉字迷住了。
我的听觉本来是非常敏感的,可汉字是视觉的东西,这更激发了我的兴趣,因为汉字是陌生的,因为汉字的透明度几乎是零。如果看英文,因为与法文很相似,很透明,所以我能猜到他的意思。可是,如果不认得汉字,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比如,你会说“谢谢”,可你若没有学过汉字,“谢谢”这两个字摆在你的眼前,你都不知道这就是“谢谢”。
正因为透明度几乎是零,我就很想发现汉字后边的境界。所以,我觉得我的发现精神、挑战精神都与汉字的神秘有关。其实,在这之前,我对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了解。
所以,我学习汉语的真正动机就是感到它很神秘,想去弄明白。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刚学过几十个汉字,马上就拿《人民日报》或者其他中文报纸看,经常坐地铁坐过站,因为特别想查到我学过的字。
按现在的话,我当时学的是“月球语言”。月球的意思就是说非常遥远,是不可能去的国家。我没想过中国会开放,我觉得中国就是封闭的。可无论如何,我对汉语还是入了迷。
入迷到什么程度?我的朋友和同学见到我时都会这样和我打招呼:“中国人你好!”因为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主要对他们讲关于中文、关于汉字、关于中国语言等方面的内容,很少讲我的另一个专业——哲学。很多人,包括我的父母问我毕业后打算做什么,我好像是这样回答的:“我知道学中文可能没有任何就业价值,但中文的学士学位毕竟是文科,可以拿这个文科学位在法国教法文。”但是,这到底可行不可行,我当时也不知道。
到中国去留学
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总会有几个时刻是难忘的。对于我来说,第一个难忘的时刻是1973年5月15日下午,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当时我正在学校里,再有一个多月就大学毕业了,正处在“继续学习中文还是就业”之间的纠结当中。这时我得到了一个消息,中国与法国恢复了文化交流,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互派留学生。我们当时对文化交流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但对中法互派留学生感兴趣。我们问学校留学生是否有助学金,他们说有,让我们赶紧去外交部,领取申请表格。
这一切就发生在我快要放弃中文的前一个月。于是,我跑到外交部拿了一张表格。我记得,表格中让我们填写研究计划。我们哪有什么研究计划呀?我都忘了当时到底填了什么,就将表格交给学校了。
中文系的学生人数虽然很少,但我们也得写一篇差不多100页的毕业论文。当时我对中国的成语典故特别感兴趣,于是去找我的两个同学,希望合作把一本中文的现代汉语成语小词典译成法文并加解释。词典里共有3000个成语典故,每个人承担三分之一,先是翻译,找出与之对应的法文俗语,再对典故加以注释。我还建议每个人写一个关于成语的导读。于是,我们按分工各自动手了。结果,他们没完成,我完成了。1973年5月,我通过了这1000个成语的论文答辩。
答辩那段时间,我已经知道去中国留学的申请已由学校转给了外交部,但申请去中国留学的人还比较多,我是最年轻的。当时还没有面试,也不知道外交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但最终我被选上了。
不久,外交部召集入选者开会,负责留学事务的官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信息,包括日常生活的信息。开会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认真地记笔记,他们向我们通报了一些比较古怪的信息,有两个我印象最深。一个是“中国的电压是110伏”。当时我就想,法国的电压都是220伏的,电压不对,我刮胡子怎么办?结果到中国以后发现,中国的电压跟法国是一样的。为什么外交部官员那样说呢?我后来才知道,只有三里屯使馆区的电压比较特殊,全中国的电压都是220伏。另一个是“中国没有洗发香波”。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们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的。这我们就犯愁了。我们在中国可能要待一年啊,不洗头怎么行?其实,到北京之后,我第一次到学校周边的商店转了一圈,发现中国是有洗头发用的东西的。
能到中国留学,我非常激动,随时做着出发的准备。1973年的夏天,我休假时都不敢走得太远,因为不知道什么时间离开法国。8月底,仍然没有任何消息。到了9月,我去外交部问,负责的官员说:“我们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能去中国,还是等消息吧。”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后期,接待外国留学生的各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北京语言学院刚刚复校。11月初,法国外交部终于传来消息说,我们11月18日出发。
那一天是礼拜天,下午4点,我们30个法国留学生乘飞机前往中国。这个时间,或者说北京时间11月19日晚上10点,像是我的第二个生日。从此以后,我的一生才真正与汉语、与中国分不开了。
当时,法国和中国之间没有直达航线。我们乘坐的航班是巴黎飞往东京的,要经停好几个地方,其中包括北京。航班上只有我们30个法国留学生,没有其他乘客,更没有中国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廉价的航班,所以飞机在中途多次经停。
经过漫长的飞行,飞机终于要降落在北京机场了。很多人激动得不能控制自己,飞机还没落地就想站起来,想最先看看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虽然天已经黑了,但我还是想早点看看中国,真有点像是到了月球上的那种感觉。
飞机落地之后,我发现外面的灯光很暗,附近的路上也没有灯,更看不见有骑自行车的。下了飞机,我们老远就看到一幅很大的毛泽东画像立在那儿。在候机楼等行李的时候,我发现地上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当天的航班信息。就这么一块小黑板!这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很遗憾,我当时没有用照相机把它拍下来。这些就是我到北京,或者说到中国后最初的印象。拿到行李出来后,我们见到了北京语言学院派来接我们的老师,然后上了大巴直奔北京语言学院。
几天后,我在给家里的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父母,我们刚到北京,旅途很辛苦,飞行时间22个小时,估计很快就能进城参观北京了,这里完全是乡下。这里很冷,可是天空蓝蓝的,中国人穿的衣服很合适,所有的衣服都是填了棉花的。”我想特别指出,上世纪70年代,北京语言学院所在的五道口是非常荒凉的。
一步步接近中国语言和文化
1973-1975年,我在中国北京留学两年。第一年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进一步学习中文。第二年在北京大学专修哲学。对我而言,这两年既漫长又短暂,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更为重要的是,在提高汉语能力的同时,我一步步接近了原本十分遥远的中国和中国文化。
在去语言学院的路上,我才意识到来接我们的这位老师一直在讲意大利语。我说:“老师,对不起,我们是法国人,不是意大利人。”这位老师说:“我知道,可是意大利语和法语差不多一样嘛,是不是?学院里没有足够的法语老师,所以就派我来接你们了。”我又说:“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多了,我们根本听不懂。”这些对话在一定程度上让我更加坚信,这的确是一个在文化和地理上都很遥远的国度。
到宿舍后,与中国同学的头几次对话直到现在我都难忘。我先到对面的水房想洗把脸清醒一下,再喝点水解解渴。这时已经很晚了,我在楼道里碰到了一位中国同学,他是学法语的,也住在3楼,正准备去水房旁边的厕所。见我之后,他主动用法语打招呼:“Bonjour, je vais aux commodities(您好!我要去出恭)……”离开法国24小时之后,等了若干年之后,第一次和中国人近距离接触,一个中国老师说意大利语,另一个中国同学使用的是路易时代的古法语,也就是只有19世纪文学作品当中才会出现的那种语言。我觉得很好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明白,这些中国学生学习法语的途经只有两个。一个是法文的《北京周报》,另一个是19世纪法国的小说选本。过了两三天,我去告诉这位中国同学,法国人上厕所现在不这么说,这样说很多人可能听不懂。
他上完厕所出来后,看到我正准备用嘴对着水龙头喝水,这位“出恭”的中国同学在我后面喊道:“小心,这个水不能喝。”我惊讶地问道:“为什么?”他说:“这是冷水。”我说:“太好了,我正渴着呢,就要喝冷水。”“可是你干吗要喝凉水呢?”他一脸惊讶地问我,然后说:“到我房间来吧,我给你点儿喝的。”我以为他要请我喝些中国酒什么的,庆祝我们到来。可是,他给我倒在杯子里的却是冒着热气的开水。我还等着他给我加茶叶,但一直没有。我说:“可是,这是热水啊。”他说:“对啊,怎么啦?”你可以想象到,我在法国从来没有听说过在中国要喝所谓的热水。当然,现在外国人都知道了中国游客要喝热水。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绝不仅仅体现在吃喝的表面上。只不过我们最初到中国的时候,对这些表面上的东西感触比较强烈而已。后来,我慢慢领悟到更多的是这些表象之下中国文化更深层面的东西。
第一次接受中国老师的邀请去他家里吃饭,还是到中国三四个月之后。邀请我的中国老师一字一句地说:“明天晚上7点到我家‘吃点东西。”他说的这句话有点模糊,是吃一点小吃,还是正经吃饭?那个时代中国北方的作息时间和我们法国很不一样。在北京,吃晚饭的时间大约是17点半到18点,之后也没有夜生活。邀请我19点去,我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在晚饭之后了。于是我17点半到食堂吃了晚饭,19点再到老师家吃点小吃就行了。到了老师家,我迅速扫了一眼老师说的“一点东西”。招待我的菜肴已经摆在桌子上了,我的天,有饺子、古老肉、牛肉片、芝麻芹菜,等等。这分明是一顿正式的晚饭嘛。打这以后,我开始注意语言背后约定俗成的东西。
第一年的学习结束之后,中国方面告诉我们,谁愿意延长可以再继续学一年,也可以回国。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法国的30个留学生当中,有18个决定再延长一年,有12个回国了。后来,中法之间又有了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交换生。我就是决定再进修一年的18个人之一。
学文学工又学农
第二年,我们继续留下来学习的人可以选择专业,中方根据报的专业分配我们到不同的大学。选择文学专业的同学被分配到了上海复旦大学,而选择中文、历史和哲学专业的同学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来北京大学的同学中,多数都在中文系和历史系,我是哲学系唯一的欧洲学生。当时,哲学系是留学生最少的系,除了我以外,还有5个加拿大的,1个坦桑尼亚的,一共7个留学生。
其实,我在巴黎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北大”这个词了,知道它有一定的名气和威望。得知被分配到北大,我有点荣幸的感觉。我还保留着1974年9月13日给家里的一封信,述说自己当时的感受。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刚刚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不用说,能进入威望这么高的一所大学就读所选的专业,确实是一种难得的特权。学校满足了我的要求,我跟一个哲学系的中国学生同住一个房间。北大校园很大,很漂亮,建筑都是中式的,还能品味到这些建筑古朴传统的气息。我迫不急待地等着‘十一,据说会有大型活动。昨天晚上学校特地为我们举办了欢迎晚会。我们走进校门,他们按照传统,用锣鼓的声音欢迎我们。”
因为留学生很少,我们上的课多半是辅导性质的,对我们提高阅读理解水平确实很有帮助。我当时还没意识到将来要从事现代汉语教学、研究汉语语言。虽然学了中文,但我对哲学还是很感兴趣的。但是,我觉得收获最大的还是中文水平大幅度提高。当时的课老师都是用中文讲,记笔记也是用中文,阅读的书难度也比较大。这些对我来说,是提高我的汉语语言、文字、阅读、书写、听力、表达的主要媒介。除了辅导课之外,系里有时给我们安排了与一些名人的座谈,有的与哲学有关,如冯友兰讲的就是中国哲学问题。也有与哲学无关的,如费孝通讲的就是社会学的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金光大道》的作者浩然作的一场讲座。在此之前,我已经读过他的书,觉得他的语言很有味道,有农村信息。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开场白:“我这几天在农村,有人通知我来北大作讲座。我没有做好准备,我只是来拜访大家的。”听他这么说,我开始还真以为他没有做好准备呢,后来听他讲才明白这是客套话。就像准备了一桌子菜的中国人,会客气地对你说,吃顿便饭。实际情况是,他讲得非常有条理,生动有趣,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讲座时我还录了音,后来把他的讲座也翻译成法语并在法国发表了。
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受到限制,出行不是很方便,只有天津对外国人是不要许可证的。所以,我们决定到天津玩玩。在天津的大街上,到处都有好奇的当地人围着我们,好像是看外星人。最夸张的一次是去洛阳旅游,在火车站,我们这些留学生曾经被街头上百人看了很久,我还在车窗里向外拍了一张照片。
然而,我们真正走到中国人中间,是当时学校搞开门办学。这原本是中国学生的专利,没有留学生什么事。我们是通过某种“抗争”方式获得了机会。其中,到工厂去学工,还是在北语的时候。
大约是1974年5月,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得到允许,把课堂般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在北京吉普车制造厂实习5天。据说,学校这样做是得到了国务院批准的。在这5天中,我们一半时间劳动,一半时间参观,每个留学生跟学一个工厂师傅。我在信中告诉父母:“我跟你们说我们将会考试,因为毛泽东说过教育要联系实际,联系日常生活,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课堂。所以,考试是用中文描写在工厂度过的5天。”
去农村,与农民生活在一起的愿望是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那一年实现的。
第一次去农村是在1974年冬天。我们一行15个人,7个留学生、6个中国学生、2个带队老师。我们分别住在几个农民家里。第二次是1975年5月,也是北京附近的农村。这些村庄尽管离北京不过百十公里,但大多数村民也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当然,我特别注意观察,注意与他们交流。直到现在,我还很难忘记当时与农民的一些简单对话。总的来说,他们问问题时话并不多。
两次在农村的6个星期里,我吃、住和劳动都和村民在一起,睡的是火炕。每天早晨6点起床,不吃早餐,先去田地干活。当然,活比较轻松。8点回来,我们跟村民一起吃早餐,多半是棒子面粥。3个星期就吃过一次肉,主要是蔬菜。我在信中对妈妈说:“如果妈妈在中国会很舒服,因为这里顿顿吃蔬菜,连医生开方子都可能开的是蔬菜。”
后来,每当我对中国朋友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他们总是说,你70年代在中国农村住多苦啊。我对他们说,哪有什么辛苦,而是太难得了。就像到了月球一样,简直太难得了。在中国,我们去了外国人一般去不了的地方,如工厂、农村。我们特别喜欢观察,也高兴能与普通中国人对话和交流。现在,你随便问当时留学的法国同学,如贝罗贝,在中国这两年中最难忘的是什么,他们一定会说在中国的工厂和农村。
1975年5月的一天,从农村回到北大的第三天,我就收拾行李回国了。
记得离开北京的那天,天气不错。学校有人把我送到机场。我注意到,刚来北京的时候在机场里看到的那块写满航班信息的小黑板没有了。这两年北京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我一个人孤单单地推着那种超市的手推车,一直走到飞机的舷梯下。说实话,离开了已经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的中国文化、中国语言,我有一点难过。
那一班法航飞机上没有多少人,空姐走到我跟前微笑地打招呼:“你好!”我礼貌地回了一句:“你好!”她又问道:“您在北京住了几天?”我说住了两年。空姐吓了一跳,说:“这怎么可能?”我告诉她我是在北京留学。她又说:“那您给我好好讲讲中国吧。”看来她不了解我即将离开的这块土地。但是,因为好像就要离开家乡一样,我的心情不是很愉快,所以没再多说话,只是回答:“好吧,等一会儿讲吧。”
飞机滑向跑道,我打开了音乐频道,戴上耳机。音乐传来,又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偶然。那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法国歌曲Capri,cest fini(《结束了,佳普利岛》),我非常熟悉。它讲的是一对恋人在意大利风景如画的佳普利岛上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结局是无奈的。没想到在离别的时候,刚戴上耳机就听到歌手唱至那句“结束了”,好像是上帝有意安排的一样。是啊,我的北京之行真的结束了。心里酸酸的,难以排解。
前面讲过,我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朋友们就开玩笑地给我起了“中国人”这个外号。如果我坚持去学西班牙语,会有人叫我“西班牙人”吗?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学西班牙语吗?肯定不会。我在自己的一本书中的引言中说过,在过去40多年里,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不是“您贵姓”,而是“你为什么学汉语”。我的回答可能会使大多数人感到惊讶,我说:“我学习汉语就是为了以后能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学习汉语。”这不是文字游戏,如果仔细思考一番,人们就能品出这个答案的内涵。(本文选自《“黑脚”的汉语之路:法国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口述》,孔寒冰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