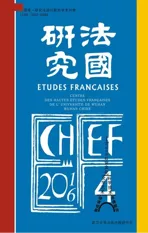巴雷斯小说《柯莱特•波多西》中的人物形象与政治隐喻
2016-04-17姚历
姚历
巴雷斯小说《柯莱特•波多西》中的人物形象与政治隐喻
姚历
作为法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巴雷斯在其小说《梅斯少女—柯莱特·波多西》中巧妙地运用了三个人物形象及其所构建的隐喻体系来影射当时备受法国人关注的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小说中的波多西夫人、阿斯莫斯和柯莱特分别象征着法兰西民族、德国人和被德国占据的梅斯。通过这部作品,作者肯定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法国遗民的法兰西民族,同时也显示出了他本人在民族观上复杂性。
巴雷斯 梅斯 阿尔萨斯-洛林 民族主义
[Résumé]Représentant du mouvement nationaliste en France à la Belle Epoque, Barrès s’est référé à la question de l’Alsace-Lorraine et a tiré l’attention du public français par son roman. A travers les trois personnages—Mme Baudoche, Asmus et Colette qui représentent respectivement la nation française, les allemands et la ville de Metz annexée et leurs métaphores politiques, l’auteur a confirmé l’identité française des habitants messins qui avaient choisi de rester en Alsace-Lorraine depuis l’Annexion et en même temps fait preuve de la complexité de sa théorie nationaliste.
小说《柯莱特·波多西》完成于1909年,就是一部影射普法战争以来长期被德国占据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状况的政治小说。小说的情节波澜不惊:德国青年阿斯莫斯前往普法战争后被割让给德国的城市梅斯谋职,寄宿在当地的波多西夫人家中,后来对其女儿柯莱特渐生情愫并向其求婚,但最终却遭到拒绝。作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巴雷斯对于收复失土念念不忘,他曾在《笔记》中写道:“在政治上,收复梅斯和斯特拉斯堡优先于一切其他事务。”[1]Maurice Barrès, Mes Cahiers, t. VI, Plon, Paris, 1931p. 204. (后文凡是巴雷斯作品中的选文均有作者自行译出)。然而,与其他受到复仇情绪[2]在历史上,复仇情绪(La Revanche)一词专门用来指代普法战争后法国针对德国的仇视。鼓动的民众不同,巴雷斯在小说中并没有刻意地去谴责德国侵占法国领土的暴行,从而煽动仇恨,而是通过讲述一个因为民族矛盾而无法结果的爱情故事展现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境遇,并借此表达了自己的民族观。在小说中,巴雷斯基于自己复杂的民族主义理论体系,分别用三个人物形象—波多西夫人、阿斯莫斯和柯莱特来对应法兰西民族、侵占阿尔萨斯-洛林的德国人和被割让给德国的梅斯,通过三者之间发生的一些或大或小之事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政治隐喻体系:“野蛮”的德国妄图用各种非暴力的手段同化梅斯的法国遗民,但后者没有受到“迷惑”,而是坚定认同自己属于法兰西民族。通过隐喻化异为同的亲和功能,小说成功地引发了法国人—无论是法国境内的居民还是被迫留守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法国遗民—对法兰西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一、波多西夫人:异化的玛丽安娜
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观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起源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3]霍布斯鲍姆在其专著《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 and nationalism since 1870)中表达了这个观点。因此,无论是在文学、政治还是文化生活中,对于共和体制的拥护者们来说,托生于大革命的玛丽安娜都是法兰西民族毫无争议的象征。历史学家莫里斯·阿奎隆认为,这种女性化寓意更能够象征对“男性”主导的“旧制度”的反抗。[4]Maurice Aguillons, Marianne au combat : L'imagerie et la symbolique républicaine de 1789 à 1880, Flammarion, Paris, 1992, p.23.虽然巴雷斯最为人熟知的是其民族主义标签,但和主张君主制的莫拉斯等极端派不同,他一直都是法兰西民族共和传统的拥护者。因此在《柯莱特·波多西》中,他沿用了法国自革命以后以女性形象表征法兰西的传统,将柯莱特的母亲波多西夫人作为法国民族的化身。
.......当阿斯莫斯走进屋子时,他就立即看到大钟的钟摆上雕刻着拿破仑和在他膝盖上玩耍的罗马王(拿破仑幼子),而四面墙上分别都挂着临摹的雕版画---大卫的《网球场誓言》和梯也尔的《土地解放者》.......[5]Maurice Barrès, Colette Baudoche, Librairie Plon, Paris, 1947, p.54. (后文中凡是出自《柯莱特·波多西》中的引文,将随文标明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然而,当波多西夫人在小说中首次登场时,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在房间里忙于针织活的孱弱妇人。这样的形象实际是在隐喻普法战争后的法国:德拉克罗瓦的名作《自由引导人民》 里那位头戴弗里吉亚帽、被战士们所簇拥的玛丽安娜已然不在,在普鲁士霸权的冲击下退缩为一个年迈体弱的弱小女性。而她因为丈夫战死而被迫出让两个房间给德国青年阿斯莫斯则是在暗示法国在普法战争后政权崩溃而又割地赔款的窘境。正如波多西夫人对柯莱特所说:“要是你父亲知道我们有一天要把两个房间让给别人,一个普鲁士人,他会感到多么耻辱啊!”(Barrès:25)波多西母女的生活十分窘迫,仅靠着亡夫留下的一份1200法郎的年金生活,而法国在普法战争之后似乎也一直境遇不佳,外交孤立、工业发展滞后,远远落在了新兴的德国后面。从1880年开始,经济又持续萧条了十几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才逐步复兴。然而,面对生活的拮据和来自敌国的房客,巴雷斯并没有让波多西夫人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使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玛丽安娜的形象回归,而是为她选择了另一条抗争道路,使之成为了一个异化了的玛丽安娜。
巴雷斯的这种处理方式,与1870年以后法国民族主义理论的蜕变不无关系。虽然很多学者都认为法兰西民族属于“由政治意愿界定的公民民族” 。[6]Malcom Crook, Revolutionary Fr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64.然而,普法战争的爆发使得这种公民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政治意义和地缘权利都相继倒塌,[7]黎英亮:《论法国民族主义的蜕变》,载《世界民族》,2004年第四期,第11页。法国的民族主义理论也随之倒向以族裔民族主义。推动着法国民族主义右转的勒南(Renan)和丹纳(Taine)[8]虽然勒南在1882年的著名演讲《什么是民族》中依然持公民民族主义观点,但从其重要著作《闪米特语言通史与比较体系》中还是持“民族”即文化种族的观点。而丹纳在其文论《英国文学史》也提出文明是“种族、环境和时机”的产物。都是巴雷斯的精神导师,而后者又将族裔民族主义中以血缘和文化界定民族的理念深深地植入到了波多西夫人的形象之中。
将种族(race)与民族(nation)的概念混淆是族裔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1853年,戈比瑙(Gobineau)出版了其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性》一书,将法国和德意志诸邦分别划归成为高卢-诺曼种族和日耳曼人种。1870年后,这个观点在法国被广为接受,甚至得到了勒南和丹纳的支持。由此,法国大革命以来那种以民主和理性为基础的民族观逐渐被淡化,法兰西民族的敌人也不再是来自国家内部的教士或者贵族,而是非我族类的“他者”,是需要排斥和拒绝的对象。因此,当阿斯莫斯来到波多西夫人家时要求租房时,后者显示出了一种近似于蛮夷之辨的态度:“您看,您住在这儿会很舒服。这条走廊将整套房一分为二,您在一边,我们住在另一边。”(Barrès:20)很显然,巴雷斯在这里使用了走廊这个意向来表面他的民族观:法德两族毫无共通之处,应当分属于两个“种族”。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阿斯莫斯与波多西母女之间的关系慢慢缓和,甚至变得十分友善,但在他们少有的几次对话之中,只要波多西夫人谈到德国或者德国人时,她都会用“您”或者“您的同胞”来代替。而在后来,当阿斯莫斯情不自禁吻了柯莱特时,波多西夫人又惊呼:“他竟然吻了你,这个普鲁士人!”(Barrès:223)可见,在她的话语体系中,阿斯莫斯始终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只是一个象征着法国敌人—德意志民族—的符号。
作为一个族裔民族主义理论影响下产生的法兰西民族形象,波多西夫人所要捍卫的不再是大革命传统中的民主和自由,而是法兰西这个古老和优秀的“种族”。而法国人想要胜过德国人,即必须证明自己的“种族”更为文明和优秀。在小说中,每晚当波多西夫人给阿斯莫斯端来茶和熟食时,两个人会有一些简单的交流,而后者会让前者校正自己所说的法语,结果竟然“不得不赞叹这门语言的优雅之处” (Barrès:30)。在圣诞节,当阿斯莫斯邀请波多西母女一同分享德国特产的年轮蛋糕时,波多西夫人回应道:“那么请允许我配上一瓶波尔多陈酒.......” (Barrès:88)此外,面对这位德国青年,她还不止一次地提及战前沙龙里的美妙音乐,而且还劝说他在复活节游历临近梅斯的法国城市南锡,因为“南锡在战前比不上梅斯,但那里的装饰很不错。我肯定您会喜欢那里的法国式优雅。”(Barrès:127)于是,在巴雷斯的笔下,当波多西夫人面对阿斯莫斯时,她拿起的是法兰西民族的“文化武器”,让法国在语言、美食、音乐和建筑等各种文化因素完全胜出,让阿斯莫斯所代表的德国文化甘拜下风。
二、阿斯莫斯:来自日耳曼蛮族的“诱惑”
虽然对于德国的排斥和敌视始终是第三共和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劲敌是普鲁士,而德意志或法语中的阿拉曼尼(Allemagne)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在法国战败后才建立的。因此在普法战争后的法国民族主义语境之中,德国人和普鲁士人的概念始终混淆不清。 而小说中的阿斯莫斯来自普鲁士王国的龙兴之地科尼斯堡(Koenigsberg),而阿斯莫斯(Asmus)本身就是德国北部最为典型的姓氏之一。因此,这个人物在设定上基本符合了当时法国人的思维,在小说中时而被称为“德国人(阿拉曼人)”,时而又被称为“普鲁士人”。
在其早年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在野蛮人的目光下》中,巴雷斯就已经阐明了其对于自我实现方式的理念—守护和创造“自我”,就必须抵挡住来自“野蛮人”—一切自我以外的人或事—的诱惑。[9]Jean-Michel Wittmann, Barrès romancier, Honoré Champion, Paris, 2000, p.27.虽然后来他逐渐否定了“自我”而转向民族主义,但这种自我主义理念却投射到了其民族观之上。如果说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异化了“自我”,那么作为普鲁士人的阿斯莫斯则代表着“非我”的“野蛮人”。
正因为如此,阿斯莫斯这个人物反映着当时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中对于德国人的想象。和很多同时期的法国人一样,面对新兴的德意志民族,巴雷斯将其与古老的日耳曼蛮族联系起来,而与此同时将法兰西看成是拉丁文明的继承者。因此,阿斯莫斯在生活中不经意间就会显露出一些“蛮族色彩”。如前面提到的那块年轮蛋糕被作者描述成“一个圆锥状的东西,中间是一个空洞,表面铺着一层粗糙的糖霜” (Barrès:87),毫无美感可言,而这样的粗陋之物却被他视为珍品。在小说中,他多次前往啤酒馆和他的那些同胞们喝得烂醉,回到住处时将墙面搞得一片狼藉,第二天却向柯莱特解释说:“这是我们的风俗”。这样的形象不由让人联想到塔西佗的名著《日耳曼尼亚志》[10]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中的日耳曼蛮族形象在19世纪被法国人视为德意志民族的原型。中对于日耳曼人粗犷和醉酒等粗狂形象的描述。而且,他还“如同所有德国人一样,利用在梅斯居住的机会来练习法语。”(Barrès:18)这似乎又是在对应日耳曼蛮族对拉丁文明的羡慕。在之前的作品中一样,巴雷斯正是借此将德国人与古老的日耳曼人联系起来,以此将前者归为一个野蛮的文明。
然而, 巴雷斯笔下的阿斯莫斯虽然带有明显的蛮族标签,但却并非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个“头戴暗绿色软呢帽,身穿或者可以说身披大学礼袍” (Barrès:15)的书生。从性格上看,他为人温和,在大部分场合的表现也算得体,对于波多西母女等梅斯的本土居民都十分友好,后来在他们一起出游时,他甚至站到法国人一边去呵斥强逼法国人说德语的德国人,和其他同时期法国小说中普鲁士人专横跋扈的士兵形象不完全一样。实际上,这不过是作者在影射德国对于梅斯乃至整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实行的柔性统治和同化策略。从1871年普鲁士军队开进梅斯以来,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对于这座城市的法国遗民较为宽容,他们可以像其他德国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力,其中还甚至有人入选了帝国议会(但这些人最后选择放弃其代表权)。更为重要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德国移民不断涌入,但法语却在梅斯依然被允许使用,[11]François Roth, La Lorraine annexée, Serpenoise, Metz, 2011, p. 133.一直到1914年大战爆发之前,梅斯都还有几家法语报社在运营之中。但是,所有这些宽松政策不过是为了最终同化梅斯的权宜之计。因此,貌似和善的阿斯莫斯依然是“和平征服大军的一部分,紧跟着那些武力征服者的脚步而来,到此已有35年之久。”(Barrès:23)他在梅斯从事的职业则是在学校里教授德语。而他也像自己的德国同事们这样表示:“我是在为自己的种族服务,我和我父辈同台演出,只是我负责的是第二声部。他们征服了这片土地,而我要征服这片土地所产出的果子。”(Barrès:162)正因为如此,阿斯莫斯并非是一个正面人物,他虽然表面上温和友善,但心中却始终得意洋洋,以征服者自居,扮演着作者意识中“诱惑者”的角色。
正因为如此,阿斯莫斯对于柯莱特的感情中始终掺杂着诱惑与拉拢的意味。例如到了圣诞节时,他特地在房间里布置好了一棵圣诞树,邀请柯莱特参观,并送给了她一本德语诗集作为礼物。德语诗集的用意不言而喻,而圣诞树在今天看来似乎普通,但在小说的语境之中却构成了一个文化意向。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圣诞树在欧洲只不过是德国北部,特别是普鲁士地区的新教传统,在当时天主教徒占多数的法国并不流行,这与巴雷斯所主张的“天主教的法国”是冲突的。而当德皇威廉二世巡视梅斯时,他更是兴高采烈地招呼柯莱特一同观看。到小说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向柯莱特求婚,这显然是在隐喻普鲁士对于梅斯的觊觎。而在等待答复的当天,他“浮想联翩,看着眼前这个优雅的社会,他似乎能够感到其中的一些悲凉,但是今天,他感到自己终于能够升级了。”(Barrès:251)这里,作者借阿斯莫斯表达了自己对于德国人的看法:他们不过是一群觊觎法兰西文明的野蛮人,即使表现出某种善意,也不过是为了征服并且通过征服来提升自我而已。因此,正如“自我”必须在抵抗“野蛮人”而得以完全一样,为了保全高贵的法兰西民族,就必须拒绝来自阿斯莫斯的“诱惑”。
三、柯莱特:自愿归属于法兰西的梅斯和阿尔萨斯-洛林
虽然小说以“柯莱特·波多西”为名,但相对于波多西夫人和阿斯莫斯,巴雷斯反而对这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着墨不多,甚至连肖像描写都不曾有。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面对“诱惑”的女孩柯莱特所代表的就是德国抢占的梅斯:小说的副标题《一个梅斯少女的故事》已经在暗示柯莱特和梅斯之间的联系,而波多西(Baudoche)这个姓氏属于梅斯最古老的家族之一,梅斯历史上有好几任市政厅长官都出自于此家族。柯莱特继承了波多西这个姓氏也就意味着她承载着梅斯的厚重历史和传统。而她与波多西夫人的母女关系也表明了作者认为梅斯理因属于法国的政治立场。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当时的法国人来说,梅斯并非一个独立的存在,而往往将其与整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联系起来。[12]阿尔萨斯-洛林这个概念并非来自法国,而是源于1860年一篇在柏林发表的名为《Elsaß–Lothringen deutsch》的匿名文章,指代法国境内的德语方言区。普法战争后,法国除了将境内的德语区割让给德国外,还被迫让后者侵占了一部分法语区,而梅斯是其中最大的城市。因此,在法国的文学作品和媒体中,斯特拉斯堡和梅斯都经常被用来指代“阿尔萨斯-洛林”。由此,柯莱特、梅斯和阿尔萨斯-洛林之间在小说中构成了一种双重投射的关系—柯莱特象征着梅斯,而梅斯又可以代表整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柯莱特的前途既决定着梅斯的命运,更预示着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未来。
在小说中,巴雷斯特别地提到了德国人在梅斯大兴土木的活动:“在这片高地之下,日耳曼人的建筑如潮水般涌现,似乎想要吞没一切......任何人一到梅斯,就能察觉到这座城市的征服者们正在按照他们的意愿和方式将其重建。”(Barrès:6)如果说德国人正在对梅斯的建筑与风貌进行破坏和侵蚀,使得这座城市最终日耳曼化,那么阿斯莫斯对柯莱特的各种示好,可以被看成是在对她进行拉拢和引诱,让她离开自己的母亲,成为德国人的新娘。虽然象征着法兰西民族的波多西人无疑是柯莱特的唯一依靠,但当阿斯莫斯几次试图与她女儿接近时,她都没有直接干涉。而当柯莱特面对阿斯莫斯的求婚时,她更是将决定权留给了自己的女儿:““亲爱的,你必须做决定了。如果你拒绝,我们就要在他的窗台上挂出招租的牌子了。”(Barrès:228)
巴雷斯在情节上之所以会如此安排,与其民族主义的地域性特点不无关系,他在《民族主义场景与理论》中写道:“社会个体构成了社区;社区构成了地区;地区构成了民族”。[13]Maurice Barrès, Scènes et doctrines du nationalsime, Trident, Paris,1987, p. 187.既然民族是由地区建构的,那么地区就有义务担负起维护民族完整的义务,因为 “法兰西的民族性来源于地域,如果后者有所缺失,那么法国的民族性也就不完整了。”[14]Maurice Barrès, Scènes et doctrines du nationalsime, Trident, Paris,1987, p. 215.因此,象征着梅斯的柯莱特必须对自己的命运和归属作出决定,回绝阿斯莫斯的“诱惑”。正如德国对梅斯实行的宽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人心的效果,阿斯莫斯的友善态度也逐步让柯莱特对他有了好感。但是,一旦他与波多西夫人意见相左,柯莱特都会坚定地站到母亲一边。然而,和母亲用文化和历史与阿斯莫斯划清界线的作法不同,柯莱特在回绝这个房客的邀请或是否定他的观点时更多地是显示出了一种态度。例如阿斯莫斯曾提出借给她一些自己带来的德语书时,她立即回绝道:“我还不会说德语”。而当有一次阿斯莫斯读到一篇关于梅斯曾臣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文章,并借此对她说:“小姐您看,您曾经属于德国。”她“红着脸”回答:“我不知道1000多年前的梅斯人是怎么想的,但我不想成为德国人!”(Barrès:247)这样的态度似乎是在回应勒南在其1882年的著名演讲《什么是民族?》中所强调的观点:民族是“公共意志”的结果。这也体现了巴雷斯民族主义体系的复杂性,尽管和1870年之后的诸多法国学者一样,面对第三共和国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的一系列执政危机(布朗热运动、巴拿马危机和德雷福斯案)以及强敌德国的兴起,他选择了族裔民族主义作为救世良方,但作为一个共和派,他的思想中又根深蒂固地保留着法国的公民主义传统。正因为如此,柯莱特在阿斯莫斯面前并没有表现出对他的特别排斥或是厌恶,更多的则是在强调:她之所以是法国人,这是她的意志所决定的。
小说的结尾部分是围绕着阿斯莫斯的求婚展开的。如前所述,求婚这个举动实际上是在影射德国希望最终能够同化梅斯以及整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将其完全日耳曼化的企图。如果柯莱特接受求婚,也就意味着接受了“诱惑”与“野蛮人”为伍,从而丧失了“自我”,她的法兰西认同也就不再存在。兹事体大,巴雷斯特别把柯莱特拒绝阿斯莫斯的场景安排在了梅斯每年一度纪念战争逝者的弥撒之后。在教堂中,她“双膝跪地,居于她的德国求婚者与母亲之间……沉浸在那些高贵的思想之中,正是这些思想触动着我们民族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感……”(Barrès:247)在这里,民族情感与宗教融合起来,使得柯莱特的个人抉择被赋予了一种宗教式的神圣感。而当柯莱特庄重地拒绝了阿斯莫斯也就是在表明梅斯乃至整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选择认同法兰西民族,而这种选择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项目】武汉理工大学校级自主创新项目《美好年代的终结—巴雷斯“东方棱堡“三部曲研究》(项目编号:20110776);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视觉艺术与叶芝的对立诗学研究》(项目编号:16CWW019)。
(责任编辑:龙山)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