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弗的来由与归宿
2016-04-14杨志
杨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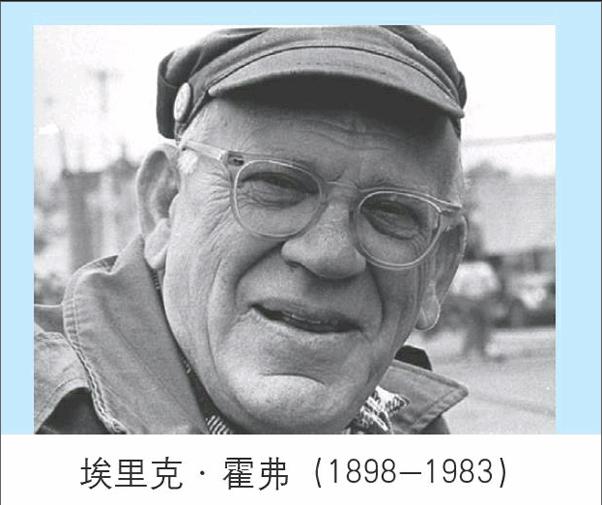
群氓研究,勒庞的《乌合之众》与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为开山作,但最可读也最震撼的,窃以为当数美国码头工人、思想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1898-1983)的《狂热分子》。该书研究群众运动中“言辞人”(煽动群众造反的知识分子)、“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直译为“忠实信徒”)与“行动者”(利用运动的牟利者)三类人的心理。这三种人的分析,以狂热分子最精彩,所以编辑把原名“论群众运动的本质”换为副标题,改正标题为“狂热分子”,这一改,“大题小做”,但点明了精华所在。书一出,轰动欧美,销行五十万册,译为十二种文字,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经典。
霍弗,一介码头工人,为何能写这样一部著作?
一、迷雾中的前半生
《狂热分子》的中译者梁永安这样介绍霍弗的生平:一九○二年生于纽约,双亲为德国移民。七岁时,眼睛莫名其妙瞎了,由德国女仆玛尔莎照顾,从未上过学。十五岁,眼睛又莫名其妙好了,他怕再瞎,如饥似渴地读书。玛尔莎说,霍弗家人都短寿,他估计也活不过四十岁。一九一九年,玛尔莎离美返德,再无音讯,但霍弗始终挂念她。翌年,父亲去世,剩下他孑然一身。这时霍弗已十八岁,心想生命近半,又无前途,便前往洛杉矶,到贫民窟一住十年,“直接从育婴室走向贫民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霍弗辗转漂泊,打零工,广泛接触各色人等,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一九四二年落脚旧金山,加入工会,当码头工人,写成《狂热分子》,一举成名。
这段介绍,转述自霍弗第一部传记《埃里克·霍弗:美国奥德赛》(Eric Hoffer:An American Odyssey,1968年),作者汤姆金斯(Calvin Tomkins),全本霍弗自述,并无旁证。这段生平,读来如先知的“神迹史”,云山雾罩,难以置信。霍弗的思想,清晰犀利,但其生平,影影绰绰,如在雾中。后读霍弗的第四部传记,贝赛尔(Thomas Bethell)的《埃里克·霍弗:码头工人哲学家》(Eric Hoffer: The Longshoreman Philosopher,2012年),才得知:对霍弗前半生大惑不解的大有人在,包括其密友。
事实是—他的生平,最早的可信史料是一则笔记。一九三四年一月,身长六英尺的霍弗孑然一身,“发现自己站在加州的圣地亚哥,身无分文,无望找到工作”。而一九三四年前,霍弗在哪?家境如何?父母兄弟怎样?做过什么?无人知晓。甚至生年都成谜,一说一九○二年生(梁永安从此说),一说一八九八年生,两种说法全是霍弗给的,并无旁证。他自称在纽约长大,但朋友发现,他并不熟悉纽约,名满天下后,也未见早年亲友来访。这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可谓异乎寻常。他的复明,医生诧异莫名,认为闻所未闻。至于“感情深厚”的女仆玛尔莎,贝赛尔发现,他最早谈及身世的信里,只字不提,倒说父亲去世后,跟姑妈住过一年,成名后才提的。
对此,熟人猜测—霍弗其实不是美国土著,而是非法移民,未经历归化程序,所以撒谎。
这个猜测,正可解释霍弗离奇古怪的前半生:为何眼睛失明又复明?因为这可解释,为何他在美国没有熟人,为何没有进过学。至于德国保姆,则能解释他为何有浓重的德国口音。这个猜测也能跟霍弗的许多事迹相印证:除了去过一次墨西哥,从未出国,因为没护照,怕回不来;不熟美国历史,却对欧洲历史了如指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九年间,百万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多数从墨西哥越境,前述笔记提到的圣地亚哥,恰恰毗邻墨西哥。
那霍弗来自哪里?
亲友猜测是德国。如在美国出生,英语当是美国腔,但霍弗有浓厚的巴伐利亚德语腔,越老越明显。事实上,他的德语很流畅,胜过英语。从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学英语卡片看,霍弗甚至不掌握许多简单的英语词。贝赛尔还指出,霍弗熟悉魏玛德国的通货膨胀,甚至能举出细节,对正经历大萧条的美国人,这有点奇怪。更重要的是,霍弗把希特勒视为自己最重大的思想背景(而非推行新政、改造美国的罗斯福),说要没希特勒,自己根本不会搞研究。纳粹正崛起于巴伐利亚,很可能,霍弗曾目睹纳粹的狂热行径。
二、思想之矛·肉身之盾
霍弗忌谈生平,常说“我的生平无足道,不值一提,思想才重要”。这话倒启发我们—“思想”是理解他这人的“一手材料”,将其 “生平”与“思想”结合,没准能窥见他情感世界之一二。
霍弗前半生,最核心的情绪,是漂泊无依,形影相吊。
一九四一年,他写过一封信,草稿今存,提及家人皆亡,孑然一身,而且,家族没一人活过五十岁。这时他尚未成名,所述当可信。按一八九八年生计算,他写《狂热分子》时正在五十岁左右。可见,霍弗是抱着“雁过留声”的绝望来写这书的,大限在即的忧惧,想必如硫酸时时腐蚀他的心。“形影相吊”的李密有祖母,处境比霍弗还强些,只有“独影自命”的川端康成跟他相近。我们知道,袁世凯决定称帝,一大动因是家族男丁无人活过六十岁,自己看看就六十了,这才妄想“只有真龙之气,才能破了这家族魔咒”。死亡逼近的忧惧,两人一样,只不过,袁世凯的忧惧,最终让他身败名裂;霍弗的忧惧,最终让他一举成名。(按,他后来改称家人都活不过四十岁,或许是不想让人看出这个心理背景。)
霍弗前半生,谈过恋爱吗?晚年,他回忆五十年前仅有的一次“恋爱”,眷恋不已,对方叫Helen,大他五岁。但贝赛尔怀疑,那是霍弗单相思,对方只是帮他的热心人而已,霍弗五十三岁前,可能一次恋爱都没谈过。我看霍弗壮年照片,其貌不扬,这也不是不可能。他也不隐讳,自己的性欲,全靠打工挣钱嫖娼解决。
孑然一身,大限将至,没有爱人,霍弗如何熬过青春,再熬过中年?抱着何等绝望,在一日又一日的辛苦劳动后,在旅馆的昏灯下孤零零写《狂热分子》?霍弗承认,自杀过三四次,都没死成。千古艰难唯一死,死何难哉?没死成,说明心不甘,情不愿。
有位美国女子克拉拉·戴尔(Clara Pearl Dyer)这样写道:
我的童年记忆由疾病、死亡和葬礼构成,从四岁到十一岁,失去了六个亲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两个姐姐……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觉得上帝一定有特别的任务交给我,否则不会只让我一人活着。
最后,她投向上帝的怀抱,“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来华传教。
但霍弗这个大老粗不同,反“逆流而上,保持愤怒”,“走向心理学上的真”,以一己肉身死扛,冷酷剖析包括自己在内的失意者:“理想的潜在信徒,应是独来独往,不属于任何集体,无法泯灭自我,无法靠团体来掩盖自己的渺小、无意义和寒酸”,“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这实为“抉心自食,欲知本味”(鲁迅语)的自厌自戕,“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冷酷”中熬煮着“绝望”。正因此,身为底层失意者的霍弗才能这样鲜血淋漓这样动物凶猛这样栩栩如生地撕出同类们的凄惨面目,暴露于众,也就无怪乎有人责他“冷酷入髓”了。
但是,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狂热分子》的无神论,霍弗也只能扛一时。他的归宿,最终还是如克拉拉,也如他冷酷解剖的狂热分子,一样是民族、上帝与国家:民族是犹太人,上帝是耶和华,国家则是美国。
霍弗是犹太人么?情人也不确定,只能说大概是。听这话,霍弗当出身不怎么虔诚的犹太家庭,没行过割礼(呃,你懂的)。霍弗有时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从未有一刻忘怀上帝。贝赛尔拜访他的宿舍,发现书架上基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卡尔、《圣经》等宗教类著作。不过,他在意的不是基督教,而是犹太教。事实上,他几乎从不批评犹太教,还写诗颂扬耶和华“是我的神。/他陪伴我,渗透我的所有思想”。以色列建国后,他欢呼雀跃,宣称:“犹太人绝对独一无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最钦佩的五个人,有两名是以色列开国功臣。直到临终,他还在关心以色列的前途。由此推断,霍弗当为犹太人,甚至,家人没准就葬身于纳粹之手。
至于美国,霍弗也容不得任何批评。左派的乔姆斯基批判美国,他怒火中烧,认定乔姆斯基这类“公知”攻击美国是出于私欲,而非公心,视为吃里扒外的市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霍弗在电视节目里大声讴歌美国,赢得一片喝彩,成为公众人物(《埃里克·霍弗:美国奥德赛》的出版正沾了光)。临终前,他还认为美国该占领沙特,抢它的石油—“我们怕谁?”
霍弗讲,狂热分子膜拜集体,源于自卑,实为“心理代偿”。霍弗如此崇拜犹太人,如此捍卫美国,也是一种“心理补偿”吗?可以推断,这跟他的孤苦离群、自卑自厌当有关联。事实上,这些情绪(特别是自卑),不但催生了霍弗的集体狂热,还激活了霍弗的另一个面相—反智倾向。
思想家还反智?说来奇怪,却是事实。一九六七年,他出版《我们时代的脾性》(The Temper of Our Time),把原先冷酷审视的“狂热分子”赞美成“脊梁”,又把“知识分子”进一步丑化为“蠹虫”,简直是“希特勒”的代名词。身处“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要知道这话,估计哭笑不得。其实,这种反智倾向,《狂热分子》里就埋伏着,其中霍弗引托克维尔的话批“言辞人”(即知识分子),但立场跟托克维尔不同:托克维尔以贵族自命,批知识分子是就事论事;霍弗则是“大老粗”鄙夷“臭老九”,洋溢着一个知识草根对知识精英的“羡慕嫉妒恨”。
霍弗,草根到何种程度?答曰:自学成才,连介绍黑格尔的册子都读不懂,经济学更一窍不通,思想家里够稀罕。不过,他说自己的思想主要源于生活,并且,除了尼采和海涅之外,未受德国影响。这就是牛皮话了。只论二十世纪,他就深受两大派德语思想的影响,而且都是学院派,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一派是精神分析。希特勒崛起,是犹太知识分子的大挑战,精神分析也不例外(精神分析的早期成员,几乎全是犹太人),晚年弗洛伊德由此开创“群体心理学转向”,写《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的赖希(Wilhelm Reich)和写《逃避自由》的弗洛姆(Erich Fromm)都是重要代表,后者对霍弗写《狂热分子》正有直接影响。不过,他极厌恶弗洛伊德,骂他是“堕落分子”,“用他的病传染我们,再来推销精神分析”(按弗洛伊德,这叫“弑父情结”)。另一派是韦伯开创的社会学。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韦伯是少数几个得霍弗青眼的之一,特别推崇韦伯的“价值中立”,还读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要知道,他没专门读过弗洛伊德的任何一本书,说“拿起来就累”。事实上,正是韦伯的存在,使霍弗有了写《狂热分子》的样板,既当“约伯”,又当“韦伯”。
或许是以自身为营养,思想家与艺术家的神奇,是能预言自己的未来。壮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结尾,皮埃尔成了名人,致力社会改革,自以为是、自吹自擂乃至固执愚钝,而妻子娜塔莎仰慕他,成了名副其实的醋瓶子。他做梦也想不到,这完完全全预言了晚年的自己。霍弗也如是。他在《狂热分子》里讲“灵感枯竭的过气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迟早会堕入狂热爱国分子、种族主义贩子和某种神圣伟业的鼓吹者的阵营”,也预言了二十年后的自己。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霍弗成了狂热保守派,支持美国政府介入越战,反对黑人民权运动,鼓吹美国白人对黑人无须负责,倒是黑人自己该反省。美国总统约翰逊介入越战,名声不佳,但霍弗力挺他,誉他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总统”。约翰逊投桃报李,成立全国民事动乱委员会时,任命霍弗为委员,参与调查种族冲突。他在会上怒目圆睁,挥拳高喊:“我穷了一辈子,捡棉花时,黑人吃的比我好,穿的比我好!”这就过了。
才华这东西,我以为,如读书人的视力,最难保住。艰难困苦,玉成了霍弗。但是,一旦他从“人性解剖者”转向“集体代言人”,又放弃“韦伯”与“约伯”的二元平衡,倒向狂热,其“社会能见度”也就大受损害了。诗人杨键,写过一首《来由》:“一触即发的欲望/造就了我和你—/
在长久的相对里生活,/我们得到了尖锐的矛和抵抗的盾。”这里的“我和你”,如果不拘泥字义,理解为“分裂的自我”,正适合理解霍弗:他的“尖锐的矛”与“抵抗的盾”,就是这样以自身血肉为战场“自相残杀”的。
这真真是霍弗的悲剧。
三、“三人行”的后半生
在《狂热分子》出版前夕,霍弗结识了一对夫妻—塞尔登·奥斯本(Selden Osborne,1911-1993)与莉莉(Lili Fabilli Osborne,1916-2010),私生活出现了重大转折。
当时,霍弗在码头忙碌之余,坚持读书,引起工会干部塞尔登注意,上前攀谈,惊其见识,邀到家里做客,介绍他认识了妻子莉莉。从此,他每到周日都去塞尔登家做客,这家人成了霍弗后半生仅有的亲人。
霍弗仇恨纳粹,也不喜苏联,这对夫妻却是坚定的左派。一九二九年,欧美爆发经济危机,很多知识分子转向社会主义,他们便是其中成员。莉莉是意大利移民后裔,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组织过工会;麦卡锡时期,因为拒绝宣誓忠于美国,丢了工作。塞尔登更激进,他出身中产阶级,读斯坦福大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读到了研究生),坚信共产主义将在美国获胜。为确保革命爆发时能站在最前线,他加入由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哈利(Harry Bridges)领导的旧金山工会,在那结识了霍弗。
霍弗半生漂泊,总抱怨没空写作,加入工会后,才获得了稳定生活,足以一面工作,一面思考,写了十一本书。成名后,他照旧在码头工作,干到退休,说:到哪都觉得是外人,只有到码头工作后,才有了家。其中原因,既是遇见了塞尔登一家,也是工会为他提供了稳定生活—也就是说,霍弗后半生,最亲密的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他提供稳定生活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霍弗不赞成他们的思想。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哈利,精明能干,美国政府视为眼中钉,却无可奈何。霍弗私下钦佩哈利,虽然偶尔叨咕,说“我的饭碗是美国给的,可不是工会”,这话也通,但多少流露出一丝气馁;但公开场合绝不夸奖对方,反含含糊糊攻击之。工会上层呢,也淡化他的存在。双方关系,尴尴尬尬。塞尔登为霍弗抱不平,给工会领导写信,要求承认他的存在。哈利专门过问此事,打了一个大大的“no”。
塞尔登,老好人。他牺牲前途,加入工会,但哈利不怎么信任知识分子,其实不受重用。他热爱苏联,霍弗则不以为然,两人争论一辈子,却为生死交。霍弗去世后,贝赛尔去采访七十多岁的塞尔登,他要求先提个问题,答对了才接受采访。贝赛尔以为是什么尖锐问题,结果,他问:“你不赞成对苏联打核战争的吧?”可见此公的老天真。
霍弗以“大老粗”代言人自居,但其实跟工友都无深交,仅有的几个友人全是欣赏他的知识分子,关系最好的,是塞尔登。塞尔登热心帮助霍弗,是他事业的助力者(后来他到大学讲课,是塞尔登牵的线),但霍弗对待塞尔登,显然没塞尔登热情。其中缘由,想来是天才往往自我中心,不怎么体恤旁人(霍弗承认自己有这毛病);何况他内心未必瞧得上视为“研究对象”的塞尔登。塞尔登未必不清楚霍弗的想法,但欣赏其才,也就不介怀了。
前述两部传记,其实差别很大:《埃里克·霍弗:美国奥德赛》是歌颂霍弗的,把“群众冷血录”的作者捣鼓成了“国民鸡汤文”的作者;《埃里克·霍弗:码头工人哲学家》呢,不时拿霍弗的世故比对塞尔登、莉莉的勇敢,显然对其人品有微词。但我以为,贝赛尔苛求了。霍弗是非法移民,莉莉与塞尔登为美国土著,处境不同。人离乡贱,霍弗流离异国,底层拼搏多年,没点滑头,如何生存?更何况,直线条也出不了霍弗这种思想家。作为思想家,霍弗的一大特色是推演慈悲变残忍、自卑变自大、自私变无私这类“心理辩证法”(他称为“心理化学反应”),勒庞、弗洛伊德、弗洛姆等倒没这种敏感。我估计,这多多少少折射了霍弗本人的情感模式。杜甫诗云:“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这是诗圣一根筋了,“蝼蚁”与“大鲸”也未必冲突。霍弗讲,最自私者,也可能极无私。这种“心理化学反应”,虽然匪夷所思,却吻合人性。比如:康有为的自私,理所当然;他的无私,自以为真。两者其实相得益彰。我怀疑,康有为要没伪造密诏杀徒行骗的“厚黑学”,是否还能写得出慷慨无私的《大同书》?霍弗自然没康有为厚黑,但他自己的前半生,连对塞尔登与莉莉也守口如瓶,可见心曲之深。而他的反黑人民权运动,几分真心,几分博名,也只有他自个儿清楚了。塞尔登也想著书立说,努力过,没成功。一个原因,恐怕是他太过良善,对人性的复杂隐微缺乏体会。(按,霍弗关注狂热分子的“无私”,对狂热分子的“狂热并算计着”强调不够,窃以为也有不足,人太自私,朋友就少,难免孤立无援的恐惧,有时候,恐惧到了极点,就不得不以狂热情绪来抵挡,但狂热归狂热,算计的自私本性还是不变的。)
贝赛尔指出,霍弗虽为塞尔登老友,却不怎么了解对方,一直把他视为狂热分子的“典型”,认为他加入工会,意在求名图利。这说明,霍弗囿于自身性格及经历,对其他阶层的想象充满了“无利不起早”的套路。虽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这样简单化塞尔登、格瓦拉这类“中产的孩子”,恰恰暴露了霍弗作为“本色思想家”的局限,也难怪他逃脱不了“代表作即处女作”的命运了。从后来的著作看,霍弗不怎么理解一九六八年革命,因为这场群众运动主要由“中产的孩子”发动,而非他谙熟的底层失意者。(按,霍弗后半生住在旧金山,这里是垮掉派的大本营,嬉皮士的发源地,莉莉的姐姐就嫁给了垮掉派诗人—霍弗不用说是反垮掉派和嬉皮士的。)
结识没多久,霍弗跟莉莉成了情人。
这事,塞尔登何时知道的?不清楚。但他默许了,没怪霍弗,始终是好友。其中原因,一是塞尔登不爱莉莉了,二是他经济困窘,难以支持家庭,也就乐得霍弗插足。一九五五年,莉莉生下第三个孩子,取名埃里克(即霍弗的名),虽然随塞尔登姓,实为霍弗之子。十四年后,塞尔登夫妇离婚(但塞尔登始终有莉莉家的钥匙),霍弗向莉莉求婚,但莉莉担心婚后得离开三个孩子,拒绝了。两人就这样保持情人关系,至死未婚。霍弗还是周日才去莉莉家,平时一个人住,过着斯巴达式生活。到过他住所的,最深印象是家徒四壁,除了书和读书卡片,什么也没有,像荒漠中的老怪物。
虽然塞尔登没怪霍弗,但这事不光彩,到底影响了孩子们。塞尔登大女儿唐娅已经懂事,不满霍弗,很早离家,不幸早逝。后面两个儿子喜欢霍弗,特别是埃里克,一直怀疑霍弗是亲生父亲,成年后,他向霍弗求证,但霍弗未正面承认(莉莉偷偷承认了)。霍弗得子时,年届花甲,喜悦之情,自然难以形容,但他显然不太懂如何跟大男孩相处,埃里克进入青春期后,跟他关系紧张,最后离家出走(埃里克后来回忆往事,说爱霍弗,也爱塞尔登,但塞尔登更像好爸爸)。
只有莉莉,是霍弗在这世间的最爱,他在一则日记里写道:“我时时提醒自己,我爱她,她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完了。”另一则日记则说:
鸠占鹊巢,夺人之妻,这是我的错。我不觉得这有多冒犯父亲,只是对唐娅和埃里克这两个孩子心怀愧疚。埃里克相信自己是我亲生的,却同我和他母亲断绝了关系。我和他爸关系倒不错。唐娅已不在人世,埃里克跑到阿拉斯加跟一个爱斯基摩姑娘过活,生了个儿子Joshua。我对这个家也并非一无是处,我不吝惜钱,也肯竭心支持。实际上,当时塞尔登已经不爱莉莉了,我的插足刚好让他解脱。昨天他跟我说,我虽然不请自来,但也给了孩子们更好的生活。哪天我走了,一切都会留给孩子。三十三年了,我对莉莉的爱一如往昔。
这日记,后来莉莉读到了,在下面激动地写道:“亲爱的,亲爱的埃里克!永远最爱的。”
莉莉小霍弗十八岁,但这丝毫没影响她与霍弗的感情。《埃里克·霍弗:美国奥德赛》提到了莉莉,没点明两人的关系,但讲了个饶有兴致的细节。霍弗爱看电影,特别是日本武侠片(想来是黑泽明之类),常带莉莉和小埃里克去影院。一次,他跟莉莉去看电影,看着看着,突然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句:“座位怎么这么热?!”莉莉一看,他的雪茄把座位的垫子点着了,正冒烟呢。她赶紧把自己的座位让给霍弗,跑到后台要了桶水,把火浇灭,再回来坐在湿漉漉的垫子上继续看电影。霍弗呢?抱怨完后就只顾看电影,爷们的头也没抬。由此可见,两人的相处模式,主要是莉莉照料霍弗,照料得“甜蜜蜜”。
霍弗自杀过三四次,都没死成,活到八十多岁,住进医院,跟医生感叹:“干吗浪费时间弄活我呢,让我死了算了。”对方说:“或许上天有它的目的。”霍弗回答:“我不相信目的。人生没有目的。纯粹偶然而已。”这时,轮流到医院照料他的,没别人,只有塞尔登与莉莉,都六十多岁,风烛残年了。一天晚上,塞尔登陪床,霍弗突然醒来,要上厕所,塞尔登起身去扶,又怕他跌倒,自己也身孱体弱,可支持不住。还好,霍弗安全回了床,沉沉睡去。塞尔登也跟着睡了,一两个小时后,他醒来,发现霍弗已经停止了呼吸,默默走了,跟谁都没道别。
二○一四年五月十九日一稿
二○一六年二月十八日五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