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心有戚戚焉”
2016-04-14钱理群
钱理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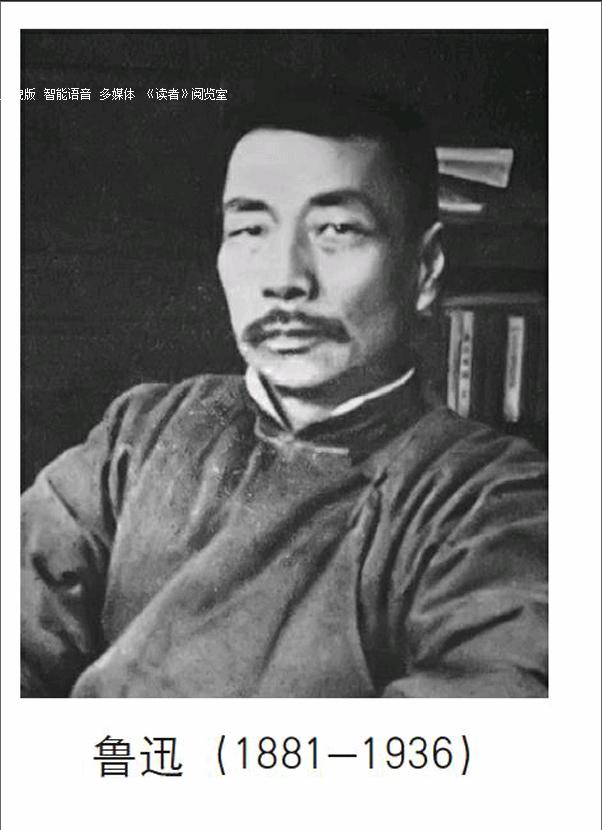
二○一五年十二月外出半个月,月底回到所住的泰康之家,桌上放着一部文稿,是我不在时一位中年人专程送来,并附了一封信。写信人自称“打工者”(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九九○年来北京的,一直在北大附近的中关村一带漂泊,现在全家人都在为硅谷电脑城一位老板打工),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又为精神的苦闷不能自拔,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了鲁迅,立刻被吸引,并沉迷其中,而且有了自己的体悟。心有所感,不得不发,于是就有了这本书。我打开一看,书名“我们还需要鲁迅吗?”,心怦然一动:这也是我一直在追问的问题,还专门写了文章(李国栋的书里也曾提及)。看看这位“打工者”如何回答吧。刚看一两章,就被抓住、镇住了,而且引发了许多的回忆和联想。
四十多年前,我也写过这样一本书,题目是“向鲁迅学习”,是手写的,请朋友代为装订成册,那时还没有条件像李国栋这样打印成书。那是“文革”后期,我在贵州山区的一所师范学校教书,三十多岁,正是今天的李国栋这样的年龄。一九九六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当时的情景:“也许是出于教师的职业习惯,喜欢和年轻人来往。于是聚集起了一批人。有工人、知青,也有少数在校学生。我们当时的个人处境都不太好,但忧心忡忡的,却是国家的命运,以及世界发展的前途,我们最热衷讨论的题目是:‘中国向何处去与‘世界向何处去。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问题,逼着我们去思考,去探索。我们内心有太多的痛苦,要寻求可以向他倾诉的朋友和导师。于是,我们找到了鲁迅。”记得差不多每次聚会,都要读鲁迅作品,一般是由我先讲,然后自由讨论。我自己更是每天读到深夜,写下了许多笔记。这样的讲稿与笔记积累多了,就编成了一本《向鲁迅学习》。当然无处发表,多次想寄给大学的老师、研究鲁迅的专家看看,却又顾虑重重,既有自卑心理,不敢打扰专家学者,又自知自己的思想有点异端,怕惹出麻烦。最后献给了老伴,算是找到了最好的去处。
我的回忆文章最后说:“鲁迅,正是在那个不寻常的岁月里,在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中国年轻一代)处于空前的迷茫、饥渴的时代,走进了我们心中,并和这一代人的生命融为一体了。”“文革”结束以后,我终于有了机会通过读研究生成了鲁迅研究者,圆了自己的梦。“尽管人们把我叫作‘教授‘专家,但我却一直以‘精神流浪汉自居”,“因为我与鲁迅的关系,绝不是学院里的教授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那样的冷漠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纯客观的)关系,而是两个永远的思想探索者之间的永无休止的生命的热烈拥抱、撞击,心灵的自由交流”(《知音在民间》,收《走进当代的鲁迅》)。这大概就是我与李国栋还没有见面,就“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原因:我们同是“精神流浪汉”,我们需要鲁迅,是因为精神的需要,内心的需要。
问题是: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还有没有精神需要?又是怎样的需要?
不错,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文革”后期贫困落后、危机重重的中国了。李国栋在他的书里也说:“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世界第二了,据说很快就要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看一看国民的餐桌、衣着和无限扩张的城市边际线,鳞次栉比的楼房,应该说,我们是富裕了。”当然,也还有贫困地区,但总体而言,全面奔小康,已经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了。
怎样看待这样一个日趋富裕与强大的中国,下一步中国应该向何处去?这是放在每一个关心中国发展和未来的人面前的问题。而且应该承认,不同的人群对问题的回答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民意的分裂,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在我们讨论的问题范围,与对鲁迅的认识有关的,在我看来,有两个方面的分歧。
首先是有人说,中国的日趋富裕和强大,就证明了中国现行制度正确,中国文化优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中国制度、道路、文化、发展模式普及推广,拯救危机重重的世界。当务之急是增强民族自信,讲好中国好故事。像鲁迅这样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国民性,起码是不合时宜,说严重点,就是扰乱人心,有碍稳定团结。这种观点在当下中国,是占主流地位的,这其实就是李国栋和许多人为之忧心忡忡的中学语文教育中鲁迅作品教学被竭力淡化的内在原因。李国栋深恶痛绝的那些以批判鲁迅为荣的学者、教授,不过是深深领悟了有人不便明说的意图。
其二,在认识甚至深感中国危机的人群中,对中国危机在哪里,如何解决中国危机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这也是本书第六章《制度与人》所讨论的问题。其实,前几年盛行一时、今天也还颇有市场的“捧胡(适)贬鲁(迅)”风里,提出的理由,就是胡适关注制度问题(主要是引入美国制度)就比鲁迅空谈批判国民性要深刻、重要得多。本来,强调制度的变革本身并不错,在当下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更具有极大的迫切性;问题是不能把某一具体制度绝对化,更不能以为只要建立了好的制度,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那就会进入误区。这就是本书作者一再强调的,制度是要人去执行的;这也是本书多次引述的鲁迅的观点:“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我也想补充一句鲁迅的话:“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华盖集·通讯》)。本书也谈到“贪官于今为烈,跟我们每一个人的送礼文化、行贿惯性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当下中国的官场腐败与全民腐败是相互影响、纠缠为一体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府的问题,也是国民的问题,政府是有一定民意基础,“代表”国民的。不解决甘于“做稳了奴隶”的国民奴性问题,就绝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即使有了,也会如鲁迅所说,“反而容易倒”。
在“制度与人”问题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我们几乎已经讲烂了却始终没有想清楚的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化”?这也是上一世纪初,也即一百多年前,鲁迅开始面对中国问题时所提出的,当时叫要建设怎样的“文明”?鲁迅在一九○七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里,反驳了几种文明观,即“以富有为文明”,“以矿路(科学技术)为文明”,“以众治(议会民主制)为文明”。在鲁迅看来,这几个方面,都是实现现代文明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根本;他提出:“根柢在人”,“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因此,在他看来,中国要成为现代文明国家,“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就是李国栋在本书里一再强调的,作为鲁迅思想核心的“立人思想”。他写这本书,就是要阐释鲁迅“立人思想”的当代意义。他最感忧虑的是,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仍然像当年鲁迅批评的那样,仅以物质富裕、科技发达和议会民主为中国改革,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严重忽略了人的问题,人的自觉、个性和精神问题。他对当今时代提出的富裕与强大的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的回答,是回到鲁迅的命题上来,“首在立人”,只有中国国民有了人的自觉,“立”起了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中国“人”,作为“人国”的中国,才有可能“屹然独见于天下”,要想依靠经济、科技、军事的实力“引领”世界,是一条行不通的危险的路。这就是他认为今日之中国“需要鲁迅”的最基本的原因,也是最引起我的共鸣,“于心有戚戚焉”之处。
而本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作者并没有将他这些内在理念和盘托出,而是隐藏在他对现实的中国精神问题的鞭辟入里的剖析之中,但也不忘在关键之处点题。这就充分发挥了他自己就是普通百姓,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优势。如他所说,就是“以小民的心,从小民的视角,看一看,想一想,鲁迅这位医生,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及精神的诊断准确否?我们身上那艳若桃花的红肿还在否?倘若按他开出的药方去治疗,能痊愈否?”而他这一看一想,就揭示了当今中国国民性、中国人空前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全民性的瞒和骗,人文精神的全面沦丧,社会空气的全面败坏,知识分子的全面堕落,以及全民性的腐败,全民性的“吃人”与“被吃”—真是惊心动魄!我之被“镇住”,即在于此:尽管我对这一切也都有所认识,但毕竟宅在书房里,实际状况接触不多,现在被身在其中的李国栋一一道来,一桩桩,一件件,活生生,血淋淋,让人浑身不自在。不由得又想起鲁迅那句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当今的中国,正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因此,我们今天特别需要鲁迅。看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或者说感觉到了这一点。鲁迅将永远是一个“现在进行式”(而非一些人希望的“过去式”)的存在。
因此,李国栋对当代中国国民性的观察与揭示,在鲁迅那里早就有了概括,这绝非偶然。这就是李国栋所说,鲁迅当年说的话,是有“预言性质”的,到“现在正纷纷变成现实”,“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像神仙一样,咋就算得那么准捏!”鲁迅话语的预言性,是由他的思维与话语方式决定的:他关注的也是现实生活里一桩桩、一件件具体的人和事,但他却能以其明锐深邃的眼光、广博深厚的知识,看到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的最深处、人性的最深处、国民性的最深处,将其揭示出来,概括为某种社会、思想的类型。从“这一个”看“这一类”,“这一个”是具体、现实的,“这一类”就能超越时空,预言未来。当然,也如鲁迅所说,他的言说的生命力,也反映了社会、思想的无进步:“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鲁迅说这正是他“所悲哀的”(《热风·题记》)。我们今天的读者,在引述鲁迅八九十年前的话批判现实时,又何尝没有这样的悲哀呢?
我感到吃惊的,还有李国栋对鲁迅著作的熟悉。他书中引述鲁迅的话,几乎是随手拈来,可见他已经将鲁迅的著作烂熟于心,甚至是融入生命中了。而他书中每一章后面附录的鲁迅生活里的人和事(这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大概是为了增强读者与鲁迅的亲和力吧),更是显示了作者对有关鲁迅史料的熟稔,其中有些细节是我都不知道的。在我看来,这也是李国栋的另一大优势。这样,既接地气,又熟悉鲁迅与之相通,在我看来,这就进入研究鲁迅的最佳状态了。
这再一次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鲁迅是属于大家的,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对鲁迅的阐释与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鲁迅的知音在民间”,或者说,“凡有思索的地方,就有鲁迅的知音”。“在中国,不仅有我们这些被承认的‘鲁迅研究专家,而且还有许多不被承认、没有得到表现机会的民间鲁迅专家。这两类专家当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互补,以至转化的。我自己,每当写作时,总是感到身后这些民间的专家的无言的存在,这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鼓舞,甚至是一种精神的支援。”(《知音在民间》)现在,我就从李国栋的这本《我们还需要鲁迅吗?》里,得到鼓舞和精神支援,而且我要说,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当代青年走近鲁迅,而且在鲁迅研究上,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一六年二月十九至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