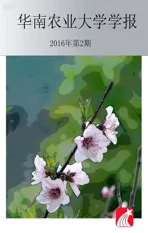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政府行为、农村经济与社会资本
2016-04-14潘海英窦俊贤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00江苏省世界水谷与水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南京200
潘海英,窦俊贤( .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00;2.江苏省“世界水谷”与水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南京200)
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政府行为、农村经济与社会资本
潘海英1,2,窦俊贤1
( 1.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1100;2.江苏省“世界水谷”与水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南京211100)
摘要:基于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16个核心城市的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和系统GMM估计方法的应用,分两阶段(以2006年为界限)检验了政府行为、农村经济、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2006年以前,中央政府政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增长的正向影响显著,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的作用不明显,但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方政府干预对农村正规金融结构优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的作用不显著。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政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的增长、结构的优化有正向影响,但对提升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的作用不明显;地方政府干预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的作用不显著。在整个研究期间,农村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诱致作用尚未显现,而社会资本和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之间也没有呈现出预期中的正向关系。
关键词:农村正规金融;政府行为;农村经济;社会资本
一、引言
随着2004年以来连续12个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三农”问题也成为各级政府的核心工作任务之一。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进行了重大战略部署,为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三农”问题的解决固然与政府涉农政策支持、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农业科技进步、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有关,同时也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中心,其作用本质上体现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终提高农民收入。2006年底银监会发布《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自由、开放的方向,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也得到了蓬勃发展。然而农村金融发展步伐还是显得缓慢,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尚处于非协调发展状态,特别是满足扶持性融资需求和产业化融资需求的程度仍然较低。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步伐,从哪些方面着手可以对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近年来,关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学术研究在不断拓展。现有文献较多地关注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1-5]、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区域差异[6-7],以及基于需求抑制论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需求[8-10]。部分文献基于供给抑制论对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变革和创新展开研究,主要涉及农村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以及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和创新[11-12]。另有一些文献侧重于农村金融发展中的政策支持研究[13-14]。
然而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于究竟是什么因素促进或影响了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功能的演变,仍少有涉及。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有待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基于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并结合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践,考察政府行为、农村经济、社会资本等因素与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关系,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应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以期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与中央政府政策、地方政府干预、农村经济增长和结构以及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探索具有适用性的区域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对策。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借鉴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并结合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实际情况,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各级政府行为、农村经济、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影响机理。
(一)中央政府政策因素分析
近4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趋于弱化,市场的作用逐渐增强,但是由于农村金融的弱质性,以及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中央政府在农村金融领域的主导作用并未发生改变。中央政府往往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意见为农村金融发展营造制度环境,明确其发展路径,甚至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多元化改革也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引。那么中央政府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具体起到怎样的作用?金融深化论观点认为,中央政府的过分干预限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金融活动的自由化,导致金融体制落后,应实行金融深化[15]。这也是目前得到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金融约束论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中中央政府干预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在政策性金融、民间金融发展方面,政府在促进金融体系的完善和稳定金融秩序方面有重要作用[16]。政府行为转变论观点认为,随着市场机制的确立和完善,中央政府应逐渐退出金融领域,由市场机制来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17]。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在引导并促进农村金融体系完善方面有积极作用,但也必然会抑制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中央政府政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有多重作用,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的增长、结构的优化有正向影响,但对效率的提升有负向影响。
(二)地方政府干预因素分析
1994年我国实行财政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作为分权制下一级独立且拥有财权和事权的机构,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并拥有相对独立的利益。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必然会向中央政府和金融部门施加其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控制力以谋求更多的金融资源[18]。与中央政府相比,在金融约束和市场增进方面,地方政府具有比较优势,并且有充足的动力实施更有效的金融约束政策和市场增进制度。尤其是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和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特征,决定了地方政府在金融制度变迁和金融市场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来说地方政府主要发挥了“中间扩散型金融制度变迁”主导者和“信用中介”的作用。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易带来金融风险的集聚、金融效率的损失[19]。周业安[20]认为在转型经济中,地方政府行为的不同特征将对金融发展产生不同的效应。他将地方政府行为划分为进取型、保护型和掠夺型3种,认为一个进取型的地方政府将能促进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一个保护型或掠夺型的地方政府将可能反过来损害这种增长效应。借鉴这一观点并应用到农村金融领域,对于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中地方政府干预这一影响因素,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1:保护或掠夺型政府干预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结构有负向影响;
假说2-2:进取型政府干预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结构有正向影响。
(三)农村经济发展因素分析
追溯金融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需求催生了金融发展,“完美”的金融秩序的形成得益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断试错——“运用自生自发秩序的有序化力量,我们有可能达成一种由极为复杂的事实构成的秩序,而它的这种复杂程度则是我们通过刻意安排所无力企及的。”[21]。而当代金融发展理论领域的著名学者Patrick[22]早在1966年指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和最优顺序。在经济发展初期,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后,经济结构的优化将诱致金融发展。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农村地区。在农村经济发展初期,农村经济增长离不开农村金融发展[23-24];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要通过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才能实现其持续发展。在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无论是传统农业的产业化发展,还是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壮大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也必然涉及到实物资源、人力资源、技术创新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优化。然而对资源的重新投入或重新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终都将归结为资本要素的供给。由此,农村经济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的发展将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就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影响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影响不明显;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存在正向作用,即农村经济越发达,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越好。
(四)社会资本因素分析
尽管金融发展内生于经济发展,但金融并不是经济的附属物,而是经济领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布罗代尔[25]指出更加严格的条件是实现金融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只有当商品交易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作为交易活动高级形式的金融交易才会出现。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农村金融发展不仅受到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包括社会资本、初始禀赋、文化、宗教等在内的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其中,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生活所具有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特性,它们能使参与者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有效地完成工作。社会资本具体表现为相互信任、公民心、互惠互利、社会关系等方面[26]。Durlauf和Fafchamps[27]将社会资本的核心特征总结为信息共享、群体认同和团队合作。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有助于提高金融交易效率,进而促进金融发展[28]。Guiso等[29]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信任促进金融发展,社会资本是决定社会信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由于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社会网络将为惩治不遵守社会规范的个人提供完善的条件,因此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度较高[30]。张维迎等[31]研究认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信任度不同”的影响。具体到农村金融领域,本文认为社会资本因素是影响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之一,并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说:
假说4: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有正向影响。
三、变量设定、研究模型和计量方法
(一)变量设定
对于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这一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King和Levine[32]的观点,选用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指标、效率指标和结构指标来衡量。具体来说,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 RFIR)选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生产总值( RGDP)①对于RGDP,国内并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本文借鉴曹协和[33]的做法,采用农林牧渔总产值来表示RGDP。之比来表示;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 RFDE)采用贷存比,即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存款余额之比表示;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 RFDS)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村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农村贷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
解释变量中,中央政府行为( CGOV)以体现各地区农业重要程度的农业增加值比重这一指标来度量,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政策性金融投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等方面;地方政府行为( RGOV)以地方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度量;农村经济增长( RPINC)以农民人均纯收入来度量,这主要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农民收入,且农民收入包括了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等更多内容;农村经济结构( RSTRU)采用农村第三产业GDP占RGDP的比重来度量,这是由于农村第三产业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参照Temple和Johnson[34]、Ishise和Sawada[35]、严成樑[36]的主张,社会资本( SCAP)以人均电话数量,即经济中总的电话数(包括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与总人口的比值来度量,从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的角度反映社会资本水平。
在本文的研究中,为尽可能控制其他因素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影响,另外加入一组控制变量,主要有农村经济市场化( RMAR,以农产品商品率,即农产品出售量与农产品总产量之比来表示)、农村城镇化率( RURB,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DSTRU,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表示)。
(二)数据获取和处理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16个核心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1998—2013年期间各城市构成的面板数据来检验前文关于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若干假说。根据以上各个变量的设定,本文研究所涉及16个核心城市的农村经济、农村金融、财政支出、非农人口、总人口、电话数等基础数据主要从各个城市历年的《统计年鉴》,以及相应年份的《浙江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收集并整理得到。农村GDP、农村第三产业GDP的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农产品出售量、农产品总产量的数据收集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相应省份和城市的《统计年鉴》。
对于农村经济类基础数据,为减少物价波动对其产生的影响,使得此类数据在时间上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历年各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人均纯收入指数,分别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进行平减处理(以1998年为基年)。基于收集到的基础数据,并利用相应的关系式可以计算得到各变量值。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研究模型和计量方法
由于当期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结构通常会对下一期的对应值产生动态连续影响,故本文建立的研究模型包含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动态项。同时,考虑到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结构之间可能存在交互影响,在研究模型中又引入了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结构滞后一期的交乘项。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 1)、( 2)、( 3)中,i表示长三角区域16个核心城市; RFIRit和RFIRi,t-1、RFDEit和RFDEi,t-1、RFDSit和RFDSi,t-1分别表示各城市在第t年和第t-1年的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结构; X为一组解释变量,代表影响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CGOV、RGOV、LN( RPINC)、RSTRU、SCAP等变量; Y为一组影响稳定状态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RMAR、RURB、DSTRU; C为常数项;ε、e、v为随机扰动项,表示不可观测效应。
由于包含了被解释变量RFIR、RFDE、RFDS的滞后项,模型( 1)、( 2)、( 3)实际上是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容易产生3个问题:一是因被解释变量受其滞后一期值影响而产生的自相关问题;二是因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值与随机扰动项存在相关性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三是由于各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也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产生的联立内生性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借鉴被广泛采用的系统广义矩估计( GMM)方法来对模型( 1)、( 2)、( 3)进行估计。系统GMM的基本原理是将模型( 1)、( 2)、( 3)视为水平回归方程,再将这3个水平回归方程和其差分方程相结合来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其主要利用内生变量本身的水平值和差分值作为工具变量,而不需要增加其他外生工具变量来克服内生性问题。在具体估计中,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为内生变量的滞后两阶水平值,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为差分滞后项。
具体来说,由于模型( 1)、( 2)、( 3)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交叉项,其内生性问题无法避免,因此将其设为内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的农村经济增长、农村经济结构与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之间也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这是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制约,农村金融主要通过资金配置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产生影响,进而对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此外,与农村相关的3个控制变量同样容易受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反馈影响。因此,在运用xtdpdsys命令进行动态回归时,本文将LN( PRINC)、RSTRU、RMAR、RURB、DSTRU也设为内生变量。为了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于“所有工具变量有效”这一原假设下的Sargan检验来完成过度识别检验。如果无法拒绝原假设就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另外,本文使用AR( 2)检验判断差分方程的残差是否存在二阶自相关,其原假设为“扰动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如果无法拒绝原假设就意味着估计是有效的。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具体研究中,考虑到2006年《意见》的发布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自此农村金融发展较以往明显提速。基于这一背景,我们以2006年为界限将样本划分为两组,即早期样本组( 1998—2005年)和近期样本组( 2006—2013年)。对早期组、近期组分别运用系统GMM于模型( 1)、( 2)、( 3),以检验各因素对长三角地区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2。表2中各个模型的AR( 2)检验值、Sargan检验值表明扰动项的差分均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工具变量在整体上是有效的。
根据估计结果,发现除了模型( 3)近期组,模型( 1)、( 2)和模型( 3)早期组中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变量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整个研究期间长三角地区当期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会受到前期对应值的显著正向影响,但自2006年以来,该地区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受前期对应值的正向影响趋于不显著。总体来说,长三角地区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其次,长三角地区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结构之间存在交互影响。具体来说,2006年以前前期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对当期对应值的影响分别随前期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的优化、规模的增长而显著增强;而2006年以后前期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对当期的对应值影响分别随前期的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提升而明显增强,随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增长而明显减弱。进一步分析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一)中央政府政策因素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增长、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带来不同影响
估计结果基本上支持假说1。模型( 1)两个组别中,CGOV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5%检验水平上显著,说明中央政府政策对于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的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 3)早期组中,CGOV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在近期组其系数也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这一结果间接表明2006年以来农村其他金融机构在农村信贷市场上的贷款余额持续增长,且其重要性日益显现,即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趋于优化。模型( 2)两个组别中变量CGOV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但以2006年为界该系数由显著转化为不显著,可见中央政府政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存在负向作用但已经趋于减弱。对于这一结果,主要原因在于本文所选择的长三角地区有其特殊性。自从《意见》实施以来,长三角地区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纷纷设立且发展迅速。例如截至2012年11月底,江苏省共有村镇银行近60家,农村小额贷款公司近500家,农民资金互助社超过300家。这些新型的金融机构和部门在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网点覆盖率、解决农村金融市场垄断导致的低效率问题、发挥支农作用等方面都有不凡的表现,但在本文中没有得到真实反映。因此,在长三角地区农村金融机构趋于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今后应继续关注中央政府政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的作用及其检验问题,特别是在研究中不应局限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有必要结合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多维度分析,关键是要突破研究数据缺乏的制约。

表2 长三角地区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系统GMM估计结果
(二)地方政府行为因素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具有负向影响
研究结果支持假说2-1成立。在模型( 1)早期组、( 2)早期组中,解释变量RGOV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不显著,而在模型( 1)近期组、( 2)近期组其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2006年以来地方政府行为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不具有促进作用,或者说地方政府干预不利于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的增长和效率的提升。模型( 3)中RGOV在早期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在近期组有不显著的负系数,说明2006年以前地方政府行为严重阻碍了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的优化,但随着中央政府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进,2006年以来这种负面作用趋于不明显。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从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作用来看,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扮演的是保护和掠夺型政府的角色,存在通过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干预来获取金融资源、发展地方经济的内在动力。然而,该地区地方政府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金融风险的集聚,同时阻碍了农村金融市场整体功能的发挥,制约了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空间。
(三)农村经济发展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不明显
研究结果基本能证实假说3成立。从解释变量LN( RPINC)来看,根据模型( 2)的结果可知,其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在早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近期影响不明显;由模型( 1)、( 3)的结果可知,其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结构的影响不明显。从解释变量RSTRU来看,其在模型( 1)早期组、( 2)早期组中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表明2006年以前农村经济结构的改善不能有效促进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的增长和效率的提升;而在模型( 3)近期组中,RSTRU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2006年以来农村经济结构的改善有助于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的优化;根据模型( 1)近期组、( 2)近期组、( 3)早期组的结果,我们发现农村经济结构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结构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正向作用尚未显现。其结果与长三角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有一定的关联。尽管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第一大经济区,但其农村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到高级的过渡阶段。从统计数据来看,2013年长三角地区16个核心城市的人均GDP均值为13749美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与挪威、新加坡、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值为2948美元,较之美国接近4万美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巨大。因此相对于发达国家,长三角地区农村经济还没有发展到高级阶段,这可能使得农村经济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诱致作用不明显。
(四)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研究结果无法支持假说4成立。根据模型( 1)早期组、( 3)近期组的结果可知,社会资本对2006年以前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2006年以来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在模型( 1)近期组、( 3)早期组和模型( 2)两个组别中该变量系数均不显著。这一结果显然与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有正向影响的假说不吻合。产生这种偏差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与其他资源一样,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需要投入资本。建立社会资本需要大量投资,在维系与他人关系方面,昂贵的投资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超过成本。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在构建和维系社会资本的过程中,所投入时间、资金成本会使交易费用增加,因此现实中社会资本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不一定会产生促进作用。第二,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农村电话普及率持续走高,农村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部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开通了手机银行业务,这不仅给农户带来了方便,也改善了农村地区银行网点不足、金融服务供不应求的状况。然而,由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手机银行还处于初始运行阶段,再加上智能手机在农村的普及率较低以及很多农户还未改变传统的支付方式,这使得在长三角地区用来度量社会资本的人均电话数量与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处于不协调状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地区16个核心城市为研究对象,应用系统GMM估计方法研究各因素对该地区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自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农村金融改革政策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农村正规金融发展规模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效率的负向影响逐渐趋于不明显;地方政府干预阻碍了农村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尤其在规模、效率方面,扮演的是保护或掠夺型的政府角色。尽管整个研究期间( 1998—2013年)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农村经济结构趋于优化,但与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正向关系并不明显;同时,社会资本并没有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但考虑到社会资本内涵的宽泛性,以及国内社会资本整体水平较低等因素,尚不能认为两者之间一定不存在正向关系。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更好地推动长三角地区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具体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国家应继续深化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在金融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度降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引导更多资本参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建立良性竞争且富有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第二,地方政府向进取型政府转型。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资源的利用,约束地方政府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干预。在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方面,建立连续绩效考核制度,完善绩效考核系统。第三,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依靠科技进步进行技术创新,大力推广优质、高产经济作物,逐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利用产品加工业的优势生产条件,实现产品附加值;大力拓展高新技术产业,完善现代农村服务性行业。同时,继续提高第二、三产业在农村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第四,促进社会资本整体水平提高。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强消费能力,转变消费观念。重视并加大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投资力度,降低沟通费用,为增进农村居民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奠定良好基础,鼓励人们重视对社会资本的积累。
参考文献:
[1]HOWARD J,JONES M,MARYLIN,WILLIAMS,ESSE NILSON,YASHWANT THORAT.Training to Address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of Rural Bank Managers in Madhya Pradesh,India: A Programmer to Facilitate Financial Inclus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7,19( 6) : 841-851.
[2]JOELI VEITAYAKI.Improving Access to Finance for India's Rural Poor-By Priya Basu[J].Natural Resources Forum,2008,32( 3) : 258-259.
[3]PAN S W,RODERICK M,HE X R.Does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Development Increase Per Capita Income in Rural China?[J].China&World Economy,2009,17( 4) : 72-87.
[4]谢琼,方爱国,王雅鹏.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了吗?[J].经济评论,2009,( 3) : 61-68.
[5]赵洪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1978—200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家,2011,( 11) : 58-63.
[6]高沛星,王修华.我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 4) : 93-102.
[7]黎翠梅,曹建珍.中国农村金融效率区域差异的动态分析与综合评价[J].农业技术经济,2012,( 3) : 4-12.
[8]田秀娟.我国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选择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9,( 7) : 146-160.
[9]黎红梅,熊紫薇.农户生产性融资需求满足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南省环洞庭湖地区为例[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1) : 62-65.
[10]于丽红,陈晋丽,兰庆高.农户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需求意愿分析——基于辽宁省385个农户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4,( 3) : 5-11.
[11]钱水土,陆会.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农户融资行为研究——基于温州农村地区的调查分析[J].金融研究,2008,( 10) : 174-186.
[12]唐礼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9,( 4) : 76-79.
[13]黄维健,王春播,屈霞.对构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支持政策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9,( 8) : 54-58.
[14]温涛,董文杰.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总体效应与时空差异——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1,( 1) : 24-33.
[15]冯涛,崔光庆.我国金融风险与政府投资行为:理论与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7,( 10) : 31-40.
[16]鲁靖,蔡则祥.金融支持弱势群体的外部效应与制度安排[J].财贸经济,2008,( 12) : 67-70.
[17]段国蕊,臧旭恒.中国式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资本深化——基于区域制造业部门的理论和经验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3,( 6) : 3-10.
[18]崔光庆,王景武.中国区域金融差异与政府行为:理论与经验解释[J].金融研究,2009,( 6) : 79-89.
[19]张璟,沈坤荣.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J].江苏社会科学,2008,( 3) : 56-62.
[20]周业安,赵晓男.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研究[J].管理世界,2002,( 12) : 52-61.
[21]冯·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124.
[22]PATRICK H 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 4) : 174-189.
[23]王修华,邱兆祥.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 2) : 71-75.
[24]吕勇斌,赵培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反贫困绩效:基于2003—2010年的经验证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4,( 1) : 54-60.
[25]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上海:三联书店,1993: 48.
[26]PUTNAM R.Mar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167.
[27]AGHION P,DURLAUF S.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ume 1B[M].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Ltd,2005: 1639-1699.
[28]KNACK S,KEEFER P.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ut?: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6,112( 4) : 1251-1288.
[29]GUISO L,SAPIENZA P,ZINGALES L.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 3) : 526-556.
[30]COLEMAN J.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94( 1) : 95 -100.
[31]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 10) : 59-70.
[32]KING R G,LEVINE R.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 3) : 717-737.
[33]曹协和.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 11) : 49-54.
[34]TEMPLE J,JOHNSON P.Social Cap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113 ( 2) : 967-990.
[35]ISHISE H,SAWADA Y.Aggregate Returns to Social Capital: Estimates Based on the Augmented-Solow Model[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09,31( 3) : 376-393.
[36]严成樑.社会资本、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2,( 11) : 48-60.
A Study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PAN Hai-ying1,2,DOU Jun-xian1
( 1.School of Business,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2.Jiangsu Provinc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World Water Valley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16 core cities from 1998 to 2013,using the estimation of system GMM,this paper studied the impacts of government behavior,rural economy and social capital on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i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scale and their role in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structure is unapparent before 2006.But their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s negative.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structure before 2006.But their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scale and efficiency is unapparent.Central government polici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scale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since 2006.But their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s unapparent.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scale and efficiency since 2006.But their role in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structure is insignificant.R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structure optimization haven’t appeared the inductivity effect on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rural form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doesn’t exist positive relationship as we anticipated.
Key Words:rural formal finance; government behavior; rural economy; social capital
作者简介:潘海英( 1970—),女,浙江台州人,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发展和现代金融管理。E-mail: hypan@ hhu.edu.cn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1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5BJY05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2015B28314)
收稿日期:2015-11-12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6.02.002
中图分类号:F830.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 2016) 02-0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