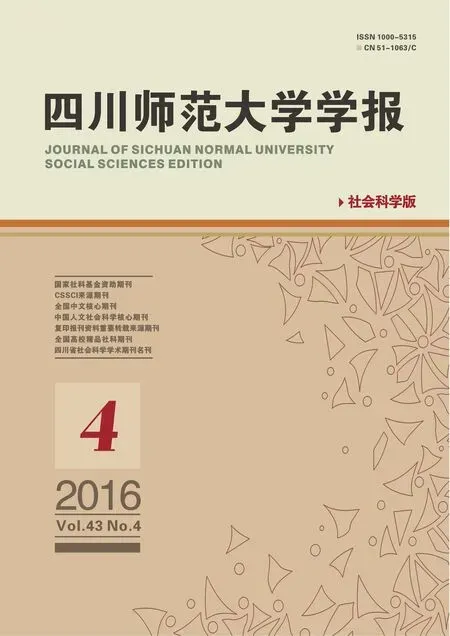批判性阐释与多维度运用
——托尼·贝内特的符号学方法及其实践
2016-04-13张碧
张 碧
(西北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27)
批判性阐释与多维度运用
——托尼·贝内特的符号学方法及其实践
张碧
(西北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27)
摘要: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托尼·贝内特对索绪尔符号学传统进行了批判性检审与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观进行了符号学维度的阐释,并将符号学运用至一系列文学及文化批评实践之中,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文化研究领域内的具体批评途径。
关键词:托尼·贝内特;符号学方法;符号学实践
作为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托尼·贝内特以其一系列理论表述及文化实践而蜚声国内外学界。贝内特十分注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上,将诸多西方批评方法融合于文学及文化批评实践中,并在其独到的符号学观基础上,亦使对符号学方法的运用成为其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践的重要维度。
一索绪尔符号学传统的再阐释
众所周知,由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突破,在当代欧陆学界,由结构语言学始祖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业已失去往昔在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辉煌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符号学支系在英语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至今仍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上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其中,贝内特曾提出以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符号学加以整合,消解两者间作为文化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矛盾性,从而表达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肯定态度[1]xi-xviii。然而,贝内特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使其能够以审慎的态度看待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的理论价值。
美国学者霍克斯援引瑞士学者皮亚杰的“生成性结构主义”观点,强调“结构”的内部调整功能属性,使其具备动态性自我建构性品质[2]6。同时,由于索绪尔的“语言”(langue)一般被视为共时性封闭形而上学整体,因此学界很少将结构的自我调节特性运用于对索绪尔“语言”概念的理解。
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贝内特指出,“语言”能够通过内部调整转化,使其派生形式“言语”,在淘汰过时的语言因素的同时,得以产生出全新的语言因素。在这一基础上,贝内特借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社群内部语言的具体形成机制展开讨论:“词汇应当……在说话人和受话人间所形成的对话性关系(dialogic relationships)中得到把握。”[3]84也就是说,人类在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交际过程中,不断检审和筛选着彼此话语中不利于交际、合作活动的言说方式,同时使有利于交际活动的言说方式得以保留和确立。因此,“语言”的更新活动,从本质上源于社会生产活动中为适应新的交际形式而形成的全新社会生产关系。由此观之,由于索绪尔忽视了“属于不同社群的诸多说话人,为其语言在社群内的正常运作赋予了一系列迥然相异的原则”[3]79的事实,因此未能意识到“语言”的“自我调整”特征恰是社会成员在生产活动中调整语言表意功能的体现。
同时,贝内特在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批判基础上,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同样进行了历史主义维度的审视。由于极大地秉承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共时性认识,俄国形式主义长期被视为对索绪尔传统的延续。客观地讲,俄国形式主义在接受索绪尔共时性研究方式之初,对这种认识维度是持审慎态度的,这从蒂尼亚诺夫与雅各布森对共时性系统的历时性阐释方式即可窥一斑[4]79-80。然而,俄国形式主义在批评实践中对文学内部结构的过分重视,却印证了结构语言学对其具有的实际影响。诚如美国学者詹姆逊所言:俄国形式主义在“将固有属性自身剥取出来”[5]43的方法论方面与索绪尔语言学异曲同工。霍克斯更是提出,“(形式主义者)与那些‘结构’语言学家,……以及此后的‘结构’人类学家,在彼此致力的工作方面,其共性十分明显”[2]45。
形式主义的重要代表什克洛夫斯基在提出文学的“陌生化”原则的同时,将陌生化视为文学形式的演变力量,亦即将文学审美经验层面的“陌生化”效应视为文学形式更迭的动力,从而使其对文学形式发展动力的认知脱离了社会历史视野,亦使其陷入共时性的形而上学化阐释方式中。
巴赫金在对索绪尔语言学的批判中,从社会历史角度评析了“语言”的形成过程,也便否定了共时性“语言”的存在可能性:“无论在怎样的历史片段中,共时性的语言系统也无法出现。”[6]66同时,巴赫金对索绪尔传统的否定,为贝内特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角度认识语言问题扫清了认识与方法障碍。互文性由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指文本之间的影响与生产关系,同时还具备以下特征:后文本往往能够对前文本所在意识形态语境及形式特征进行不同程度的复制。贝内特指出,推动文学形式演变的动力,并不基于“陌生化”的抽象替代;新文本的出现,是伴随着历史社会的变动,不同意识形态在争夺文学语言符号的过程中经由排斥、融合之后所产生的互文性产物,“文学性(literariness)……决定于在统治性意识形态域的母体(martrice)里、为文本所确立的诸多属性的位置。文学性并不在文本里获得体现,而是体现在镌刻于文本之中、文本之间的诸多互文性关系内”[3]63。换言之,文学形式的变更并非基于审美效应的更迭,而是由于文本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交流,导致文本自身在形式上发生的碰撞与融合。贝内特由此将对文学形式的演变的阐释引向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维度,使其摆脱了原有的形而上学阐释方式。
二话语抑或实存:“历史”的符号学分析
历史主义批评在西方文学批评传统中始终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常被理所当然地归入这一批评支系。然而,随着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批评观念的兴起,“历史”的本质内涵在西方人文社会学界饱受争议,而其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合法性亦引起广泛探讨。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经典论述,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被广泛置换为历史/文学这一相应范畴。然而,“历史”这一概念的意涵含混性却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陷入合法性危机中。以新历史主义为代表的诸多西方批评流派认为,历史至少应包括“历史事实”与“历史陈述”两种形态,前者指涉历史现实中不能够被人的主观意志所改变的实存事实,后者指在对前者进行叙述化后形成的话语符号。事实上,即便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这种对“历史”的二元划分同样存在,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沙夫在对语言符号与现实的关系模式进行总结后[7]183,提出历史既是一种“客观性事件”[8]183,同时其形成也必须受认知主体的主观意识的某种影响[8]191。显然,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基础”的规定属于前一范畴。然而,当基础被以“历史”名义置换入文学批评领域中时,“历史”的后一种含义便往往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须面对“基础是否只是一种话语符号”的方法合理性问题。
在贝内特看来,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中,伊格尔顿对历史的错误论述,便是由于对“历史”的含混界定而引发的阐释困境的体现之一。伊格尔顿认为,包蕴着特定意识形态的历史话语决定了文学作品的生产方式,亦即为文本的意义生成提供了具体产生语境;同时,文学文本在被完成后,具备了指涉现实中历史事实的功能,“戏剧性生产(dramatic production)由特定历史决定,是其产物;……它同时还使文本在其内部建立起与自己的客体的关系”[9]67。这样,历史便既是文学意义得以生成的话语基础,同时也成为文学能够对之加以还原的客体。对此,贝内特从符号学角度指明了伊格尔顿对“历史”概念的混淆,认为其将分别作为“能指”与“所指”的“历史”——亦即为文本提供意义语境的历史符号,与作为历史实存的指称物(referent)的“历史”混为一谈:“伊格尔顿谈及作为文学所指的历史时,他心中一定考虑到不只一个层面的意义……但他谈及作为文学起源和指称物时的历史时,他却在话语的‘超出话语的开端’的意义上,使用了该术语的其他意义。”[10]42事实上,由于历史事实必须通过历史叙述——亦即作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物的话语符号作为基本载体,因此指涉历史实存的指称物在历史叙述的建构过程中似乎总是缺失的,原因在于“似乎发挥指称物功能的文献记载及原始材料等,和我们说的指称物的指称物(真正的过去状态)间,横亘着一条难以弥合的天堑”[10]56-57。如果进一步从解构主义角度来审视历史,历史会被视为纯粹建立于缺乏历史的物质性根基的话语符号的基础上,也由此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构成极大的威胁。恰如美国学者柏格森所言:“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被重新命名为‘话语结构’,由此体现出一种清晰的符号学假想:集体属性的本质在于话语,而非历史性社会关系。”[11]14那么,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如何界定其历史基础的实存性、物质性?换言之,如何以指称物的物质属性来夯实作为话语符号的历史表述的基石?由此,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历史的物质性基础的证明便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
贝内特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质出发对这一问题予以了解决。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强调理论在掌握群众之后所具有的物质性力量。贝内特对这一论断加以延伸,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类历史进程及社会革新具有的预见性和指导性,使得社会运动得以沿循历史规律而获得发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预设的历史叙述,能够对无产阶级民众进行指导、组织,也使其摆脱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并在相应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下投入到社会活动之中。因此,体现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中的历史观,尽管以话语符号形式出现,却由于具有改变社会进程物质属性的理论力量,从而与指涉历史实存的指称物关联起来。
然而,贝内特并没有阐释以下问题,即作为话语符号的马克思历史叙述在其建构之初,是如何与作为指称物的历史实存产生关联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早年曾从事诸多社会实践工作,尤其是任职于《莱茵报》的经历,使其通过对一系列社会具体事件的接触和认识,为其此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打下基础。同时,马克思曾提出以客体的物质属性作为对其加以认知的基准[12]276-281,从而在事实上从符号学指称物的角度强调了符号的物质属性、实存性所具有的基本重要性[13]171-172。在这一基础上,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德拉-沃尔佩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恰是建立在通过对具体、客观历史事件的总结归纳之上,呈现出从“具体”到“抽象”的符号化理论建构逻辑[14]200。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符号,正是建立在对作为指称物的历史事件的分析与思考的基础上的。
三超越索绪尔:大众文学研究中的阅读构架理论
贝内特除对索绪尔符号学传统本身的审视中,表达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有别于学界一般认识的阐发观念,同时还将这种独到阐发体现于对索绪尔符号学的具体运用中,其中即包括贝内特的“阅读构架”理论。
“阅读构架”(reading formation)在贝内特的界定中,意指在特定社会群体某种集体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文本所形成的统一性阐释范式或话语表达方式。在阅读构架的作用下,该群体成员能够对同一文本采取基本一致的阐释维度。受过特定学术批评训练的批评家,往往能够在统一性学术思维的规范下形成相对一致的批评方式,亦即形成统一性阅读构架。因此,研究者往往能够通过对文本结构的剖析而发掘出该批评家群体的阅读框架。然而,伯明翰学派在其大众文化研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对于大众小说而言,应如何确定其庞大、零散而未经学术训练(untutored)的读者群体的阅读构架?
贝内特从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元模式来理解文本结构/大众读者阅读构架的对立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贝内特此处对索绪尔的“言语”进行了灵活处理:“言语”意指说话者富有个性化的具体言说方式,贝内特从具有非统一性特质的言语角度来理解具有统一性特征的阅读构架,显然认识到了阅读构架在具体话语表述方式上的自由特质。因此,言语与阅读构架的相似性仅体现在话语的表达方式层面,而非阅读构架的统一性阐释倾向方面。
在这种基础上,贝内特提出通过文本结构来探究阅读构架,从而在符号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索绪尔进行超越。尽管索绪尔提出,作为人类语言能力集合的“语言”——而非作为具体个性话语的零散“言语”,是语言学真正能够加以有效研究的对象,但由于“语言”的先验悬设性质,索绪尔对“语言”的探讨实际仍旧是建立在对具体言语的归纳与分析总结的基础上。与之类似,结构人类学代表列维-斯特劳斯对部族“血亲结构”的形而上学探讨,同样体现于对诸多具体部族组织格局的归纳之中。因此,结构主义实际上是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来印证其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从而呈现出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间的矛盾与断裂。
然而,索绪尔及其追随者的这种矛盾性理解,客观上为贝内特从辩证的角度理解“语言”和言语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言语离不开语言的规范体系以免使自身因具有创造性而过于偏离语言规范;反之,语言同样离不开具有创造性特征的言语,以免使构成它的规则性体系彻底僵化”[15]221。因此,在对待文本结构和阅读构架的关系时,应当根据文本结构自身以确定其可能具有的阐释范式,亦即通过对文本结构“内在符码”(fixed code)的解读,重构出文本的基本意义结构。事实上,贝内特这种方法构想的合理性,已得到当代叙述学的佐证:通过对文本,尤其是大众文学文本的阅读,往往能够确定其基本审美、伦理倾向,亦即确定其隐含作者,并据此推断出隐含读者,或曰文本的基本意义结构。
难点在于,读者群体往往因其社会阶层背景的不同而对文本采取差异性阐释,亦即对文本基本意义的解码采取“过度阐释”、“弱阐释”等偏离其原初内涵的不同解码方式,使得阅读架构因其阶层属性背景的差异而呈现出极为混杂而矛盾的状况,一如巴赫金所言,语言体系是阶级斗争的场域[6]23。贝内特据此提出,必须在检审读者所处特定阶级背景的前提下,结合具体社会语境来分析读者的话语阐释策略,“个人言说(speech)活动,亦即言语事件(events of parole)……绝非对语言(langue)加以个性化、主观化使用的产物,而是产生于以不同阶级为基础(class-based)的话语在形成时所发生的融合过程中”[15]222。也就是说,作为话语符号的基本意义结构,在具体阶级语境中获得了相对恒定的阐释模式,意义结构由此获得准确锚定,从而使该阶级的阅读架构得以突显。
可见,贝内特是从阶级属性角度来审视文本所可能召唤而出的阅读架构的。这种理解,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基本把握,也体现出对索绪尔符号学的改造性运用,从而呼应了当代学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阐释学方法的努力。
四大众文化现象的互文性透视
互文性理论由克里斯蒂娃提出后,迅速由其被创立之初的纯哲学形态,过渡为广受人文、社会学界用于分析社会泛文本的实证性批评方法[16]211-216。尤其在包括伯明翰学派在内的英语世界中的文化研究领域,这一理论被运用为对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探讨工具。
如前所述,贝内特曾从互文性理论角度批判性地重构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演化现象的论述。同时,他还在将互文性界定为“指涉其他文本的体系”[17]44以及“不同具体接受条件下,诸多文本之间的社会组织关系”[17]45的基础上,将该理论运用于对“邦德现象”等大众文化的分析中,对具有互文性关系的诸多邦德文本间的意识形态关系进行探讨。
英国小说家伊恩·弗莱明笔下的詹姆斯·邦德作为大众小说中的经典角色,其形象作为原文本被广泛改编为电影、电视及各种宣传片等诸多泛媒介文本。贝内特认为,在邦德小说流行之际,作为能指的“邦德”形象借由其他媒介形式派生出诸多其他邦德文本,贝内特由此从互文性角度来界定邦德现象,指出诸多具有邦德形象的文本之间呈现出怎样的流通与影响机制。由此,诸多媒体形式的邦德形象文本间便产生了十分复杂的文化联系。贝内特主要从下列两个方面探讨了邦德现象的互文性特征。
首先,贝内特认为“邦德”形象是一种具有变异性的能指(mobile signifier)。作为小说文本的邦德,在影视、音乐、广告等诸多媒体及口红、玩具等日用品中,被生产为一系列互文化产物。同时,邦德形象在前一种媒介文本中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也得以被后一种媒介文本所接纳。“邦德形象在一系列门类广泛的文本所形成的持续变化的过程中得以生产,这些文本在自己建构起来的邦德能指的作用下,彼此结合在一起。”[17]45在互文效应下生产出的文本与前文本形成了具有逻辑关系的统一性,不断生产、改造或传播着前一文本的意识形态。
其次,各种邦德文本基本是在同一社会文化语境中被生产出来,因此如仅仅通过对这一整体语境的考察,无法确定划分诸多单个邦德文本所具有的独特客体属性,而唯有将这些文本置于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中,通过对它们之间媒介转换关系的审视,确定其各自的文化、意识形态属性之间的关系及差异,才能实现对单个文本客体性的检审,亦即“在媒体形式的消费形式被调整时,将诸多单个‘邦德文本’从互文性关系转换中抽取出来并使其稳定化”[17]90。
可见,贝内特准确地意识到意识形态在互文性理论被用于批评实践中所具有的关键作用,考察到诸多互文性文本间的生产逻辑,并通过实证方式,对隐藏在互文性文本之后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辨析,从而使其批评实践呼应了自己对“探究文化如何在不同社会关系语境中发挥作用”[18]438的文化研究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式界定。
综上所述,贝内特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上,对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进行了本体论层面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并以此为据,从符号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进行了一系列文学及文化批评实践,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文化批评理路,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的方法视域,同时也在客观上彰显出作为“普遍方法论”的符号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批评方面的有效性[19]85。
参考文献:
[1]BENNETT T.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Turn to Gramsci”[M]//BENNETT T, MERCER C, WOOLLACOTT J.(eds.)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6.
[2]HAWKES T.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M].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3]BENNETT T. Formalism and Marxism[M].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4]TYNJANOV J. JACOBSON R.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Language[M]//MATEJKA L, POMORSKA K, ARBOR A.(eds.) Readings in Russian Poetics. Michigan: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 1978.
[5]JAMESON J.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6]VOLOSINOV V N.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New York and London: Seminar Press,1973.
[7]苏珊·佩特丽莉,奥古斯都·庞奇奥.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及社会批判[C].张碧译//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符号与传媒:总第7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8]SCHAFF A. History and Truth[M]. Toronto and Frankfurt: Pergamon Press, 1976.
[9]EAGLETON T. Criticism and Ideology[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10]BENNETT T. Outside Literatur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1]BERGESEN A. The Rise of Semiotic Marxism[J].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1993,36(1):1-22.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张碧.马克思主义的潜在符号学意识[C]//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外文化与文论:总第30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14]DELLA VOLPE G. Roussean and Marx[M].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1979.
[15]BENNETT T. Text, Readers, Reading Formation[J]. Literature and History, 1983,9(2):214-227.
[16]张颖.从对话到互文性——回应克里斯蒂娃[C]//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符号与传媒:总第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
[17]BENNETT T. WOOLLACOTT J. Bond and Beyond: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a Popular Hero[M]. London: Mcmilan Education, 1987.
[18]BENNETT T. The Multiplic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Utility[J].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13,14(3):438-441.
[19]郭鸿.作为“普通符号学”起点的科学符号学[C]//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符号与传媒:总第10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唐普]
收稿日期:2015-11-1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视域中的符号学研究”(12XWW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碧(1982—),男,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4-01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