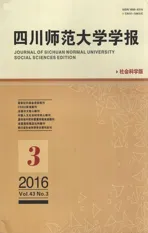清末宪政编查馆的立宪困境与反思
2016-04-13卢野
卢 野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
清末宪政编查馆的立宪困境与反思
卢 野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
对于宪政改革,就欧洲的历史经验而言,大多数现代宪政国家都是由绝对主义国家过渡而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证明了这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亚洲专制国家而言都是一条具有可行性的发展路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立宪实质上也是走这样的道路。清廷成立宪政编查馆,为的是仿行宪政,统筹整个立宪改革,但该馆在立宪过程中却无法逾越如何在巩固君权的同时、又能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并能维护君主权威的困境,这样的困境使得清末立宪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而这种困境的无解则可以从清廷对立宪与君权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传统中国君权的维系模式中去探求答案。
清末宪政改革;宪政编查馆;立宪困境;君权宪法化
清末立宪是中国迈向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步,立宪制度对于中国的传统政治而言是一个舶来品,清末立宪实则是一个宪政本土化的过程。由于受制于几千年封建思想以及当时清末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虽然是“仿行宪政”,但清末立宪注定是一个独特的、充满探索与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在宪政本土化的过程中,到底是宪政化于中国多一点还是中国化于宪政多一点,而对该二者的选择也将直接决定清末的立宪模式。西方历史学家对中国清末这段历史的研究往往采用的是“西洋的冲击——中国的回应”(Westert impact-Chinese response)的模式①,认为中国在清末宪政改革中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忽视了近代中国自身所具有变革动因②。清末宪政改革固然深受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但是在选择立宪模式以及进行宪制构建时,却不断发挥着主观选择与改造的作用,使得清末的立宪模式并不同于西方,可以说在中国宪政化和宪政中国化的天平上,清廷更偏向于后者。
正是由于清廷独特的立宪进程,使得这次改革并非像西方那样最终取得成功,但此次立宪所面临的困境与失败的原因却能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提供经验和教训。在整个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作为改革的核心机构宪政编查馆的所作所为无疑是立宪困境最为集中和具体的表现。
一 清末立宪中的宪政编查馆
1905年,清廷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五位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大臣归来之后,一再向清廷陈请宣布国是、预备立宪。特别是载泽在其奏折中提出宣告立宪不但不会影响到君权,而且还有利于“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并且力举了17条君主立宪对君权维护的作用,还指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1]173端方也以万言之巨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陈述立宪之利,加之日俄战争结果对清朝的冲击,使得慈禧终下决心于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宣布“仿行宪政”。
为了统筹整个改革,清廷专门成立了用以推动立宪的机构——宪政编查馆,该机构是清廷效仿日本在明治维新时设立的“宪法取调局”的基础上成立的。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并于同年11月25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谕令设立考察政治馆③,此为宪政编查馆的前身。而慈禧于1906年宣布“仿行宪政”以后,考察政治馆的主要事宜也从“考察”变成了“仿行”,而内容则从“政治”变为了“宪政”④。此时,考察政治馆的名字便不合时宜了,1907年8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五日),庆亲王奕劻等上奏:“拟请旨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以便切实开办”[2]45,同日清廷发布改名的上谕。8月24日,清廷下谕旨:“宪政编查馆王大臣关防谨择于七月十六日启铃(钤),其考察政治馆关防应即销毁……”[3]120,标志着考察政治馆向宪政编查馆转换的完成。至此,宪政编查馆作为清廷专门设立的用于宪政改革的“宪政之枢纽”,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宪政编查馆设立之初有三局三处,即编制局、统计局、官报局以及庶务处(后改名总务处⑤)、译书处、图书处,主要职责是编制法规和统计政要。编制局和统计局都下设三科:编制局下第一科掌属宪法之事,第二科掌属法典之事,第三科掌属各项单行法及行政法规之事;统计局下第一科掌属外交、民政以及财政之事,第二科掌属教育、军政以及司法之事,第三科掌属实业、交通和藩务之事⑥。后在1909年1月2日增设考核专科⑦,用以专门考核各立宪事项。
宪政编查馆虽然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存续时间也只有四年(1907—1911),但不同于日本“宪法取调局”只是制定日本宪法、设立日本国会的进程。宪政编查馆在整个立宪过程中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⑧。它参与统筹所有与立宪有关的事务,是推动清末立宪的核心机构,也是君权在立宪过程中的代表机构。其在推动立宪的过程中的进退维谷,也折射出清末立宪所面临的困境。
二 限权抑或护权的立宪两难
立宪改革,顾名思义,首先需要立宪,即拟出一部宪法。这是宪政国家立宪的应有之义。但清末立宪并不在于限权,相反其立宪的目的在于巩固君权。这就使得清廷需要面对如何在宪法的框架下去维护君权的问题。这也是作为宪法文本起草的主要机构,宪政编查馆所要解决的问题。
就《钦定宪法大纲》⑨的内容而言,其维护君权的意志十分坚定。《钦定宪法大纲》大体是模仿日本明治宪法,不仅是内容,于条文编写的方法也有借鉴⑩;而且,与之相比较,该大纲在对君权的保障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对于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相比于日本天皇受到特例条款的限制,清朝的皇帝则完全不用面对任何“但书”的规定;2.对于宣告戒严之权,清朝的皇帝可以随意宣布而且还能限制臣民的自由,而日本天皇的戒严权则需“法律定之”;3.对于发命令及行使发命令之权,日本天皇需要以为保持公共之安宁秩序及增进臣民之幸福为前提,而清廷则无此要求;4.对于议院闭会期间发布诏令之权,清廷比日本多了一个可“以诏令筹措必须之财用的权利”,而且次年议会开会时,也只是将此诏令交由议院协议,协议后怎么办不得而知,日本则明文规定次年交由议会后,若议会不承诺,则“失其效力”;5.就皇室经费而言,清廷可以设“常数”,而且也没有像日本宪法规定的若以后需要增加经费需要议会同意的条款;6.就皇室大典,日本宪法明文规定“不得以皇室典范变更本宪法之条规”,此规定相当于剥夺了皇室修宪的权力,但《钦定宪法大纲》并无此规定,就君主立宪本质而言,修宪权也非君主所有,不作此规定也无可厚非,但从宣统二年十月初四日清廷发布《派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谕》⑪可以看出,清廷将修宪之权牢牢抓在了手中,溥伦作为资政院总裁尚且说得过去,而载泽的选择则不得不说是清廷想控制修宪权的意图;7.臣民遵守法律之义务,这是一条十分值得注意的条款,日本宪法中也无对应的条款,其规定了“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但并没有规定皇帝有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更没有规定皇帝有遵守宪法的义务,虽然在大纲之前的说明中写道:“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最后还写道:“上至朝廷,下至庶人,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但在具体条文中却没有出现。此外,《钦定宪法大纲》也更加防范议会对皇权的限制,其在第五、六、十四条中都明确规定了“议院不得干预”,第七条中规定“议院不得议决”,第十三条中规定“议院不得置议”,而这几条都与皇权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清廷对议院防范之深。
宪政编查馆在拟订《钦定宪法大纲》的时候,一直在努力维护君主的权力,力图使其成为“巩固皇权”的宪法性文件。正如章太炎所言:“虏廷所拟立宪草案,大较规模日本。推其意趣,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义(乂)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亦有摭拾补且(苴),深没其文以为隐讳,使各条自相抵触者。”[4]100但是,如同“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一样,《钦定宪法大纲》的出台,虽然规定了“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是这条条款的本身就已经使君权从“奉天承运”走向了法律规定,从“不可知”走向了宪法化。在传统封建政治体制中,皇帝是天子,其权力来源于天的赐予,无需任何文本的确定,而当皇权被写进宪法后,皇帝的权力不再受天的庇护而转由法律保护,其身份从天的代表变为了法律规定的最高统治者,从类似于神的地位跌落到了人间。所以,拟订宪法大纲行为的本身就是对君权的限制,这是宪政编查馆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在启动“仿行宪政”之初就注定了的目标指向。
《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是一部尽量维护君权的宪法性文件,但其对君权也有相应的限制。如前文所讨论的,大纲的说明中明确规定了朝廷应当遵循钦定的宪法,虽然在具体条文中没有此规定,但就公开宣称朝廷应遵循法律的这一说法,已经开了限制皇权的先河。或许以前皇权的行使会受制于宗法礼数,但受制于法律还是第一次。在具体条文中,大纲第三条规定皇帝只能颁行法律,而具体立法工作则由议院议决,这也是对君主的立法权进行了限制。而第十条中规定皇帝对于司法权虽为总揽,但委任的审判衙门需遵钦定的法律行之,皇帝不得以诏令随时更改,此规定一方面是维持了司法的独立,但更为重要的是避免了皇帝以诏令的形式随意修改法律。这样的限制,同样出现在第十一条当中,皇帝虽有发布命令之权,但对“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之”。第十二条也明确在议院闭会期间,遇紧急之事,皇帝可以代发法律之诏令,但次年需交议院协议,虽然没有规定议院协议不过之后怎么办,但终究也算是对皇权的一种限制。
除了直接对皇权进行限制以外,《钦定宪法大纲》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为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以来第一次明确将臣民的权利义务列于法律之上。虽然此条款内容寥寥无几,但其意义却很深远。这些条文的出现,表明臣民的权利与义务不再来源于“君”,而是来源于“法”。这与中国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从侧面削弱了君权的范围。
由此可见,《钦定宪法大纲》内容体现出在护权与限权间的相互矛盾,如此的情况并非是宪政编查馆的疏忽或者无能,而是源于隐藏在这些文本背后的立宪价值冲突。
三 难以避免的困境与发生逻辑
从近代各国的宪政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各国的立宪改革既有相似性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但从近代西方国家立宪主义的源流来看,立宪理论大体可以包括三种:其一为自由主义,其二为有限政府理论,其三为社会契约论⑫。而这三种理论的背后都有限制权力的价值取向,其立宪的过程也是围绕着权力宪法化展开的。在亚洲,日本明治之后受到普鲁士启蒙绝对主义思想的影响,其效仿普鲁士的立宪模式带有十分明显的反议会主义与君权主义的思想。对于清廷而言,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们对德、日模式多有青睐,在德、日停留时间也较长⑬。而且载泽和端方的奏折中都以日本立宪为典范,指出:“中国之情势,实与日本当时无异”,立宪的模式“则日本所行预定立宪之年而先下定国是之诏,使官吏人民预为之备者,乃至良至美之方法,可以采而仿行者也”[1]49。而当时清廷立宪的目的,就是“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5]52。稳固皇权、抵御外侵、平定内乱,是清廷立宪的初衷,因此清廷自然也就选择了类似于日本的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立宪模式。
正因为这种立宪模式的选择,使得宪政编查馆在设计立宪制度的过程中处处以巩固权力为导向。清末立宪改革之初目的就很明确,为的就是“大权统于朝廷”,稳固清廷的统治,维持君权绝对的地位。在以此为目的的主导下,这次立宪的价值起点、方式和过程都脱离了传统立宪的轨道。但清末立宪运动毕竟是进行君主立宪,困于君主立宪的范式,对于君权的追求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制度的约束,其立宪的性质必然会使得君权从神明化走向宪法化。这也就使得清末立宪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如何在巩固君权的同时,又能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并能维护君权权威的困境之中。在“中国化”的立宪目的与传统立宪价值的碰撞以及立宪行为与立宪宗旨背离的情况下,也必然表现出绝对君权与君权宪法化的难以调和,而作为立宪核心机构的宪政编查馆一系列的立宪困境也由此产生。
以立法权和立法机构为例,宪政国家大多都有议会,议会享有立法权、对行政的监督权和弹劾权,是实现民主的一个重要途径。清末要立宪,也自然要设立议会,这是立宪的基本要求。而且议会对清朝皇室而言也并非完全没用,其能有效地监督内阁的权力以及地方督抚的权力。但是,清廷的统治者却绝不愿意议会限制或哪怕威胁到自己的权力。所以,在清末立宪过程中,涉及到议会的事宜则充满了犹豫与冲突。按照西方传统的立宪路径,宪法往往出自于议会,也能体现民权的意志。但这恰恰是清廷所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巩固皇权,清廷必然不会使宪法出自他人之手,这一点从宪政编查馆的奏折中便能看出:
……东西各国立宪政体,有成于下者,有成于上者,而莫不有宪法,莫不有议院。成于下者,始于君民之相争,而终于君民之相让,成于上者,必先制定国家统治之大权,而后赐于人民闻政之利益。各国制度,宪法则有钦定、民定之别,议会则有一院、两院之殊。今朝廷采取其长,以为施行之则,要当内审国体,下察民情,熟权利害而后出之。大凡立宪自上之国,统治根本,在于朝廷,宜使议院由宪法而生,不宜使宪法由议院而出,中国国体,自必用钦定宪法,此一定不易之理。[6]5977-5978
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以后,将改革官制列为首要任务,当时对于开启国会之事尚未提及,更别说起草宪法了。到了1907年,各地出现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日益增多,端方等人也上奏起草宪法,但此时清廷仍没有在意⑭。直到1908年7月22日,宪政编查馆上奏《咨议局章程》后,清廷终于感受到了起草宪法的紧迫性,于是在《咨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均照所议办理著各督抚限一年内办齐谕》中写道:“著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督同馆、院谙习法政人员,甄采列邦之良规,折衷本国之成宪,迅将君主宪法大纲及议院选举各法择要编辑,并将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各事分期拟议护(附)列具奏呈览。”[7]684正式启动了宪法大纲的起草。
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⑮将拟订好的《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等文件上奏朝廷。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宪法性文件从起草之初就在努力维护着王权。虽然这份文件是由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拟订的,但具体由谁起草则对于整个文本的价值倾向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对于谁是该大纲的具体起草人可谓众说纷纭,章太炎认为杨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⑯,张一麐也认为是杨度起草的⑰;胡思敬则认为大纲出自杨度和汪荣宝二人⑱,但是杨度自己对此予以否认⑲,并称自己在宪政编查馆并没有得到什么重要的差事⑳,也就不可能起草《钦定宪法大纲》了。从之前胡思敬的记载以及其他报纸文献㉑和学术著作㉒的讨论来看,《钦定宪法大纲》应当出自汪荣宝之手而非杨度。而且,据《汪荣宝日记》中的记载,其于宣统三年二月二十日(1911年3月20日)与陈邦瑞、李家驹一同纂拟《宪法》㉓。如此来看,其能起草宪法,也应与其之前有起草大纲的先验有关。汪荣宝与杨度虽都有留学日本的背景,但相比于过于激进“屡次被参”㉔的杨度,父辈是清廷命官的汪荣宝,相对更加温和,虽也主张清廷应效仿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其终究是属于改良派,改革也是以维护清廷统治为前提。由此可见,宪政编查馆让汪荣宝起草《钦定宪法大纲》,恐有为了避免该大纲过于激进以妨碍“巩固君权”之意。
清末立宪中,按照清廷的安排,一共成立了两个准议会组织:资政院与咨议局。该二者被称为“议院之基础”,资政院在中央,咨议局位于各省。其中,咨议局监督的是各地方督抚,与皇权无直接的关系;而资政院则不同,其作为国会的预备模式,对于皇权而言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也是清廷在整个立宪过程中防范最深的机构。虽然资政院的设立与之后的章程修改,都与宪政编查馆无太大关系,但宪政编查馆作为代表皇权的立宪机构与资政院代表民权的立宪机构在二者并存的那段时间彼此却有着很明显的冲突,而这些冲突也源自各方对绝对君权与君权宪法化的态度。
从宪政编查馆成立的时候清廷发的上谕,“著即改为宪政编查馆,资政院未设以前,暂由军机处王大臣督饬原派该馆提调详细调查编定,以期第施行”[8]64中,可以看出,清廷将宪政编查馆设置为资政院成立前的一个临时机构,资政院成立之后其职责交由资政院行使。但随后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却在拟呈的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折中对二者的关系作了微妙的改变,其在奏折中对所奉懿旨的陈述中写道:“考察政治馆即改为宪政编查馆,暂由军机处王大臣督饬原派该馆提调详细调查编定,以期次第施行”,此句与原旨相比故意漏掉了“资政院未设以前”几个字,而且还写道:“俟资政院设立后,随时将臣馆核定之稿送由院中陆续议决,盖一司编撰,一主赞定,庶政府尽提议法案之责,而国民有参预立法之权,立宪之基将由此以巩固。”[2]47-48再者,从宪政编查馆所拟的宪政筹备九年清单来看,其第三年就计划资政院开院,这就意味着届时资政院已经开始运作了,但之后到第九年宣布宪法都是“宪政编查馆办”㉕。以上种种不难看出,宪政编查馆在成立之初,就没有打算在资政院成立之后裁撤,宪政编查馆将与资政院共同推进立宪,而且更是将资政院的立法权据为己有。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宪政编查馆自己的作为,其也不敢擅自改变上谕,根本原因还在于清廷对资政院的制衡。在追求绝对君权的目的下,清廷绝不可能轻易将立宪改革的主导权交给代表民权的议会。
正是由于宪政编查馆设立之初的安排,导致了其日后与资政院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到了1910年资政院正式开院以后,冲突越发明显。例如当时的《四明日报》在《评宪政编查馆擅发命令侵夺资政院权限》中,就报道宪政编查馆擅自核议浙江督抚与浙江咨议局的争议,授意浙江督抚裁撤浙江省咨议局,违背了《资政院章程》,侵夺了资政院的权力㉖。1910年资政院开会期间,议员易宗夔就以清廷以前设立宪政编查馆的上谕为依据提出质问说帖,要求裁撤宪政编查馆㉗。而对此,当时报纸的报道称:“资政院前据议员易宗夔质问宪政馆说帖,兹悉宪政馆答复。略称:查说帖内开宪政馆是否仿各国内阁所设之法制局,抑仍握最高之立法权等语,本馆组织系占各国内阁之大部分,无论资政院已未成立,实非仅一法制局之比。至立法事项,不特本馆未握其最高权,即现在成立之资政院及将来应设之上下议院,其对于立法权亦仅以协赞为限。”[9]469由此可见,宪政编查馆完全无视资政院的立法权,且将资政院的权力从“赞定”变成了“协赞”。对于议院就上谕中“资政院未设以前,暂由军机处王大臣督饬原派该馆提调详细调查编定,以期第施行”中“暂”的解释,宪政编查馆回答称:“此‘暂’字乃指军机处王大臣而言,非谓资政院成立后即行裁撤宪政馆也。”[10]2其实,宪政编查馆在整个立宪过程中都是集宪政、立法、司法三大权于一身。这也是清廷为维护绝对君权、力求主导立宪而故意为之。所以,宪政编查馆有如此强硬的态度,也在意料之中。至此开始,资政院对于裁撤宪政编查馆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的报纸一度也认为宪政编查馆将会被裁撤㉘。不过,直到1911年5月奕劻内阁出台,同年6月清廷颁布《内阁属官官制及内阁法制院官制》后,宪政编查馆才被裁撤,其所管事项由内阁法制院接管。由此可见,宪政编查馆完全不受资政院的影响和监督。对于一个宪政编查馆尚且如此,资政院在整个立宪过程中又怎能拥有独立且实在的权力呢?
按照立宪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资政院应当拥有完整的立法权与监督权,但是在以君权为推动力量的立宪背景下,清廷想立宪又不愿意放权,资政院也就一直受到军机处以及宪政编查馆的限制。虽然在历次会议上,议员们据理力争,以求真正的立宪与民主政治,但终究难以有较大的成绩。而这样的冲突,也使得资政院与咨议局最后并没有促成清末立宪的成功,反而在武昌起义以后,其中部分成员成为了革命的中坚力量。这也是绝对君权与君权宪法化无法调和的必然结果。
四 困境的背后——君权与君主立宪
就欧洲的历史经验而言,大多数现代宪政国家都是由绝对主义国家过渡而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证明了这是一条对于无论西方还是亚洲专制国家而言都具有可行性的发展路径。清末立宪实质也是在走这样的道路,其立宪的路径和方式是建立在效仿他国的成功经验之上。但这场政治改革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禁固,立宪也并非完全移植外国的模式,相反在其中还具有很多中国自身的特殊因素。而正是这些特殊之处导致了绝对君权与君权宪法化难以调和的困境,立宪结局也与效仿对象截然不同。
五大臣出洋考察回来之后,极力推崇日本的立宪模式,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环境和日本相似,而且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天皇的权力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清廷因此认为君主立宪可以实现其既巩固君权又巩固君位的效果。因此,在起草《钦定宪法大纲》时,“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字句与日本宪法如出一辙,但是这样的文字在当时引起了立宪派不小的反感,而这样的情况却并没有在日本发生。究其原因,在于考察大臣忽略了一个事实,日本天皇在明治维新之前其实并没有什么实权,天皇更多的是作为宗教的领袖,真正的大权是掌握在幕府手里的。因此,当德川幕府的统治权日益丧失时,掌握日本实权的政治精英自然会将天皇重新置于政治的中心,天皇是改革的受益者而非对象,而且此时的天皇也并非拥有清廷想要巩固的那种实权㉙。但是,清廷不同,皇帝自古都是权力的中心,不存在需要一个由虚到实的过程,而且当时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将其对象指向清廷,所以,“如果君主的统治岌岌可危,又如何构建起新的权力中心呢?”[11]123对于习惯于大权在握的清廷而言,君权与君位被画上了等号,“万世一系”的前提是“君权永固”。正是这样的认识,使得清廷并没有理解到君主立宪的政体对于皇权的真正作用。“正因为统而不治,不承担直接的政治责任,君主才获得超然性的地位,进而获得无上的尊严,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政治发展史皆说明了这一点。日本如此,更早的君宪国家英国亦是如此”[11]124。制度化的君权维护的是作为意识形态中心的君权,是树立君主的精神权威以起到维护国家统一的象征性作用,君主立宪必然会限制到实在的君权,立宪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巩固君位而非君权。
清廷无法放弃实权而实现日本立宪效果的原因,在于传统中国君权产生与维护的特殊性。君权得以维系的前提是君权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日本天皇一直是一脉相承,期间并没有更迭,而且日本天皇作为日本神道教的宗教支撑具有超然的地位,因此日本天皇的君位从未受到质疑。如伊藤博文在《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中所言:“神祖开国以来,虽时有兴衰,世有治乱,然皇族一系,帝位兴隆,与天地同寿,无有终焉。本条首倡立国之大义:我日本帝国始终与万世一系之皇统相依,君民关系古往今来始终如一,万世长固,永不改变。”[12]3而中国的皇帝却已经历了数次改朝换代,孟子也主张臣民拥有反对暴君的权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点也使得对于君位的拥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权的大小,而非完全建立在对君的崇敬之上。虽然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寄希望通过抽象的天命论加强皇权的威信,却没能将皇权推至类似于神明的宗教地位,反而是世俗的统治者取代了天命的话语权,通过权力的暴力推动证明其神圣性。皇权的变更缺乏宗教仪式的神秘过程,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位必须紧紧依靠权力才能生存。到了清末,统治者的权威原本已经岌岌可危,加之慈禧的“垂帘听政”使得君与权早已割裂,而当时的政治精英并不对此有太多的非议,他们只是听命于权而非君,这就更进一步降低了君的地位和权威,家国同构的传统中国国家观已被打破。而慈禧与光绪离世之后,整个清皇室的统治权威几乎消失殆尽,载沣为人平庸,没有力挽狂澜之力,何况清朝的统治者原本是少数民族,满汉之争从建朝之日起就未曾停歇,而且当时日益壮大的革命派更是以此为宣传口号,力图推翻清廷。如此的情况,使得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备受争议,若此时君权再被割裂,君位则很难延续,所以清廷不会放弃权力而去寻求超脱的君位,也就不可能遵循传统的君主立宪路径。
清廷立宪之初,由于在对日本考察的基础上认为立宪有助于维护绝对的君权,由此便如火如荼模仿并开展了起来。但中日的差别,使得清廷在逐渐立宪的过程中发现清末立宪必然会导致君权的削弱,这与其立宪的初衷是相悖的。因此,在随后的立宪过程中,清廷力图掌控整个过程,在绝对君权与君权宪法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立宪的轨迹已不再向其预设的那样发展,可以说“不是清王朝依其初衷驾驭了制宪运动,而是制宪运动支配了清王朝”[13]209。当清廷逐渐明白君权宪法化是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而不得不放弃绝对君权的梦想,并转向真正的立宪时,民众却已经失去了耐心,这场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也伴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落下帷幕。
五 结论
清末立宪的过程,是在力图维护绝对君权的框架下走向君权宪法化的过程。这样的立宪目的与路径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立宪困境,而这样的困境源自于对君主立宪这样的政治制度舶来品的错误认知以及传统中国君权的维系模式与君主立宪政体的不合。虽然到了1911年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出台,清廷终于在君权与君位之间做出了选择,但为时已晚。正如梁启超所说:“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贻我中国以难题。使彼数年以来稍有分毫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使所谓十九条信条者,能于一年数月前发布其一二,则吾民虽长戴此装饰品,视之如希腊、那威等国之迎立异族耳,吾知吾民当不屑断断与较者。而无如始终不寤,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然后迫于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14]348
政治改革注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取舍的过程,是一个革新与传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过程。观之今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充满了各种挑战。在面对这些困境时,我们或许可以从清末的那段历史中去寻找经验和教训。
注释:
①费正清在其著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 d China)、《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Trade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ponse to the West-A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建立了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范式,其中“冲击—回应”模式为该范式的核心,贯穿于其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费正清认为,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动态社会,中国是一个长期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这样的社会使得中国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近代中国只有在西方不断的冲击下,才能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进步。这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也逐渐被美国史学界所采用。
②美国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在其著作《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对“冲击—回应”模式做出了批判,认为该模式忽视了中国内在的变革力量,中国近代的变革不仅仅是西方冲击的结果,其社会自身内在也具有变革的因素。参见:〔美〕柯文《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胡大泽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上谕写道:“前经特简载泽等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著即派政务处王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参见:《设立考察政治馆谕(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④其实,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时,本想以“考察宪政”为名,但顾忌慈禧对“宪政”一词的反感,只能以“考察政治”取代之。参见: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
⑤宪政编查馆在《宪政编查馆奏派员分任馆务折(并单)》中,将庶务处改为了总务处。参见:《宪政编查馆奏派员分任馆务折(并单)(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政治官报》总第41号,第4-5页。
⑥参见:《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拟呈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折(附清单)(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51页。
⑦参见:《宪政编查馆会奏遵设专科考核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酌拟章程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政治官报》总第432号,第8页。
⑧清末有报纸曾如此评价宪政编查馆:“谓其立法,则彼固能筹备宪政,督饬督抚之进行,则有涉行政矣;谓其行政,则彼固能解释各种法律,则凡刑法上之疑义,固得由其解释,则又涉司法矣;谓其司法,则彼固能订立各项章程及宪法大纲,且得不经资政院之通过,则又类立法矣。”宪政编查馆虽然从属军机处,按照机构划分应当是行政机关,但从宪政编查馆的立宪活动来看,其起草钦定宪法大纲是立法活动,解释法律的疑惑是司法活动,督饬督抚立宪是行政活动,所以可以说其集三权于一身。参见:《论宪政馆之误国殃民》,《民立报》宣统二年十一月初八日,收入马鸿谟编《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一)(1909.5-1910.12)》,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8-569页。
⑨《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折(附清单二)(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59页;《大日本帝国宪法》。下文对《钦定宪法大纲》和《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介绍均出自于此,不再另注。
⑩对此,国内学者彭剑在其著作中有专门的论述,其认为该大纲学习了明治宪法的“外记法”,而此方法则是达寿在日本考察宪政后所学,通过在条文中对君权进行详细规定以避免将来产生疑问,也防止开设国会时为法律所限制。参见:彭剑《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1]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八日)[G]//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庆亲王奕劻等奏请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折(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五)[G]//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
[3]为具奏本馆开用关防日期并附奏请销旧有关防由[G]//清宪政编查馆奏稿汇订.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4.
[4]章太炎.代议然否论·附虏宪废疾六条[G]//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北京:三联书店,1977.
[5]宣誓预备立宪谕(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G]//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6]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折:附清单二.(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G]//光绪朝东华录(五).北京:中华书局,1958.
[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咨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均照所议办理著各督抚限一年内办齐谕(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G]//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
[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谕(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五)[G]//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
[9]宪政馆强硬答复一[G]//马鸿谟.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一)(1909.5-1910.12).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10]资政院纪事[N].盛京时报,1911-01-25(2).
[11]郭绍敏.清末立宪与国家建设的困境[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12]〔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M].牛仲君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13]贺嘉.清末制宪[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14]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欧阳哲生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
The Constitutional Dilemma and Introspe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mpilation Burea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U Ye
(School of Administrative Law,South 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Fro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Europe,one can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ransition from an absolute state to the modern constitutional state is a feasible path.It is further proved by Meiji Restoration in Japan.The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actually of the same way.In order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European countries and Japan,the Qing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Constitutional Compilation Bureau to overall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But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stitutionalism the bureau was unable to solve the dilemma that how to consolidate the monarchical power and carry out the restriction of system of monarchical power while maintain the authority of the throne in the meantime.Such dilemma led to the final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This dilemma cannot be settled because of the cognition of the Qing govern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monarchical power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mode of the monarchial power in ancient China.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Constitutional Compilation Bureau;the Constitutional dilemma;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monarchical power
DF209
A
1000-5315(2016)03-0102-09
[责任编辑:苏雪梅]
2016-02-15
卢野(1984—),男,四川成都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