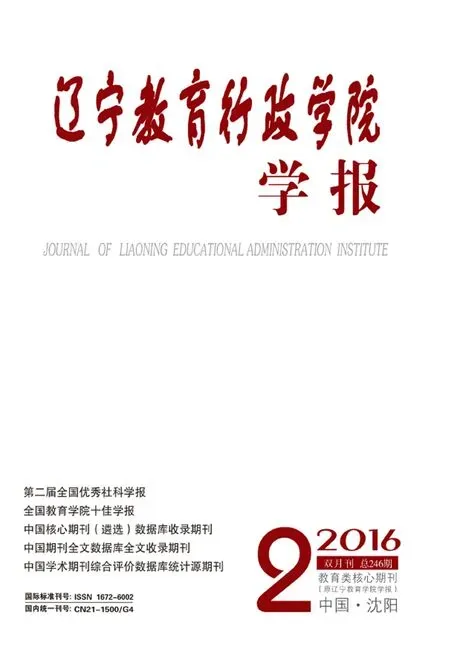试论“星”的量词属性
2016-04-13曹英豪
曹英豪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
试论“星”的量词属性
曹英豪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
摘要《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不仅没有标明“星”的量词属性,也没有说明“星”是否可以归入量词范畴,围绕这两个问题,对“星”在北大语料库里的语料进行了定量统计分析,发现“星”不但和基数词组成数量结构,而且,它们所组成的数量结构可以计量所修饰限制的中心词的量,同时,它们所修饰限制的中心词在语义范畴上表现出了多样性。
关键词“星”;数量结构规范性;模糊量;语义范畴多样性
一、引言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没有说明“星”是否属于量范畴,也没有标明其词类归属,围绕这两个问题,在对“星”和“一、两、半”的组合情况①进行定量分析后,发现“星”有三方面的情况:一是可以和“一”“两”这两个基数词进行组合,且它们所构成的数量结构具有规范性;二是它不能和“半”组合,因为在北大语料库里,没有发现“半星”这样的语料;三是它们组成的数量结构所修饰限制的事物不但在语义范畴上表现出了多样性,而且所表现出的量具有明显的模糊性质。
二、“星”量词属性的表现
基于“‘星’能否和数词组合、能否修饰限制事物、能否表示所修饰限制事物的量”这三个标准,本文对“星”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星”在量词属性上有三方面的表现:
(一)数量结构的规范性
数量结构的规范性指的是“星”和基数词能够组成规范的数量结构。在对“星”的语料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发现,和“星”所组合使用的数词多是大于零,小于“两”的基数词,其中,和“一”组合使用的语料有152例,和“两”组合使用的语料有4例,例如:
(1)……爱的手表、皮带、毯子等换回几颗白菜,几个马铃薯,几条酸黄瓜和[一星]半点面包充饥。(《1994年报刊精选》)
(2)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S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朱自清《冬天》)
例(1)中,“面包”前面的“一星半点”和例(2)中,“灯火”前面的“一两星”都是数词在“星”前,中心词在“星”后,它们都是规范的数量名结构。
(二)中心词语义范畴的多样性
基数词“一”“两”和“星”组成的数量结构所修饰限制的事物在语义范畴的归属上表现出了多样性,即:这些事物可以被归入“主观事物和客观事物”这两个上位范畴,同时,主观事物范畴又可以分出隐喻类和非隐喻类等两个下位范畴,而客观事物范畴也可以分出发光物和非发光物,其中,非发光物又可以分出固体事物、液体事物、气体事物。例如:
1.主观事物。主观事物指的是由“星”组成的数量结构所修饰的事物具有主观性质。
A.隐喻类事物
隐喻类事物指的是目标域在相似性的基础上,逆推寻找原域以建立认知联系的过程,其中,目标域指的是隐喻类事物,而原域指的是“星”,它们之间有相似性,例如:
(3)不过,知识分子心田中孕育之[一星]理想之华,却始终在拨弄这位遗民巨儒的思想与行为:磨剑抗清、浪迹……(《初白庵著书砚边读史漫兴》)
(4)不敢论散文当如何做,止窃思,凡一片情绪,一点心迹,[一星]思想的火花,笔之于纸,若为韵体(固非纯粹之韵),便是诗了。(《读书》)
例(3)中的“理想之华”和例(4)中的“思想的火花”指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具有发光性质的事物,而“星”本身含义中也具有发光的性质,从这里可以看出,它们在“发光”这个性质上具有相似性,正是这个相似性不但把它们联系到了一起,而且使“理想之华”“思想的火花”变得具体可感。
B.非隐喻类事物
非隐喻类事物是指中心词和“星”之间没有“发光”这个相似性,它们在量少的基础上联系起来,例如:
(5)撕裂着你的心肺,只要能给这位行将命赴黄泉的姑娘注入一滴力量,[一星勇气],即使付出一切,你也在所不惜。(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
(6)金星回到寓所,已经三更过了;虽然腿脚很困,却没有[一星]睡意。(姚雪垠《李自成》)
例(5)中的“勇气”和例(6)中的“睡意”的性质中没有“发光”,所以,它们和“星”之间的联系不可能是基于相似性,而可能是在量少的基础上,它们在认知中被联系到了一起,比如:例(5)中的“一星勇气”是说“勇气”的量少,例(6)中的“一星睡意”说的也是“睡意”的量少。
2.客观事物。客观事物指的是“星”后中心词所代表的事物具有看得见或摸得着的性质。
A.发光物
发光物指的是“星”所修饰限制的事物具有发光性质。例如:
(7)他看见亮起了[一星]光点——星星不会这么低的。使威廉斯吃惊的是:竟然没人向光点射击。(《读者》)
(8)那微眯的眼睛有些惊讶地睁了下。然后[一星亮光]就被无力的迷惘和痛惜淹没了,暗淡下去。(陈世旭《李芙蓉年谱》)
(9)头发像稀疏的枯草,眼睛像桔井,再大的冲动也激发不出[一星]泪光。(陈世旭《将军镇》)
例(7)中的“光点”、例(8)中的“亮光”以及例(9)中的“泪光”,都具有“光”这个语素,表明了这三个中心词所代表的事物不但是可以发光的,而且是看得见或摸得着的事物,而“星”和它们表现出了相似的性质,且“发光”“客观”这两个性质决定了,“星”和这三个中心词在认知过程中结合在了一起。
B.非发光物
非发光物指的是“星”所修饰的事物中不具有发光性质的那一类。本文按照形态的特征把这类事物分成三类:
①固体事物
固体事物在形态上,表现出了散状、细小整体状、模糊痕迹的特征。
(10)一手调馅,馅调得又香又绵,面和得软硬适度,最后盆手两净,不粘[一星]面粉。(人民日报》)
(11)忽然,[一星]烟灰把漂亮的新椅垫烧了个洞。(《读者》)
(12)面对这么多的不幸和苦难,儿子那稚嫩洁白、没有[一星]尘土和皱褶的小心灵,被深深地震动了。(陶斯亮《住中南海对门的日子》)
(13)比长江还长,把全中国都照亮,再没一点渣滓,[一星灰尘],整个的像块水晶,里边印着青的松竹与金色的江河。(老舍《一块猪肝》)
(14)用麻布袋子把窗户蒙住,拿起钦刀,没有一点点声音,不留[一星星血迹]地把一口猪杀了。(周立波《暴风骤雨》)
上面这五个例子中“一星”后面的中心词都是固体形态的,只不过,它们之间具体的形态特征有差别,即:例(10)中的“面粉”和例(11)中的“烟灰”具有散状的特征,例(12)中的“尘土”和例(13)中的“灰尘”具有细小整体的特征,例(14)中的“血迹”表现出了模糊迹象的特征。
②液体事物
这类事物具有液体的性质,例如:
(15)他是只许自己在别人头上拉屎撒尿,不许别人在他脸上溅[一星唾沫]的。(汪曾祺《大淖记事》)
(16)当是很妥贴的。可浪涛再大,也溅不到那张瘦削、清秀、白净的脸上[一星泡沫]。(张正隆《雪白血红》)
例(15)中的“唾沫”和例(16)中的“泡沫”在形态上都具有液体的特征,这个形态特征可以从上文的“浪涛”看出。
③气体事物
(17)连闹新房的人都没有,几个毛人儿对一盏油灯闲磕牙,哪有[一星儿喜庆的味儿]?(戴厚英《流泪的淮河》)
(18)老赵已经四十开外,虽然身躯粗壮,可没有[一星儿]漂亮的气味!(矛盾《子夜》)
例(17)中的“味儿”和例(18)中的“气味”在形态上表现出了气体的特征。
(三)量的模糊性
“星”在计量中心词的量时,在量的多少上表现出了模糊性,例如:
(19)他也是重感情的人。他提到维尔希克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一星泪水]。(《鹈鹕案卷》)
(20)假农药也参与了这种“惯性”运转,只有伤人作用,别无[一星儿]“药效”,连老鼠都药不死。(《1994年报刊精选》)
例(19)中“泪水”和例(20)中“药效”的量的多少在“一星”的计量下,是模糊的,至于这两个中心词确切的量,“一星”是计量不出来的。
此外,“星”自身不含有数量性,它的量词属性多是借助“一”“两”这两个基数词来表达,因为它的前面不能加上“半”。
三、结语
通过对“星”在北大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定量分析,可以看出“星”表现出了三个方面的量词属性:一是数量结构规范性。“星”不仅可以和“一”搭配,还可以和“两”搭配;二是中心词语义范畴多样性。“星”的中心词的语义范畴大体上可以分成主观事物范畴和客观事物范围;三是量的模糊性。“星”不能计量事物的准确的量,即:“星”所计量的事物的量在多少上没有准确的数值。从这三个量词属性可以看出,“星”可以被归入量范畴。因此,《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应该标明“星”的词类归属和量词属性。
注释:
①在北大语料库里,没有发现“星”和大于“两”的数词组合使用的语料,所以,本文只统计分析了“星”和“一、两、半”等的组合情况,且“星”不可以和“半”组合使用。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Z].商务印书馆,2005.
[2]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
[3]吕凤端.现代汉语个体量词的认知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3.
[4]江蓝生,谭景春,程荣.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Z].商务印书馆,2013.
(责任编辑:彭琳琳)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H0
收稿日期2016-01-27
作者简介:曹英豪(1989-),男,山西永济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论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