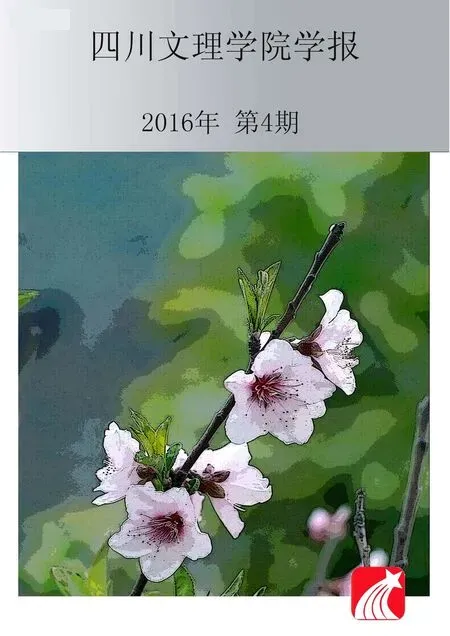遵循内心的真实
——浅析《八部半》中隐含的现实主义
2016-04-12王卓尔
王卓尔
(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重庆沙坪坝400044)
遵循内心的真实
——浅析《八部半》中隐含的现实主义
王卓尔
(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重庆沙坪坝400044)
摘要: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与英格玛·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1918-2007)、安得烈·塔尔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32-1986)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代表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最高峰,且对后世电影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对费里尼重要作品《8 1/2》(1963)(译名《八部半》)进行浅析,探讨其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下,关照内心、采用超现实手法表现心理现实主义的拍片风格。
关键词:费德里科·费里尼; 《八部半》;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
影片《八部半》讲述了一位导演在构思其第九部影片时遭遇了创作瓶颈。他强烈渴望成功,却无力摆脱来自妻子、情人、制片方、记者、演员、教会等多方面的围堵,最终思想陷入了极度混乱,未能完成影片拍摄。无论对其工作还是生活他都已逐渐失去自我掌控,在此期间,他时而处于现实,时而陷入幻想与梦境,本片成功的反映了他在意识中反抗和逃避的心路历程。
一、费里尼与新现实主义
学术上有关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概念以及截止日期并没有明确而一致的界定,通常认定其始于1945年,(在大卫·波德维尔看来,该时期最为重要的电影制作潮流于1945年到1951年)其代表作品为罗伯托·罗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执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a,cittàaperta)(1945)(编剧费里尼)。因反对主流的法西斯宣传片以及公式化的白色电话片,追求一种“将摄影机扛到街上去”的纪实风格以及着重于表达社会上的小人物的生活,新现实主义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以及民族性。也恰是如此,自费里尼作为导演拍摄了被称之为“孤独三部曲”的《大路》(LaStrada)(1954)、《骗子》(TheSwindle)(1955)以及《卡比利亚之夜》(LeNottidiCabiria)(1957)之后,有评论认为其逐渐背离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而继其更为激进的《甜蜜的生活》(LaDolceVita)(1960)以及巅峰之作《八部半》(8 1/2) (1963)之后,有关费里尼是否还能被隶属于新现实主义导演的争论久未停歇。“费里尼在继续顽强地寻求电影中的新事物,但是在他的创作中已经出现了使他脱离新现实主义道路的危险的征兆。”[1]而正如罗培托·罗西里尼所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现实主义,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是最好的。”[2]费里尼本人对新现实主义的定义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宣称自己所有作品“都明确地具有新现实主义风格”。“新现实主义不是你要表现什么的向题,它的真正精神是你如何来表现它”。[2]以诚实的眼光来看待现实,并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的物质现实表象,事实上深层次的人的精神世界、心理状况的现实,同样甚至在某些层面上能够更加本质的表达现实的真正内核。费里尼坚称自己属于新现实主义,所不同的是,他将人的心理、意识甚至梦境同样纳入到现实的范畴之内,在我看来,这种内心现实主义不仅不是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背离,反而是一种别样的升华与拓展。电影之于费里尼,不仅是关注角色的外部遭遇,更重要的是通过表达人物内心的运动状态,对其命运的兴衰际遇进行人文关怀,他的这种富于幻想的内省式拍片风格,在影片《八部半》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本文将在后面详述。
二、《八部半》所表达的外在现实
《八部半》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似梦似幻的电影风格,大量的现实、梦境、幻想与意识流场景相互交融,使整部片子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超现实格调。其形式虽不能算是原创——有关闪回、意识流甚至现今所流行的穿越的拍摄手法其实在很多欧洲艺术大师的杰作中都有体现,如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Smultronstället)(1957)以及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1959)等;然而此片也堪称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以及意识流表现手法推向极致之作——片中十一个闪回和幻想片段已成为研究费里尼乃至欧洲艺术电影当中的精神分析理论与电影语言结合的典范。《八部半》无论从人物设定还是对话中,都体现出导演对二十世纪中叶的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所面对的现实矛盾和精神危机,极为诚实和准确的看法。1963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奖之时,费里尼曾就本片回答记者问题,“很难在《八部半》中划分出这样的界限:哪一部分是我个人事件的开始或结束,从哪一点起.我是在塑造形象(包括我对这个形象的构思在内)——我只知道我的目的是,叙述一个内心混乱的导演的经历,显然,在接触这样一个题材时,就会包含最诚恳的、最无顾忌的自白”。[3]如果说费里尼几乎所有电影都充斥了反复出现的意象,如喧嚣或荒诞的马戏团表演、荒芜阴暗的道路、充满隐秘的恐惧感的海岸、与情节几乎无关的各色小丑等,似乎让人在观赏同一部影片,那么《八部半》则可称之为他最为直白赤裸而又质朴的表现自我的杰作——片中男主人公基多的形象设定影射了当时广泛的欧洲中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然而其原型更多的则是依据导演费里尼本人。就片名来讲,《八部半》则暗含了费里尼在此之前执导过的七部故事片以及略等于半部影片的两个插曲。而影片男主角,导演基多的设置,其生活工作环境,周边人物状况等也暗喻了费里尼自己。本片采取循环的套中套式的复调叙事结构,从基多的主观视角,发展出较为平行的两条心理轨迹:一是基多在电影创作中遭遇灵感枯竭,焦灼之中充满困顿和绝望;二是他在与妻子、情人、缪斯女神(其中一位演员)相处时,逐渐失去自控,甚为不如意的情感状况。在此处,我们可以认为该片展示的圆周型复调结构为:费里尼讲述导演基多的故事——基多讲述自己构思的电影——而这部电影讲述费里尼本人。影片结尾处,导演放下手中的扩音器走进被意象化的角色之中,随他们跳起了圆圈舞,这也预示着从费里尼本人出发,回至圆周的原点。叙事结构与叙述方式的特点,表明了电影内容中探索的焦点。《八部半》正如一个社会万花筒,让形形色色的人以极富表现力的方式,一一从镜头面前闪过,例如电影从6分半时表现疗养院风景以及人物的超长镜头,配合激昂的交响乐,向观众展现了一副二十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浮世绘。费里尼惯于使用戏剧化镜头,去透露出俏皮而些许荒谬的讽刺,在此片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面对周遭,基多面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产生困惑与绝望,只能倦怠的逃避;他期望如稚童般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渴求不负责任的解决身边的一切难题的做法,是费里尼对基多所代表的一类人(现代欧洲知识分子群体)的直接感受。这种灵魂的集体挣扎与焦虑,寻求出路却毫无方向的无力奔突,正是费里尼延续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写实的一面,毫无隐藏,不加矫饰的直面人的心灵危机与困顿。剥开《八部半》夸张而华丽的视听语言之表象,隐藏着费里尼对于那个年代的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现实的入髓透视,只不过相比起描写宏大的社会景观,他采用了更加关注个人的微观方式而已。
三、《八部半》所探索的心理现实
电影之于费里尼,是一种自然的需求,当追求视觉想象力的提示,通过对《八部半》的解析,笔者认为费里尼受到了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却又与之有别。超现实主义只表现潜意识领域不具有任何现实色彩的意向和幻想空间,力图创造一种比现实更加真实的东西,而其毫不借助故事或任何其他理性的方法,时常让观赏者感到无比困惑。超现实主义电影所体现的真实,与现实的关系更为暧昧和隐晦,甚至是凌驾于现实表面特征之上的,然而费里尼所采用的超现实主义手法,仅仅是为自己内心所遵循的真实服务,是对外在现实表征的强化以及解释,即便是与外在现实相悖,依然是以外在为基础而延伸出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心理现实。如影片中,基多幻想妻子和情人和睦相处,进而自己如苏丹王一样坐拥后宫成群,对女性享有绝对的权威。这一内心的渴望是一种空穴来风——正因为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妻子、情人还是与之暧昧的女演员等,均已逃脱出自己的掌控,这让基多焦灼不安,却又无法解决矛盾,因而才出现近乎荒缪的幻想。由此可见,超现实对于费里尼来讲,并非是目的与归宿,而是手段与方式,并以此更为深刻的表达现实而已。
那么,费里尼所遵从的内心现实,究竟是怎样一种现实呢?从他几乎每一部影片都会引用到的小丑情节,我们可以窥见一二。他所拍摄的纪录片《小丑》(I Clowns)(1971)可谓是完整的解释了他为何对小丑如此着迷,以及他所认为的小丑的世界,其实就是现实世界的观点。对费里尼而言,小丑分为两类——“白面小丑”和“奥古斯都”:
“前者代表优雅、可爱、和谐、聪明、清醒,在道德是完美的,惟一的,无可置喙的神圣……而奥古斯都则与之对抗……”
“奥古斯都,是会把大便拉在裤子上的小孩,对那种完美心生反感 ;他醉酒,在地上打滚而且瞎蹦乱跳,因此,是一次永恒的对峙。”
“这是一场高傲的理性偶像(与唯美主义相结合)和本能、无拘无束的直觉之战。”
“总之,这是人的两种心态 :往上和往下的推力,截然不同,彼此分离。”[4]
就两者而言,费里尼是偏爱“奥古斯都”的,因其率性而为、张扬恣肆,彰显着自由与不受意识形态规驯的处事哲学。然而人只有戴上人格面具,才能够扮演社会所要求的角色,而“白面小丑”恰好就是这样一种类型:一方面他们受到意识形态制约,在人格面具的笼罩下几乎无一例外采取了自我阉割;另一方面,当他们无法达到社会预期,其内心评价便会受到重创,或自卑、或自责,其采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要么倾尽全力寻求突破,要么龟缩壳内逃避厌世,无论何种措施,总会引发出孤独无力以及无法沟通之感受。费里尼敏锐的捕捉到了人格面具装卸之间的戏剧性,可以说他所理解的世界,恰好如马戏团一样,在表演时同社会人一样都带有面具,少量的“奥古斯都”担当丑角的配置,与“白面小丑”形成尖锐对立,而卸下面具之后的空虚、混乱、无助、孤寂才是生活本身。难怪很多人评论说费里尼的作品,总洋溢着某种忧伤与不甘。
费里尼的影像基本上延续了其对小丑世界——现实世界之间暧昧关系的探讨,如果说他的《大路》和《卡比利亚之夜》描述了置身于“白面小丑”秩序之中的“奥古斯都”的痛苦与解脱,那么《八部半》则将摄影机对准了“白面小丑”的精神难题——基多,就是这样一个不愉快的“白面小丑”,他的自我价值在事业与生活当中都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他既无法满足社会对自己的预期,拍出让人满意的作品;又无法在生活中得到认同(无论是妻子还是情人,甚至暧昧的女演员其实都并不需要作为个体的自己)——情人用肉体换取利益,妻子对婚姻的绝望,女演员只关心在片中的角色等。作为一个不称心如意的“白面小丑”,基多既无人理解,又缺乏或疲于沟通,他与外界的关系,在喧嚣热闹的表面之下只剩下孤独与陌生。面对现实,他的策略是粗暴而荒诞的幻想,对生活中的女性、朋友以及家人;对工作中的同事;甚至对代表着神圣的宗教群体进行肆意的嘲弄和讽刺,龟缩在自己想象的空间里舔舐伤口,既显得无奈与可悲,又变得可恨与无耻。而这一切看似荒谬的行为,实则符合了基多这类知识分子面临困窘时所采取的方式,费里尼遵循内心现实,撕开早已破败的遮羞布,将人们内心的逃避与厌世、倔强与焦躁、粗鄙与懦弱统统展现于荧幕之上。
《八部半》令人着迷之处,还在于它通过对电影这一媒介所进行的探讨,表达出费里尼眼里的真实。众所周知,电影于传统好莱坞,是一个造梦的工具,满足观众的感官欲望即是满足了电影的商业价值;而对于欧洲艺术家来讲,他们似乎更习惯于将电影看作是表达自我奇思妙想与艺术理念的方式,观众的理解与电影本身的商业价值相对来说并非最为重要。然而“梦”或者“幻想”或者“意识”本身的含义,对于艺术家们,正如同“一千个读者,则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究竟物质的现实与意识的现实相比较,谁最趋近于真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显然,对于费里尼来讲,电影即便是造梦,也源于对个体的自我认知,所造的是最为贴近人类本心、最为原始坦荡的梦境——梦这对他而言是最真实的存在,“梦是一种由影像构成的语言,再也没有什么比梦更真实的了,因为梦拒绝被明白地断言出来一一梦采用象征的表达手法,并不作明确的意念陈述,所有的梦里出现的东西,每一种颜色、每个细节……都有所指涉”。[5]费里尼眼中的“梦”不仅是一次次奇妙而新鲜的探险,它甚至还充当了电影脚本的角色——正如费里尼所执导的梦境电影热烈而夸张,《八部半》中的导演基多也一心想要拍出伟大而富有深意的电影,然而这难以逾越的鸿沟最终止于其精神难产。在此片中,基多的梦境与现实相互交替游走,既有迹可循又凸显张力,沉浸在基多的梦境当中,其意象能够给子我们最真实的感觉:为创作障碍而饱受焦灼之苦;对不可控制的两性关系而感到恐惧;为缪斯女神的出现而倍感欣喜,却又因为其现实当中的势力而感到幻想的破灭……莫名交织的复杂感受都是真实的,尽管这些感觉瞬息万变,但却阻止不了它的切肤性。电影是表达梦的最为有力直接的工具,因此这些皆源于他对“梦”的真实性以及其力量的强调的看法,体现出他对感性直觉的狂热以及其对自我认知的执着。
费里尼让摄影机直接闯入人的精神世界,探讨人的内心的可视性,由此奠定了他特有的现实主义风格——以超现实手法描绘心理现实,正如挖掘掩埋在海面之下的巨大冰山,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延伸至意识的层面。是对新现实主义创造性的继承与发扬,是一种升华和超越,而非背叛。
参考文献:
[1] 彼罗·涅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道路[J].世界电影,1957(11):92-94.
[2] 罗伊·阿米斯,沈善. 二十年后回顾意大利新现实主义[J].电影艺术译丛,1980(4):163-176.
[3] 黄式宪. 《世界电影鉴赏辞典》条目选登(三)——8 1/2[J].电影评介,1990(10):24-26.
[4] 费里尼.我是说谎者——费里尼的笔记 [M].倪安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163-164.
[5] (美)夏洛特·钱德勒.我,费里尼口述自传[M].黄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15.
[责任编辑范藻]
收稿日期:2016-01-20
作者简介:王卓尔(1984—),女,四川达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影视评论与跨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248(2016)04-0114-04
The Voice from Hearts: Realism Implied in 81/2
WANG Zhuoer
(Film Academy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Federico Fellini, Ernst Ingmar Bergman, and Andrei Tarkovsky are called the “Holy Trinity” of the modern film, who have represented the peak of European film and greatly influenced on the world film since 1960s. 81/2(1963) by Fellini is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film style of surrealism to present psychological realism, which focuses on the inner worl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talian new realism.
Key words:Federico Fellini; 81/2; new realism; re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