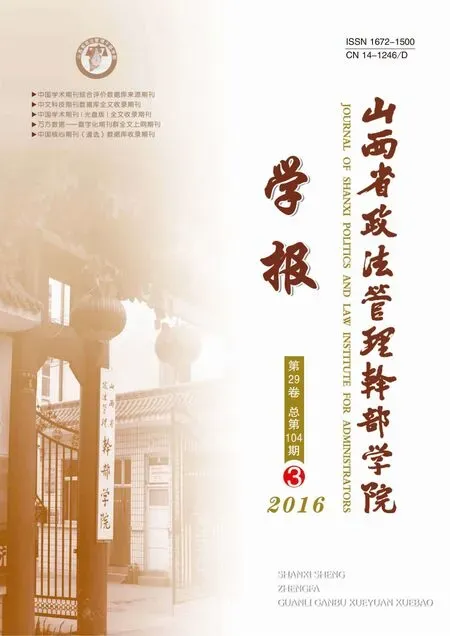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完整性的再阐释
2016-04-12韩晗
韩 晗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刑事法学论坛】
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完整性的再阐释
韩 晗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自出台至今已十年有余,学界对该项制度的理解也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对域外经验的借鉴也让该项制度获得了广泛认可,学界对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完整性也形成了以全程性(不得选择性录制)和录音录像资料与相关讯问笔录的同步性为主要内容的狭义理解,这反映了学界现有理解的局限性,因而有必要将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完整性置于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生活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理解,并辅之以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确理解,方能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讯问;全程录音录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5年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姜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进展及成效等方面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会上表示:“对重大案件全面实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并逐步扩大询问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最终实现对所有刑事案件的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1]此番表态一出,引发了学界热议。实际上,对于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讨论由来已久,官方从较早之前已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与尝试,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而2012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则在第一百二十一条中正式规定了侦查讯问的录音录像制度,其中强调“录音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对于刑事诉讼的发展而言,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确立和推行是一项伟大的进步,笔者看来,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核心是录音录像的完整性,完整性保证了该制度的生命力。因而,对于完整性理解的正确与否则是该制度发挥效能的关键所在。
一、对全程录音录像完整性的理解
目前,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对全程录音录像完整性的理解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于全程录音录像完整性的狭义理解,即全程性,或者称之为不得选择性录制。选择性录制主要是指“侦查机关仅仅选择有利于证明犯罪事实和讯问合法的审讯片段进行录音录像的情况下,无论公诉人员是否当庭播放录音录像资料,辩护方都难以通过录音录像来发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线索或者证据。”[2]这是最传统意义上违反完整性的行为,在此种情形下,录制出的音像资料是不具备连续性的,换言之,从讯问伊始至讯问结束,在此期间存在着“内容黑洞”。比如,在广东吴某某,康某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案中,黄某某的辩护人曾提出“本案讯问过程只有部分录音录像,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的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规定。”*取自《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刑一终字第223号。在此情形下,丢失部分*对于黄仕华的辩护人提出公安机关应依法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意见,经查,龙川县公安局缉毒大队于2015年6月3日出具情况说明称,时因公安局办案中心的电脑中病毒关系,本案部分审讯视频资料损坏,后派出专业电脑技术员拟再提取原来的视频资料,确认原损坏的视频实无法恢复,以致无法补充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的时间段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录音录像的完整性还体现在录音录像资料与相关讯问笔录的同步性。该问题在当前虽然不是最突出的的问题,但也时常被学者指出,而且,在实务中也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在刑事案件的辩护中也出现过因为存在“录像与供述笔录形成时间不同步”、“篇幅不相符合”等情形,而要求排除相关供述的辩护意见,比如,贵州王某受贿案中,被告人王某上诉称只进行过的两次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的部分内容无法一一对应,以此主张应依法予以排除。再如,在河南省安阳市常某某受贿案中,辩方指出“数次书面笔录内容篇幅较长,而录像形成时间较短,且在短期的录像时间内,基本上没有记录人的同步记录的行为动作,认为同步录音录像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排除。”*《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殷刑重字第3号。而对于此项辩护意见,控方也仅仅以“由于笔录中很多关于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信息,比如个人情况、工作简历,工作职责等信息都是事先在电脑中打好的,且这些信息就要占到很大篇幅”*《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殷刑重字第3号。进行回应,但这种回应依旧无法清晰划分出犯罪嫌疑人供述和办案人员事先准备好的文字间的区别,更无法解释为何基本上没有同步记录的行为动作这一质疑。
上述两个方面是目前学界对全程录音录像完整性的主要理解,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也确实是目前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所要亟待解决的,但上述理解更多的可视为对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完整性的狭义理解。因为无论是“不得选择性录制”,还是“确保录音录像资料与相关讯问笔录的同步性”,都是单纯从录音录像本身出发,以“讯问”为视角的理解,并没有放到整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大背景下来理解,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个更广义的理解。
二、对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完整性狭义理解的局限性
对全程录音录像完整性的狭义理解不能够完全阐释录音录像制度的内涵意义,由此而产生的针对性的方法也不能完全解决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在实践中出现的困窘。对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狭义理解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一致,根据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的前两项之规定:“讯问被告,应全程连续录音;必要时,并应全程连续录影。但有紧急情况且经记明笔录者,不在此限。笔录内所载之被告陈述与录音或录影之内容不符者,除有前项但书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为证据。”但却忽视了大陆在实践层面上的特点,根据目前的法律和司法实践,除了讯问聋、哑犯罪嫌疑人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会对侦查机关的讯问形成一定程度的限制外,其他情况下,侦查机关完全控制了讯问程序。在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办案人员在讯问开始之前便通过讯问技巧、策略,或者是引诱欺骗,甚至是刑讯逼供等方式迫使犯罪嫌疑人在录制音像资料时按照办案人员预想的内容进行录制,这样录制出的音像资料是完全能够符合对全程录音录像完整性狭义理解的,但这已经背离了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初衷,而且,这种“合法形式”下的证据材料反而将违法行为彻底掩盖,录音录像在实际上起到了固定言词证据以强化证明力的作用。[3]在犯罪嫌疑人未被羁押时,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采取不法行为时还有所顾忌,即便是采用也很难产生“连续多次,前后一致”的有罪供述,但当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时,上述问题则变的常见并且难以处理,因而解决问题的重点应当放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期间。
针对这些问题,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也在采取措施,如最高检于2006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技术工作流程(试行)》(下称《工作流程》)中对于讯问中录音录像的起止时间,场所选择,连续录制状态的保持,介质更换,封存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有学者也建议“原则上应当既录音又录像”;[4]坚持“录审分离”机制,严格禁止录音录像的“自录自审”;[5]“实行辩护律师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在场制”;[6]以及“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讯问录音录像程序的监督,必要时可以派员在场”[7]等等举措。但这些举措还是局限在“录音录像”的形式层面,都无法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骗供、诱供以及刑讯逼供后再录制音像资料的问题。
三、对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完整性的重新理解
2006年1月17日在浙江宁波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现场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提出了实行讯问录音录像有利于固定关键证据;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和诬告办案干警;有利于通过再现审讯过程,从中研究寻找新的案件突破口的四个优点。[8]由此可知,之所以建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归根结底是为了减少控辩双方的“诉讼麻烦”,提高诉讼效率。当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因讯问时办案人员是否有违法行为而各执一词且相持不下之时,录音录像作为关键证据的出现可以使双方定纷止争,从而使得庭审得以顺利推进。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既可以满足控方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和诬告的需求,“当人犯咬定自己的权利受到了各种方式的侵害,供词不是自己自愿所作,或审讯员在审讯过程中有违法的和不正当的行为时,录音和录像都可以有效地用作证据,驳斥其翻供和狡赖行为”。[9]同时也可以满足犯罪嫌疑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制作以及作为证据在庭审过程中进行质证会促使司法权力规范行使,使犯罪嫌疑人人权得到更好地维护”。[10]正因如此,该制度成为了平衡控辩双方力量的重要保证。
但该制度实现减少控辩双方的“诉讼麻烦”,并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实现是建立在录音录像能够真实地反映讯问情况和结果的基础之上,而录音录像的“真实性”来自于其“完整性”,换言之,对录音录像“完整性”理解和适用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了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在实践中的成败。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当前国内对“完整性”的理解还仅限于狭义层面,故而在制度设计时就会产生“先天缺陷”,即制度仅着眼于录音录像形成的本身,而未能从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大背景下去进行制度设计。
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期间,羁押场所对其生活进行全面的监控,这其中也包括了对其被讯问生活的监控,换言之,羁押期间犯罪嫌疑人的被讯问生活与其他时段的生活只有保持着紧密的衔接时才能认为犯罪嫌疑人这段被羁押的经历是完整的。不能单纯和孤立的看待对犯罪嫌疑人的录音录像,而且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来看,部分之与整体的效用在于部分自身的完整性以及能够与整体完美衔接发挥效能。对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完整性的正确理解或者是广义理解就应该放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生活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理解,那就是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完整性不仅仅包括上述所说的全程性,或者称之为不得选择性录制和录音录像资料与相关讯问笔录的同步性,还应当具有“衔接性”,即羁押期间犯罪嫌疑人的被讯问所形成的音像资料的起止时间和长度应当与其他时段的被监控生活的相关资料相互衔接,无“时间空挡”。如何理解“衔接性”呢?比如说,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于看守所内,监区监控显示某日上午9时被带至讯问室进行讯问,10点被带回休息区,其间进行了录音,但录音时间只有40分钟,并无设备损坏、介质更换情况的记录,中间有20分钟的时间空挡;或者,监控显示犯罪嫌疑人上午9时被带入讯问室,但录像开始时间显示为9点15分,此处出现了15分钟的时间空挡。在诸如此类情形下,这段时间空挡内发生的事情便会陷入“罗生门”的境地。比如,发生在湖北的廖某某贪污、受贿罪案,廖某某的辩护人对检察机关提供的2010年6月11日、6月18日、7月7日对廖某某的录音录像严重违反程序规定。因为根据鄂州反贪押(2010)08号《提押证》显示,侦查人员于2010年6月14日提解廖来生,同月17日16时0分才还押;2010年7月1日17时30分提解廖来生,同月5日7时10分才还押。侦查人员提解廖来生的上述行为明显违背”不得超过12小时”的规定,但其间所做的讯问笔录没有超过12小时。对于这种情况,鄂州市检察院解释称“在检察机关办案区讯问犯罪嫌疑人,没有对讯问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只是违反了检察机关内部的办案规定,但并不违反当时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当然不是非法证据。即使该部分证据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部分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鄂刑二抗字第00004号。但法院最终没有采信控方说法。
四、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衔接性”的适用
在对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完整性进行了重新阐释后,我们还要正视的问题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难适用,即便是控方提交的录音录像材料存在着选择性录制,不同步以及无法衔接的问题,实践中,只要控方进行解释,法院基本都会采纳,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案件,在讯问中采用录音录像的案件中,相当一部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了对录音录像证据资格的怀疑,但这种质疑基本上没有被法庭采纳,即便是采纳,也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似的将相关部分排除,很少会将整个的录音录像材料排除的,比如,前述的贵州王某受贿案,针对王某的主张,法院最终认为“对讯问笔录个别内容与同步录音录像不一致的部分,由于不影响该讯问笔录的真实性,对讯问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内容相一致部分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是定案证据,不一致部分不予采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黔高刑二终字第7号。再如前述的广东吴某某,康某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案,其中的部分录音录像存在遗失,对此,控方辩称“因公安局办案中心的电脑中病毒关系,本案部分审讯视频资料损坏,后派出专业电脑技术员拟再提取原来的视频资料,确认原损坏的视频实无法恢复,以致无法补充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最终法院予以采信。
对于这种情况,有学者认为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的问题,认为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扩大,将录音录像制度所面临的问题置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控制下,就可以将问题解决。笔者以为不然,这并是一个“扩容”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问题就出在我们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此处,给非法证据排除留了一个“口子”,正是这个“口子”导致了这些问题,换言之,什么是“合理解释”?怎样界定“合理解释”?这些问题都不能通过“扩容”进行解决。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法条表述是“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这一规定导致的结果有四种,即“只能予以补正”,“只能做出合理解释”,“予以补正和作出合理解释任选其一”,“予以补正和作出合理解释必须同时具备”。对于不同的证据瑕疵,应当由上述四种情况视情形而处理,不能一概而论,但是由于立法技术的粗糙,以及司法证据实践水平的局限,往往一概而论,正是这种粗糙的理解使得上述案例中的瑕疵证据在作出了所谓的“合理解释后”便被法庭采信,在实践中就形成了所谓的“自由裁量的不排除规则”。[11]
有鉴于此,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录音录像的性质,笔者无意在此讨论录音录像的证据类型,但无论何种类型,都应当关注到录音录像的客观性是各类证据中最突出的,换言之,对于录音录像不完整的部分只能进行补正,不可以要求解释的,如果不补正,只进行解释,那无论如何去解释也都弥补不了不完整的部分。换言之,如果补正不了,那就应当直接进行非法证据排除,对录音录像证据的瑕疵而言,是不能进行解释的。只有这样,具备广义完整性的录音录像制度才能在实践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1]邹春霞.公安部:刑事案件询问全程将录音录像[N].北京青年报,2015-09-22(4).
[2]王 超.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异化——以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选择性录制与播放为视角[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3]彭志敏.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若干问题探析[J].人民检察,2006(6)上.
[4]沈德咏,何艳芳.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科学构建[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2).
[5]董 坤.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发展路径[J].法学研究,2015(6).
[6]王金华.论侦查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完善[J].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
[7]金 鑫.普通刑案讯问录音录像有待规范[N].检察日报,2012-02-15.
[8]我国检察机关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将全程录像—华律网[EB/OL].http://news.66law.cn/archive/4976.html,2006-01-18/2016-02-10.
[9][美]阿瑟S·奥布里、鲁道夫R·坎普托.刑事审讯[M].但彦铮,杜 军,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0]潘申明,魏修臣.从规范执法到诉讼证据——以检察机关侦查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为视角[J].证据科学,2012(20).
[11]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李麦娣)
2016-06-26
韩 晗(1992-),男,山东潍坊人,山东大学法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DF73
A
1672-1500(2016)03-008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