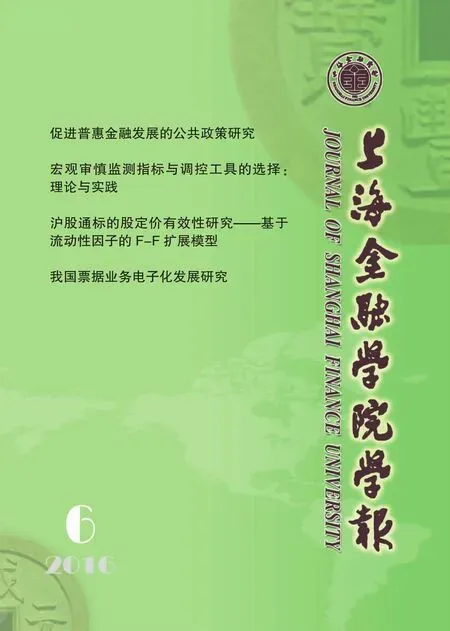后SDR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的审慎评估与演进逻辑
2016-04-11陈鸿祥
陈鸿祥
(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江苏盐城224001)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诱因
综合国力今非昔比成为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单一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缺陷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诱因。不同禀赋货币赋予多元化市场选择,人民币国际化缓解国际货币体制桎梏、制约货币霸权和单边独裁。
(一)中国货币政策陷入“囚徒困境”
追溯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采取盯住美元联系汇率制度,人民币“搭便车”(美元贬值周期)策略、叠加劳动力人口红利,中国制造业赢得出口“黄金期”,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峰值4万亿)、美元持续贬值呈现反向变动,中国货币当局喜忧参半、备受困扰。一方面,遭遇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陷入外汇储备贬值(购买力损耗)、输出人民币升值的斯蒂格利茨“资本循环怪圈”;呈现“巨额外汇储备、狭窄投资渠道(购买2-3%收益率美国国债)”“不成熟债权国”特征,与资金要素禀赋背道而驰(余永定,2015)。另一方面,超量外汇储备通过外汇占款渠道造成基础货币被动超发,流动性泛滥、房地产泡沫。冲销基础货币成为“次优选择”:一是行政化冲销,提高法定准备金(20%)、限制正规金融媒介,催生难以监管“影子银行”体系;二是市场化冲销,公开市场发行央行票据(高息)减少流动性过剩,“完全清洁”冲销难度加大,市场利率产生上涨压力,吸引更多热钱。
(二)美元发行激励约束机制不相容
美联储扮演“全球银行”角色,新兴市场缴纳“铸币税”成为无形“枷锁”。1971年牙买加体系后美元独霸国际货币体系,绝大多数经济体丧失国际货币选择权,脱钩黄金的美元发行机制没有硬性约束(“嚣张特权”),借助浮动汇率机制安排、主宰全球财富再分配。美联储鉴于美国利益(贸易逆差、财政赤字)相机抉择,实施量化宽松(QE)稀释美元债务、发行国债低成本募集资金。尤其采用盯住汇率制的新兴市场增持美元资产“自我保险”,成“击鼓传花”最后一棒。新兴市场的金融市场欠发达(缺乏信用基础)、货币错配(贸易顺差积累美元)、汇率水平高估等结构性缺陷,贸然开放资本账户后,一旦遭遇汇率波动和投机冲击,内在脆弱性暴露无遗。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审慎评估
2009年7月,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崛起意味着欧元诞生后美元流通市场再次萎缩,引发隐性货币战争。当前处于经常项目跨境贸易、审慎开放资本项目和有序扩大离岸市场的叠加期,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予以审慎评估。
(一)综合实力仍有差距,出口贸易优势递减
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似乎“富可敌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6,徘徊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城乡、地区间结构性贫富差异面临“从欧洲到非洲”的尴尬局面。短期内“经济大国”跨越“经济强国”并不现实,难以支撑重要经济体选择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币种。庞大经济规模依赖资源消耗、劳动密集型粗放式发展,劳动力人口迎来“刘易斯拐点”,低端产业面临越南、缅甸、柬埔寨及非洲等低成本竞争替代。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50%以上、徘徊在全球工业价值链低端,缺乏计价货币选择权、面临转嫁汇率波动风险(范小云,2015)。“跛足”跨境贸易(东南亚进口零部件、终端产品出口欧美)区域性结构缺陷,外贸顺差源自欧美(美元计价、结算)挤压人民币辐射范围。
(二)金融媒介碎片化,金融市场欠成熟
一是金融媒介碎片化。受制于金融垄断与行政干预,产生中国特色“金融悖论”: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嗷嗷待哺”、市场宽裕资金供应“苦寻出路”。长期依赖商业银行间接融资,金融抑制的隐性成本,中小私营企业被迫转向影子银行融资、承受高息成本及展期风险。二是债券市场步伐缓慢。中国债券融资和投资工具较少(国债主导、公司债滞后)、缺乏资产抵押债券,中央财政政策仍显保守(国债约占GDP比例20%),短期政府债券流动性较差(绝大多数购买者持有到期),债券市场容量、流动难以承接境外投资者配置。三是股票市场未能提供资本正能量。境外投资者参与市场仍有诸多限制,股票市场缺乏长期信用支撑、难以与实体经济有效互动,2015年6月股市暴跌显示中国股市远非成熟市场。
(三)资本项目审慎开放,管制效应呈现递减
资本项目开放选择性实施有限、定向的审慎性安排:一是避免利率定价机制和汇率形成机制扭曲前提下,引发跨境资本“金融攻击”、富裕阶层资本外流;二是匆忙全面放弃资本管制、追随发达国家陷入“零利率陷阱”引发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麦金农,2014)。先后注册制、备案制允许涵盖境外央行(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等逐渐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沪港通”、“深港通”实质启动、“沪伦通”渐行渐近、上海自贸区探索复制经验,推动境内外资本要素市场互联互通;全部40项资本账户(IMF分类)交易中36项全部或部分可兑换,通过QDII和QFII等对短期跨境资本的市场准入和额度控制,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信托、衍生工具等处于管制状态。非法资本流动部分隐藏在经常账户下非商品贸易渠道(预售或延迟账款、转移定价)逃避资本管制,虚假外商直接投资(FDI)(维珍群岛、开曼群岛等)规避税收。
(四)市场信用基础缺失,西方渗透信用评级机制
金融市场对外资、民资准入限制,中国特色的金融垄断及行政干预,商业金融的国有情结、国企偏好,鼓励低效投资(产能过剩)、信贷贩卖的腐败行为,软预算约束的国企挤占推高社会融资及生产要素,形成国内储蓄过剩背景下的利率畸高、资金“出口转内销”现象,高杠杆经济缺失市场信用基础,金融领域充斥坑蒙欺诈 “庞氏骗局”(潘英丽,2015),政府信用诱发金融风险转嫁国家,1985-1997、1997-2006年被迫实施商业银行、股票市场的功能财政化。美国主导的穆迪、惠誉、标普等西方评级机构运用股权或技术合作,毫无障碍实现对中国信用评级市场全面渗透,干扰宏观调控政策话语权、歪曲金融资产定价权。
(五)加大金融统计监测难度,削弱货币政策调控效应
一是加大金融统计监测难度。缺乏人民币跨境流动统计方法、监测制度,精确统计跨境资金流通数据、边境贸易人民币现钞结算,尤其是高报出口、记“错误遗漏”账等并不现实。二是削弱货币政策调控效应。伴随着金融脱媒加速,境外(离岸)人民币需求难以预测,数量型调控工具(准备金、信贷额度等)以及M2中介目标有效性下降;汇率和利率预期变化驱使国际投机资本跨境流动,债券市场配给机制、价格管制手段受到显著干扰,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削弱、外溢性增强。
(六)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休眠”状态
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旨在危机期间提供流动性支持,助力人民币计价、结算及储备功能。截止201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与 36个央行(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3.3万亿人民币)、与20个国家(地区)签署人民币清算安排合作备忘录。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对象大多数是发展中新兴市场,侧重央行总额结算(限制单笔交易功能)、协议期限短(均为3年)、双边互换限制(尚未自由使用)(王国刚,2014),尤其多数协议停留纸面形式。例如与韩国、阿根廷等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危机时刻人民币没有派上用场。美联储、欧洲央行签订多边货币互换协议基本是OECD成员国,美联储与新兴市场(巴西、墨西哥、韩国和新加坡)多边货币互换实质性交易,对崛起人民币产生“掣肘”效应。
(七)离岸市场呈现“非均衡性”
离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双轨制”下减缓投机资本跨境冲击、释放资本账户开放风险的次优选择。人民币离岸市场多集中香港(政治地缘优势)、新加坡(东盟贸易渠道)和伦敦(全球金融市场),尚未覆盖纽约、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一是离岸市场人民币计价产品深度不够,香港离岸市场停留在传统的存贷款、国际结算,存贷款结构、基础产品与衍生产品之间结构失衡,难以体外循环的短期人民币产品极易冲击在岸市场。二是自由定价的离岸市场与干预管制的在岸市场,价格双轨制(CNH、CNY)催生跨境无风险套利套汇,香港实行联系美元汇率制度,内地利率水平受到管制扭曲,诱发内地企业避开境内融资监管约束,到香港离岸市场获得商业贷款或债券融资。
(八)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基础薄弱
东南亚金融危机刺激“10(东盟)+3(中日韩)”启动《清迈倡议》(CMIM)框架下区域货币互换网络(去美元化),旨在区域内短期流动性保障体系、初现“人民币圈”雏形。根据蒙代尔“金融稳定性三岛”(欧元、美元、亚元),亚洲国家政治体制、发展水平及宗教信仰差异,缺乏区域金融合作、货币联盟的战略认同。亚洲货币联盟意味着让渡“经济主权”、主权货币消亡,尚未形成亚洲自贸区(FTA)的“最优货币区”条件,“亚元”面临诸多预估难题。人民币和日元充当亚洲主导货币竞争分歧与日俱增,东京金融中心阻滞人民币承担亚洲区域计价、结算货币。东亚地缘政治矛盾挤压“10+3”机制,货币合作机制艰难博弈、呈现“制度过剩”。
(九)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蓄意瓦解
人民币国际化触动美国霸权利益,美国抱着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企图将人民币国际化“扼杀腹中”。一方面,美国智库彼得森推演人民币崛起地缘空间是东南亚,太平洋战区(覆盖中国90%外贸、投资通道)骤然紧张: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激化朝鲜半岛矛盾、挑起东海南海主权争端,利用安全诱饵瓦解中日货币合作、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中澳自贸区,亚太“小伙伴”与人民币离岸市场渐行渐远;另一方面,新一轮政治经济联盟强化美元体系根基,相继开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项谈判。
(十)缺乏约束性国际治理与协调机制
G7代表发达国家垄断全球货币治理权,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冲击G7合法性。IMF缺乏有效最终贷款人机制,亚洲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IMF在救援时效性不足、附加诸多苛刻条件。IMF在修改协定、调整份额等重大事项必须85%以上加权投票,美国(16.76%)、欧盟(30%)均拥有一票否决权,新兴市场国家缺乏国际货币体系话语权和公平参与权。IMF缺乏强制性治理规则、阻滞实质性改革,人民币加入SDR让渡额度是欧元、英镑和日元,美元对SDR分配主导权没有受到影响。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演进逻辑
当前,美国全球政治经济基础并未根本性动摇、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具备颠覆美元霸权的技术条件,中国综合实力尚未取得压倒性优势。全球货币重复博弈最终源自市场选择,在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夯实微观经济基础前提下,随着综合实力消长,逐步稀释“美元霸权”、迎来美元“网络惯性”拐点,最终破解“劣币驱除良币”的“格雷欣定律”。
(一)夯实微观经济基础,释放“熊彼德”内在动力
在欧美“再工业化”、“工业4.0”及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夹击背景下,我国应实施“制造2025”、“互联网+”战略,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升级资本技术型高端产业,中国商品留住国内消费者、吸引国外消费者,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微观经济创新活力,出清低端过剩产能、重现高端优质产能,供给、需求更高层次匹配,是提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环节;破除约束生产力的结构性、体制性痼疾束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围绕“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智能转型”,释放经济潜在增长“熊彼德”内在动力。
(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构建金融监管生态系统
一是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避免货币政策赋予派生功能、干扰基础目标—价格(含汇率)稳定,注重总量调控和结构性工具并重,传统工具(利率、存款准备金)、新型工具(SLO、SLF、MLF、PSL)灵活搭配,熨平流动性波动,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有效沟通及预期管理①等等。二是构建金融监管生态系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赋予民营、外资平等准入待遇,建立分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缓解弱势群体融资难题;金融监管协调匹配,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避免金融混业经营的监管真空;从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计提等方面抑制金融顺周期效应;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引入市场化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存款保险制度,控制局部“尾部风险”,避免不良贷款政府全额埋单。
(三)退出常态式市场干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根据蒙代尔“三元悖论”,浮动汇率机制成为现实选择,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前提条件。适时退出常态式市场干预,强制结汇制转为意愿结汇制,矫正扭曲汇率形成机制;构建“蛇形浮动汇率走廊”,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避免跳跃式、断崖式震荡,按照市场供求机制“清洁”浮动;有序退出“盯住”美元制度,根据13种外币权重(美元26.4%、欧元21.4%、日元14.7%)加权计算人民币汇率指数(CFETS),引导市场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浮动汇率;适时推出“外汇平准基金”,借鉴美国“汇率稳定基金”、日本“外汇基金特别账户”的经验做法,平抑外汇市场异常波动。
(四)完善金融市场功能,构筑市场信用基础
投资目标多元化、投资期限差异性的融资工具削弱金融市场“羊群效应”。发挥股票市场“晴雨表”功能,完善证券交易所股权融资功能,规范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区域性股权市场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保护散户投资者合法权益。健全债券市场发行交易制度,扩大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丰富政府债券期限结构,统一银行间、交易所债券市场。强化市场利率定价自律,健全Shibor基准利率,反映流动性偏好与风险溢价的收益率曲线。丰富金融衍生品工具,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扩容离岸市场风险对冲工具和套期保值产品,探索开展利率互换、货币互换、NDF、远期合约、保理和福费廷等。完善信用评级体系、构筑人民币信誉屏障,健全本土信用评级机构、避免西方评级机构垄断市场,发布特定货币评级结果的信用评级机构必须符合国际标准(IOSCO条款)。
(五)审慎放松资本项目管制,稳健推进金融交易自由兑换
确保真实贸易或投资背景的人民币跨境流动,减少资产配置的制度摩擦和交易成本(彭兴韵,2015)。美联储加息、欧债危机背景下新兴市场流动性紧缺,为人民币输出提供契机,在印度、越南等(劳动力低成本)创设境外产业园;有序拓展 QFII、QDII、RQFII、RQDII的参与主体、投资范围和额度限制,实现跨境证券投资审批制为注册制;逐步解除QDII、QFII跨境股票、债券、基金投资限制,推出QDII2满足境内居民全球化资产配置;扩大境外机构发行人民币“熊猫债”规模,获得的资本利得及利息收入实行税收优惠,鼓励人民币债券成为境外官方储备。有序扩大CIPS业务容量、运行时区和服务功能,提供覆盖全球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净额清算;加强跨境流动性统计监测,选择若干反映人民币跨境异常性流动的预警指标,运用大数据技术实施动态监控(尤其往返境内外资本市场);构筑跨境套利“防火墙”,采取价格工具(征收“托宾税”、远期购汇保证金、存款准备金等)、列出负面清单(居民外汇兑换、流入资金存留期限、短期资本账户管制、特殊审查制度等)。
(六)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推动双边本币互换常态化
培育、完善上海自贸试验区(人民币贷款)、香港离岸市场(企业债券)、伦敦金融中心(主权债券)分工机制;加速离岸市场人民币衍生与循环,活跃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相当数量人民币供需自行对冲,避免干扰在岸市场汇率;美元贷款利率参照Libor源于马歇尔计划的欧洲美元市场“网络惯性”,人民币定价权具有相似演变路径,避免旁落香港、伦敦或新加坡等离岸市场(乔依德,2014)。扩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含展期、续签)数量与规模,推动互换协议下人民币实质性使用,尤其外储大国相互增持对方货币作为储备,选择性引导部分货币与人民币挂钩、或者纳入一篮子参考货币。
(七)大幅增加黄金储备,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功能
黄金储备没有刻上“主权”铬印、发挥着隐性担保作用。中国外汇储备中约10%是IMF储备头寸、SDR及黄金,黄金储备仅占1.8%(美国72%、德国66%)。利用国际市场黄金、大宗商品价格低迷时机,持续增持黄金、石油等战略储备,“央行购金”、“藏金于民”并重。作为大宗商品(石油、铁矿石)最大净进口国,人民币定价权占据更大优势。加强与中东、北非及俄罗斯等产油国战略对话,签订人民币贷款换石油、“人民币—石油”交易结算等协议;实现澳大利亚大宗商品(铁矿石)人民币计价战略突破,等等。
(八)借助国际多边框架机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推动G20(多边机制)取代G7(美国主导)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借助巴塞尔委员会(BCB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获取国际金融准则制定参与权。实质性重组IMF、世界银行(WB)治理架构和份额分配,在SDR基础上创建超主权货币,增强IMF发行独立性、提升SDR价值稳定性,涵盖主要经济体、降低美元权重(遏制单边行动);大幅增加SDR发行规模,为SDR、美元资产渐进兑换创造条件;SDR仅限成员国或国际组织偿还IMF贷款或国际收支逆差,拓宽SDR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与资本流动中计价、结算与储备功能。
(九)构筑区域性制度保障,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一是构筑区域性制度保障。“一带一路”战略契合欧亚新兴市场经济体产业结构互补性,推动政治文化交流、弥补意识形态差异,衍生境外人民币交易动机,培育人民币黏性需求;借助亚投行(AIIB)、金砖银行(BRICS DB)、丝路基金(SRF)等区域性多边性安排(除美国、日本),提升人民币持币意愿、拓展“人民币圈”。二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遵循“互惠共赢”取代“丛林法则”,与周边邻国捐弃前嫌、双边谈判合作,避免美国借助东盟“敲诈”中国;实质性提升国防现代化,尤其加大尖端军事科技投入与研发能力,对破坏亚洲自贸协定、东亚货币联盟(人民币核心)的霸权行为形成震慑。
注释:
① “8.11汇改”校正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技术回调”,央行操作不透明引发“单边贬值”预期,引发境外投资者减持人民币的“羊群效应”,央行被迫实施收紧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组合拳”,香港隔夜拆借利率(Hibor)飙升。
[1]余永定.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之辩[Z].东方出版社,2016,(1).
[2]彭兴韵.人民币国际化功夫在SDR之外[N].上海证券报,2015.12.1.
[3]潘英丽.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误区[N].金融时报,2015.3.11.
[4]范小云,王道平.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至关重要[J].南开学报,2015,(1).
[5]王国刚.人民币国际化的冷思考[J].国际金融研究,2014,(4).
[6]罗纳德·麦金农.中国汇率、金融抑制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冲突[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3).
[7]乔依德,葛佳飞.人民币国际化: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互动[J].国际经济评论,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