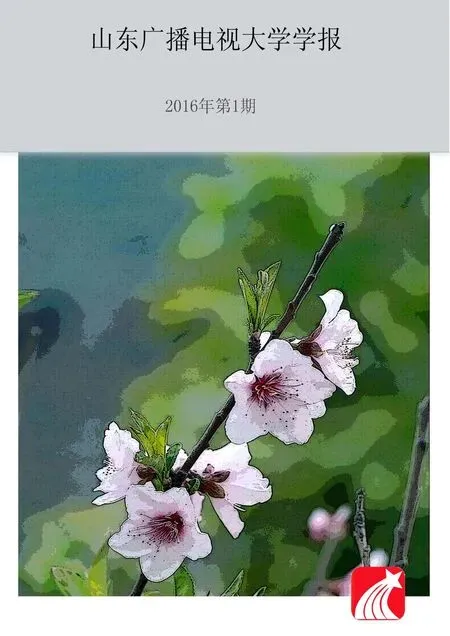身体的二重异化
2016-04-04弓依静
弓依静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身体的二重异化
弓依静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摘要:现代社会中,技术所陷的悖论诱发作为主体的人在身体解放浪潮中自我的迷失。身体在消费时代下获得高度关注的同时,也令其自身在感性泛滥中沦为欲望享乐的商业之地。身体美学的内涵被大众文化的导向力量颠覆,身体的异化成为引发人们深思的导火索。
关键词:身体美学;感性;异化;快感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球村模式的开启,当西方理论、西方文化汹涌而袭,起初我们以睁眼看世界的新奇满怀期待,一切在拿来主义的支配下全部接受。思想资源大幅更新,我们用所谓西方最前沿的理论系统释过去,观未来,既受惠于斯也局限于斯。西方文化同质论下,身体美学与感性也在不断衍化,甚至出现了异化。
一、解放与束缚:技术所陷的悖论
全球化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技术的不断更新。自第一次工业革命,瓦特改良型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珍妮纺纱机的投入使用,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就已被开启。人类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下缔造了辉煌而庞大的工业文明,滞慢的生活状态、贫乏的文化活动迅速的成为了过去式。作为主体的身体再也不用以繁重的体力投入来换取生存的资本。现代化工厂、智能型机器、大设备的一体化运行,使人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解放,从最初“手”的解放到如今“身体”的解放,技术在尽可能地减轻社会从外在给予人身体的负重,提供一种轻松的工作环境,延伸为高质量的现代生活。
但,这种美其名曰“解放”的技术成果,表面上是人在支配技术,可反过来技术也在插足着人的生活。每一次技术的更新都要求人的无条件配合,似乎在技术的进步与人的适应这两种双向循环下,人被技术不断的催赶,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技术主宰了人。对技术的依赖和迁就造成了由人所创造的物反过来却在奴役着人的局面。劳动者角色下的人“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1],催生为主体的压抑和身心的背离。机械制造时代更多的是将人与社会群体分隔,每个人终会成为单个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单元。“通过劳动分工维持的自我生存过程越是扩展,就越是强烈地迫使个人按照技术结构来塑造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作为主体性自身的先验自我最终被抛弃了,并被自动化机器的有序运转所代替”[2]。因而,商品生产中,人和机器的价值是相近,快捷、精准、不带思考的习惯性动作占据了主要,这一点也正是工业进程必然的客观要求,即“在社会客观运转面前,人的主体的东西恰恰是无关紧要和有害的,所以人必须被量化为客观要素以便具有可计算性、可操作性”[3]。机械复制的方式取代了主体的创造性实践,“人们不仅远离了自然,而且彼此间也完全疏离开来。人与人之间不再具有真诚,个人也就变成了彼此分离的孤独的社会原子,即使人本身也出现了精神的物化。因此,所有人都只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他们要做什么。每个人都变成了一种材料,他可能是某种实践的主体或者客体,也可能某种不值一提的东西。在工业文明中,为了适应现代工业体系对个人提出的越来越普通的要求,为了能维持自身生存而不至于成为无用的人,包括未经训练的失业者和非熟练工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更加物化。在这里,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本身出现了极度异化”[4]。
人作用于技术上的力在推动社会运转中所表现的的合理性都在人与技术无限循环式的不合理性中消失殆尽。“人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质世界。人建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机器来管理他建立起来的技术机器,但人的全部创造物都高于他的控制。他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创造者和中枢,反而觉得自己是一个他用双手造出来的机器人的奴隶。他释放出来的力量愈是有力和巨大,他就愈感到人的软弱无能,他面对着体现在事中的自主力量,这一力量的发展脱离了他自身”[5]。于是,身体的机能不被开发,个体的情绪长期压抑,人的异化趋于明显。技术所束缚的正是身与心的自由、适意。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如今技术所束缚的正不断要求解放。
二、身体感性与快感体验的误认
身体作为沟连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在心理机制的媒介,对身体的关注就是对人作为主体的尊重。十九世纪以一切从身体出发的尼采,“重新审视一切将历史、艺术和理性都作为身体的弃取得动态产物”[6],从哲学角度视身体为权力意志,变现为生存的欲望和创造的本能,随着弗洛伊德、柏格森、福柯等人的深入研究,身体的主体性被不断发掘。九十年代,当美国实用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提“身体美学”后,身体问题或身体研究就再次获得聚焦,在其著作《实用主义》一书中提“身体美学可先暂时定义为:对一个人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环境。因此,它也致力于构成身体关怀或身体改善的知识、谈论、实践以及身体上的训练”。既而,对身体的审美欣赏和对作为感官的身体感觉、经验研究,就成了身体美学的一大任务,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压抑的激发下,感性诉求呼之欲出,身体的解放运动纷至沓来。
身体,既是个体欲望的倾泄之所,又是审美活动的实践之地,人本然的天性解放和商业运作的利益导向共同作用于赞美身体的感性表达。回首向来,往昔纷纭繁杂的历史抗争似在梦境中淡忘殆尽,文化苦旅的峥嵘岁月早已无法抗衡今日梦想之不羁力量,悠远浑厚的文化积淀在消费时代资本运行的渗透下,丧失了原有的优越感,日渐迷失于纸醉金迷的现代帝国。日渐更新的社会文化所带的不适应感以“幻”的幔帐遮蔽了人的真实存在。物的极大丰盈,成为了欲望的外在驱动力。无所顾忌的本能冲动、驰骋高原的身体奔突,以感性的方式释放被束缚已久的身体激情,获得心灵的酣畅淋漓,成为主体对身体的自觉践行。进而,身体美学、身体感性的表达呈现为以身体需求为核心的一切消费,身体的解放被身体的快乐取代,感官欲望的直接满足是其主要的特征。
自身体在感性解放的呼声下挣脱传统理性的打压后,随着关注度的持续升温,身体就迅速沦为现代商业趋利求乐的跑马场。从各种选秀活动催生的人造美女、人造美男到艺术实景创作的身体展示,人们对身体的认识一改往日的隐瞒、规避。开放的胸怀、欣赏的姿态促使身体的感性层面得到最大程度的肯定和开发。尤其是视像时代的到来,这种感性直观的强烈渴望引发对身体的无限拓展。影视娱乐中愈为盛行的视听盛宴的打造,传统模式化的舞台表演限于老套、呆板,而走向自困。炙手可热的是生活实境体验的真人秀节目,具有较高道德素养和文化积淀的老一辈艺术家被明星中的少年偶像团体抢尽了风光,成为大众追捧欢呼的焦点,“大众媒体关注的范围由以前的大众化变得越来越私密化,‘身体展示’的过度商业化,会把迎合男性欲望作为标准,并且变为消费时代欲望的符号”。在文学创作圈,也出现了“80、90美女作家”与“实力派”的划分,出现了“身体写作”的概念,卫慧、棉棉们的“身体写作”以张扬女性本能冲动的方式消费着身体与性,木子美、竹影青瞳则彻底将身体创作沦为生理欲望的宣泄,虚无的精神危机一触即发,正如杰姆逊所言“现在人们感到的不是那种可怕的孤独与焦虑,而是一种没有根、浮于表面的感觉,没有真实感,这种感觉可以变得很恐怖,但也可以很舒适”。舒适的状态恰是感性对主体欲望的蒙蔽。感性的泛滥“一方面无限制地扩张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物欲动机,‘物体’利益需要被有意识地当做人们‘自我实现’的具体条件。另一方面,又巧妙地为这种物欲及其实现掩上一层‘诗意’的审美包装,使得物欲的生物性利益在幻觉性的审美满足中取得自身独立性,成为个体实践的堂皇理由,而‘审美’在日常生活中则成了人直接占有,实现自身物欲动机的一种享乐方式,是一个驱逐了精神浪漫并呈现为经验性世俗存在的官能对象”。因而,这种在“诗意”假象下完成的感官的享乐,其本质就是虚妄的、非真实的,被卷入的身体也是徒劳的、倦怠的。
视听时代、消费时代下,眼球经济诱发和膨胀了大众的媚俗文化。王德胜先生在“当代审美文化批评视野的‘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指出“娱乐是一种低级的生理欲望,而不是高级的心理需要,与审美有关但并不是审美”,由此观照,当下的大众文化趋于娱乐,娱乐流于浮夸而渐同于恶搞式发笑,享乐主义使“回归身体”呈现为欲望宣泄的粗暴式身体表达。身体美学的狂飙激进浪潮将身体感性简单误认为身体感知。身体的审美化建构在感官机能的满足中削弱,甚至忽视了身体心理性快感所经营的情感活动,幸福的愉悦体验被压缩为瞬间快感刺激。身体的生理性体验的过度挖掘造成了感性的泛滥与理性的断连。审美认知、诗意栖居、崇高信仰的坚守、自由惬意的舒心存在,都在身体的狂欢和欲望的沉溺中化为虚无之影。身体的过度消费使其在解放之路上渐行渐远,来自快感体验的误认也让身体背负了沉重的疲惫感而止步不前,身体陷于亟待拯救的泥淖中。
三、迷失之后的反思
长期以来,美学需要突破理论的束缚,在社会进程中找到新的契合点,以充满时代精神的姿态完成美学学科的再发展。形而上的研究的虚无缥缈使美学自身发展失去生活的根基,失去大众的期待,而身体的介入恰如其分地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美学始终都围绕着“人”去探讨如何诗意的生存,以审美的价值形态和观念系统去引导完成对人格的重塑和文化素养的建构,而身体研究有效将这一目标化为现实的实践。身体的实用主义与美学对自我把握和美德的追求在直接实践中得到强化,通过对生命价值的增加,实现身体的审美潜能开发,在知行合一中走向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身体美学的理论设想,也是身体与美学在良性互动下所达到的理性与感性的平衡。
身体美学究其本质是通过心灵与躯体的和谐共处,在理性与感性互渗下达到从外而内的“心”的建构与完善。但在当下社会,“身体”被无限放大,流于形式,人们以感官享受和快感刺激企图唤醒身体的解放。于是我们仿佛走进了卡夫卡笔下的世界,每一个空无依傍的个体都在自己的“城堡”中竭力寻找人生的出口,行为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行为本身就已丧失了价值。大众文化以“变形记”的形式不断吸引着我们的眼球,刷新着我们的体验,审美疲劳与新鲜感的比拼持续升级,“饥饿艺术家”式的行为已成旧闻,“甲壳虫”式的变身也都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大众期待视野里的猎奇感趋于饱和,精神的困乏与体验的倦怠感席卷而来。终于,浮躁、空虚的价值因子让我们开始“审判”身体行为的肆意狂荡是否等同于身体美学的实践。
回顾之后的反思,让我们明白:当突然间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还来不及准备,我们就要和国际接轨;还容不得思考,外来文化就倾泄涌来。于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希望从外者那里找到自己的确证。我们在极欲追求世界的脚步时,极欲在世界格局中有立足之地时,我们好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中西方之间隐性的鸿沟具有不可逾越性,双方所谓的理解仅仅只是在双方各自认为理解基础上的理解。反过来思考,如果真的可以理解,就不会出现“对话”,至少这个词在当下是极为流行的。“对话”就是双方以表达观点的方式取得某种共识,也就意味着对话之前分歧矛盾的不可调和。当身体美学大量移植西方理论时,也就顺带移植了西方文化中不溶于中国的且具有破坏性的异质因子,一味的仿效西学必然导致失语。而习惯性对身体美学或美学的研究,我们都旨在人文精神的指引下,以“人”为中心,从审美的角度,完善人类精神的建构,塑造主体性性格,利导民族精神形态,也许正是这长久以来厚重的使命观和责任感,让这个学科的发展尤为沉重,以致在商品经济的文化带动下迅速迷失。
“我们古人预言的‘天下大同’的理想,随着‘同’的负面作用的逐渐凸显,它不再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当“野蛮笼罩”下的“天下大同”式“乌托邦想象”的假面被揭露后,我们真的要思考一下,我们只不过是中国人,世界不是我们的。全面西学的渗入除了引发身份认同的危机外还会使我们陷入更为深久的迷失。身体的解放或身体美学的实践方式也并不是依靠狂欢迷沉就能达到的,它最终依靠的肯定是“中国”的方式。
参考文献: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王凤才.批判与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汪民安,陈永国.尼采的幽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40(2016)01—0073—03
作者简介:弓依静(1992-),女,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文艺美学方向。
收稿日期:2015-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