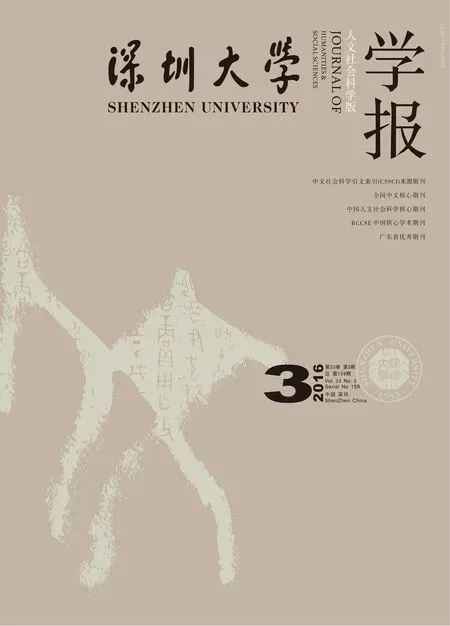从理论的(单向)旅行到(双向)对话
2016-04-04王宁
王宁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上海 200240)
从理论的(单向)旅行到(双向)对话
王宁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上海 200240)
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始终笼罩在西方理论的阴影之下,西方的理论可以通过翻译的中介长驱直入进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中。虽然理论的旅行会发生某种变异,但这种旅行和变异长期以来却一直是单向的,也即从西方到东方。美国文学理论家希利斯·米勒最近同时在西方和中国出版的一本演讲集则一改这种理论单向旅行的路径,加进了与中国学者对话的部分,这应该是一个可喜的开端。本文作者认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文化和文学理论走向世界也提到了中国学者的议事日程上。在这方面,米勒与中国学者张江的对话可以说预示了这种理论双向旅行的开始,但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与西方以及国际主流学者进行交流和对话。也许翻译的中介会使得中国的理论在西方世界发生变异,但是如果中西文论的对话能够持续进行下去,那就是值得的。
理论旅行;米勒;西方文论;中国话语
在最近几年的中国和西方学界,美国文学理论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一直十分活跃,虽然他已接近九十高龄并以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获得终身成就奖告别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但他依然在家里著书立说,总结自己所走过的漫长的学术道路。最近同时在美国和中国出版的《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An Innocent Abroad:Lectures in China,2015)就是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中国的十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所作的三十多场演讲的精选文萃[1][2]。作为学者型批评家的米勒从不满足为了演讲而撰写的稿子,他总是反复地在吸取中国听众所提问题的基础上修改扩充原稿,使之成为能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单篇论文。现在米勒又应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邀请,按照这些演讲的内容精选出十五篇具有代表性的演讲稿修改并编辑成书,从而使其有着内在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读来不禁令人颇为亲切,同时又不无启发。米勒的这本书的出版不禁使我想起另一位曾在西方和中国一度炙手可热的人物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他的《东方主义》早已成为当代后殖民理论批评的奠基性著作。一度时期,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言必称赛义德及其《东方主义》。然而,在中国,赛义德还以另一篇单篇论文蜚声文论界:《理论的旅行》,这篇论文不断地引发人们的讨论甚至争论。本文就从这篇文章开始说明,中西方的理论交流是如何从当年理论的单向旅行到今天理论的双向旅行和对话之境地的。这应该是中西比较文学和文论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一、理论的旅行:从西方到中国
在中国学界,除了那本享誉世界且备受争议的《东方主义》一书外,赛义德最广为人们引证的另一部著述便是论文《理论的旅行》(Traveling Theory)。这篇论文最初于1982年发表于《拉利坦季刊》(Raritan Quarterly),后收入作者出版于1983年的论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 and the Critic,1983)。在这篇文章中,赛义德通过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的“物化”(reification)理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的翻译和传播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提出了一个颇具洞见的观点:理论不仅在其产生的时间和地点发生影响,它有时也可以“旅行”到另一个时代和场景中,而在这一旅行的过程中,它往往会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反叛性而产生某种变异。这种情况的出现多半受制于那种理论在被彼时彼地的人们接受时所作出的修正、篡改甚至归化,因此理论的变形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有时理论的旅行和变异也能引发新的东西的产生。在这里,赛义德显然指的是西方的理论通过翻译的中介旅行到非西方国家所产生的变异和影响[3](P226-22)。在赛义德看来,处于强势的西方理论旅行到非西方世界是天经地义的,而且会自然地在非西方世界得到接受并产生影响,因为那里的人们需要来自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理论,并用它来解释本土的文化现象。当然,在产生影响的同时,理论也会因接受者主观的理解和能动性接受和阐释而产生一些变异。对此,米勒在另一场合作了进一步回应。米勒在承认“理论旅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同时,还希望自己的理论能够在异国他乡产生反响甚至讨论。他在自己的著述中也以此例来进一步证明西方的理论,尤其是经过美国的中介,旅行到非西方国家后所产生的效应和影响。但是他却辩证地指出,“可以想象,真正的文学理论,也即那个货真价实的东西,也许不可能言传或应用于实际的批评之中。在所有这些意义上,即语词是不可能传送到另一个语境或另一种语言中的,因而理论也许是不可译的……翻译理论就等于是背叛它,背离它。但是,事实上,某种叫做理论的东西又确实在从美国被翻译到世界各地。这种情况又是如何发生的呢?”[4](P6)他的上述看法倒道出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认识到翻译的“悖逆”和“创造”作用,尽量在研究某种理论时通过阅读原文来进行;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能总是通过阅读原文来研究所有的理论,因为一个学者不管多么博学也不可能学遍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他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得依靠翻译,因此翻译就是 “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德里达语)。熟悉多种西方语言的文学理论家和研究者米勒对此更是有着直接的体会和亲身的经历,应该承认,他在这里依然指的是西方的理论通过翻译的中介从美国进入到其他非西方国家,尤其是进入到中国后所产生的变异和影响。他的这本书就见证了西方的理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是如何经过他的阐释、介绍和批评性实践并通过翻译的中介在中国产生影响和发生变异的。应该承认,米勒的理论在中国学界产生的反响证明了他的上述观点,同时也使得他在中国的知名度甚至高过了在美国的知名度。
但是不可否认,在赛义德和米勒等西方学者看来,长期以来,理论的旅行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单向的,往往总是从处于强势的(西方)国家旅行到处于(弱势)的东方国家。由于那些非西方国家的接受者对西方的理论有着迫切的需要,无论这些理论经历怎样的变异或曲解,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十分明显的,有时甚至可以引出一个批评流派的诞生。当年,当美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十分渴望欧洲理论的引入时,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的进入美国就受到了时任耶鲁大学教授的德曼和米勒等人的追捧和接受,而促成了所谓解构主义批评在美国的诞生和 “耶鲁学派”的形成。米勒在中国的演讲虽然未能促成一个批评流派的形成,但却在本世纪初引起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讨论,而且那场关于“文学终结”的讨论一直持续了多年①。当然,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尤其是我们在读了他的这本书之后,就不难看出,这其中有着较多的误解和误读的成分,但却印证了他和赛义德等人所认为的“理论旅行”和变异的看法。但米勒与赛义德所不同的是,他在注重讲述理论的同时也注重与异国接受者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对话,通过这种交流和对话,他可以对自己原先不成熟的看法进行修正,这样也就打破了理论的单向旅行之格局,使理论的旅行成为一种双向的交流和对话。在讨论这种理论对话的意义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回顾一下米勒本人的文学理论批评之特色。
二、米勒的批评理论特色再识
关于米勒的批评理论之特色,我曾在其他场合作过评述[5]。几年前,我应美国 《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主编托马斯·比比(Thomas Beebee)约请写过一篇英文书评[6]。虽然我评的是伊蒙·敦纳(éamonn Dunne)的书《现在阅读理论:和米勒一起享受快乐阅读》(Reading Theory Now: An ABC of Good Reading with J.Hillis Miller)[7],但实际上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也进一步深入了解了米勒的批评理论和阅读方法。米勒早年在大学里学习的是物理学,但他后来出于对文学的强烈兴趣转而改学文学,并在后来成为一名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在长期的学术和批评生涯中出版了三十多部专著或文集,其中不少已经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他的批评理论与实践的误解也十分常见,为此,我认为敦纳的这本书的出版是十分及时的,对于我们全面地了解米勒的批评理论特色很有帮助。
作为文学理论著作的读者,我始终认为,阅读米勒的著作不啻一种快乐,这不仅是因为他经常为读者理解经典文学作品和当代文化现象以及当下的前沿理论思潮提供深刻的理论洞见,而且还因为他的著作总是以一种流畅的富于雄辩的文体写成,从而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确实,米勒的著作涉及广博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知识,尤其体现于这样一点,他的著作几乎论及了西方文学和理论史上所有最重要的经典作家和理论家,在作家方面他讨论的有乔纳森·斯威夫特、查尔斯·狄更斯、乔治·爱略特、托马斯·哈代、约瑟夫·康拉德、马塞尔·普鲁斯特、D.H.劳伦斯、欧内斯特·海明威、华莱士·斯蒂文斯等,所讨论的理论家则包括康德、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让-陆克·南希、杰弗里·本宁顿、J.L.奥斯汀、德雷克·阿特里奇、艾布拉姆斯、德曼等。这其中一些人是他的同事或朋友,也有一些是他的前辈师长,但他总是以一种对话的姿态从细读他们的某一种著作开始自己的论述。这一特点自然也体现于他的这部中国演讲集中。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讨论。米勒与他的许多学界同行所不同的是,他对理论的兴趣如此之浓厚以致于大大地超越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学科本身,他始终将自己的写作定位在文学和文化理论之间,文学和文化批评之间。他并非那种空泛地谈论形而上理论的理论家,而更是一个文学批评理论家,也即他尤其擅长于将各种不同的理论教义融为一体运用于自己的文学批评和文本阐释中,即使他在被人们认为是最坚定的解构主义者的同时,也可以在他的批评文字中见出普莱的现象学理论教义和严格的新批评训练的影子。而他对当今网络文学的崛起以及其对印刷文学构成的挑战和威胁所发表的文字则体现了他早年所受过的自然科学的训练。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文学理论批评家。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米勒对阅读十分擅长,而且速度极快,因此他的阅读量很大,不仅是文学作品,还包括各种理论著作。对他来说,“每一次阅读米勒都要将理论工具带进那些文学文本中,同时又对那些理论工具进行质疑。”[7](P155)如果我们说德里达是一位非常仔细的读者,任何东西都难以逃过他那敏锐的眼睛,那么米勒便可算是真正有效地掌握了解构主义的阅读策略和技巧并将其推向极致的批评家。因此,“这种方式的阅读使我们懂得,当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阅读一个文本时,任何单一的理论都无法预示将出现什么结果。”[7](P155)即使在讨论理论问题时,米勒也从未忘记理论著作中的文学成分。因此对米勒来说,阅读理论就是一种乐趣,而绝不是沉重的负担。
例如他的《论文学》(On Literature)就是一部为对我们的生活发生持续影响的文学所作的充满激情的辩护,同时也是米勒从阅读文学所感受到的巨大乐趣的一个绝妙典范[8]。敦纳认为,他的这本小书可以被看作是进入米勒与文学和理论有着特殊关系的那些作品的“敲门砖”[7](P167)。在这本书中,米勒鼓吹一种“优雅的阅读”(good reading):不紧不慢,仔细深入并对细节给与批评性关注。我们用这种方法来阅读就会享受到文学的美感。这也许正是米勒与他的同时代不少文学理论批评界同行的一个重要差别:阅读他的文学批评著作,我们会发现其中充满了理论的洞见;而阅读他的理论著作却见不到玄而又玄的高深理论推演,他的理论洞见就隐没在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上。因此读者们一般会同意,米勒确实是一位有着卓越的阅读方法和技巧的文学和理论著作的读者和阐释者,而且他在表达上也独具自己的流畅和优雅风格,使人读来丝毫不感到腻烦。
人们也许会问,既然米勒曾经跻身其中的解构主义大潮早已过去,解构批评也早已成为历史,为什么他在当今,尤其在中国,仍有这么大的名气呢?我认为这样几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其一,他本人确实在美国属于主流人文学者,单从他的一系列经历和所拥有的头衔,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在美国学术界所处于的领军地位:他长期执教于蜚声世界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而且很早就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并曾出任过影响很大的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主席。他在中国学界的知名度如此之大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他从一开始就被当作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美国的最重要的代表和实践者介绍给中国学界的,他的一些著作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就被陆续译成中文,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和比较文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两年在国内文学理论界讨论得很热火的那本《小说与重复》虽然迟至2008年才有完整的中译本,但在此之前关于这本书的评介性文章就已经不少了。由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确实需要像米勒这样的既有理论又擅长细读的批评大家,同时对中国学界来说,我们也确实需要像米勒这样的主流人文学者为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推波助澜,因而米勒的批评著述引起中国学界的特别关注就不足为奇了。这一关注在本世纪初以来甚至发展到了几所名牌大学的多位博士生以他的学术思想和批评理论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而这即使在他的祖国美国也不多见。难怪他不无调侃地说,“我在中国的知名度大大地超过了我在美国的知名度。”其三则是米勒与一些非常神秘的西方理论大家均不同,他为人十分和善和亲民。无论是蜚声学界的大教授还是初出茅庐的博士生,只要给他写信请教学术问题,他总会在第一时间亲自回复。而相比之下,不少年纪小于他的中国学者也许早就不上电脑了,所有的信件均由家人或学生代为回复,或根本不予回复。而米勒则亲自回复来自各方面的来信,这样便使他在中国学界有着广泛的人缘和很好的口碑。接踵而来的就是不少大学邀请他前往演讲,不少国际会议邀请他作主题发言,而他一般没有其他允诺大多会满足中国学者的要求。经过这么多年一直延续下来,这些早先的演讲稿经过他本人的反复修改最后就形成了这本演讲集。
现在这本演讲集很快就要在中文世界出版了,这其中的一篇篇闪烁着批评睿智和思想火花的论文正是中国当代十分需要的,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各种高科技数码技术的发展,人文学科被放逐到了边缘,更不用说印刷在书本中的文学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将向何处发展”成了每一个致力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学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位毕生致力于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米勒对此尤为关注,并不断地在各种场合为文学的幸存而作“最后的一搏”。但是他同时也提请人们注意:既不要对文学的衰落感到沮丧,也不必与文化全球化的大潮逆流而动,正确的选择是在全球化高科技的大潮面前表现出冷静的态度,利用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高科技来服务于文学和文学研究,这样就可以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以不变应万变,从而安心致志地从事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这应该是对我们每一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的一种告慰:文学是不会消亡的,但它再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处于“黄金时代”了。人文学科也是如此,它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但失去一种人文精神则会造成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弥补的损失。由此看来,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不时地流露出一位毕生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人文学者为了捍卫文学的合法地位而作的最后一搏,饱含着深刻的人文情怀。
三、从理论的旅行到理论的对话
在上面两节里,我仅以米勒的演讲集为个案说明理论旅行的(独白)常态和最近发生的(对话)变态。也许读者们要问,在这样一个文学不景气的全球化数码科技大发展的时代,出版米勒的这本纸质的演讲集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想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对我们有着启迪的意义外,本书对中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其两篇附录,因为如果前面的十五篇演讲主要是米勒的理论独白的话,那么作为附录的一部分则体现了这种独白已经发展到了一种对话,这尤其体现于本书所收录的中国学者张江近年来和他进行的两轮对话。我认为,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近年来在国际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我们过去总是不惜代价地将西方文学理论大家请来中国演讲,却很少推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大家;即使偶尔推荐出去了,也很少引起西方学界的重视,更谈不上与西方主流学者平等对话了。更为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国内的不少居于主流的人文学者仅仅满足于与西方的汉学家进行对话,而怯于与真正的主流学者进行对话,这样看来,中国学者张江率先与西方主流人文学者米勒进行平等对话便有着重要的意义和表率作用。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学者往来的书信将分期发表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和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共同主办的权威刊物 《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第52卷(2016)上,这也是该刊自创立以来首次连续发表一位中国文论家与西方文论家的通信式对话。这一事件将在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产生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人们也许会问,张江与米勒的对话之意义具体体现在何处呢?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其他场合作过评述,此处毋庸赘言[9]。我在此只想再次指出,这一意义尤其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这分别是两位中国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著名文学理论家之间的两轮通信,这些通信将告诉我们的西方以及国际同行和广大读者,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即使在理论衰落之后的“后理论时代”仍然对西方文论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仍在认真地研读其代表性著作,但是这种兴趣不仅体现于虔诚的学习,更在于对之的讨论和质疑;其次,这两封信也表明,中国的文论家并非那种大而化之地仅通过译著来阅读西方文论家的著作,而是仔细对照原文认真研读,而且并没有远离文学文本空谈。他们在仔细研读西方文论著作的过程中,不时地就一些疑惑和不解之处提出一些相关的甚或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通过与原作者的直接讨论和对话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识;再者,两位批评大家在仔细阅读了对方的通信后,深深地感到中西方学者和理论家就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误解和分歧,因此迫切地需要进一步沟通和对话,只有通过这样的交流和对话才能取得相对的共识,并且推进国际文学理论批评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米勒和张江的对话始于张江对米勒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著作《小说与重复》的兴趣和疑惑。张江长期以来专心文学理论研究,但是从不脱离文学文本的阅读,这一点倒是与米勒的治学颇有相似之处。正是出于对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教义的不满,张江向米勒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确定的文本究竟有没有一个相对确定的主旨,这个主旨能够为多数人所基本认同?”[2](P343)确实,他在阅读米勒的著作的过程中对这一现象感到不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主旨的话,为什么米勒总是试图在阅读一些英国小说的过程中寻找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模式?针对这一问题,米勒的回答是,“我原本认为,确定一个主题只是一个对于特定文本深思熟虑的教学、阅读以及相关创作的开端。”[2](P350)然后他通过说明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奇》作为一部有着多重主题的作品,为之作了辩护。当然,他也认识到中西方学者在阅读策略上的差异,因此在他看来,“我们倾向于认为只有具有原创性的解读才值得出版,而中国学者可能认为,通过在新的文章与书籍中进行重复来保持那些被普遍接受的解读是很重要的。”[2](P350)虽然米勒并不想花费很多时间为别人的阅读寻找一种模式,但是他的这种“重复”对中国读者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来说,却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并在发挥作用了,或者说他不知不觉地已经确立了这样一种模式。这一质疑确实对米勒是一个挑战,因此米勒便从自己的角度对之作了回应,对话就这样开始了。
其次,米勒和张江的对话也澄清了一些理论上的误解。例如,张江在信中表达了他本人以及许多中国文学研究者对解构主义的阅读和批评方法的兴趣,他想知道米勒本人究竟是否可以算作一位解构主义者,以及解构主义是否仅仅要摧毁文本还是同时也有着积极的建构性的一面。他的这一疑惑同时也反映了许多中国学者的疑惑。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解构是8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批评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思潮,甚至在它衰落之后仍然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而米勒本人在中国的知名度则体现在他被认为是其影响力仅次于德里达的最杰出的解构主义批评家。这也正是为什么张江对德里达的理论教义与米勒的批评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感到如此困惑和好奇的原因所在。而米勒则作了这样的回答,“如果说我是或曾经是一个‘解构主义者’……的话,我可从来不拒绝理性,也不怀疑真理……我认为,我也不否定所有先前的批评……我希望以开放的心态进行我自己的文本阅读。”[2](P351)这样米勒既为自己的与时俱进作了辩护,同时也为解构主义批评作了辩护,旨在说明,他本人虽然曾一度沉溺于解构主义批评,但与他的其他耶鲁同行所不同的是,他的批评生涯是与时俱进的,也即他不断地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吸纳新的理论思想,即使对他的老朋友德里达的理论也绝不盲从,因而他在长期的批评道路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风格,或者说建构了一套自己的独特的理论批评话语。而对此国内的文学理论教科书编写者则缺乏某种跟踪研究的意识,仅仅停留在认为米勒是一位解构主义者这一固定的看法。在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同时也看出了两人的一个共同点:两人都不是大而化之地谈论理论,而是从阅读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入手讨论其中的理论问题。因而米勒在批评实践中显露出与解构的理论原则相抵牾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米勒是一位有着开放心态并带有积极的建构意识的解构主义批评家。他从不满足于既有的程式,总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而调整自己的批评立场,这就是他总是活跃在学术前沿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对于米勒在阅读过程中转变注意力这一点,张江一开始也感到困惑并难以理解他的这种转变,在他看来,米勒的这种转变立场是否说明了解构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也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而米勒则回答道,确实,德里达基于海德格尔的“破坏”(Destruktion)这一术语而发明了 “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术语,但是这个术语经过德里达的改造后同时含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含义:也即破坏和建构的成分并重。这样,米勒的回答便解决了困扰许多中国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困惑,他们过去确实对解构主义批评多有误解:只看到其消解中心和意义的一面,而忽视了其积极建构的另一面。而按照解构本身的含义,它在破坏了既定的结构主义教义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些新的东西,而这一点恰恰为大多数中国学者和批评家所忽视。因此这应该是两人对话的一个积极的成果。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探讨这个问题,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当文学和文学理论再也不那么吸引人时,张江与米勒的对话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一部出版于上世纪80年英语世界的旧著今天还能吸引一位中国文论家,并促使他通过反复阅读进而提出一些理论问题?我认为,它的意义至少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其一,一部原本在一种文化语境中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通过翻译的中介,会在另一文化语境中发生变异进而具有“持续的生命”或“来世生命”,米勒的旧著在中国批评界的持续影响就说明了翻译的巨大能动作用;其二,当文学和理论在西方处于衰落状态时,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其他地方也会处于衰落的状态,比如说,在中国,文学理论仍然有着一定的读者和研究者以及广大的市场,尽管它们不像十年前那样曾有过那么多的读者和那样大的市场。当文学研究受到文化研究的挑战时,一些中国学者依然对阅读文学作品情有独钟,并且从中探讨一些有意义的理论问题,还有些学者则试图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寻找某种平衡关系和赖以对话的基点。在这方面,我们不难看出,米勒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但他却在中国的演讲中大谈文化研究,而且表现出对高科技条件下文学艺术的新形式的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他在讨论这些文化现象时又总是离不开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和分析。这应该是对我们的文学和理论研究具有启迪意义的地方。
最后,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强调指出,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始终笼罩在外来影响的阴影之下,先是20世纪初的西方理论,后来又是50、60年代的苏联教义,文革结束后,我们又经历了新一轮对西方理论的膜拜和大规模的翻译与接受。西方的理论可以通过翻译的中介长驱直入进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中。与之相反,中国的理论和学术著作要想进入西方世界则举步维艰,即使提供了现成的译本有时也难以为主流出版机构接受。虽然理论的旅行会发生某种变异,但这种旅行和变异长期以来却一直是单向的,也即从西方到东方。而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文化和文学理论走向世界也提到了中国学者的议事日程上。我们应该果断地结束这种单向的理论旅行,而应该倡导一种双向的理论对话,通过与我们的西方乃至国际同行的平等对话,将中国文化和文学精髓介绍出去使之为世人接受和分享。因此在这方面,米勒与中国学者张江的对话可以说预示了这种理论双向旅行的开始。但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还应该积极主动地在人文学科的各分支学科与西方以及国际主流学者进行全方位的交流和对话。在这方面,翻译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许翻译的中介会使得中国的理论在西方世界发生某种变异,或者说会失去一些中国固有的思想概念或美学精神,但是如果中西文论的对话能够持续进行下去,这种变异和失却就是值得的。
注:
①这主要是围绕米勒担心全球化时代的电信等高科技对文学领地的压缩和纸质文学书籍的可能消亡。他的这种担心被误认为他本人就是“文学终结论”的鼓吹者和代表人物,因而引起了一些中国文学理论家的非议和质疑。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总结和分析可参阅周计武的文章,《语境的错位——米勒的 “文学终结论”在中国》,《艺术百家》,2011年第6期,第89-95页。
[1]Miller,J.Hillis.An Innocent Abroad:Lectures in China[M]. Evanston,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5.
[2]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M].国荣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Said,Edwar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C].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4]J Miller,J.Hillis,New Starts: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M].Taipei:Academia Sinica,1993.
[5]王宁.希利斯·米勒和他的解构批评[J].南方文坛,2001,(1).
[6]Wang,Ning.Reading Theory Now:An ABC of Good Reading with J.Hillis Miller[J].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2013,(50):687-691.
[7]Dunne,éamonn.Reading Theory Now:An ABC of Good Reading with J.Hillis Miller[M].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 Press,2013.
[8]Miller,J.Hillis.On Liter atur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
[9]王宁.再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国际化战略及路径[J].清华大学学报,2016,(2).
【责任编辑:向博】
【】【】
Theory Transmission:from One-way to Two-way
WANG Ning
(Institute of Arts and Humanities,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200240)
For a long time,China’s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was overshadowed by Western theories. Through translation,Western theories have a clear path to China’s literary critical discourse.There are changes and aberrance during the transmission,but the transmission and aberrance have long been unidirectional:from West to East.J.Hillis Miller,an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 recently published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in the West and China at the same time.The theories do not travel in a one-way system in this book,to which he adds the dialogues between Western theorists and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This marks a good beginning.In this paper,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llows Chinese scholars to bring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ies to the world.In this regard,Miller’s dialogue with Chinese scholar ZHANG Jiang probably signifies the beginning of a two-way transmission of theories.However,we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ommunicate and dialogue with the mainstream academics in the West and the world.It is true that translation might well cause aberrance of Chinese theory in the West,but it is worth it if we continue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theory transmission;Hillis Miller;Western literary theory;Chinese discourse
I 2
A
1000-260X(2016)03-0122-06
2016-03-07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西方现当代文学和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