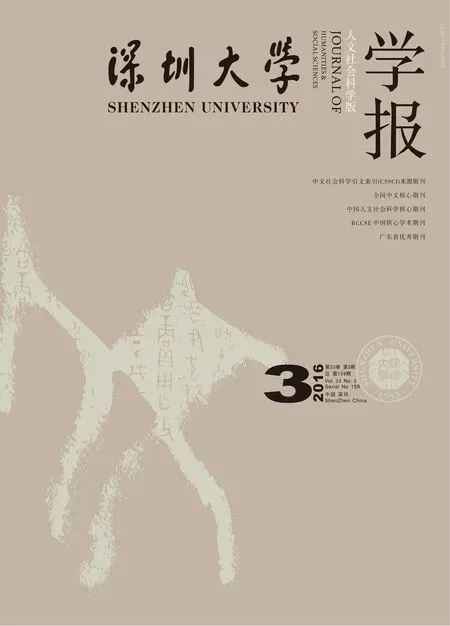社会互动视角下女村官的角色困惑和调适
2016-04-04周仲秋谭咏梅
周仲秋,谭咏梅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社会互动视角下女村官的角色困惑和调适
周仲秋,谭咏梅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女性就被逐步排斥在政治门槛外,与“政治领域”渐行渐远。20世纪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冲击了女性参政壁垒,为女性进入政治领域提供了机遇。然而,悠久的历史因袭仍作用于现实社会,传统与现实叠加导致女性在参政过程中易出现角色困惑问题,广大农村地区的女村官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尤甚,在封闭化、熟人化、从众化、差序化的乡土社会里陷入文化漩涡、认同困境。在此情形下,角色调适是打造新型女村官队伍,推进中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实践的必由之路。
社会互动;女村官;角色困惑;角色调适
新中国的成立为妇女参政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社会条件,女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民主制度在农村的推行、农村大量青壮年男性外出务工和妇女参政意识的提高,使得一批优秀的农村妇女走向政治舞台,成为我国村民自治的一大特色。然而,传统与现实原因的双重叠加使得女村官们的表现并不如我们所预期一般成功,女村官们在政治舞台上正面临着究竟何为“女村官”的角色困惑。
一、社会互动理论及中国农村的互动特色
奥尔格·齐美尔从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出发研究社会交往形式,指出个人行为是个人动机及其对环境结构的瞬时反应结果。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明确提出“自我”概念,将“自我”分成“物质我”、“社会我”和“精神我”三方面。在其之后,库利发展“自我”概念,进一步提出了“镜中我”的概念[1](P77)。“镜中我”表明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是自我的反映,多样的社会关系构成多样化的身份,个体生活在“多镜子”的世界,每一面“镜子”从不同侧面角度反映“自我”角色。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社会交往互动活动,构成多样化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具有情境性。米德在综合詹姆斯和库利等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互动论”,“认为角色概念建立在个体层次上,角色形成于个体相互行动的过程,通过象征性互动与扮演特定角色发展自我概念。“自我”分为“主我”和“客我”两方面,“主我”是未经社会化、自然形成的我,“客我”则是经过社会化结果的我。通过自我概念的发展,“主我”不断对变化的“客我”作出反应,在个体与他人的接触互动中,起着影响或支配个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行为的作用[1](P78-79)。
传统文化的积淀与现代文化的冲击,使中国农村的社会互动既展现传统本土的一面,又有革新的趋势,呈现出复杂性与多变性。中国农村的社会互动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封闭化
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是乡土性的,农村更甚。从中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精耕细作可以看出,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粘附在土地之上的。流动性的衰弱使得人与人在空间上的排列整体具有孤立和隔膜的特点。在以村落为基本单位的乡土社会,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来说的,人口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村落的生活方式具有地方性,形成一个较为孤立的社会圈子[2](P6-7)。农村的互动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基础的,建立在地缘、血缘和姻缘等关系上的人情性的互动。
(二)熟人化
历世不移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在“生于斯,死于斯,终老是乡”的农村社会,世代黏着构筑的是一个面对面的社群,每一个人的平素接触的互动对象基本上是与生俱来的人物。社会与个人相通,人情往来大多通过“习”得的礼俗,人际交往具有长期性、连续性,寻求的是关系网络中的“动态平衡”,进行情、理、法三位一体的人际交往活动。
(三)从众化
熟人社会的互动多表现出交换与合作的特点。中国农村的“习”这一方式是通过反复地做,时间磨炼而形成的一种惯性方法,社会互动中遵循的就是不断进行 “习”得来的那一套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办法。当一个人碰到问题时,必然会向比他年长的人寻求解决办法,在经验构筑的“礼治秩序”遵循“长老”这一教化性的权力意见,权威教化自上而下,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追随文化。从众心理与随大流在当前村民参与村务时的表现十分明显,甚至在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时,村民也往往惯于从别人的行为特别是村中有较高威望的人中寻找行动依据[3]。
(四)差序化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个体由己向外形成了一种具有伸缩性的格局,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同心圆”。“克己复礼”是差序格局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与传统的男女有别,家族氏族思想混杂,形成了多元社会圈。乡土社会所追求的稳定使得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下形成性别鸿沟,男女被内在地行为分工合作,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经济和生育事业,形成有秩序的、安稳的、差序化的“同心圆”格局。
二、女村官的源起及角色厘清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女性开始走向政治舞台,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这一现象是基于我国的宏观社会背景下逐步发生的,是制度、社会、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逐渐建立起来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村民自治”的提法最早见于我国1982年修订颁布的《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明确了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但此次并没有涉及女性参与问题。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标志我国村民自治走上制度化道路,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村民自治,其中规定了“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名额”,农村女性开始在走向政治舞台[4](P24-25)。21世纪以来,“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中都有‘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要占一定比例’或‘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等规定。”[5]
我国农村女性走向农村政治舞台既是民主意识觉醒,制度进步的结果,同时也是现实社会的必然需求。“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农村经济学家陈翰笙先生在广东农村进行考察时就发现 ‘妇女劳动力在用于土地的总劳力中所占的比例异常之大’,这一现象反应了劳动力的消减甚至丧失,并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下降。”[6]改革开放使得大量农村青壮年男性向第二、三产业聚集的大城市转移,女性被滞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农业女性化”凸显。农业女性化使农村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在农村事务的影响力也逐步扩大。
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中担任决策、管理的领导集体成员,女村官角色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村庄事务管理好坏,关系农村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女村官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的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就女村官的角色而言,本文主要从政府和个人两方面分析。就政府而言,对女村官角色定位于政策宣导、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行使民主权利,配合完成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矛盾调解等工作,更好地实现村庄治理的目标。研究表明,村庄治理中女村官与男村官的治理目标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两方的首要目标均为发展村庄经济;次要治理目标中,女性比男性更加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而男性则更加注重安定团结和公共利益[4](P33-34)。实践中,女村官更多地扮演着“柔性”角色,利用女性独有的温柔、善良等特点成为村庄治理的“黏合剂”。
个人角色是指女性在向女村官这条从政道路上的参政动机、对角色的自我期望。调查分析发现,30.3%的女村官参政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女性的社会价值,25.5%基于想为村民服务,4.8%是为了给女人争口气,即有60.6%的女村官参于竞选是出于个人意愿和要求,仅有39.4%的是因别人推选或家人支持才参加竞选[7]。女性选择“女村官”这条道路是出于自主、自觉行为,满足自我价值的愿景。
女村官的角色职能在于在内构建农村社会信任资本,沟通与规范乡村人际网络关系,促进农村合作组织的团结合作,提高农村管理效能;在外重于获取资源积累,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壮大农村等。
三、女村官的角色困惑及原因分析
女村官角色扮演的成功与否,主要依赖于农村这一社会网络中对女村官角色的认同、期望以及给予的社会资源等。角色扮演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常常会出现现实与期望的落差,甚至遭遇失败,产生角色失调现象,带来角色困惑问题。现实生活中,女村官充满着对自己的“角色困惑”。
(一)文化漩涡——认同困境
现代社会妇女意识得到极大解放,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中指出:“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为女人,与其说她生下来就是女的,不如说她是经过后天社会文化的培养而富有女人味”[8]。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不存在生理性别,只存在社会性别,主张以“性别表演”取代性别与社会性别两分的概念,女人本质上是一个模仿的过程,“性”差异本质上是性别表演的结果差异所致。传统文化与现代妇女意识的相遇,碰撞出女性呐喊的火花,男性也开始重视女性的作用,意识到女性并不必然是男性的敌对面,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男女生理差异筑就了男女间的性别鸿沟。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中阻碍共同生活的人充分了解的确是个人生理上的差别,永远划分人们生理差异的是男女两性,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2](P71-73)。传统思想强调“男主内,女主外”。这一文化互动的历史劣势使得女村官们的社会嵌入性较低,工作效能不佳,角色自我认同度较低,产生角色困惑。
(二)制度偏差——名不副实
时代的进步让传统的父权制受到了挑战,但父权的式微并不表明父权意识的消解,父权意识作为文化心理积淀仍然左右人们的价值选择。尽管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中妇女应当有适当名额,然而,“适当”一词留有的巨大伸缩空间常常被人利用。在我国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过后,妇女当选情况往往不太乐观。当前我国村民委员会中女性当职呈现出“一低两多两少”的局面,即当选的比例低;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据民政部统计,2000年底,妇女在村委会中所占比率为15%,在村主任和村支书等“一把手”职务尚不足1%[9]。2011年第3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调查显示,2.2%的在业女性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为男性相应比例的一半;高层人才所在单位一把手为男性的占80.5%[10]。整体来说,女村官在村委会中比例少、层次低、职位边缘化。
(三)封闭社会——相融困境
相融困境主要体现在女大学生村官或上级政府派选的外地女村官在异乡农村的融入难题。农村社会是基于血缘、地缘和姻缘基础上的以家庭、氏族为单位的熟人社会,重人情往来,同时又内在地包含竞争与合作的统一互动。氏族即根据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2](P61-63)。在这样一个较为封闭的熟人社会里,农村复杂的社会互动关系常常让她们水土不服,成为一个伸展不开手脚的“旁观者”。
(四)多重角色——互动危机
现代社会不仅内化了“女主内”这一角色趋势,同时女性也开始承受一定的家庭经济负担。2011年第3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调查显示,72.7%的已婚者认为,与丈夫相比,妻子承担的家务劳动更多[10]。在湖南省的主要数据报告中,有75.0%左右的女性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或全部日常家务劳动。已婚在业女性工作日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为122分钟,比已婚在业男性多81分钟;休息日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长达205分钟,比男性多122分钟[11]。精力和体力的有限、村官待遇较低等因素往往使得女性在家庭之外往往难以缺乏再去从政的热情,农村中的已婚女村官影响尤甚。心理和经济双重压力将角色界限将越来越模糊,难免导致角色从内的冲突,产生角色困惑和失调。
(五)去女性化——角色困惑
我们过去选择女性进入政治领域大多是看中女性温柔、善良、具备亲和力等妇女特点,以便更好地开展计生、民事协调等工作。这从逻辑上说是强调男性生理的差异所带来的女性意识,强调女性的回归,女人味的回归,让“女人”去做工作。但是,现实生活中,女村官往往还需要强硬的、所谓的“男子气概”,这种形象与很多人想象的相去甚远,消磨着她们被社会人认定的女性特质。然而,“社会性别”反复强调的是要求缩小以至消灭社会性别差异,这是男女平等、性别平等的基本条件,对“女人味”的强调实质上是加大了“社会性别”的分化,我们强调“女性意识的回归”本质上是“去”妇女解放的[12]。女村官们在社会互动中,常常需要在“女性化”与“去女性化”两种角色特质中准确切换。
四、女村官的角色调适
(一)构筑舆论保障——弘扬“社会性别”平等文化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人是有性别的,人的性别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性别不平等是社会文化构建的结果[13]。社会性别理论强调缩小乃至消灭社会性别差异。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有其很成熟的整体纲领,强调“半边天”、“男女都一样”就是那个时期的典型的“社会性别”平等的思路,这里的“男女”不是生理意义上的男女,而是“社会性别”意义上的男女[1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过于强调妇女意识的回归,犯有矫枉过正的问题,这一行为是建立在男女生理差异的基础上,强调女性独有的“女人味”的回归,本质上是进行重新社会性别化,是“去”妇女解放的。打破农村地区的“男女有别”思想,引领农村地区树立正确的妇女发展观,任重道远。
(二)消解身份危机——确立女村官法律地位
2010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六条中指出: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14]。“应当有”正如“适度”概念一样模糊,给投机分子留下操作空间。首先,可以将政策进一步细致化,在选举程序、环节和制度保障上体现性别平等意识,“应当有”修改为妇女比例应达到30%比例,或规定根据地区性别比例来确定女性选民人数,从而规定农村女性参政比例;其次,对女村官职位规定明晰化,尤其是对于女大学生村官或异乡村官,除传统的计生、民事协调等工作外,规定女性当选为领导的比例,从而为女性发挥自身领导管理决策能力提供舞台;再次,追求性别平等并不等于否认性别差异,针对女性生理特质政策应当做出相关保护规定,例如对处于怀孕期或哺乳期的女村官工作的考核、选任等。
(三)提升综合素质——打造新时代“女村官”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绣花要得手绵巧。尽管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在当今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女性与男性处于平等的主体地位[15]。现代社会女性要赢得男性的尊重,关键在于自身素质的提高,对从农村生活走向村官舞台的农村妇女而言尤甚。有学者调查了来自全国近20个省市区不同地域、不同村庄的近百名女性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发现她们之中文化程度高中占41.5%,中专占25.6%,大专及以上的占23.2%,初中占9.8%,女村官们对自身权利和村务管理有一定认识,但有待加强[16]。女村官们普遍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这有助于开展工作,但进入权力结构后,会遭受内外两方面压力的挤压:内压主要是对自身能力价值评估的怀疑、不信任;外压多体现为男性两委的态度和村民的不信任等,内外压力的叠加往往使女村官缺乏自信力。因此,打造新时代“女村官”的关键在于优化女村官文化心理结构,克服自卑心理,打破对传统男性的依赖,提高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决断意识。其次,“实践出真知”,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打磨,女村官的能力才能提升。女村官要加强政务参与意识,既要走基层一线,理解村民需求;又要提升概念化技能,利用宏观视野,梳理村庄事务,谋求村庄发展。
(四)提高村官待遇——增长留任信心
在 《全国百名女村官调查报告:社会性别的视角》中,任杰在询问女村官们为什么不愿意参加下一轮竞选时,30.5%的认为是 “收入太低”,26.8%的认为是“村级经济基础太差”[16]。待遇问题是导致女村官角色困惑的又一原因,女村官处于“非官非农”的尴尬地位上,家务劳作和村庄事务基本上是生活的两大块,经济来源自然成为突出问题。农村经济收入来源单一,如何增长女村官上岗、留任的信心?关键在于对大力发展村庄经济,而村庄的发展又依赖于村官的能力发挥。留住女村官,就要提升女村官的待遇水平,让她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不被过多经济因素所困扰。这方面要提高,可以参考本地区乡镇录用公务员工资收入水平标准确定,并做好女村官的相应保障和后续招聘工作,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圈。
(五)丰富组织培训——构建集体认同
个人能力的成长离不开所需的政策环境。在实践工作中,女村官尤其是领导岗位的女党支部书记、女村主任的工作特点有时会呈现出“去女性化”的特点,在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其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男性化或者中性化的特征。她们的办事方式更倾向于传统男性的刚毅、果断,与群众所期望的“柔情似水”的感觉相去甚远。这既是某些领导岗位所需特质,又是现实所迫的无奈。“历史劣势”的积累、“性别平等”的异化和村务“力治”的需要都使得女性褪去身上的女性特质,成为一个强硬的“男性”领导。女村官在女性生理与“去女性化”的双重影响下很容易对自己的角色困惑,究竟是要保持传统的女性特质,成为“女性化领导”;还是保持强硬作风,成为“男性化领导”。这种情况下,充分发挥组织培训的作用,增加女村官之间的交流,增强女村官对自己生理特质和工作特点具有重要意义。除了传统的依靠妇联组织来增强女性的集体认同外,我们还需要民间的合作。2010年,中国民政部与李嘉诚基金会联合发起展璞计划,这种培训可以将各地的女村官们联结起来,共同分享工作经验,增强身份认同;又通过与政府、高校的合作,既增加了女村官的社会资本积累,又能无形中丰富女村官们的领导管理决策能力方法艺术。
五、结语
村官作为村庄事务的管理者、决策者,其工作能效高低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的水平。村官扮演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完成政府各项功能,带领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建设新农村。如何解决女村官的角色困惑?性别平等舆论先行,在全社会营造“男女都一样”的话语氛围;制度执行是保障,女村官的法律地位要得到体现、落实;个人能力提升是关键,女村官需要用自己的综合素质赢得尊重,赢得社交互动圈;待遇增加是补充,让女村官能够兼顾事业与家庭,更加专注村庄事务治理;组织培训是辅助,让各地女村官们通过培训交流经验,充分发挥高校的理论优势,结合女村官自身实践,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村庄事务治理之道。
[1]周远清.新编社会学大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吴思红,贺雪峰.国家与农村社会互动的具体处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91-95.
[4]李秀颖.村庄治理中的女村官研究:以湖州市为例[D].杭州:浙江大学,2013.
[5]李晓广,吴国清.农村女性参政缺失的新制度政治学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48.
[6]刘筱红,姚德超.农业女性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分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00.
[7]陈福英.性别棱镜透视下的女村官政治参与——基于福建省的实证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12):11-12.
[8][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南姗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518.
[9]刘筱红.支持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的公共政策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33-35.
[1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材料.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EB/OL].http://www.china.com. cn/zhibo/zhuanti/ch-xinwen/content_23687810.htm.2011-10-21.
[11]湖南省妇联.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湖南省主要数据报告[EB/OL].http://www.hnwomen.org.cn/article/ 130542.2012-03-26.
[12]柏棣.性别的政治:谈“社会性别”概念的不确定性[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5):5-6.
[13]杨凤.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研究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9.
[14]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EB/OL].http: //www.gov.cn/flfg/2010-10/28/content_1732986.htm.2010-10-28.
[15]师凤莲.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问题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24.
[16]任杰.全国百名女村官调查报告:社会性别的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07,(4):97-100.
【责任编辑:张西山】
【】【】
Female Village Officers’role Confusion and Adjustment from Social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ZHOU Zhong-qiu,TAN Yong-mei
(School of Marxism,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1)
After humans entering patriarchal society,women have been gradually kept out of the threshold of politics,and drifted further away from"politics".Since 20th century,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has helped tear down barriers to politics for women,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to enter political arena.However,deeply-rooted historical factors still affect the real world.The superimposition of tradition and reality makes women feel confused about their roles when they participate in politics,particularly the female village officers in the governance at grass-root level in vast rural areas.They get lost in the cultural whirlpool and identity dilemma in the isolated and hierarchical rural society of a high degree of acquaintance and conformity.In this case,role adjustment is the only way to build a team of new female village officers,and promote the autonomy at grass-root level in rural China.
social interaction;female village officer;role confusion;role adjustment
D 035.5
A
1000-260X(2016)03-0080-05
2016-02-11
湖南省教育厅“节约型政府视角下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实证研究——基于湖南省G县的考察(11K041)”
周仲秋,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基层治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谭咏梅,湖南师范大学讲师、在职博士生,从事基层治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