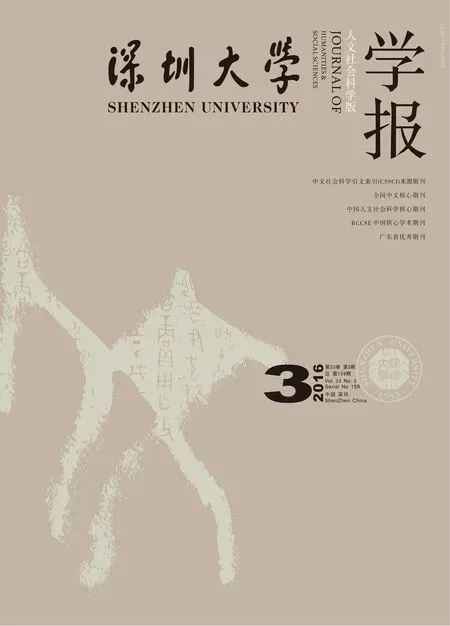胡塞尔视角下笛卡尔感觉与身体观的悖论及解决
2016-04-04佘碧平
王 继,佘碧平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胡塞尔视角下笛卡尔感觉与身体观的悖论及解决
王 继,佘碧平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理智主义者笛卡尔并没有忽略意识中自明的感觉,而是从感觉出发证得了身体的存在方式,并几乎得出身心交融的结论。可是他又坚持理智主义态度,因此不仅二元论在身心关系中得到贯彻,而且相反机械还原主义也获得了生长的机会:一方面身体被还原为生理器官,另一方面心灵中的感觉乃至心灵所有能力面临着被还原为神经生理活动的危险。这种悖论的出现,从胡塞尔现象学来看是因为没有进行彻底的悬搁,没有发现感觉体验原初的意向性结构。胡塞尔对感觉和身体的分析不仅可以解决笛卡尔的悖论,而且对于现代医学、神经生理学等的发展都有启发意义。
笛卡尔;胡塞尔;感觉;身体;意向性
通常我们关注的是笛卡尔的普遍数学方法,认为他是唯理论的代表,在身心问题上持二元论态度,对感觉谈得较少。实际上他一方面做着抽离感觉的工作,以便达到理智上的自明性;另一方面要回到自明的起点又不得不面对感觉所呈现出的自明性。因此他在理智论证过程中也直面了感觉问题,并以其独特的演绎推论法,由感觉出发论证了身体的存在,以及身心结合的方式,尔后又专门讨论了感觉在身体上的发生机制和分类。总体来看,他持机械论的身体观,但又肯定了感觉的独特地位。胡塞尔恰恰从他对感觉所持的悖论观点入手,坚持感觉的意向性结构,批判了其机械还原主义的感觉和身体观。本文以感觉为视角来审视笛卡尔突入身体问题的论证思路,并从胡塞尔的感觉与身体观来分析他在此问题上的得与失。
一、普遍怀疑中的感觉与身体——悬搁的不彻底
笛卡尔为了寻找到所有知识得以建立的最终自明的根基,首先通过怀疑排除了一切不可靠的成见。这种怀疑其实是一种双重抽象,而他对感觉、身体的怀疑便贯穿于其中。在第一重抽象中,首先,他以外感觉判断经常会出错为例,排除了外物存在的可靠性;其次,对身体的感觉也可能是错的,比如幻肢现象,于是他也排除了感觉器官的存在,“我们的手以及整个身体也许都不是像我们看到的这样”[1](P16);最后,即使抽掉了身体的具体形象,使它只剩下广延这种几何性质,仍然可能是错误的知识。因为可以设想一个骗子上帝,是他虚构出这种数量关系来骗我。笛卡尔通过逐层怀疑,便同时排除了从感觉经验到抽象数学乃至上帝的可靠性,所剩下来的就是在思维这个事件。于是他把作为思维活动的我思确立为最终自明的根基,而思维活动是感觉、想象、情感、愿望、理智等。也就是说,他在怀疑中排除的只是这些思维活动所涉及的判断内容,保留下来的则是这些思维形式。拿感觉和基于感觉的想象来说,它们涉及的判断内容虽不可靠,但就其作为被意识到的思维形式来说却是清楚分明的,“我称之为感觉和想象的这种思维方式,就其仅仅是思维方式来说,一定是存在和出现在我心里的”[1](P34)。这样他便将感觉、想象纳入意识内而承认了其自明性。这为他阐明身体的存在方式埋下了伏笔。
到此为止,笛卡尔的怀疑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基本上是类似的,后者也悬搁了常识态度下对身体及整个世界的存在信念,返回到了具有感觉、想象、判断等活动的意识本身[2]。但接下来笛卡尔又在第二重抽象中即意识内部抬高了理智而贬低了感觉和想象在认识中的作用。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感觉、想象等思维功能在概念形式上获得清楚明白的区分得源于理智,“在它们的形式的概念里……包含着某种理智作用”[1](P83);另一方面仅限制在思维内部的观念领域,与感觉、想象有关的观念也不如单纯理智观念清晰。比如蜡块的颜色有多白等感觉观念总是很模糊,而在抽离了这些感觉观念后,与单纯理智相应的广延观念则很稳固清晰。由于对理智的推崇,他在阐明上帝存在且不是骗子时,也从理智入手进行了本体论证明。尔后他又用完满的上帝来担保理智上清楚分明认识的客观有效性。按照胡塞尔的看法,这表明他还没有进行彻底的悬搁,而是以普遍数学方法为前见,因此注重理智上演绎推论的自明性[3]。与其理智主义思路不同,胡塞尔在回到意识的自明性后,并没有贬低感觉和想象的作用,相反认为它们是原初被给予的直观体验,唯有它们才是认识的合法来源,一切抽象的本质认识都要回溯到感知或想象才能获得充实的明证性[4](P53)。因此在笛卡尔那里用来担保认识合法性的上帝,也被胡塞尔判定为超越于意识之物而排除了[4](P153)。不过笛卡尔虽然在普遍怀疑中持理智主义态度,但也承认了感觉在形式上的自明性。正是对感觉与理智既进行分离又同时承认,导致他在阐明身体及身心关系等问题时呈现出了两重性。
二、感觉与物体存在的证明——感觉意向性的缺失
正如对身体和外物的怀疑是同步的,笛卡尔对身体与物体存在的论证也具有同构性:一方面身体是物体性的;另一方面身体是主体性的,是主体感知物体的条件。我们先来看感觉在其证明物体存在时的作用。首先,他根据实体与属性的关系论证了思维和广延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如上所说,在他看来,我们在思维中拥有清楚分明的广延观念,它是单纯理智所抽取的纯数量化几何关系,是一种天赋观念。同时广延不同于思维,广延的本质是可分性,思维则是进行思维的活动,它本质上不可以分成各自独立的部分,而是作为整体“全部从事于愿望、感觉、领会等的”[1](P90)。因此这两种观念所表征的属性必然从出于不同的载体,以作为思维与广延观念的原因。思维属性的载体就是正在思维着的我,至于广延属性的载体,笛卡尔又以理智分析的态度说它可能是外在于思维的广延实体,也有可能是上帝,因为万物都源于它。如何排除上帝选项呢,这时他就诉诸感觉和想象。首先,感觉、想象和理智的不同在于,后者的内容可以从思维内部分析出来,前者的内容则被清楚地把握为不单来自于思维本身,而是有外在的来源[1](P77)。其次,感觉和想象的东西虽千变万化,但它们总有广延形象。最后,思维中具有对改变位置等运动的清晰感觉,这些运动功能依赖于广延而不是理智[1](P83)。于是便得出必然有外在的广延实体的结论。因为在感觉、想象中具有颜色、声音等形象,所以广延实体就是被这样的形象所丰富的物体。不过,笛卡尔在这里只是从形式上利用了感觉和想象,来指明必有一般的外部对象,而对外物存在的证明步骤仍然是基于理智的推论,并且感觉、想象涉及的具体判断内容,如颜色、味道等在理智看来依然没有明晰性可言。这着重体现在他对“相似说”的批判上。相似说认为我们心灵中的感觉观念类似于它们所从出的对象[5](P81),比如认为火堆里有与热和光类似的东西。笛卡尔认为其荒谬性在于从感觉推出了感性形象的外在存在。在他看来对感觉的描述只能限制在感觉范围内,比如说“我感觉到热和光”这是可以自明的,但由此判断热和光存在于火堆却是错的,事实上在火堆里存在的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小部分之间的激烈运动,这些运动使我们获得了热感和光感[5](P83-84)。可见,与他的数学化理念相应,物体被抽象为物理动力学意义上的物,感觉在此退场。
从现象学来看,笛卡尔对广延物的证明依然带着理智主义的预设,割裂了感觉体验和理智观念、外物存在间的内在联系。笛卡尔所说的感觉、想象指向了外在对象已经有突入意向性的踪迹[6](P84-85),但他并没有将意向性贯彻到底,认为感觉只是感觉而已,它一旦越出自身范围而指向具体判断就不可靠,故而依然从理智出发推论物体的存在。胡塞尔则认为感觉不仅仅是感觉,而总是携带着意向性结构。意向性结构分为实项内在的部分和意向超越的部分,这两部分共属一体,彼此不能独立存在。感觉在其中是实项内在的,必然与意向超越部分处于结构性关联中。因此,就广延和物体而言它们既不是意识内现成拥有的天赋观念,也不是绝对外在之物,而是在知觉体验中意向性立义的相关项,而且它们在知觉中具有发生学的同构性,“空间显现、空间感知总是作为事物显现和事物感知”[7]。胡塞尔描述空间和事物原初的知觉发生机制时,要远比笛卡尔基于理智的推论详尽。他将感觉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对象性材料的感觉,如视觉和触觉;另一类是不具有材料内容的动觉(Kinasthese)[8](P136)。实际上笛卡尔在如上证明物体存在时也隐含地涉及到了这两类感觉 (位置改变的感觉相当于动觉),只不过他那里还带着朴素性,缺失感觉意向性,因此对他而言感觉到的是既定的广延和物体。胡塞尔则认为两类感觉一起参与了空间及物的构成。由于材料感觉中的表象都包含着延展性,所以动觉虽不像材料感觉那样提供表象内容,但却是表象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8](P136)。因而不像笛卡尔所说运动以空间存在为前提,相反“动觉意识是自身构成着空间的”[9]。他通过主题化隔离的方式逐级描述了从单眼运动、双眼运动、头部运动到整个身体运动中空间的构成层阶①。在这个图景下,笛卡尔所谓的广延观念只是在广延感觉基础上“通过‘理想化’而获得的几何学理念”[10],同时物理学物也只是基于感性物的理念化产物。这样他就通过赋予感觉以意向性,恢复了它在物体构成中的基础地位。
三、感觉对身体的证明——循环论证的嫌疑
笛卡尔在证得物体存在的同时,身体的存在便也获得了自明性。我们可以根据他的论述分出两个层次:第一,我对自身改变位置等运动的感觉需要一个它们依附于其上的广延实体,并且这个实体是属于我的;第二,笛卡尔在怀疑之后又诉诸上帝所赋予的自然本性,认为我有一个身体是自然的、清楚分明的,因为疼、饿、渴等感觉直接在这个实体上产生不同的反应[1](P85)。这样一个有广延、并被感觉到是属于我的物体,就是我的身体②,“我相信这个物体(肉体)(由于某种特殊权利我把它叫做我的)比其他任何物体都更真正、更紧密地属于我”[1](P80)。这也是身体与一般物体的区别,因为一般物体可以与我随意分开,并且产生不了属于我的感觉。因此身体与心灵的结合在笛卡尔看来并非像船只与舵手的关系那样是外在可分离的,而是“融合、掺混得像一个整体一样”[1](P85)。于是笛卡尔便从起初的思维之我推进到了身心结合体的我,认为身心结合才构成了整个的人,有感觉属于人的自然本性。然而他立马又表示人的本性存在着缺陷,在认识方面就表现为由感觉引起的判断并不可靠,必须用理智来辨明,甚至认为没有感觉和想象功能我作为单纯理智实体仍然可以领会到自己的存在[1](P82-83)。这种看法应和了精神与物质实体二分的推论。所以他很谨慎地说身心只是结合得“像”一个整体。
胡塞尔相较于笛卡尔,在运用感觉证明身体时最大的区别在于,他引入了感觉的三重功能说,即除了区分材料感觉与动觉,还区分了同一感觉三个层次的意向性功能[11](P9)。比如视感觉,就其指向外物来说,被统握为颜色感觉;就其指向视觉的载体来说,便使眼睛这种物多了一个感觉层,由此身体便从单纯的物体被统握为了正在感觉着的身体,它所具有的感觉状态是“‘纯’物质物所欠缺的”[12];同时不论感觉指向外物还是身体,它们都可以被意向性统握为是我体验到的感觉,即都归属于心灵状态。胡塞尔对感觉三重功能的划分体现了感觉与意向性的结构性关联,说明身体也是感觉意向性的构成物。而笛卡尔虽然认识到了感觉与身体的内在联系,实则潜藏着预先承认身体存在的朴素态度。这从根本上说包含在物体、精神实体二分的理智推论中,这里他又靠上帝来指明我对自己身体的感觉是自然而真实的,即借用上帝来支持对身体的实存预设。这样他就面临着循环论证的嫌疑:用感觉来证明身体,同时又将物体与精神的联合视作感觉的来源[1](P85)。与其不同,胡塞尔在现象学还原后虽然也运用了身体感觉类词汇[13],但这只是对原初体验的描述,并没有预设身体的存在,相反作为主题而描述了其意向性构成方式后,身体存在才得以显明。
虽然笛卡尔隐含着对身体的预设,不过也体现出他并没有简单忽略感觉与身体问题。如果感觉的自明性被严格贯彻下来,那么依胡塞尔观点,通过感觉指向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功能,恰恰可以推翻他的二元论,而走向身心交融论。事实上笛卡尔也接近了这一点,例如他说“当我感觉到痛苦的时候,它就不舒服”[1](P85),这里的痛苦是指心灵的感觉,不舒服是指身体上的感觉,二者是一同发生的。实际上这是同一种感觉即疼痛感的两种意向性指向。尽管笛卡尔对感觉意向性的双重功能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但他凭借对身体感觉与心灵感觉同步性的描述,已经觉察到了身心应是紧密结合的整体。不过如上所说,他以理智主义为前提必然会分析出物质与精神实体的二分,所以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是两种实体的有机融合还是机械相加,如果是前者,那么两种异质的实体如何能够融合在一起?即便可以,岂不是在两种实体之外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实体?如果是机械相加,又如何解释溢出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之外的感觉——既然单纯物体和单纯理智都无感觉?换句话说,如果感觉是存在的,那么二元论就面临着困境;相反,如果坚持二元论,那么感觉就难以成立。笛卡尔采取的解决方式是,既坚持二元论,又直面人的自然本性,承认身心结合的人整体的存在③,认为二者的结合产生了感觉。为了调和这两个方面,他提出了遭人诟病的松果腺理论,并最终诉诸上帝来解释心灵感觉与身体生理机制的相应性[14]。实际上这只是呈现了他在感觉和身心问题上的悖论,并没有真正解决它。胡塞尔则沿着感觉的三重意向性入手,批判两种实体的预设,在阐明物体是感觉意向性的构成物后,展示出身体首先也显现为物体,尔后通过感觉层而确认了身体是感觉器官,在此基础上说明感觉最终指向了对心灵的统握。也就是说物质层、身体层、心灵层是逐阶奠基的关系,如果没有对物体的感觉,那么作为感觉器官的身体便不存在,如果接受感觉的器官不存在,也就无所谓有感觉性的心灵了。所以,对心灵的意向性统握实则奠基于通过感觉对身体的统握,“心灵统握一般是以身体统握为根基的。两种统握通过感觉的双功能缠结在一起”[11](P12)。因此在胡塞尔看来,心灵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与身体通过感觉原初交织在一起。而身体和心灵两个概念的形成,则是基于意向性的主题化把握。这样在现象学视角下笛卡尔二元论就被解构了。
四、感觉的生理机制与感觉的不可还原性
从物体与精神实体的二元论,到身心二元论,这其中的过渡依赖于感觉:感觉使物体成为了身体,使单纯理智成为了心灵。由此出发,笛卡尔对感觉发生机制和感觉内容的解释仍然是二元的:前者是生理学的,后者是心理学的。一方面,他用物理学的动力论(机械因果律)来描述身体各器官的构造和运行模式,以及身心互动中感觉的发生机制。比如他用物体的机械运动律,来说明身体的运动不是由灵魂所推动的,而是身体各生理组织相互作用的表现,身体的热量也不是灵魂给予的,而是血液运动所致[15](P4-9)。身体中最精细的血液(又被他称为精气)涌入大脑,与小腺体中的灵魂互相作用而产生了各种感觉[15](P28)。另一方面,他又从感觉内容方面阐述了感觉种类的差异。感觉的生理机制与感觉内容这两个方面在他看来是泾渭分明的,感觉本身属于灵魂的能力,不能将其等同于神经生理活动,不然的话,心灵感觉到的就应该是神经活动④。这种看法虽然体现了其二元论思想,但同时也说明了感觉体验不能被还原为生理活动。不过感觉的作用始终受其理智主义所限制,比如他认为身体上两种基本的感觉是痛苦与舒适,然而单靠感觉进行趋利避害的选择是不够的,如水肿病患者喉咙会发干,单凭感觉而去喝水反倒会危害身体[1](P89)。因而为了真正对身体和灵魂都有好处,必须诉诸灵魂的理性能力。因为只有理性能力才能帮助我们辨明好坏,从而补救感觉的不足,引导意志去施行真正好的行动。
笛卡尔对身体和感觉的生理学解释乃是基于普遍数学的理念,是数学在自然科学中运用的表现。在生理学模式下身体的构造以及感觉的发生机制都透明化了,可以被准确操控,这无疑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⑤。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不但身体被机械还原为了物体,而且归属于心灵的感觉也因生理基础而面临着被还原的危险,继而心灵本身由于寓居于大脑也会成为被还原的对象。这是笛卡尔的二元论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坚称感觉不同于神经生理活动,并肯定了灵魂的自由意志和理性能力。可是悖论就在于,如果坚持从理智出发的二元论,就必不可免地会走向还原论,从而解构掉我思的主体性。胡塞尔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笛卡尔的二元论是一种实存预设,并没有进行彻底悬搁,于是精神实体被潜在地等同为心灵,并被转移至大脑。因此怀疑后的精神实体“仍然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16]。这无法解释无广延的心灵如何能在大脑中占据一个位置。同时,笛卡尔对意志、理性的分析虽然突出了灵魂的主动作用,但因二元论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它的身体基础,认为它们出自灵魂自身,可以与身体分离。所以在他的二元论框架中,对身体的理解只能止于生理身体的层面。虽然身体也通过感觉影响灵魂,灵魂靠身体实现自己的意志,但它们看起来是两张皮,而非水乳交融的关系。胡塞尔则通过意向性分析,不但明确了身心交织的关系,而且说明身心统一体是携带着意向性的人格主体,于是身体便不单是生理学研究的客体,而真正成为了主体。人格主体与周围世界交互作用所依凭的感觉体验总是携带着个人的动机化倾向,因此身体行为本身也在这种交互作用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意义生成中的身体是主体自身的生命活动,不是单纯遵循机械因果律的物体,所以不能用单纯的生理机制来描述。
五、结 论
如果感觉体验不存在,那么笛卡尔从我思分析出的精神实体和广延实体似乎就可以并行存在而无矛盾。然而他并没有忽略意识中自明的感觉,由此证得与我切近的物体是身体,精神实体是有感觉的心灵实体。可是他又坚持理智主义,因此不仅二元论在身心关系中得到贯彻,而且相反的机械还原论也获得了生长的机会:一方面身体被还原为生理器官,另一方面心灵中的感觉乃至心灵所有能力面临着被还原为神经生理活动的危险。这种悖论的出现,在胡塞尔看来是因为他没有进行彻底的悬搁,没有发现感觉体验原初的意向性结构,而是带着理智主义的前见预设了身体、心灵的存在。从他在普遍怀疑的原则下既坚持理智主义又突入了感觉问题来看,我们便可以深入理解胡塞尔的这个观点,即认为笛卡尔既是近代唯理论又是经验论的起点[6](P85-86),并开启了冲破理性主义而突入先验现象学的线路[6](P74-75)。如果沿着胡塞尔的思路,坚持从原初感觉体验出发来描述身心显现方式,那么不仅身心二元论会被解构,同时机械还原主义也会显示为是悖论。不过笛卡尔毕竟看到了感觉、心灵的独特性,并坚持了心灵的主体地位,而在当代的医学、脑神经科学研究中,反倒将自然主义进行得更彻底,甚至抛弃了他的二元论,将心灵状态视作大脑活动的副现象,在具体科学实践中把身心都作为物来研究,因此完全悖论性地还原了主体意识,无视了个人的生命体验。这时我们不仅要返回到笛卡尔的哲学起点,阐明其因追求意识自明性而保有的对感觉的肯定,更要反思其理智主义的悖论,然后从胡塞尔现象学那里汲取对感觉和身体主体性的分析,从而使我们自身的生存体验获得关照。
注:
① 对于空间构成与动觉关系的详细分析,可以参看:刘丽霞《胡塞尔的“空间”构成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86-99页。
② 笛卡尔在谈论物体、身体时用的是同一个词(corps),这既是法语词汇本身所致,也体现了他有意在物体、精神二分的前提下来定位感觉。胡塞尔则明确区分了物体和身体,分别用的是德语词K rper和Leib,以体现身体不同于物体的感觉性和生命性。
③贾江鸿在《论灵魂的激情》中文译序中提到,笛卡尔在和伊丽莎白公主的通信中谈及,除了思维和广延这两个原初概念外,还有第三个原初概念,即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人。不过并没有看到他提出第三种实体的说法。具体可见:《论灵魂的激情》中文译序,第1页脚注3(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贾江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④笛卡尔在反驳“相似说”时举了声音的例子,说一些哲学家认为声音只是振动的空气撞击耳朵所形成的,如果按照相似说,那么我们感觉到的就应该是空气的振动,而不是声 音(René Descartes.The World,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volume 1[M].Translated by John Cottingham,Robert Stoothoff,Dugald Murdoch.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81.)。虽然笛卡尔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客观的物理过程不同于感觉印象,但恰恰也可以用来说明感觉与感觉的生理机制是不同的。
⑤国内学者李琍正是从现代医学角度肯定了他的机械论身体观,并对笛卡尔的神经生理学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对此可参看她的两篇文章:李琍《身体的权利——试论笛卡尔机械论身体观的哲学动机》,北京:世界哲学,2013年第6期,第44-50页;李琍《身体的激情——论笛卡尔激情理论的现代性》,北京:哲学动态,2015年第3期,第58-64页。
[1]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五篇讲座稿)[M].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5-26.
[3]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M].张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4.
[4]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5]René Descartes.The World,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volume 1[M].Translated by John Cottingham,Robert Stoothoff,Dugald Murdoch.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6]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7]单斌.空间是直观形式吗——胡塞尔与康德的空间观比较初探[A].倪梁康.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十四辑)[C].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376.
[8]Edmund Husserl.Thing and Space:lectures of 1907[M]. tanslated by Richard Rojcewicz,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7.
[9]Elizabeth A.Behnke.Husserl’s Phenomenology of Embodiment[J].In James Fieser&Bradley Dowden(eds.),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10]倪梁康.关于空间意识现象学的思考[A].倪梁康.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十一辑)[C].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6.
[11]胡塞尔.现象学和科学基础——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3卷)[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2]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卷)[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21.
[13]Shaun Gallagher.Hyletic experience and the lived body[J]. Husserl Studies3:131-166,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6.142.
[14]René Descartes.Treatise on Man,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volume 1[M].Translated by John Cottingham,Robert Stoothoff,Dugald Murdoch.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02.
[15]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M].贾江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6]张廷国.重建经验世界——胡塞尔晚期思想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28.
【责任编辑:来小乔】
The Paradox and Solution of Descartes’View on Sense and Bo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sserl
WANG Ji,SHE Bi-ping
(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
As an intellectual,Descartes did not neglect the sense which is self-evident in consciousness,but proved from the sense how the body exists,and nearly drew the conclusion that body and mind were integrated. However,he still insisted on intellectualism.Thus not only dualism was implemented in body-mind relation,but mechanical reductionism has a chance to grow as well.On one hand,body was reduced to a physiological organ. On the other,sense and even all the abilities of mind were on the verge of being reduced to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y,the occurrence of this paradox was due to the fact that Descartes did not make thorough epoche or find the intentional structure of sense.Husserl’s analysis of sense and body can not only resolve Descartes’paradox,but also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ine and neurophysiology.
Descartes;Husserl;sense;body;intentionality
B 516.52;B 565.21
A
1000-260X(2016)03-0052-06
2016-04-12
王继,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与现象学研究;佘碧平,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法国哲学、现象学及欧洲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