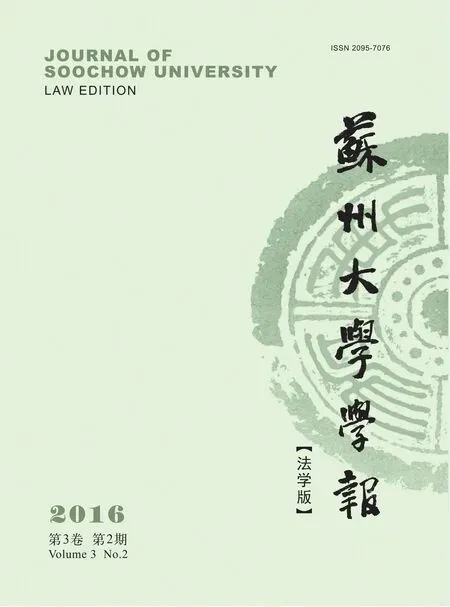私法教学改革与未来的民法典编纂*
2016-04-03智利阿尔瓦雷斯著
[智利]阿尔瓦雷斯著 姚 远*译
私法教学改革与未来的民法典编纂*
[智利]阿尔瓦雷斯**著姚远***译
现行私法教学有三大疏漏,即想当然、零散、不完备。理应把法律视为社会事实的结果,运用观察法学习法律史、实定法以及比较民事立法这三门基础课程。未来的法典编纂应该根据某些根本原则形成一套编纂机制,既允许私法为适应(而不是反抗或屏蔽)社会变迁而作出调整,同时又为法律制度赋予《拿破仑法典》时代的那种稳固性。我们所倡导的根本原则和指导理念,不是源自或多或少有着形而上学性质的理论和思辨,而是来自我们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所施加的现代立法趋势的观察。法典化宜根据制度而非根据主题展开。法国肩负着完成《德国民法典》未竟事业的使命。
私法教学;《拿破仑法典》;民法典编纂;法治改革
引言
§1. 政治科学和法律科学对各民族命运的影响毋庸置疑。它们既熏陶统治阶级,也锤炼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难道不是必定要通过选举,来参与国家事务的运作吗?他们的心态不正聚合成公共舆论吗?
由此可见,为这两门科学指明一定的方向,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乃是重中之重的事情。既然这两个主题的教育可以催生不胜枚举的裨益,它就应该从当代的需要和趋势中汲取灵感,因为每一门社会科学都顺应着社会条件本身的变化。这一点被认为是就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的。私法典的研究则特立独行。我经常听闻,私法典不是与时俱进的;纵然它确实与时俱进,我们也不能这样考虑问题,因为只要立法未作出修改,我们就必须始终适用法典条文。
我们在所有的法典化国家都可以明显感到,法典中的原则和各法院对这些原则的适用之间,各法院对这些原则的适用和现代生活的社会需要之间,隔阂日渐深重。法律不再符合正义,有时甚至背叛正义。有鉴于此,难怪立法者和法官日益斯文扫地!
未采纳法典化的国家,是否另有一番景象呢?倘若人家确有另一番景象,我们是要谴责法典化呢,抑或要把弊病归结于成文法典的错误解释方法和适用方法?兴许这两个理由同样成立吧。
我们在别处简要地考察了19世纪的社会变迁,①阿尔瓦雷斯将这些社会变迁作了如下简要分类:法律制度或其根本原则和指导理念,因应着《拿破仑法典》以来的三类影响,即政治事实、经济事实、理论。政治影响是指国家主权的衰落和民主政体的巩固;经济影响是指19世纪的工业扩张,它改变了不动产和动产的相对权重,并催生了阶级意识;理论是指我们经由社会团结观念和民主观念所感受到的东西。参见Alvarez,Une nouvelle conception des études juridiques et de la codification du droit civil(Paris,1904),pt. ii,chaps. v-x,pp. 111-146. 相应英译文收入“欧陆法律史丛书”(Continental Legal History Series)第11卷《19世纪大陆法系的进展》(Progress of Continental Law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aris,1917)。——英译者注【相关中译文参见方孝岳编:《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陶孟和校,曾尔恕、陈敬刚勘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译者注】及其对法律的影响(尽管有法典编纂)。这些变迁为法律关系赋予的性质,同那些法律关系在《拿破仑法典》颁布之初所具有的性质截然相反。各种关系已经变得纷然杂陈、界限暧昧、变动不居;法律关系趋向于国际化和社会化,并沾染越来越多的公法色彩。②尽管实际社会状态的立场反对《拿破仑法典》颁布时期的立场,从而也反对“旧制度”的立场;但国家在当今社会的地位日益显要,使社会服从于类似旧有秩序的警察法令,就此而言,当今社会趋近于“旧制度”的立场。越来越频繁亮相的社团、尤其是劳工阶级的社团——其性质和目的在许多方面接近“旧制度”的行会——则是当今社会和“旧制度”的另一个相似点。
因此,民法的条文虽原封不动,其所经历的调整却蔚为大观,民法的界限、根本原则和指导理念均已改变;《拿破仑法典》所包含的不少制度已被撤回,要么完全归于寂灭,要么融入公法,要么构成在原则和理念上有别于《拿破仑法典》的单行法规的主题。崭新的制度应运而生;作为主干的其他制度仍然经历着局部调整,如今既受制于当年激荡着《拿破仑法典》的那些观念,也受制于另一些别出心裁的观念。因此,这些五花八门的元素——有的来自过时的立法,有的来自新时代的制定法、习惯和司法造法——欠缺一致性。我们现在理应为那些不容小觑的法律难题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而非恪守《拿破仑法典》所给出的解决方案。③一些人虽然从新原则的立场充分领会新立法的重要性,却未能洞悉法律正在经历的间接变动。尤其参见Leroy,Le Code civil et le droit nouveau(Paris,1904).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三条结论:
1.一方面,当年的立法者没有提供让法律同实际生活情势相衔接的机制,另一方面,新的立法、教材编写者以及法院则正在很大程度上落实这一衔接工作。因而,法典化并未像通常以为的那样遏制法律发展。它仅仅插入一道屏障,将法律发展掩盖起来。这一事实只不过导致法典和社会不相吻合。
2.与众多一流学者的信念不同,④参见阿尔瓦雷斯提出的批判,收入Progress of Continental Law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oston,1917。——英译者注问题不单单在于寻求一定的法律体系,其条文更富弹性,因而可以适应生活的新需要;还在于发现一定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据之认识法律制度中迄今发生的变化,概览其真正的历史属性,进而汇总客观的解释指南,以便妥善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3.新的法典化体系,理应能够使私法同社会上持续发生的变化相衔接。这样的体系不应像现有体系那样遏制发展或者掩盖发展;但它也得确保法律关系像《拿破仑法典》支配时那般稳固。
一、私法教学改革
§2. 现行教学体制的疏漏。私法教学必须迎来新的时代。后代的法律教育必须有别于前人的法律教育。法学家、律师和法官必须做好准备,妥善解决社会上出现的愈加纷繁的问题。法律教育的改革迫在眉睫,其方向、趋势和方法亟待转变。
现行教学有三大疏漏,即想当然(empirical)、零散、不完备。
说它想当然,是因为一旦脱离制定法的条文,它就开始浸染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精神,对生活实情置若罔闻。
说它零散,是因为它被划分为众多单列授课的法律部门,而且有时这些法律部门互相对立,比如公法和私法。这种方法令我们难以感知法律制度的整体和本真维度,难以捕捉法律制度的内在性质。
它的不完备,是就若干角度而言的。首先,学生在钻研私法的各个部门时,局限于对法条的或多或少笼统的注释;他们注意到法律留下的种种疑团,以及从诸般事务中生出的新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根据的是传统的解释规则,参考的是法院的既成准则。真正生动且与时俱进的法律学习——作为一门立足于观察的科学——遭到彻底无视。法律学习的根本指导理念及其性质,这些理念在社会事实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下发生的或多或少深刻的转变,法律制度由于同样原因发生的变动,法律制度同实际需求的衔接模式——凡此种种皆被一笔抹煞。
未来人们理应排除详细的注释法学,代之以某些一般原理,便于我们明确把握所考察的法律制度的性质。简言之,人们须将法律学习塑造得更加实证和客观。
如何分配私法主题方可达成这一目标呢?新教学的基础和方法是怎样的?如果我们打算挽救当前的不幸事态,我想就得解决这些难题。
(一)课程的分配。过去的法律关系简单明了,如今的法律关系复杂含混,有鉴于此,一切法律部门——各部门法实际上都是在处理法律关系的某一方面——都应被归入单一主干(即实定法)加以学习。我们将在实定法中,从总体上探究全部法律关系的各个方面,例如,国内法或国际法、公法(行政法)或私法(民法)、经济法(商法、劳动法和产业法)或社会法。
接下来,须从一般特征入手,分别考察实定法课程所述及的主要制度,例如,亲属法、财产法、公司和社团法、一般契约法、雇佣契约法等等。
而课程的第三步,应该囊括关乎同一系列现象的全体法律部门,以便矫正迄今为止十分明显的一项缺陷,即把同类法律事实的学习再作切割。这样的话,学生将在同一类别中,在一门延续数年的课程中,或在若干教师——他们信受相同的统一性理想——所指导的数门课程中,考察具有共性的全部现象: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学生将彻底钻研每个现象的方方面面,其体现于法学著作、制定法和司法判决,体现于现实生活,也体现于应运而生的惯例。这类学习将强调法学和政治学的相辅相成,因为二者其实属于同一个大的系列。学生在学习宪法时,会将它作为立法和实践中所观察到的政治现象的一部分,并将它同行政法的某些部分联系起来。学生将在实定法中以及在学习各项制度时,触及行政法的其余部分。学生将把经济事实作为一组事物来学习,密切联系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来钻研法制的经济方面,这样就能够弄清每组现象的重要性、范围、对法制的影响,以及社会进化在每组现象驱动下所采取的方向。这类学习的结果,将真正令整个法学大获裨益。
最后,应该学习法律史的本真维度和充分意涵。法律史应该包含罗马法制史和比较民事立法。①为确保效益最大化,学生也应该从事一些实践训练,但应该从迥异于当下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实践训练。学生应该研究某些法律或制度的用处、它们的利弊得失、它们的调整成效以及它们在其他国家的效果。学生还应该有起草一般立法的经验,尤其要关注主题的界定以及形形色色的法益,了解立法者必须克服的困难和相关事项的指导理念。这类工作会吊起学生的胃口,久而久之,学生将脑洞大开;并且他会越来越意识到:法律关系的性质在变化,立法机关不可能规范和预见每一件事。后面这一点,新的法律教育理应开宗明义。
(二)基础课程。在我们看来,以上罗列的课程里,最基本的要属法律史、实定法以及比较民事立法。学生理应潜心钻研这几门课,运用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即观察法。我们为何确信这三门课是法律教育的基础?对它们能够运用观察法吗?①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将仅仅谈及主要法律部门所采用的学习方法,不考虑一般的方法论和历史考证,学生通过修习哲学课程或者通过法学院第一年的学习,应该已经熟悉后者。
§3. 法律史的学习。由于人们误解了制度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因此长期忽视制度史。它未被赋予科学的或实用的目的;过去的事情似乎仅是猎奇之谈。以前人们认为,惟有基于人性研究的法哲学才是真正的法律科学,它也因而应该成为立法的灵感来源——在持有以上信念的时代,法律史无从获得真正科学的目的。另一方面,鉴于以前人们认为立法者所创设的制度尽管有其历史,却借助于法典化而摆脱历史,被赋予独立的存在,因此制度史不可能具备直接的实用目的。于是,制度史学习的重要性遭到贬低。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人们在学习一国的早期立法时,采用了符合前述思路的方法,即一种单纯描述性的方法,依年代次序详细罗列一国的立法,而不进行批判的省思。
如今人们同样承认,法制史的学习有着根本的实用维度。我们若要理解现存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现象对其施加的影响,就必须了解现存制度的历史。
(一)弗拉赫(Flach)的观念和方法。如上所述,学习法律史,无论从科学的角度讲还是从实用的角度讲,都很重要。对此我们稍后再议;我们现在来考虑能够促成这双重目标的学习方法。
我们不必理会两种如火如荼的取向,即社会学的取向,以及摩尔根(Morgan)、麦克伦南(MacLennan)、波斯特(Post)和莱图尔诺(Letourneau)所代表的民族学法学的取向。法兰西学院的顶尖教授弗拉赫,因其首次表明和践行了达成前述两种目标的恰当方法而声名鹊起。他第一个站出来抵制双重错误,即单纯从民族的角度和单纯从描述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史。他斩钉截铁地指出,若不了解整个文明史的轮廓,就不可能研究任何单个民族的历史;同样,若不了解所有其他国家的制度史轮廓,就不可能研究某个国家的制度史。
在他看来,法律史等同于比较法律史。他说:“假如血脉同出一源的各民族,虽经千百年分道扬镳,在其语言、传统和民间文学中依然保有共同的遗产,那么这些民族为何不应在其法律中保存着上古的遗迹呢?相邻各民族曾经兵戎相见,今天你征服我,明天我征服你,后来又由于商贸、艺术和文学结成的纽带而唇齿相依,难道我们会否认这些民族对彼此的法律产生了绵绵不绝的影响吗?”②Flach,Les Origines de l’ancienne France(Paris,1886),Introduction,no. vi.
弗拉赫也让我们领略到制度的生命,亦即制度的起源、发展、环境事实对它们施加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施加方式。他说:历史研究“在于通过分类、比较和确证,毅然依照一种有条理且兼具批判性的方式,逐个国家、逐个种族、逐个时代地详细审视法律文本,从而,我们借助于分析(analysis)从海量素材中发现的要点,在那些法律文本中交相印证;以及在于慢条斯理、小心翼翼地建构一套科学的综合(synthesis)”。③“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 des législations comparées au Collège de France,”in Revue I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vol. xxxv (1898),p. 310;cf.“Le Lévirat et les origines de la famille”,from Annales des Sciences Politiques(May,1900),pp. 3-7.弗拉赫在Les Origines de l’ancienne France一书里,以及在他1879年以来为法兰西学院开设的比较法课程中,采用了这种制度史的观念和历史方法的观念。
(二)制度史。制度史的学习必须完备;它应该严格遵循归纳的方法。制度史的学习应该始于罗马人的法制,继之以关于西方国家之四大族群——拉丁国家、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日耳曼国家和斯拉夫国家——的制度总论课程。
上述整体主题的学习务必仅仅求其大要,从而呈现出各国制度的一般特征,以及诸般社会现象对制度施加的或深或浅的影响。制度史的时代划分应该比现行做法在时间跨度上更大、特点更鲜明;学生将考察每个时代中如下普遍现象的影响,例如,基督教、教会法、封建制、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斗争、宗教改革、君主专制。这样一来,才有可能准确评价历史大事的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唯有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制度,方可理解封建制。这样我们就会弄清楚,为何特定现象出现在一国而非另一国,例如,为何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法律是封建性的,而西班牙的法律具有显著的宗教性,甚至某些古老法典看来几乎完全是写给僧侣看的。
随后,学生将考察每一个时代,尤其侧重于其祖国所属族群的制度史。学习的宗旨是说明制度的起源和变迁,并揭示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环境影响。因此,学生首先要考察特定时代的社会环境,即形形色色的现象;其次,判定这些现象的强度和分量;最后,探索各种制度如何在这些现象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与此同时,学习中也将强调法学家和法官所运用的不同方法,他们在解释的外观下运用这些方法发展法律,使其或多或少准确适应新的社会需要。
水行政执法是水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依法治水的重要手段。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是维护正常水事秩序的需要,也是贯彻执行水法律法规的需要。只有执法主体和相对人都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才能有效地扼制水事违法行为的发生,创造和谐的水行政秩序,有效实施水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最后的课程将讲授某些主要法律制度,例如亲属法和财产法。这些课程旨在按照严格的历史线索,描述总论课程中已经分期考察过的那些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起源和演化,并且要比总论课程详尽得多。
(三)社会环境。学习社会环境及其对制度的影响,无疑十分困难。社会现象相当复杂,彼此相互作用,往往难以准确判定每种现象的影响力。况且某些影响可能非常微弱,并仅仅与其他因素一道逐渐产生相互作用。这些障碍纵然存在,学习终不能免,因为这方面的学习还是可行的。要是我们准备打破沙锅问到底,那的确困难,可要是我们满足于勾勒主线和一般特征——这是最优选择——倒也并不困难。这方面的学习要是打破沙锅问到底,其实并不妥当,除非这样做真有裨益。
虽然依照我们提示的方法学习法律制度确实是件难事,但我们将由此真正洞悉法律制度。这样的学习将阐明法律制度之间或强或弱的相互依存性,以及法律制度之根本元素和次要元素的可变性,前者体现于漫长的周期,后者的声势则更加迅猛。这样一来,法律制度不会表现为抽象的东西,更不会表现为不变的东西;相反,它们将被视作各时代总体状况的产物。
§4. 实定法的学习。如前所述,这种学习旨在从整体上大略地把握全部法律关系,而眼下人们在着手学习时却将其当作各自为政的分支。若要公允地领会法律关系的真正本质,以及法律关系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变迁,若要确保获得用以解决未来问题的客观规则,那种整体学习便不可或缺。
因此,首先理应重构(不断变化着的文明所塑造的)当前形态的法律关系,其次理应推导出客观的解释方法。
(一)民事制度的重构。如前所述,民法同其他实定法分支纠缠在一起,经历着不绝如缕的变化。《拿破仑法典》时代以来原封不动的制度和销声匿迹的制度,其实少之又少。然而,在字面上或精神上,它们几乎全都烙有旧法的某些印记,以及其他新的难以调和的印记。我们必须重构或重新整合这些改变了的制度,展示其真实面貌。应该把发生变动的元素分离出来,强调其独特性,而由于《拿破仑法典》的当前教学体制存在疏漏,这种独特性并没有得到彰显。经过重构的制度,不会像《拿破仑法典》所规定的制度那样明晰、持久、精确。它们会表现为或多或少的混合类型。可问题显然既不在于解释本身,也不在于解释方法,而在于立法所经历的变化。
撇开这条第一原理不谈——即便那些最顽固不化地恪守法律文字之人,也很难质疑这一点——让我们考虑考虑如何实施这种重构。在重构的过程中,法官或教师不得随意改变法律制度的属性。换言之,我们必须探求法律解释的成功进行所需要的客观准则。
(二)重构的方法。要进行这种重构,我们就应该首先通过总论,阐明法典编纂的根本原则、驱使立法者开展工作的观念以及立法的分工。然后,我们应该研究《拿破仑法典》规定的主要制度,特别是法律人格、能力、财产和法律行为,这些制度相当重要,支配着整个民法。
总论在民法学习中居于重中之重的地位,①纵然新的《德国民法典》已经颁行,德国法学家对总论研究的热情丝毫不减,为此撰写了大量作品。在这个主题上,法国目前为止仅有一部著作面世:Capitant,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civil(Paris,2d ed.,1904).旨在厘清民法的机理和真正范围。②这样就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即如何对三年攻读学士学位期间的课程进行最优分配。我们不可能在不经总论的条件下学习某些制度,这正是困难的根源。眼下法国各高校的法学院,正在考虑加松(Gasson)和维莱(Villey)向“最高公共教育委员会”提交的一项改革动议。《拿破仑法典》各项内容间将建立起逻辑关联,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分散排布。这样一套迥异于《拿破仑法典》的体例,其优势在于把某些主题融会贯通,而由于迄今仍抱持着一种信念,即各个方面分属不同的特定法律部门,人们往往不把那些主题归拢到一起,或者仅仅作出片面零散的分析。
于是,我们将在总的逻辑综合之下,学习关于财产的一切事项。我们将澄清财产的不同形式,及其各自所属的法律部门。我们将有详有略地考察财产的各具体分支——工业财产、商业财产、文学财产、艺术财产等——的独特要素,并最终考察通常意义上的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所有那些构成对他人财产的权利的民事③民事与商事相对。——英译者注制度,同样将被安排在一起学习,尽管眼下的教学无视其间的自然关联,采用了逐次分解的办法。
在着手学习每项制度之始,将首先概览该制度的不同历史阶段;不过,揭示该制度的演化过程这一任务将留给法律史课程,因为这样一种回顾的目的仅限于弄清制度的既往意义。接下来,我们要以立法机构和法院对制度的发展为基础,推导出关于制度的法学综合,据此框定制度的准确范围;同时,我们决不是要通过法学综合来预见一切可能的困难,所有采纳该方法的学者都犯下了这样的错误。
由此得到的无成见的综合,并不承认惹尼的批评意见,后者宣称每项逻辑综合都隐含地假定了一切实定法皆为成文法。④Gény,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et sources en droit privé positif,no. 25.上述方法其实无非是把科学的统一性运用到法律上,只有它能让我们准确把握各种制度、制度的目的、制度的范围及制度间的相互关联。
(三)新旧方法之对比。我们到此为止勾勒的方法体系,并不是新的东西。它曾为察哈里埃(Zachariae)所采用,在奥布里(Aubry)和拉乌(Rau)那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在布夫诺尔(Bufnoir)手中臻于完善。⑤奥布里和拉乌的体系受到批判,因其引论部分不够充分。我们向智利大学法学院提交了文中所述的民法学习规划,并获得采纳;该规划收录于Alvarez,La Réforme des études juridiques et politiques(西班牙文,Santiago of Chile,1901),pp. 46-83.
但这几位学者的疏失在于终究没有提出上述法学综合。他们认为制度是一成不变的,没有花心思观察制度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持续变化,这些变化正是制度的生命所在,其中恰恰包含着我们要为法律学习引入的新元素。法律学习必须抛却关于经院式问题的教条探讨,它们眼下挤占了总论课程的宝贵时光。这样的细节问题将成为有意从事此类学习者的专门选修课的研讨素材。一旦得出上述法学综合,我们就要转而关注社会现象所直接或间接催生的变化,并探究某一给定制度所关涉的各种法律部门的异同。这样一来,我们将了解每项制度的真正面貌。
上述重构若是经由观察得到的结果,立足于社会科学从而具备真正的科学性,则不能被指责为主观臆断,或曰必定出自建构者的纯主观心智。诚然,上述重构带有个人的色彩,但难道解释最明白无疑的法律规则时就不受制于个人考量吗?这类重构的价值并不因此受损,毕竟这类重构的基础——亦即塑造着它们的社会事实——是实实在在客观的东西。若是认为这种方法造成了混淆、杂糅了不同的法律部门,故而拒绝在学习制度时采用该方法,就等于对这些制度断章取义,没有展现出它们实际具有的形态。鉴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这些综合性学习须被不断修正,方能与时俱进——我们对此无需赘述。
对法律作出的这些重构,是法院不可多得的参考;法学家的真正使命,与其说是投身于事后诸葛亮式的争论,不如说是启迪法院觉醒。
(四)结果。我们的宗旨是:让法学摆脱那些包裹其外围的细节、争议和三段论,并通过对法律制度作出一定的考察——不是考察任何给定时刻(例如,当成为立法主题之时)的法律制度,而是考察它们迄今为止的全部演化过程——恢复法学真正的社会科学属性。我们将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演化本身由文明的发展所推动,立法不可能预见日新月异的社会存在所提出的一切问题。法典将不被视为包打天下的终极规定,而仅仅被视为对特定时代各个主题的反映。法典将仅仅成为我们据以观察后续制度发展的出发点。
上述重构应以比较立法学之要览为补充,后者将归纳同一批制度在自然划分的四组国家情境中的较一般特质。作为总论课程的一部分,这种比较的目的仅限于强调制度的相对性(它们总是随着时代或国家的改变而改变),并通过参考国外立法而提供一种立法指引。
最后,制度的学习必须借助于考证的方法,即运用政治科学、经济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统计学,甚至运用法医学的资料。①关于婚姻,参见Brouardel,Le Mariage(Paris,1899).此外,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应该说明特定群体的需要和目标。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社会主义者的群体,因为他们并不朝秦暮楚,而是有着旷日持久的抱负;他们的力量每天有增无减。②从这一点看来十分重要,参见Menger,État socialiste(米约的法译本,Paris,1904).
§5. 私法解释。法官和法学家认为,法典化之后,他们不再拥有从前的——即早期法兰西法和罗马法的支配时代——那种解释权。他们认为自己惟一的职责,就是恪守法律文本,遇到新问题时探求立法者的意图,而不考虑能否直接把既有的立法规定套用在这些新情境上。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在19世纪的进程中,他们虽然迷信法律文本,却尝试着——诚然是打着解释的幌子小心翼翼进行的——通过把法条理解得更加灵活、采取扩张解释甚或创制新的规则,令法典适应实践的崭新紧迫要求。最终我们看到,一批现代法学家如何寄望于达成法典和新社会需要之间的完全契合。他们缔造并果敢提出了法律解释的新观念,由此法学家和法官可以开诚布公地从事他们眼下投鼠忌器的事情。
在这批学者中,萨莱耶(Saleilles)对这一新观念的考察最透彻也最有新意,他勇于揭示这种新解释方法的客观要领。他在自己的一篇论文中表明,③Saleilles,“La Réforme de la license en droit,”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Apr. 15,1904),pp. 320-322.须区分法律解释中的两条考虑因素:(1)转换为一条法律规则的条件是否成熟;(2)促成这种转换应采用怎样的方法。他认为,罗马法不仅在过去而且甚至在今天都是这两方面的最佳楷模。
(一)未来的解释功能。在我们看来,令法律同实践需要相适应的问题,不单靠新的解释方法来解决,法典化并不能阻止法律制度的变迁。因此,若要再现法律关系的本色,就必须钻研这些变化。当我们钻研了这些变化,钻研了法律制度演化的模式和方向,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关于如下两件事的新观念:首先,解释的目的是什么?其次,如何达成该目的而又不被谴责为主观主义?
我们已经讨论过其中的第一条考虑因素。现在必须着手讨论第二条考虑因素。它自然而然分为两项追问:我们未来如何看待解释的功能?解释的方法将会是怎样的?
就解释的功能而言,我们不可能像萨莱耶至今念念不忘的那样效仿古罗马法学家,毕竟我们的政治社会状况今非昔比了。在罗马法的时代,正如在《法国民法典》颁布之前的时代,法律关系性质的变化缓慢且整齐,故而那个时代的解释只可能有一项功能,即把法律规则阐发得更加灵活。于是,逻辑成为唯一的工具,古人借助它创造了诸多精妙表述(subtleties),这些精妙表述标志着深藏不露、持续推进的缓慢演化。
该方法在今天不奏效了。法律关系几乎到处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它们不同于早期的法律关系。现在是个转型期,疑难之事蜂拥而至。因此,解释的功能就不能是把今非昔比的情况涵摄于现行立法规则之下,因为立法者若是当年不得不面对那些情况,肯定会设立迥异的规则。解释的当代功能显然必须是:帮助制度朝向社会现象所推动的那个方向演化,按照与那种演化相协调的方式解决新案件。
故而解释的这种新观念并不是专断的,它源于对社会事实及其法律关系影响的钻研,出自社会生活本身,摒弃这种新观念就等于无视作为活生生有机体的社会。
(二)未来的解释方法。依据这种新观念的解释方法将是怎样的?鉴于我们对解释功能的以上描述,问题便不再是拿或多或少精确的规则来框定解释,而仅仅在于能够通过解释查明特定制度的发展方向。我们不妨借助于前述的制度重构方法。
制度的演化并不遵循统一的路线。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同当前规则和通常信念相反的是,不可能存在统一的解释方法,我们必须根据法律关系演化的不同阶段,相应地诉诸不同的规则。因此,在制度演化的总论课程中,我们有必要考虑那些在19世纪一成不变或几乎一成不变的罕见情形;考虑作为主干的那些经历了局部修改但未曾改头换面的情形;考虑那些焕然一新的情形;最终考虑那些诞生于《拿破仑法典》时代、并且在性质上有别于《拿破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情形。
这四类制度的分界线不易划定,但这无伤大雅。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制度演化的方向,以便让法律解释与之合拍。
就第一类制度而言,应该按照立法者过去宣布的意思适用法律规则。应该遵循传统的解释方法,因为既然制度未曾改变,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制度的规定就无需调整,立法者过去颁布的内容足矣。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须注意,解释的目的决不像人们误以为的那样在于求得立法机关多年前的意图,而是要在给予法律字面适当尊重的前提下,为其赋予最合乎当前社会需要的含义。
就第二类制度而言,我们在解释法律时不宜再依照过时的规则,或者早期立法的一般精神,而须依照制度演化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新趋势。要查明这些趋势倒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影响到制度变动的事实已将其彰显出来。于是,例如,我们在解决家长权或夫权方面的问题时,就应该考虑如何最契合自由以及妻子或未成年子嗣的法律-经济独立性,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为了弄清一项制度的取向,我们必须诉诸我们已在现代法律中看到的总体特征,因为这些总体特征呈现出各项制度的前进方向。我们必须参考特定领域中比较立法学的研究成果,因为当今各国都面临着相似的现象,而各国的制度趋势都是以相似手段作出应对。
雇佣契约是第三类以及第四类制度中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在解释这方面的法律关系时,应该根据法律关系的新属性和新目的,而不是像迄今为止不幸成为惯例的那样诉诸民法的一般原则。①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不采用我们所提议的方法体系所可能导致的不便之处,即最高法院(Court of Cassation)对1890 年12月27日之法案——作为《拿破仑民法典》第1780条之补充——所作出的司法解释。该法案当时的目的是防止雇主强行解雇员工。最高法院不为该立法目的所动,遵循民法的一般惯例,很长时间以来都允许雇主搁置该法案的规则,并剥夺员工在不经告知即被解雇情况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认为这是产业管理的一种措施,理由是员工既然加盟雇主的产业,就等于已经接受了这些条件。这样一来,最高法院就把契约法旧日的一般惯例,用到了旨在限制契约自由的新原则上。
(三)该方法的客观性。上述解释方法,不像传统规则那样稳定和精确。但我们不妨对该方法心满意足,因为要获得那样的稳定性和精确性,势必牺牲法律规则与其所满足的社会需要之间始终应该存在的和谐关系。我们的方法不如传统方法那样清晰精确,但它却有着必然的客观性。它既阻却了人们对解释的滥用,又通过不断因应制度的常规发展,为悄无声息的法律变迁留下足够空间。
我们不接受如下反对意见:上述方法并没有牢牢固定在法律领域,它只是要用个人所理解的公正和善心的诫命取代《拿破仑法典》的规则。相反,我们那套解释规则之所以有效,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是因为法律作为有生命力的构造在经历各种变化,而我们那套解释规则的唯一目标就是遵循这些变化。因此,我们那套解释规则的根基是客观的,它真正在谋求实现社会正义,同时又不至于给法律关系带来丝毫烦扰。
§6. 比较法学。对外国制度的研究由来已久。18世纪的哲学家对此兴致勃勃,孟德斯鸠在其著述中十分强调这一点。因此,法国大革命所催生的公法就受到了比较法学的影响。
比较法学这一研究分支在19世纪有所推进;不过,法律史实在太抢眼,比较法学的对象仅限于东方文明。英国的梅因(Maine),法国的拉布莱(Laboulaye)、达雷斯特(Dareste)、吉德(Gide),德国的柯勒(Kohler)、耶林(Jhering)、萨维尼(Savigny),这些名扬天下的楷模向世人展示了法律生活的新方面,以及在时空上与我们相距甚远的文明社会的新方面。在过去25年间,比较法学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展,涵盖了西方各国的现行法律。学者不仅研究早期制度的历史,或者不同文明民族的制度史,还从事法律观念的比较研究,后者几乎在每个国家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②比较法总论方面的最早著作,参见C.-F. Gabba,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Milan,1862);Gumercindo de Azcárate,Essai d’une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a législation comparée(Madrid,1874);De Filippis,Cours complet de droit civil comparé(Naples,1881,10 vols.). 如下法文著作不应被归入比较法学的行列:Saint-Joseph,Concordance entre les Codes civils étrangers et le Code Napoléon (2d ed.,4 vols.,1856).
(一)关于比较法研究目标的不同意见。大家并未就比较法学的目标达成共识,这里有必要逐一考察那些相互分歧的观点。③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比较立法学大会,努力在各法律部门间就此问题达成共识。比较民法学方面的与会者发言表明,大家在这件重要事情上莫衷一是。
1.比较法作为一门技艺。该阵营包含四种观点。有人认为,比较法研究的目标仅仅是促使人们熟悉外国法。因此,它具有科学的价值,并且在实践中有助于国际私法问题的解释。
另一些人认为,比较法仅仅是为了推动一国的私法研究与时俱进。该观点曾经盛行于法国,当时法国引进了比较民法学的高级选修课。
还有人认为,比较法研究是国内立法不可或缺的准备工作,因为它向立法机关指明了未来推行改革的可能方式。
第四种理论的提出者是朗贝尔(Lambert)。④【阿尔瓦雷斯曾经提过这种理论,参见Alvarez,Une nouvelle conception des études juridiques et de la législation comparée,pp. 97-99.——英译者注】Lambert,La Fonction du droit civil comparé(Paris,1903),vol. i.在他看来,比较法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比较法旨在从所研究的不同法律体系中,提取比较的共同法(comparative common law),或曰一切国家共有的法。该工作的目的有二:(1)这样一套共同法将持续作用于作为其来源的各种不同法律体系,并通过启迪法院和激励立法改革而充当解释的指南;(2)更重要的是,这套共同法倾向于统一各国的私法,至少是逐步削减偶然的法律差异。
2.比较法作为一门科学。为了论述这第二个阵营的各种观点,必须提提三位人士的大名。
罗甘(Roguin)认为,比较法是一门旨在成体系地研究和对比不同国家法律的科学,并且强调各国为解决有组织社会的诸多难题所采规则之异同。①Roguin,Traité de droit civil comparé;Le mariage(Paris,1904),Preface.
不过,塔尔德(Tarde)并没有从实践目标的角度看待这门科学。对他而言,比较法的目标是科学的,即对形形色色的既定法律制度作出真正的分类,该分类要为一切法律体系赋予一定的位置,并让我们能够追踪每一种制度的发展过程。他要创制的法律体系分类,和其他人类知识领域——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等——的分类相仿。这样的研究将有利于推进社会学。②Tarde,“Le Droit comparé et la sociologie,”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1900),pp. 529-537.
萨莱耶认为,比较法既是一门基础性的科学,也是一门辅助性的科学。作为基础性的科学,比较法首先旨在从社会立场研究不同的法律体系,亦即观察它们的实施并比较其效果;其次,比较法应该立足于它们的根本相似之处,从研究各自为政的法律体系得出法律和惯例的一般原则并作出对比。最后,作为结论,比较法应该表述所处理的法律体系类型;这项比较性的评判,将成为不同国家法律体系逐步努力趋向的目标,当然,我们同时还要保留各种传统的形式及其相互之间的历史差异。这样一来,比较法就为所研究的每项制度提供了一种理想,而不考虑某个国家是否引入该制度。这后一个问题其实属于立法政策的讨论内容。作为辅助性的科学,比较法应该有助于本国法的进步,方式是确立一个兼顾立法发展、学者理论和司法解释的实证目标,以便让它们能够尽量接近理想类型,从而使它们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社会之共同法的素材。③Saleilles,“Conception et objet de la science du droit comparé”,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1900),pp. 383-405.此文是向1900年国际比较法大会的投稿。
(二)这些观念的缺陷。要指出我们所认为的比较法学理应确立的目标,只消批判视其为一门科学的各种观念。
关于把比较法视为一门技艺的前三种意见的缺陷,我们只需提提朗贝尔做出的痛快淋漓的批判,他的大作我们已经引证过。④Lambert,Études de droit commun législatif ou de droit civil comparé,Introduction:La Fonction du droit civil comparé(Paris,1903),vol. i,pp. 8-107.
不过,朗贝尔的体系本身似乎与他所驳斥的那几种体系一样狭隘。他开篇高调抛出一种比较法的观念,称其为一门科学;⑤Ibid.,p. 7.他在结尾时又将比较法的功能化约为一门技艺,⑥Ibid.,pp. 916-918,922-924.一门从所研究的不同法律体系中提取比较的共同法(或曰一切国家共有的法)的技艺。这么一套观念并不新鲜。萨莱耶就是这种观念的倡导者,诚然,他并不认为这是比较立法学的唯一目标,视之为次要目标。就此而论,萨莱耶的理论比较经得起推敲。⑦Saleilles,ibid.,p. 397.至于朗贝尔的理论则难以获得认可,因为它克减了这门科学的目标。
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律的统一性并不像朗贝尔主张的那样得自比较法研究,而是源于其他的更深层原因。①有朝一日将会达成完全而绝对的统一吗?通说对此予以否认,而且大多数学者相信,完全而绝对的法律统一既不可能也不可欲,因为据说这样会危及各国制度的原创性。另一些人——尤其是朗贝尔,他极其强调比较立法学是推进法律统一的手段——则认为,立法的绝对统一是可欲的,尽管不切实际。参见Lambert,ibid.,pp. 907-908. 还有一些人坚信立法的统一既是可能的也是可欲的,于克(Huc)大概可算作其中一位,参见Huc,Le Code civil italien et le Code Napoléon:études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2d. ed.,Paris,1898,vol. i,Preface. 于克认为《拿破仑法典》在这个方向上迈出重要一步,并认为一旦其他国家效仿《拿破仑法典》,一旦缔结足够多的国际协定,法律的统一就会成为现实。我想我们必须在此区分两件事。血脉同源的各民族——尤其是拉丁国家——之间的法律统一,几乎已是既成事实,因为拉丁国家都紧紧追随《拿破仑法典》。它们过去在公证婚姻和离婚问题上的根本隔阂日渐消失。如今,它们之间的分歧仅仅是细节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若非血脉同源的各民族之间要实现法律统一,相形之下困难得多,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基于历史和民族性的巨大差异。不过,若说这种统一纯属无稽之谈,倒也太过偏激。现代社会演化的特点恰恰在于,现代社会背离了自己的过去和个性。一切国家如今都受制于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新现象,由此催生相似的结果,各国人士也都在努力采取相似的解决方案,尽管各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千差万别。商法尤其如此。土耳其和日本在这方面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法律。这个现象正好说明了人们何以对比较法学抱有浓厚兴趣。各民族又一次开始相互融合。因此,法律关系趋向于(如我们所言的那样)沾染国际色彩并获得一致调整。民法(至少在大的方面)逐渐变得与国际私法合而为一,或者说,国际私法开始仅仅作为民法的一个新方面,因为将来它势必要为国际性的法律关系提供单独的一套规则。这样一来,它将成为推进法律统一的最强大实践动因。上述两种情况倾向于祛除民族法的个性,摧毁四个族群的法律体系的全部特征。如此看来,以下说法无可厚非:各民族过去的历史所特有的相互隔阂状况,为各民族的立法赋予了独特性和历史性,同样道理,各民族的融合以及它们如今所面对的同一现象,则趋向于有朝一日缔造法律的统一。可是,法律的统一并不会同等落实于一切法律部门。法律的统一已经开始表现在并将很快落实于如下法律部门:社会现象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或者各国之间的“重新对接”在其中贯彻得最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商法,以及民法里面的财产法(亦即债法和物权法)。亲属法就不是如此,尽管我们甚至在亲属法的某些问题上也能觉察统一的趋势,特别是在公证婚姻、离婚等问题上。【《19世纪大陆法系的进展》一书的第3部分“法律的国际同化运动”(“The Movement for International Assimilation of Law”)探讨了这个问题。——英译者注】
朗贝尔为比较的共同法赋予的第二个目的恰如其分,即助推各国的法律解释,但我们已经指出,这个目的固然是有待考量的最重要事项之一,却不是唯一的考量事项。
(三)真正的目的和方法。那么,比较法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它的真正方法又是怎样的?
比较法的目标是,在兼顾与之紧密相联的法律史,及从各种现象的前述整体研究中所得结果的前提下,展现真正的制度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创造真正的法理学。这门科学要兑现的目标和功能,相当于自然法或曰形而上的法哲学在过去乃至当今所兑现的目标和功能。②§7将讨论这个问题。
法学界一致认为,应采用观察的方法来钻研比较法。然而在决定如何观察的时候,共识便不复存在。迄今为止不幸占据主流地位的取向是,诉诸研究《拿破仑法典》所奉行的那种教条主义。该方法不能从比较法研究中汲取全部可能的裨益。
我们认为,真正的方法是我们在制度史学习中所认可的那种方法,毕竟比较立法学仅仅是制度史的延续。③鉴于朗贝尔把比较法化约为一门单纯的技艺,由此可知,他虽然承认法律史有助于这门科学,但并不认为这门科学能够采用相同的方法。参见Lambert,ibid.,pp. 913-926.弗拉赫认识到并强调了这一事实。他是实际践行该方法的第一人,④他在自己的比较民法学(亲属法和财产法)课程里贯彻了该方法,这门课他已在自由政治学堂(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教了25年以上。并且迄今得到一些顶尖法学家的首肯。⑤Bufnoir,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1890),p. 66;Saleilles,“Conception et objet de la science du droit comparé”,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1900),p. 395.
比较法确实必须同法制史学习紧密对接,比较法仅仅是在历史考察止步之处继续考察法律制度。在比较法以及法律史中,我们都应该观察和分析法制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并考察这种相互依存性,这种相互依存性正是令人欲罢不能且启人深思的研究对象。学习各项制度的时候,应该顾及它们的发展环境,否则就谈不上理解,我们的工作也就将仅仅成为对其心摹手追的小把戏。例如,除非我们了解大地产制对英、德、俄的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否则我们不可能理解这几个国家的农业立法。
学习比较法和学习法律史一样,应该从前述四族国家的法制基本原则入手。学生要观察制度与制度发展条件是什么关系;通过参考影响因素的异同,观察制度在每一族国家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观察制定法和判例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发生了哪些改变。这种总体考察,将使学生谙熟后续要学习的那些制度的本性。接下来,学生要再次学习四族国家中每一族的制度,只不过这一次的学习内容要详实得多,并且要比较制度以及制度的效果。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不同的法律是否由于所应对现象的相似性而显现出统一化趋势,抑或相反,某种切实的分歧是否能被人觉察。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会追问为何出现这种分歧,而一旦起因看起来不是难以两全的情况,我们就会寻求那种已经或看来被主要民族广泛认可的体系。①我在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寻求的就是这种比较法的方法和观念,参见Influence des phénomènes politiques,économiques,et sociaux,sur l’organisation de la famille moderne. 1900年以来,我就在智利大学教授比较民法学的课程。
§7. 法理学的真正基础和目标。法理学至今没有牢靠的基础,因此饱受质疑。迄今为止,法理学只拥有一套形而上的构造,被称为自然法或法哲学。人们已经弄清,该观念对于法典编纂的根本原则和指导理念,对于法律解释,对于一般而言的法律精神,有着怎样的影响。
归纳法在自然科学中带来的进步,相应地开始对抗法学中的上述形而上学取向。有人曾经希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成果锻铸法理学;甚至有人想过,法学应该接受进化论的指导。这些思潮的阐发者,是一个尤其在意大利有着强大号召力的学派。②例如,Cimbali,La nouvelle phase du droit civil;D’Aguanno,La Réforme intégrale de la législation civile,especially chap. vi;Chironi,Sociologie et droit civil;Saint-Marc,“Droit et sociologie,”in Revue critique de législation(1888),p. 59.该学派取得的成果欠缺明确性,因其基础不明确。其他意见认为,制度史是法理学的唯一建筑材料。但这样的基础并不恰当。
真正的法理学的唯一基础,就是批判地观察时空关联中的制度,及周围事实对制度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把握法律的生动原则,亦即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制度的次第变迁、制约着制度的因果关系、制度的指导原则。这样,法理学将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将不再像现在这样担当法学引论的角色,而将成为法学的结论,因为法理学是全部岁月法学心血的结晶。
从该基础向外生发的法理学(要是有人不喜欢这个名称,不妨换用法律史和比较法),注定要取代自然法,并且在科学影响和实践影响方面,同自然法的昔日建树以及今日依然具有的成就旗鼓相当。法理学将成为真正的哲学,因为它的目的是认识事物;法理学将使我们重新体认法律的哲学基础和目标,该问题在漫长岁月中都萦绕在哲学家的心头。基础和目标将不再像昔日形而上学法学家以为的那样绝对不可动摇,也不会像某些哲学家希望的那样从教条观念派生出来而置历史于不顾。③尤其参见Fouillée,L’Idée moderne du droit(4thed.,Paris,1897),bk. i,p. 1.[该书的节选英译本,收录于“欧陆法律史丛书”第7卷《现代法国法哲学》(Modern French Legal Philosophy)。——英译者注]相反,基础和目标将表现为彻底相对性的东西,表现为时代社会政治状况的产物。《拿破仑法典》时代的法律目标,据称是保障自由和平等;这两条目标已经实现;社会状况已然改变,法律的功能如今开始转向建立社会团结以及人伦纽带。
(一)法理学作为一种理想。新法理学将提供指引法律的真正理想。形而上学的和哲学的法学研究,令法律理想的观念声名狼藉,以至于“法哲学”这一术语竟成为荒谬无稽的代名词。新法理学的理想将判然有别。它要采纳的模板,不是某种终极而普遍的立法形式,而是这样一些类型的法律制度,它们对于并未闻知它们的国家来说,代表着一种容易兑现的正义理想。该理想将在这些国家引发一场运动来支持恰逢其时的改革,这场运动将比别处已经催生新立法的既有类似现象更加激昂。新科学提供的规范,不像以前那样抽象和绝对,而将是实质的和相对的,亦即取决于时空方面的考虑因素,并且能够始终精益求精。
因此,我们打算借着新法理学的契机,真正复兴一门关于诸般社会理想的科学,某些认识到这门科学的必要性、但不知道如何缔造这门科学的社会学家,就是这样称呼它的。①参见Georges Renard,“La Méthode d’étude de la question sociale,”in Revue Socialiste(Jan. 15,1897);Le Régime socialiste(4thed.,Paris,1904),App.
(二)法理学和国际法。法理学的另一个目标,与前述目标密切相关,就是凸显法律关系的国际维度及其最佳调整方式。我们已经谈过,法律关系正变得国际化,因而相互趋同。该事实催生了民法和国际私法的新局面,二者因此趋于统一。法理学将指明具有国际性的民事关系,并且人们将依照那些民事关系的最佳调整方法来引导国际私法。
人们显然没有理由提出如下抗议:参与阐述国际私法这一新局面的法官和法学家,背离了他们的真正职守。与通过解释法律文本来履行自己的新使命相比,法官和法学家的上述做法同样算是恪守本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职守都取决于法律关系的性质本身。无论法院多么尊重法律文本,如今在某些国际私法冲突中,即便没有制定法的明确指示,法院不是照样搁置属地法而实施外国法吗?在表述未来的国际私法规则时,这一点势必更加明显。
于是,对国际私法新局面的形成和发展而言,法理学将成为最牢靠的基础。
(三)法理学、立法和司法判决。法理学也将为立法者、法官和律师提供牢靠的指南。
法理学让立法者开眼看世界,了解其他地方存在的立法类型及其利弊得失。可以说,这是一种可令任何国家的立法机关都受益匪浅的先见之明。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应该照搬他所获知的那种立法。假如他认为必要,或者假如立法的统一性在他祖国那种政治社会状况下仍旧只是泡影,他就必须进一步改造他所获知的立法。我们的现代法理学,为立法者提供了逐步实现其社会理想而不至于激起血雨腥风的手段,因此迥异于先前那种无视理想实现手段的科学,也迥异于单纯诉诸暴力的大革命观念。
这门新科学也将令法官和律师受益匪浅,指导他们适用作为他国立法之借鉴或效仿的本国法。一旦在某个问题上还不存在本国法,我们这门科学的价值就是为法官造法奠定基础和指明方向,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法官造法最为可靠地帮我们判定社会变迁所指引的制度演化方向。法官和律师将在法理学中发现立法的真正精神,其实也就是显现在制度中的那些一般新趋势。如果我们要(在旧法许可范围内)塑造法律解释的方向,那么理解这种精神就是有益的。这样,各地法院将在充分占有事实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走法理学所探求的道路,让立法者在其准备推行的改革中经受磨练。
以上并没有穷尽这门新科学的全部目的,其他目的同样重要。这门新科学将形成新的法律标准,该标准具有根本的实证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现行标准所特有的那种形而上属性。最终,这门新科学将推动社会学的真正发展,而社会学迄今为止仍然是想当然的,无力摆脱纯粹的形而上学思辨,这主要是因为,作为社会学最牢靠支撑的法理学尚未找到真正立足点。
二、法典编纂的未来
§8. 未来法典编纂的根本原则。对于已经采纳法典化的国家,我们要如何阐述未来的法典编纂问题呢?
在法国,事实上正如在一切法典化国家,未来的法典编纂问题,通常等同于对《拿破仑法典》作出或多或少全面修订的问题,至多兼及探索有待采纳的指导理念。尽管有这样的想法,全面重新编纂法典的观念在意大利有不少拥护者,但在法国甚少得到响应。这不是因为法国人感到这样的任务纯属扯淡,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宜让法院负责调整法律以适应社会,或者说因为他们感到当前的《拿破仑法典》满足了实践需要,因此法律修订的唯一目的就是收录《拿破仑法典》生效后通过的法令。①最后这条意见,正是一部打算作为教材的民法学新著的意见,参见Surville,Éléments d’un cours de droit civil français(Paris,1904),vol. i,no. 78.
我们相信,迄今为止的研究足以否决这种论调。未来的法典编纂问题,仍以纷杂的头绪困扰着我们;实际上它是个让我们如履薄冰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要宣布法典化已然失灵,转而颂扬据说避免了法典化缺陷的英国体制?
或许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接受这种诱惑,毕竟法律关系的相互依存性和变动性使得法典编纂日益棘手。行政法领域的法典化尝试,正受到这一理由的强烈抵制。据说,行政法的法典化不但如镜花水月,而且分外不利,因为尚未法典化的行政法反倒更容易顾及公共利益。它被称为一种衡平法,这是对英国法的比附。②Hauriou,Précis de droit administratif(5thed.,Paris,1903),pp. x-xi.此外还有人宣称,在没有法典化的条件下,法院更容易扩展、塑造甚或创设法律规则;正是该事实导致人们把法国最高行政法院(French Council of State)的判决称为“准裁判官的”或“半裁判官的”。③Laferrière,Traité de la juridiction administrative et du recours contentieux(2ded.,Paris,1896),vol. ii,p. 411.这些通常在行政法领域盖棺定论式的考虑因素,似乎在民法领域同样如此。
可是,这样的解决思路太草率了。法典化的确有这样那样的弊端和困难,但也具备其他理应保持的重大优越性。因此,若对这个问题作出断然肯定的回答,将有失偏颇;比较可取的做法是,根据某些根本原则形成一套法典编纂机制,既允许私法为适应(而不是反抗或屏蔽)社会变迁而作出调整,同时又为法律制度赋予《拿破仑法典》时代的那种稳固性。
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随后我们将讨论新法典编纂的指导理念,及其最易取得成功的方法。
(一)相关理论。很少有人追问:要避免现行体制的缺陷,未来的法典编纂当采取怎样的根本原则?但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带着批判的目光,逐一审视现行法典化的根本原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许会找出线索来判定取舍。
就我们所知,关于未来法典编纂的根本原则,只有两种理论和两则事实可作为我们研究的立足点。这两则事实就是《西班牙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
1.我们必须考察的第一种理论,来自我们已经稍加关注的法国学者。在他们看来,现行法典化的缺陷完全归咎于一则事实,即它屏蔽了除立法之外的其他一切法律渊源,尤其是习惯和法官造法,故而理应改变法典编纂的根本原则,以便未来采纳这些东西作为法律渊源。
已经讨论过的理论无庸赘述,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些学者(或许是无意识地)经历一番辗转后,又回归早期法国法的体制,或者回归当前英国法的体制,而后者的缺陷我们理应避免。
2.第二种理论的提出者是瑞士法学家罗甘。他主张直截了当地偏离传统的法典编纂根本原则。他尤其认为,必须将立法职能和司法职能彻底分离。应该惟有立法机关有权制定法律;法院应限于根据立法者的意图严格适用法律,不要兼顾任何其他因素。
那么,罗甘认为应该如何维系法典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呢?他并不认可向习惯的回归,也不会把逐步改善法律这一任务托付给法院和学者;他同样反对采用那些因应实践需要而颁布的不完备法律。他的结论是:“唯一可能而且合理的方式,亦即看来没有任何弊端并能应对民法僵化风险的唯一方式,就是定期进行彻底的重新法典化。”①Roguin,Observations sur la codification des lois civiles(Lausanne,1896),pp. 77-98.他据此提议,在宪法上规定每隔25年要对民法典进行一次总修订,而且立法机关在法律上有义务将整部法典提交讨论和重新研究。未必每次修订都要改变法律,法律的改变应以必要为限。在每个25年周期临近结束之时,立法机关将公布新版法律,这样一来,无论专业人士还是外行人,都将拥有一套可以参照和适用的法律,而无需诉诸先前的条文。这将引发彻底的立法更新。
简言之,罗甘明确提议效仿俄国体制。②参见Korkounov,Cours de théorie générale du droit(切尔诺夫的法译本,Paris,1903[英译本收录于本丛书,译者是W. G. 黑斯廷斯,Boston,1909]).他同样借鉴了我们随后要讨论的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体制。为完善他的体制,他提议创设一个特别委员会,其职责是筹备法律改革并将之提交立法机关,因为惟有立法机关有表决权。③Roguin,op. cit.,pp. 98-104.
就立法意图的表述风格而言,罗甘不赞成简明扼要的风格。相反,他坚信法律的主题应得到发展;法律应当明确覆盖可能产生的各种具体问题,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不得同时表述抽象的规则。因此,立法者的工作成果既是普遍性的也是特殊性的。他认为,进步就在于增加法典的条文,并把一般规则和专门规则结合起来。然而,这样一套方法远不能造就完美法典,亦即“轻松应对一切难题的法典”。罗甘表示,为了尽可能实现他的理想,在前述法典之外,“立法机关应该表决通过一部官方评注,它与法典本身同时出台,实际上是法典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的拘束力”。这部评注的工作将交给立法委员会、执委会或其他类似机构。这部评注应该有一份说明所用术语的附件,经官方批准后随同评注一并公布。罗甘从国际私法领域援引了一条先例,支持自己关于官方评注的构想:1869年法国和瑞士就管辖权和民事判决执行问题所签署的协定。这项协定有一份说明性的备忘录作为附件,它与协定本身拥有同样的效力。④他要是援引如下协定的话会更有说服力:1883年3月20日关于保护工业财产的协定、1886年9月9日关于保护文艺财产的协定(最终备忘录)。
罗甘这样总结自己的观点:“法律应该是单单属于立法者的工作。法律的宗旨是解决已经预见的全部难题。我们应该仅仅根据立法者意图来解释法律。法律的形式必须严密而且清晰,法律的语言必须精确而且固定。”⑤Roguin,op. cit.,p. 133.
我们显然可将他的观点化约为两条:通过定期修订,维系法典与社会需要的一致性;在一切情况下都要弄清立法者的意图。因此,一切问题的回答要么来自法典,要么来自官方评注;法官的职能或许会比现行体制下更加机械,因为法官在每个案件中都仅限于严格适用立法者意图。
罗甘的基本观点里面,关于定期修订法典的那一条是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要求立法者通过制定法本身或者官方评注预见所有问题的那一条,既不可行也不必要,因为这不符合法律关系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和天然的非独立性。要求立法者就一切可能性作出规定而法官无所作为,恰恰违背了法律关系的本性。我们将会看到,法律关系如何要求立法者作出越来越有弹性的规定,而这意味着法院必须享有更广泛的权力来使法律适应社会环境。
(二)《西班牙民法典》。我们现在转向对事实的考察,首先考察《西班牙民法典》。
这部《民法典》在其三条附加规定中,要求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每年向法务大臣提交一份报告,说明《民法典》适用过程中显现的不足和困难;他们应当详细指出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和要点,以及可能带来疑难的条款和省略。法务大臣则奉命将这份报告连同当年的民事案件统计数据,一并转呈最高法典编纂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审议这些文件、最高法院判决以及西班牙不妨借鉴的他国法律进展,然后每10年表述一次其认为适宜的改革方案,并提交给政府。
《西班牙民法典》创设的这套机制,肯定标志着法典编纂领域的长足进步。可它不完全是西班牙的独创。1855年《智利民法典》包含着类似的条款,尽管不那么完备。它取法于早期西班牙法律的如下规定并将其发扬光大:凡遇疑难情况,法官应提请适格官员予以关注。①参见Alvarez,Une nouvelle conception des études juridiques et de la codification du droit civil(Paris,1904),p. 56,note(1),英译文收录于“欧陆法律史丛书”第11卷。应该提一提法国1828年7月30日的法案,它与《智利民法典》第5条大同小异,参见Dalloz,Jurisprudence générale,1828,iii,p. 3,art. 3:“Dans la session législative qui suit le référé,une loi interprétative est proposée aux chambres”,Bulletin des lois,no. 244,Law no. 8800. 该法案后来被1837年4月1日法案所撤销,如下文献记载了此事并附上了“事由”:Dalloz Jurisprudence générale,1837,iii,p. 152. 亦参见《乌拉圭民法典》第14条、《厄瓜多尔民法典》第19条和《秘鲁民法典》第11条。——英译者注
(三)《德国民法典》。虽然《德国民法典》代表着当今立法学的权威观点,而且注定成为将来立法者的模板,但它维持了《法国民法典》的根本原则;事实上,《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当时并未充分考虑根本原则的问题。
不过,这部法典确实包含着一些明确的创新。在法律渊源问题上,《德国民法典》对习惯的法律价值不置可否。这就允许德国法律人推断:具有成文法那样的拘束力,因而能够完善、修正甚或取消成文法的普遍习惯或帝国习惯,是可以存在的。至于地方习惯的法律效力问题,如今依旧众说纷纭。②Saleilles,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civil allemand(Paris,1904),no. ix;“Introduction”to the official 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German Civil Code,published by the Comité de Législation Étrangère(Paris,1904),vol. i,no. xvi;Gény,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et sources en droit privé positif,pp. 384 seq.
这部新法典的立法技术和法律术语特色鲜明,而且从解释的观点看至关重要。实际上,不仅该文本将带有教条性的观念一律清除,不仅没有哪个观念被包裹在法律程式里,甚至就在有必要隐含地采用某种法律程式的场合,正如不得不接受这种或那种具体解决方案的时候,该法典也会专门宣称:这类理论没有法律拘束力,仍然受制于法律思想的批判和摇摆。③Saleilles,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civil allemand(Paris,1904),p. 105;“Introduction”to French translation of German Civil Code,no. xxiv.不过,德国立法者虽然避免把法学理论确立为法律,却并没有排除法律定义。相反,法律定义的数量惊人,构成了这部新法典的最显著特征之一。这些定义的目的决不是表达理论观念或抽象观念,它们仅限于指明立法者通篇所用某些表达方式的具体准确含义。④Saleilles,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civil allemand(Paris,1904),pp. 110 seq;“Introduction”to French translation of German Civil Code,no. xxiv;定义和术语的清单,参见ibid.,pp. xli-xliv.
《德国民法典》包含一些规范法官权力的惹眼条款。法官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仅限于单纯解释法律的字面意思。在特定场合以及特定条件下,法官可以限制权利的行使或者更改契约;在某些情况下,他还拥有根据公道(而非恪守刚性规则)作出判决的自由裁量权。这已被人们公允地称为,法律在民事领域的司法个别化(judicial individualization)的首次尝试。⑤Saleilles,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civil allemand(Paris,1904),p. 118.
最后,就法律解释而论,尽管《德国民法典》避免明确采用任何体系,但从起草的筹备工作可以看出,它接受了前述萨莱耶的体系,有两位用心讨论该主题的教材编写者都持这一观点。⑥即赫尔德(Hölder)和埃利希(Ehrlich)。试比较Saleilles,ibid.,no. x.
总的看来,《德国民法典》并没有解决法典编纂的根本原则问题,它在这方面不宜作为将来立法的典范。《德国民法典》体现了进步,但恐怕它不久之后就会落伍,并带来法国法典编纂所带来的那些不便。
(四)根本原则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更加明确地表达未来法典编纂理应采取的根本原则问题。要让法典化得到迄今所示的那些优点,首先必须厘清立法者的准确出发点。为此我们必须摆脱成见,悉心观察在19世纪期间,哪些优点和缺点能够归因于现行法典编纂的根本原则,以及哪些优点和缺点能够归因于流行的新立法的根本原则。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已做过考察;我们看到现代法律如何处处受到新型指导理念的激励,现代法律的立足点今非昔比;而且我们认为,旧立法和新立法的抵牾主要归因于这个事实。当我们带着取舍的目光,重新审视法国法典编纂最重要的根本原则,我们必须首先判定成文法是不是调整法律关系的惟一法源。
其实这种通常的提问方式并不令人满意。问题实际上在于,什么权威机关理应享有法律创制权?
未来的法律创制义务应该单单托付给立法机关——这样的论调在我们看来不切实际。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反驳了以上论调。法律规则的发布机关,应当在详述法律时不受议会制度的阻碍,并顾及一切创新法律关系的力量。换言之,必须发现这样一套体制,它不把制定法的效力赋予司法判决或习惯,但会顾及司法判决、习惯以及其他真正缔造法律关系的元素。
惟有运用双重手段,方可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摒弃那条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原则,即立法职能和司法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必须同时允许立法权和司法权在一定范围内调整法律关系。再者,应该规定某些社会团体有权采纳约束全体内部成员的行为规则。这条原则将使民主理想浸润生活现实和法律现实。
(五)司法机关以及某些团体的立法权。1.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赏识行政权和司法权相分离的理由。这条原则巩固了新生政权,是政治自由的有效保障。在孟德斯鸠写作的年代,掌握行政权的主权者谋求尽可能地扩张行政权,达到滥用的地步。如今,在共和制的民主国家中,人们已不再为这种权力滥用感到忧惧。另一方面,假如司法机关被允许立法,将会出现公共职能间的真正合作,而不是一种职能吸收另一种职能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意志帝国,公法学家长期以来几乎不约而同地拒绝分权原则。①Laband,Le Droit public de l’empire allemand(冈迪隆和拉库尔的法译本,Paris,1901),vol. ii,p. 268,note 2;试对比Mayer,Le Droit administratif allemand(法文版,Paris,1903),vol. i,sec. ii,§6,pp. 83-101.相反,分权原则在法国风采不减当年,大多数学者把该原则奉为不证自明的东西,②Rossi,Droit constitutionnel,vol. iv,lesson 93;Jules Simon,La Liberté politique,chap. iii,no. 5;Aucoc,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administratif(Paris,1865),pp. 24-27;“Rapport sur le concours relatif à la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from the report of the“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Paris,1879);Saint-Girons,Essai sur la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Fuzier-Herman,La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Paris,1880);Ducrocq,Cours de droit administratif(7th ed.,1897),vol. i,nos. 7-54;Berthélemy,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droit administratif(1902),vol. i,§1;Jacquelin,La Juridiction administrative(Paris,1891),“Introduction”§§2-4;Roguin,Observations sur la codification des lois civiles,pp. 77-78.甚至照搬孟德斯鸠的论点。③与之相反,采用其他推导方式的,参见Vareilles-Sommières,Les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u droit,pp. 228-229.但他们也意识到,作为构成要素的这三项权力不应该相互绝对独立,只不过它们的职能应该彼此分开。
如果说立法职能和司法职能曾经有可能绝对分离,现在则不复如此。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一样,应该有权调整法律关系;法院应该能够发布类似于早期法国议会“一般法令”④“Arrêts de règlement”. 参见Brissaud,History of French Public Law,p. 445.——英译者注那样的规则。这项职能自然而然要托付给最高上诉法院,后者迄今为止的目标仅仅是确保各地法院解释的一致性。
这套体制决不是要把司法意见(尤其是最高上诉法院的司法意见)变成法律渊源。那样的话法官依然拘泥于法律文本,尽管他们在解释法律文本的时候,会通过或多或少间接的方式使其合乎实际需要。相反,我们的体制为法官赋予了一项至高权利,即在不提及任何制定法解释的条件下,设立有拘束力的法律规则。这样一来,立法和司法意见将相得益彰,而决不再两相对峙,因为法院一旦看准改革时机,将会正大光明地通过法律推行改革。
如果我们将现实的政治状况考察一番,就会看到上述解决方案势所必然。议会制倾向于让法律制定机关来统治而非立法;因此立法机关侵入了行政机关的职能保留地。那么,司法机关怎么就不可以在合理程度内取代立法机关呢?
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同一权力不能既制定法律又适用法律。但有何不可呢?难道我们不可以说,立法权有着非常特别的法律适用使命吗?当以制宪权身份行事的立法机构如今创制了宪法时,它以立法者身份行事时不正要服从这部宪法吗?当行政首脑及其代表被要求适用法令时,行政首脑不正是在以相同方式发布法令吗?那么,既然颁布宪法和行政法令的权力正是随后加以适用的权力,为何不可认为制定法的情况同样如此呢?要是司法机关有权在私法问题上立法,我们就能避免法典化的主要弊端。
该权威的范围有多大呢?这要由宪法或制定法说了算。但我们不妨在此就该问题提出一条准则。当立法者调整私法关系的时候,他惟一的目标就是创设宽泛灵活的一般原则,将其所查明的法律留给法院去填充;因此,立法者应当满足于指明那些据以建立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就足够了。于是,司法权将承担的任务是:根据社会需要,以或多或少准确而具体的方式调整法律关系。
2.至于授予特定社会团体的立法权问题,法律应就这些团体及其立法权的性质作出规定。法律要宣布用于治理特定团体的一般规则,这些团体则去确定规则适用的细节。这些团体甚至被赋予解决内生冲突的权力。法律为社会团体授予立法权的时候,必须广而告之,确保一切利益相关方知悉社会团体颁布的规则。
以上观念没什么新颖之处。某些要求立法特权的团体已经体现出上述趋势,而且某些劳工组织在数世纪以前就取得了立法特权。①Jay,La Protection légale des travailleurs(Paris,1904),p. 217.
(六)根据制度而非根据主题的法典编纂。应当断然否弃的另一项法典化根本原则是,根据主题编排各部法典,也就是说,把关乎某部法典标题的一切事项都整合在一部法典里。结果是,某项制度有多少方面,就由多少部不同的法典来调整。因此,在法国,《民法典》调整财产的民事方面,《商法典》调整财产的商事方面,《森林法典》则调整财产的乡村方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根据这样的方法,我们无从把握制度的真正本性以及制度正在经历的变动。
未来的法典编纂不能采取依主题编排的形式。上述理由,以及法律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在驳斥上述方法。未来的法典必须限定于单一制度;也就是说,同一部法典应该调整关乎给定制度各个方面的一切事项。我们将会有一部亲属法典、一部财产法典(其中将会按照合理分类说明全部的财产形式,例如商业财产、工业财产、农业财产)、一部公司法典和一部社团法典,还会有一部一般债法典、一部关于特定类别的民商事契约的法典、一部劳动法典,等等。
至于该方法从法律本身、法律解释以及法律研究角度展现的优势,我们毋庸赘述。
(七)其他根本原则。还有另一些基础,未来的法典编纂也要顾及。这些基础源自我们在当代法律关系那里发现的显著特征,即多样性、复杂性、灵活性以及社会趋势和国际趋势。
法典编纂若要符合这些基础,就必须立足于如下原则:
1.有鉴于法律关系的多样性,立法权威——一旦法官被赋予立法职能,也要按下述方式考虑法官——应该摒弃如下观念,即认为能够预见一切可能的法律关系,并在一部法规内加以调整。实际上,在那些法律关系出现之前,不宜用法律来加以框定。
2.有鉴于社会的复杂性,应以足够宽泛的表述来公布法律原则,使其能够同等适用于公法、私法或国际法。
3.立法者不应自负地认为能够同等精确地调整一切事项。他在工作中必须始终留心,他要调整的制度的灵活程度如何。如果这项制度的性质变动不居,那么他就应该摸索前行,包括起草暂行法,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实际立法,以及如果新法有效达成预期目标就愿意扩展新法的适用范围。
4.应该对法律作出非常宽泛的理解,法律要有足够的灵活性,这样各地法院才能不断让法律适应所面对的情况。
这条原则对现代的法律制定者而言并不新鲜,因为公法法规已具有该属性,而且负责实施这些公法法规的机关在解释的时候,享有很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对某些极端重要的问题,宪法和行政法其实并未加以规定。这样一来,它们的自由发展就不会受到任何法律条文的妨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情况同样如此。如今,不仅在评价犯罪的要件事实方面,而且在适用法律的时候,法官的自由都与日俱增。这方面的例证俯拾即是,包括细枝末节的认定、刑罚的悬置、关于不确定宣判的理论和关于刑罚个别化的理论。最后,我们也应该记得,中世纪那套专断的“法定”证明规则迄今早已声名狼藉。
5.宜把法律制定得灵活些,但此外还应为法官赋予《德国民法典》确立的三重权力。
6.有鉴于法律关系日益社会化的这一事实,负责宣布法律的权力也应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尤其当法律直接影响公共利益的时候。它应把这项监管工作托付给政府代表或利益相关团体。
(八)那些要否弃的原则。最后,我们必须考察旧日法典编纂的一些原则,现代的立法者应该予以否弃,因为它们不再适宜现存的社会状况。
第一条原则是法律适用的范围与国界一致。该观念起源于法国,当时是为了对抗“旧制度”的滥用情形,如今它在所有的法典化国家作用都被夸大了。理应放弃这条原则,跨越不同地理区域的国家尤其如此,例如拉美国家,那里各地的社会需要并不相同,因此得有适当的区域法规。关于水权、乡村地役权甚至一般土地权的规定,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不仅应该为一定的地区制定法律,或排除法律对特定区域的适用,而且也应该允许地方法院在预先设定的权限内,为了所辖区域的利益采取某些措施。
其次,不能再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原则来维持,至少不能按照旧日的绝对方式来维持。我们已经完成了这项改革的一部分,这项改革比前者的根基更加稳固,尤其在劳工立法领域。①1901至1902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二次泛美会议上,与会者提交了关于国际私法法典化的动议。动议的撰写者是国际法委员会秘书,他有能力起草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关于法典编纂理应采取的原则,他在动议中提出了本文这一节所表达的某些观念。泛美会议批准了所提交的法典化规划。参见Actes et documents de la deuxième Conférence pan-américaine(Mexico,1902),pp. 302-307.
§9. 未来法典编纂的指导理念。想要改革现行法典的人,仅仅盯着法典的内容问题。这方面存在三套理论,通常立足于经济社会方面的考虑,并且各有千秋。
1.社会主义者要求变革一切法律关系,方法是深刻改变家庭组织,以及压制财产权和继承权。门格尔(Menger)对《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抨击,代表了这一派中相对温和的取向。他的批判着实可圈可点,但在某种意义上过犹不及,因为其目标无非是创设工人阶级的特权。②Menger,Le droit au produit intégral du travail;“Du Rôle social de la science du droit”,in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1896),pp. 62-86;L’État socialiste(米约的法译本,Paris,1904). 对门格尔学说的批判,参见Nani,Le Socialisme dans le Code civil(Turin,1892).另有为数众多的一批人,要求推行各式各样的专门社会改革,按照他们的特殊性情,这些社会改革被视为满足当前社会需要的必要条件。这批人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学派。③Gianturco,L’Individualisme et le socialisme dans le droit contractuel;Salvioli,Les Défauts sociaux du Code civil;Polacco,Fonctions sociales de la législation civile moderne;Posada(西班牙法学家),“Le Droit et la question sociale”,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Vol. vi,pp. 225-250.
2.意大利学派一呼百应。它号称要按照实证科学的结果改革《民法典》,排除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立法者在研究法律进化时,必须参酌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结论,这些将使其了解法律现象的规律。立法者还必须准确把握社会需要。意大利学派宣称,只有上述要素准备就绪的时候,才能催生所谓“社会的私法典”(Social Code of Private Law)。
他们的方法过于含糊;他们倡导的改革要么不可接受,要么显而易见以至于如今无庸赘述。①要了解这个学派及其改革举措,参见Cimbali,L’Étude du droit civil dans les États modernes(1881),especially pt. i,chaps. ii,iii,iv,and pt. iii;D’Aguanno,La Réforme intégrale de la législation civile,especially chaps. ii,iv;Genèse et évolution du droit civil(西班牙文版),chaps. iv,viii,xii,xvi,xx;Cogliolo,La théorie de l’évolution darwiniste dans le droit privé.
3.最后一派将使未来的立法单单立足于团结(solidarity)原则,该原则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石,因而理应支配私法。这种观念现在不再新颖。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主义者和哲学家曾经清晰表述过该观念,尤其是傅立叶(Fourier)及其学派,他们认为团结是一条“自然规律”。由于我们道德观念——趋向于把大我置于小我之上——的进步,该原则如今广为流传。然而,尽管我们越来越赞同以团结的观念浸染法律,该观念仍然含糊不清,而且还没有谁条分缕析地表明该观念在什么意义上指导立法者。有些人虽然要求改革,但并不宣称隶属于某一派。②巴特比(Batbie)的题为《拿破仑法典之修正》(Revision du code Napoléon)的系列论文,投稿发表于Revue critique de législation et de jurisprudence,vol. xxviii,pp. 125-162,308-364;vol. xxix,pp. 116-167;vol. xxx,pp. 50-64,128-148,213-231,322-346,402-436.不少人仅限于要求民商法合一,理由是应该废除商人的专门法律特权。他们把《瑞士统一债法典》视为民商法合一的先例,该法典适用于一切类型的人,不做任何区分。
(一)《德国民法典》引入的改革。让我们从理论提议转向现实,考察现代法典、尤其是《德国民法典》所蕴含的指导理念。
《德国民法典》并未采纳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体系。然而,它抵制作为其他一切法典之基石的双重个人主义。首先,它拒斥那种始终孤立化地看待人的个人主义。它用一大节的篇幅规定法人;③Book I,title ii,arts. 21-90.法人的规则依赖于共同资金或资本的形成,并受制于社团团结的观念。
再者,它通过采纳团结性的四种法律表现中的两种,也背离了旧日的个人主义。诚然,它没有确立互助原则,尽管它在关于主仆的法律中对此有所触及;它也没有把责任延伸到表现出来的实际可责性之外。《德国民法典》在这方面没有进步;它恪守传统的主观可责性体系,没有设法确立客观社会风险的体系。不过,它确实明显认可团结性的另两种表现。它的规则将社会利益置于单个人利益之上;它特别采纳了关于“权利滥用”的准则[“以不损害他人财产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财产”(sic utere tuo ut alienum non laedas)]。《德国民法典》拿出整整一章,规定权利行使之限制、自卫和自助。④Book I(总则),sec. vi.它接受了关于权利滥用的理论,规定“权利的行使,不得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⑤Art. 226.法官可据此判定,一切权利行使一旦超越了善良风俗、公平和社会关系理解所划定的界限,皆属无效和非法。⑥Saleilles,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civil allemand,no. xi;and“Introduction”to French translation of German Civil Code,no. xviii;ibid.,notes to arts. 226-231,vol. i,pp. 334-349.在某些场合以及在特定条件下,法官可以修改契约。
最后,为防范家长权和夫权在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时的滥用,《德国民法典》创设了法院延伸控制家庭的制度,这是一种由司法官员代为行使的、针对家庭事务的国家最高监护权。
以上革新的结果是,意思自治在《德国民法典》中的作用,迥异于它在《法国民法典》以及其他显然基于个人主义原则的法典中的作用。《德国民法典》确实看重意思自治,但这并不意味着,意思自治像在其他法典中那样始终居支配地位,即便与法律相冲突时亦然。《德国民法典》的大多数规则,尽管不是绝对令行禁止式的,但也并不想代表当事人的意图,而是要确立法律意志的至高地位。按其规定,个人之间的约定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十分符合法律理应遵循的政策,也就是说,系公平和社会正义所要求的法律效果。诚然,当事人经一致同意后可以排除这些法律效果,但这样的废止必须清晰而且合乎形式要求,否则将推定适用法律规则。①Saleilles,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civil allemand,no. vi,尤其pp. 44,45,51.
此外,《德国民法典》将法律实施托付给个人,只要他的行为目标确实是依其判断在固定界限内行使权利。个人遂被赋予一种可以称为自由裁量权的处置权。但与此同时,为了明确一件事,即该功能来自法律的赋予而不是一项主观权利,《德国民法典》大大增加了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明确情形和默示情形,这项自由裁量权让法官得以在每个案件中做出恰如其分的判决,并且屏蔽规则原本具有的僵硬的普遍适用性。
(二)《德国民法典》的局限。《德国民法典》采纳了法律中的团结观念,但点到为止。它在两方面确立了团结观念,而在另外两方面则放弃了团结观念。
或许我们可以拿此事批评《德国民法典》,但我们不应责备它在社会路向上走得不够远。我们必须谨记,当今时代是危机和转型的时代,经济发展一往直前,进而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社会-法律组织。在这样的时刻不可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立法;我们必须为转型铺路;我们必须调和激进意见与保守意见。《德国民法典》那清楚开明的指导理念,必定受制于其诞生之时的转型期社会状况。这个时代与颁布《法国民法典》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特别适宜清晰的法典编纂。
这部新的《德国民法典》虽因没有全盘照搬法律中的团结原则,而留下颇多遗憾和期许,但恐怕这话并不适用于它所调整的专门制度,尤其是财产法所涉及的那些制度。这个领域中的各项改革,契合了现代经济社会状况。《德国民法典》对关乎如下问题的处理符合社会的新需要:债②Book II.以及物权(尤其是占有、财产取得方式、对他人财产的权利形态)③Book III.。亲属法④Book IV.和继承法⑤Book V. 参见Saleilles,“Introduction”to French translation of German Civil Code,nos. xix-xxiii;“La Théorie possessoire du Code Civil allemand”,from Revue Critique de Législation et de Jurisprudence(Paris,1904).亦如此。
但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情况下,德国立法者对问题的决断方式,除了过度的逻辑之外别无其他正当理据,而且在另一些情况下,德国立法者还不敢同基于罗马法的传统理论决裂。⑥Saleilles,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civil allemand,p. 119.
§10. 根本原则和指导理念变迁的缘起。须注意,我们所倡导的根本原则和指导理念,不是源自或多或少有着形而上学性质的理论和思辨,而是来自我们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所施加的现代立法趋势的观察。我们要特别强调,我们的主要观察结果是,鉴于社会状况与采用《法国民法典》之时不可同日而语,未来法典编纂的根本原则和指导理念必定判然有别。
1804年的形势有利于法典编纂。当时的社会状况分外简明,因为新的政治组织强劲有力,工业革命还含苞待放。问题仅仅在于调和当时并存的两套法律体系,以及使之契合于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当时的立法者不必关心,未来如何塑造法律以使其适应社会要求。他的目标是通过统一和简化法律,巩固当时的新社会秩序,故而他不须理会进化着的法律生活。于是,他在起草《法国民法典》时所依据的,就是那些会统一和简化法律、使之明晰化和精确化的原则。他的指导理念来自那散发着个人主义气息的新政治秩序。若按这些原则来推理,那么解释的全部功能就仅仅在于探求立法意图,而且解释者会将《法国民法典》所采纳的那些主要概念适用于现代问题。解释者的设想是,新问题在本质上等同于《法国民法典》所预见的老问题;而真实情况是,假如一个世纪以前的立法者预见了这些问题,他原本会按照截然不同的思路作出规定。
相较于1804年《法国民法典》通过之时,我们的社会状况今非昔比。我们不再置身于十分简明的社会状况,我们的时代经历着开放的发展;我们的个人主义体制正在湮灭,继之而起的是一种它无从知晓的新社会秩序,即社会主义。因此,当今立法者的工作迥异于立法者19世纪初的工作。问题不再是巩固一套社会秩序并统一和强化法律。我们别忽视如下事实:法律的加速进化终将转变现有秩序,并形成一套截然不同的秩序。实际上,这番进化必定成为新体制需要遵循的一个出发点;法典化必须从这里出发,迈向崭新的目标。
随着法典编纂的根本原则和指导理念发生改动,法律解释必定有相应的转变。当面对新的问题时,法律解释不能像以前那样寻求确定的立法者意图,对问题的性质置若罔闻,而必须不断调整法律,使之适应新的法律关系,这样一来,法律就会契合社会变迁为新法律关系赋予的性质。新的法典编纂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理应采取什么根本原则?法律解释要完成它的新功能,理应考虑哪些要素?对上述问题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的结论。我们还说过,德国立法者在这方面的角色表现不是完全现代的,法国在未来修订《民法典》的时候不应效仿邻国。
我们在权衡新法典要采纳的指导理念时务必慎重,要考虑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别夸大任何一条指导理念。
不过,团结的观念已为社会变迁所彰显,我们必须比《德国民法典》走得更远来发展该观念。我们不仅应该在《德国民法典》承认的那两个方面接受团结,而且应在另外两个方面接受团结,即互助的观念——尤其主仆之间、同一社团的成员之间以及一般而言有着相似利益的人之间——以及超越实际主观可责性的责任。简言之,只要条件允许的话,应该用义务来软化权利。
我们必须比《德国民法典》更加凸显一般利益或者团体利益——只要法律旨在让一定的团体受益——的观念,因为此类利益必须支配作为单元的个人的利益。何谓团体利益呢?这个问题不难判定,因为那些为捍卫该团体而创设的不同组织代表着团体利益。一般利益虽然有时不易确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得到精确判定,尤其是在工农业事务方面。
以上观念应该尽可能成为新法典编纂的灵魂,为它赋予新的生命,弥补它的缺陷,使它浑然一体。此外,惟有按此方式,我们才会拥有契合当代民主精神的法律制度。
就引入新法律规则并因应实际需要而言,德国的《民法典》和专门法规提供了顺利完成该任务的必要典范素材。
§11. 修订的方法。现代法律、特别是现代法典的起草方式,是立法者和政治家极其感兴趣的问题。
理论和实例密不可分。在理论层面我们发现,几位法国法学家提议在起草法律时联合最高行政法院,以便弥补立法机关起草工作的短板。①Varagnac,“Le Conseil d’État et les projets de réformes,”in Revue des Deux-Mondes(Sept. 15,1892);Tarbouriech,“Du Conseil d’État comme organe législatif,”in Revue du Droit Public et de la Science Politique(1894),vol. ii,pp. 272-285;Michon,L’Initiative parlementaire et la réforme du travail législatif(Paris,1898);Charles Benoist,La Réforme parlementaire(Paris,1902),Introduction,pp. xvi and xxxvii.
全面立法修订的倡导者贝特朗(Bertrand),②出席最高法院的国家检察官。明确地重新采纳了罗西(Rossi)旧日的法律起草观念。按照他的看法,议会应为法律修订奠定基础,然后转而要求行政机关准备草案。行政机关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将开展实际的起草工作。草案将提交立法委员会审查,并经过起草者和立法委员会成员的公开商讨。③Bertrand,“De la codification”(在最高法院开幕式的致辞),Paris,1888,pp. 30-31.
罗甘提议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后者既有权利也有义务筹备必要的立法改革,并将之提交立法机关,只有立法机关拥有表决权。照他的看法,这个委员会要么是类似于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机构,要么是从国家宪法取得权威的行政委员会,后者更可取。它的职能是研究并起草立法机关后面要表决的法律。他还提议建立一些具备相似职能的常设委员会,由议会两院的成员组成,或者建立一些具备超议会性质的常设委员会。初始工作就是向议会陈述未来立法准备采纳的指导理念。议会将对此表达自己的意见,继而开展制定详细规则的实际工作。该任务将交给适当的委员会,并根据议会批准的指导理念来执行。④Roguin,Observations sur la codification des lois civiles,pp. 100-104.
(一)《西班牙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起草方法。当我们放下理论,转而考察法律起草的实例,就会发现当今各国的法律准备工作与以往大相径庭。我们尤其看到,议会本身极少起草基于社会学调查的法律;法律由法律人或训练有素者组成的班子预先准备好,并提交立法机关。这些班子在就立法主题进行发挥之前,会先弄清事实、相关规则的性质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立法;这些班子也会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1.《西班牙民法典》的法典编纂方法自成一格。议会两院1888年5月11日发布命令,要求“法典编纂委员会”(尤其就民法部分)起草一部法典,并要求该委员会在开展工作时取材于1851年的草案、比较法资料以及立法机关在《1888年法案》中制订的28项基础规定。草案一经完成便提交立法机关,并在作出某些文字调整后获得通过。这样看来,《西班牙民法典》的编纂体制,近似于曾由罗西提议、1888年又由贝特朗重申的编纂体制。
2.《德国民法典》是按照另一种方法起草的。德国联邦参议院任命了一个五人筹备委员会,负责处理某些基本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素材的编排体例,以及未来《民法典》所涉及的范围(鉴于某些事项宜保留给地方法);接下来的问题是此类准备工作应当遵循的方法。
这部《民法典》草案本身的准备工作,交给负责具体实施的第一委员会。不过,草案的每个主要部分都有指定的起草人,后者就相应主题进行汇报,其文本将作为整个委员会的讨论基础。联邦参议院任命了12名成员在这个委员会中开展工作,他们要么是官员要么是教授。尤其那些被点名就特定主题进行汇报的成员,为此任务耗费了七年心血。此后,委员会的一体化工作启动,历时六年。草案被提交给帝国首相,继而转呈联邦参议院,后者要求官方发布草案,以便其尽可能为公众所知晓,并使之成为研究和批判的对象。这样一来,学术界和实业界就可以了解、审视、讨论和批评该草案,他们的批评意见促进了立法机关的工作。
后来,联邦参议院任命了一个新委员会负责准备第二草案。这个委员会有22名成员,不仅遴选自法律专家,而且多数成员遴选自国家重大利益的代表者,尤其是地主和工商业领袖。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辅助成员。这个新委员会把第一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并且新《民法典》的各个部分一经起草即向社会公开。这样一来就能在最终草案完成之前听取批评意见。实际上,该委员会对第一草案进行了彻底修改,由此形成经过修订的第二草案。
接下来,这份修订草案由帝国首相转交联邦参议院,后者将其报送司法委员会,指示该委员会予以审查并做出必要改动。司法委员会做出若干处改动之后,将修订草案发回联邦参议院,后者于是得到了由第二委员会起草并经过司法委员会修订的定稿。该草案由帝国首相呈交帝国议会,后者就应当遵循的讨论方法展开一番争论后,任命了一个代表所有政治派系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帝国议会酝酿的一些具有法律性质的改革。全体委员会中的所有政治派系,都恪守经过各自委员会代表所讨论和采纳的那些原则。全体委员会仅仅讨论某些具有社会性质和宗教性质的宽泛问题。经过全体委员会的认可后,该草案被发回联邦参议院,继而由后者批准。①要了解更多细节,参见Saleilles,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civil allemand,no. iii;and“Introduction”to French translation of German Civil Code,nos. ix-xvi.
(二)结论。在研究法制的进化以及前述立法实例后,我们不妨就未来法典编纂的最佳方法作一番总结。
首先,筹备委员会应该从容地研究法典编纂的根本原则。接下来不妨创设一个法典编纂常设委员会,其内部分工要么对应着通常的法律部门,要么对应着特定的制度,这取决于法典编纂的实施过程将立足于何种基础。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法学家和技术专家,只要他们对那个法典化主题感兴趣。假如该委员会按照特定制度来分工——我们认为理应如此——那么各部分法典编纂计划所涉及的每一种利益都应该在其中有所体现。
各工作组应该在各自的领域内,透彻钻研现行制度的缺陷,认真考量这些缺陷的权重,借鉴各门相关科学的成果。他们应该调查其他国家的问题解决方案,以及引入他国的某一种或某几种法律制度所可能遭遇的阻力。他们应该就改革的提议以及改革的应然方向,向社会中的利益相关团体征求意见。最后,他们应该界定如下事项:立法机关应在什么范围内调整那些制度,以及哪些事情适宜留给法院或相关利益团体来调整。凡此种种的信息——尤其在涉及社会学问题的事情方面——的获取,有时不算难事,②例如,笔者向1901年在智利圣地亚哥举办的首届拉美医学大会提交了一篇文章,题为《法医学和比较立法学视野下的精神障碍》(Mental Incapacity in Medical Jurisprudence and in Comparative Legislation)。笔者在文中提出了智利法律亟需的一些改革,以便智利法律充分汲取医学和经济学的成果,并从比较立法学的既有工作中获益。文中提议的改革包括:1.“失智”(demencia)一词的病理学含义有局限,应在《智利民法典》第1编第19题中替换为含义更宽的“精神错乱”(mental derangement)。2.不仅那些彻底精神错乱的人,而且那些只是官能足够失常因而无法照看财产的人,都应该被判定为由于精神障碍而不具有法律行为能力。3.《民法典》应采纳1856年法律的规定,后者类似于法国1832年法案关于疯人院就诊者的规定。4.精神错乱者的无行为能力状态,应该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使得精神错乱者本人或其继承者能以行为无效为由提出抗辩;这也使得他们有权认可其行为;这还使得他们的行为在时效期届满后不受指摘。5.神志清醒的聋哑人,即便不能通过书写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也不应在法律效果上被判定为无行为能力。6.铺张浪费者的无行为能力状态应该是相对的,仅限于财产转让行为;他在财产管理行为方面应该保有完全行为能力。7.迟钝愚弱者应该参照铺张浪费者来处理,经过确认的醉汉和酗酒者亦然。8.因疾病而丧失财产照看能力的人,应依其要求设立财产监护人。这样的财产监护不会导致被监护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只不过他们未经其监护人的参与就不能管理或转让其财产。因为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部门中都有常设的调查局,尤其负责调查劳工事务并向政府汇报其调查结果。
这些调查有了结论之后,就应该起草法律,而且法律草案应该广而告之,这样才能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公布一段时间之后,草案无论是否经过相应工作组的修订,都应提交立法机关,由其中代表所有派系的委员会商讨。立法机关应该仅限于批准或否决整部草案。
一旦草案经过立法机关批准成为法典,常设委员会将继续开展调查研究,并且每隔一段时间(例如五年或十年),都会根据立法机关应当认可的新法律原则,以及那些应当继续构成法院或特定经济团体之自主规定的原则,准备一份报告和一份草案。
(三)拉丁国家比较立法学大会。关于我们认为新法典编纂理应采取的根本原则和指导理念,以及落实新法典编纂的方法,我们已经得出研究结论。
我们认为,法国肩负着完成《德国民法典》未竟事业的使命。这样一来,法国才能在本世纪延续她曾经对法典编纂产生的影响力。但惟有在法国兴起一股卓有成效的学术运动,方可达致这一结果。最高教育协会(Société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立法研究会(Société d’Études Législatives)和比较立法学协会(Société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应该要求所有拉丁国家派遣代表共赴盛会。这样的想法是可行的,因为南美国家已经召开数次大会,欧洲的拉丁国家要这样做应该也不难。在这场大会上,各国代表将就本国借鉴自法国、但结果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的法律制度进行汇报。他们将说明制度失灵的原因,并解释本土的制度、采纳新法的理由以及由此造成的结果。关于每份报告的筹备和商榷,将成为拉丁国家比较法研究的精品。单单这一条就可以成为举办这场大会的正当理由。这类作品必定采取汇编的形式,不可能像通常以为的那样出自单个法学家之手。
通过这种大会的工作而获益的,不单单是作为科学的法学;实务界也将受益匪浅。我们极有可能就所有拉丁国家之统一立法的一般原则达成共识。和谐的状态将成为相对容易的事情。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大同小异,有条件达成这种立法统一。如果说全盘共识可望而不可及,那么各国至少可能形成某种相互理解,以便削减或彻底清除那些纯属偶然的立法分歧,或者表述国际私法的统一规则。这场大会的成果和决议,以及先前的准备工作,将成为拉丁国家法院的丰富信息来源,指明制度的当前变迁方向及进一步变化的可能方式。无论如何,这类大会的科学收获毋庸置疑。它将标志着拉丁文化复兴的一个阶段,并开启整个法律进步的新纪元。
于是,这将成为我们希望法律研究获得的新动力,以及关于法律解释和未来法典编纂的新观念。
一旦落实法律教学、法律解释和法典编纂这三重改革,法律就会至少转达时代的真正社会需要和它所追求的正义理想。法律将获得道德认同,后者是规则真正具有实效的前提。法律、正义和公平将最大限度地成为同义词。立法者、法学家和法官将各自致力于实现私法的目标,即按照当今社会的物质需要和道德观念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许小亮)
Methods for Scientif c Codif cation
Alexandre Alvarez(Author) Yao Yuan(Translator)
The present system of teaching private law has three defects of being empirical,disjointed,and incomplete. We ought to regard the laws as the results of social facts,and use the method of observation to study the fundamental courses such as “Legal History”,“Positive Law” and “Comparative Civil Legislation”. It is preferable to work out a system of codification upon underlying principles,permitting of the adjustment of private law to social change,without opposing it or concealing it,and yet conferring upon legal institutions the same security as under the Napoleonic Code.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and governing ideas which we have advocated are not derived from theories and speculations which are more or less metaphysical,but from an observa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present society and of the trend imparted by them to modern legislation. The codification needs to be enforced according to institution rather than subject. To France it falls to complete a work which the German Civil Code but partly realized.
Teaching of private law;Napoleonic Code;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Legal Changes
D913
A
2095-7076(2016)02-0029-25
*译自Alexandre Alvarez,“Methods for Scientific Codification”,trans. L. B. Register,in Science of Legal Method:Select Essays by Various Authors,trans. Bruncken and Register,The Macmillan Company,1921,pp. 429-497. 法文原出处是Alexandre Alvarez,Une nouvelle conception des études juridiques et de la codification du droit civi(lParis,1904),pp. 1-2,147-232. 标题为译者改写。本译文是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和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巴黎大学法学博士,20世纪拉美著名法学家,智利圣地亚哥大学比较民法学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