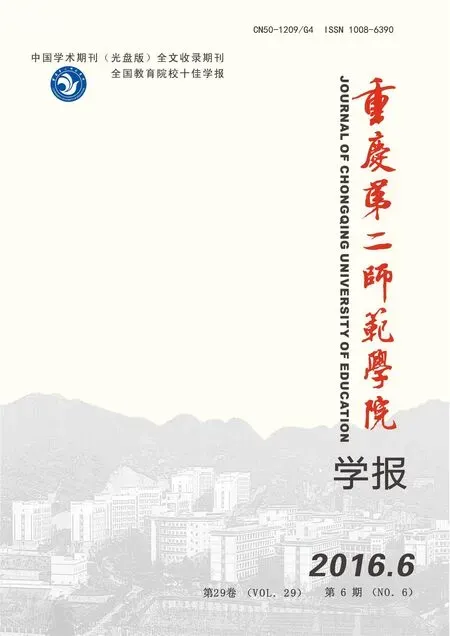《尚书》对商纣王暴君形象的文化阐释
2016-03-30李英
李 英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尚书》对商纣王暴君形象的文化阐释
李 英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尚书》中商纣王的恶行导致人神关系的疏离,也造成了人世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周人作为朝代更替的胜利者,对商纣王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是出于其维护新王朝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其所持有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反映了商周交替时期人们对历史兴亡的独特认识。
《尚书》;商纣王;暴君形象;伦理秩序
《尚书》描述了商纣王的恶行败德,并将他塑造为一个荒淫昏聩、人神共弃的暴君。商纣王的暴君形象是历史的真实记载,也是周人在天下初定之时重建社会政治伦理基础的一种塑造,揭示了周人对人神关系、王朝兴衰与政治秩序的独特理解,并对后世君主治国理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尚书》中的商纣王形象
商纣王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尚书》中,相关描述共13篇,其中《商书》2篇:《西伯戡黎》《微子》;《周书》11篇:《泰誓》(3篇)、《牧誓》《武成》《酒诰》《召诰》《多士》《无逸》《多方》《立政》,古文《尚书》中有《泰誓》《武成》,其余皆出于今文《尚书》。《商书》中的纣王自恃负有天命,肆意毁弃社会常法;《周书》中的纣王则怠慢神灵,施行暴政,荼毒贤臣和百姓。纣王的行为严重违背商周时期根深蒂固的神灵至上观念,并由此导致现实社会的极度混乱。
(一)荒废祭祀,不敬鬼神——人神关系的失衡
在商周时期,上天拥有掌控一切的神力,是令风令雨的主宰者。上天可以左右国家、个人的命运和吉凶祸福,人们心中充满了对天神的敬畏。祖先神灵是人间和天神相沟通的重要中介,先王先公可以直接宾于帝廷,向上帝转述人间的诉求,同时他们也有监督后世子孙并决定福佑或是降灾的权力。《盘庚》篇借用上帝和祖先神灵的权威对人们施加压力,劝说商人迁都,集中体现了商人的鬼神观,即盘庚借用上天和神喻来劝说人们迁都,体现了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和信仰,以及人神分殊时期神灵拥有对人世社会不可侵犯、不可违抗的绝对权威。
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畜:好)。[1]102
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1]105
鬼神世界与人世社会是同构的,后世子孙的善恶、是非、赏罚都由先王和祖先来判断和决定。祖先神是现实社会的价值源泉,维系着基本的道德和秩序,使社会保持稳定有序的法度。
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比:齐心)。”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1]103
商人对于神灵的崇拜呈现出一种宗教式的迷狂状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表达人间对祖先神灵的追怀和敬意,同时为政者希望借此来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古代的君主不仅负有治国理政的职责,也是沟通神人之隔的重要媒介。“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过其族。”[2]437君主祭祀神灵的各种行为都有严格的典章制度,若有不当就可能会遭受上天降咎。《高宗肜日》篇中祖己因高宗肜祭时有雊雉之异,认为是上天故意降下妖孽以警示君王修省正德,“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1]117,劝诫君王祀庙不可丰昵,要严格遵守祭祀礼制。
殷商时期的祭祀之风很浓厚,且祭祀名目繁多,“表现于占卜的频繁与占卜范围的无所不包,表现于‘殷人尚鬼’的隆重而繁复的祭祀”[3]561;“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4]724。在如此重视祭祀的社会背景下,商纣王作为君主却荒废祭祀,不敬神灵。《牧誓》载其“昏弃厥肆祀弗答”[1]132,《多士》载其“罔顾于天显民祗”[1]193。《书集传》曰:“祭,所以报本也。纣以昏乱弃其所当陈之祭祀而不报。”[1]132《尚书正义》曰:“不事神祇,恶之大者。”[5]424商纣王遗弃祖先神灵的宗庙,怠慢、亵渎神灵,没有履行作为君主沟通天人的义务,破坏了当时社会的人神关系和价值标准。
当神灵的权威和圣洁受到挑战和亵渎时,其便失去了对人们最基本的道德约束。据《微子》记载:“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1]121而《书集传》曰:“牺、牷、牲,祭祀天地之物,礼之最重者。”[1]121奉献给神灵的祭品乃是用以沟通神人的神圣之物,但草寇奸邪之人无视神灵的威严,竟敢亵渎并偷食祭品,且没有受到惩罚,表明当时的人神关系已经严重失衡。“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6]12君主以暴戾贪婪之风临下,则民亦化之。《微子》记载:“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1]120可见纣王的无德对当时的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沉迷酒色,奢侈腐化——自身私德有亏
商代的王为群巫之首,巫君与神明交相感应所必须具有的“‘与神同在’的神秘敬畏的心理状态理性化为行为规范和内在品格”[7]23,即君主不仅要对神灵怀有敬畏之心,而且自身必须具备美好的德行,才有资格承担沟通天人的职责。纣王既怠慢神灵,又不修德行,沉迷于口体之奉、逸游之乐,因而招致人神共弃。
1.酗酒无度。商代巫风盛行,酒在沟通鬼神的过程中能够起到帮助和促进作用。从现今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来看,酒器的数量相当惊人,可见当时饮酒之风十分盛行。《说文解字》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8]311性善之人饮酒有添于德,性恶之人饮酒则无异于助纣为虐。商纣王在生活上酗酒无度。《微子》有云:“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1]120“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1]121纣王身为天子却酗酒败德,上天将要降下灾祸。这里既体现出上天对君主自身道德的要求和约束,也可以看出君主的德行好坏与国家的命运长短有密切的关系。《酒诰》篇曰:“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1]174商纣王不仅自身酗酒,而且以风化下,秽德酒气闻于上天,非天虐民,不眷爱于殷,乃殷民自酿其祸。《诗经·大雅·荡》云:“咨汝殷商,无不湎尔以酒,不义不式!靡明靡晦,式号式号,俾昼作夜。”[9]852可见当时上至君主朝臣,下至普通百姓都染此恶习,殷商百姓酗酒已经达到不分昼夜的严重程度。
2.耽于逸乐。据《西伯戡黎》载:“惟王淫戏用自绝”“不虞天性,不迪率典。”[1]118纣王淫戏毁弃典制,自绝于天而天亦弃殷。《多士》云:“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1]193纣王不顾念先王勤于国家政事,大肆荒淫作乐,上帝不佑而降下大灾。“玩人丧德,玩物丧志。”[1]151“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1]70为政者若六者有其一,皆足以导致覆灭,纣王穷奢极欲,又何止有其一?可见商亡而周兴,也并非完全出自天意,实在是咎由自取。
3.沉迷女色。《牧誓》云:“‘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惟妇言是用。”[1]132《书集传》曰:“《列女传》云‘纣好酒淫乐,不离妲己。妲己所举者贵之,所憎者诛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颠倒昏乱。”[1]132纣王不仅沉迷美色,且国家大事不听取贤良之言,而偏蔽于妲己一人之意,置国法纲纪于不顾。
(三)智藏瘝在,毒痡四海——人世社会的混乱
商纣王自身德行败坏,造成人神关系严重失衡,而人神杂糅直接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价值标准的颠倒和基本道德的沦丧。正如《国语·楚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时所说:“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2]512
1.残害贤良,宠信奸佞。商纣王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偏蔽于佞臣小人,疏远甚至迫害朝中的亲贵和忠臣。《微子》云:“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1]121《牧誓》云:“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1]132纣王不畏其所当畏,不任用长老旧臣,遗弃亲族兄弟而不加以抚恤。故《尚书正义》曰:“小人皆自放恣,乃无所畏,上不畏天灾,下不畏贤人,违戾其耇老之长,与旧有爵位致仕之贤人。”[5]388“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6]239比干、微子、箕子等股肱之臣,劝纣王修身克己,勤政爱民,甚至不惜以死相谏;他们代表的是对天理道德的坚守,对纲纪常法的维护,忠心为国却落得悲惨的结局,可见纣王对待贤良如此狠毒,为政何其昏暴无道。
古来昏君凡是疏远贤良,必定会亲近佞臣,也必定会有居心叵测的小人依附左右。《牧誓》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1]132纣王纠集天下有罪逃亡之人,宠信尊崇之并委以大夫卿士之职。《立政》云:“其在受德瞽,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1]218《尚书正义》曰:“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恶,自强惟进用刑罚,与暴德之人同治其国,并为威虐,乃惟众习为过德之人,与之同共于其政,由其任同恶之人。”[5]688纣王所任用的大都是行为不端、德行有亏的谄媚小人,这些人不遵守正常的社会制度和规则,只是一味地逢迎纣王,投其所好并助纣为虐,其行为方式和行政方式不仅严重背离正常的社会制度,而且打破了长老政治和贵族政治的格局,致使诸侯日渐离心离德。是非善恶标准的颠倒带来的是政治上的忠奸不辨、贤佞倒置,以及行政方式的错乱。纣王排除异己,打压贤臣,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
2.暴行肆虐,荼毒百姓。政治上的混乱失序必然会波及到百姓遭受无妄之灾,承受暴政带来的沉重负担和痛苦。《牧誓》云:“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1]132商纣王暴戾无道,昏君奸臣沆瀣一气,劫夺商邑百姓的财物并草菅人命,表现了为君者的残暴狠毒所引起的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以及法度的破坏。《无逸》中的纣王不体察百姓稼穑之苦,“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1]198,耽于逸乐,不知小人之所依,必定不能尽抚民恤民之责。《召诰》云:“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1]181百姓有不堪其虐政者,携妻抱子哀号出逃,欲逃离此涂炭之地而不得,可以想见当时社会民不聊生的惨状。纣王身为天子以有天命者自居,肆意破坏法纪伦常,不恤百姓疾苦并肆意践踏和压榨,没有丝毫为君者应有的仁德之心。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6]356恤民者民亦敬之,虐民者民亦恨之,恨之者无不欲其亡,“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2]6。商纣王的残暴无道、涂炭生灵与当时周文王“不敢侮鳏寡”、“抚民以宽”、“克明德慎罚”的宽仁怀民相比,牧野之战中的前徒倒戈也在情理之中。
在今文《尚书》中,商纣王的恶行主要表现为荒废祭祀、骄奢淫逸、黜贤亲佞、施虐于民等,这些几乎是历代昏君所共有的表现,并没有过分暴虐的罪行。战国时期,商纣王的罪状则比之前增加了许多,出现了“剖心”、“斫胫”、“炮烙”等后世所谓的暴行。直到汉代,纣王形象在《史记》中被最终定型。有了前代典籍过分夸张的传言增词,在东晋的伪古文《尚书》中,商纣王的暴君形象较今文《尚书》更为突出。“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10]1099顾颉刚在《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一文中将历代关于纣王罪行的描写作了清晰的梳理,并认为纣王的荒淫暴虐行为是由历史“层累地”叠加所形成的。[11]“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6]250纣王的暴行虽没有后来人们传说的那么多,但既已有恶行负恶名,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们自然会把天下所有的恶德都归到他那里。
经由《尚书》的描写,商纣王的恶德昭著于历史,“助纣为虐”、“酒池肉林”、“桀纣之君”、“炮烙之刑”等词语都是后世在对商纣王形象“传言增词”的过程中演化而来,而他也被永久定型为一个人神共弃、昏聩荒淫的暴君形象,在此后历代王朝中出现的以商纣王所代表的暴政统治都遭到了百姓的憎恨和反抗。
二、周人政治伦理的建构
商纣王的昏暴统治带来的是当时人神关系失衡的严重后果,并由此造成人世社会伦理秩序的极端混乱。面对这样一个人神杂糅、彻底颠倒的社会局面,周人在建国初期力图廓清商末的社会恶习和不良风气,重建社会的政治伦理基础,使人神关系和人世社会复归于有序化和制度化。
(一)天威棐忱,民情大可见——天命即民意
在周灭殷之前,周文化属于殷商文化的一部分;灭殷之后,周朝继承殷商文化并继续向前发展,周人的鬼神观念呈现出新旧交替的特点。
1.天命不常。西周初期周人因袭“行天之罚”“受天命”的思想,“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牧誓》)[1]132,依然服从并信仰天神权威。“君权神授的观念自古有之,周人亦不例外,他们需要用君权神授的观念证明自己统治的正当性,他们也不会摆脱这种君权神授的观念,所以他们仍然相信这种观念,而不是只用来欺吓被统治者。”[12]176但同时周人的天命观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滋生对天神的清醒认识以及人的自觉意识,从之前对天神的盲目崇拜到开始逐渐意识到“天命不常”和“天命有常”。“天命不常”是指天命不是永恒的,不会永久地赋予一个王朝,如周公在《康诰》中提出“惟命不于常”[1]170,反对纣王的“我生不有命在天”[1]119。“天命有常”即上帝所降下的赏罚福祸不再是喜怒无常、难以琢磨的,而是与人的道德紧密相关。《君奭》中有“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1]204,上天降割殷命,武王有德而集大命于其身。“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1]208我后辈只有延续文王懿德,上天才不会绝弃文王所受的天命。周人以道德来作为能否受天命的评价标准,既成为小邑周取代大邑商的正当理由,也反映了人自身道德意识的觉醒。
2.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厥德!”[1]181天意决定于民意,民意决定于王的敬德与否。天意成为民意的体现,被赋予了道德与伦理内涵,这是周人天命思想中发生的重大转变。因此,《康诰》提出:“恫鳏乃身,敬哉!天威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1]166周公清醒地认识到了民意是王朝命运长短的决定因素,统治者要以怀柔治民,谨慎地勉力民事。这一认识上的巨大转变,预示着周初人文理性的开启。
(二)敬德保民,受天永命——祈求国祚绵长
周公在商周巨变的历史现实中意识到了统治者自身道德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民心的向背,而民意又可转化为天意,从而决定王朝的命运。因此,周公在文诰中屡次强调统治者要“敬德”“保民”,这样才能永享天命,弘扬先祖光烈。
1.敬德持谨。“敬”字早已在《尚书》周初的文诰里频繁出现,“敬德”则是西周初期提出的最重要的思想。《召诰》云:“王敬所作,不可不敬德。”[1]182“尤其是一个敬字,实贯穿于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这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13]20为政者既受天命,所作所为都当怀有敬德之心,若有疏忽则会丧失天命。《无逸》云:“君子所其无逸”[1]197,“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1]199就是劝诫成王当效仿文王,要勤于政事以得庶邦之供,不可耽于逸乐。《酒诰》云:“越庶国惟饮惟祀,德将无罪。”[1]172饮酒也当持一“敬”字,不可酗酒乱德。《周官》云:“居宠思危”,“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1]224要时刻保持安危意识,消弭祸患于几微之间,这样才能祈天永命,延绵国祚。为政者只有做到“敬德”、“明德”,才能长保王命。这其中包含有强烈而深切的政治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表现了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即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13]19,体现了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的萌芽。
2.用康保民。“保民”是“敬德”思想中的重要部分,《尚书》多次提到为王者当恤民抚民。《无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1]199周公以文王勤政保民之德,与纣王的耽于逸乐形成鲜明对比,借此深警并勉励成王努力承续文王美德。《梓材》云:“无胥伐,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1]177劝诫为政者当悯鳏寡、哀茕独、济孤弱,使民各得其所,用其所当用。周公从商周更替的变革中清醒地认识到了民意在历史变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只有安民惠民才能凝聚民心、永保天命。这既是周初统治者的治国纲领,也是周公政治思想中民本意识的体现。
(三)推贤让能,敬尔由狱——健全政治秩序
周人鉴于商纣王政荒民怨的严重恶果,在为政上极为谨慎,一再申明要选用有德之人治理百姓,并慎用刑罚,力图稳定新王朝的社会秩序,安抚朝代更替时期涣散惶恐的人心。
1.以公灭私,崇德象贤。周人在任人选官上与商纣王的黜贤臣、亲佞人形成了鲜明对比。《立政》云:“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1]220文王用人惟以有德者任之,且不敢居上以下侵庶职,严格遵守法纪制度。《君奭》有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1]204,文王用此五人以修和万民。“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无载尔伪。”[1]227在官位不可长骄横之气,持俸禄不可滋侈靡之风,而当恭俭养德,不可伪饰于人。周人自国初便开始反思夏商两代政治的失误,并认真吸取其用人不当的教训,在这里表现出神权意识的淡化,并认识到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透露了人文理性之光。
2.敬明乃罚。商纣王凭借个人好恶滥施刑罚,无视纲常法度,以致上天绝讫殷命。汲取殷亡的教训,西周初期的统治者对此特别重视,并提出了“慎罚”的思想。《康诰》突出显示了周公对刑罚的谨慎:
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1]166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1]167
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
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1]168
刑罚程度要根据认罪态度的好坏来定,如果能够悔改,虽有大罪也可不杀,而不思悔改者,即使是小罪,也不可不杀。对于犯罪者的判决要慎之又慎,案件需要经过多日再作断定,以免操之过急导致误判误罚。这里提到了不仅大奸大恶之人当被刑罚,不孝不友之人也不可宽恕赦免,否则就会扰乱人伦秩序,破坏纲纪礼法。可见在西周初期,刑罚的适当与否对于新王朝的稳固以及纲常伦理秩序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从周人文诰发布的对象及内容可以看出,周初统治者对待殷商后裔和周人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对殷商后裔强调周代殷兴是由于纣王昏暴无德,上天黜降殷命赐予周,周革殷命是顺承天命,不敢不从。如《多士》云“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1]192,《多方》云“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1]213,表明伐纣之举合乎天意,而非犯上作乱之举;对周人则强调天命不常,要居宠思危,如《君奭》之言“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1]202,“天不可信”[1]203,敬德慎行才能常保王命,体现的是周人对兴亡更替的清醒认识和面对胜利的忧患意识。
三、结语
从周人对商纣王暴君形象的刻画中,我们可以窥知在商周时代天命决定论的思想背景下人们对天命、民意、王命等天道观的独特理解,周人对与王朝兴衰、民心向背的历史观的理性认识,以及所建立的以“敬德”、“明德”为基础的政治伦理观念和秩序。在此后漫长的历史中,后人对商纣王的评价都深受《尚书》的影响,纣王已被固化为暴君的符号,历代明君贤臣无不以之为前车之鉴,借以自警和自省,而不为善政的昏庸君主也会被世人比为“桀纣之君”而遗臭万年。“德”也成为衡量后世君主贤能与否的道德标准,并以此要求人君不仅在政治上能够选贤任能,广开言路,虚心接受贤良之士的讽谏,而且要以仁慈之心爱护百姓,即孟子所谓的“民为贵”,还要严格约束自身,修省蓄德以正君心,作为天下仪则,成为万民敬仰和效仿的道德楷模。
[1]蔡沈注.书集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2]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3]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孔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金良年,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M].北京:三联书店,2015.
[8]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9]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0]张双棣.淮南子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顾颉刚.古史辨: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2]陈来.古代宗教与理论——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三联书店,1996.
[1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责任编辑 于 湘]
2016-06-12
李英(1990— ),女,河南邓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I206.2
A
1008-6390(2016)06-007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