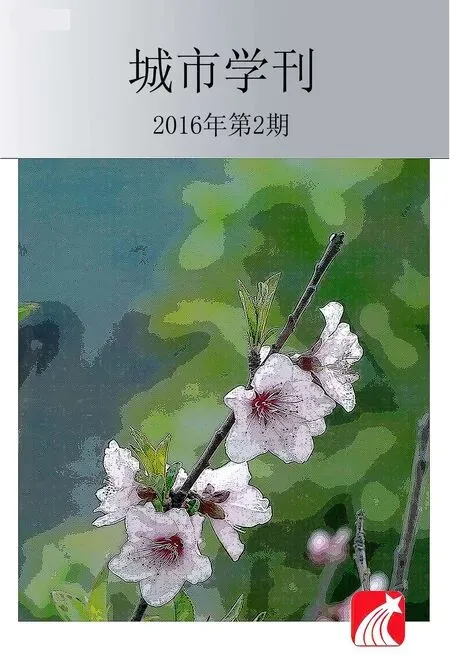关于隋唐长安皇城的几个问题
2016-03-29赵阳阳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710062
赵阳阳(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 710062)
关于隋唐长安皇城的几个问题
赵阳阳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 710062)
隋唐长安皇城虽来源于“隋文帝新意”,但皇城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包括宫城外官署机构集中和宫城内官署机构发展变化两方面,到了隋代才发展出成熟的皇城制度。皇城与宫城在规划上实为一城。隋唐皇城的出现,最终完成了“两城制”向“三城制”的转变。唐中后期,皇城出现新的变化,宋元明清各代的皇城,名称虽延续不变,但形态结构和功能却迥然不同。从隋唐皇城出现到明清皇城的演变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隋唐时期;长安城;皇城;城市空间
皇城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宫城一起构成都城中最重要的政治空间。皇城制度肇始于隋,开古代都城中央官署机构集中布置的先河,影响深远。皇城作为中央政府官署机构集中布置的专门区域,是隋唐时期都城建设的一大创举。
关于隋唐长安城,一直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成果蔚为大观,汗牛充栋。但由于某些文献资料的缺略和学人关注点不同,以至于一些问题仍有较大的挖掘空间。比如说对这一时期长安皇城的考察,虽有杨宽、史念海、刘庆柱、傅熹年、王维坤、李久昌、张永禄、肖爱玲等诸多学者对该问题有过探讨。[1]但其所论多从皇城形制和空间构成等内容展开,而关于皇城形成与“隋文帝新意”、皇城与宫城的关系、皇城与都城空间发展、后期皇城新变化等问题尽管也有所涉及,不过某些方面仍有不清之处,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在前人相关论述之基础上,意欲就上述问题谈一些浅见,以求方家指正。
一、皇城与“隋文帝新意”:皇城的形成轨迹
皇城虽肇始于隋大兴城,但在隋唐两代文献中,并未发现有关皇城产生原因和过程的相关记载。直到宋代,宋敏求在《长安志》中首次提及皇城出现的原因,认为皇城产生出自“隋文帝新意”:“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帝新意也。”[2]
这是已见较早对隋唐长安皇城产生原因的专门论述,元代《类编长安志》记载相同。可见,皇城主要是为解决旧有都城中的不便问题——“有人家在宫阙之间”而专门新置的。但宋氏所论过于简单笼统,不能很好诠释皇城从无到有这一阶段的过程和变化,因而有必要重新考虑。
目前尚无对皇城形成过程和“隋文帝新意”的专门探讨,大多认为隋唐皇城制度向上追溯到曹魏邺城或汉魏洛阳城。①如宿白认为古代都城中央衙署开始集中分布自曹魏开始,见《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刘庆柱认为在东汉中晚期以来出现的宫城单一化和中央官署集中化趋势发展的基础上,北魏洛阳内城出现,实质就是隋唐长安的皇城。见杜金鹏等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5页。史念海认为北魏洛阳借鉴南朝建康的规划布局,在宫南御道旁群列府寺,是隋唐“惟列府寺”皇城的滥觞。见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23页。傅熹年认为北魏洛阳内城和邺南城规划,宫前衙署的扩大,是隋代发展出皇城的前奏。见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06-107页。这些论述基本着眼于古代中央官署机构在宫城外集中布置的变化,事实上忽略了发生在宫城内的另一个变化——在宫城内,中央官署机构也在不断调整变化。笔者以为,正是这宫城内外两种趋势发展的共同作用,方才促成成熟的皇城制度。
隋唐以前都城,总体没有严谨的功能分区,呈现出宫殿、官署、居民市里等混杂无规状态。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宫城内,存在一批“闲杂人等”,②中国古代都城中,很多中央官署机构的办公地点就在宫中,以备随时被帝王召见咨询、处理政务。为保障这些官员的正常生活,因而他们的随从和家属也可一同入住宫中的官署机构中。这方面例子很多,如《后汉书·赵岐传》记载:“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也。初名嘉,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注曰:以其祖为御史,故生于台也。”(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21页。《后汉书·黄琼传》记载:“初(黄)琼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第2033页。《陈书·徐陵传》记载:“自晋以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省在台城(即建康宫城)内下舍。”(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38页。包括一些低层的政府行政官署及官员,官员的门生随从、家属等;二是宫城外,部分中央官署机构与居民生活里坊相杂处。[3]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宫城作为皇帝专有的朝寝生活场所,这些非机密或御用性质的行政人员和闲杂人等,势必要移出宫城。而宫城之外的官署机构,为便于安全防卫和提高效率,使官民各不侵扰,也需要互相分离安置。这两个趋势的共同发展,最终促使皇城成熟地出现在隋唐都城中。弄清楚皇城制度源头后,就可以把这一过程分为几个剖面,理清这个制度的发展轨迹和历程,可加深对皇城制度的理解。
(一)秦到汉:宫城内尚书崛起,部分官署机构开始集中
西汉长安城缺少全局事先统一规划,造成闾里夹杂处于宫阙官署之间局面。[4]中央官署在宫城内外都有,如丞相府在未央宫东阙外,大司农所属太仓和中尉所属武库在未央宫以东等。[5]这些国家行政机构布局分散,与居民里坊混杂,不仅不便于平民的正常生活出行,也不利于中央政府的统治和管理。到了东汉洛阳时,都城布局出现新变化,当时主要的中央官署太尉、司空、司徒“三公府”已比较集中在都城中南宫东南开阳门内一带。[6]
秦及西汉初年,宫外丞相开府辅政,权力极大。“初,秦变周法,天下事皆决于相府”。[7]相府内人员众多,分曹办事,形成一个直接听命于丞相的掾属群僚班子,领导并协助宫城内诸卿行政。相权一支独大,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丞相群体代表功臣元老集团;另外也与当时君主专制制度刚建立不久,皇权专制制度尚未充分发展有关。皇帝尊重并且信任丞相,放心地把大权交给丞相,形成以皇帝与丞相为首的统一的决策行政中心。[8]丞相权力内外兼有,参与决策、诏书起草下达、监管全国政务的处理。西汉中期以来,专制主义发展,君主不能容忍受制于相权的局面,开始调整权力中枢,建立内外朝制度。[9]削弱相权,提高尚书的地位和权力。打破过去君权统一中心制,使宫内逐渐出现一个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议政决策集团。皇帝依靠内朝制约外朝,丞相外朝渐向主行政趋势发展。内外朝体制加强了皇帝对决策权的直接控制,开始把决策权移于宫廷,权力中心由宫外丞相府转移到宫城中皇帝手中。东汉尚书内朝制度继续发展,以尚书为首的内朝官在皇帝的操纵下,不仅参政议政,且侵夺外朝公卿权力,直接指挥行政,大有取代原有三公,发展成为新的宰相机构的趋势。因此,随着君权的不断加强,尚书逐渐由幕后走向前台,由权力边缘走向权力核心。尚书的崛起,实质是皇权的强化,“三公”府所代表相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逐渐下降,其机构也相应出现外移的变化。
(二)魏晋时期:宫城内出现宰相机构尚书台,中央府寺分化并外移
魏晋时期,尚书台脱离少府,正式成为独立国家机构。[10]尚书台取代过去的三公,权力发展到极盛,总揽天下政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机构,是宫城内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行政机构。而原先宫城之中兼有职掌皇室私事的诸卿机构,经过权力的剥夺与分化,逐渐分离出了尚书、侍中等近侍、谏官、决策官和宫廷服务等内廷服务的官职,以补充宫内中朝官和宦官系统,其余的逐渐移出宫城,开始了公卿府寺在宫城外的发展聚集过程。[11]如汉代少府位于宫城内,后经过权力的分离和机构重组,其属官太医署、太官署等仍留在宫城,少府寺搬出宫外。随着单一宫城的出现,北部宫城中除中枢决策、秘书机构和内廷服务机关外,三公诸卿官府大都在宫城南大街两侧。如《魏都赋》记载:“当司马门南出,道西最北,南向相国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寺。道东最北奉常寺,次南大农府。出东掖门,正东道西太仆寺,次中尉府。出东掖门魏王宫东北行北城下,东为大理寺、宫内太社、西郎中令府。”[12]曹魏邺城中央官署机构的布局开启了在宫城南部中轴线两侧布置官署机构的先例,影响深远。
江南孙吴政权,仿照邺城,在宫南大街两侧建官署。据《景定建康志》引《吴纪》“天纪二年(278年)修百府,自宫门至朱雀桥,夹路作府舍。”[13]《吴都赋》描述,“列寺七里,夹栋阳路,屯营栉比,解署棋布……李善注云:吴自宫门南出苑路,府寺相属,夹道七里也,解犹署也,吴有司徒、大监诸署,非一也。”[14]东晋南朝建康城宫室制度大致沿东吴旧制,[15]宫城大司马门南经宣阳门向朱雀门大道两旁主要官署有鸿胪寺、宗正寺、太仆寺、太府寺、中堂等。①[唐]许嵩撰:《建康实录》卷19《世祖文皇帝》“中堂,在宣阳门内路西,七间……在鸿胪寺前,西南卫尉寺,南宗正寺、太仆寺、大弩署、脂泽库,更南即太史署、太府寺,东南角逼路宣阳门内过,东即客省、右尚方。”(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67页。此外,宫城东面大道及城外也散布有部分官署。
这一时期,都城布局最明显的特征是宫城内尚书机构独大,脱离内廷皇帝之手,在宫城中占据一席之地,[16]公卿府寺机构大多集中在宫城南中轴大街两侧。
(三)南北朝时期:尚书省分化并外移,中央府寺进一步集中在宫南
已成为宰相机构的尚书省,事务繁多,组织庞大,人员众多。省内官员在宫内办事,按制度可拖家带口,一同生活在宫城中,对宫城门禁和君主安全保卫工作十分不利。在过去门阀势力强大、君权不张的情况下,这种不便被延续下去,未能改变。自南朝刘宋起,寒族崛起,皇权伸张,且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便不能允许这种不便于君的状况继续下去。同时,由于尚书省权力隆重,威胁皇权,皇帝需要在身边再设立新的咨询秘书机构,取代原来的尚书。皇帝任用离自己更近的人,设立新的秘书决策中枢,削弱尚书权力。“魏置中书省,有监、令,遂掌机衡,而尚书之权渐减矣”。[17]。后又重用离自己更近的侍中,新成立门下省,又分割中书省权力。新中枢决策机构的出现,使尚书参与决策和机密出令权力丧失,开始向外转向政务。
但由于历史惯性,如此重要的一个机构不可能一下子移出,故尚书省在南北朝时期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分化成尚书上省和下省两个不同机构。尚书上省即原来都座及附属办事机构,都座是尚书八座、丞郎等议事之地,是宰相机构的主体部分,留在原处,方便日夜入值官员在出现紧急情况下及时向禁中皇帝报告或接受指示、咨询;而包括两百多名令吏在内的具体办理政务尚书诸曹,则移出此重宫城之外。②南朝建康都城宫城是多重的,但具体二重还是三重,尚无定论。朱偰等为代表认为建康宫有三重宫墙,见其氏著《金陵古迹图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而贺云翱等倾向认为宫有两重,见氏著《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但无论二重还是三重,尚书省主体部分已经被迁移出最内一重宫城。迁移到过去值宿的“休沐之处”下舍,称尚书下省,或迳称尚书省。[18]为方便尚书上、下两省联系,隔墙之上有阁道相连,如《陈书·徐陵传》记载“省在台城内下舍门,中有阁道东西跨路,通于朝堂(即尚书上省)”。[19]
北齐邺南城时期,尚书省机构大部分已外移出宫城。③《邺中记》记载北齐邺南城尚书省时称“尚书省及卿寺百司,自令仆而下之二十八曹,并在宫阙南”,认为此时尚书省已全出宫,见[明]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卷20《邺下》,(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85页。但《邺中记》一书成书晚,可信度不高,不能尽信,所以具体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种变化应与自南朝中期后中书舍人权重,三省分工制度出现造成的尚书权力和地位下降有关。新的中书、门下秘书咨询机构,因能常伴君主左右,提供咨询、出令,权力不知不觉扩大。梁武帝时,史称当国秉权者“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异”,[20]何敬容是当朝尚书省长官尚书令而被称为外朝,中书郎朱异又加侍中头衔,兼掌中书、门下二省大权,居中用事,称为内省,说明三省职权的内外之区分已很明确。中书、门下二省参与机要和掌握起草、下达诏令职权,成为新的内省决策机构,尚书省主体却降为执行命令的外朝行政部门,渐与诸卿寺监机构同列。权力的变化,最终导致尚书省被移出宫城。
此时,中央官署机构主体分布在宫城南中轴线两侧的态势更加显著。北魏洛阳都城模式也是宫室在北,宫前有南北主街,左右建官署,外侧建居住里坊。中央官署机构大多集中在宫城南铜驼街两侧。据《洛阳伽蓝记》记载,“阊阖门前御道东,有左卫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国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庙,庙南有护军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卫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将作曹,曹南有九级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阴里”。[21]在铜驼街左右各约占一坊之宽,形成中央衙署专区。近年洛阳考古过程中,沿街两侧发现的二三十处大型夯土台基,应是这些官署建筑基址的遗存。[22]这些宫城外中央衙署的分布已较为成熟,已有一定的规划。
到了隋代营建新都,隋文帝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又迈出重要一步,即把尚书省全部迁出,与其他中央行政官署机构全部集中一区,周以城墙,安置在宫城之南。出现一个只有中央衙署和庙社机构纯粹的行政区域,并命名皇城,正是这一举措,改变过去都城之中官署、市里相杂处的弊病,使都城之中,明确分为由皇帝朝寝的宫城、百官行政的皇城和百姓生活的外郭城三部分,公私有别,秩序井然,开辟了都城布局的新篇章。
综上,所谓“隋文帝新意”,其实并非简单地出自隋文帝个人一时的创造,而是有其独特的背景和发展历程。它的出现与汉末开始的宫城南部官署机构集聚有关,而且也离不开宫内尚书等近侍机构的发展变化的影响。经历数百年,直到隋文帝规划新都。这可能才是宋敏求所赞叹的“隋文帝新意”的真实情况。
二、长安皇城与宫城关系
皇城的外形和空间位置比较独特,在都城中轴线北部正中,东西与宫城同宽,平面呈规则长方形,与宫城总体呈“日”字形状。皇城外形、大小与宫城相仿,这就难免使人生疑,两者最初在规划设计上是独立的两个城还是为一城的上下两部分?
皇城紧靠宫城南侧,东、西、南三面筑有城墙,但无北墙,以横街与宫城相隔,东西城墙与宫城东西墙连接。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都没有皇城城垣的数据,①张永禄主编的《唐代长安词典》记载,皇城城垣高三丈五尺,墙基厚曰18米;宫城城垣规模与此相同。但未见其数据来源,在长安城考古报告中不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6-67页。因而成为这一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杨宽先生认为隋长安城规划属于内城外郭形制,大兴城分郭城和内城两部分,内城又分宫城和皇城,这是先制定好的规划,然后陆续建成的。一些学者也认为皇城东西二墙是宫城城墙向南自然延伸,[23]皇城城墙应与宫城城墙规模同等。
也有学者根据同时期东都洛阳三城的墙垣记载,“宫城四丈八尺,皇城三丈七尺,外郭城一丈八尺”。[24]据而推测长安皇城城垣高度也应在宫城、外郭城之间,[25]从而认为皇城和宫城是两个规格递减不同的城。但是,东都洛阳的规划虽然与长安同属一人,由于洛阳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形势,其皇城和宫城并不像长安那样正北居中,而是在都城西北隅。且皇城围绕在宫城的东、南、西三面,东西两侧与宫城成夹城。所以两者仍有较大的差异,不能简单的相对照。
从另一种角度考虑,有理由相信杨宽先生所说皇城和宫城是内城的两部分的观点。首先,从城门命名上看,长安宫城北门是玄武门,皇城正南门是朱雀门,北玄武南朱雀,以传统四象方位观念而命名正是我国古代都城城门常见命名手法。“四兽”早在汉代之后已被普遍应用于都城城门或殿阁的命名。[26]其次,对比大明宫,其宫城北门为玄武门,南门丹凤门(即火凤凰),正好对应了太极宫的玄武门和皇城朱雀门。另外,从建筑建设手法上,傅熹年先生经过周密的推算,将皇城、宫城视为一个子城,认为宇文恺在规划新城时,“首先确定子城之宽深,以此为模数,分全城为若干区块,在区块内布置里坊。在子城南部,以子城之宽为宽,以子城之深一半为深,划定三大区划;在子城左右,以子城总深为宽和深,划定两大正方形区块;在它们以南,又以子城总深为宽,以它一半为深,各划定三个区块……这就形成全城的棋盘格局形街道网和规整的里坊。”[27]
所以笔者以为,长安城在功能分区上是三城,但在形态上,宫城、皇城两者一体,同为一城。皇城的东西城墙应和宫城东西城墙自然相连,规模相当,为两条完整的城墙。但还有待于考古成果的进一步论证。
三、从“双城”到“三城”——隋唐长安皇城在都城空间发展史的地位
“中国古代都城是古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是国家历史的缩影,因而都城的布局形制实质反映着古代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重大问题。”[28]刘庆柱先生考察历史时期城市主体与城市空间的演变历程,认为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城中,王侯贵族是城内的主体,城是贵族的专属区,而附属的民则在城外点状分布,是为一城制,对应“邦国时代”;后城中民的地位上升,开始在城内生活居住,“盛民”的郭城在宫城外出现,是为双城制,对应“王国时代”;随着社会继续发展,中央政府官僚集团在管理国家和处理行政事务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故而在宫城外(应该是宫城中分离出)出现另一个城,作为中央集权帝国政府官僚群体的行政区域,是为三城制,对应的是“帝国时代”。由于都城建筑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它的变化与政治社会变化不是同步的,具有相对滞后的特点。所以秦汉时期的都城形制仍然持续战国的制度,呈现“两城制”的布局,这一滞后性直到北魏洛阳城才结束,北魏洛阳都城是古代帝国社会都城的三城制模式的开端。
笔者以为,刘先生所论第三阶段的北魏洛阳城是“三城制”都城时代的标志,这一观点有待商榷。从单城制到三城制,属于城市空间不断分化的结果。但从北魏洛阳的建设过程可以看出,“内城”并非专门空间的产物。北魏初期洛阳城仍沿用魏晋故城城垣,基本维持“九六”城的形制,并无外郭城的规划。外郭城的规划直到景明二年(501年)才提出,这是因为要解决迁都所带来的大量人口在城内居住的问题。据《隋书·经籍志》估计当时全国各地汇集洛阳人口有数十万之多,原有的旧城难以容纳。同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统治者为自身安全考虑,不能将人口全安置在“九六城”内。为妥善安置居民,巩固统治,遂沿袭旧都平城旧制,规立外城。“(元)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29]在洛阳城外三面建坊,并筑墙。新成的外郭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客观上使汉以来的旧城“升级”成内城。不过,此时的外郭城,尚处草创,并不成熟。所以在北魏洛阳外郭城遗址发现以前,学界对洛阳有没有外郭城一直有争议。
正是为了安置人口,管控居民,成为北魏洛阳外郭城出现的根本原因,况且当时洛阳内城内仍存有不少寺院、居民,[30]所以笔者认为北魏洛阳仅在形式上具备“二城制”向“三城制”的变革,内涵上并未有所突破,并不是前所说的城市政治空间的革新。因而只能说在人口压力下,外郭城建成后,原先的外城变为内城。但这个内城是以官府为主体的一个特殊区域,客观上具备了某些隋唐“三城制”皇城的因素。所以,“建筑文化滞后期”直到隋唐新都长安出现才结束。都城中出现一个纯粹的只有中央衙署集中布置的城,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正式完成了刘先生所说的从封建“王国时代”到专制集权“帝国时代”的转变。
四、继承与嬗变——皇城的新变化
隋唐时期,在全国推行封闭的城市管理体制,使中国古代坊市制城市达到鼎盛时期。[31]所有的城市在外形上趋于规整形态,城市内部采用封闭的坊墙分割形态,实现严格的阶级和身份的划分。都城作为首善之区,更是如此,“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各有分区。不同的空间由城墙、城门等界限严格的区分开,整个都城呈现出秩序井然、公私皆便,互不干扰,各安其职的状态,是传统儒家模式都城的光辉典范。
皇城制度从孕育到成熟,大约经历数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但这种严格功能分区的都城模式,却如昙花一下。自唐中后期,皇城的功能便开始减弱,被宫城边缘化。又经过宋元明清各阶段,皇城的名称虽沿袭下来,但形态结构和功能作用与隋唐相比,迥然不同。
(一)唐代中后期的皇城
自唐代政治中心转移到大明宫,政治核心开始远离皇城,深刻影响了皇城内的机构分布和功能作用,促使皇城出现新变化。
这一时期,随着大明宫城内新出现一系列行政权力机构及使职差遣制度的发展,[32]大明宫城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些宫城内新的官署办事机构,广泛的侵夺替代原皇城内政府机构的职权,致使皇城内官署机构在新的权力秩序中的地位下降,其行政机构出现闲废化的趋势。时人于邵提到“……惟礼部、兵部、度支职务尚存,余曹空闲,案牍全稀,一饭而归,竟日无事”。[33]“自天宝末,权置使务已后,庶事因偱,尚书诸司,渐致有名无实,废堕已久”。[34]“及安史之乱。戎机逼促,不得从容,政事推行,率从权便……吏、兵之职废矣……户部之职废矣,至于刑工之职,亦不克举”。[35]
开元十一年(723年),唐代政治体制发生重大转变,中书门下体制初步建立。[36]中书门下成立后,原最高行政机构的尚书省地位和职能受到侵夺,中书门下最终取代尚书省成为国家常务的主要裁决机构。由于尚书省地位和职权的降低,机构的闲废,在实际政事运行中起到的作用大不如前,所以在一些特殊时期内,经费不足,省内财政状况常难以为继、捉襟见肘,用于维持尚书都省日常开销的经费常都成为问题,不得不奏请借钱度日。[37]有些过去修建比较宏丽的办公部门机构,因职权过于闲简甚至被拆毁荒废。如户部职权被侵夺最严重,基本工作不能正常运行,户部郎中厅、员外郎厅和户部考堂等,其行政机关所在的厅堂建筑被拆毁,荒废成“户部园”。[38]但尚书省仍有一定职权,在名义上始终是官方承认的“天下政本”。[39]
唐代职官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使职差遣制度流行,“为使则重,为官则轻”。唐代中后期的使职,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可以独立运作,发挥自身的职能与作用,维持唐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唐前期中央行政体制为尚书部司寺监体制,后期至贞元、元和之后,中央行政体制变为使职行政体制为主。[40]大明宫内宦官把持的使司机构列局于内侍省,总理内廷诸司使的内侍省也渐由宫廷服务机构变为左右政局的北司,形成南衙北司对立的政治格局,对唐代后期政治制度带来极大的影响。[41]
唐中后期,宦官势力膨胀,大明宫内新出现一个庞大的宦官内诸司使办事机构,在宫廷内大量窃取原属于尚书六部、寺监和其他行政系统部门之权。“唐代具有一个庞大的由宦官指挥的内诸司使行政系统,北衙的诸司使分部细密,组织庞大,与南衙以宰相为首的行政系统相对立。宋王旦说‘唐设内诸司使,悉拟尚书省…'内诸司使侵夺尚书省职权。自三省以至卿监,很多设有对口或相关的北衙诸司”。[42]宦官诸内使竟然参拟朝廷官僚组织,设置分部细密的科室系统,自三省至卿监,基本都设有与其相关的部门。“唐设内诸司使,参拟尚书省,如京,仓部也;戍宅,屯田也;皇城,司门也;礼宾,主客也……”;[43]杜牧亦记载北衙宦官有“二十四司”。[44]宦官内诸司对皇城的冲击影响主要就是大肆侵夺皇城内行政机构的权力。宦官为使,普遍插手六部政务,不断侵夺六部职权[45]。宦官侵夺外朝行政管理事务,使内侍省规模膨胀,“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余人,衣朱紫千余人”。[46]内诸使司地位凌驾政府机构之上,形成无所不入的权力纲。[47]史载内侍省规模“前后厅馆,东西步廊,启彼重□,联其华室,大小相记凡五百余间”。[48]直到唐末诛灭宦官后,“内诸司一切罢之,皆归省寺”。[49]
宦官内诸司行政系统,与南衙以宰相为首的行政系统相对应,两者并行势必造成互相影响和攻伐,造成行政体制的混乱,“当时目为南北司,爱恶相攻,有如同水火”,[49]5064对唐代后期的政治造成极坏的影响。
(二)宋元明清时期的皇城
北宋时期,皇城与宫城不再是两个不同实体,而是合二为一,一城两名。[50]当时主要中央官署分布,并没有一个专门集中分布区域。[51]南宋临安也如此,皇城即宫城,又称皇宫、大内。
元大都共三套方城,即外城、萧墙、宫城。很多学者都以明清都城构造而称呼元大都分为外城、皇城、宫城三重城结构,似已成定说。但在元代文献中,萧墙是整个大内宫城的外墙,并不称皇城,皇城所指仍承两宋,是宫城别称。如《析津志》说“十月皇城东华门外,朝廷命武官开射圃,常年国典”,[52]东华门即是宫城东门东华门;同书《岁纪》篇又有“皇城游”,[53]皇城仍指宫城;直到明代初年,徐达“计度元皇城,一千二十六丈”,[54]皇城依然所指的是宫城。
明初南京只有宫城,皇城指宫城。后借鉴元大都萧墙,在宫城外增建了一道“周九里三十步”的外垣。外禁垣确定后,皇城的范围比以前扩大很多,于是宫城同外禁垣一起统称皇城,这一叫法一直延续到永乐北京都城的营建。明代中期,称宫城为内皇城,外禁垣为外皇城;到明代中晚期,随着紫禁城叫法出现,宫城改叫紫禁城或大内,外禁垣称皇城。[55]皇城的称呼就固定下来,成为特指的从属宫城的外围空间,沿用至今。明清北京皇城大致继承元大都萧墙布局,西部是西苑太液池休闲区,东南部是东苑,有重华宫等宫殿,其余大部分都布置皇室内府衙门服务机构,还有各种库房、厂坊台堂等。皇城已成为紫禁城的外院,其性质已变为供皇室成员休闲娱乐、服务皇室的后勤保障为主。
从秦汉到隋,皇城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萌芽,到了隋大兴城,终于成熟地出现在都城中。却也仅存在于这一时期,唐中后期直到明清,皇城又经历了一个明显而复杂的变化历程。从长安皇城到北京皇城,虽名称继承下来不变,但形态构成和性质功能却迥然不同。正如郭湖生先生所说,“宫城是都城的核心。皇城,在隋唐时期是政府百司和首都戍卫部队所在,还有仓库,而到明清,皇城是皇帝的后宫内苑和庞大的内侍机构所在地,简而言之,是休闲和后勤区域,和隋唐皇城性质不同……这个问题一直没人研究清楚,可以说是最后一个空白和难点。”[56]从这个意义上说,隋唐长安皇城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转折点,加强对隋唐长安皇城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宽都城的研究内容,加深对中国古都发展演变规律的探讨,也可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政治空间和皇权政治演变打开一扇窗户。
[1] 刘庆柱. 长安春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杨宽.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172; 史念海. 中国古都和文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523; 王维坤. 试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构造与里坊制的起源[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9(1): 73-110; 傅熹年. 中国古代建筑史: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106-107; 李久昌. 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研究[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7: 291-312; 傅熹年. 中国古代建筑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106-107; 肖爱玲. 隋唐长安城[M].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8; 张永禄. 唐都长安[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0.
[2] 宋敏求. 长安志[M]. 刻本. 镇洋: 毕氏, 1784 (清乾隆四十九年).
[3] 杨宽.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09-114.
[4] 刘敦桢. 中国古代建筑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46.
[5] 王社教. 汉长安城[M].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0: 118-119.
[6] 王仲殊. 中国古代都城概说[J]. 考古, 1982(5): 505-516 .
[7] 李林甫. 唐六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6.
[8] 李玉福. 秦汉制度史论[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136.
[9] 韩养民. 论汉武帝时期的中外朝[J]. 西北大学学报, 1978(2);劳诚鉴. 论西汉中外朝的形成与作用[J]. 江汉论坛, 1983(4): 87-92; 李宜春. 论西汉内朝政治[J]. 史学月刊,2000(4): 30-37.
[10] 徐坚. 初学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59.
[11] 郭济桥. 曹魏邺城中央官署布局初释[J]. 殷都学刊, 2002(2): 34-38.
[12] 萧统. 文选[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77.
[13] 周应合. 建康志 [M]. 清嘉庆六年刊本影印。
[14] 萧统. 文选[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17.
[15] 苏则民. 南京城市规划史稿古代篇·近代篇[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100.
[16] 郭湖生. 中华古都[M]. 台北: 空间出版社, 2003: 165-181.
[17] 杜佑. 通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29.
[18] 祝总斌.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15.
[19] 姚思廉. 陈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338.
[20]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516.
[21] 杨衔之. 洛阳伽蓝记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M].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519.
[23] 宿白. 隋唐长安城与洛阳[J]. 考古, 1978(6); 肖爱玲. 隋唐长安城[M].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8: 84.
[24] 李健超: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25] 李瑞. 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2005.
[26] 何清谷. 三辅黄图校注[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190.
[27] 傅熹年. 中国古代建筑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345.
[28] 刘庆柱. 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J]. 考古学报, 2006(3): 281-313
[29] 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29.
[30] 杨衔之. 洛阳伽蓝记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380.
[31] 李孝聪. 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250.
[32] 妹尾达彦. 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7(4): 101-112; 薛明扬. 论唐代使职的功能与作用[J]. 复旦学报, 1990(1): 27-33.
[33] 李昉. 文苑英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3123.
[34] 薛居正. 旧五代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999.
[35] 严耕望. 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1: 431-507.
[36] 刘后滨.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
[37] 王钦若. 册府元龟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6083.
[38] 王溥. 唐会要校证[M]. 牛继清, 校证. 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2: 1019.
[39] 王孙盈政. 天下政本—从公文运行考察尚书省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地位 [J]. 历史教学, 2012 (24): 35-39.
[40] 刘后滨. 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及其在唐宋制度变迁中的意义[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6): 41-47.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211.
[42] 唐长孺. 山居存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253.
[43]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1977: 4003.
[44] 杜牧. 樊川文集校注 [M]. 何锡光, 校注. 成都: 巴蜀书社,2007: 622.
[45] 唐飞. 唐代中使研究[D]. 扬州: 扬州大学, 2010.
[46] 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856.
[47] 袁刚. 中国古代政府机构设置沿革[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442.
[48] 吴钢. 全唐文补遗[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4: 38.
[49]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4777.
[50] 周宝珠. 宋代东京研究[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28; 邱刚. 北宋东京皇宫沿革考略[J]. 史学月刊,1989(4): 47-52.
[51] 焦洋. 北宋东京皇城、宫城的“名”与“实”[J]. 南方建筑,2011(4): 72-77.
[52] 熊梦祥. 析津志辑佚·风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05.
[53] 熊梦祥. 析津志·岁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11.
[54] 李燮平. 元明宫城周长比较[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0(5): 43-48.
[55] 李燮平. 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 [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06: 102-114.
[56] 郭湖生. 中华古都[M]. 台北: 空间出版社, 2003: 143.
(责任编校:贺常颖)
Some Problems about Imperial City of Chang'an Tow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ZHAO Yangyang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Shaanxi 710062, China)
The imperial city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ncient capital. Accoding to rereading literatures and investigating base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e author has some opinions. Firstly, the imperial, it wasn‘t the product of New Thoughts given by the Emperor Suiwen and it has a long development time which included two stages of the City. Secondly,the imperial city and palace city are a whole. Thirdly, the imperial city appearance was a symbol that was compeled the changement from “Two cities”toThree cities”. Fouthly, there are some significant changes on the imperial city after Sui and Tang Dynasties. So we will have many problems to resolve about the imperial city from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ang'an city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581-905 A,D,); imperial city; formation and changement; city space.
K 928.5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6.02.016
2096-059X(2016)02-0067-08
2016-01-12
赵阳阳(1987—),男,汉族,河南温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研究。
①所谓皇城,也称子城或内城,处于宫城之外,郭城之内,是中央行政机构和宗庙所在地,为全国封建统治的中枢。见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3页。隋唐两代文献中,有关隋唐时期长安皇城的直接记载较少,且部分史料记载混乱有误,试举几例:《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大明宫南兴安门“南当皇城之启夏门,旧京城入苑之北门”,按启夏门为京城(外郭城)南门,非皇城之门;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内护国天王寺在左神策军球场北,寺与大内隔墙,即皇城内城东北隅也”,按皇城之内,不可安置佛寺,护国天王寺在大明宫内,故此处皇城应为大明宫城;《旧唐书》卷38《地理志》:“京师皇城在西北隅,谓之西内。”按长安西内指太极宫城,且方位也不在西北,应为东都洛阳的记载,《唐六典》云:皇城在(洛阳)都城之西北隅;韦述《西京新记》:皇城南面六门,正南承天门,门外两观……按承天门,为太极宫城正南门,故皇城应为宫城。在今后使用类似史料时,须加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