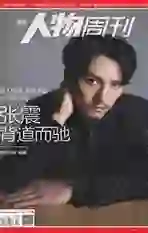钱颖一比起批评者,我更想做建设者
2016-03-23许祎
许祎



他是世界一流经济学学者,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高考分数最高的学院做了十年院长,虽“做事情累得要命”,却依然相信“要改的实在太多了
2015年10月的一天,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授了一堂公开课,用的是他只学过一年的中文。他一字一顿,语调常拐到古怪的地方,专注地听上一会儿难免让人疲惫,但台下没有人分神——这类顶着巨大光环的人身上总有些能暗暗牵动你的东西。
结束时,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跨步走上讲台,像鼓励一个刚刚完成第一次演讲的新生那样,大力拍了拍“小扎”的肩膀。钱颖一慈祥地笑着,“小扎”也乐呵呵地松了口气,额间渗出细密的汗水。光环好像消失了。
几个月后,我们在清华经管学院接待室聊起这件事。钱颖一是那种不知不觉地释放出气场、却又不会让人感到压迫的学者,正是他一力说服了扎克伯格用中文授课。解释这么做的用意时,钱颖一把一只手比在下颚处,另一只手抬过头顶,用以描述扎克伯格实际的中文水平和最后展现的中文水平。他认为这30分钟完美地示范了一个人的勇气和潜能。
“听听人家扎克伯格,外国留学生还有什么理由不学好中文?”他突然变得有些严厉,像在训导一个偷懒犯错的学生。“这时你就会发现,一堂听不懂的课对你教育最大。”
作为一位教授,同时是全中国最好大学里最具影响力的学院的管理者,钱颖一有种出人意表的机敏与率真。这或许部分源于个性,部分来自他的专业——经济学。他在经济管理教育改革的一线奔走,频频与学生互动,理解年轻人的骄傲和困惑,适时为他们展示榜样、指点迷津。
在中国,体制内外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声不绝于耳,但钱颖一鲜少流露无力之感。当然他也会感叹:“做事情累得要命啊!”可一转身,他又启动了下一项改革,因为“要改的实在太多了”。
“有用”与“无用”
2016年是钱颖一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第十年。做院长之后,他把原本三行之长的学院“使命”浓缩为16个字:创造知识,培育领袖,贡献中国,影响世界。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与清华大学和建设世界一流经济管理学院相一致的定位。
和世界上许多商学院的使命一样,它有种气吞山河的野心。然而清华经管可能是国内最有资本发此宏愿的学院。在过去这些年中,清华经管学院成为各省状元和高考分学生扎堆的地方,每年录取的状元都在20个左右。2009年,钱颖一推进以“通识教育,个性发展”为核心的本科教育改革,有人笑说:“你这学院改革多容易啊,全是状元。”钱颖一却摇头:“恰恰相反,我们是最难搞这个改革的。因为想报经济管理专业的人,很难没有功利性!”话里一半玩笑,一半认真。
钱颖一在许多场合发表过对于“功利”的看法。比如他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之一是“短期功利主义”盛行。“现代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基础之上的。功利主义在中文中具有贬义,但在英文语境里比较中性。作为一种哲学,我们不能批判功利主义,但值得警惕的是‘短期功利主义。”钱颖一解释道。
和大多数的本科教育一样,过去的清华经管本科培养重技能、高度专业化。而按照改革后的培养方案,经管本科生在四年内(通常是大一、大二)需要完成24个学分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这套课程在经管学院开设,分为8个课组,包括“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中国与世界”等,学生在每个课组中至少选修一门课。
2015年春季学期,钱颖一请来清华政治学系的刘瑜讲授“中国与世界”课组下的一门课——“比较政治转型”。当时正读大三的李琳佳在一次课上遇到钱老师(学院师生都称钱颖一为老师,而不是院长)来旁听。课下她收到钱颖一的邮件,向她索要刘瑜开的书单。她记得其中一本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再见面时钱颖一问,“你们读了吗?”多数人摇头。他有点不高兴,“你们没读?我都读了。”
“中国与世界”课组下另一位鼎鼎有名的老师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他也是钱颖一几经周折邀请来的。
“真有点像西南联大时那种大师云集的感觉。”大四学生陈嘉证说。他重点谈到了“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课程涉及一部分逻辑学,一部分道德哲学,从康德到密尔再到罗尔斯。他正在申请美国几所顶尖大学的法学硕士,他认为清华经管强调的逻辑思维能力、领导力和沟通力,都为他的跨专业申请打下了基础。当然,担任院学生会主席的经历无疑让他更接近目标。“每门课都给你一个新的描述世界的视角,”他带着兴奋和自信总结道,“你进到一个学院来,是闭着眼睛一条道走到黑,还是能有主动性,能选择,区别是非常大的。”
并非所有人都理解钱颖一推行通识教育的初衷。有学生抱怨人文课程对找工作、找实习没帮助,不如多开一些会计课、金融课。于是钱颖一就转述毕业校友的话,耐心开导:“等过几年你会发现,人文知识对你的思维帮助很大”、“到时数学公式全忘了,但历史哲学精髓记得最清”。有老师抱怨通识课不好教,深浅难易无从拿捏,学生评分低,钱颖一就一个个去听课,与老师们沟通,给予安慰。
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验在中国高校并不新鲜。北大的元培学院、复旦的复旦学院、中大的博雅学院等,都试图打破专业壁垒,却也都在推行中遭遇了与传统体制的艰难角力。
钱颖一仍然选择激流勇进。在他看来,通识教育的目的还不是开阔眼界,也不是为专业学习打基础、作补充,而是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为人的一生做准备。
在2012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他发表了一篇演讲,题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他也在许多别的场合提到一些美国商界成功人士在本科时读的是“无用”的专业:投资银行高盛的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在哈佛的本科专业是历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史蒂夫·施瓦茨曼在耶鲁的本科专业是文化与行为,网上支付公司PayPal联合创始人和前CEO、《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在斯坦福的本科专业是哲学——谁能想象在普遍被认为最“有用”的经管学院,还有人这样郑重其事地谈论“无用”的价值呢?
世界一流的顾问委员会
清华经管学院接待室的墙上,挂着前三任院长的照片。第一任院长朱镕基笑容可掬,牙齿微露。这张照片是钱颖一在朝阳公园一个民间金融博物馆里意外发现的。“朱院长的照片一般都比较严肃,我一看,诶,这张好啊!”钱颖一眼神发亮。

2002年4月28日,清华校长王大中为钱颖一颁发特聘教授聘书
2000年,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在时任院长朱镕基的主导下成立。美国前财长、高盛前CEO亨利·保尔森在《与中国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一书中提到了那段历史的一个细节:“1997年秋天,我和朱镕基碰过一次面,那时高盛刚刚帮助中国移动完成重组和上市。他敦促我设法为类似的中国公司培育管理人才。‘我们的管理太落后了。朱用他一贯的坦率说。”

2002年特聘教授项目开创了海外学术人才引进新的模式,为后来国家的“千人计划:提供了范例
2001年,朱镕基辞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在告别演说中他提到,之所以成立顾问委员会,是为了“把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者邀请来”,“希望对经济管理学院的成长有帮助。”
如今的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云集了像保尔森这样的世界级政商领袖,阵容比起哈佛商学院这样的顶尖商学院的顾问委员会更加耀眼。委员们来清华开年会、提建议、像扎克伯格那样走进课堂、为学院引荐重要的人和机构,以及捐助教育事业。概言之,贡献他们的见识、人脉,和资源。
外国顾问委员反映学生英语口语水平低,讲英文听不懂,钱颖一就推进英文教学。一年之内,经管学院一百多门本科课中用英文授课的就从七八门变成了五十多门。国内顾问委员反映学生中文水平低,文书写不好,钱颖一就在一年级增加了中文写作课和中文沟通课。
声音被听取,多少加强了顾问委员们的角色感和参与热情。可说到底,外国顾问委员们为什么愿意来?
“他们也渴望了解中国下一代领导者在想什么。”钱颖一说。
学院合作发展办公室原主任潘庆中每年都陪钱颖一拜访顾问委员,“世界各地跑了好多地方”。高通创始人欧文·雅各布是顾问委员会最早期的委员之一。2013年,钱颖一和潘庆中代表学院第三次拜访他。在加州La Jolla的滨海别墅里,这位波兰裔犹太人和他的太太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告别前,客人掏出一本精美的相册,里面印着夫妇两人在清华参会和授课的照片。适逢他们结婚60周年,这是颇为贴心的礼物。
相册封面上,几片星星状的贴纸透着点拙朴的童趣。那是前一天,突然发现年份写法不合英文规范时,两个中年男人的急智之作——他们在异乡的小商店里买剪子、买胶水、买贴纸,嘁里喀喳忙活一通,才用小星星遮住了字母。钱颖一把这段插曲讲给雅各布夫妇听。
雅各布当场承诺为清华经管学院捐设一个讲席教授席位。建立讲席教授席位这项机制使得学院在有限的大学薪资之外,能以较高薪酬从海外聘请学者。2004年,留美经济学家李稻葵和白重恩从香港回到清华经管学院任教,就是得益于AIG(美国国际保险公司,保险业巨头)前总裁霍顿·弗里曼先生捐赠的讲席教授基金。
拜访每一位委员之前,钱颖一都会把对方的背景资料细细整理、打印,反复琢磨,坐飞机坐车也不肯放松。前往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偏僻小镇拜访霍顿·弗里曼时,他们乘坐的螺旋桨飞机又小又旧,发动机震天的声响中,潘庆中只听清钱颖一说了一句话:“我有什么本事啊,就是比别人勤奋一点。”
几乎所有和钱颖一接触过的人都谈到他的勤奋与执行力。2007年钱颖一启动MBA改革,现任院党委书记高建时任院长助理,他印象中的钱颖一总是火急火燎的,常常一个任务布置下去,两三天内就要督促完成。也是在2007年前后,《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曾经为写作《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约访钱颖一,当时正值顾问委员会年会期间,他对钱颖一的忙碌和事必躬亲记忆深刻。
顾问委员会年会每年在清华召开。短短不到两天时间,除了领导人会见、大小会议之外,钱颖一还要为学生安排值得翘首的环节。2014年,他同蒂姆·库克对谈。2015年,他与埃隆·马斯克对话,还请扎克伯格讲课。这几位顾问委员都是年轻人中极具号召力的偶像。
“马斯克的谈话中有两点值得挖掘。一是物理学第一原理对他影响很深。物理学第一原理不是定理,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说凡事要刨根问底,回到最原始的假设。他造火箭就是靠这种思维。二是他认为量子力学很重要,因为它反直觉(counter-intuitive),却是正确的。创新也常常是反直觉的。这跟乔布斯讲的think different(不同的思维),彼得·蒂尔讲的contrarian thinking(逆向思维),是类似的意思。无独有偶,扎克伯格女儿出生时网上流传一张照片,他们夫妇抱着孩子拿着一本书,书名就叫《婴儿版量子力学》。”
“这些人的相同之处就是,都是与众不同。”钱颖一如此归纳。他似乎有种迫切的希望,希望学生看到这些顶尖的人物是如何思考自我、思考世界。
结缘清华经管学院
自加入清华经管学院后,钱颖一从没带过博士,偶尔给本科生讲《经济学原理》,常常回答学生关于个人发展与人生道路的提问。有些问题他认为太细节,不值得过分关注,比如“投行怎么面试?”有些问题他认为重要,应当现身说法,比如“我不喜欢现在的专业,可研一了,换专业成本会不会太高?”
钱颖一就不止一次地换过专业。高中毕业的他在北京密云县乡下一边干农活,一边自学英语和数学,度过四年插队时光。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清华数学系。之后赴美留学,他先后转了3个专业方向,先取得两个硕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和耶鲁大学运筹学),最后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我刚到哈佛的时候,跟我一起出国的同学博士都快毕业了,”和学生聊天时,钱颖一也反问他们,“你说这成本高不高?”
当代青年在看似丰富的选择前踟蹰,那一代学人则像月夜行船,小心翼翼地摸索航向。1983年,在耶鲁读运筹学的钱颖一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经济学,其中的数学部分他游刃有余,但经济学部分却异常艰深——计划经济环境下成长的一代,根本不知市场中的供给和需求为何物。适逢曾任社科院研究员的吴敬琏在耶鲁做访问学者,钱颖一和他多有交流,并深受启迪。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浪潮汹涌,经济问题复杂而崭新,这让大洋彼岸的钱颖一立定志向,投身经济学。
1990年起,钱颖一先后在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经济系任教。从那时起他就频频回国,在北大讲课,与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财经部门沟通交流,提供改革政策建议。在90年代,1993年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汇率并轨和银行商业化,90年代末为加入WTO的准备等若干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大事件相继发生,中国的市场经济框架逐渐成型。
钱颖一的研究集中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问题,比如企业改革中的“产权”问题,金融改革中的“激励机制”、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等,同时引介国际上相关的经济学说,包括诺奖得主、几位“信息经济学”奠基人的学术成果(其中乔治·阿克尔洛夫是钱颖一在伯克利加州经济系的同事,其妻子、时任伯克利加州经济系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则是招聘钱颖一入系的委员会主席)——由此集结的、在2003年出版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一书成为当时国内最前沿的转轨经济学著作。
在这本书出版13年后的今天,当被问及中国经济的“转轨”(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否完成时,钱颖一这样回答:“这是一个一直在进行的过程,要看你以什么标准去衡量。如果谈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经济、谈公平的市场竞争、谈明晰和安全的产权,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1年,当时的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赵纯均找到钱颖一,请他帮忙引进海外经济学人才。当时和钱颖一同批留美的经济学者中,一些人已经获得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立即辞职回国任教的可能性甚微。在钱颖一的建议与联络下,清华经管学院在2002年采用“特聘教授”制度,聘请了包括他在内的15名海外经济学学者,利用美国高校学期短的特点,每年来清华授课3个月。十多年过去,如今这15人中,有12位正在或曾经担任国内经济相关学院的院长,国内的经济学教育事业藉此开枝散叶。
2006年,钱颖一出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十年间,他每年主抓一个教学项目,完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MBA、EMBA各个项目的改革。“乔布斯说过,人生不能事先把一个个点连接到未来,只有回过头来看,才能把这些点连上。我也是一样,改革并不是都是事先计划好的。某个时候有机会了,我就做,并把它做成。”

钱颖一对话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他还是喜欢引用乔布斯的故事,就像他喜欢引用扎克伯格、马斯克,以及一切优秀人物的故事一样。他让你想起那句谚语,并觉得信服:教育的本质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
人物周刊:为什么国内高校的经济和管理专业,有的分开在两个学院,有的合在一起?
钱颖一: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在国外有两种叫法,二战前成立的大多叫Business School,二战后成立的大部分叫School of Management。在美国,经济系不在商学院,通常在文理学院或社会科学学院。在中国前20的大学中,大约有一半是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分开的(比如北大、复旦、华中科技大学等),而另一半是经济和管理合并在一个学院的(比如清华、上交大、武大等)。
人物周刊:合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吗?
钱颖一:管理学研究企业内部如何有效经营,而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有效配置资源,企业是其中的一个单位。经济学家科斯的贡献是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其实也是一个变量,到底什么应该在企业内部交易,什么又应该在市场中交易,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比如特许经营制就是一种中间模式。麦当劳是一家企业吗?它不是传统的模式,因为它的每一家分店都是独立的,但又是加盟的,总部要收专利使用费。可口可乐也是一样。这类问题既是经济学问题,也是管理学问题。把经济学和管理学结合在一起,会有新的理论突破。
人物周刊:在中国是否还有国情原因?
钱颖一:对。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在计划经济下,经济和管理不分,企业都是国有的,管理经济和管理企业是同一个问题。即使在今天,在我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能力远大于其他市场经济。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不仅要懂管理,也要懂经济,还要懂政治。美国企业家也要懂经济,懂政府政策,但他们可以通过聘用律师来解决法律问题。但在中国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论坛,企业家都去听。他们希望更多地及时了解经济、政策、法律的变化。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创业创新的热潮?
钱颖一:我们的习惯思维是,创新是政府的事,是专家的事,是从上而下的,比如 “两弹一星”的成功,就是举国体制。去年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一个思路上的变化,就是在创新上,要相信老百姓的创造力。乔布斯如果在我们这里,他连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可能都评不上。
人物周刊:这种创业环境下,高校应该站在什么位置?
钱颖一:高校的使命是教育,是人才培养。清华经管学院在2013年就创建了“清华x-空间”(清华x-lab),这是一个为学生搭建的创意创新创业的教育平台。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我们不是以项目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的,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学生创不创业不是关键,关键是培养创造力,培养一种意识、一种思维,让他们终身受益。你说我现在是在创业吗?我是在大学,是在国有事业单位。我在学院里面搞改革,也是在做创新的事。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供给侧改革的要旨是什么?
钱颖一:几年前我和吴敬琏讨论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时,都认为用“三驾马车”作为理论基础来思考经济增长不对头。消费、投资、净出口是凯恩斯的需求方模型中的要素,这个模型是针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而经济增长是长期的,应该使用供给方的增长模型,代表人物是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什么是供给方要素呢?是资本、劳动力、教育程度、改革开放,还有技术进步、创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