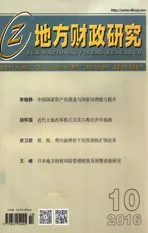西方治理理论的“中国困境”解读
2016-03-20杨松武
杨松武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西方治理理论的“中国困境”解读
杨松武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81)
内容提要:借力经济全球化浪潮,西方治理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强势传播,对我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与深入影响,成为当前的学术热点。然而,与学界反应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的治理实践却同西方治理理论保持着适度距离,冷静地坚守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西方治理理论对中国治理模式转型的边际影响甚微,其传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中国困境”。而这一结果的出现并非偶然,西方治理理论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理论的非普适性,与中国治理模式在价值层面上的差异与对立,弱化了理论适用的前提和基础,对中国治理实践的潜在危害则为“中国困境”的出现提供了充分的现实解读。
西方治理理论中国困境国家治理公司治理NGO治理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异地移植向来是个难题,制度、思想、理论也不例外。西方治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不断对外扩散。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该理论开始快速传播于我国的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波持续性的治理研究热潮,公司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范畴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及其交叉学科——财政学等诸多领域相继成为研究热点。然而,随着西方治理理论向私人与公共治理领域逐步渗透,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与不适开始不断显现。甚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背景下,以现代科学形象示人的西方治理理论也未能登堂入室,“治国理政”①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外文出版社,2014年。的官方基调,释放出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治理理念与信号。即使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为目标,但是“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②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2015。与纯粹的西方公司治理原则却是格格不入。在国外NGO组织大量进入中国的今天,《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通过,显示出我国针对NGO组织的治理也并未沿着西方治理理论的指向前行。西方治理理论对中国治理实践的边际影响相对有限,“雷声大、雨点小”,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传播形成鲜明对比,西方治理理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中国困境”。本文即以此为研究对象,从西方治理理论的特殊性或非普适性、同中国治理模式的价值对立与冲突、以及对中国治理实践的潜在危害三个维度,对西方治理理论的“中国困境”做出深入解读。
一、西方治理理论植根于西方治理“土壤”——理论非普适性的历史溯源
(一)治理诞生的西方学术背景
治理(Governance)一词古已有之,向上可以追溯到古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但作为一个现代专业术语,却只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事。1976年,Jensen和Meckling在《企业理论:管理者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一文中,正式将企业代理成本问题抽象至理论高度,在逻辑上为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诞生铺平了道路。此后,公司治理先是围绕处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探讨,后来又扩展至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最终形成了企业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经平等协商,设计相互制衡的权利结构与机制,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架构。
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后不久,治理便开启了进军公共领域的征程。1989年,世界银行发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报告,首先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从1992年起,报告更名为《治理与发展》,治理旋即成为政治学、公共管理、公共行政、社会学等学科的时髦词汇,并通过加上不同的修饰语,如“全球”、“国家”、“政府”等,细化为多个分支领域。人们将治理同统治(government)与管理(management)区分开来,将其上升为人类处理公共事务的新方式、新方法,赋予其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实践中为了评价对象国的治理质量高低,治理学者设计并开发了“治理指数”,测算某一时点上某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供信息揭示与政策制定使用。为了给出国家治理质量的规范性标准,“好的治理”或曰“善治”的概念得以诞生,治理拥有了清晰的主观价值体系,该体系同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等观念密切融合在一起。
(二)治理理论兴起的西方动力
1.股份公司的普及与危机
古典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以出资人为中心形成集权型的企业治理关系,同利润最大化目标在逻辑上保持一致。然而,随着现代公司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两权分离衍生出的企业治理危机从可能逐渐变为现实。早在1932年,美国学者伯利和米恩斯就根据翔实缜密的实证数据警告世人:在股权高度分散化的美国公众公司中,管理者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屈一指,资本家将失去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这一论断石破天惊,不啻于是对资本逻辑的一次断然否定与严峻挑战。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公司治理危机若隐若现,公司治理失败案例层出不穷。在这一背景下,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在公司中如何控制“控制者”这一核心问题,于是以“权力分立、相互制衡”为基本理念的制度设计——公司治理应运而生。
2.直接民主的局限
“一人一票”式的直接民主是西方民主的基本形式。它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根据投票结果制定规则、选择方案,实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不可否认,直接民主有其体现民意的一面,但是它的民意涵盖率和决策效率却常常不能令人满意。直接民主的选举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选民”,一人一票更多体现的是“中间选民”的偏好,直接民主的初衷与其结果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直接民主同时也受困于决策效率低下问题,民众人数众多,偏好差异大,通过平等协商取得共识成本巨大,机会渺茫。直接民主的决策效率还可能受到“投票悖论”的影响,即某些初始条件达成时,集体投票程序决定投票结果,稳定一致的投票结论不可得。在西方直接民主实践中,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高福利”、“高赤字”现象成为各届政府的施政难题,布坎南用“赤字中的民主”对其进行了深度诠释,究其根源,依然同直接民主密切相关。为了克服直接民主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局限,主张“分权制衡、平等协商、多元共治”的治理理念开始崛起,凭借政府、政党组织、利益集团等主体的竞争与协作,优化决策机制,以提高决策效率。
3.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共生
市场与政府是人类社会自发演化的处理社会事务的两大机制。从亚当·斯密时代始,政府即被主流观念赋予“守夜人”角色,由“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乃至“大萧条”时代,市场失灵的严重后果引发了世人关注,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乘势兴起。上世纪70年代,“滞胀”问题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人们由此认识到政府机制也不完美。90年代后,“低增长、高失业”问题在多个欧洲国家并存,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相互叠加,为“欧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为了应对政府与市场的共同失灵问题,“第三条道路”成为各国政府新的路线选择,即除了依靠政府和市场两大机制外,通过引入“市民社会”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在同政府、市场的相互协作中,推动更为有效的集体行动。
(三)治理理论对外传播的西方模式
二战后,经济全球化掀起新高潮,商品、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统一配置,市场主体间的时空距离大幅缩短,相互交往的频率显著增加,交往规则不断趋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政府、大型跨国公司,凭借其掌握的全球化规则制定权,将西方治理理论与治理规则,大力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衍生出的强大话语权,使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采纳了西方治理规则并在本国推行相应治理实践。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IMF等国际组织,以西方治理理念为价值标准,制定了系统的治理指标评价体系,用来评估受援国的治理水平,变相强制输出西方治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巨大。
二、西方治理理论与中国治理模式在价值层面上存在深度冲突
(一)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
1.西方治理理论以契约论为基础
与管理不同,治理属于战略问题,涉及制度架构与基本规则,如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市场治理、企业治理、NGO治理等,同环境治理、黄河治理、网络治理等技术性概念相区分。这些治理领域虽不同,但存在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契约论。与亚当·斯密将交易作为人类本性和分析的起点类似,契约论将交易的达成——签约视作逻辑出发点。因发生领域不同,交易可以表现为政治交易、经济交易等不同形态,相应地,契约也表现为政治契约和经济契约等不同类型。具体来讲,国家是一个社会政治契约,是全体国民通过让渡自身部分权利而建立的、为保护自身利益服务的组织(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代表)。作为国家的代表,各级公共部门也是公民签约的结果。企业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同样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以阿尔钦、詹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为代表)。签约主体涵盖出资者、经理人、员工、债权人……其差异仅在于运营目标是赢利还是其他。签约者是利益相关人,有权为自身利益表达欲求。签约后的契约执行存在不确定性,组织运行需面对机会主义行为的侵扰,因此需要订立制定制度或规则,形成权力制衡架构,产生激励与约束机制,谓之“治理”。
2.中国治理模式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国家理论为基础
在中国,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国家理论占据社会政治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国家被视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与契约理论强调“无知之幕”假设、签约人地位平等、相互协商、自愿签约不同,阶级国家理论并非从抽象的、无差别的人出发,而是从社会政治经济实际出发,首先承认因生产资料占有不同所衍生出的阶级差别的存在,并对不同社会阶级赋予了差异化的政治经济地位与权力。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不存在社会签约的基础,跨阶级的共同治理也就无从谈起。虽然不存在跨阶级的治理,但马克思理论的强大包容性也并不排斥在广大统治阶级群体中,人民大众通过有形或无形契约形式选择政治、经济治理的具体模式,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即是统治阶级民众的具体治理选择。
(二)秉承不同的政府理念
1.西方治理理论的消极自由主义哲学与有限政府
治理理论的逻辑基础可以追溯到将自由视为最高价值的西方自由主义哲学,尤其是其中的消极自由学说。消极自由秉承“免于……”的自由理念,积极寻求个人自由的最大私人空间,对于任何干预“私域”自由的行为,皆持反对态度。在干预、控制私人行为的主体中,政府作为唯一合法垄断暴力资源的组织,危险系数最高,为持有消极自由哲学理念的人群所不信任。为了限制政府的干预能力,减少政府的干预行为,“有限政府”主张将政府限定为“守夜人”角色,而通过发展强大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来完成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治理。自由主义哲学在西方源远流长,虽被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所打断,但在上世纪70年代后重新崛起,西方治理理论即是在此自由主义复兴的大潮下发展壮大的。
2.我国治理模式中“强政府”传统与政府的强信托责任
我国拥有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历史,“强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特征,这既是对古老政治传统的传承,也是适应国情的制度自发演化。与“有限政府”相比,在处理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中,政府往往表现出强大的控制力,发挥更大的规制和引导作用。在治理规则的形成中,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着“元治理”角色,掌握着最终决策权。然而,政府强势并不等于政府权力毫无节制,政府权力要受到信托责任的严格制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深刻揭示了政府对民众的依存关系,政府行使公权力是基于民众的信任,当这一基础丧失时,失去治理权力就成为必然结果。“人民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信任与托付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强信托责任在社会主义中国比以往任何时代表现得更为突出。
(三)坚持不同的民主导向
1.西方治理理论坚持麦迪逊式民主理念
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中心主义,主张权威在多个政治或经济主体中分配,彼此间形成制衡与制约,从而区别于单一权威下的政治、经济统治,以确保公共或集体利益得以实现。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同大众式民主相对立的麦迪逊式民主理念。大众式民主遵从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原则,可能带来“多数人的暴政”问题;在大众民主中,个别精英派系的做大做强,可能通过合法程序转向专制统治。为了规避以上威胁,麦迪逊式民主继承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思想,并将其运用于美国的建国与立宪实践。麦迪逊式民主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并将其视为实现民主目标的重要工具,鼓励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实现各派势力之间的力量均衡。随着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兴起,市民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它们同政党、利益集团一道,成为实现西方民主与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政治经济力量。
2.我国治理模式的中式民主基础
民主,是大众的统治。在西方,形式上“一人一票”的大众式民主,因忽视选民的初始资源条件,结果上可能滑向“一元一票”的钱主。麦迪逊式民主以利益集团参与治理为基础,导致利益集团主导国家政治经济秩序,与民主初衷相背离,同时会遏制国家政治经济活力。与之相比,中式民主是一种结果导向的民主形式,以实现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将追求民意的最大公约数作为民主的本质所在。在民众的同意与支持下,我国衍生出超越狭隘政党利益、阶层利益的国家、社会治理主体,避免了利益集团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阻碍,展现出中式民主治理模式的高效与生命力。
(四)追求不同的治理均衡
1.西方治理理论的多元中心与竞争均衡
西方治理理论继承了自由市场经济重视竞争的传统,认为在资源稀缺条件下,通过发挥竞争机制作用,高效分配有限资源。在市场领域,买方之间、卖方之间、买卖双方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在公司内部,股东与经理人相互竞争,大股东之间彼此竞争;在政治领域中,政党之间、政客之间、利益集团之间也是明争暗斗。多元竞争在各方能量相互抵消的条件下,可以达成短期治理均衡。但是随着各方实力的变化消长,治理均衡将处于不断调整中。这种非稳定治理均衡可能产生积极效应,如督促在位者勤勉,纠正前期的错误决策,提高运行效率;也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如竞争者相互拆台,提升社会成本;政策的短期性与不稳定性问题;选举轮替,权威只负担有限责任,事实上也成为一种巧妙的卸责机制。
2.中国治理模式的“一元为主、多元参与”与合作均衡
与西方治理治理理论强调“竞争”不同,我国治理模式更讲究“合作”。在合作治理架构的中,一元为主、多元参与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典型特征。一元为主意味着核心治理主体的权力突出,责任重大,有利于达成相对稳定的治理均衡;多元参与则为不同治理声音的发出提供通道,有利于发挥辅助与监督作用。具体来看,我国的政党治理模式,既不同于两党或多党频繁轮替执政的竞争模式,也不同于一党仅存的统治模式,而是一种“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模式。该模式是历史的产物,具有坚实的民意基础,能够在充分发挥执政党一元决策高效率的同时,也能听取来自其他政党的不同声音,对于保证决策的科学性至关重要。在公司与其他经济社会治理领域,始终坚持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也是该模式在微观领域的具体延伸。与竞争均衡相比,稳态治理均衡能够带来制度与政策的稳定性与继承性,易于形成治理主体的代际合力,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一国治理水平的质量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核心治理主体的“选贤与能”能力以及确保贤能追求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在中国,执政党严格、严密的组织机制,为各层级优秀治理人才的选拔提供了程序保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超越性政治定位,再加上“从严治党”的基本方针,为实现高水平的国家、经济组织与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西方治理理论的盲目植入可能对中国治理实践产生潜在危害
(一)抢夺治理话语权,削弱中式治理自信
理论发明及传播事关学术话语权,尤其是社会科学思想成果,其话语权的争夺通常与国家利益、阶级利益、集团利益紧密相连。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世界经济史上“中国奇迹”的出现,从治理视角观之,当然同中国拥有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效治理模式密切相关。成功的治理实践催生科学的治理理论,对中国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抽象升华,理应成为中国治理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然而在治理领域,在中国特色治理理论尚未系统建立的当下,西方治理理论的盲目植入,从客观效应上讲,属于西方话语权在东方的攻城略地。随着西方治理理论影响的不断扩大,势必压缩中国特色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空间,削弱国人对于中式治理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从而可能干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及其目标的实现。
(二)侵蚀中式治理根基,带来治理实践混乱
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治理模式,西方治理建立在西式民主基础之上,强调多元竞争以实现治理绩效;中式治理以中式民主为根基,通过一元主导、多元合作机制达成治理目标。两种治理模式都是在各自长期的历史、文化、制度变迁中不断发展演化的,都体现出各自的独特性、针对性和适应性。如果用西方治理理论指导中国治理实践,用西方治理模式改造中国治理传统,归根结底,是用西方民主去取代中式民主,用多元竞争否定一元主导,结果必然是中式治理根基遭受侵蚀。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企业制度、社会组织制度等将面临全面洗牌,原有的稳态治理均衡被人为打破,治理实践陷入混乱。从国际视角看,南部非洲和拉美地区部分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用鲜活的历史事实,诠释了盲目植入西方治理理论及模式、割裂自身治理传统的危害性。
(三)背离效率原则,降低治理效能
西方治理理论自身也存在逻辑缺陷,不加分辨地将其应用于中国治理实践,可能衍生出治理问题甚至治理失败。西方治理理论是一个内嵌着效率与价值二重目标的理论体系,且二重目标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治理的初衷是对效率的追求,即通过治理在经济领域实现资源约束下的利益最大化,在公共事务领域实现社会公共福利的最大化。作为社会科学分支,治理理论又无时不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强调分权竞争,追求多元中心价值。然而,作为“理性人”的利益相关者拥有不同的目标函数,在相互讨价还价过程中,难以保证符合效率原则的方案被选出,甚至陷入“囚徒困境”,致使公司决策与公司价值最大化背离,公共决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背离。“权力清晰、权责对应”是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传统治理模式下,出资人是企业控制权主体,掌握着企业的最终决策权,承担企业破产的主要风险;政治权威享有政策制定权和执行权,同时担负着因政策失败所带来的政权更迭责任。与之相比,治理理论在激励约束条件的达成上存在逻辑与现实困难。多元权力中心并存,治理主体分享权力的比重是相互博弈的结果,该信息事前并不可知,使建立制度、清晰分权变得不可能。类似地,治理主体在集体决策中的边际贡献无法厘清,也就无法为治理主体划分决策失败的相应责任,这为治理主体卸责提供了良好借口。因此从技术角度讲,西方治理理论与效能原则的背离,同样会对中国治理实践产生负面影响。
四、结束语
西方治理理论是西方治理实践的产物,具有特殊性与条件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以“多元中心、分权竞争、民主共治”为内核,在价值层面上,同“一元为主、多元合作、权威责任”的中国治理模式间存在显著差异甚至冲突对立。中式治理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功,而盲目植入西方治理理论与模式,可能对在正确轨道上运行的中国治理实践产生危害。因此需要以批判的眼光对西方治理理论加以审视,以战略定力对中国特色治理模式加以坚持。以上因素共同作用,为西方治理理论的“中国困境”提供了深入解读。
〔1〕Francis Fukuyama(2014),“America in Decay.The Sources ofPoliticalDysfunction”,ForeignAffairs,September/ October.Vol.93(5),pp.5-26.
〔2〕Jensen MC,Meckling W(1976),“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Behavior,AgencyCostsand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October,1976, V.3,No.4,pp.305-360.
〔3〕[美]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 [M].李增刚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美]伯利,[美]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M].甘华鸣,罗锐韧,蔡如海译,商务印书馆,2005.
〔5〕[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德]马克思.资本论.(1、2、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
〔7〕杨瑞龙.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8〕[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华夏风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1).
〔9〕[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0〕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1〕王诗宗.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基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9.
〔12〕张小劲,于晓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六讲[M].人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王东伟】
D035
A
1672-9544(2016)10-0019-06
2016-07-14
杨松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治理理论、财政理论与政策。
中央民族大学校级学术团队建设项目“国家治理维度的民族地区财政问题研究”(课题号:2015MDTD33C)阶段性成果,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