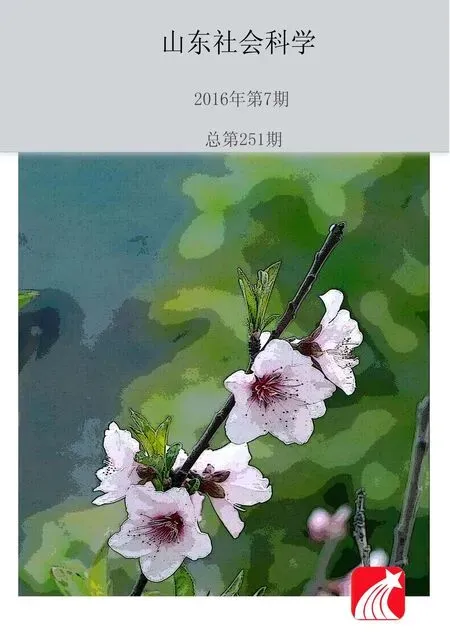恐怖艺术的悖论
——以当代西方学界的观点与论争为中心
2016-03-19章辉
章 辉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恐怖艺术的悖论
——以当代西方学界的观点与论争为中心
章辉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443002)
[摘要]恐怖艺术的悖论指的是观众享受了恐怖性虚构所产生的恐惧和厌恶。当代西方学界提出了补偿论、享受论、控制论等多种思路解决这一悖论,其思路和观点对中国学界具有高度的启发性:一、不同风格类型的艺术品具有不同的特质,恐怖性愉悦所指的对象是不同的;二、不同欣赏者的认知情感反应不同,从恐怖性作品中所获得的愉悦的特质和程度有差异性,需经心理学实验的调查和认定;三、如果艺术性恐怖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否需要和如何获得理论的普遍性就是一个问题;四、补偿论、享受论、控制论等观点,相互之间有冲突也有互补,都从某个层面、某个角度解释了恐怖艺术的悖论现象。恐怖艺术的悖论涉及艺术品的特质、观众的认知情感反应、心理学事实的界定等诸多层面的问题,关系到审美心理学、艺术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问题的解决,需在前人的基础上,面对具体艺术作品,借助心理学的实验,提出新的理论假设。
[关键词]恐怖艺术的悖论;补偿论;享受论;控制论
恐怖艺术的悖论由三个命题组成:一、人们常常从恐怖性的虚构中获得了享受;二、恐怖性虚构在观众心中产生了恐惧和厌恶;三、恐惧和厌恶本质上是非愉悦性的情感。这三个命题各自成立,但综合起来看,即是观众享受了恐怖性虚构所产生的恐惧和厌恶,这是不合逻辑的,其中必有一个命题是错误的。那么,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怎么可能享受恐惧和厌恶呢?当前西方学界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观点众多,歧义纷纭,其多维的思路对此悖论的解决具有高度的学理意义。本文拟梳理和分析当代西方学界的这一问题史,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提供思想参考。
一、补偿论
一方面我们厌恶生活中恐怖恶心的东西,被迫去接近会是不愉快的经验。但另一方面,很多人从恐怖性虚构的描绘中获得了愉悦。问题就是,为什么观看恐怖性虚构的观众会被在日常生活中排斥的东西所吸引?或者是,观看恐怖的观众如何从本质上是不舒服的可怕之物中获得了愉悦?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提出了补偿论解释这一现象。在卡罗尔的理论中,魔鬼的出现是艺术性恐怖的前提条件。在界定魔鬼时,他借用的是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生物学范畴和裂隙性实体(interstitial entities)的概念,魔鬼的恐怖性效果来自文化性地决定的分类实体的需要,其所激发的恐惧和厌恶被文化人类学家视为禁忌反应(taboo reaction)。卡罗尔认为,恐怖中的核心生物即魔鬼基于其“不洁”(impure)让我们产生厌恶感,它们的不洁违反了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范畴系统。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卡罗尔认为,恐怖情节让观众投入发现、寻证、解释、设想和确证的过程,所有这些都指向恐怖性的魔鬼。既然这些魔鬼是不可能的存在,它就不能以我们既存的概念去解释。我们容忍恐怖艺术的恐惧和厌恶,是因为我们有深刻的欲望去理解那些魔鬼。我们从恐怖电影中获得的愉悦并非来自我们恐惧和厌恶的经验,而是来自好奇(curiosity),即恐惧和厌恶的不快经验被我们参与恐怖性虚构中所获得的认知性愉悦所超越。
这就是说,恐怖性虚构作品的叙述结构与其产生的愉悦相关。大多数恐怖题材都是叙事性的,在很多恐怖叙事中,这些故事常常是围绕着证据、揭开、发现、证实某种不可能之物的存在、某种违反既存概念之物而展开的。部分故事中,与人们的日常信念相反,认为这样的魔鬼是存在着的,结果是,观众的预期围绕着这些存在之物在故事中是否被证实而发展着。有时这些信息(即魔鬼存在着)被推迟到虚构作品的结尾。有时即便观众已经知道情节发展,虚构中的人物仍然必须经历魔鬼是否存在的揭开过程。人们想知道,魔鬼是否为科学家或巫师所创造。而且在魔鬼的存在已经被揭示之后,观众仍想知道魔鬼的本质,它的身份、它的起源、它的目的、它的超人的力量和特性,包括其弱点。这样,“很大程度上,恐怖故事是为好奇所驱使,它把观众投入到发现、揭示、证据、解释、设想和确证的过程之中。怀疑、害怕魔鬼的存在只是揭示了魔鬼存在的陪衬。”*Noel Carroll,“Why horror?” in Alex Neill and Aaron Ridley,Arguing About Art,Routledge,2002,p.279.这里,愉悦是认知性的。因此,“对这些魔鬼的厌恶可能应该被视为从对其的揭示中获得的愉悦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厌恶自身,或多或少地是为好奇所控制的。”*Noel Carroll,“Why horror?” in Alex Neill and Aaron Ridley,Arguing About Art,Routledge,2002,p.283.即是说,我们的愉悦来自对这些不可能之物的叙述所产生的好奇,是一系列推论、发现、揭示、解释等带给我们愉悦,厌恶只是这一发现过程的伴随物。
卡罗尔把恐怖性的愉悦奠定在认知之上,有人可能反对说,在非叙述性的艺术品如摄影和绘画中缺乏这样的叙述策略,不需要一系列的认知过程,那么恐怖性的愉悦来自哪里?卡罗尔认为,不能说好奇仅仅是情节的功能,恐怖艺术中的物体本身就产生了好奇,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能够支撑情节展开的原因。恐怖艺术中的物体是不纯的、异常的,其异常的本质使得它们是搅扰性的、令人不安的、讨厌的。但它们偏离了我们分类世界的图式,这就立刻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要去探索其令人吃惊的特质。即是说,基于它们的非常规的本质,它们是令人厌恶的,但也是吸引人的,它们以某种以前无法设想的景观激发了我们的认知性兴趣。总之,“其愉悦的来源是整个的叙述结构和恐怖之物的形象本身。大多数时候,则是情节结构产生了魅力。”*Noel Carroll,“Why horror?” in Alex Neill and Aaron Ridley,Arguing About Art,Routledge,2002,p.288.小说和电影的叙述过程强化了我们的好奇心,而且,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是虚构的,相比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它们,它们所激起的恐惧和厌恶要弱化得多,这就使得好奇心的愉悦更为容易地压倒了恐惧和厌恶的不快。
卡罗尔的观点可称为补偿理论。补偿理论认为,X风格类型的艺术品提供了补偿性的愉悦Y,后者超过了它们所引起的痛苦。对于动力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看X风格类型的作品呢?补偿理论的回答是,这样的作品提供了某种类型的补偿性的愉悦,要大于其所引起的痛苦的情感。但问题是,说愉悦超过了痛苦,这是什么意思呢?需要多少智性的探索才能相当于一个恐惧或厌恶?卡罗尔可能回答说,他并不认为观众会有意识地做这样的计算,某种无意识的对快乐的计算可能基于我们以前对于这类艺术的经验。对于大多数人,过去的经验应该是更为愉悦的,而非痛苦的。阿诺·斯玛特(Aaron Smuts)指出,对于补偿理论,需要这样的观众报告的证据,表明其经验整体是愉悦性的。但是面对痛苦性艺术,这样的要求很难实现。*Aaron Smuts, “The Paradox of Painful Art,” in Journal of Aesthetics Education,Vol.41,No.3(Fall,2007),pp.59-76.
二、享受论
高特(Berys Gaut)采取的是一种独特的情感认知理论。主流的现代情感理论认为,情感是认知性的,害怕某种东西就评价其为危险的,对某人产生愤怒就评价其行为是错误的,悲痛是因为意识到某种东西失去了,等等。如果情感以其评价而相互区别,那么在积极和否定情感之间的差异必定包括评价性想法之间的差异。即是说,使得否定情感是否定的原因不是情感反应的痛苦或其客体的痛苦,而是基于这一事实,即这些情感所指向的客体是被置入否定性的评价之中如危险的、错误的、可耻的等。基于此,高特认为,既然我们能够否定性地评价某种东西而无需发现它是非愉悦性的,那么结论就是,可能存在着既是否定性的情感反应,又发现它们的客体是愉悦性的。这样,诉诸情感的评价理论,我们能够说明,在否定性情感的愉悦中,不存在悖论性的东西,因为只需要某个人否定性地评价这些情感的客体。高特认为,卡罗尔很清楚情感的评价理论,但他没有看到的是,他所认为的恐惧所需要的“非正常的、身体所感受到的激动”,不必是不愉快的状态,因为情感的否定性能够借助情感的客体而获得解释,而非情感自身是非愉悦性的。*Berys Gaut, “The Paradox of Horror,” in Alex Neill and Aaron Ridley,Arguing About Art,Routledge,2002,pp.301-303.高特说,在评价和愉悦之间存在着概念性的连接。如果某个人积极地评价了一种状态,那么他在想获得它的时候就会感到愉悦;相反,如果某个人否定地评价一种状态,他就会发现身处那种状态是不愉快的。这些是“必要性的典型的”情况,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典型的”情况,或“非典型的人们”能够享受否定性的情感。他们知道电影是虚构的,他们和电影演员都没有处于危险之中。这样,我们就能够消解恐怖艺术的悖论。*Berys Gaut, “The Paradox of Horror,” in Alex Neill and Aaron Ridley,Arguing About Art,Routledge,2002,pp.304-305.因此,高特说,简单的解决悖论的方法是他的享受理论(enjoyment theory),即是,恐怖具有吸引力是因为人们在害怕和厌恶中获得了享受。这种观点的证据可以在人们所描述的其他活动中找到,比如登山、玩滑翔伞、坐过山车等。参与者都认为,其愉悦部分地来自把自己置入危险境地而引起的害怕。*Berys Gaut, “The Paradox of Horror,” in Alex Neill and Aaron Ridley,Arguing About Art,Routledge,2002,p.298.高特还说,这些现象不限于害怕,人们也可以享受其他的否定性的情感如厌恶,比如大学校园流行的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的电影《粉红色的火烈鸟》(PinkFlamingos)。愤怒这种否定性情感也可以被享受,有些脾气暴躁的人要寻找机会发怒。类似地,我们可能欣赏一种安静的忧郁感,流连于生活的悲痛和失望,为世界的悲哀而流泪等。
凯特琳娜(Katerina Bantinaki)的研究进一步充实了高特的理论。传统观点认为,生理症状的快乐的特质决定了一个情感的效价(valence),即或者积极的或者否定的。如果我们承认,恐惧伴随着不同类型的生理上不愉快的症状,我们就被迫承认,恐惧必然是否定的,整个来说是不愉快的情感,对恐惧的享受在我们遭遇恐怖电影时就是悖论性的。但凯特琳娜认为,传统观点是不准确的:不是身体症状的快乐特质(hedonic quality)决定了某个情感的效价,心跳加快、呼吸加速既是否定情感也是积极情感的身体反应,比如看到一条蛇,或者看到了心爱的人的反应。而且,不同的积极的和不同的否定的情感感觉起来是非常不同的,它们并非具有某个现象性的共同的能够把它们完全归类为积极的或否定的范畴的公分母。那么我们能够假定,情感的效价是为对其客体的评价所决定的,就如情感的认知主义观点说的那样吗?凯特琳娜认为,这也存在疑问。一方面,如罗伯特·苏龙(Robert Solonom)说的,同样的一个情感能够联系于许多评价,某些是积极的,某些是否定的。比如愤怒,包含否定的评价之于冒犯者或他的冒犯性行为,但它也包含对自我的积极的评价。另一方面,某些情感比如怀旧似乎具有积极的或否定的立场即便其组成部分的评价是固定的。不论怀旧是否包含对过去的积极的评价,或者对当前环境的否定性评价,无可怀疑的是,有时它被经验为否定的、破坏性的情感,但在其他的时间则是积极的、温暖的情感。吃惊是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既非生理学症状,也非构成性的评价决定了某个情感的效价,那么,情感经验的什么方面可能具有这种功能呢?
凯特琳娜认为,情感和其表现方面能够严格地两极化为相互排斥的或积极的或否定的方面的观点忽视了日常生活中情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这种可能,即在一定的环境中,恐惧可能不是完全的否定性的情感,尽管它包含否定性的生理学症状,或否定性的对于其客体的评价。普林茨(Prinz)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他认为所有情感包含“效价标识(valence markers)”,否定性的情感包含了作为内在的惩罚的组成部分,即一种标识说:减少之!积极的情感包含了作为内在的奖赏的组成部分,即一种标识说:增加之!这种自我指涉性的评价不是认知性的,它不是一种判断,而是内在的状态,是生理学的机制,并非必然有意识地被感受到,但是对于行为具有影响。因此,虽然包含了痛苦的身体性症状的情感更可能是否定的效价,愉悦的身体性症状包含的是积极的效价,但并非必然如此。有可能的是,某个情感是积极的效价,虽然它包含了不愉快的生理学症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与传统观点相反,恐惧不必然是否定的情感呢?回答是肯定的。凯特琳娜的观点是,在恐怖反应中的恐惧,是一种积极的情感。*Katerina Bantinaki,“The Paradox of Horror:Fear as a Positive Emotion,” 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70:4( Fall,2012).凯特琳娜的观点似乎加强了享受理论的说服力,但享受理论难以解释的是,人们对很多电影的反应不是愉悦性的,比如,电影《为了国王和国家》中战争的非人性、小说《勇敢的新世界》中的政治压迫以及很多名著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谋杀、强奸、折磨、酷刑等,这些作品给人的经验都是不愉快的。
三、控制论
约翰·莫瑞尔(John Morreall)的观点可称为控制论,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够享受否定性的情感。比如在恐惧中,我们判断自己处于险境,有动力去消除危险,此时神经系统会发生变化,我们提高警觉,肌肉紧张,心跳加快,血液在全身重新分配。这其中的许多变化我们可能并非都能够意识到,但我们能意识到它们产生的兴奋,就是这种兴奋,使得恐惧是愉悦性的。特别是对于过着比较单调乏味的生活的人,恐惧所产生的刺激就是愉悦性的。但有一种情况,其中恐惧不是愉悦性的,比如跳伞者没有打开降落伞,这完全是非愉悦性的恐怖感。因此需要把恐惧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即我们能够享受否定性的情感,只有在我们能够对自己的处境有完全的控制之时。莫瑞尔说,当我们仅仅参与了某种事件而不会有实际后果的时候,控制通常就是最容易的,比如当我们从远距离观看某种与我们无关的事件的时候。这里,控制需要我们有能力去自由地运用注意力,即我们可以去注意,也可以停止注意。当我们具有了这种开始、停止等指向我们的经验的能力时,我们就能够享受这种经验,甚至是“不愉快的”经验。我们能够享受性地观赏某个赛车中的车祸,甚至能够享受温和的疼痛,比如当我们用舌头探索嘴巴里的某个疼痛的点,或者只为产生这种感觉而拉伸某个疼痛的肌肉。甚至是更为强烈的疼痛,我们实际上是不能享受的,但基于我们能够某种程度地控制它们,我们也较少地为其所困扰,比如当牙医告诉我们何时开始、何时停止钻孔的时候。
莫瑞尔指出,与恐惧类似,在愤怒中也存在愉悦,愉悦来自在表达愤怒之时告知了某个人我们的心灵,它界定和表达了我们的自我形象。在悲哀中也存在愉悦,此时我们撤回到内心世界,就如在床上取暖那样,我们撤回到关于自己的思想之中,去体会我们所经验到的或失去的东西。在表达悲哀之时也有愉悦,就如在愤怒中痛快地哭一场,也是对我们自己和其他人表达我们是谁、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当其他人在场时,表达悲哀也会引起同情,他们抚慰我们也会增加愉悦。我们能够从其他人的或肯定性的或否定性的情感回应中获得满足,这种同情的愉悦关系到我们作为社会性的种类,加强了我们合作的行为。相反,在真实的恐怖性的情境中是不愉悦的,因为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注意力以及我们的身体和整个的情境。无客体的恐惧或一般性的焦虑也不是愉悦性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来源,我们感到无法控制它和我们的处境。在极度愤怒中,我们失去了控制,不再指向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在温和的愤怒中的愉悦,即集中在我们自身、告诉世界我们是谁,在这里就消失了。因此,在愤怒、悲哀、同情以及其他的否定性情感中,要获得享受的话,控制的元素非常重要。莫瑞尔指出,指向虚构的情感和指向过去的情感缺乏实践的动力,这是其区别于指向当前情境的情感的地方,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够享受否定性的指向虚构的情感。在我们参与对我们缺乏实际性的后果的事情之时,控制是最容易的,我们能够开始、停止、调整我们的注意力。*John Morreall,“Enjoying Negative Emotions in Fiction,” 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Volume 9,Number 1(April 1985),pp.95-103.莫瑞尔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对虚构所引起的否定性情感的享受基于我们的控制。
罗伯特·雅纳尔(Robert Yanal)不赞同控制理论,他说,如果某个观众被困在剧院里,按照控制理论,虚构作品在观众看来会更为痛苦,但这显然不是真的。但阿诺·斯玛特反驳说,这个结论可能很荒唐,但它没有否定控制理论。如果某个观众被困在椅子上,眼皮被撑开,相比普遍的观众他可能感受到更多的痛苦,就如控制理论预言的。在游戏中,要获得愉悦,参与者必须是自愿自由的,只要他愿意他必须任何时候都能够走出游戏。经验虚构类似游戏,我们对于虚构的投入的控制使得它们更少痛苦,或者说如果我们失去了控制,其经验将变得更为痛苦。*Aaron Smuts,“Art and Negative Affect,” in Philosophy Compass4/1,2009,pp.39-55.阿诺·斯玛特指出,最近的实验支持了莫瑞尔的控制理论,比如,在受试者能够控制施加给他们手指的压力何时停止的时候,他们能够承受很大的压力和疼痛;相反,在他们不能控制实验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大得多的痛苦。类似地,我们对艺术的经验较少痛苦,因为我们通常知道它们是否会发生、何时应该停止,我们甚至能够决定离开剧院或合上书本。但斯玛特认为,控制理论没有可信地回答我们为什么想要去经验这样的否定性的情感。我们对虚构文本的否定性情感经验可能不那么痛苦,因为我们能够某种程度地控制其发生,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们根本就不是痛苦的。虽然我们能够决定去看一场电影,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走出电影院,但当我们走出音乐剧院或看完一部恐怖电影的时候,我们不能停止感受紧张和不安。即是说,控制理论没有回答动力问题。*Aaron Smuts, “The Paradox of Painful Art,”in Journal of Aesthetics Education,Vol.41,No.3(Fall,2007),pp.59-76.
那么,我们去体验艺术中的否定性情感的动力何在呢?斯玛特的解释是,我们通常从艺术中而非现实生活中寻求这种经验,因为艺术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性,这种安全是不会呈现在激起了极端的痛苦、厌恶、愤怒、恐惧、可怕以及其他一系列反应的现实情景之中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大多数这种反应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所有而不遭致重大的危险,这些危险是我们所不取的,因为它们远远超过了所得。如控制理论说的,既然这种经验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够控制它们,牵涉其中的痛苦往往就没有跨过一定的可容忍的限度。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我们最丰富的审美经验来自遭遇痛苦的艺术,人们很少有机会能够这么完全地、智性地、情感性地投入痛苦艺术之中,拥有这样的经验本身就是奖赏。在艺术中,我们能够感到恐惧而无需有生命之虞,同情而无需看到我们的爱人受苦,紧张而无牢狱之灾。斯玛特的观点是,艺术安全地提供给了我们机会去拥有丰富的情感经验,这些情感经验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危险的。*Aaron Smuts, “The Paradox of Painful Art,”in Journal of Aesthetics Education,Vol.41,No.3(Fall,2007),pp.59-76.斯玛特的观点解释了参与痛苦性艺术的动力问题,是对控制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马克·帕克(Mark Packer)认为,莫瑞尔的问题是,主要把控制放置在欣赏者而非艺术家。帕克说,即便莫瑞尔说的是对的,自我控制能够把日常生活中的不快转换为愉悦性的经验,但这并非可宽泛地应用到艺术之中。更常见的,是艺术家在欣赏者的情感之上操练了规则和权力,欣赏者常常无法控制其情感反应,我们甚至要求某个戏剧引起观众的自发的反应。对于控制理论,当积极的和否定的情感被视为相互意图性的时候就有问题了。莫瑞尔认为,当我们经验悲剧的时候,悲哀或者愤怒才是愉悦的对象。虽然不是病态的,对否定性情感的享受,在莫瑞尔看来,很显然是孩子兴趣的成年人操练,这包括增强某个人作为受苦者的自我意识,激发同情,偶尔地享受一次大哭,或投入自我正义性的愤怒之中。这种行为,虽然基于其净化价值是可原谅的,但它是不成熟的,常常演示这种行为的人就被视为孩子气的。莫瑞尔没有分析审美性的对否定性情感的享受,它区别于这种孩子气的自我中心的行为。控制理论的问题是,它暗示,审美经验只是社会所允许的这种孩子气的情感沉溺的陪衬物。帕克认为,审美情感包括同情,但也牵涉到情感反应之于更为普遍性的由作品流露出来的意义,这对于解决悲剧的悖论具有决定性作用。*Mark Packer,“Dissolving the Paradox of Tragedy,”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47,No.3(Summer,1989),pp.211-219.
莫瑞尔认为,在虚构中特别容易享受到否定性情感,因为虚构之于观众没有实际性的后果,这个时候控制是充分的。一旦他失去了这种控制,比如因为虚构生动地描述了暴力和苦难,以至于他的否定性情感变得极其强烈,那么他可能不再享受那种情感了。高特指出,这种回答仍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能够享受本质上是不愉快的情感,即便我们能够控制情境。而且,被虚构所吸引时,我们感到我们是不能控制自己的,还有,许多人似乎不能享受恐怖性的虚构即便他们知道它仅仅是虚构。高特认为,人们彼此之间差异很大,是否能够享受恐怖电影不能预期。如果某个人不能享受它们,不一定是因为她不能充分地控制她自己的注意力,而是因为当她把注意力指向血腥的尸体的时候,她不喜欢她所经验到的东西。但另外一个人可能相信,他享受恐怖性的愉悦是当他的眼睛为可怕的景象所抓住之时。因为,毕竟,如果某个人在享受某种东西,是他的注意力不可抵抗地被吸引住了。*Berys Gaut, “The Paradox of Horror,” in Alex Neill and Aaron Ridley,Arguing About Art,Routledge,2002,p.300.
四、问题与论争
当前西方学界就恐怖艺术的悖论展开了持久的讨论,多方观点的交锋呈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思路的多维性。在呈现了几种主要的观点之后,我们再看看围绕具体问题的争论。高特撰文对卡罗尔的观点作了反驳。高特指出,不是所有的恐怖电影都关系到魔鬼,一个重要的现代恐怖电影的亚类“绞肉机”电影,即精神病患者的系列谋杀案就并非如此。精神病患者不是魔鬼,他们是真实的现象。但卡罗尔反驳说,有些这样的精神病患者被呈现为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因此是真正的魔鬼。*Noel Carroll,The Philosophy of Horror or Paradoxes of the Heart, Routledge,1990,p.37.他还说,如果主人公是人,但类似魔鬼的话,那么牵涉到他们的虚构则是在恐怖的边缘地带,我们应把这些虚构视为“可怕故事(tales of terror)”。*Noel Carroll,The Philosophy of Horror or Paradoxes of the Heart, Routledge,1990,p.15.但高特批评说,如果是后者,这就把恐怖艺术的悖论转换为可怕故事的悖论,关系到魔鬼的解决方案就行不通了。另一方面,把某些人类的精神病患者说成类似魔鬼,这是依赖于魔鬼这一概念的比喻性的延伸。卡罗尔诉诸魔鬼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我们能够厌恶和害怕人类,因为他们做了罪恶和可怕的事情,无需提及魔鬼就可以解释我们的反应。*Berys Gaut, “The Paradox of Horror, ” in Alex Neill and Aaron Ridley,Arguing About Art,Routledge,2002,p.296.
高特认为,卡罗尔的问题还在于,大多数恐怖电影的情节是如此的模式化,其魔鬼和杀手是如此类型化,以至于很难相信我们的好奇心会经常被充分地激发以去克服这些作品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不愉快的情感。最后,设想某个叫罗曼的人从电影院里出来后很失望地说,电影不够恐怖,他想要的是真正的可怕。卡罗尔的解释应该是,他的好奇心没有被激发(heightened)。但这并非罗曼的意思,他想要表达的是,这部电影不是可怕的(frightening)。*Berys Gaut, “The Paradox of Horror,” in Alex Neill and Aaron Ridley,Arguing About Art,Routledge,2002,p.297.即是说,卡罗尔认为,电影没有满足罗曼的好奇心,他把原因归为认知性的;而高特认为是电影不够恐怖,把原因归为情感性的。这就回到了恐怖艺术的悖论的核心:人们似乎享受了否定情感。高特的享受理论认为,恐怖具有吸引力,是因为人们能够享受恐惧和厌恶。这种理论能够解释罗曼的抱怨,能够解释恐怖电影的突出特征,即这种类型的电影就是有意地致力于在观众身上生产恐惧和厌恶。而且,大量的这类作品缺乏严肃的艺术价值,它们纯粹是娱乐性的,就是简单地提供享受性经验。考虑到这些,最简单最直接的解释恐怖性欣赏现象的理论就是,人们享受了害怕。*Berys Gaut,“The Paradox of Horror,” in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Vol.33,No.4(October,1993).
卡罗尔对高特的批评作了回应。卡罗尔说,恐怖性虚构包含了魔鬼,这是科学难以解释的。在恐怖片《外星人》(Alien)和《掠夺者》(Predator)系列中是身体方面的科学性虚构(science fiction),而在《沉默的羔羊》中则是精神方面的科学性虚构,从科学的正当性角度看是名副其实的魔鬼,这不冲突于他的理论。关于情节的模式化和魔鬼的类型化,卡罗尔回答说,首先,要分清预期性的消费者(prospective consumer)和积极的消费者。对于前者来说,既然恐怖性小说是如此的模式化,购买恐怖性小说就是不合理的吗?不是的,因为有如此多的恐怖小说,下一本可能就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了。对于积极的消费者,他能对模式化的情节和魔鬼入迷吗?回答也是肯定的。高特忘记了,虽然这些情节是模式化的,但这些模式是精确地安排的,没有人否认它们激起了不可抵抗的好奇。罗曼抱怨电影不够恐怖,卡罗尔说,我们不能从罗曼的说法中贸然得出结论,他的说法可能指的是:“我太过顽固了,不能为这种东西所感动。”连高特都承认,理论家常常搞不清恐怖性虚构的吸引力的来源,何况普通人如罗曼呢?
高特论证的逻辑起点是,害怕和不愉快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比如登山享受高度的恐惧。但卡罗尔认为这不能说服他。卡罗尔说自己没有登山的恐惧性愉悦的经验,但他享受过滑水。在这种经验中,他注意到他没有害怕,他必须完全集中在情景本身。类似地,如果某个人的汽车在冰面上打转,他就必须集中注意力把车轮转向打滑的方向,不能沉溺在当下的害怕之中。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愉悦的,但如果有害怕的话,就不能有愉悦了。登山的情况与此类似。而且,卡罗尔认为,诸如电影《粉红色的火烈鸟》的欣赏者并没有享受厌恶的经验。他们从夸耀好的趣味中获得愉悦,就如先锋派的趣味触犯了中产阶级那样。面对让他们的父辈厌恶的奇观,沃特斯的追随者欢笑并尖叫着,这种笑声表达了一种优越感、一种青春期的身份,对立于他们先辈过时的成规。
卡罗尔也赞同情感的认知评价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情感不能等同于参与其中的心灵的特质和生理性的骚动,比如恐怖,不能等同于恶心感。但这种观点并非否定这一事实,即无论什么样的感觉关联于恐怖,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感觉本质上是不愉快的。这就是说,我们否认情感等同于特殊的感觉,但关联于某个情感的感觉的范围是有限的,比如恐怖,其限制就是,关系到它的感觉一般来说是不愉快的,比如恶心、胃疼、窒息、毛骨悚然等。
最后,高特认为,当处于恐怖中,人们必然典型地经验了不快,这就否定了某些人,即非典型的人,或可能是所有的人在非典型的环境中也能经验害怕。但是,卡罗尔说,他能够提供相反的例子,比如《侏罗纪公园》以及前此大卖的恐怖小说,电影公司声称这是第一部票房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电影,而且预测说,在美国之外比美国卖得还要好。那么,能够说,它的世界范围内的消费者是非典型的吗?也不能说,阅读恐怖小说或看恐怖电影而害怕了是非典型的。因为在工业化国家,我们很少经验恐怖,除了在艺术中之外。比如卡罗尔自己,不记得在审美经验之外有过任何恐怖性的经验。即是说,艺术恐怖的经验就是非常典型的。因此,如果必然地、典型地害怕了的人们经验了本身就是不快的情感,大多数看《侏罗纪公园》的人必定是经验了不快,高特的享受理论就没有解释大多数这种人的现象。如果他们享受了电影,那么他们必定是享受了某种害怕了的东西之外的东西,卡罗尔认为,他们是对魔鬼入迷了。*Noel Carroll, “Enjoying Horror Fictions:A Reply to Gaut,” in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Vol35,No 1(January,1995), p.67.
针对卡罗尔的回复,高特再次作了批评。卡罗尔说,作为恐怖片,《沉默的羔羊》是关于心灵的科学性虚构,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病,它是想象性的或神话性的存在。但高特反驳说,要说电影中的精神病是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病的虚构性推演,并不表明他们就是不可能的存在之物,比如我能够说某个真实的人具有魔鬼般的性格。而且,卡罗尔观点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解释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病的入迷,即对非虚构性的连环杀手类型的书籍的兴趣是真实的。真实生活中的杀手不是不可能之物,我们对无论是虚构性的还是真实的精神病杀手有兴趣的最好最简单的解释,是怪异的罪恶的人们让我们入迷(想想人们对希特勒的兴趣),他们打破了我们的局限,甚至是想象。在高特看来,如果卡罗尔吸纳其他类型的存在,入迷理论就更具有阐释效力。即便如此,这种理论仍然存在问题,因为它认为我们不能享受害怕。
高特的第二点反对意见关系到大多数恐怖电影的模式化问题。高特说,按照卡罗尔的逻辑,如果我们设想恐怖性虚构所产生的恐惧和厌恶是需要克服的不利的东西,那么,这些虚构所激发的好奇心的程度将必须是非常大的,大到使得整个经验是愉悦性的,但是,大多数恐怖电影的情节是可预测的。根据卡罗尔的观点,这也是令人困惑的现象,即既然幻想题材(fantasy genre)也牵涉到魔鬼,而且没有在观众那里激发害怕和厌恶等不利因素,那为什么这种题材的作品并不比恐怖题材更为流行。卡罗尔诉诸侦探小说也没有能够支持他的观点:这些小说没有产生不愉快的情感。因此按照他的观点,恐怖艺术所产生的好奇必须比侦探故事所产生的好奇更大,如果要使得它是相当快乐的话。但是,刚好相反,一部好的侦探小说激起的好奇就相当大,而在恐怖电影中,并没有相当的设置让我们投入其中并收获智性推测:在我们看到它之前,我们就知道有一个魔鬼,还有线索关于魔鬼是什么样的,缺乏如同侦探小说般激发我们的智性好奇的东西。对于恐怖的模式化,高特提出了不同于卡罗尔的解释:恐惧集中在它们的对象。大量的恐怖题材依赖这样的恐惧作为其效果,不奇怪的是,模式常常被反复使用。因此,恐怖的模式是产生恐惧的模式,不是激发好奇的设置。
高特的第三点反对意见关系到观众抱怨某部电影不够可怕,他认为卡罗尔的解释不可信,因为如果人们想要有趣的魔鬼和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情节,他们完全能够在幻想性的虚构中获得。高特指出,他们需要的其实是卡罗尔认为阻碍了他们享受的恐怖虚构中的害怕和厌恶,因为普通观众、电影制作者、广告商都在讨论和评价恐怖电影的惊吓人的能力。
针对卡罗尔的批评,高特说,欣赏恐怖电影的人可能被这种欲望所激励,即相比其他人而言在趣味上有优越感,但如果这是事情的全部,为什么他们不满足于看喜剧片去嘲笑他们的父辈呢?为什么要忍受基于厌恶所带来的不愉快呢?事实上,这些电影的广告说它们是令人厌恶的、污秽的,这就是观众所需要的。最好的解释就是,厌恶本质上不是不愉快的。 关于卡罗尔提到的典型性问题,高特的回答是,不是人们是非典性的,而是人们所面对的条件是非典性的,即面对虚构。高特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感受到恐惧和厌恶,关系到这些情感的典型条件是真实生活而非虚构。这两种情感常常是在面对虚构的条件下才在一起的,在现实中常常是独立的情感。虚构性的条件是非典型的,不是因为它们不是经常发生的,而是人们不相信所描绘的事件和人物的真实存在。可信的是,害怕的功能是让我们回避危险的情景,相对于这种功能,我们在虚构中经验这种情感的条件,即我们知道自己不是真的在危险之中,就被视为非典型的。*Berys Gaut,“The Enjoyment Theory of Horror:A Response to Carroll,” in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Vol 35,No 3(July,1995).
阿历克斯·尼尔(Alex Neill)也对卡罗尔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卡罗尔的理论有两大问题,一是他没有讲出恐怖性虚构之于欣赏者的独特吸引力,二是他没有抓住恐怖性虚构的情感效果。尼尔认为,如果恐怖性叙述所带来的好奇就是卡罗尔所说的关于未知的、不可能存在之物的好奇,那么,这种好奇也就是寻找上帝、超人的出生,或哲学家的石头、圣杯等叙述所带来的好奇。尼尔认为,恐怖艺术的悖论没有什么神秘的,痛苦的东西能够是美丽的,或令人惊奇的、激动人心的,我们能够认识或欣赏其美丽,从中获得愉悦,同时感受到痛苦。他认为,在亚里士多德和休谟那里,悲剧的愉悦不是伴随或并存于同情和恐惧的痛苦,而是同情和恐惧的愉悦(pleasure of pity and fear)。因此,他认为,恐怖的愉悦,很大程度上就是害怕的愉悦(being horrified),我们所经验到的之于恐怖性虚构的愉悦和恐怖反应是分离的,它们的对象是不同种类的,这就错失了“心灵的悖论”(paradox of the heart)。尼尔指出,卡罗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卡罗尔曾说,他的观点似乎使得害怕的经验太过远离题材的经验,我们对恐怖之物所感受到的厌恶太过分离于我们在这种题材中发现的吸引力。*Noel Carroll,The Philosophy of Horror or Paradoxes of the Heart, Routledge,1990,p.187.他还说,作为对既存的文化范畴的违反,恐怖性虚构中的魔鬼是搅扰性的、令人厌恶的,但是同时,它们也是迷人的客体。*Noel Carroll,The Philosophy of Horror or Paradoxes of the Heart, Routledge,1990,p.188.尼尔说,这就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为它试图结合愉悦和否定的情感,这就能够解释恐怖的独特的吸引力。但是卡罗尔的观点仍然没有走到这一步,因为他的观点仍然是“并存”的,其关键之点是我们的愉悦的魅力“超过了”或者“补偿了”我们所经验到的厌恶。事实上,卡罗尔没有意识到从恐怖中获得的愉悦是独特的,而是认为,我们可以从其他非恐怖之物中获得这种愉悦,比如从仙灵故事和神话中获得。*Noel Carroll,The Philosophy of Horror or Paradoxes of the Heart, Routledge,1990,p.192.即是说,卡罗尔认为,人们欣赏恐怖不是因为从中获得的独特的愉悦,而是因为它所给予的一定数量的愉悦。但尼尔认为这种观点不对,他认为,艺术性恐怖的经验本身就是愉悦的,恐怖的特殊吸引力基于它是恐怖性的这一事实。
问题是,面对艺术性恐怖,厌恶确实就是痛苦的或否定的情感,它本身如休谟所说的,是令人不快的和不适的,但是,一个反应(注意,这是一个反应,不是对同一个东西有两个反应)怎么可能同时是愉悦的又是痛苦的呢?尼尔的策略是,否认我们对恐怖的反应是痛苦的或令人不快的。他的论证是这样的,想象站在拇指大小的大头针上面的经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痛苦的、不快的。但是,当我们在描述一种情感诸如艺术性恐怖为痛苦的或不快的时候,我们试图获得什么呢?表面上看,我们不喜欢经验这样的情感,但是实际上,与这些情感如同情或恐惧伴随在一起的感觉和感知不是痛苦的或不快的,不是如走在大头针上面的感觉和感知那样。更准确地说,关于这些情感的不快的或痛苦的东西是它们的认知性部分,宽泛地讲,就是它们所涉及的信念或思想所关系到的东西是不快的,比如事物、状态或处境。同情或恐惧的情感不是痛苦的,相反他认为,在描述某种情感为“痛苦的”或“负面的”、“不愉快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在经验这种情感时而对之反应的某种情境,即是说,是这种情境而非情感是可怕的或不受欢迎的,我们把它比喻性地描述为痛苦的或不愉快的。因此,对于恐怖艺术的悖论的回答是,面对艺术性恐怖,情感反应自身并非痛苦的或不快的。我们为艺术性恐怖所吸引,是因为它提供了独特的愉悦,这是其他题材无法提供的。这样,就不存在什么悖论了。*Alex Neill,“On a Paradox of the Heart,” in Philosophical Studie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in the Analytic Tradition,Vol.65,No.1/2,(Feb.,1992),pp.53-65.
卡罗尔对尼尔的批评也作了回应。卡罗尔反驳了尼尔的例证,圣杯和哲学家的石头不是恐怖故事,因为它们涉及的是物体(objects)而非生命(beings),而卡罗尔的理论指向的是生命,不是物体。“超人的起源”是一个事件(event),事件也不是合适的艺术性恐怖的题材。一般来说,对上帝的追寻也不是艺术性恐怖的合适的对象,因为在西方文化中,上帝属于特殊范畴,可称为神秘的,因此需要特殊的反应。尼尔说,痛苦的和不快的是处境本身而非情感,卡罗尔举例反驳说,比如我为一个恶作剧所惊吓,情况似乎不能说是这种经验的客体即恶作剧是不愉快的,毋宁说是,我受惊了,身体状况是不舒服的感觉,我的荷尔蒙要逐渐调适到一个平衡的水平。关系到对恐怖性虚构的厌恶,比如胃搅动、恶心等,这些难道不是痛苦的、不舒服的、不快的感觉吗?这并非尼尔说的比喻性的痛苦,而是真实的不舒服感。*Noel Carroll,“A Paradox of the Heart:A Response to Alex Neill, ” in Philosophical Studie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in the Analytic Tradition,Vol.65,No.1/2(Feb.,1992),pp.67-74.
苏珊·费金(Susan L.Feagin)也对卡罗尔的观点提出异议,她认为,很多之于虚构的反应是感觉性(affects)的而非情感,即是某种状态(states),它无需认知性的部分,生理学或现象学界定其为“激动”(agitation)。卡罗尔说,我们是为魔鬼所恐惧(horrified),但是他没有说清楚这个“为(by)”的用法。魔鬼是那种引起了我害怕的东西。卡罗尔把魔鬼等同于思想内容或一套特质,导致问题更为混乱,因为如果一个魔鬼是某种思想内容或一套特质,那么似乎我们能够给予“为(by)”这个词常规的因果性的解释,即我们是为一套特质所害怕,这种观点就不可信了,因为一套特质不能是本体论上合适的危险的东西。费金的观点是,我们可能享受恐惧和厌恶的感觉性部分(feeling components),如肾上腺上升、刺激、颤抖、恶心等等。此外,在艺术性恐怖的观看中,我们能够获得元愉快(meta-pleasure)。首先,我们能够在操练我们的能力对这种作品作出反应的时候获得愉悦。这种情况下,某个人能够从这一事实中获得愉悦,即他害怕了或厌恶了,既然这么反应对于恐怖性虚构的作品是合适的。其次,从恐惧和厌恶的感觉性部分获得愉悦,这是一种不同的能力,操练它是一个成就。最后,我们能够基于这一事实而获得元愉快,即某个人在心智上是十分优越的,以至于他能够在这些东西上获得愉悦,他能够“成长”(grow)和“改变”(change)。否则,他就缺乏趣味的能力。*Susan L.Feagin,“Monsters,Disgust and Fascination,” inPhilosophical Studie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in the Analytic Tradition,Vol.65,No.1/2,(Feb.,1992),pp.75-84.
但卡罗尔发现费金的方案难以服人。费金的观点是,恐怖欣赏者是享受“吓怕了”(grossed-out)。但卡罗尔质疑,如果他们只是享受“吓怕了”,那么很难说,他们如何能够获得成就感(a feeling of accomplishment),即如何从“吓怕了”中获得愉悦呢?费金的第二个元愉快就如第一个元愉快,对人们来说是满足的虚假来源。类似地,最后一个元愉快,即费金说的,智力高超,能够享受“吓怕了”因而从中获得愉悦,对于恐怖欣赏者来说也是一个奇怪的愉悦来源,因为,假如这些人只是简单地享受“吓怕了”,其智力高超表现在何处呢?卡罗尔说,他以自己的经验也不信费金说的话,因为就像他这样的恐怖电影的冷淡的欣赏者,当魔鬼要出现的时候也感受到了要离开屏幕或合上书本的强烈的意图,这是一个真实的紧张的时刻。即是说,他有一种不舒服的厌恶感,虽然这种感受会为对立的情感,特别是基于魔鬼的违反范畴的迷人所克服。即是说,他感受到了不快,而非那么多重的愉悦。
另外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阅读恐怖小说的时候,我们害怕的是什么东西?卡罗尔认为,这个因果链条中的第一步是小说,更精确地说,是小说中的描绘。这些描绘,我们以诸如“吸血鬼”命名之,是我们的刺激物,它引导我们去产生某种思想或某种心理再现,这些产生了艺术性恐怖的情感。相关的心理再现的思想内容是为文本描述的命题性内容所推导出来的,这些命题性内容关系到恐怖性魔鬼的特质,这些提供了我们心理再现中的魔鬼的具体形象。即是说,“为魔鬼所害怕”,开始于真实的客体(real objects),即对魔鬼的描绘,它呈现给我们的一套特质,我们命名为“吸血鬼”。说我们为艺术中的吸血鬼所害怕,意思是,在我们情感反应的第一步,是特定特质的呈现,即是标签为“吸血鬼”的所指。这些描述然后提供了命题性的内容,从之我们的心理再现被推导出来,我们容纳这些再现作为未明言的思想(unasserted thoughts),这就产生了艺术性恐怖。也可以说,我们是害怕恐怖小说中的相关描述,既然这是在我们身上激起了相关思想的东西。*Noel Carroll, “Disgust or Fascination:A Response to Susan Feagin, ” in Philosophical Studie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in the Analytic Tradition,Vol.65,No,1/2(Feb.,1992),pp.85-90.卡罗尔的反驳是合理的,因为文字诉诸心理再现,魔鬼的心理再现的形象就是吓人的。
恐怖小说在西方历史久远,恐怖电影的兴起则直接向西方美学界提出了恐怖艺术的悖论问题。基于篇幅局限,本文仅清理了当代西方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几种观点,特别是西方学者就这一问题的诸多争论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路径的多维性,值得中国学界关注。恐怖艺术的悖论关系到艺术品的特质、欣赏者的认知情感反应、心理事实的再界定等诸多层面的问题,关系到审美心理学、艺术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总结西方学界的讨论,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不同风格类型的艺术品具有不同的特质,恐怖性愉悦所指的对象是不同的;二、不同欣赏者的认知情感反应不同,从恐怖性作品中所获得的愉悦的特质和程度是有差异性,需要经心理学实验的调查和认定;三、如果艺术性恐怖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否需要和如何获得理论的普遍性就是一个问题;四、本文所论及的补偿论、享受论、控制论等观点,相互之间有冲突也有互补,都从某个层面、某个角度解释了恐怖艺术的悖论现象。综合性的解决,应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诸多学科的知识资源,面对具体的艺术作品,提出新的理论假设。
(责任编辑:陆晓芳)
收稿日期:2016-03-12
作者简介:章辉,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楚天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7-009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