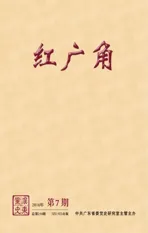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大论战
2016-03-18刘仁
刘 仁
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大论战
刘 仁
【摘 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大论战对我国学术界影响重大。毛泽东十分关注这场逻辑学大论战,对于此次论战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与毛泽东对建国初期《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以及胡风文艺思想等论战中的态度相比,他在逻辑学论战中的态度是比较恰当的。通过对比,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历史经验:在学术论争中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学术创新,实现国家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学术论争,并把学术问题政治化。
【关键词】毛泽东;逻辑学大论战;历史启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逻辑学界关于逻辑学问题的讨论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次重大的学术盛事。毛泽东特别爱看研讨哲学问题的文章,十分关注逻辑学研究的进展,密切关注那场关于逻辑学的讨论。对于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论战的态度与他对其他论战的态度的比较研究,是目前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论战研究中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因此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文试图分析毛泽东对此次逻辑学论战的态度并通过对比他对其他论战的态度,探讨领导人的态度对学术争鸣的影响。
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逻辑学大论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逻辑学的大论战,这次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及其要达到的目的,都直接受苏联逻辑学界讨论的启发和制约。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的发表,传统形式逻辑在新中国逐步得以“解禁”。与此同时,苏联斯特罗果维契所著《逻辑》一书及苏联《哲学问题》杂志所发表的《逻辑问题讨论总结》一文,成为新中国逻辑学界的指导性文献。①余品华:《十年建设时期哲学若干学科建设的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苏联斯特罗果维契所著《逻辑》的主要观点是“高低说”,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
1953年马特在《新建设》上发表《论逻辑思想的初步规律》,拉开了关于逻辑学问题争论的序幕。1956年党逐步确立起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精神,为逻辑学问题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和很好的学术氛围。1956年周谷城在《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的《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把讨论推向了高潮。该文提出了新的见解:“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②周谷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7页。王方名在1957年连续发表了5篇文章,也不同意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的“高低说”,而是更明确地指出形式逻辑是独立具体科学,把形式逻辑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了。逻辑学界学术讨论氛围十分浓厚,很多学者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有赞成周谷城、王方名观点的,也有质疑他们观点的。1961年春,王忍之在《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论形式逻辑的对象与作用》一文。文章发表后引发了新一轮争论,当时一些逻辑学家在不同程度上不赞同王忍之的主张。这次讨论的阵地先由《新建设》、《哲学研究》等学术刊物转向《光明日报》等全国性大报,进而转向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党刊《红旗》杂志。①张燕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论争的反思》,《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与此同时,逻辑学文章的发表和著作的出版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关于逻辑学问题的争论,对于我国逻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肯定了传统形式逻辑在我国的地位,达到了学术讨论的目的。这次论战历时近十年,使辩证逻辑由哲学向逻辑科学前进了一大步,奠定了辩证逻辑在中国实现科学化的理论基础,在中国现代逻辑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毛泽东对逻辑学大论战的态度和做法
毛泽东十分支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逻辑学论争。早在1920 年,毛泽东已经熟悉逻辑学的基本内容,并谈到逻辑学上的错误。他于1920 年11 月26 日给罗学瓒的信中说到逻辑学的错误是以情论事,时间上以一时概永久,空间上以偏概全,以主观概客观等。并认为后三者错误他可以避免,“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66页。尽管当时毛泽东对逻辑学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准确,但它说明毛泽东已经开始关注逻辑学的问题。
在早年和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很爱读有关逻辑学方面的著作,到了五六十年代他仍然对逻辑学著作很感兴趣,并且十分关心逻辑学问题的学术讨论。建国后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流行于我国,毛泽东也读了该书。对当时学界关于形式逻辑地位的看法,毛泽东没有发表意见,自称“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③唐昕:《毛泽东与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周谷城一文发表后,他主张的“主从说”在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大的争论。毛泽东看了他的文章后,表示赞赏其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见解。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同志开会。会上谈到批评要有说服力时,毛泽东说:《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④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1页。公开赞许了周谷城《形式逻辑与辨证法》一文。在上海的毛泽东还特意找来周谷城同他谈论逻辑学问题。在谈论中,毛泽东多次鼓励他积极写文表达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提到王方名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三篇文章与周谷城观点相同,他还提议将王方名的文章编成小册子《论形式逻辑问题》于1957年10月出版。1958年6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周谷城专门就形式逻辑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再一次聚谈逻辑问题。
毛泽东于1957年3月15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康生、陆定一、胡绳、陈伯达、田家英讨论逻辑问题。他“反复强调了两个观点,一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高级之分;一是形式逻辑是普遍适用的,没有阶级性。”①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7页、128页、137页、136页。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等,说周谷城文章的观点“比较对”。②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邀集逻辑学界、哲学家人士到中南海颐年堂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在会上,他说:周、王二人的观点很相近,可以作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说到“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③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7页、128页、137页、136页。问题还在争论,出于对学者的尊重以及对学术自由讨论的维护,在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的观点。
到了60年代,毛泽东学习和研究逻辑学的兴趣十分浓厚,还一直关注对逻辑学问题的讨论。基本上60年代出版的逻辑学著作,毛泽东篇篇都看过。1961年夏天,毛泽东在庐山同李达的谈话中说:“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可以是正确的。”④唐昕:《毛泽东与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1965年10月8日上午,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朱波的《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一文也是研究逻辑学的。在谈话中,他也遗憾地表示党员们研究哲学没有研究逻辑学。1965年12月,《红旗》杂志第12期上刊登了朱波《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并且有自己的看法。1965年12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当有人提到朱波这篇文章时,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⑤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7页、128页、137页、136页。
毛泽东还十分关心逻辑学著作的出版和论文集的刊印。在他的关心和要求下,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逻辑组负担挑选逻辑专著的出版,由三联书店再版逻辑丛书11本。⑥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7页、128页、137页、136页。这些著作的出版,宣传和普及了有关逻辑学方面的知识,极大地推动了逻辑学的研究和发展。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学习逻辑知识、运用逻辑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出了“学点逻辑”的伟大号召。毛泽东说,“写文章要讲逻辑”⑦《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7页。,他甚至把这个作为一条“工作方法”而加以提倡。逻辑科学一度成为热门科学,学习逻辑一度成为全国性的一场运动。这场逻辑学大讨论推动了逻辑科学的普及和发展。
三、对毛泽东关于逻辑学大论战态度的评价
毛泽东对待这场逻辑学论战的态度是关注、支持与推动、不压制。这种态度是这场论战得以正常开展的重要原因。他很关注这次逻辑学论战,在会议上认真倾听与会学者的发言,并且阅读了很多关于这次论战的文章。他虽然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并不轻易地发表评价;而是鼓励学者发表观点,为学者提供争鸣的场所和机会,允许论战中有不同观点存在。在这场论战中,他尊重逻辑学争论,不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对比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以及胡风文艺思想等论战中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在逻辑论战中的态度是比较恰当的。
1950年12月随着电影《武训传》(孙瑜编导、赵丹主演)公映,国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武训传》及武训本人历史评价的大讨论。毛泽东观看《武训传》后,一直关注文艺界的这场讨论。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改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的这篇社论以最高权威的形式对电影《武训传》作出了裁决,名为讨论实际上是吹响了大批判的号令。《社论》开了建国后直接从政治上给文艺作品下结论的先河。“社论”发表后,讨论迅速由正常的学术争鸣演变为政治批判,武训以及《武训传》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写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为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批判作了总结。
1954年9月,李希凡和蓝翎在《山东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批评文章。看了他们的文章后,毛泽东于1954年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要求,在政治上要团结俞平伯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①《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135页。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一场针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以及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大批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了。中共中央在1955年1月、3月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公开向社会表明中共中央直接发动并领导了这场思想批判运动。毛泽东由对胡适的批判,引发了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
1953年9月梁漱溟在政协会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了质疑。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而梁漱溟认为毛泽东误会了他,与毛泽东发生激烈的争吵,结果梁漱溟被迫长期在家闭门思过。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评主要发生于1953年9月16日至18日,根据《毛泽东选集》记载,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有15个方面,并公开在政协会议上批判他。他的文化保守主义被当做“封建思想”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由于这些政治因素,他的文化哲学与乡村建设运动被全盘否决。
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是围绕他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及“现实主义”展开的。胡风问题的实质是因为他的文艺观与毛泽东的文艺观相抵触,所以他的文艺思想遭到了批判。1952年3月文艺界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文艺整风运动。1953年1月29日,由全国文协在文化部小礼堂召开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人民日报》于1955年5月13日、24日,6月10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随后把这些材料汇编成书。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了序言和二十多条按语,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达到了高潮。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最后演变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集团案”。
相比之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的论战是当时党内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成功典范。这场关于逻辑学的大论战之所以能够成功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逻辑学的研究,与毛泽东本人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毛泽东对逻辑学论战的支持不是“政治干预”,是与他本人对逻辑学感兴趣以及对逻辑学科学性质的正确认识直接相关的。毛泽东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界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论战很感兴趣。他立足于逻辑学界的前沿,密切关注逻辑学争论的研究与发展成果,搜集大量有关逻辑学知识的资料,并通过认真的阅读和研究,力求对逻辑学论战的过程有全面的了解。在论战过程中,他多次召开会议,与金岳霖、周谷城、王方名等学者共同探讨逻辑学方面的问题。他发表过一些有利于讨论的见解,但是对于逻辑学具体问题的争论则采取谦虚谨慎的态度。毛泽东坚持逻辑学论战应该是在学者有关学术问题上自由讨论和争论中进行,而不应该将其变成一场政治批判。正是因为他这一科学的态度,使得当时逻辑学问题的争论能够生动活泼地进行,也使得参加讨论的各方学者能够毫无顾忌地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从而推动了逻辑学的研究与发展。
毛泽东对待逻辑学论战的态度是科学、合理的。他用科学态度对待学术界的争鸣,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学术问题应该以学术讨论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在学术论战中鼓励学术创新,他多次组织座谈会的目的在于鼓励学术上的自我创新。这也是我们从那场学术论争中获得的有益启示之一。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奇生vs黄道炫:研究中共党史必须具有全球史眼光
王奇生:研究中共革命,现在国内学界面临一个普遍性的困境是,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太密切,而研究者懂俄语的不多。研究中共,首先要关注其与苏联的关系,而且要把整个国际共运史搞清楚。国内尽管有“国际共运史”这个学科,但研究还有很大欠缺。要从纯学术意义上研究国际共运史,哪些是国际共运中的共同性,哪些是“中国特色”,哪些是受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一些基本东西都还不大清楚。
王奇生:我们不仅对苏联的历史研究不够,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历史了解也不够。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历史也有深入的了解,才能看出相互关联与异同。以“世界革命”为诉求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全球性的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必须具有全球史的眼光。
最近数年来,一批历史学者开始重视中共党史研究。目前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1949年以前)大体可分为两大范式:一是“革命史视野下的中共党史”,一是“民国史视野下的中共党史”。后者尽量将中共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将革命的主体、客体以及局外各方放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中探讨,以再现其复杂多元而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
王奇生:我个人感兴趣的,既不是纯事实层面的东西,也不是纯抽象层面的东西,而是那些确实能够运用到行动之中的机制。我们的研究,不只是简单地把一个过程讲清楚,还要看看背后的机制是怎么形成的,又是如何运作的。
黄道炫:机制的运作,机制的落实,这是最有趣的。我们做历史研究要借鉴社会学、政治学,在视野上,这些学科确实比历史学胜出一筹。
王奇生:我们做历史研究老是强调求真,其实求解也同样重要。“真”是唯一的,“解”可能是多元的。并非所有发生过的历史都能弄清楚,很多情况下只能做出一个推断。推断就可能见仁见智了。当我们把事实弄清楚之后,事实后面的机制还有必要深入探讨。
黄道炫:首先是求真,不能因为无法复原完全的真就放弃努力。总的来说,现在要研究的事实太多,判断其意义关键要看背后有没有大的关怀。纯粹的事实研究也有它的意义,但是有限。人生苦短,我们的研究还是应该有选择。这就涉及所谓碎片化问题。
王奇生:所谓碎片化就是就事论事,没有打通它的内在联系。
黄道炫:如果探讨的背后有更大的眼光,任何小问题都是大问题。如果只是就事论事谈一个基础性的事实,再大的事情也不能说不是碎片。
(摘自澎湃新闻网,内容有删减)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07-0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