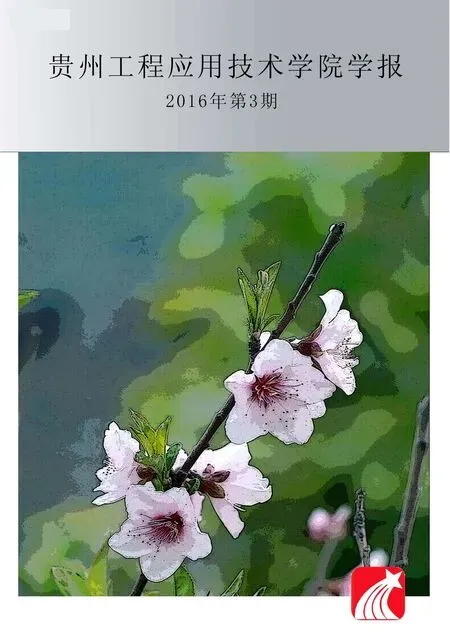平鳌苗族杉木种植的传统知识及其利用
2016-03-18耿中耀
耿中耀,杜 薇
平鳌苗族杉木种植的传统知识及其利用
耿中耀1a,杜薇1b
(1. 贵州民族大学 a.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b.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黔东南州锦屏县平鳌苗族在杉木采种、育苗、移栽、林粮间种、采伐、礼仪中保留着杉木种植的传统知识,蕴含着对杉木生物特性的准确把握和巧妙利用,是当地生态系统与民族文化长期互动的结晶。在我国民族地区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践中,应该正确认识本土技术体系的价值。
平鳌;杉树;传统知识
中国贵州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苗族侗族居民,自明末清初以来,长期进行杉木种植和利用。在数百年的林业经营中,不仅形成、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民间契约——锦屏文书,而且还运用传统知识造林、营林和护林。他们对杉木进行可持续的开发保护,使木材贸易长期繁盛,生态环境良好保持,较好地处理了生态环境维护和经济建设的矛盾,为今天清水江地区的生态建设提供了宝贵借鉴。黔东南州锦屏县平鳌苗族在杉木采种、育苗、移栽、林粮间种、采伐、人生礼仪中展现的传统生态文化正是该地区杉木种植的传统知识及利用的缩影,调查、记录、发掘和研究平鳌苗寨林农在杉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传统知识的运用,对我国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区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平鳌苗寨的自然与社会情况
黔东南州锦屏县平略镇平鳌寨,位于清水江南岸,东与三板溪相临,西与河口乡文斗村相望,南与岩寨、中仰、九佑村相接,北与原中寨村、陡寨村,平秋镇相接,距离锦屏县城90分钟车程。平鳌寨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边缘向湘西丘陵过渡地带,海拔860米,四面环山,地势险峻,南面是海拔965米的满天星大山,北面是三板溪水电站坝边的鸡冠坡,东面是锁口山,西面是去文斗的关山口。寨内两侧为田,中有一条长岭坡,山形酷似一条大鱼,当地老人称之“鳌鱼”,故名平鳌。光绪年间《黎平府志》载“(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八月······平鳌、文斗、苗光、苗馁等寨生苗皆纳粮附籍”[1]这是平鳌苗寨在历史典籍中留下的较早记载。平鳌苗寨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在调查点查阅到《姜氏家谱》手抄本一份,其中姜文德写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的序言中记载:“洪武五年(1372年),(姜)承德公见平鳌一带山清水秀,不愿归里,因而宗室于兹。”①现平鳌苗寨262户1230人中,姜姓为大姓,占全寨人口的85%,杨姓占24%,付姓仅有3户占1%。
历史上,平鳌苗族囿于地势偏僻、语言不通,疏于与外界交流,“木材采运活动”[2]未开始之前,曾很长一段时期被划为“生苗地带”,直到清代初期开辟“苗疆”,才以占据便利交通和盛产优质木材的有利条件参与到木材贸易中,生计方式、社会组织与文化也相应逐步改变。到今天,平鳌苗族仍然以林、农混合的生计方式为主,林业主要栽培杉木,混合培育松、桐、竹等;农业主要种植水稻,兼种玉米、红薯、大豆、小米等,传统经济主要来源于林业、养殖业。
平鳌占地面积25869亩,其中有稻田571.5亩,耕地1900.8亩,荒山440亩,现有林地19095亩,森林覆盖率高达72.8%。平鳌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1月平均气温4.6°C,7月平均气温25.9°C;一年中,有330天以上日均气温在0°C以上,300天无霜期,年均降水量1326.2毫米。冬无严寒,夏无盛暑,雨量充沛,水热同季。这些气候条件都较为适应杉木的生长。此外,平鳌拥有海拔高、坡度适中、土壤有机质积累多、光照充足等能直接影响杉木长势、材质、胸径的各项有利生态因子,使其所产木材更具有耐腐性、干后不裂、木质细腻轻软、纹理笔直、宜加工等特点。因此,平鳌苗寨被誉为锦屏的“杉木之乡”。
“豆鸡”,是平鳌苗语中杉树的发音。在平鳌,村民的生产生活紧紧围绕杉木这一物种展开,护理杉木之余,将砍伐回来的条木修理成材,出售、建房或做成工具、家具等。在实践中,平鳌苗族把对杉木的认识加以发挥,用到极限,杉树的每个部分都有所用:树干做家具、房屋,树枝当柴,树叶当农肥,树皮用来覆盖房屋。平鳌苗族在生产生活中不断认知杉木的生物特性,不断尝试,在反复的经验积累过程中构建了一套与杉木相关的传统知识。
二、平鳌苗族杉木种植的传统知识及利用
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别名沙木,是我国南方特有的传统用材树种。贵州省黔东南三江(清水江、都柳江、融江)流域地处我国杉木最佳种源区,又是杉木原产地和中心产区之一,杉木栽培历史悠久。平鳌苗族所培育的杉木,根据其材质和色泽分为红杉、白杉两种。红杉坚实多油,又称“油杉”,白杉则松软、纹理鲜明。清光绪版《黎平府志》记载杉“有赤、白两种,赤杉实而多油,白杉松浮而干燥,有斑纹如雉尾者谓之野雉斑,入土不腐,作槽不生白蚁。黎郡遍山皆杉,约栽植二三十年可作屋材,五六十年可作棺具”。红杉、白杉都有主根不明显,须根、侧根发达,穿透力弱的特点,若处于雾多风少、温暖湿润、土壤排水良好等环境中则长势更佳。平鳌苗族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数百年的人工营林中,不断认识杉木的特性和影响杉木生长的因素,从育苗到砍伐积累了一套完备的本土技术体系。下文根据平鳌苗族在杉木种植过程中的生产环节,分别从育苗、移栽、林粮间种、砍伐4个方面来考察其中所蕴含的相关传统知识。
1.育苗中的传统知识
杉木种子成熟时间会受海拔、坡向、坡位、光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清水江流域,杉木果实一般于11月上中旬成熟。平鳌苗族将采摘时间选定于“霜降前后”,认为此时种子最饱满。选择采种的母树有一系列严苛的标准。必须符合树龄在20-30年之间,长势旺盛;生长于向阳坡,孤林木;稀疏林中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等条件。采种时,直接砍下结实、果球大的枝桠,将果球取下后晒干或阴干,待鳞片张口后捶打取出种子即可。留足播种幼苗的数量之后,剩下的可以出售。
杉树的育苗工作较为繁杂,从每年春耕之时开始准备,具体内容可分以下3部分:第一,选定育苗场地。育苗场地的选择较为考究,限制条件较多,必须是杂木丛生的荒地,且土壤肥沃、背风,向东或东北方有“半天日照”的“山腰”台地,这样的选址更为符合杉木幼苗的生物特性需求。这也与笔者实地调研的直观感受一致。调研期间,只要是晴天,村寨周边的“山腰”早上均有雾霭笼罩,将近中午浓雾散开之后才有太阳照射,造成向阳坡地的苗场具备了适宜的光照、水分和湿度。另外,土质硬、有积水、当风处菜地和已经连续几年育苗的地段都不能使用。第二,整理育苗场地。平鳌苗族遵循“三挖三烧”三个步骤整理场地,先将杂草杂树砍倒、晒干焚烧,深挖拍碎土块并整理干净;再浇上粪尿,铺上一层干树枝再次焚烧,再翻挖;待冰雪将土里的虫子冻死,疏松土质之后,再铺上树枝杂草焚烧,再翻挖。此后使用石灰和杀虫剂等对土壤进行消毒和杀虫,最后对场地进行再施肥,肥料一般以农家肥为主,近年来也开始结合过磷酸钙使用。第三,做苗床。苗床一般宽1米左右,高0.25米左右,步道0.5米左右。
杉木播种时间,平鳌苗族一般选在清明前后。每亩播种5-7.5公斤,种子需拌上草木灰播入苗床后用草覆盖。幼苗5-6月出土,此后进行数次施肥、除草和间苗,施肥先淡后浓,以氮肥为主,入冬前最后一次施草木灰肥,使幼苗木质化,便于过冬,除草坚持“除早、除小、除了”原则,最后一次间苗间距为2-3寸。此后两年,仍要定期看护,待第三年长到高30-40公分,即可移栽。
1953年以前,平鳌苗寨杉木育苗均为自用,少数农户拿出去销售,调剂给无苗林农。徐晓光教授考证:“那时(清朝)每到春天,锦屏平略、王寨等地,每逢市场(当地人称‘赶场’)均有杉木出售。”[3]1953年后,平鳌苗寨经历了农业合作社形式的国营育苗、“公分制”育苗、合同形式育苗等,1985年以“山分山、树分树”方法实行林地承包到户之后,恢复林农自行育苗。尽管平鳌苗族育苗的组织形式几经变更,但在育苗技术上仍然延续传统育苗方法,即使在国营育苗时期,国家也只对其苗圃的规模和幼苗数量进行管理,并没有改变传统育苗技术。正如我国地方性知识研究专家杨庭硕教授在访谈中所说:“看似怪诞的植杉办法,其实有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这一点是现代社会也可以继续利用的本土知识和技术。”[4]
2.杉木栽种中的传统知识
平鳌苗族载杉有“七刀八火冬腊挖,来年入春栽嫩杉”之说,即在农历七月时,在选好的荒山或采伐完毕的林地上,用刀砍杂草,清理土地,农历八月时,用火焚烧,待到冬月、腊月进行开垦翻挖。次年春,拍碎土块,去掉杂草杂树,即可挖坑种植杉树。种植杉树时,平鳌苗族非常重视土壤的肥沃程度。当某些山场出现因杉木砍伐土壤被雨水冲走的情况时,村民便会去土地肥沃的地方,一篓一篓背土到山场,以保证杉木的生长。笔者在访谈中也得知“背土种树”这种情况常有发生。“背土种树”与侗族“堆土植杉”的方法略有差异,但二者都要进行整理土地的技术操作,都是为了达到清除地表微生物和提供营养的效果,其目的就是要给杉树防病、治病,同时增加年均集材量,提高经济收益。
平鳌苗族根据雨季来临时间和气温的变化,确定每年的种植时间,一般在3月,超过3月就不能种杉。植杉苗时,让杉苗主根直立居于土坑中央,侧根的四周留出空间,填土到一半时用手轻提杉苗,使根更加舒展,然后将土填至根茎位置,用脚轻踩,松紧适宜。最后,在斜坡上方距离树苗五六寸的空地上,插一块巴掌大小的“护林牌”,防止山上的石头滚下来压伤幼苗。这一技术细节也是立足于对当地生态环境特征的深刻了解。杉木种下后,当年及次年的5-6月、8-9月各除杂草杂树一次,第三、四年每年再除草2次之后即可成林。从第五年开始,不再除草,但仍然需要护理。他们奉行“一年种树长期管理”的原则,长期管理的内容包括清理杂树杂草、除萌培蔸等。杉木长到十四五年之后,进行一次间伐,原则是“砍大留小,砍密留稀,砍病留好”,20年左右成林后即可全砍。
3.“林粮间种”中的传统知识
平鳌苗族将杉苗移栽后,通常会在幼苗间套种粮食作物,即林粮间种。从当地收集的林业契约来看,“栽杉种栗”的内容多次出现,可以推知在该区域长期通行着“林粮间种”的生产方式,利用杉木的生长期种植粮食作物维持生计。从访谈中得知,间种的粮食作物除小米外,还可以选择玉米、大豆、饭豆等作物;时间一般为2年,第一年主要种植小米、玉米,第二年种植豆类作物。
平鳌苗族之所以进行“林粮间种”,大体有以下3个解释:其一,正如上文中提到平鳌杉木为浅根型,无明显主根,侧根和须根发达,因此,在杉木未成林之前,林间仍有“空白土地”可以利用,而平鳌林多地少,加之杉木成林周期长,林农需要充分利用这一片土地提供粮食,另外,作物的枝桠正好为杉苗挡住强烈的阳光,增加成活率;其二,“林粮间种”可以为杉木松土,这是多数学者的观念,笔者实地调研资料也证实了这个观点。在套种粮食作物时,其根深入到土中,等粮食收割完,埋在土里的根就会腐烂,从而形成通道,保证土壤的透气性,就地堆放的作物秸秆腐烂后提高了土地的养分,同时套种的粮食召来的蚯蚓等也可疏松土地,利于杉苗的生长;其三、粮食作物吸引来的各种鸟类,能够抑制危害杉树生长的害虫的滋生,有助于形成良性的生态系统。由此来看,“林粮间种”是平鳌乃至整个清水江流域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生态智慧的体现,也是当地居民在生产生活中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产物。
4.采伐中的传统知识
平鳌苗族一般不随意砍伐杉木,在繁荣的木材交易时期有严格的碑文和契约作为习惯法规约着村民,如“六禁碑”、“护林防火公约”等明文规定禁止乱砍滥伐,“在这种契约习惯法的作用下,林业经济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5]
如今,杉木采伐则由寨老、村委和林业站共同管理,村民采伐之前需要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内容包括砍伐地点、砍伐数量、砍伐缘由等,然后村委会对其申请进行审核,审核内容主要有以下6项:子女读高中、大学者优先批;重大病灾者优先批;建房者优先批;不违反计生政策者优先批;从没乱砍者优先批;去年砍过的今年不批。从上述审核内容中可以看出,平鳌苗族非常重视教育,从而将“子女读高中、大学者”列为第一审核内容,也可看出平鳌苗族在时代的变迁过程中,逐步调整自身传统文化,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加入“不违反计生政策者”等与国家法律相关的内容。村委会邀请寨老共同商议评估,若村委会与寨老协商通过则递交林业站,林业站通过则批示砍伐,不能通过则等待下一年继续申请。获得批示砍伐的村民,还需要缴纳相应的保证金,待砍伐后的林地再次种上杉木之后才能退还。
实地访谈中,村民提到的关于采伐的具体操作细节如下:砍伐时候选择上坡方向(朝向山头一方)先砍,至2/3处,树的重心便向上倾,随后在树的下方(朝向山脚一方)略高原先伐口2-3寸处砍几斧头,用绳子往上一拉,杉木即往上方倒。这样砍倒的杉木树尖朝上、蔸(根)朝下,便于木头下山,如遇树干倾斜或树枝大部分向外的杉木,需要边拉边砍,此时必须要两人或多人合作。杉木砍倒后随即剥皮、打枝,枝不打完,留尖端部分扯水(吸收水分),这样杉木宜干。砍伐时间以夏至-秋分时为最好,此时易剥皮,树身表面不生霉。
三、平鳌苗族传统民俗中杉木传统知识的运用
平鳌苗寨是一个以家族和宗族构建的村落社会,当地村民尤其重视家族繁荣、人丁兴旺,在平时的祈佑中,繁衍生命和祈求平安被看成一项重要的活动。而杉木在这一文化事项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在搭建“子生桥”、种植“十八杉”、“打保符”等当地传统民俗活动中的运用。
平鳌人如果想要孩子,就会请阴阳师搭建“子生桥”。“子生桥”的位置一般选在田头地边或溪流之上,搭建子生桥必须使用杉树,且杉树需要长势好,至少有5-6颗从根处发出的杉木枝条方可使用,其寓意为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十八杉”则是在新生儿出生之后,由家人为其种植一片杉树,孩子长到18岁时,杉木也刚好成材,女孩出嫁可作为嫁妆,男孩则可建房娶媳妇。
每年正月“天保日”这天,全寨要进行一次所有人参与的“打保符”仪式,为期3天,每家出钱15元,从“先生”那里得到1块红布,戴在手或脚上,再象征性的抓一把米回家煮熟全家人吃,认为可护佑家人四季平安,1天之内,寨子5个位置——东、西、南、北、中分别挂上5面旗(旗上写着保佑全村人平安的字符),每一面旗都需要一颗高大的树作为桩,早上升旗,晚上降下后挂上马灯,这颗桩必须是杉树,且挂过旗的杉木若用来建猪圈、鸡圈等,认为能六畜兴旺。
平鳌苗族从生到死都在与杉树互动,正如他们认为“人是从树中来,死后又要回到树中去”。多数村民在生前就为自己准备棺木,他们对杉木精挑细选,制作过程细致入微,如材料上要求必须是整块木头、不能拼接,数量上要求上下为单数,两侧为整数,上下各3块,两侧2块,两头2块,总共10块等。平鳌每个家族、宗祠都有公共坟地,由后人种植一片主要为杉树、松树等常青树种的坟地林,将其视为圣地精心呵护,这种植树护树的观念对村民的生态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维护村寨生态环境也有重要的作用。[6]
平鳌苗族在砍伐杉木之前有一项祭祀仪式,砍伐者先请阴阳师算好日子,于前一天带上香纸去山场进行开山祭祀,祭祀者需一边烧纸点香一边祈求山神允许杉木被砍走,同时请求不要给采伐者带来厄运。第二天早晨,采伐工带斧头、柴刀、丁牛②、拉绳等工具进山,出门忌不吉利的语言。根据平鳌人“雨大不砍伐,风大不进山”的说法,砍树需要避开有大风或大雨的恶劣天气。此外,砍伐的整个过程都非常小心,忌大的响声,避免惊动睡觉的山神,将丁牛钉在树上的时候,也用鞋底进行隔音,怕太大声惊动山神,从而带来厄运。笔者在访谈中有村民提到有伐木工因砍树声音太大惊动山神而被倒下的杉木活活打死的事例。平鳌苗族之所以产生上述与杉木砍伐有关的仪式和禁忌,笔者认为除了砍伐杉木这项工作具有危险性之外,也由于杉树在平鳌人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砍树意味着一个较长的生产周期的结束,因此,他们用仪式来表示出对杉木“死亡”的尊重。并且把杉木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相连接,用文化较好地整合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6]
终上所述,在地方性知识理论视野下,平鳌苗族关于杉树种植的传统知识技术体系能够传承至今,正是得益于当地社会文化的塑造和辅助。对于这一有价值的本土技术体系要科学认识,重视蕴藏在传统知识中的对当地生态环境特征的深度了解、认知、规避和利用。在建设生态文明“地球村”的时代,从事生态建设与维护要避免简单地将特定区域的本土知识搬到不适合的生态背景下机械恢复和利用,而是应该正确认识各民族传统知识中本土技术体系和独特民俗的价值,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立足全国生态维护与建设的大视野,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注释:
①《姜氏家谱》,姜泽材手抄本。
②丁牛:一种砍树时候使用的铁制工具,三角形状,一头比较锋利用于钉进砍倒的树木里,另外一头绑上两根绳子,由两个人拖住绳子就可将木材拖住。
[1](清)俞渭修,陈瑜.黎平府志·武备志(卷5下,三十七)[O].光绪十八年黎平府志局刻本.
[2]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9.
[3]徐晓光.清水江流域传统林业“生态补偿”的实践与经验[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66-71.
[4]杨庭硕,孙庆忠.生态人类学与本土生态知识研究——杨庭硕教授访谈录[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5-23.
[5]徐晓光.“清水江文书”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启示[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16(3):105-113.
[6]杨庭硕.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23-29.
[7]姚瑶,赵富伟,谢镇国,等.黔东南苗族对杉木林的传统经营、利用和保护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623-629.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the Utilization of Pingao Miao Nationality’s Planting of Fir
GENG Zhong-yao,DU Wei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25,China)
The Miao people of Pingao in Jinping county,Qiandongnan have kept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planting fir in the process of seed collecting,seeding,transplanting,inter-planting of trees and grain,felling and the manners,which contains the accurate seizure and adept utilization of fir’s biological nature.And it is the long-term resul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ecological system and national culture.For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minority regions,we should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indigenous technology system.
Pingao;Fir;Traditional Knowledge
C95-05
A
2096-0239(2016)03-0108-05
(责编:谭本龙责校:明茂修)
2016-02-11
贵州省教育厅重点项目“锦屏文书村寨原地保护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1ZD005。
耿中耀(1989-),男,贵州毕节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人类学。杜薇(1973-),女,贵州铜仁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