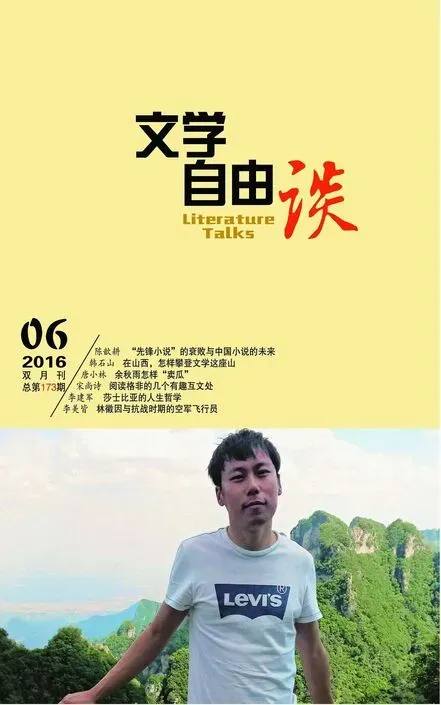莎士比亚的人生哲学
2016-03-16李建军
□李建军
莎士比亚的人生哲学
□李建军
戏剧以直观而生动的方式展示人生世相。每一个戏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每一部有深度的戏剧作品,也必然表现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说:“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一个缩影。”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强调说:“书里没有人生的认识,这种书是没用的,因为书所能教训吾人者除了生活的艺术还有什么呢?”马修·阿诺德则告诉人们:“文学的功用不只在娱乐众人,它最后的目标是人类生活的评衡。文学给于我们生命的安慰与同情,指导我们如何能与人生融洽。”丹纳也在《艺术哲学》里说:“一切对待人生的重要观点都有价值。几千年来,多多少少的民族都努力表现这些观点。凡是历史所暴露的,都由艺术加以概括。”一部有价值的戏剧和文学著作,应该对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理念产生积极的影响,否则,就很难说它是一部具有完整价值的作品。
人生哲学,观其大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理性的、低调的,一种是非理性的、高调的;前者是积极的和健全的,后者是消极的和病态的;前者是合乎人性和道德律则的自然主义的生活哲学,后者是悖乎人性和道德律则的反自然的生活哲学。
健全的人生哲学意味着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权力和金钱,对待一切有可能扭曲人性的异化力量。与此相反,病态的生活哲学则追求那些虚妄的价值,例如权力和金钱,崇拜那些不值得崇拜的人和事物。
就人生哲学看,莎士比亚的作品昭示着这样的生活原则:人必须有成熟的理性意识,必须以理性来制约人的欲望,不能放任自己的非理性的贪婪和攫取的冲动,更不能以毁灭一切的方式,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真实而可靠的生活,不应该是云端里飘渺的幻景,而是在大地上的现实事务,是与那些朴素的事物关联在一起的。他试图说服人们认同和接受低调的自然主义的生活态度。
也就是说,尽管他的戏剧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但是,莎士比亚却从来就不单为了“好看”和“好玩”而写作。他将戏剧当作反思历史和探索人生的伟大手段。他之所以显得伟大和让人敬仰,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关注那些与人生相关的重要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和庄严的回答,正像柳无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莎士比亚的光荣永久存在着,因为他懂得人生,人生的微奥;他的作品犹如一个灿烂的宝石圆顶,里边照映着各色的人生及情感。”(柳无忌:《西洋文学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第211页)
莎士比亚的戏剧与汤显祖的戏曲所表现的人生哲学,有着很大的相契之处,甚至可以说,基本属于同一价值谱系。汤显祖将人的“情”和“欲”分开来,高扬“情”的旗帜,拧紧“欲”的阀门,认为过度膨胀的欲望只会给生活带来灾难;而莎士比亚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只不过,他更强调“理性”的作用。
在《哈姆莱特》的第四幕第四场,哈姆莱特尖锐地批评了那种放纵欲望、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生!上帝造下我们来,使我们能够这样高谈阔论,瞻前顾后,当然要我们利用他所赋与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和灵明的理智,不让它们白白废掉。”(《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01页)第三幕第二场,哈姆莱特在赞扬霍拉旭的时候,还说过这样一段话:“自从我能够辨别是非、察择贤愚以后,你就是我灵魂里选中的一个人,因为你虽然经历一切的颠沛,却不曾受到一点伤害,命运的虐待和恩宠,你都是受之泰然;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得那么适当,命运不能把他玩弄于指掌之间,那样的人是有福的。”(《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第69-70页)这是哈姆莱特的肺腑之言,也是莎士比亚的生活观念。有的批评家就认为:“以理智控制情欲是理解莎氏伦理观念的钥匙。”(张泗洋、徐斌、张晓阳:《莎士比亚引论》(下),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第189页)当然,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精神的影响,莎士比亚的人生哲学,比汤显祖的人生哲学,显然要复杂得多,所涉及的方面,也更加宽阔和广泛。
在我看来,莎士比亚的生活哲学,可以用“理性而低调的自然主义”来概括。哈兹里特说:“阅读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会喜欢帝王。”(威廉·哈兹里特:《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顾钧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同样,所有将历史悲剧和人生悲剧看透的人,几乎全都认同理性而低调的自然主义人生哲学。
朴素的自然主义,原本就是一种英国气质。如果说,法国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民族,德国是一个理性主义的民族,那么,英国就是一个自然主义的民族,就像勃兰兑斯所说的那样,英国气质的本源,“即生气勃勃的自然主义”(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英国的自然主义》,第四分册,徐式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
人生哲学范畴的自然主义是谦卑的,它没有那种野心勃勃地战胜一切的妄念;相反,它承认人的能力和生命的有限性。就像约翰逊博士在《展望死亡》中深刻揭示的那样:“懂得生命短暂的道理,在克制我们喜怒哀乐的同时,也会使我们心中的谋算有所收敛。即使是所向披靡的天才人物和最勤勉不懈的人士,也无法将自身的力量拓展到一定范围之外。强王霸主在心中狂妄地谋划征服世界的伟业,鸿儒大师则荒唐地奢望自己能通晓所有门类的学问;这两类人最终都发现自己所企及的显赫高度是人类绝无可能达到的,他们雄心万丈,痴妄地想着自己能摘下一项殊荣,殊不知天上的神早已颁下法谕,令凡人毕其一生也无法能够得这样的殊荣,他们因此失去许多使自己有用于世、幸福于世的机会。”(塞缪尔·约翰逊:《饥渴的想象:约翰逊散文作品选》,叶丽贤译,三联书店,2015年,第19页)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叙事来看,约翰逊博士所概括的人生哲学,无疑也是莎士比亚所赞同和乐意接受的。
是的,低调的人生哲学,符合英国人的精神“习俗”。在那本著名的《英国特色》中,爱默生曾如此谈论英国人的“习俗”:“浮夸永远是令人讨厌的。他们在衣着和仪态上却走上了低格调的极端。他们避免虚饰,径直进入事物的心里。他们憎恨言不及义、多愁善感和高谈阔论,他们使用一种处心积虑的平易。甚至他们的花花公子布雷美尔也以衣着简朴为特点。他们在公事方面以没有戏剧性的东西而自豪,在私事方面以简明和中肯而骄傲。”(爱默生:《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下),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第911页)这种追求朴素和自然的文化“习俗”,不只培养英国人对植物和动物的兴趣和喜爱,也不只是培养了他们对大海的热爱,还培养了他们求真的思维习惯和自然的生活态度。
莎士比亚常常通过对自然的描写,象征性地表达自己的生活哲学。例如,在《暴风雨》和《冬天的故事》等故事中,他就宣达着一种摆脱了功利主义缠绕的自然而又充满诗意的生活情调。在《暴风雨》中,爱丽儿这样唱道:
蜂儿吮啜的地方,我也在那儿吮啜;
在一朵莲香花的冠中我躺着休息;
我安然睡去,当夜枭开始它的呜咽。
骑在蝙蝠背上我快活地飞舞翩翩,
快活地快活地追随着逝去的夏天;
快活地快活地我要如今
向垂在枝头的花底安身。
在《冬天的故事》里,潘狄塔与王子弗罗利泽的爱情受到国王的阻挠。潘狄塔并不想趋炎附势,她明白爱情和尊严的关系,也清楚地知道,在同一个太阳下生活,人们之间是平等的,而生活的意义,也不因地位的差异而有什么不同。所以,她对震怒的国王波力克希尼斯和自己所爱的人说:
虽然一切都完了,我却并不恐惧。不止一次我想要对他明白说:同一的太阳照着他的宫殿,也不曾避过了我们的草屋;日光是一视同仁的。殿下,请您去吧;我对您说过会有什么结果的。请您留心着您自己的地位;我现在已经梦醒,就别再扮什么女王了。让我一路挤着羊奶,一路哀泣吧。
对潘狄塔来讲,能在太阳的平等的照拂下生活,就可以心安理得,就应该觉得幸福和有尊严,就无须在有权力的人面前自惭形秽。这里体现的,其实就是一种朴素的自然主义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哲学。
很多时候,那些失去了国王地位和最高权力的人,往往会在巨大的绝望和痛苦中,认识到低调的寻常生活的意义。《理查二世》中的理查王被赶下国王宝座之后,大发感慨:
国王现在应该怎么办?他必须屈服吗?国王就屈服吧。他必须被人废黜吗?国王就逆来顺受吧。他必须失去国王的名义吗?凭着上帝的名义,让它去吧。我愿意把我的珍宝换一串祈祷的念珠,把我的豪华的宫殿换一所隐居的茅庵,把我的富丽的袍服换一件贫民的布衣,把我的雕刻的酒杯换一只粗劣的木盏,把我的王节换一根游方僧的手杖,把我的人民换一对圣徒的雕像,把我的广大的王国换一座小小的坟墓,一座小小的小小的坟墓,一座荒僻的坟墓……
理查二世本来就是一个残忍的暴君,所以,他的悲惨下场,也许让人震惊,但并不让人同情。一个傲慢的暴君,纵然有可能在某一特殊的时刻,发出羡慕底层人的普通生活的感叹,但却不大可能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自然主义生活的意义。
比较起来,《亨利六世》中的亨利王对人生的认识,就完全不同了。他清楚地知道一个普通人的自然主义生活,有多么自在,有多么惬意。在与叛军战斗的间隙,在战事陷入困境甚至显露出败兆的时刻,他忧心忡忡,百感交集,便发了这样一通感慨:
……这场恶斗就形成两不相下的僵局。我在这土岗之上,暂且坐下来歇一会儿。上帝叫谁得胜,就让谁得胜吧!我的御妻玛格莱特和克列福将军都逼着我离开阵地,他们说只要我不在场,他们就有好运。我真宁愿死掉,如果这是符合上帝旨意的话。活在世上除了受苦受难,还有什么别的好处?上帝呵!我宁愿当一个庄稼汉,反倒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就像我现在这样,坐在山坡上,雕制一个精致的日晷,看着时光一分一秒地消逝。分秒积累为时,时积累为日,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一个人就过了一辈子。若是知道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就该把一生的岁月好好安排一下;多少时间用于畜牧,多少时间用于休息,多少时间用于沉思,多少时间用于嬉乐。还可以计算一下,母羊怀胎有多少日子,再过多少星期生下小羊,再过几年可以剪下羊毛。这样,一分、一时、一日、一月、一年地安安静静度过去,一直活到白发苍苍,然后悄悄地钻进坟墓。呀,这样的生活是多么令人神往呵!多么甜蜜!多么美妙!牧羊人坐在山楂树下,心旷神怡地看守着驯良的羊群,不比坐在绣花伞盖之下终日害怕人民起来造反的国王,更舒服得多吗?哦,真的,的确是舒服得多,要舒服一千倍。总而言之,我宁愿做个牧羊人,吃着家常的乳酪,喝着葫芦里的淡酒,睡在树荫底下,清清闲闲,无忧无虑,也不愿当那国王,他虽然吃的是山珍海味,喝的是玉液琼浆,盖的是锦衾绣被,可是担惊受怕,片刻不得安宁。
亨利六世虽然性格复杂,却并非十恶不赦的坏人和暴君,甚至算得上是一个温厚的国王。他缺乏玩弄权力的狡狯和野心,“天生反感野心和权力的搅扰,宁愿在无欲无求的闲散和冥想中度过自己的一生。”(《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第176页)所以,他的这段话,就具有足以打动人心的悲剧意味和积极性质,因而,也就与《雅典的泰门》中贵族泰门对金钱的诅咒一样,值得重视,颇堪玩味。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莎士比亚自己对权力的看法,也宣达着他的朴素而低调的生活哲学。
低调的自然主义生活方式,意味着人们可以轻轻松松地满足自己最基本的需求,例如,可以保障自己有好的睡眠和食欲。然而,绝对权力却是甜美睡眠的敌人。
古罗马的暴君卡利古拉最大的痛苦,就是失眠。他“每夜睡眠的连续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而且睡得不实,奇怪的梦境使他惊恐万状,比如有一次梦见一个海怪和他说话。他夜里大部分时间都睁开眼睛躺着,因此心情非常烦躁,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沿着长长的廊柱徘徊,一次又一次呼唤着黎明,盼望着它的来临。”(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83页)同样残暴的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也备受失眠的折磨:“他每次的睡眠时间很短,通常在午夜前醒来;因此有时他白天主持庭讯时也打瞌睡,律师有意提高嗓门才好不容易使他醒来。”(《罗马十二帝王传》,第213页)《亨利四世》(下篇)中的亨利王,显然也被失眠折磨着。他知道,睡眠对普通人更温情,对戴王冠的人很无情:
我的几千个最贫贱的人民正在这时候酣然熟睡!睡眠啊!柔和的睡眠啊!大自然的温情的保姆,我怎样惊吓了你,你才不愿再替我闭上我的眼皮,把我的感觉沉浸在忘河之中?为什么,睡眠,你宁愿栖身在烟熏的茅屋里,在不舒适的草荐上伸展你的肢体,让嗡嗡作声的蚊虫催着你入梦,却不愿偃息在香雾氤氲的王侯的深宫之中,在华贵的宝帐之下,让最甜美的乐声把你陶醉?啊,你冥漠的神灵!为什么你在污秽的床上和下贱的愚民同寝,却让国王的卧榻变成一个表盒子或是告变的警钟?在巍峨高耸惊心眩目的桅杆上,你不是会使年轻的水手闭住他的眼睛吗?当天风海浪做他的摇篮,那巨大的浪头被风卷上高高的云端,发出震耳欲聋的喧声,即使死神也会被它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啊,偏心的睡眠!你能够在那样惊险的时候,把你的安息给与一个风吹浪打的水手,可是在最宁静安谧的晚间,最温暖舒适的环境之中,你却不让一个国王享受你的厚惠吗?那么,幸福的卑贱者啊,安睡吧!戴王冠的头是不能安于他的枕席的。
显然,亨利四世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却不理解这现象背后的实质和真理。他不知道,缺乏制约的权力,帝王的窳败的德性,不仅会导致社会性的政治混乱,而且,也必然折磨着大权在握的最高统治者的神经,造成他们的精神焦虑和心理混乱,而失眠,实在不过是这种心理混乱的一种结果和表征而已。事实上,在这段话里,莎士比亚不仅揭示了人物的复杂而丰富的心理活动,而且还肯定了低调的自然主义生活态度和人生哲学。也就是说,一个最高统治者,倘若能卑己自牧,而不是高自标树,动辄要人家向他折腰下跪,或对他喊“万岁”,那么,他的良心就会安宁很多,睡眠这个“温情的保姆”,也会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他温情脉脉,眷顾有加。
关于睡眠,关于人生乐趣,关于权力和伟大,关于尊敬和荣耀,关于“煊赫的排场”,《亨利五世》中的亨利王,也有着深刻的体验,也有过深刻的思考,也发过深深的感慨:
做了国王,多少民间所享受的人生乐趣他就得放弃!而人君所享有的,有什么是平民百姓所享受不到的——只除了排场,只除了那众人前的排场?你又算是什么呢——你偶像似的排场?你比崇拜者忍受着更大的忧患,又是什么神明?你收到多少租金,又带来了多少进账?啊,排场,让我看一看你的价值是多少吧!你凭什么法宝叫人这样崇拜?除了地位、名衔、外表引起人们的敬畏与惶恐外——你还有些什么呢?你叫人惶恐,为什么反而不及那班诚惶诚恐的人来得快乐呢?你天天喝下肚去的,除了有毒的谄媚代替了纯洁的尊敬外,还有什么呢?啊,伟大的“伟大”呀,且等你病倒了,吩咐你那套排场来给你治病吧!你可认为那沸烫的发烧,会因为一大堆一味奉承的字眼而退去吗?凭着那打躬作揖,病痛就会霍然而愈吗?当你命令乞丐向你双膝跪下的时候,你能同时命令他把康健献给你吗?不,你妄自尊大的幻梦啊,你这样善于戏弄帝王的安眠。我这一个国王早已看破了你。我明白,无论帝王加冕的圣油、权杖和那金球,也无论那剑、那御杖、那皇冠、那金线织成和珍珠镶嵌的王袍、那加在帝号前头的长长一连串荣衔;无论他高倨的王位,或者是那煊赫尊荣,像声势浩大的潮浪泛滥了整个陆岸——不,不管这一切辉煌无比的排场,也不能让你睡在君王的床上,就像一个卑贱的奴隶那样睡得香甜。一个奴隶,塞饱了肚子,空着脑子,爬上床去——干了一天辛苦活儿,就再不看见那阴森森的、从地狱里产生的黑夜。他倒像是伺候太阳神的一个小厮,从日出到日落,只是在阳光里挥汗,到了晚上,就在乐园里睡个通宵;第二天天一亮,又一骨碌起身,赶着替太阳神把骏马套上了车;年年月月,他就干着这营生,直到进入了坟墓。像这样,一个奴隶,欠缺的就只是煊赫的排场,要不然,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远远地胜过了做一个皇帝。
这也是一段特别值得注意的台词。亨利五世是一个贤明、能干的国王,也是莎士比亚很喜欢的历史人物。在自己的剧本中,莎士比亚将他塑造成 “好人中的国王”,“并极力为他的所作所为辩护”(《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第162页)。正是由于莎士比亚将亨利五世当作人格健全的人物来写,所以,上引的这段长长的独白,就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詹言曲说,而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庄言正论。
在亨利五世看来,做国王的代价,就是放弃正常的人生乐趣。国王可以享受“排场”,但为此得付出“更大的忧患”。他可以让人们恐惧,却无法令自己快乐。他只会得到虚情假意的逢迎——“有毒的谄媚”,却很少收获真心实意的赞美——“纯洁的尊敬”。虚假的“伟大”不会治愈国王的疾病,不会慷慨地惠赠他健康。最可怕的是,“高倨的王位”和“煊赫尊荣”,反而会搅扰你的睡眠,使他无法“像一个卑贱的奴隶那样睡得香甜”。也就是说,一个奴隶,虽然没有国王的“排场”和“煊赫”,但却享受着那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幸福——甜蜜的睡眠和充实的生活。
低调而朴素的自然主义人生哲学,不仅意味着满足人们的最基本的需求,而且,还意味着亲近自然,并按照自然所暗示的原则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会不约而同地写到大地上的万物,写到草木、山水、月亮和太阳,写到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事象,例如,睡眠和食物。
在《南柯记》中,契玄禅师的生活,就离不开林泉、清风与明月:“老住西峰第几层,琉璃为殿月为灯。终年不语看如意,长守林泉亦未能。……无影树下,弄月嘲风。没缝塔中,安身立命。可以浮沤复水,明月归天。”(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32页)在《邯郸记》行将结束的时候,吕洞宾用“人世上行眠立盹”(《汤显祖集全编》(六),第3094页)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朴素而低调的生活,可以使人自如地进入睡眠,进入一种极为自在的生活状态;又用“好香”的“黄粱饭”,嘲笑和否定了卢生汲汲以求的“列鼎而食”的奢靡生活。
就像亨利五世一样,吕洞宾也将享受日常生活中的幸福,视为无权的底层人,尤其是求道之人的专利,而有权力者与势利之徒无与焉:“求道之人,草衣木食,露宿风餐,你做功臣的人怎生享用的?”(《汤显祖集全编》(六),第3088页)其实,对这类话的解读,不可拘囿于“道家”的“游仙”的范围。就像莎士比亚用贵族们的故事,表现了人类共同的经验一样,汤显祖也用仙人和禅师的思想,阐释了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生活哲学,肯定了一种低调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一切深刻的人生哲学,都具有低调和克制的特点。希腊人的生活哲学,也属于这种朴素的自然主义的类型。他们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放纵,而是克制。就像汉密尔顿所揭示的那样:“任何英语单词都无法表达希腊文sophrosuné一词的涵义,而它却是希腊人最为珍视的品性。尽管它常被译为克己、自制,但它却远超出这个义项。它正是对德尔斐两大神谕精神的界说:‘认识自己’和‘任何事都不要做过头’。傲慢与目空一切是希腊人最为憎恶的两种品性,sophrosuné则与之严格对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sophrosuné本身的含义是,承认潜存于人类共性中的那种持中的美德,限制放纵,规避无节制的冲动,服从和谐与平衡的内在法则。”(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曹博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然而,19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的后五十年和21世纪的最近十多年,人类的生活彻底背弃了 “和谐与平衡的内在法则”。种种极端主义的社会法则和原教旨主义的生活法则,控制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人们似乎更倾向于认同和接受那种征服一切、攫取一切的高调的人生哲学。
在大自然、时间和种种神圣的事物面前,我们表现出一种极其浅薄的傲慢和肆无忌惮的恣睢。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战无不胜。我们只追求形式上的成功和虚妄的荣耀。我们先是贪婪地攫取权力,后来就疯狂地攫取金钱。
不再有慷慨的给予和温柔的同情。残忍和冷酷成了一种心理习惯。对别人的不幸和痛苦我们视若无睹。骇人听闻的伤害,恐怖性质的破坏,在在可见。
生活完全失去了方向和目标。生活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尖端,但生活哲学和价值体系,却越来越低级,越来越混乱。
重读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也许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那种古老而又智慧的人生哲学。
是的,低调而理性的自然主义,实在就是最可靠的生活哲学和最有效的价值体系。
无论对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还是对21世纪的“新人类”,这样的sophrosuné,这种低调的自然主义,无疑仍然是伟大的人生哲学,仍然是我们必须服从的普遍法则。
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2016年10月16日,北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