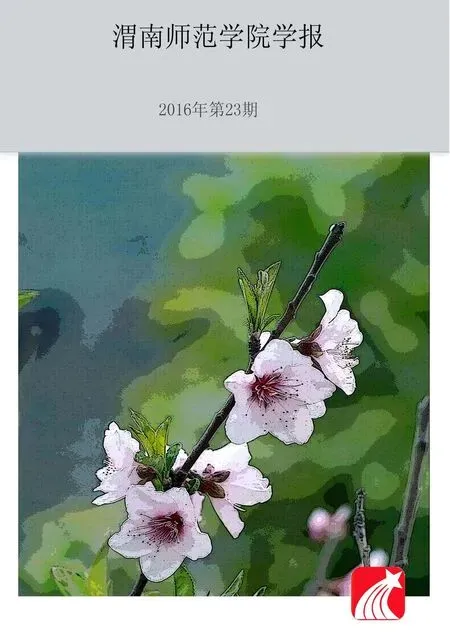渐进的总汇文学
——《雅典娜神殿》第116条断片解读
2016-03-16张世胜
张 世 胜
(西安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西安710128)
【语言文化与文学研究】
渐进的总汇文学
——《雅典娜神殿》第116条断片解读
张 世 胜
(西安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西安710128)
《雅典娜神殿》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文学批评杂志和多位浪漫主义文学家宣传文学纲领的媒体。其中的第116条断片 “渐进的总汇文学”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文献,它提出了“浪漫主义文学是渐进的总汇文学”这一文学观点,阐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和历史地位。文章对这一条断片进行逐句解读,探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意义。
《雅典娜神殿》;总汇文学;德国浪漫主义文学
一、《雅典娜神殿》简介
文学是一种过程,是整个社会思想的过滤器;文学也是一种推动力,一种反思手段。对文学的这种认识在如今很受重视,日益著名的《美艺术学苑》(Lyceum der schönen Künste)和《雅典娜神殿》(Athenäum)的诸多断片中处处都有体现。[1]239
18世纪末期,德国出现了数量繁多、各不相同的杂志。其中,施莱格尔兄弟的《雅典娜神殿》(1798—1800年)最为特别。这份杂志在当时只出版了3年就不得不停止,但在20世纪却重版了好几次;可见,这一杂志在20世纪获得了更大的认可和推崇。作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文学批评杂志,它在宣传浪漫主义文学纲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95年,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年)邀请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年)到耶拿去帮助完成文学杂志《时序》(Die Horen,也译为“季节女神”)、《缪斯年鉴》(Musen-Almanach)、《文学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的编辑工作。不久后,弟弟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年)也到了耶拿。兄弟俩在那里开始研读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费希特从1794年起就在耶拿大学讲授自己的唯心主义;他认为,人们可以借助于绝对自我的自由行动来消除外在世界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界限。这种哲学思想对施莱格尔兄弟等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很大影响。
由于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对《时序》杂志进行了批评,使得施莱格尔兄弟与席勒的关系破裂了。于是,他们积极地筹划自行编辑一份属于自己的杂志。就这样,《雅典娜神殿》问世了。杂志那个很有古典意味的名称源自古希腊的首都雅典及其保护神雅典娜,那是因为施莱格尔兄弟认为雅典象征着古典民主和政治自由。
该杂志的编者和主要撰稿人是施莱格尔兄弟:哥哥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和弟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其他作者有文学批评家、作家多罗特娅·施莱格尔(Dorothea Schlegel,1764—1839年,当时还不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妻子),作家、翻译家卡洛丽娜·施莱格尔(Caroline Schlegel,1763—1809年,当时还是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妻子),作家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年),语言学家、作家奥古斯特·费迪南德·伯恩哈迪(August Ferdinand Bernhardi,1769—1820年),诗人、作家索菲·蒂克(Sophie Tieck,1775—1833年,作家路德维希·蒂克的妹妹)、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5—1834年),哲学家、教育家许尔森(August Ludwig Hülsen,1765—1810年)以及瑞典外交家、德语诗人卡尔·古斯塔夫·布林克曼(Karl Gustav Brinckmann,1764—1847年)。由此可见,《雅典娜神殿》是诸多浪漫主义作家和理论家宣传其文学纲领的重要媒体。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是领导者,也是最具决定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写作者。
《雅典娜神殿》成了早期浪漫主义运动(包括耶拿浪漫主义和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据地,为浪漫主义的形成作出了很大贡献。1798到1800年间,《雅典娜神殿》每年出版一期,每期共两卷,一共出了六卷。除了施莱格尔兄弟作为编者和作者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作品外,还有其他好几个作者。早期浪漫主义作家的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文章就发表在这份杂志上,比如说诺瓦利斯的《花粉》和《夜颂》。各个作家之间的意见分歧也体现在该杂志内容及形式方面的多样性上。杂志出了三期即六卷后就停办了。施莱格尔兄弟自己出版杂志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要推动“协作哲学”(Symphilosophie),让诸多具有各种特性的人们相互补充相互“碰撞”,一起塑造出共同的哲思作品。最直接的原因是,施莱格尔兄弟想要摆脱其他编辑的指手画脚,将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不受干扰地传播给读者。
可惜的是,杂志并没有获得较大的影响。由于文章大多难以理解,而且都极具挑衅性,杂志很快就遭到了各种攻击。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在最后一期上发表了《论不理解》,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消除误解,因为很多读者觉得自己在文章了受到了嘲弄。《雅典娜神殿》停办3年之后,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于1803年推出了新的杂志《欧罗巴》,试图再续前缘。值得指出的是,德国的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学会自1991年起出版的年鉴也叫《雅典娜神殿》,而且刊载的也都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研究论文或者新发现的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
《雅典娜神殿》刊登的文章大多是断片。文学领域的断片概念有三种含义:已经完成、但因天灾(火灾、水涝、虫害、发霉)人祸(政局动荡、战争、移民、文化变迁)没能完整传世的作品,没有完成的作品(比如:斯特拉斯堡的《托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或者是作者有意选择的文学体裁。此处的断片指的是第三种含义,施莱格尔等人故意选择了断片,并将它改造成为一种文学体裁(Gattung)。
二、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的断片概念
弗·施莱格尔为浪漫主义的总汇文学和先验文学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他的《雅典娜神殿》断片作品一开始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出于“渐进的总汇文学”的考虑,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并没有企图为“断片”这种文学形式给出一个统一的、不可更改的定义。所以,他在《雅典娜神殿》第206条断片这样写道:“一条断片必须宛如一部小型的艺术作品,同周围的世界完全隔绝,而在自身中尽善尽美,就像一只刺猬一样。”[2]78这让人一方面联想起格言(Aphorismus)的完善性来,另一方面也让人重视起断片在形式上的矛盾性:“没有形式的形式。”[3]398
对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而言,断片是不能跟格言相互混淆的。格言以足以自洽、彻底封闭的方式传达意见,而断片决然不会满而自足。断片更多地想要激发其他的文学作品和智识之见,这一点跟施莱格尔兄弟的动机相吻合,他们就是要推动大家一起来协作哲思(symphilosophieren)。真知灼见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后天寻找出来的;也不具有普遍性或必然性,而是适应于某个情境,总是相对的。
在施莱格尔看来,断片概念甚至适用于小说理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必须是断片。相关的典型例作就有浪漫主义长篇小说诺瓦利斯的《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1800年完毕,1802年由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推出)和路德维希·蒂克的《弗朗茨·斯滕巴漫游记》(Franz Sternbalds Wanderungen,1798年出版)。而一些评论家认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本人的小说《卢琴德》(Lucinde,1799年出版)也属于没有完成的作品。
正因为这种特殊的体裁可以激励新的断片来继续填补旧的断片文学作品,断片的表现力就极为广泛,已经超越了语义学方面的潜在可能性。断片不仅标志着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也在哲学和诗学范畴内获得了重要性。后者当然对前者有所影响,再加上断片中的多种多样的反思形式,使得断片在不同的层面上来回移动。断片概念的矛盾性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们没有承认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都在文本内部。矛盾是早期浪漫主义有意追求的,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所有思想的暂时性;即使这些思想是以印刷形式,即完整定型的方式出现的,其暂时性或过渡性质仍然存在。
三、《雅典娜神殿》第116条断片逐句解读
《雅典娜神殿》中的第116条断片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文献。下面就试图对这条断片逐句进行解读(本条断片的译文参考了李伯杰[2] 71-72和聂军[4]26-27的译文):
(第一句)“浪漫主义文学是渐进的总汇文学。”
这一句是整个断片中最短的句子,也是最简明扼要的一句。后面句子的内容几乎都包含在内了,这句话更像是一个总结性的标题。接下来的句子相互交织,有的还相互矛盾。与古希腊传统逻辑——种加属差定义法(definitio fit per genus proximum et differentiam specificam,从普遍性即最近一级更高的概念和特殊性即区别与其它同级概念的特征两方面来定义一个概念)——相符合的是,后面的阐释分析都围绕着这句话来进行。
施莱格尔所理解的“浪漫主义文学”相当于当时的另一概念:“小说文学”(Roman-Poesie)(施莱格尔在《关于文学的谈话》中论述过这一点),所谓的“小说文学”并没有特指作为文学形式的小说,而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形式并不单一。多位学者认为,总汇文学作为一种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已经超越了小说的形式,而小说比较开放的形式和较大的活动余地最有可能满足渐进性的要求。[5]LII[6]164[7]29因此,作者在这里简明扼要地对浪漫主义文学做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让浪漫主义文学包含了他理解的范畴。
(第二句)“它〔浪漫主义文学〕的使命不仅仅是,将文学所有分隔开的形式重新统一起来,以及将文学与哲学和修辞学联系起来。”
浪漫主义文学的任务是,综合所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和文学类别,构成一种大的、融会贯通的文学形式。但是,这句话中的“重新统一”却让人有些懵懂。如果其前提不是在神话曾经存在过的“黄金时代”的话,那就不得不追问,文学的种种形式何时有过大一统呢?
此处,施莱格尔的说法与《研修文章》中的说法似有矛盾,他将绝对概念确定下来,远离了追求客观性的理想。在发表在《雅典娜神殿》第三期第一卷的《断想集》中第95条断片他这样写道:“所有古代人的古典诗歌都彼此相关,不可分割,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正确地看,所有古代人的古典诗歌只是一首诗,是惟一在其中诗艺术本身显现为完善的诗。从类似的方式来看,完善的文学中一切书籍都只是一部书。在这样一部永远在变化生成的书里,人性和文化教养的福音得以公诸于世。”[2]116
在统一各种文学形式这一点上,隐约出现了关于“总体艺术”的设想,尽管这个词后来在理查德·瓦格纳那里才出现,其思想在施莱格尔的“总汇文学”里就已经初显端倪了。
关于总体艺术,我们可以由此总结出两点倾向来。一种是叠加,就是把单个的艺术形式简单相加;另一种是综合,就是坚持认为各种文学形式有上下层次的区别,而总体艺术是指向无限的绝对形式。按照这种思想,浪漫主义文学既是总和,同时也是艺术的最高形式。[7]28这种核心思想在这一断片的最后一句中直接出现了:“比艺术更多,同时就是文学本身。”从浪漫主义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上的特点来看,它最接近“无限”;这类似于辞书的要旨,什么都要说,也要说“不可说”。
(第三句)“它〔浪漫主义文学〕的目的和任务就是,把诗歌和非韵体、创造性和批评、艺术文学和自然文学时而混合起来、时而融合起来,让文学变得富有生机和吸引力,让生活和社会具有诗意,把智慧诗意化,为艺术形式添加各种各样精致的教育材料,让艺术形式拥有足够多的教育材料,让幽默回荡在艺术形式中,使得艺术获得灵魂。”
在这里,哲学理论、文学和生活实践的巨大综合能力得到进一步阐述。浪漫主义文学的内涵得到了定义,因此应该扩大其影响,甚至对社会产生影响。这里也提到了文学批评的一种理想化形式,强调了文学批评的对话性质。施莱格尔可能是想到了涉及社会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把文学当作过程,当作从原则上讲永远不会终结的过程。
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成了民主的公众教育的基石,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消除18世纪时期由于新的读者群体的形成而产生的高雅艺术与庸俗艺术之间的鸿沟。[1]238
“幽默”可能是让·保罗(Jean Paul,1763—1825)所说的那种幽默,即并不局限于一些具有幽默性质的词句、是贯穿于整篇文章的幽默;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小校长武茨》和《关于滑稽的理论》。
(第四句)“它〔浪漫主义文学〕包括一切凡是诗意的事物、包含好些个体系的大艺术体系,甚至包括正在创作的孩子吹进质朴的歌声中的叹息和轻吻。”
“诗意的”在这里是指所有自身具有表现力的事物,既包括艺术的,也涵盖自然的、本能的。我们几乎可以认为,和第三句一样,这里也在阐述艺术文学和自然文学、意图和本能之间的综合。“正在创作的孩子”可能也有一个形而上的含义,即普普通通的人们。这种理解也还说得通。
“吹进质朴的歌声”可能意指口头性与文学性的多重矛盾含义,只有本身已经“死亡”的文字才可能重新获得口头性。由此,浪漫主义反讽就获得了生存地。
(第五句)“它〔浪漫主义文学〕可以消失在被表现的事物中,人们甚至可能认为,它的一切和唯一就是刻画出各种各样的诗意化的个体。但是,还没有一种文学形式可以完整地表达作者的精神:以至于一些原本也只想写一本小说的艺术家只是表现了他们自己。”
这里强调了浪漫主义想象的主体性,这与双重反思的形式相符合。双重反思一是指对世界进行反思,另外是指自我反思。
(第六句)“只有它〔浪漫主义文学〕和史诗一样,可以成为是整个周围世界的一面镜子和时代的画像。”
依照施莱格尔此前的《关于神话的演讲》和《研修文章》,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已经拥有了浪漫主义文学的这种能力。施莱格尔在这里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意义再次肯定,将它放到与史诗文学一样的地位上。浪漫主义文学的反讽功能以及它形式的自由性足以表现整个时代的特点。
(第七句)“但是,它〔浪漫主义文学〕也可以不带任何现实或理想的想法,乘着诗意反思的翅膀在被表现的事物和表现者之间飘浮,而且一直增加这种反思机会,从而形成无数的镜子。”
镜子的比喻在这里遭遇了物理学上的不可能性,不过这在施莱格尔那里不算罕见。承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意反思的翅膀”暗示了超越和运动。超越是指升到一定高度,而这种文学反思没有尽头,应当不断超越自身的界限,把自己当成观察对象。运动是指永不停止,一直来回“漂浮”。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文学被看成了一个自主行动、有所企图的主体。
正如第三句所说的那样,这种结合了“创造性和批评”的反思是一种“文学之文学”,浪漫主义反讽促成了“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之间的不停交替”。这种既针对表现内容、也针对表现过程不断进行的反思的源头就在苏格拉底的哲学及对话和费希特的知识学。超验哲学中,认识主体在自身找到了认识的根本原因;在施莱格尔看来,超验文学同样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文学的根源就在于文学自己,就在于人类思想中根本性的文学力量。由此,文学也具有了批判性。同样的,施莱格尔所追求的文学与哲学、艺术与科学的统一就达到了。
(第八句)“它〔浪漫主义文学〕有能力完成最高级、最全面的教育;不光从里向外,而且还可以从外向里进行教育。其方式就是,将所有部分为每个人以类似的方式加以组织,而实际上每个部分都是一个整体;通过这种方式,浪漫主义文学获得了新前景——一种无限增长的完美。”
这句话让人想到施莱格尔的《关于歌德的麦斯特》,他十分欣赏这部小说,认为它有许许多多的组成部分;而各个组成部分也都是均衡、完整的整体,就是说,在小说的大体系中,各部分都是“体系”[5]LXII。
这是一种类推的思想,即部分体现了整体。“无限增长的完美”可能是指超越神话之外的、无限的、渐进的“新神话”,这在《关于神话的演讲》中有过详细阐述。[3]265
很明显,施莱格尔设想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统一与无限并不冲突,在浪漫主义思想看来,二者应该相互结合。
(第九句)“浪漫主义文学在艺术中的位置相当于哲学中的智慧,生活中的社会、交往、友谊和爱情。”
这里再次肯定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地位,人的生活中离不开社会、交往、友情和爱情。哲学中的智慧在联系起不同现象的过程中创造出了相近的关系,同样,社会是不同阶层的统一体,而交往和友谊把截然不同的个体带到一起来了,爱情超越了不同性别之间的对立。
这里确定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创造和保持。
(第十到十三句)“别的创作方式带来完成了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彻底地得到分拆。浪漫主义文学还处于形成过程,这甚至就是它的本质,它一直处于形成过程,永远不会完成。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彻底挖掘它的含义,只有预言式的批评才敢于想要描述浪漫文学的理想:浪漫主义文学本就无限,正如它本就自由;只有预言式的批评才会承认,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法则就是:作家的任性不会容忍任何限制。”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和未完成性是由它的反思性质决定了。施莱格尔在《文学笔记》(Literarische Notizen)第207篇中描述了它与别的创作方式的区别:“古典文学在历史上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无效,同样的,莎士比亚的感伤文学也彻底宣布自己的无效。只有渐进的文学没有,就是说,它可能经常毁灭自己,但立刻又创造出自己来。”[8]289
对施莱格尔来说,浪漫主义文学作为总汇艺术的能力就来源于其高度的自我反思。由于自我反思的过程像永动机一样,没有结束的时候,所以,自我反思自有超越自身和不会终结的趋势。[7]29
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所坚信的意识的自由出现在“作家的任性”中,出现在没有法则的法则中。
(第十四句)“浪漫主义是唯一的不只是创作方式的创作方式,它同时就是写作艺术本身: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文学都是或者都应该是浪漫主义的。”
断片的最后一句采用了比较模糊的语言风格,特别是“在一定意义上”使得语气相对减弱了。它虽然要求所有写作艺术具有浪漫主义风格,但是这种要求已经非常谦和了,甚至与前文中的激情有些矛盾。《文学笔记》中是这样说的:“哲学文章不可能以纯粹的修辞结尾,必须由反讽来收尾。”[8]289
“像一只刺猬一样的”断片就这样收起了它的锋芒,它以有些挑衅的方式激发了反思的开始。
四、结语
始终伴随这一断片的印象是,概念以及想法一直在相互消解。很难在断片中找到贯穿始终的思想。反复出现的概念经常变换其语义,这就使得我们不可能把某个概念确定下来。
每个思想都只有很短的有效期,这可算是一直向前运动的“漂浮”精神的标志。反思精神想到达到的完美性永远不会停止,永远不会终结,发展的过程没有终点,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二者之间的互动一直持续下去。《文学笔记》这样说:“意义就是自我限制,就是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结果。”[8]289自我限制可能就体现在,必须要写出一些东西,有时还要印刷出来,因为人们只有在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有限之中借助于浪漫主义反讽让自己忘却一件事:把一切都说出、彻底的诉说是不可能的。《美艺术学苑》第48条断片中是这么说的:“反讽是矛盾存在的形式。所有既好又大的事物都是矛盾的。”[3]288简而言之:“反讽就是义务。”[8]481就这样,反讽成了联系有限与无限之间的根本态度。不管对施莱格尔还是对诺瓦利斯来说,混沌拥有一种与宇宙无限性相关的创造力。
但是,这一条断片给人的印象——特别是对没有思想准备的读者来说——却是,它是无序的大集成。我们可以由此看出,黑格尔对施莱格尔哲学的随意性乃至混乱无序性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施莱格尔的哲学中万事万物都相互关联,但却不注重体系性。
从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可以理解:早期浪漫主义出于总汇性的要求就只有选择断片这一文体了;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正是在这种微型的形式中衍生出在“绝对自我”[3]265中得到最佳体现的、对一统性(Totalität)的要求了。[7]20
《雅典娜神殿》第116条断片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文献,解读这条内涵丰富、思想驳杂的断片有利于了解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设想。如果一定要总结这一条断片的主要内容,我们就有必要再一次强调:浪漫主义文学是要成为一种过程,成为整个社会思想的过滤器;浪漫主义文学也是一种推动哲学思考和认识能力的力量,更是一种反思手段。
[1] Huyssen, Andreas. Nachwort. Republikanismus und ästhetische Revolution beim jungen Friedrich Schlegel[M]//Friedrich Schlegel. Kritische und theoretische Schriften. Stuttgart: Reclam 1997.
[2] 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M].李伯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 Schlegel, Friedrich. 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 Bd. 2: Charakteristiken und Kritiken I (1796-1801) [M]. Hg. von Hans Eichner. München, Paderborn, Wien: Schöningh, 1967.
[4] 杜瑞清,户思社,聂军,等.欧洲浪漫主义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5] Eichner, Hans. Einleitung[M]//Schlegel, Friedrich. 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 Bd. 2. Hg. v. Hans Eichner. München, Paderborn, Wien: Schönigh,1967.
[6] Pikulik, Lother. Frühromantik. EpocheWerkeWirkung[M]. München: Beck,2000.
[7] Kremer, Detlef. Prosa der Romantik[M]. Stuttgart, Weimar: Metzler,1997.
[8] Schlegel, Friedrich. Literarische Notizen 1797-1801[M]. Frankfurt a. M., Berlin, Wien: Ullstein, 1980.
【责任编辑 马 俊】
Progressive Universal Poe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Athenaeum’s Fragment 116
ZHANG Shi-sheng
(School of German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thenaeum is a journal of literary criticism for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and a platform through which Romantic literary critics publicize their principles. Athenaeum’s Fragment 116 on progressive universal poetry is an epoch-making document as it 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Romantic literature is progressive and universal”, thereby expounding the attributes and historical position of Romantic literature. This paper offers a sentence-by-sentence interpretation of Fragment 116 and 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intellectual significance of German Romantic literature.
Athenaeum; universal literature; German Romantic literature
I109
A
1009-5128(2016)23-0059-05
2016-08-20
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反讽(12JZ030);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项目:德国浪漫主义反讽研究(09XWA04)
张世胜(1971—),男,陕西西乡人,西安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德语文学及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