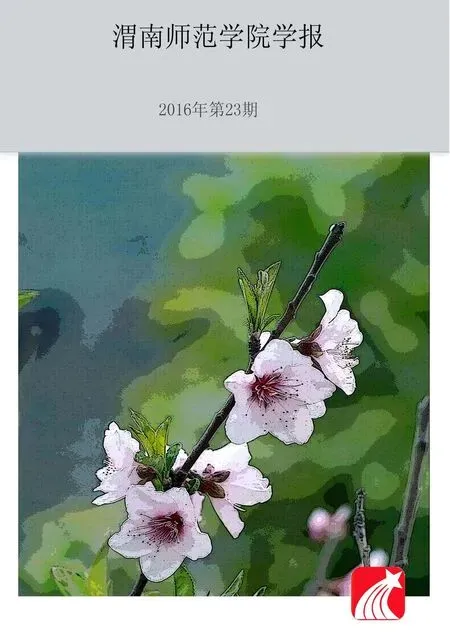印光法师母教思想论析
2016-03-16吴兴洲
吴 兴 洲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秦地文化研究】
印光法师母教思想论析
吴 兴 洲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印光法师是中国近代佛教发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精通佛法,熟谙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母教重于父教,母教乃天下太平之根本。这种观点,既张扬了女权,体现了佛教众生平等观,又突破了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思想偏重于父教的历史局限,凸显出儒、释融合的思想特色。
印光法师;母教;胎教;思想
所谓母教,乃是指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广义而言则泛指中国传统家庭婚育女性对居家成员及家族门风的培育和影响,它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教育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因为母亲是家庭生活的中心,贤良淑德的母亲之于子女、丈夫甚至其他家庭成员,不仅是血缘亲情关系的纽带,而且也肩负着和睦家庭关系、端正家族门风、兴盛家族事业、培育治国良才等重大的社会历史责任。
传统中国社会,尤其宋明以后,由于封建礼教的约束,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偏低,其家庭责任和社会贡献亦往往被忽视甚至有意贬低,但这并未妨碍女性发挥其独特的家庭和社会作用。“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俾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1]2因为社会本由男女二性构成,男权无论如何膨胀,均离不开女性阴柔之美的调节与粉饰。“男以强为贵,女以柔为美”[2]5,且“稽古兴王之君,必有贤明之后”[3]106。
自古及今,关于母教的记载和事例颇多,如太任教子、孟母三迁、岳飞刺字等不胜枚举。正是由于这些贤淑母亲的哺育、培养,才造就了我国古代历史上一大批圣哲英雄,他们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历史发展,而且也为后人树立了典范,留下了大量英雄史诗般的不朽壮举和历史遗迹,传之千古,泽被后世。是故古人云:“闺门乃圣贤出生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
一、传统母教思想
“母教”一词最早出自春秋末期思想家、孔门“宗圣”曾参。据《韩非子》一书记载,曾子为教子诚信之道,曾对因事以虚言欺瞒儿子的妻子告诫曰:“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4]174意为母亲若是欺骗了孩子,孩子便不再信任母亲,这不是教育孩子的好方法。曾参要求妻子在日常生活中对儿子善尽抚养之责,做到言出必行,重信守诺,不能以空言、戏言欺骗儿子,从而破坏了为母者的形象,达不到教养儿子的目的。
另据汉人韩婴所撰《韩诗外传》卷九的“贤母使子贤也”。明确指出孟子之贤系出孟母。正是因为有孟母这样贤良淑德的母亲,才培育出一代儒学大师、孔门“亚圣”孟子。同时在论及孟母教子时,韩婴又进一步揭示出孟母以胎教形式教育儿子的历史典故。“吾怀妊是子,席不止,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说明中国古代的母教,不仅强调孩子出生以后的道德教化,而且非常重视母亲孕期内对胎儿的教育。
西汉末期古文经学家、校雠学家刘向,则于《列女传·邹孟轲母》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孟母与孟子、贤母与贤才之间的生成与培育关系。“孟子之母,教化列分。处子择艺,使从大伦。子学不进,断机示焉。子遂成德,为当世冠。”表明只有贤母方能哺育出贤子。虽然此一时期“母”与“教”二字并未形成一个固定词汇,但后世学人遂以“母教”一词狭义地称谓并理解其为“母亲对于子女的教育”。当然,母教的主体也被限制在“贤良淑德”之母这一具体而微的范围内。于是,如何培养和造就具备“敬顺之道”和“慈惠和让”之德的贤母,便成为中国古代母教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之妹、曾与马续受命续写《汉书》的班昭亦曾言道:“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2]4寥寥数语,凸显出祖先遗泽和母亲对其一生成长的影响和培育。她称母亲为“母师”,明显带有母教的意涵,认为母亲乃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在其《女诫》一文中,班昭为女性的日常行为之道,罗列了三大基本素质和要求:“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一为 “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卑弱下人也。”二为 “晚寝早作,不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三为“操正色端,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而且班昭亦反复强调,只有“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2]5。
另在《妇行第四》篇中,班昭又为女性品德和素质的修养总结出四大要素,亦即古人所谓“四德”。“幽娴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摆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织,不好嬉笑,洁齐酒食,以供宾客,是谓妇功。”由内而外、由表及里,可谓全方位、立体式地打造中国古代的贤善之女和贤妻良母。而且班昭也特别强调:“此四者,女人之大节,而不可乏无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2]6此一认知,显然是在为君臣、父子、夫妇的封建名教秩序而服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但不容否认的是,班昭重视女教和贤母培养的超前意识,在此一时期无疑是绝无仅有的旷世之言。受历史时代原因的制约,班昭虽博学多才,胆识过人,敢为兄班超上书请命,并且被和帝视为和熹皇后邓绥和宫中贵人师表,亦曾参与政事,但她亦无力改变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父权至上的历史现实,只能在男权和女权之间寻求某种不平等的平衡。
关于女德的教育,东汉文学家蔡邕亦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在其所著《女训》一文中,他以修身为旨,借修容而喻,具体阐述了女性修德重在修心的道德意旨。“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则尘垢藏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咸知饰其面,不修其心,惑矣![2]14说明“蔡中郎”在女德教育方面,更加重视女性内在道德素质的培育和善心、善性的发扬光大,务求女子表里如一。
南北朝时期,颜之推于《颜氏家训》中记载了颇多母教正反两方面的事例。“王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为三千人将,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故能成其勋业。”[2]46意谓正是因为有“明哲妇人”王母的“严正”,才成就了大司马王僧辩的一世“勋业”。而春秋郑庄公子叔段,因得母宠,玩鲁不修,后叛郑出奔,导致身死。颜之推以为“共叔之死,母实为之”[2]47。
由此而观,表明中国传统的母教思想,并非泛泛地指称母亲对于子女的教育,更深刻地理解,应指贤母对贤子、贤女的培育,属正能量的体现。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指母亲对子女个人品性和道德素养的教化,形式上则有胎教、家教等,目标上则主要集中于对家国社会有用之才的培养。
显而易见,母教之所以为先贤所推崇,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2]5。而更重要的则在于“母师能以身教”,亦即在家庭生活中,母亲能够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塑造他们的人格、品性,成就他们的事业和人生。“在胎则禀母之气,幼时则观母之行,闻母之言,已熏陶于读书之前。及其读书,则措之躬行,而为贤人、善人故也。”[5]154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母亲是家庭生活的中心,母亲之于子女,不仅是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密切接触和悉心照抚,更重要的,她们还是子女感情慰藉、精神寄托的心灵家园。子女能否健康成长,家庭是否富足安康,国家能否和谐稳定,很大程度上均有赖于母教的积极有为和创造性贡献。所谓“君子嘉焉,编于母德”“慈母生孝子”“母贤则子亦贤”等,均是女性尤其母亲对中国传统家庭和社会所发挥的独特影响和作用。所以孙中三先生说:“天下的太平安危看女人,家庭的盛衰看母亲。”
作为中国近代佛教发展的代表性人物、净土法门第十三代祖师,印光法师的母教思想独具一格。一方面,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厚的精神营养,传承了儒家伦理思想和道德理念的基本观点,提倡家庭教育之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积极贡献,推崇母教,倡导教女,认为“自古圣贤,均资于贤母”[6]404。另一方面,他又站在一个佛教人士的立场,融佛于儒,援儒入佛,主张以善恶果报思想推进家庭教育,进而影响世道人心,阐发出儒、释融合的母教思想。“现今之世,欲世道人心转向,欲家庭儿女贤善,若不认真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则绝无希望矣。”[6]392所以法师强调,家庭教育中,母亲的角色重于父亲,母教重于父教。
二、母教乃天下太平之根本
传统中国家庭,由于血缘宗法制的长期影响以及父权家长制的制约,加之父母的责任与分工不同,“男正乎外,女正乎内”[3]103,所以男性在家庭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父亲对家庭和子女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明显大于母亲,父教重于母教。所谓“教妇初来,教儿婴孩”[1]9,“养不教,父之过”,“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7]7等,都是父权和父教在家庭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具体体现。而母亲的角色则有意被淡化,她们很大程度上处于从属和辅助性的地位,主要承担养儿育女,奉养公婆,和睦妯娌与姑嫂关系等家庭责任。不过由于母子之间天然的依存和血缘关系,怀胎十月,哺乳养育,因此传统中国家庭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母教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父导之以严,母摄之以慈,父以刚克,母以柔克”,“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1]7,并且亦肯定母教的先导性,“母仪先于父训,慈教严于义方”[3]108。但这种思想观点仅限于理论上的阐述和认可,以及“女教”经典著作对女性的自我勉励与内在教化,实践中则由于礼教的制约,所以封建时代乃至近现代中国社会,传统家庭依然把父教放在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首要位置。
但法师对此的认知却截然不同,他以佛家慈悲心和众生平等观为出发点,在父教与母教之间,突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父权至上、男权主导的男尊女卑旧习俗、旧观念,一切从人际生活的社会现实出发,在肯定父教作用的前提下,尤为重视并突出母教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人之幼时,专赖母教。父不能常在家,母则常不离子。母若贤惠,则所言所行,皆足为法。见闻已熟,心中已有常规,再加以常常训诲,则习以成性。”[8]45意思是说,由于母亲在怀胎十月时即与子女建立了深厚的血缘亲情关系,加之日常生活中相依相偎,相亲相伴,所以耳濡目染之间,子女无形中便秉受了母亲潜移默化的人格影响和道德熏陶,形成了早期的行为习惯和个人品性。其后,若是再加以常常训诲、督促,则母亲的道德仪范和贤良品性将固化为子女的个性特征。所以他说:“人之性情,资于母者独多。居胎间禀其气,幼时则习其仪。其母若贤,所生儿女,断不至于不屑。”[8]47正是基于此,以故法师认为,家庭教育的中心是女性,子女的成长、成才以及家庭成员间的和谐、和睦,必须仰赖女性尤其是母亲的独特作用,“世有贤母,方有贤子”[5]80,母教比父教更重要,母亲的社会责任比父亲更大。
近代历史上,由于西学东渐,西方男女平权思想进入中国,影响所及,学者认同者不在少数。诸如与法师持相近观点的尚有清末民初学人辜鸿铭。“中国人的婚姻……是一种社会婚姻,一种不建立在夫妇之间,而介于妇人同夫家之间的契约——在这个契约中,她不仅要对丈夫本人负责,还对他的家庭负有责任。通过家庭再到社会,维系社会或公民秩序。实际上,最终推及整个国家。……这种婚姻的公民观念,造成了家庭的稳固,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和公民秩序,乃至中国整个国家的稳固。”[9]92辜先生早年游学欧洲,学贯中西,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因而他崇尚女性,重视女性对家国民族以及社会的责任与贡献,有其必然性。不排除印光法师也同样受到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但更大程度上,法师是从现实生活的家庭关系出发,以佛教众生平等观为基础,肯定女性的社会影响与作用。当然这种认识,也是他对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状况的积极回应。“世乱极矣,人各望治,不知其本,望亦徒劳。其本所在,急宜知之。家庭母教,乃是贤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8]44
三、贤母必从贤女始
母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固然重要,相夫教子,敬老爱幼,“谦谦俭恭,思尽妇道”,但贤能的母亲却是由良好家庭教育下的女子成长而来。“以有贤女,方有贤妇贤母。”[6]1345母亲是否贤淑端庄,能否承担起子女教育和贤才培养的家庭与社会责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未嫁时的个人修养和受教育程度,亦即女子是否是一位贤淑之女。而贤女的养成则必须具备相应的家庭条件,即 “见贤思齐”、仁孝治家的家族门风[10]73,“威而有慈”的父母,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女子是否拥有一位“德纯而行笃”的贤善之母。因为法师认为:“无贤母,又何由而得贤子女?”[6]1188此一看法,表明在法师的认知视域里,贤女与贤母两者相生相伴,互为表里,她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由此达彼的生成关系,即“贤母必从贤女始”[6]404,“无贤女,则无贤妻、贤母”[5]154。所以在家庭教育尤其对子女的教育方面,印光法师尤为重视对女儿的教育和贤淑之女的培养。“教儿一事,关系极大,教女比教子更加要紧。以女若贤,在家则可令兄弟姊妹相观而善,出嫁则相夫教子有法,俾夫与儿女皆为贤善。”[11]302
这些观点,明显与被誉为“百代女师”的班昭和明末刘姓王节妇的女德思想有着继承或渊源关系。“曹大家”曾言:“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2]5王节妇亦云:“正家之道,礼谨于男女,养蒙之节,教始于饮食,幼而不教,长而失礼。在男犹可以尊师取友,以成其德。在女又何从择善诚身,而格其非耶?是以教女之道,犹甚于男,而正内之仪,宜先乎外也。”[3]105说明在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统治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班昭和王节妇两位巾帼也认为,虽然家庭教育中教男、教子重要,但教女亦不可偏废。所不同者,班昭以教男、教女两者并重,而王节妇和印光法师则以为教女比教子更重要。“教子为治天下之本,而教女为尤要。以无贤女,则无贤妻、贤母,因之亦无贤人矣。”[5]154
既然贤善之女的培养关系到家族门风的端正,社会风气的改善以至治国安邦人才的培养,那么在女子教育的方式、方法以及教育的内容方面,法师则给出了明确的建议。一方面,他主张对女子进行儒家伦常的教育,“初开知识,即为彼说做人之道理,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另一方面,他则强调对女子进行佛教“三世因果之罪福、六道轮回之转变”[5]63的传习,以求把女子塑造成明仁义、守礼节、知进退的贤妻良母。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对女子个性品德的培养,强调母亲在教育女儿时,一定要注意养成其“贤良淑德”的内在道德品质和“温婉端庄”的外在伦理行为,以及“柔顺贞静”的个人品性。因为“女子性柔和,则家道亦可和睦,所生儿女亦悉慈善柔和”[6]406,进而可造福家国社会。 俗语云“家和万事兴”,意即只有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知礼守节,才会有家族事业的兴旺发达。推而广之,“一家和而一国和,一国和而天下和矣”[3]67。反之,如果女子从小被溺爱娇惯,养成了刁蛮任性、自私自利、不分是非善恶的个人品性,若是嫁为人妇,“不但不能相夫教子,于义于道,且将诱子为非,教其作恶”。此等结果,无论是对一家一姓还是国家民族,都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法师强调,“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11]302。
显而易见,法师是把女子教育、贤女培养,上升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认为它是齐家治国之本,治国平天下之权,关系到家庭和谐、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纵观古今,国家废兴,未有不由于妇之贤否。”[3]58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礼教思想和男尊女卑的封建旧道德、旧秩序明显不同,反映了法师尊重女性、张扬女权,提倡妇女自由、解放的思想本质,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女权与母教理念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对此,辜鸿铭先生亦有相似的认知。“一个民族中的女性正是该民族的文明之花,是该文明国家的国家之花。”[9]81
四、母教第一是胎教
印光法师的母教思想,相较于传统的家教观,有继承又有发展,但其思想深处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那就是他非常重视贤善之母的培育和养成。既然贤母必由贤女始,贤女的培养关乎民生安乐,家国之治,于是在重视母教,突出贤女培养的基础上,法师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胎儿的教育。“母教第一是胎教”[8]44,胎儿的教育关系到贤女的培育和贤母的养成。很明显,法师是想借助中国传统的胎教形式,从根子出发,构筑一条由胎儿到贤女、贤女到贤母、再由贤母到贤女、贤子培养的通途大道,服务于家国民族。因为在中国古代,胎教作为传统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始终受到先贤的推崇和认可。“伊古圣母,从事胎教,钧陶于禀质之初,化育于未生之前,而必期其习与性成也。”[9]80所以,在法师的家庭教育尤其母教思想体系中,对胎儿的教育,不仅是贤子、贤才培养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贤女培育的所由之处、必然过程。
法师早年习儒,青年时期因病患而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所以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思想非常熟稔,他崇尚母教,强调教女,突出胎教的前导性作用和地位,既是对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的继承,也是对传统母教思想的创新与发展。“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1]7可见,传统的胎教之法主要着眼并侧重于规范和调节孕期母亲的外在环境和内在道德约束。对此,法师亦高度认同,并且强调孕妇在怀孕期间,“务必居心、动念、行事,唯诚唯谨,一举一动,不失于正。尤宜永断腥荤,日常念佛,令胎儿禀受母之正气,则其生时,必安乐无苦。所生儿女,必相貌端严,性情慈善,天姿聪明”[6]1187。因为法师以为,胎儿在母体中能够感受到孕妇言行、情绪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进而促使其生理和心理的发育,形成其人生最初的品德素质和人伦教养。这种认识,颇与中国传统胎教思想的基本理念相契合,也符合儒家一贯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的伦理要求。唯一不同者,是他将佛教的意旨引入了胎教的内容中。
由于法师重视胎教在贤女培育中的重要作用和前导性地位,所以他极力建议孕妇在孕期内必须严守礼法,践行妇德,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姿容仪范甚至饮食、起居等,务必给胎儿提供一个的亲善、和睦、友爱的家庭氛围和“孝仁礼义”的外部生存环境,使胎儿秉受母之贤良、正气,养成良好的自然天性,成长为有益家国民族的贤才。为此,法师谆谆告诫世人:“欲家门兴盛,子孙贤善,当以吾言为圭臬,则所求皆得矣。”[6]393当然,对于胎教的实践价值和社会效果,法师也旁征博引,以古论今,诚心予以礼赞,认为其与民生、社会、国家,倶是大功德、大贡献。“如周之三太,阴相其夫,胎教其子,皆女中之圣人,实开周家王业之基。”[11]304
总而言之,印光法师的母教思想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观,颇具特色。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受男尊女卑观念和封建礼教思想的束缚,女性往往被约束在家庭的牢笼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必须接受男权的奴役和控制,基本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人身自由,根本谈不上为社会发展、国家民族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而法师的母教思想,张扬女权、提倡教女、强调胎教,甚至认为教女比教子、母教比父教更重要,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母教乃“天下太平之根本”,在处处均体现了佛教的众生平等观,为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思想注入了活力,平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同时,在教女的内容方面,他一则主张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传承,二则强调佛教因缘果报思想的修习,由出世而入世,反映出其独具一格的儒、释融合思想特色和“人间佛教”学术风格。
[1] [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M].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
[2] 包东波.中国历代名人家训精粹[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3] [清]王相.女四书女孝经[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4] [战国]韩非.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 印光.印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 释印光.印光大师文钞[M]. 张育英,校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7] [春秋]左丘明.左传[M].武汉:崇文书局,2007.
[8] 释广定.印光大师全集[M].台北:佛教出版社,1991.
[9]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10]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 智随法师.灵岩遗旨[M].长沙:岳麓书社,2008.
【责任编辑 马 俊】
Master Yinguang’s Thoughts on Maternal Education
WU Xing-zhou
(School of Humanities,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Master Yinguang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in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development. He mastered Dharma, had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e advocated the maternal education but not the paternal education and he put forward that the maternal education is the basis of the world peace. Hence his idea praises women and spread the Buddhist equality among all living creatures, moreover, he made the breakthrough abou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family education focusing on paternal education, integrating the ideological features of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Master Yinguang; maternal education; prenatal education; thought
B946
A
1009-5128(2016)23-0014-05
2016-10-31
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印光大师佛学思想研究(12JK0228)
吴兴洲(1965—),男,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