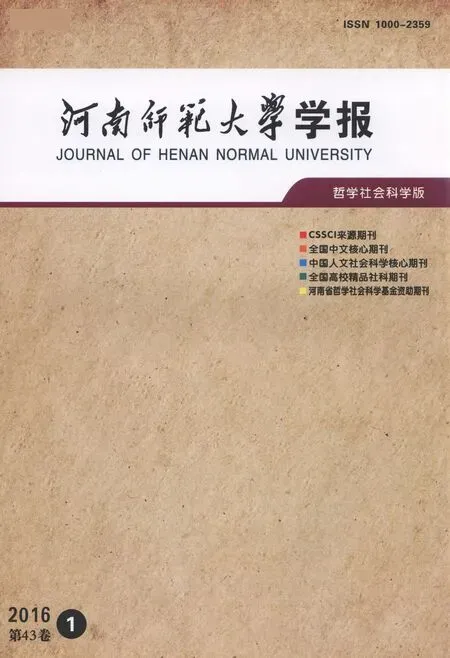皮尔士、索绪尔与符号学的元理论
2016-03-16尹德辉
尹 德 辉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皮尔士、索绪尔与符号学的元理论
尹 德 辉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符号学家们一般将索绪尔和皮尔士作为他们的元理论家。然而,尽管语言学家索绪尔和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通过他们的符号研究确实为符号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毕竟分属于不具可通约性的两个理论体系,他们各自的符号关系所处的时空范畴是不同的。皮尔士关注的是符号在任意的个体中、偶然性地形成中的历时性过程;索绪尔关注的则是符号在一定社会群体中,必然性的共时性关系。所以,在索绪尔和皮尔士之间做直接的类比是不可能的,符号学的元理论研究要超越索绪尔和皮尔士符号理论之间的差异性,在其产生的哲学渊源中去发现他们共同的理论统一性。
索绪尔;皮尔士;符号学;符号
陈炎先生在《文学艺术与语言符号的区别与联系》和《再论文学艺术的超符号性质——兼答唐小林先生》两篇文章中,以索绪尔静态语言学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作为判定符号的依据,指出从本质上说艺术作品不是符号。唐小林先生先后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索绪尔局限与朗格难题——论符号诗学推进的几个关键问题》和《文学艺术当然是符号:再论索绪尔的局限——兼与陈炎先生商榷》,对此提出质疑。但是,抛开在概念使用等方面的一些细节纠葛,可以发现两位学者在基本立场和观点上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位学者在关于符号判定的问题上产生了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呢?
任何一个独立的学科,都要有这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以之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可以受到该学科体系之外的各种批判,但其自身一定要有逻辑自洽性,这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学科的整体完善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众多学者如李幼蒸、赵毅衡等诸位先生的带动下,符号学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要看到,符号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还有待加强。比如,在作为符号学元理论的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之间,显然存在着不可兼容性,当然,这并不是说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理论本身有缺陷,也不是说它们不能成为符号学的理论基础,而是说,对符号学元理论和索绪尔、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之间存在的模糊不清之处,不能只存而不论地一直悬置在那里不去解决。符号学作为当下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尚需要在自己的学科元理论上做出严肃与更富开创性的基础性探索。这里,我拟就以下几个问题对之做一点突破性的尝试,也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第一,索绪尔、皮尔士和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符号学的关系。第二,在符号学中有关索绪尔和皮尔士的比较研究问题。第三,符号学的元理论和皮尔士的符号定义,以及对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是否存在缺陷等问题的不同意见。
一、索绪尔、皮尔士和符号学
在符号学的形成发展历史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主要有索绪尔、皮尔士、叶尔姆斯列夫、雅各布森、格雷玛斯、罗兰·巴特、艾柯、普罗普和洛特曼,等等,在他们之外,卡西尔、苏珊·朗格、梅洛·庞蒂、萨特、利奥塔等也有关于符号的哲学性论述。然而,很容易看到的是,在所有这些学者(派)之间并没有一个关于符号学的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特征。在1966-1969年间,符号学正式出现于欧洲,但和传统的人文学科如哲学、历史、文学等相比,新兴的符号学实际上更像是一个与传统学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跨学科研究范畴,一方面从语言学、文学、哲学等各个传统学科中吸收营养,另一方面又促进和反哺于各传统学科。应该看到,人文学科中的跨学科性是当代学术研究对西方18世纪以来学科分化现象的一种反拨,有利于消除人为的学科壁垒,开阔人文科学研究的学术视野,避免知识生产的局限和僵化。所以,即便是把符号学作为一门和传统学科相并行的学科,也要看到符号学和传统学科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历史区别,没有必要片面地求取和传统学科一样的学科地位。这是由符号学自身的学科历史和当代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作为一门新兴的理论学科,符号学的基础理论建设相对薄弱,所以,如果把符号学作为一门有生长潜力的学科,那么首先就要着重于符号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建设对一门学科来讲,固然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和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相比,还是属于次要一点的问题。对符号学来说,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当然是符号,就像“什么是哲学”对哲学、“什么是艺术”对艺术学一样,“什么是符号”就是符号学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苛求符号学者必须给“符号”下一个毫无异议的定义,而是说作为研究者要把和“什么是符号”有关的问题置于学科布局的优先地位,并且在研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对这些问题做出更深入一步的探讨。
在符号学出现之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各自提出了他们的符号理论,并提出了建立符号学的理论设想,尤其是皮尔士还为符号划分了详细的类别。因而,人们通常也把索绪尔和皮尔士看作是符号学家,把他们的符号理论作为符号学的两个重要理论来源。但是,在索绪尔和皮尔士的学术时代,符号学并不存在,而且他们本人的研究目标也并不是去构建一个作为学科的符号学。
索绪尔的确提出了一个有关符号学的理论设想,但对于设想中的语言学之外那个范围更大的符号学,索绪尔似乎并没有做出超出语言学之外的努力去实现这一设想。国内致力于索绪尔手稿研究的屠友祥先生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明白索绪尔提出‘符号学’构想的意图在于解决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他着眼于整体语言(la langue),而不是个体语言(la parole)。原因就是整体语言具有社会性,是一种约定的社会制度,语言符号的本质在其中充分地呈现。索绪尔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为了更好地阐述他心目中语言学明确的研究对象——整体语言,也为了巩固对整体语言社会性的看法,顺理成章地把目光投注到完全具有社会约定性的符号学上来。”[1]也就是说,索绪尔提出符号学的设想,目的并不是要离开他的语言学研究,开辟一个更大范围的符号学,而是为了更清晰地阐明自己的研究范围。索绪尔明确将其研究对象限定为以共时性为主轴的静态语言学,在静态语言学和动态(历史)语言学之间,索绪尔搁置了历时性而只关注共时性,“我选择继续探究静态语言学”[2]144,也就是人所熟知的以“能指”和“所指”关系为基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虽然对结构主义起到理论奠基作用的“能指”和“所指”关系,在其后的解构主义和各种后现代思潮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对索绪尔来说,这并不构成其语言学自身的理论缺陷,而只不过是他的一种主动选择。因此,不管在语言学和符号学之间存在怎样的从属关系,在一个语言学家的索绪尔和符号学家的索绪尔之间还是应该存在一些区别的,尤其是当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部分地撷取于后来的符号学中时。
如同索绪尔始终是一位语言学家一样,皮尔士也始终是一位哲学家。皮尔士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哲学和逻辑学,而不是符号学,阐述符号的目的是用来说明他的唯物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作为指号学的逻辑:指号论》一文中,皮尔士开篇就指出:“在一般意义上,逻辑,正如我已表明的那样,只是指号学的另一名字,是关于指号的类似必然的或形式的学说。”[3]276由于皮尔士的符号论可以上溯至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的唯名论,而其直接来源是洛克和康德的知识论,其中的符号(signs)相关于词语(words)和理念(ideas)[4]2-6,并且,皮尔士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把符号的范围扩展到词语之外,因此,这段话完全能被理解为:如果哲学、认识论都要依靠逻辑,那么在同等意义上也可以说,哲学、认识论都要依靠符号。皮尔士的符号论实际上就是他的哲学的一个基础部分,作为认识世界的方式,世界上的各种关系自然也就是各种符号之间的关系。显然,正是这个哲学基础决定了皮尔士会比索绪尔更受到符号学家们的青睐,近来的符号学界主流“越来越偏向皮尔士”而逐步舍弃索绪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逻辑学家的皮尔士,对符号的研究和论述最终是服务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把皮尔士看作是后来出现的符号学的启示者,这没有问题,但是在皮尔士的基本立场和以后的符号学家们的基本立场之间直接划等号,似乎还有待商榷。例如,担任皮尔士著作编辑出版项目(Peirce Edition Project)的顾问委员会主席T.L.Short先生,在他的《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一书前言中指出,皮尔士的符号理论“已经被一个跨学科的符号学家所组成的队伍,沿着与皮尔士本人的观点和目标相反的方向所继续了”[4]Ⅸ,“皮尔士强调的是探究(inquiry),是知识的无尽增长,是哲学而不是具体的科学(special sciences)”[4]Ⅺ。
不能否认索绪尔和皮尔士作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奠基者的地位,但是索绪尔和皮尔士的语言学和哲学并非天然就能成为符号学的基础理论,在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中,符号学家们至少应该努力达到与索绪尔和皮尔士相比肩的水平,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引述他们的某些局部性论述。索绪尔和皮尔士在语言学和哲学领域中取得的理论成就和声望,并不能被直接带入半个多世纪之后的符号学中去,反过来说,如果在当代的符号学研究中出现了问题,也不能直接归因于就是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皮尔士的哲学出了问题。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理论在他们各自的语言学和哲学中是能够自洽的,而在后来的符号学中产生的问题还是应该在符号学的自身中去解决。
二、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理论的统一性
在近年来国内的符号学研究中,往往过于强调索绪尔和皮尔士符号理论之间的区别,甚至厚此薄彼。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忽视了索绪尔和皮尔士各自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不能把握两者之间的统一性所致。在索绪尔和皮尔士的比较研究中,首先应该承认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是不同的,索绪尔和皮尔士所设想的符号学分属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符号”并不能直接成为两者间的理论交集。如果对索绪尔和皮尔士关于符号的论述进行比较研究,首先要做的是找到一个可以比较的基准,作为实现其可通约性的理论基础。这个基准本身既可以作为连接两个不同符号体系的理论枢纽,并且也不影响两个体系原本各自的独立性。实际上,研究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论理论的统一性要更有价值于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处在这种统一性中的内容才有可能成为符号学基础研究中的元理论。
由于任何符号都不是一种人之外的自然存在,而是作为人的创造物,所以,不管对索绪尔还是对皮尔士来说,符号和符号过程都需要有一个承担者来实现,也就是每个符号都有一个潜在的承担主体,符号的形式载体和符号负载的意义都是对这个主体而言的。对皮尔士和索绪尔来说,他们各自的符号承担者必然都是以人为主体,这是他们之间的共性,但是皮尔士的符号承担主体和索绪尔的符号承担主体在性质上却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先从皮尔士的另一个符号定义来开始。“指号或表象(representamen)是这么一种东西,对某个人来说,它在某个方面或以某种身份代表某个东西。它对某人讲话,在那个人心中创造出一个相当的指号,也许是一个更加展开的指号。我把它创造的这个指号叫做第一个指号的解释者(解释项,interpretant)。这个指号代表某种东西,即它的对象(object)。它代表那个对象,但不是在所有方面,而只是与某个观念有关的方面”[3]276。皮尔士随后又说明了符号(First,第一者)、对象(second,第二者)和解释者(解释项,third,第三者)在符号关系中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第三者在符号关系中的无穷性[3]278。这里,这个无穷的第三者和后来罗兰·巴特的符号理论中的第二层能指很有些相近之处,但关键性的区别在于,皮尔士的这个“第三者”同时还凸显了解释主体的现实存在性。“对指号来说,称它为指号是必然的,因为它必须被看成是指号,是这样思考的那个人的指号,如果它对任何人均不是指号,那么它就绝不是什么指号。那个人必定认为它是与其对象有联系的,才可以做出由指号到实物的推理”[3]300。也就是说,在皮尔士的符号论中,他特别强调了这个解释者(解释项)的在场性,即符号的承担主体和符号、及其对象是同时存在的,只有在解释者(解释项)的存在中,符号中的其他两项(指号和对象)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三者是缺一不可的。这决定了在皮尔士的符号关系中,符号的承担主体更侧重于是某个个别的、具体性的现实个体。
对索绪尔和罗兰·巴特的符号来说,索绪尔明确指出了他的研究对象是整体语言,是处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作为符号体系的抽象的整体语言”,所以,对索绪尔的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来说,这个关系的接受主体并不一定是社会中的某一个个体,而是一个抽象和整体的隐性主体,是不在场性的社会主体,即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人。换句话说,对某一个个体来说,他对一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的接受与否,并不构成对索绪尔符号关系的否定性。比如,一个人可以从符号任意性的角度把允许通行标志的绿色信号灯替换成红色信号灯,那么,当他在红色信号灯亮起并进入十字路口的时候,必然会引起交通秩序混乱,他也必然会受到之后相应的交通规则处罚。实际上,虽然索绪尔强调符号的任意性,但他也指出任意性是有条件的。“就‘任意性’这词,须再提几句。它不是‘取决于个体的自由抉择’这一意义上的任意性。相对于概念来说,它是任意的,因为它本身与这概念毫无特定的关联。整个社会都不能改变符号,因为演化的现象强制它继承过去”[2]86。所以,不管就个人而言,还是对某个集体来说,这种符号的相互替代并不能任意发生。作为索绪尔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的接受者,并不是偶然性和个体性的个人主体,而是必然性的和群体性的社会主体。
对逻辑学家皮尔士来说,强调符号主体的偶然性和个体性在于强调符号自身的生产性,就是说,符号的出现是一种意义或信息的崭新的创造过程;符号产生于个体,产生于偶然性,符号一经产生就要在人与人之间起传递意义和信息的作用,其中,有些符号的传播范围很小,传播时间很短,不久便失去了符号的效用,而有些符号的形式和内容在社会的交往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地磨合并固定下来,渐渐失去其中偶然的个性化情感要素,而成为具有最大公约性的理性符号。接下来,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中,这些理性符号作为意义和信息传达的载体,其形式指向符号的能指,其内容指向符号的所指,符号和它所传达的意义逐步就成为固定的、人们约定俗成不能任意改变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索绪尔语言学中的符号。所以,符号中的理据性和任意性是一对辩证的关系,二者并不是对立而是相生相随的,在符号的历时性的产生过程中,虽则偶然的任意性成分居多,但却表现为理据性,而在符号的共时性的意义传播过程中,虽然以必然的理据性作为主导要素,但却呈现为任意性原则。
就是说,皮尔士的符号处在一种时间性的历时结构中,他关注的是一个符号在任意的个体中出现的时间过程,所以,符号的承担者是具体的、但却是偶然性的个体性主体;而索绪尔的符号则处在一种空间性的共时结构中,他关注的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群体的必然性的符号关系,所以,符号的承担者是抽象的、但却是必然的社会性主体。如果把皮尔士置入索绪尔的语境中,皮尔士关注的是历史语言学或符号的历时性形成过程;如果把索绪尔置入皮尔士的语境中,索绪尔关注的则是存在于同一时间断面中的关于符号(第一者)的抽象化了的解释项(解释者,第三者)和对象(第二者)的关系。
因此,由于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各自的承担主体所处的时空关系是不同的,索绪尔和皮尔士所关注的符号也是处在不同的时空结构中的不同性质的符号,所以,不管是在“能指”、“再现体(符号)”和“所指”、“对象”之间,还是“解释项(解释者)”和“第二层能指”之间,有着怎样的直观相似性,但都是不能直接相互类比的。
三、符号的判定与符号学元理论
近年来,皮尔士的符号论不仅是在符号学界,而且在艺术学、传播学领域中也受到了逐渐地关注,但是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很多研究者仅仅是把皮尔士的符号理论直接套用在研究对象上,然后得出某个预期的结论。实际上,这种做法既过于简单地理解了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也为准确把握皮尔士的思想增添了新的障碍。比如,在关于“XX是不是符号”的判定问题上,这在索绪尔的符号语境中是存在的,但对皮尔士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深究之下会发现,在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中,类似“XX是不是符号”并不是一个性质判断,不是有关“XX”是否具有“符号性质”的性质判断,而只是一个表示“S从属性于P”,如“所有的艺术家都是人”这样的关系判断。
皮尔士的符号论实际上和卡西尔的符号论一样,都是哲学意义上的符号论,如果说卡西尔-朗格的符号学模式在符号学研究中“缺少可操作性”,那么在准确把握皮尔士符号论的前提下,从皮尔士出发的符号学者们同样会遇到这个“缺少可操作性”的问题。我们下面通过对皮尔士的符号(指号)定义的具体分析,来说明如果把皮尔士的符号论引入现代符号学未必能得出符号学者们所期待的结果,因为从皮尔士的符号论中得不出“什么是或什么不是符号”的判断依据,只有在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中,才存在“XX是符号”与“XX不是符号”之类的性质判断。
在皮尔士的晚年,大约从1886年开始,他先后为符号下过近十次定义。为后人所常引用的是1901年他为麦克米兰出版的《哲学心理学辞典》(1903)编写的一个词条。
符号(拉丁文是Signum,指一个记号,一个标志):任何事物决定其他事物(它的解释者、解释项,its interpretant),去指称这个事物本身以同样的方式去指称的一个对象(an object),这个解释者(the interpretant)依次成为一个符号,如此以致无穷。
毫无疑问,智性的意识(intelligent consciousness)必须进入到这个系列之中。如果这个解释者们(successive interpretants)的系列结束了,那么至少,这个符号会因此而不完美。如果,一个解释者的观念(an interpretant idea)被决定于一个独立的意识之内(in an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它不能决定任何向外的符号(outward sign),而且,那个意识湮灭了,或者失去了所有的记忆或符号的其他重要效应,那么,这个情况(在那个意识中曾经存在如此那般的一个观念)将成为绝对不可发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理解“那个意识中曾经有过那样的一个观念”这种说法具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样说的本身就成为那个观念的一个解释者(解释项,an interpretant of that idea)了。”[5]
接下来是一段皮尔士对符号简要分类的文字,包括图像(icon)、标志(index)、象征(symbol)。我们从摘取的两段中可以看到,皮尔士在给符号下定义的同时,也指出了符号可能存在的三种状况。第一、是能使“解释者(解释项)们的系列”“如此以致无穷”的“完美的符号”。第二、是“不完美的符号”。像“朕”这个符号,在现代社会中被使用的机会越来越少,以后完全可能不再有解释者能把它和一个对象相联系,因而变成一个不完美的符号。第三、是那种只存在于“一个独立的意识之内”的符号,实际上就是一种“非符号”。举例说,你有一个观念A,但是你从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也没有写在或画在任何地方,总之除了你之外没有人知道你有这个观念A,而且,一段时间后,连你也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那个观念A,那么,这时如果有人(包括你自己在内)说“在你(我)的意识中曾经有一个观念A”,这句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就没有形成任何一个符号。但是,虽然没有形成任何符号,但这个过程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形成所有符号的必经过程。
可见,皮尔士在符号的定义中设定了三种情况:1.完美的符号,2.不完美的符号,3.形成中的符号。把这三种情况倒过来排序,实际上就是一个符号的生成与发展的历时性过程,而且,由于符号的历史并不是一个自为的过程,如皮尔士所说“智性的意识必须进入到这个系列之中”,是由意识和符号解释者(解释项)的承担者,即人来实现的。在1904年写给韦尔比夫人的一封信中,皮尔士提出了解释者的两种三分法,即“情绪的(emotional)/活跃的(energetic)/逻辑的(logical)”和“即刻的(immediate)/动态的(dynamic)/最终的(final)[4]180,这和皮尔士在符号定义中对符号的三分法是恰相对应的。可以看到,皮尔士在符号定义中通过对意识主体作用的强调,超越了静态的具体知识范畴,进入了人的认识领域,符号关系中的符号、对象、解释者只能出现在人的认识现象中,因而,符号的范围要大于具体知识的范围,其中必然要包括一部分尚未成为确定性知识的非理性内容。
我们接下来看皮尔士在上述定义中为符号划定了怎样的范围,或者说他的符号定义能否成为判定符号的标准。显然,从皮尔士的符号理论出发,没有什么事物可以不是符号,否则就不能进入人的认识范围。今天的符号学如果把皮尔士的符号论作为自己的学科基础,那么其中就不存在一个某事物是否是符号的性质判断问题,只要承认事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把它包括在皮尔士的“符号——知识”范畴之内了。在这种条件下,以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为标准来说明某物是不是符号,实际上并不会形成一个关于某物是不是符号的性质判断,而至多只会出现一个有关符号类别的关系判断。所以,如果说今天的符号学由于在运用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中受到了一些局限,而逐步地偏向皮尔士,但如果把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上升到符号学的范畴,那也是一个最广义的符号学,在这个以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为基础的符号学研究中,就没有什么事物不是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根本不存在“XX是不是符号”的性质判断问题。
当然,也许这正是符号学家们所期盼的情况,但由此出现的另一方面问题在于,皮尔士基于哲学、逻辑学奠定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当其他理论体系中的概念和他的符号理论相遇时,如果不经过严谨的论证、转换和检验过程就直接地予以等同性的对待,往往就会曲解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例如,有很多学者往往将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与皮尔士的“再现体”(符号、指号)和“对象”做出类比,以得出某些预期的结论,但是不管结论怎样,这个类比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个类比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皮尔士符号三分法中的“解释项”,作为符号过程中的这个“解释项”(解释者)才是皮尔士符号论区别于索绪尔的核心所在,把皮尔士符号论中的这个第三者抛开,实际上就成了索绪尔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同义反复,从这个前提出发不会得出有价值的论证。再如,关于符号分类,皮尔士曾经做过多种尝试。他基于符号的三分法,依据符号、对象、解释者的每一个三分法做出分类,产生出二十七种组合方式,基于常识排除了十七种,到1903年,符号的十种分类法被确认下来[4]207。所以,符号的分类法在皮尔士的理论系统中自有其严格的规定性,国内学术界中近年来出现的众多诸如“艺术符号”、“理据符号”、“二度符号”、“二级符号”等这些分类方式能否适用于皮尔士的理论体系,实际上还需要做出更多对应性的分析和判断。
另一方面,在国内和包括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者在内的对索绪尔符号理论的批判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批评者们完全漠视了索绪尔对静态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划分,但是,这是在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中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存在前提。索绪尔明确指出,对能指和所指的划分只能出现在“抽象的整体语言作为符号体系”之内,“我们从内部进入一个符号体系,此时,就有设立〈彼此对立的〉能指和所指的必要,使它们处于相互面对的境地。能指和所指是构成符号的两个要素”[2]107。可见,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适用范围是很明确的,即在“抽象的整体语言”里。而且,索绪尔对“整体语言”、“群体语言”、“个体语言”,“语言”、“言语”等概念之间的区分,不仅决定着他的语言学的总体结构,更重要的是为他的“能指”与“所指”关系限定了存在的理论语境。换句话说,“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无条件的形而上学,怎样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并不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要看那种运用是否和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设定中的具体语境相一致。并且,即便是在静态和抽象的整体语言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也并非是绝对化的,索绪尔指出:“在每一种整体语言里,都须在处于完全的任意性状态和可称为相对的任意性之间做出区分。在任何语言内,只有一部分符号是完全任意的。……每种语言都并行地包含两种要素:完全无理据的和相对有理据的,以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它以不同的比例包含这两种要素,并据各类语言而呈现极度的变化不定。这种比例构成了某某语言的特性。”[2]96-98因此,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并不存在什么内在的缺陷,并不是索绪尔的语言学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者们,在运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时抛开了索绪尔所设定的前提之后,他们自己所出现的问题。只要能保证处在一种静态的共时性关系中,我们离开语言学范畴进入其他任何领域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作为对立分析的两个方面都能具有积极的适用性。
以上所涉及的问题,其根源在于研究者没有理清索绪尔和皮尔士符号理论的逻辑关系,没有从他们的历史渊源中找到共同的理论基础,因而也不能准确把握其间的区别所在。皮尔士的符号理论直接来源于洛克和康德。他强调符号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符号的三分法中,符号可以完美、也可以不完美、甚至不成立,这就使符号超越了具体的知识范畴,符号的范围必然要大于知识的范围,从而,皮尔士的符号理论就具有明显的认识论倾向。相比之下,索绪尔语言学的直接来源要复杂一些。一般认为有涂尔干、迪尔海姆的社会学,洪堡、惠特尼等人的语言学,古印度语言学,甚至同时代的经济学思想,等等,这决定了他的语言符号学具有更多的社会学色彩。但是,在皮尔士和索绪尔之间,还可以追溯到更长远的理论渊源,即他们共同承续了西方的理性思辨哲学,比如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论事物的命名、到中世纪的唯名论、再到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概念论等等的历史影响,所以,皮尔士和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可以统一于西方的传统哲学,区别仅在于其各有所侧重:皮尔士重视符号意义的历时性创造过程,索绪尔强调符号意义的共时性传递关系。在此基础上,符号学的元理论研究就可以从两个维度上同时展开,即符号及其意义的创造性生产和社会性传播,这就使作为符号学核心对象的符号处在一种时空关系的相对论中,从而具备了超越索绪尔和皮尔士符号观念的理论可能性。
[1]屠友祥.索绪尔“符号学”设想的缘起和意图[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2]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皮尔士.皮尔士文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T.L.Short.Peirce’s Theory of Sign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5]James Hoopes,Peirce on Signs[M].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239.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1.029
2015-07-1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2YJA760087)
I0
A
1000-2359(2016)01-0148-06
尹德辉(1970-),男,河北南宫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临沂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艺术学、文艺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