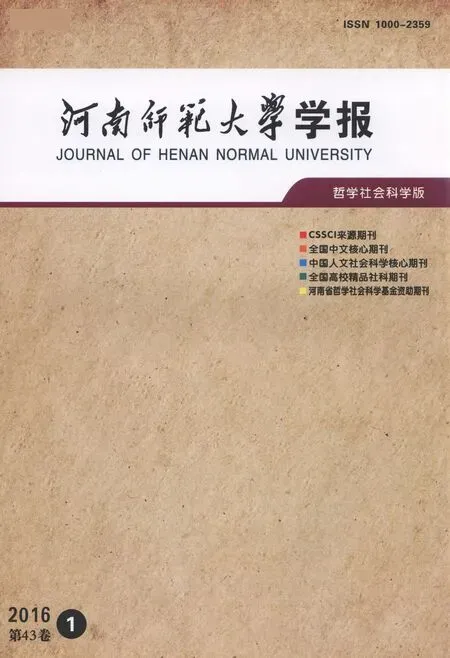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及其社会原因
2016-03-16孟祥晓
孟 祥 晓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及其社会原因
孟 祥 晓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频繁,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影响社会稳定。究其原因,除了受卫河所处地理位置、河道特点、季风气候及漳河的迁徙不定、不断入侵等自然因素影响外,更与当时的社会因素息息相关。如堤防被人为破坏;河流滩地被居民垦种;不合理的隄防工程影响;太行山区的过度开垦;河道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以及政府的渎职、官吏的腐败,这些因素无一不包含有人类活动的影子,尤其是嘉道以后更为明显。故可以这么说,社会因素是造成卫河流域水灾频发的主因,即所谓“人事”重于“金穰木饥”,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研究这些社会因素,对今天河流生态环境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水灾;社会因素;卫河流域;清至民初
一、卫河流域范围及清至民初的水灾
卫河流域包括清代卫辉府、彰德府、大名府及临清州等全部或部分地区,此区域大致从今焦作修武、获嘉县起,沿太行山西南至东北走向沿伸,至卫河与京杭运河交汇处之临清止。西依太行,东至运河,南起黄河,北达漳河附近。因其地处华北平原南部,自古为古黄河泛滥变迁之地,故地势相对低洼,极易遭受洪水侵袭。
清至民初时期,中国灾害类型总体呈现涝灾多于旱灾[1]的特征。卫河流域因其所处区域的地形、地势等自然特点,更是水灾频发。据研究,清至民初的280多年中,卫河流域所属的21个州县,共发生水灾1117年次,年均发生水灾的州县数约为4个[2],水灾发生的频繁程度可见一斑。综合来说,卫河流域水灾总体上清后期多于清前期,并表现出随时间推移而多发的趋势。具体而言,在时间上呈现出几个水灾发生较密集的时间段,且嘉庆以后水灾日益严重,几乎无年不灾,这与清朝社会由盛转衰有一定的关联性。在空间上,卫河流域各县水灾发生次数以滑县以下为最,但严重水灾的发生次数则以浚县以上的中上游为主,说明上游水灾更易造成严重的损失与后果[3]。而造成卫河流域严重水灾的原因固然与直隶地区相似,与大面积的农田开发有关[4]580,除此之外,还受卫河流域所处地理位置、河道特点、季风气候及漳河的迁徙不定、不断入侵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因当时诸多社会因素所致。
二、卫河流域水灾中的人为因素
关于造成灾荒的原因,邓拓先生曾经指出,自然条件只是外因,外因只有通过社会的内部条件,才可能导致严重的灾害发生,从而对社会产生影响[5]84。时人对此问题亦有清醒看法,指出天之所以为灾,完全是人为的因素使然,地无沟渠以致造成水旱灾害,把灾害归因于天,完全是不懂科学常识之故,从而发出“‘天灾’,岂天之过欤?”之责问[6],可谓一针见血。具体来说,人为的社会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堤防被人为破坏
河道的堤防,是约束洪水的重要屏障,可是,在中国古代生产力低下,人多地少的情况下,百姓为了生活,就会不惜一切开垦土地种田,即使河道堤防也不放过。卫河流域的河流季节性很强,在枯水期甚至断流干涸。漳河每逢春季,河水“深才没胫,极小船亦不能行驶”[7]疆域志·河渠,有时则完全干涸。百姓看不到堤防的长远作用,就破堤开田,如临漳县境内的漳河堤防,当地居民为了开地耕种,就在漳堤上取土,“犹可望其填淤肥美”,如此使得“堤旁取土皆成坑坎”[8]卷十六,可以想见,这样的堤防在大水来临之时,是不能起到堤防的作用的。
大名县境内的堤防亦是如此。居民贪地之利,往往以河为圃,为了灌溉,就用桔槔或在堤防上挖洞,洪水来临,往往由此决溃。“濒河居民嗜利忘害,每以河为圃,桔槔致之或穴堤以通沟洫,水至而后涂隙,深涂浅溃多由此。”[9]即使在下游临清附近,沿河居民也把河道、堤岸及岸外埝道变为耕田。如清末民初,临清至黄河北岸的一些河道、滩地等即为如此,而且得到政府的认可,“向之交通孔道悉变为膏腴良田”,黄河以北的会通河完全废弃[7]疆域志·河渠。这样的堤防状况,一旦洪水来袭,决堤漫溢必不可免。
(二)河流滩地被沿河居民垦种
滩地是平原河床季节性淹水的微地形。河流的滩地虽然不是河流行洪的主河道,但当遭遇几十年一遇或百年一遇的洪水时,滩地却是河流行洪的重要区域。而对于季节性较强的卫河而言,往往会在涸水期“泉源微细,时常干涸,而民间常以河身种麦,地方官不加查察,一有水发,则弥漫遍野,所以贪尺寸之利而受患无穷也”[10]21。一些地方官员因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甚或为了政府租课收入的增加,往往采取给耕牛、麦种等形式劝民开垦。这种行为还往往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和歌颂:陈大玠,福建晋江人,五经进士。居官仁明勤慎,严绝苞苴。遇漳水泛涨,坏民居,沿村给钱修整,按地亩给麦种,详请发仓储万余石散赈。邑西南地洼水聚,开渠十二注诸河。劝民垦河滩,助以牛种。总督王士俊称之曰:“民歌令德几于掩西门轶史公矣。”李宜芳,山东诸城人,进士。详免漕米豆四千余石。请豁租课地二百顷,赔粮河滩地四十三顷[8]卷七。这种情况都是以为民请命的父母官的形象被记入地方志中,足见人们对此问题只是停留在发展农业的层面上,而完全没有考虑可能因此造成的严重水患。
临漳县漳河迁徙频繁,沿河居民大多无固定的田地,只有在漳河向南迁移时种北岸,向北迁移时种南岸[8]卷一二。这种在涸出滩地上临时耕作的方法,且不论收获如何,重要的是当洪水来临,必然会阻碍洪流的下泄,人为地造成水灾的发生。所以时人有“人与水争地为利,以致水与人争地为殃”[11]卷二二九的担心与警告。
更有甚者,一些排水河流的下游河道也常常被当地居民开垦耕种,进而影响河流洪水下泄,给上游地方造成水灾。修武县“东北一带地势洼下,至辉获二县则其势渐高,断梗腐草之所棲泊,浊流浮沫之所停蓄,而辉获附河居民遂以河所经由之道垦为耕作之田矣。每至夏秋,太行山水暴涨与夫一切沟浍之水并汇于新蒋二河,辉县人又筑堤其北,水势益不获所归,俾两河上游之田禾日在若灭若没之中,遂人人抱无年之痛矣。由是言之,二河末流不通,附河居民之获利有限而上游诸村之受害无已时也”[12]卷四。这种原因造成的水灾,不能不说是当地居民的短视之果!
(三)不合理的堤坝工程
堤坝虽是为了防水,但也要因地制宜,否则就会适得其反,“约束愈严,冲决愈甚”[13]。乾隆时期的贡生吕游就曾极力反对筑堤束漳,力陈筑堤之弊,他指出:“大凡无堤之处,水皆四散分流,随来随去,故水虽大不能为灾,但见为利不见为害。唯有堤束之,岁旱则水利绝不可得,至于堤溃之时,水皆聚于一处。夫水之性,散之则其力弱,聚之则其势猛。”[8]卷一六他认为,有堤防“岁旱则水利约不可得,至于堤溃之时,水皆聚于一处”,根本起不到堤防应有的作用。
吕游生长在漳河岸边烟落寨,对漳河应该相当熟悉,他“笃于桑梓兴利除害竟尤挚”,根据当时的情况,“漳河数徙,乃筑堤堵水,民罢于役,莫能除也。为著《衡漳考》,有开渠筑堤等篇,极言堤工之弊。乾隆二年……乙未夏河决小柏鹤,又决朱家庄,盛暑兴工,甚骚扰,乃以《衡漳考》上周君元谦上大宪,役乃罢,民困苏”。可见,他的建议在当时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并得以执行。其后,“上宪屡欲复堤,王君允楚、王君果、姚君柬之皆取此书上之,卒得请”[8]卷九。此三人均系嘉道时人[8]卷七,所以,至少在嘉道以前,吕游的“无堤论”还在发挥着影响。当然,吕游的不筑堤防是与当时漳河的地理形势相一致的。某些地方河身低于堤外的堤防,在水灾发生时,阻碍洪水宣泄入河,从而加重灾情,造成更大的损失。毁去堤防,就是拯救万民于水害之痛苦,也许正因为如此,上述三人民才“德之”。
如果临漳筑堤会影响沿河洪水的汇归入河而加重水灾,那么局部堤坝还会对其他地方的水灾产生影响。修武县东北部的水灾即因辉县人在新、蒋二河的北面筑堤所致。新、蒋二河系修武县泺水下泄的重要渠道,本来修武东北部就地势低洼,加上下游的辉县、获嘉二县则地势较高,所以容易遭受水灾。何况下游辉县、获嘉沿河居民不但开垦河道耕种,而且辉县人又在北部筑坝挡水,对于辉县居民来说,筑坝当然是为了本地免于水患,但如此一来,新、蒋二河下游被人为的堤坝阻挡,水无去路,自然会造成修武地方洪水停蓄,田禾淹没。“每至夏秋,太行山水暴涨与夫一切沟浍之水并汇于新蒋二河,辉县人又筑堤其北,水势益不获所归,俾两河上游之田禾日在若灭若没之中,遂人人抱无年之痛矣。由是言之,二河末流不通,附河居民之获利有限而上游诸邨之受害无已时也”[12]卷四。这种因小失大,顾此失彼的方式在有清一代各地经常出现,从而人为增加了水灾的发生和损失的扩大。
(四)太行山区过度开垦,水土涵养能力下降
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土地的开垦历来受到政府和百姓的重视。尤其是在人口快速增长、地少人多的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更加剧了人们向山区进军的步伐。清代从乾隆十八年开始,全国人口就急剧增加,嘉庆十七年达3.6亿[14]261-262,到1912年时,全国人口超过4亿。与此同时,人均占地面积则大幅度下降,如此时期直隶地区的人均占地面积六十年间下降了37.8%[14]394-400。加上清中后期,各种自然灾害频发,更使得大量的灾民涌向山区,为了生计,他们砍伐植被,开垦山田。而森林的砍伐和山地的开垦无疑会加重水土流失,一遇大雨,极易暴发山洪,形成泥石流。
山区的过度开垦,必然破坏山区植被,从而降低土壤对水分的涵养能力,加剧水土流失的程度。辉县地处太行山区,清乾隆年间,地处太行山区的辉县西山一带,草翠山绿,环境怡人,“辉之四境,独西面辽阔,遥望西山一带,翠色扑人,尝闲步柳荫,小桥流水,稻秀莲实,虽江南不是过”[15]卷一七。可是,为了增加额赋,政府及地方官均鼓励当地百姓开垦山间荒田,“辉县之境,北西东三面皆山,而正西、西北则太行绝顶,俱与山西为邻,有辖入深山六七十里者,近亦不下二三十里。其山上、山腰、山脚、山峡旧皆有田,皆有民人居住,其废庄累累,砌崖参差尚可考而知也。自明末至今百年,邻邦州县俱开荒成熟,而此山之田荒芜仍旧,即间有开垦者,不过十之一二”。这些在山间开垦的田地,皆是“磊石为岸,聚土成田,名为梯田,全借人力,自无人修理,则岁久岸倾,土去石出,不堪耕种矣,又受山西数百里之水,每一暴发,建瓴之势冲塌居多”。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有净露石骨者,有冲成河身者”[15]卷一七。
虽然一些地方官员在其任期内也曾鼓励种植树木,绿化荒山,但当百姓青黄不接或灾荒年景生活无着时,便会毁坏山林,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不无关联。清道光年间,知县周际华眼看田园日废,曾著文劝百姓多种树[15]卷一八,在当地产生不错的效果,浅山居民,曾栽植很多树木,逐渐成林。但清末至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劳动人民的压迫日甚一日,农村经济破产,农民为生活所迫,因而砍伐树木现象日益严重。……造成童山秃岭,水土流失面积显著增加,山区均受其害[16]。所以,太行山的森林覆盖率到清末,由隋唐时期的50%左右降到10%以下[17]。原来被茂密森林覆盖的太行山区及其东麓地区,经过长时间的过度采伐和破坏,森林资源日渐枯竭[18].河南林县一带原是“多良田美水,周田七八十里”的低山丘陵区,到清末民初也“童山濯濯,弥望皆是”[19]。到1949年,太行山林地覆盖率仅为3%左右[20]。
因为能够起到涵养水源、预防水患、防风固沙等作用,森林在民国初期已受到政府的重视。民国三年政府颁布了《森林法》,提倡植树造林、禁止滥砍滥伐和水源地开垦等[21],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但现实生活中,民国时期滥伐森林以至于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仍十分严重。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包括卫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河南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和水利事业的失修[22]。看来到民国时期此种情况依然没有改观。
三、卫河流域水灾中的管理因素
造成卫河流域水灾多发的原因,除了人为因素以外,还有当时政治及政府管理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河道管理上的条块分割
清代水利的兴修都是以县为单位,各自为政,“一邑之计,则数十里外即为异境”,这样的现实,造成“在此为切己之忧者,在彼未免为秦越之视”[10]4的局面,所以,即使有“爱民如子者欲兴利以除害”,也往往会动辄掣肘。临漳知县吕游曾经设想,在漳河沿岸各郡“得一廉能之吏,统领漳滨数郡而总领之”,按照宜疏不宜防的原则,顺水就下之性而不与之争,则既可利农,又可减轻水灾之患。但是,在(康熙)乙未之夏,漳河决小柏鹤村时,虽然临漳县在洪水过后,已经种上二麦,但下游的大名县等地却洪水成灾……虽然如此,吕游却极力主张不在小柏鹤决口处筑隄堵口,并得到巡抚徐中丞之支持而实行。这无疑也是一种地方利益为主的片面做法,虽然“临魏两县蒙恩多矣”[8]卷一六,但可以想见,位于下游的大名境内却因此而受灾惨重。可见,如果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即使所谓的廉能之吏也脱不了以地方利益为重的巢臼。
辉县在道光年间发生了一次“从古未见”的特大水灾,据周际华所记,当时“汗漫无津,南北街成渠,深丈许,入民房者三四尺,墙倾屋陷,水势雷鸣。余困于镇者四日,乡邻音耗不得通,水稍杀,登楼而望,麦田皆泽国矣”。这次大水,固然也是河道不通所致,但当知县劝百姓捐资购买地亩,出夫疏浚“庶几水有所归,不致横决”之时,当地百姓却佥曰:“如此办理,甚善。顾以御小水则可,若大水至,则南流之丹河壅滞而北下之水势难消,虽辉邑疏通,其如获嘉、新乡之阻碍何如也!”[15]卷一八也就是说,即使本邑疏通,下游不通,水无所归,依然无法解决当地水患。在河道的条块管理面前,本地惨重的洪涝灾害也是如此的苍白!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辉县出现此种“辉邑通而获嘉、新乡阻碍”的情况,地居沁河较近的修武县也一样受此困扰,所不同的是,修武经过多年努力,最终通过自己出资、自己疏凿的方式解决了本县东北部的水患问题。由于修武离沁河很近,所以经常遭到沁河决口的危害,“延陵邨西北正北有沙河一道,系乾隆四十九年武陟卢里邨沁河决口。嘉庆二十三年武陟古樊邨又决,水出五里许即入修武境南霍邨、北雎邨,县南诸邨正当其冲,损坏田庐无数。道光三年秋武陟老龙湾沁河又决,淹没县南一带田禾,每逢秋潦水涨,河漏水流不息,至今犹然”[12]卷四。这种情况,均是因为“每至夏秋,太行山水暴涨与夫一切沟浍之水并汇于新蒋二河,辉县人又筑堤其北,水势益不获所归,俾两河上游之田禾日在若灭若没之中,遂人人抱无年之痛矣。由是言之,二河末流不通,附河居民之获利有限而上游诸邨之受害无已时也”。其实早在此之前的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五年,“官斯土者屡有疏壅决滞之举,但以地界辉获二县,不免有所牵制,是以功终不就”。可以想见,虽然同为一河,却事涉卫辉、怀庆二府的三县,地方所属不同,自然难免掣肘。只有多方协作,方能达至彻底治理之效。但问题是,涉及二府三个县,利益不同,协调起来并不容易。
到了道光初,在修武知县的多方协调下,历时一年多方才动工,最后完成新、蒋二河的疏浚治理,“遂会同卫辉怀庆二府辉获二县图度形势,折衷郡议,区处擘划者年余而后克从事焉。……新河自翠梧桥之北迤东,其挑五百余丈。蒋河自头道横河起二道横河止,其挑七百余丈,河面俱宽二丈、深五尺,河底宽八尺,共用制钱七百缗有奇,皆明府捐办不以累民。今而后修邑东北一带庶免淹没之患乎!”但是,这种“导达之举,未能上下数十里通体疏沦,故不数年辄堙塞如故”。道光十年(1830年),虽然知县赵凤崖让上游附河居民,各随地亩所值修筑崖岸,决排壅滞,但下游辉获二县的河道依然没有疏治,于是“乃多雇役夫,独力任其经费,而少府陈莲峰又左右之,新河下游疏凿五百七十五丈,蒋河下游疏凿六百二十五丈,新河由头道牐口入丹。蒋河由二道牐口入丹,凡阅三旬而事毕,而水道遂以舒畅无滞[12]卷四。为了本邑百姓的安危,修武知县只有自己出资,疏凿本不该归本县管理的辉县、获嘉二县的河道,从而最终得以解决修武东北部水患问题。可见,条块分割式的管理方式对治理水患的巨大影响。
(二)政治腐败及官吏渎职
清中后期卫河流域水灾几乎无年不灾,除了自然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清朝政府统治的失效和腐败。孙中山先生就曾指出,官僚系统的腐败是造成各种灾害甚至是盗匪常年猖獗的主要原因[23]。这种政治的贪污腐败加上后期帝国主义的入侵,更加剧了卫河流域灾害的发生。随着政治的黑暗,叠加社会的动荡,浩繁的军需又占用了大量的财力,故道咸之后,清政府更无暇兴修水利,导致河务废弛,加之各级官吏贪腐盘剥、目光短视,只顾自己、不管大局,造成以邻为壑、遏水病邻的事件多次发生,加重了其他相邻地区的灾情,此种灾害即为典型的人为因素所致[24],如清末的河南省,虽“地势平衍,卫、淇、沁、潭襟带西北”,然“今河道半皆壅滞,沟渠亦多荒废”[11]卷一二九,如此情形,水灾频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何况,河务工作多有弊端,职责划分模糊不清,事权不一,即使在清初期也不能幸免。据怡贤亲王所奏:“臣等奉旨查修水利,遍视诸河,堤岸坍颓,河身淤塞,盖由事权不一,稽核难周。统辖于总河者既有遥制之艰,专隶于分司者不无因循之弊,以致钱粮不归实用,工程止饰目前,冲溃泛溢率由于此。……畿南诸河旧有管河同知、通判、州判、县丞、主簿等员悉听管辖。至……大名道止管广、大二府,所属州县钱粮命盗案件原听直隶藩臬稽核考成,道员甚属闲冗。今既定为河道专管,应将所属州县事务总归知府考成,省无益之案牍,励有用之精神,而河道事务可以悉心料理矣。”[10]20可见清政府已认识到此种弊端,但治理结果却并不明显。
四、小结
卫河系华北平原的一条中小河流,其流经区域系古黄河泛滥区,因地势低洼,河道弯曲,加上漳河的不断迁徙入洹、入卫以及季风气候的影响,不难想象其对该流域水灾发生的影响。但一般而言,自然条件相对稳定且变化比较缓慢,故在清至民初这段时期,自然条件对当地水灾的影响与之前相比应该变化不大。之所以在此期间,尤其是嘉道以后,卫河流域水灾随时间推移愈来愈重,当是因为诸多社会因素综合影响所致。通过对卫河流域发生水灾的社会因素分析,可以发现,在导致卫河流域水灾的因素中,无论是河道淤塞、植被破坏,还是人为耕垦、制度弊端等,无不透射出人类的影子,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可以这么说,人类的因素是此时期卫河流域水灾的主因。故古人“人事”重于“金穰木饥”[10]33的说法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1]冯贤亮.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59.
[2]孟祥晓.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与人地关系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1:254-260.
[3]孟祥晓.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时空分布特征研究[J].兰州学刊,2014(11).
[4]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J].科学,1927(12).
[5]邓拓.中国救荒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84.
[6]茌平县志[G].台北: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卷一一.
[7]临清县志[G].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8]临漳县志[G].光绪三十年刻本.
[9]大名府志[G].康熙十一年刻本:卷三一.
[10]吴邦庆.畿辅河道水利丛书[G].道光四年益津吴氏刻本.
[11]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修武县志[G].道光二十年刻本.
[13]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北通志稿:第一册[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卷三.
[1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5]辉县志[G].光绪十四年郭藻、二十一年易钊两次补刻本.
[16]辉县志编辑委员会.辉县志:第二卷[M].石家庄:石家庄日报社,1959:267.
[17]贾毅.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4).
[18]单锡五.给河北省政协王葆真副主席的一封信[N].河北日报,1957-05-01.
[19]林县志[G].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二十一年:卷十.
[20]梁勇,等.历代破坏太行山区林木的概览[J].河北地方志,1988(1).
[21]陈嵘.中国森林史料[M].北京:中华农学会,1951:66.
[22]马雪芹.明清河南自然灾害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1).
[2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89-90.
[24]池子华,李红英.灾荒与流民——以19、20世纪之交的直隶为中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1.027
2015-08-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ZS072)
K252
A
1000-2359(2016)01-0136-05
孟祥晓(1973-),男,河南滑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明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