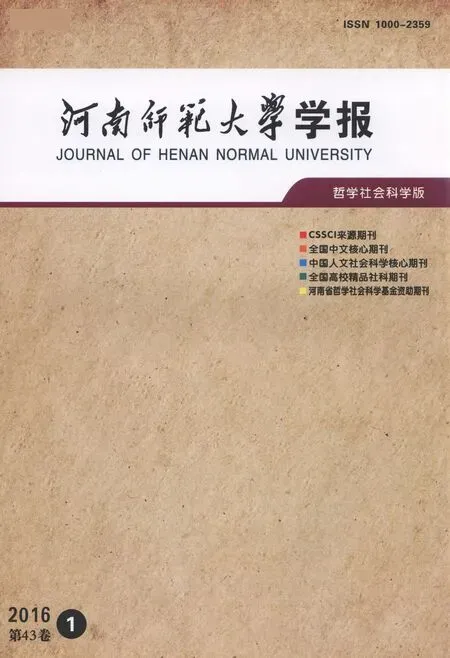自白任意性规则本土化建构探析
2016-03-16范再峰
范 再 峰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自白任意性规则本土化建构探析
范 再 峰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自白任意性规则作为非任意自白的排除规则,在证据规则中有着重要的价值。我国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发展在立法上存有缺陷,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更是被长期忽视。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本土化建构应以作为底层的思想理念为基石,包括正当程序理念、无罪推定原则和刑事司法文明化。其表层的制度构建应结合当前的司法改革背景,从保障自白的任意性及排除非任意性自白两个方面出发,分别建构预防性措施和保障性措施。
自白任意性规则;刑事司法;正当程序;本土化
自白任意性规则,作为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是指只有基于被追诉人自由意志而做出的自白,才具有证据能力;缺乏任意性或具有非任意性怀疑的口供,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均不具有可采性”[1]。自白任意性规则作为重要的非法证据言词排除规则,在西方各法治发达国家的证据法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却对此没有做足够的考虑。刑诉法的历次修订虽然补充了一些与自白任意性相关的内容,但总体上并未将其在我国刑事立法中予以明确,而在刑事司法中也不受重视。缺乏自白任意性规则,不利于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和展现刑事司法的正义性,也不利于我国现阶段所推动的“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全面而充分的落实。由此,在当前司法改革的整体背景下重新审视我国所面临的问题,并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自白任意性规则之现状与问题
我国的自白任意性规则是伴随着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和完善而逐渐发展的。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与自白任意性相关的内容规定在刑诉法第32条,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该内容规定在第43条,并未予以变动。总体来讲,该条内容的立法意图在于纠正“文革”中不受约束的刑事追诉手段对法制的践踏,并不过多涉及对自白任意性的要求。而2013年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相较于前述两部法典关于自白任意性的规定,做出了较为明确的拓展和细化。初步建立了具有一定操作意义的自白任意性规则框架。
新刑诉法中与自白任意性相关的法条主要体现为:第50条从正面做出如下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54条则从反面规定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第118条规定了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前首先要告知的事项,以及“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以上法条的规定,使自白任意性规则在我国具备了一定的实施依据,为避免非任意性自白的出现设置了一些限制性条件,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仔细研读和比较以上条文,却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是不同法条之间的冲突。新刑诉法第50条明确阐述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刑事司法准则,而第118条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所谓“应当如实回答”,暗含了“必须”这种强迫意味。而自白任意性所强调的,显然是基于被追诉人自愿性的自白。由此,上述两法条的冲突,势必会导致实践中审查讯问时的迷惑甚至矛盾;其二是对任意性的规定较为模糊。1979年刑诉法对于非法方法有着明确的界定,即“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在新刑诉法中,第50条遵循了1979年刑诉法的规定;而第54条在排除非法方法时,则仅有“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对于引诱、欺骗这种在刑事司法中较为常见的非法取证行为却没有提及。两条间隔如此之近,却没有在条文上做到一一对应,似乎是立法者有意模糊了这个问题,没有将后述之非法方法明确予以排除[2]。由此,新刑诉法中关于自白任意性规则之条文前后不对应的情况,无疑是立法上的一个漏洞,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被有意无意地利用,致使某些自白无法排除。
与立法上的冲突和漏洞相应的是,自白任意性规则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被追诉人往往不愿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而侦查人员为了能尽快破案,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去获取被追诉人的自白。在刑讯逼供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其他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开展的讯问手段,因其对任意性具有模糊的意味而更容易被采用。这似乎已成为我国侦查人员办案的一种潜规则,对此难以察觉和追究责任。从表面上看,其所反映出的,是我国现阶段刑事司法侦查手段的文明化程度还有待于提高,对法律的规定还需做进一步贯彻落实;而如果从更深层次的角度上看,则暴露出我国对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诸多缺陷和问题。
“在中国,法律条文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现实之间总是有着既宽且深的鸿沟。”[3]究其原因,在于作为“上位”的法律条文与“下位”的司法实践中的思维传统或曰思维惯性是不一致的,从而导致法律条文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总是难以达到其在设计之初的预期效果。这种衔接上的断层源于司法实践中缺乏制定法律条文所需的精神基础和人性情怀,致使司法实践总是刚性的,缺乏应有的“人情味”。在我国本就缺乏自白任意性规则立法的情形下,这种非任意性也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习惯法”了。由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构自白任意性规则,首要解决的是传统与理性之间的衔接问题,即思想和精神层次的问题,否则,法律条文的价值就只能永久停留在应然层面。
二、自白任意性规则本土化之底层建构
制度层面(即表层)的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建构,需要以作为底层的思想根基为依托,从而解决从条文到实践的断层问题,此谓底层思想根基之建构。在我国,非任意性自白的出现往往源于打击犯罪、有罪推定这种传统刑事诉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刑事司法手段缺乏有效引导,而受追诉人也因而沦落为刑事诉讼的客体。由此,底层建构应从正确认识刑事诉讼的目的、树立无罪推定的理念入手,并以此为先导,推动刑事司法文明化,为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制度性建构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正确认识刑事诉讼的目的
刑事诉讼的目的在我国总结起来即“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在日本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在第1条,为“维护公共福祉和贯彻人权保障;查明事实真相;适用刑罚法令”[4]。总体来讲,刑事诉讼的目的从学理上可表述为“发现实体真实和正当程序”,这在各法治国家的刑诉法中均已得到确认,并不存在争议。而问题在于,应如何认识诉讼目的的两个元素,是孰轻孰重还是等量齐观。按照我国通说观点,发现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应两者并重,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刑事诉讼程序。但在实践中,这种观点往往被异化为重发现实体真实,轻正当程序。虽然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国家的刑罚权,但并非是应以牺牲正当程序为代价。在两者的价值权衡上,正当程序甚至应优于发现实体真实,从而至少保证无辜的人免遭刑事处罚。毕竟,漏放一个有罪之人比误杀一个无罪之人所承担的司法风险要小得多,因为刑事诉讼对事实的认识本就无法达到绝对真实的程度。由此,相较打击犯罪的刑事诉讼传统,正当程序成为刑事诉讼目的的首要价值,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正当程序的理念既要在立法中有充分、明确的体现,在司法实践中更要深入人心,从而纠正单纯追诉犯罪的错误认识,实现对人权最大程度的尊重和保障。
(二)明确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与刑事诉讼的目的这一宏观层次概念相比,无罪推定无疑是从微观层面定义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和程序的重要基石。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至今没有对此原则予以明确。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的“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5]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之规定相比较,我国刑诉法第12条所规定的“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只是对法院作为定罪权之唯一主体的确认。事实上,目前在我国刑诉法中并不存在纯正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该原则还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而缺乏无罪推定原则的刑事诉讼程序终归是先天不足的,它使受追诉人在程序之初就有遭受不确切风险的可能。基于“有罪”推定的理念,受追诉人的无罪辩解会被认为是有意逃避法律制裁而不被采信。为获得“有罪”供述,侦查机关可能会自认“合理”而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致使任意性自白的出现变得十分渺茫。而若假定被追诉人“无罪”时,所有可以施加强迫行为的理由便不成立了。因为从追寻真正犯罪人的角度讲,既不必要、也不允许任意对任何“普通”公民实施刑事司法手段,从而阻碍了侦查机关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的可能,而只能通过向其展示各种证据或采其他合法方法,使被追诉人能够基于自由意志而做出认罪供述。由此,无罪推定的价值对自白任意性之实现便充分彰显了出来。
(三)推动刑事司法文明化
相较前两种倾向于“心证”层面的理念,刑事司法文明化则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虽然对正当程序和无罪推定的确信已暗含了司法文明化的元素,但刑事司法之文明化更多是通过显性的行为表现出来,“文明与否”可谓受追诉人对刑事司法最直观的感受。刑事司法文明化是一种宏观层次的概括性理念,就自白问题而言,当被追诉人在接受讯问时,如果能受到“文明化”的待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其意志自由就能免遭被强迫的风险。文明化的司法行为对自白任意性的实现,能够起到有效的助推作用。
刑事司法文明化是刑事司法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产物。伴随着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迅猛提高,它由早期社会的野蛮司法逐渐演变为文明司法[6]。从目前司法文明化的发展程度上看,发达国家的发展程度普遍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则总体较低。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而刑事司法文明化的程度却并没有显著提升,在某些方面甚至停滞不前。最为典型的便是刑事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不断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滕兴善案,到上世纪90年代的佘祥林案、呼格吉勒图案、杜培武案,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念斌案等,刑讯逼供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着“勃勃生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7]。公安司法机关在这些个案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公然践踏人权的行为,势必导致司法公信力的整体下降。为了避免司法信任危机的出现,推动刑事司法文明化势在必行。
三、自白任意性规则本土化之表层建构
底层建构为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实现提供了逻辑前提,而具体规则的外部化运行,则需要以切实的制度为依托,此所谓表层的制度建构。就现阶段而言,制度建构要讲求实效性,应充分结合我国当前所进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使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建构能切实接上本土化的“地气”。通过保障自白的任意性与排除非任意性自白此正反两方面,来建构起相应的预防性措施和保障性措施。
(一)预防性措施
预防性措施是从正面的角度,针对自白任意性规则的第一个方面来考虑的。其目的在于将非任意性自白出现的概率降至最低,确保自白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具体措施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必须毫不犹豫地把保护生态放在首位,绝不可再走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的老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承诺,更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繁荣发展的庄严承诺。
一是切实降低自白的定罪作用,保证其他证据的独立定罪效果。新刑诉法第53条所提到,“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同样规定在1979年刑诉法第35条和1996年刑诉法第46条。其目的就是要弱化自白在刑事诉讼证明中的作用,降低侦查时对自白的依赖程度,提高其他实物证据的证明效果。然而该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被有意无意地异化:无意的异化是指我国刑事侦查本就以获取自白作为侦破案件的重要标志为传统,自白在侦查中的实际作用并非一则条文所能改变;有意的异化,就是该条所称的“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有可能被作为对非任意性自白的“补强手段”。即当侦查人员明知自白的获取因程序不正当而缺乏证明的稳定效果时,会千方百计用其他实物证据予以补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自白的取得缺乏任意性要件,也不会受其他证据证明的驳斥。由此,该条对非任意性自白的预防效果是十分有限的。而笔者认为,要在法条中明确对自白定罪作用的削弱,突出其他证据对自白的反证作用,就应“割裂”两者的紧密联系。自白与其他实物证据的获取要采用同步的方式进行,改变以往的先口供后证据的传统办案方式,使实物证据能够起到切实独立的证明作用。
二是维护侦查讯问的独立性,减少来自外界的干扰。侦查讯问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讯问人与被讯问人之间心理上的较量。由于讯问和被讯问双方的心理状态并非处于均势,前者通常具有明显的心理优势。一旦有外界干扰所带来的压力,这种心理优势就会转化成对被讯问人的一种强势态度,容易导致讯问偏离正当的手段和方式。就外界的干扰而言,主要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外部方面是指新闻媒体、舆论对办案的影响,内部方面则是指司法机关内部对办案的非科学化指导,典型的即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限期破案”“命案必破”等上级指示或自我宣言。前者之影响往往源于新闻媒体、舆论对突发性事件的本能关注,而后者则源于我国公安机关长期形成的军事斗争的执法理念和过度追求破案率的思维习惯。司法实践充分表明,过分追求效率而忽视侦查案件的客观规律,往往事与愿违。如若在上述内外两方面的双重作用下,便有极大的可能使办案人员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从而以一种不理智的思维去侦办案件,各种侦讯手段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是完善自白获取程序的监督机制,促使自白的获取受到全面严格的监控。就讯问时的录音录像而言,一方面要适当扩大录音录像制度之适案范围;另一方面应确保录音录像做到全程进行,而不仅限于侦查讯问阶段。具体操作上:每次讯问应制作两盘录音录像带,其中一份封存,作为对自白取得合法与否之佐证。同时,为确保录音录像资料真实和完整,应由专人在事后对其予以妥善保管,并将真实性与完整性作为判断该供述可采性的重要参考。在录音录像的同时还应确保律师在场,从而实现对讯问人员的外部监督和增强被追诉人的防御权。毕竟被追诉人往往对司法程序不甚了解,对讯问人员采取的有可能导致非任意性自白的行为无法有效识别。而律师在场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在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敦促侦查人员以合法方式进行讯问。
四是发挥自白在庭审中的作用,维护被告庭审的质证权,以被告庭审时的最终自白为准。维护被告庭审的质证权,对证人出庭作证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长久以来,我国刑事庭审证人出庭率极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8]。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被告人的质证权无法得到保证,其所作出的自白因缺乏质证环节而天然被降低了可信度,导致被告处于一种相当不利的境地。而以被告庭审时的自白为准,是指当被告在庭审前做出的自白与庭审时的自白出现不一致乃至冲突的情形时,应以被告庭审时的自白作为影响其定罪量刑的依据。这是因为相较庭审前,庭审时的自白因其公开性,可大大降低非任意性自白出现的可能性。同时,作为决定其最终命运的关键阶段,如果被告在先前的诉讼阶段被迫做了非任意性自白,且该自白与事实相悖,那么其在庭审时必然会向法官吐露真相。否则,就会失去最后自我救赎的机会。此外,以被告庭审时的自白为准,也符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自白任意性的要求。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质就是以庭审为中心,决定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实体问题都要放在庭审中予以解决,从而实现庭审的实质化[9]。因此,自白作为重要的言词证据,对其真伪的最终认定也应放在庭审中进行。这是被告人所享有的质证权和最后陈述权的充分体现。虽然不排除存在一些被告人在庭审中恶意翻供,扰乱法庭秩序,意图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形,但如果其他实物证据能够充分证实被告人的罪责,这种故意翻供并不会影响实然公正之实现。在审判中心改革的背景下,要充分赋予自白这种实体和程序价值,使任意性自白在特殊情形下成为拯救无辜、伸张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起到对刑事庭审的兜底性作用。
(二)保障性措施
保障性措施是从反面的角度,通过排除非任意性自白,来实现维护正当程序的最终目的。笔者认为,应重点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即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标准的认定。
就证明责任分配而言,刑事诉讼中一般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被追诉方有罪的证明责任,被追诉方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自白却有所区别。由于被控诉人的自白是言词证据,如果仅以文本的形式表达,并不能确定其系自由意志而得,还需要被追诉人的自述。而在现阶段,我国非任意性自白的证明责任是由被追诉人承担的,如果其声称自白是在强迫等违背自由意志的情形下作出的,就需要自己承担证明非任意性存在的证明责任。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机关,在仅有被追诉人个人陈述的情况下,对此非任意性的证明恰恰是难以实现的。由此,可以考虑将非任意性自白的证明责任加以迁移,使其主要由控诉方承担。当被追诉方提出自白系非任意性所得时,为避免败诉风险,控诉方应提供自白系自由意志所得之证据。如果控诉方无法提出反驳之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存有严重瑕疵乃至无法进行补强,则应对此自白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这种证明责任的分配平衡了控辩双方在力量上悬殊差距,并迫使侦讯人员合法、适当地履行职责,保障诉讼程序和裁判结果的质量。
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本土化建构,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对证据规则的制度化设计,而其中却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在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本土化建构将更进一步推动我国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虽然这一过程会带来程序的繁复和诉讼成本的增加,但从更大的范围和价值考量上来看,则是必要和合理的。因为刑事诉讼的最大目的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并非仅就个案经济成本做单方面的考量。当通过规范刑事诉讼制度,每一个案件都能够让当事人和公众切实感受到公平与正义时,我们得到的将是一种更大的划算和回报。
[1]樊崇义,等.刑事诉讼法原理与适用[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136.
[2]张建伟.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法律价值[J].法学研究,2012(6).
[3]郑曦.自白任意性规则的中国运用[J].证据科学,2013(5).
[4]田口守一.刑事诉讼的目的[M].张凌,于秀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45.
[5]杨宇冠.国际人权法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影响[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296.
[6]陈建军.论司法文明[J].云梦学刊,2004(4).
[7]何家弘.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17.
[8]史立梅.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及其评价[J].山东社会科学,2013(4).
[9]樊崇义.“以审判为中心”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论[J].法学杂志,2015(11).
The Exploration of Localization of Voluntary Confession Rule
FAN Zai-fe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The voluntary confession rule, as the exclusive rule of non-voluntary confession, is of great value in the rules of evidence.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ary confession rule in China is legislatively defective, and has been neglect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 criminal judicial practices. The localization of voluntary confession rul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hought and idea of the interior level, including ideas of due process, the principle of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civiliz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The system building of the exterior level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current judicial reform, and from such two aspects as securing voluntary confession and excluding non-voluntary confession to establish preventive and secure measures respectively.
voluntary confession rule;criminal justice;due process;localization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1.011
2015-10-17
D925.2
A
1000-2359(2016)01-0053-05
范再峰(1989-),男,汉族,河南新乡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