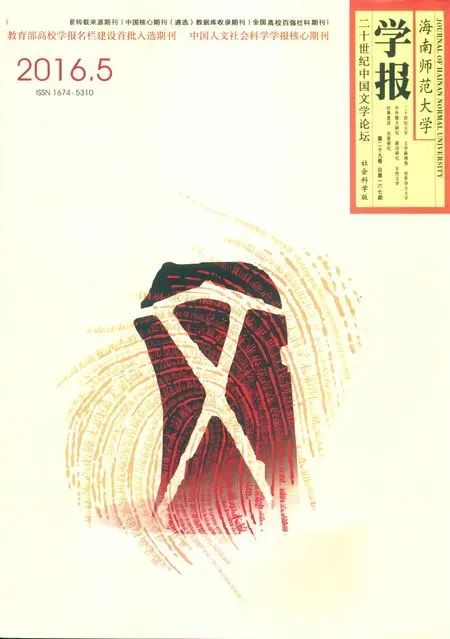故土的执著守望
——贾平凹乡土小说论
2016-03-16陈宗俊
陈宗俊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11)
故土的执著守望
——贾平凹乡土小说论
陈宗俊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11)
摘要:对乡土的执著书写是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书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对故土奇景、奇人和奇俗的描写,对故土自然、人物、事件以及生命体验之神秘的探幽,以及对故土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性撕裂的思考。贾平凹的这些乡土小说也存在诸如情节结构、人物与意象等的重复,以及思想力度提升不够等问题,折射出作家创作上的某种瓶颈。
关键词:贾平凹;乡土小说;神秘性;撕裂性
作为新时期文坛“奇才、鬼才、怪才”的贾平凹,从197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至今已逾40年。纵观他40年来的小说创作,一个关键词就是对乡土的深情书写。无论是早期的《山地笔记》,还是确立其文坛声名的“商州系列”,抑或是1990年代以来的《高老庄》《怀念狼》《秦腔》《古炉》等小说莫不如此。因此,我们这里重点论述的就是贾平凹的这些乡土小说,而对于其都市小说如《废都》等只是作为一种论述时的参考背景。此处的“乡土小说”,是指贾平凹以乡土为主要书写对象或为故事背景而展开的小说,其重要特征是对“工业文明参照下的‘风俗画描写’和‘地方色彩’”*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描写,以及由此寄寓的作家对当代中国乡土问题的持久思考。
神奇之故土
贾平凹的文名和闻名,是与其故乡“商州”联系在一起的,“贾平凹的肉身生养是商洛的山水和大地滋养的,他的创作灵魂和艺术生命也来自于商洛的历史和现实。因此,贾平凹——商洛,商洛——贾平凹,已成了一个地域和它的文化的通用符号,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李星:《一部独特的区域作家群研究专著——序〈当代商洛作家群论〉》,邰科祥等:《当代商洛作家群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9页。作家也说:“商州的乡下……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贾平凹:《高老庄·后记》,《贾平凹文集》第15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8页。,“我是商州生长的一棵树”*贾平凹、黄平:《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因此,对故土之奇的书写就是贾平凹乡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贾平凹的小说开头喜欢对商州自然之景特别是奇景进行细细描摹,“几乎成为一个定式”*汪政:《贾平凹论》,《钟山》2004年第4期。。尤其是早年“流寇时期”*〔日〕盐旗伸一郎:《贾平凹创作路上的第二个转机》,《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和1980年代“商州系列”的小说创作更是如此。如,作家写山与石之雄奇:“路旁的川里,石头磊磊,大者如屋,小者似斗,被冰封住……山已看不见顶,两边对峙着,使足了力气的样子,随时都要将车挤成扁的了。”(《商州初录·黑龙口》)写丹江水之变化:“丹江从秦岭东坡发源,冒出时是在一丛毛柳树下滴着点儿,流过商县三百里路,也不见成什么气候,只是到了龙驹寨,北边接纳了留仙坪过来的老君河,南边接纳了寺坪过来的大峪河,三水相汇,河面冲开,南山到北山距离七里八里,甚至十里,丹江便有了吼声。经过四方岭,南北二山又相对一收,水位骤然升高,形成有名的阳谷峡,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冲起千堆雪,其风急水吼,便两边石壁四季不生草木。”(《商州初录·龙驹寨》)写白浪街一石踏三省的奇妙:“以这怪石东西直线上下,南边的是湖北地面,以这怪石南北直线上下,北边的街上是陕西,下是河南。”(《商州初录·白浪街》)等等。
除了奇景,奇人奇事也是贾平凹笔下常见的描写对象。如,拎着大包裹四处流浪的美丽提兜女阿娇(《提兜女》)、一生坎坷生前就写悼词的厦屋婆(《“厦屋婆”悼文》)、身怀绝技的“河南旦”(《沙地》)和村长成义(《土门》)、每日用漂流瓶征婚的“摸鱼捉鳖的人”(《商州初录》)、有特异功能的石头(《秦腔》)和狗尿苔(《古炉》)等等。奇人必有奇事。于是,赵阴阳预测并应验的黑豆丰产和死后有人盗尸(《龙卷风》)、侯七奶奶预言死时天空出现五个太阳(《瘪家沟》)、天空会出现飞碟(《土门》)、狼变成人(《怀念狼》)等奇诡之事在贾氏小说中也数见不鲜。这些带有“几分奇异、怪异、诡异乃至妖异”*郜元宝:《贾平凹研究资料·序》,郜元宝、张冉冉编:《贾平凹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的奇人奇事描写,使小说故事引人入胜,同时充满了某种神秘。
风俗之奇亦是故土之奇的一个方面。所谓风俗,“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页。贾平凹小说中的商州民间风俗也充满了神奇。这些风俗之奇的描写,大致包括诞生礼仪、婚嫁礼仪、丧葬礼仪、节庆礼仪等方面。如,认干亲、招夫养夫、换亲、冥婚、踏坟、“做七”、闹社火、乡会、占卜、测字等等。这些风俗,是商州地域文化上开出的一朵朵奇异之花。
贾平凹对故土之奇的描写,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这些描写与小说的整体氛围结合起来,成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寄托了作家的某种思考。如《浮躁》中对州河浮躁的描写,与改革之初人心和社会的“浮躁”这一主题相吻合;《古堡》中的张老大和光大的换亲,折射出乡村的贫困和婚姻的无奈;《怀念狼》中人狼大战,意在表达现代化进程对乡村文明侵蚀;《秦腔》中“清风街,天天都有致气打架的,常常是父子们翻了脸,兄弟间成了仇人”*贾平凹:《秦腔》,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的描写,表现了作家对现代乡村伦理的失落思索,等等。故土之奇的书写,贯穿了贾平凹乡土小说的创作始终。这一方面表明作家自觉继承现代乡土小说以来注重小说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这一“现代乡土小说赖以存在的底色”*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第24页。外,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作家创作有着自己的宏大抱负,“以商州这块地方,来体验、研究、分析、解剖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社会的变迁,生活的变化,从一个角度反映这个大千世界和人对这个大千世界的心声。”*贾平凹:《在商州山地——〈小月前本〉跋》,《贾平凹文集》第6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0页。写故土之奇就是写中国之奇,从而使小说具有某种深远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
神秘之故土
神奇和神秘仅隔一道门槛。神秘性亦是贾平凹乡土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神秘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自然之神秘、人物之神秘、神秘之事件以及生命体验之神秘。
自然之神秘。在贾平凹乡土小说中,一些山川河流、花草木石、鸟兽虫鱼等等都充满着神秘。如每月三次如期而至的达坪镇雾罩(《商州》),仙游川沟口两个石崖的神奇(《浮躁》),湖心岛石眼每年4月5日出鱼奇观(《龙卷风》),有飞碟出现的白云湫(《高老庄》),地形酷似女阴的七里沟(《秦腔》)和瘪家沟(《瘪家沟》),八石洞中似人非人的八具钟乳石(《妊娠》)……这些自然景物,除了神秘外,还充满着某种灵性与神性。如,在《怀念狼》中,红岩寺老道去世后,群狼口衔金香玉为之送葬,以报答老道的昔日救助之恩;《古炉》中,“文革”因“太岁”被挖而始因“太岁”被食而终,等等。
人物之神秘。这在贾平凹乡土小说中随处可见。这里,这些“异秉”人物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种情况:一类是儿童或老人,儿童如《高老庄》中的石头、《古炉》中的狗尿苔,老年如《土门》中的云林爷,《秦腔》中的中星爹等;一类是美男子,如《浮躁》中的金狗、《白朗》中的白朗,《五魁》中的景唐等;一类是传说中的先祖,如《土门》中的梅梅的祖先、《妊娠》中的苟旦的始祖等。这些神秘人物,或有病,或身世奇特,或经历传奇。如石头出生时,高老庄出现飞碟;金狗生时大难不死,被誉为是“钻山狗”转世;土匪白朗的升伏与宝塔的合裂;小儿麻痹的独眼云林爷,一病之后精通肝病医术;梅梅和苟旦的祖先都长有尾骨等等。
神秘之事件。这些神秘事件在贾平凹乡土小说中俯拾皆是。典型作品如《太白山记》。这是一组由16个小故事构成的中篇小说。如,寡妇和死去的丈夫晚上过夫妻生活而寡妇浑然不知(《寡妇》);村祖由一个鸡皮鹤首的老者变为一名新生儿(《村祖》);挖参人悬挂照贼镜护家,其妻却在镜中看见他每日行踪直至他的横死(《挖参人》);村寨人在情欲中活得逍遥自在,等到那个被认为是“万恶之源”的泉水被隔绝后,一切情欲全部消失(《人草稿》);公公与媳妇“意淫”,媳妇生下了酷似公公的孩子(《公公》)……这些作品,“一方面,他有意继承了古代小说谈玄说怪的传统,写出了民间奇特的信仰和感觉……另一方面,他也在作品中融入了对于当今农村弊端的讽刺,使作品具有了当代性”*樊星:《当代文学新视野演讲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218 页。而被称为当代“新志怪”小说。
生命体验之神秘。与上述几种神秘不同,生命体验之神秘,主要强调生命中一种内在于心的东西,是一种类似“第六感觉”的冥冥之思。这种生命,既包括人,也包括动物。在《高老庄》中,小说多次写到了西夏的“梦”,而这种“梦”不久在现实中就得到验证。如一次西夏梦见石头舅舅欠她十二元三角四分钱,后来背梁淹死后,果然从他身上找出十二元三角四分钱。这里数字一、二、三、四就是一个谜,象征着小人物背梁一生的匆匆与无奈。《秦腔》中夏天智死后,陪伴他的那条叫来运的狗也不吃不喝,呜咽不止,狗似乎预先感觉到了主人死亡的气息。“人为灵,兽为半灵”*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3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9页。,这是动物的生命体验。
上述贾平凹乡土小说中的神秘书写,使这些小说充满了“浓郁的史诗性、寓言性”*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第26页。。除此之外,在这些神秘性内容的书写背后,更透露着作家对自然与生命的一种体悟和思考,尤其是对庄禅思想的偏爱。贾平凹曾说:“我作品中写的这些神秘现象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都是社会中存在的东西,我老家商洛山区是秦楚文化的交界处,巫术、魔法民间多的是,小时候就听,看那些东西,来到西安后,到处碰到这样的奇人奇闻异事特多,而且我自己也爱这些,佛、道、禅、气功、周易、算卦、相面,我也有一套呢!”*贾平凹、张英:《地域文化与创新:继承和创新》,《作家》1996年第 7 期。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外文化尤其是地域文化的熏陶下,贾平凹的个体生命已开始与传统文化中佛、道相契合,并投身于自己的创作。同时多年的疾病让他对自然和生命多了份内在参悟:“我开始相信命运,总觉得我的人生剧本早被谁之手写好,我只是一幕幕往下演的时候,有笑声在什么地方轻轻地响起。《道德经》再不被认作是消极的世界观,《易经》也不再是故弄玄虚的东西,世事的变幻,一步步看透,静正就附体而生,无所慕羡,已不再宠辱动心。”*贾平凹:《高老庄·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 357 页。费秉勋先生曾指出,贾平凹的创作具有“生命的审美化”*费秉勋:《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的倾向,尤其是在1980年代以后,他对宇宙人生的苦思冥想空前沉静和深入,“结果,他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混沌感受中,感性地、融合性地接受了中国的古典哲学,其中既有儒家的宽和仁爱,也有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有着程朱理学对世界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在这种融合中,老庄哲学似乎占了较重要的地位,而禅宗的妙悟也使他获益良多。”*费秉勋:《贾平凹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3页。因此贾平凹的这些乡土小说中的神秘性就有了一种宗教色彩*谭桂林先生认为:“贾平凹的小说神秘叙事的形成则是中国民间宗教与佛道文化结合的产物。”(谭桂林、龚敏律:《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235页)。石杰也认为,《太白山记》和《烟》等作品,是典型的中国“当代的佛教文学”(石杰:《贾平凹及其创作的佛教色彩》,《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同时她还认为,贾平凹小说与道教有深厚的关系(石杰:《道家文化与贾平凹作品中的意象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和生命色彩。
撕裂之故土
如果说贾平凹乡土小说中有关神奇与神秘的书写,还带有作家对故土的某种欣赏的话,那么对于故土正在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发生的巨变,作家笔下的乡土书写则充满了矛盾:“故乡呀,我感激着故乡给了我生命”,但“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苹果腐烂,如一泡脓水,或许它会淤地里生出了荷花,愈开愈艳,但那都再不属于我”*贾平凹:《秦腔·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这种复杂的情感,在作家乡土小说中表现为一种煎熬与守望交织的撕裂之痛。
这种撕裂之痛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如作家对现对代化进程中乡村土地流失与环境破坏的无奈、对金钱与权力对人性腐蚀的愤怒与哀伤等等。在此我们想追问的是,作家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是如何深化与深入的?又是如何体现出贾平凹作为一位“深具现代眼光的批判者与思想者”*程光炜、杨庆祥与黄平主持的“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专栏之“主持人的话”评价语,《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心灵之痛的?
实际上,作家从创作之初就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一方面,作家渴望农村尽早摆脱贫困与愚昧,农民过上好日子,“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贾平凹:《秦腔·后记》,第497页。另一方面,作家对现代化对乡村的负面作用以及农民的劣根性保持着某种必要的警醒,“为这个时代的一至两代人的茫然和无措的生命而悲哀”*贾平凹、黄平:《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就贾平凹40年来的乡土小说创作而言,作家对上述问题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两个过程。
在1980年代,作家对乡村现代化进程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典型的例证就是,此期乡土小说中出现了一批农村改革者的正面形象,如《鸡窝洼人家》中的禾禾、《腊月·正月》中的王才、《小月前本》中的门门、《浮躁》中的金狗等。作家对农民的发家致富持肯定与鼓励态度。同时作家对现代化与都市文明的负面作用也开始有所警惕,如在《阿秀》《任小小和他的舅舅》《浮躁》等作品中,作家对都市文明对人性的异化作了初步的探讨:为何淳朴的阿秀、忠厚的舅舅一到城市就变得虚荣与虚伪?为何“淳朴的世风每况愈下,人情淡薄,形势烦嚣”*贾平凹:《浮躁》,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页。?但总体而言,在此一时期,作家对现代化与都市负面作用以及农民的劣根性的认识,处在一种中间情感状态,批判的锋芒不强。
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市场经济的实行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农村开始显现一系列的问题,如土地大面积被征用、农民工进城、金钱至上与道德滑坡等等。自此,贾平凹的乡土小说开始这对种现代化与都市的负面影响、人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入持久的反思,批判的锋芒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土门》《高老庄》《秦腔》《高兴》等就是作家对上述问题思考后的系列作品。
《土门》是贾平凹第一篇书写乡村城市化的乡土小说。作品讲述了仁厚村反抗都市化而失败的事故。仁厚村最后的失败,就像作家创作《废都》与《白夜》那样,作家“流露了对现代性城市明显地反感和厌恶”*旷新年:《从〈废都〉到〈白夜〉》,《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的情感相似,《土门》表达了作家对土地撕裂后的反思,以及“对今后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忧患”*孟繁华:《面对今日中国的关怀与忧患——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土门〉》,《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1期。。随后,《秦腔》《高老庄》《高兴》几部小说则是沿着这种思路不断深化。在《秦腔》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乡村荒芜图:田园荒废、人口流失,就连平日抬棺、启墓道的人手都不够。另外,人性的异化现象处处皆是。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在夏天智死去的当天,已进城卖淫的侄孙女翠翠和昔日的恋人陈星躲在屋内做爱,最后为嫖资而大吵大闹。这里情义彻底输给了名利,乡村伦理已丧失殆尽。正如作家在《秦腔》后记里所言:“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贾平凹:《秦腔·后记》,第498页。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高老庄》与《高兴》可看作是姊妹篇。前者写子路“返乡”,后者写刘高兴“进城”。二人的原始身份均是农民。两部小说试图通过子路和刘高兴之眼观察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之变化。但结果是,高老庄依旧是落后破败的乡村,这里有暗娼、皮条客和争权夺利的乡政府政客;而城市,也不是刘高兴、五富、孟夷纯们的城市,商州清风镇依然是他们最终的归宿。五富之死便是最好的说明。而作者对农民身上劣根性的批评,已摆脱了早期乡土小说中的犹疑。如子路,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教授,返乡后身上的劣习如沉渣泛起,不讲卫生、自私、冷漠等等,就连自己的妻子西夏也认为子路已是另外一个人。子路和《秦腔》中的夏风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贾平凹1990年代的这些乡土小说,将笔触深入到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与人性深处。
实际上,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自诞生以来,在文化层面一直存在着两个传统:以沈从文、赵树理为代表的封闭型传统和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开放型传统——前者表现为乡村文明对现代文明采取某种排斥与抗拒的姿态,后者表现为乡村文明对现代文明的某种吸纳与借鉴的眼光。以此参照贾平凹的乡土小说,作家似乎在两者之间徘徊,或者说更倾向于前者。因此,这种对故土撕裂书写的背后,寄寓着作家对故园的深切隐忧、焦虑、警惕甚至是“仇恨”*在《高兴·后记(一)》中,贾平凹写到:“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写越写不下去,到底是将十万字毁之一炬。”(贾平凹:《高兴》,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446页。)。这样,贾平凹这些乡土小说就生动地展示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变迁的图景,揭示的依然是“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出版社,1948 年,第 17 页。这百年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未竟事业。这种现代化,当然也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体国人的国民素质的现代化。因之,贾平凹乡土小说中有关故土撕裂的书写就显现出一种历史的厚度。
故土之后何为
陈忠实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当代陕西作家的文学创作:“无论老一代作家和这一茬中青年作家,他们的全部创造性的劳动成果,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陕西作家的作品带着普遍的地域特色,艺术上有着迥然不同的个性,成为当代文学百花园里的西部之花。”*转引自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8页。确乎如此。贾平凹的乡土小说,以编年史的方式忠实记录了三秦大地乃至整个乡土中国在新时期以来发生的巨变过程,描绘了四十余年来传统农业文明在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壮丽图景,表达了作家在农村现代化途中的的欣喜、忧患与思考。这些乡土小说,是作家自觉继承和丰富自鲁迅、茅盾等前辈作家开创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生动体现。商州,如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贾平凹奉献给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因此,贾平凹以“对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道德品格、意识情绪的不倦探索这个总目标”*雷达:《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读书》1986年第7期。的乡土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同时,这些作品还具有一定的文化史、民俗史与移民史等方面的意义。*商州,按其地理区位来看,处在陕南,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地带。在文化上有秦楚两地的特色,但“商州文化中楚文化的韵味更浓郁”(崔志远:《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新时期乡土小说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216页)。在阅读贾氏的这些乡土小说时,我时时惊异于其作品中的某些“安庆元素”。这些“安庆元素”至少包括以下内容:有关“下河人”的描写、安庆戏曲、习俗与方言等,参见拙作:《贾平凹小说中的“安庆元素”》(2015年8月30日), http://weibo.com/p/1001603881567645757327?from=page_100505_profile&wvr=6&mod=wenzhangmod。另外,一些地方性学术机构如安庆市根亲文化研究会对安庆与陕南两地间的移民文化进行了初步的发掘与研究等的研究成果,也值得我们借鉴与参考。
在肯定这些乡土小说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贾平凹乡土小说创作的某些不足。
一是小说情节结构、人物与意象等的重复。在早期一些乡土小说的开篇,如《春暖老人》《阿秀》《二月杏》《古堡》等,作家就喜欢来一段景物描写,然后再进入小说主题。到了1990年代,作家喜欢以简洁、设置悬念、大信息量等方式开头,尤其是在长篇创作上。如《土门》开头:“当阿冰被拖下来,汪地一叫,时间是一下子过去了多少岁月,我与狗,从此再也寻不着一种归属的感觉了。”*贾平凹:《土门》,《贾平凹文集》第10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高老庄》开头:“子路决定了回高老庄,高老庄北五里地的稷甲岭发生了崖崩。”*贾平凹:《高老庄》,《贾平凹文集》第15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页。《秦腔》开头:“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贾平凹:《秦腔》,第1页。《古炉》开头:“狗尿苔怎么也不明白,他只是爬上柜盖要去墙上闻气味,木橛子上的油瓶竟然就掉了。”*贾平凹:《古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另外,在一些长篇小说的后半部分,总有一个事件掀起故事的高潮,然后小说走向结束。如《高老庄》中蔡老黑抬尸大闹地板厂,《土门》中村长成义与警察间的“警匪大战”,《秦腔》中清风街的村民年终抗税风潮,《怀念狼》中人狼大战,《古炉》中的劫人事件,等等。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存在雷同现象,如《浮躁》中的金狗与《高老庄》中的成义,《秦腔》中的引生与《古炉》中的狗尿苔,《商州》中的珍子与《秦腔》中的白雪,《高老庄》中的子路与《秦腔》中的夏风等等。在意象方面,为了表达乡土的神奇与神秘,一些意象在不同小说中反复出现,如再生人、通说、太岁、被雷击、测字卜卦、半神半仙的老者等等。因此,在这些情节结构、人物以及与意象上的相似性,让读者觉得作家思维在做惯性滑行,是在重复自己,抄袭自己。所以有学者指出,“大约是从长篇小说《商州》开始,贾平凹的作品就存在着一种人物类型和结构模式。”*汪政:《贾平凹论》,《钟山》2004年第4期。这在90年代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于是出现了贾平凹创作中“好的80年代,坏的90年代”*程光炜:《批评对“贾平凹形象”的塑造》,《当代文坛》2010年第6期。的惊呼。另外,对故土神奇与神秘的书写,似乎也有些故弄玄虚之感,在“追求相对独立的‘道家’风范,不仅实际上难以行得通,而且易被当作‘异人’和‘怪物’”*陈断会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37页。。
二是思想力度的提升问题。李建军先生曾直言陕西当代作家身上存在两个致命性的欠缺:一是接受完全、系统教育的比例较低,这影响了他们在思想上的成熟和深刻,使不少作家“不能以更高远的视界来审视世界、观照生活”;二是部分陕西当代作家“缺乏现代文明指衡下的主体精神姿态和价值理念”,“缺乏彻底的批判精神,独立的人格意识,现代的公民意识和自由意识”。*李建军:《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这两种缺陷在贾平凹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尤其是思维与眼光的局限性。贾平凹总是说他是农民,并著有《我是农民》一书,这一方面说明他不忘初心,不忘乡情,另一方面也说明作家的这种“农裔城籍”*李星:《论“农裔城籍”作家的心理世界》,《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2期。的身份导致思维的狭隘性,“一旦失去了这片土壤,作家便会失去优势,变得六神无主。”*吴炫:《贾平凹:个体的误区》,《作家》1998年第11期。因此,如何书写有深度的乡土,突破自己创作上的瓶颈并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是贾平凹成为真正意义上“大师级的作家”*三毛:《三毛致贾平凹的信》,《贾平凹文集》第12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6页。的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毕光明)
On Jia Pingwa’s Local Novels
CHEN Zong-jun
(School of Literal Arts,Anqing Normal University,Anqing 246011,China)
Abstract:The persistent writing of the native soi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Jia Pingwa’s novels, and this kind of writing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a portrayal of local wonders, prodigies and queer customs; a probe into local nature, personages, events and mysteries of life experience; and considerations on humanity disinteg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Jia Pingwa’s local novels also embrace problems like repetitions in plot structures, characters and images as well as the shortage of ideological power, which reflects some bottleneck in his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Jia Pingwa; local novels; mystery; disintegra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小说发展史论”(编号:10BZW089)
收稿日期:2016-03-14
作者简介:陈宗俊(1974-),男,安徽怀宁人,文学博士,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5-003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