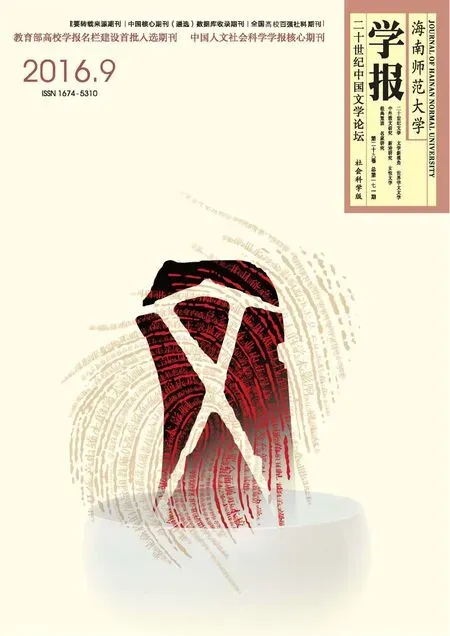求一个自在充实的人生
——关于《论编拾零》的隔空对话
2016-03-16陈骏涛肖菊蘋
陈骏涛,肖菊蘋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2. 沧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北 沧州 061001)
求一个自在充实的人生
——关于《论编拾零》的隔空对话
陈骏涛1,肖菊蘋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2. 沧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北 沧州 061001)
陈骏涛(以下简称“陈”):2016年1月,拙作《论编拾零》(《闽籍学者文丛》之一)编定,需要有一个序言,主编建议最好以一篇“访谈”或“对话”代序。“访谈”或“对话”倒是有的,但那都是隔年的“旧货”了,不适用。以往“对话”或“访谈”都是面对面进行的,如今北京正值寒冬,又三天两头被雾霾包围,请谁来做这个“访谈”或“对话”都有些“于心不忍”,于是想到了肖菊蘋。
肖菊蘋是河北南皮人氏,现为沧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是我的关门女弟子。肖菊蘋访学结业的一部书稿叫《鲁迅女性观考辨》,对鲁大师女性观的现代性(先进性)和异质性(局限性)作了一番考辨,开启了从性别文化角度研究鲁大师的一道门,颇有一番心得。于是我想请她看看我这本《论编拾零》,对它也来一番“考辨”,怎么品头论足都可以,当然不单是从性别观角度的考辨。但肖菊蘋却自有主意,她认为对话可以,但“考辨”却不可以,我说那就随意吧,不过主题应当是关于这本《论编拾零》的。于是,这场“隔空对话”就这样在网上开局了,实际上是网上的一篇聊天记录。
肖菊蘋(以下简称“肖”):陈老师,去年(2015年)8月29日,您的学生在福州会馆为您举办了80大寿庆生会,在此次聚会上我们得到了您馈赠的新作《陈骏涛口述历史》,厚厚的一大本,49万余字,您的大弟子、该书的采编陈墨先生致辞说:将这部书的出版作为献给您80大寿的寿礼。您当时在书的扉页上给我题写了8个字:“珍惜人生,善待生命” 。您能谈谈那次庆生会和那本书吗?
陈:好,菊蘋,首先得谢谢你应承做这么一个“隔空对话”。你说的这个“庆生会”确实是陈墨他们倡议的,就跟2006年的那个70生辰“庆生会”一样。其实,“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就没有过生日的记忆”——这是我在2006年的一篇《庆生》的小文章中说的,的确是实话。2006年的那个“庆生会”,就开了一个先例。我那篇小文还引了杜诗中的一句:“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作为我同意陈墨他们筹办那次“庆生会”的依据。这一次是80生辰(这是按农历算的,公历应该是79),这是“古稀”与“耄耋”的更迭年,似乎更重要,也更有理由。我也从善如流,其实主要是想借这个机会,大伙能在一块聚一聚。聚一次就少一次嘛,这也是实话。正好那次聚会之前,陈墨和朱侠夫妇策划的《陈骏涛口述历史》(以下简称《口述历史》)出版并拿到了几十本样书,所以才能人手一本。
说到“珍惜人生,善待生命”,不是我一时兴起、心血来潮,而是我一生的生命体验。一个人的一生实在太快了,尤其是到了后半生,总觉得是越走越快!我1955年夏秋从福州北上求学到了上海,在复旦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一呆就是8年,连头带尾实际上是8年半,到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时还叫学部文学研究所,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报到的时候,已经是1964年4月,是人生的第27个春秋了。如果能够从这个时候真正开始做事倒也不算晚,但却不料1966年撞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革命”,就“革”了10年,到1976年秋天“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是40周岁,到了人生的“不惑”之年。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而我呢?40岁了,过往的岁月不过是一片空白。怎么办呢?只有急起直追了!这是当年我的一种真实心态。那时,我似乎只看重“珍惜人生”,却不怎么看重“善待生命”——又走了一个极端!不过,如果没有从1976年以后的急起直追,也就不可能有我后三四十年的历史了。陈墨是亲自见证我这后三四十年历史的人,也是最接近我的人,还是最尊崇古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人,恰好他这些年又一直在搞电影界老人的口述史,已经是这个领域颇有名气的一个“行家”了,所以才有我这部《口述历史》的降生。
说到这部《口述历史》,开始陈墨提出这一动议的时候(大致是2012—2013年之交),我是感到很突然的。我想:我算什么人物?值得做这个口述史吗?像我这样的人,不要说在知识分子圈中,就是在文学研究所,也是可以一抓一把的,轮得上我吗?再说,即便搞出来了,又有哪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呢?但陈墨却很耐心地说服我,而且替我先期联系了一家一流的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把这家出版社的老总和责编请来跟我会了面,我这才动心了。终于在2013年9月,我出医院(就是2013年的那场大病)才一个多月,就开始上阵,其间历经近两年,终于在2015年8月出版,赶上了我的80生辰。这些话,我在这部《口述历史》的序言中都简要地说了,你也看到了。
肖:在您身上,“可以说凝聚着一部中国当代社会、当代文学的个人史”,您80年的人生,历经社会变迁,见证了“新中国文学的成长、曲折和发展”(《口述历史》)。听您讲述你的人生,仿佛跟随您的脚步亲临彼时现场,又仿佛是在看一部波澜壮阔而细节丰满、含蕴幽微的历史连续剧,而您作为剧中主人公,既有被时代潮流裏挟的小人物的身不由己,也有立于时代潮头奋力搏击的肝胆与风釆。陈墨先生采编这部口述史可以说为中国当代社会、文化、文学做了一件意义独特而深远的事。这部著作出版仅仅四个多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又要推出您的一部新作《论编拾零》,作为闽籍学者文丛之一种。学生真为您感到骄傲和高兴,您能谈谈出版这部著作的缘起或一些情况吗?
陈:你这引号内的文字是出自《口述历史》扉页上的“内容简介”。说实话,当这本书的责编当初把它发给我看时,我真有些“受宠若惊”——一则以惊,一则以喜。我曾向自己发问:它果真是那么回事吗?但冷静下来一想,倒也确实是那么回事:我在口述史的访谈过程中,确实不是把自己当作脱离整个大氛围的一个孤立的自我,而是当作与整个当代社会、当代文学紧密相连的个体,这个个体确实是见证了新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成长、曲折和发展的历史。这么一想,当然就觉得,做这部口述史,倒也不单是为我个人“树碑立传”了,它也许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不过你说的“立于时代潮头奋力搏击的肝胆与风采”之类,就是带有一些“夸张”色彩的文学描写了,不完全属实。
说到这本作为“闽籍学者文丛”之一的《论编拾零》,也是有点缘由的。
关于闽籍学人的历史渊源,说来话长,这里且不去说它。单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学评论界,就有所谓“京派”“海派”和“闽派”的说法。“以开放眼光开拓思维空间,用改革精神革新文艺评论”,是当年福建文学界提出的响亮口号。在北京、上海、福建等几个地方都集聚着一批有全国影响的闽籍批评家,如谢冕、刘再复、孙绍振、张炯、林兴宅以及已先后故去的潘旭澜、李子云、童庆炳等人。其后,这个队伍又不断扩大,有所谓“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闽籍学人相继涌现,比如南帆、陈晓明、王光明、林建法、林丹娅、谢有顺等人,我这里就不一一列名了。我作为闽籍学人之一,虽然不算出类拔萃,但出场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我记得1985年福建《当代文艺探索》创刊号上有一个闽籍评论家“亮相”的笔谈,我就忝列其中。我还和林兴宅共同组织并主持过当年影响很大的、在厦门大学召开的“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这些就不一一去说它了。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只是想表明:所谓“闽籍学人”,并非空穴来风!
再说这套“闽籍学者文丛”,我曾经向主编表示过不参加的想法。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近年由于身体不佳、思维迟滞,除了写过一些回忆性文字以外,几乎就没有什么正经的评论文字问世,而以往写的那些主要文章又都已经入选我的一部文学评论选集《从一而终》——这部书也在2013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再选吧,必定要“炒冷饭”,另起炉灶吧,又力不从心……但主编认定我还是应该加入,可以从不同角度选择一些有影响的文章。我想这样也好,既可以在“文丛”中留下一个痕迹,又能够炼炼我这个有些迟滞的脑力。这样,我就匆促上阵了,从我历年文论和编著这两方面的实际出发,分三辑择选了29篇文章,姑名之曰《论编拾零》。我曾经考虑过用《论编拾翠》或《论编撷英》这两个书名,但“翠”或“英”似乎不好自封,那就低调一点吧,于是就取了“拾零”。就是这么回事!
肖:陈老师,我说您“立于时代潮头搏击风云”并非夸张之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您就建设性地提出“新美学—历史批评”的文学批评范式,您应该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人吧?90年代初,您再一次敏锐地感应到商业化大潮的来袭,在纯文学日益边缘化的颓势下,力图在商品化与纯文学之间谋划一种双赢,以文论家兼编辑家的身份,主编了大型文学丛书《跨世纪文丛》,以开阔的视野和极高的辨识力将当代有代表性、实验性、探索性的各类各派作家作品囊括其中,成为当时一道绚丽的文学风景;9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在中国刚刚崛起,您就主编了《红辣椒女性文丛》,并积极投身女性文学建设中,为女作家与女评论家写评作序,大加鼓励与扶植,而且一直坚持至今,是为数不多的一直陪伴女性文学成长的男性学者之一。我认为这不仅体现一种敏锐的素质,更是一种智慧和境界呢!
陈:嗨,你总是喜欢用这些“高大上”的词汇,什么“立于时代潮头搏击风云”之类,说得我都有点发毛了。事实并非如此——我从来就不是那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年轻的时候爱出风头,但到中年以后,就逐渐收敛了,更注重于实干,只求一个自在充实的人生。我除了做编辑、写文章以外,确实还曾经提出过一些在文坛上有点影响的命题,“新美学—历史批评”即其一。这个命题当年在理论批评界是有点影响的,我记得陈思和、孟繁华、朱向前、白烨、樊星等人对它都有过肯定性的评议,陈晋、陈墨还跟我就这个命题有过一个长篇对话。我这个人在理论批评方面的最大问题也是最大弱项是“浅尝辄止”,缺乏“掘一口深井”的工夫和毅力,所以,我难以成为“理论家”,充其量也就是个“评论家”。“新美学—历史批评”问题就是这样,虽然也曾经写过几篇文章,有的文章还给自己带来过不大不小的麻烦,但却并没有深入开掘,搞成一本“专著”。倒是陈墨接过了这个话题,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好几万字的长文——《新美学—历史批评论纲》,但外界知道的人似乎也并不多。
说到主编《跨世纪文丛》和《红辣椒女性文丛》,倒确实是我注重于实干的明证。关于这两套丛书,已经说得很多了,外界似乎也有定评。它既是现实的一种需要,也是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情势下,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寻找的一条生路,也是跟我的本职工作——文学编辑和文学批评——紧密关联的一个新的领域:主编文学图书。其实,除了这两套文学丛书,我还主编或者参编过其他的书,都没有越出文学领域,例如《中国文学通典》《中华文学通史》《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纪文学60家》等。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从90年代开始到新世纪,我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啊!不管做得怎么样,我总还是尽心尽力去做了。这跟我碰到的一些好人是很有关系的,像邓绍基、张炯这样的老同事、老领导,像长江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燕山出版社的老总和责任编辑,还有书业界的几位人士,我至今都很感念与他们合作共事的那些日子……
话题还是转到那两套文学丛书上吧。《跨世纪文丛》似乎比《红辣椒女性文丛》影响要更大一些,它出了7辑67种,延续了将近10年,从1992年到2001年,真正是跨了世纪。这就不去说它了。就我个人的实际情况来说,仅仅出了4辑的《红辣椒女性文丛》对我的影响可能并不小于《跨世纪文丛》。这主要是指在我的晚年——如果是以60岁为界线的话,也就是在我60岁以后,又迈进了性别文学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虽然我一再说明我只是女性文学的一名“票友”,并非“行家”,但外界可不这么看。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我参加这方面的活动和写的这方面的文章确实也不算太少,用陈墨的话说就是,我经历了“从青年师友到女性之友”这么一个过程。有的人甚至认为,我可以出一本关于女性文学方面的专集了。但我有自知之明,我觉得与其去拼凑出一本专集,还不如选几篇还说得过去的文章,所以,我才在这本《论编拾零》中设置了一个“性别”专辑,选收了我关于女性文学的8篇文章。
肖:陈老师,您除了是文学批评家、编辑出版家,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老师,这一生您指导过的学生有多少恐怕连您自己也记不齐了吧?日本的栗山千香子说过一件事让我至今印象深刻,您曾帮她联系作家史铁生,然后亲自骑着自行车带她去史家拜访。说到这件事我又连带想起女作家毕淑敏讲过的另一个故事,当初在她对评论界与作者之间一些负面关系的传说感觉困惑茫然的时候,您作为一个颇有影响的评论界“大腕”,为写一篇文章专门赶到很远的北京铜厂去探访她,而她连顿饭都没有管,有这事吗?
从您书中所列“学术简表”看,仅为他人所作的序跋就有32篇,这些人中,有陈思和、孟繁华这样在文学批评领域有很大影响的评论家,也有陈染、方方这样在文学创作上自成一格的写作者,当然也有影响不那么大的作者。这些人中有的与您有师生之谊,原先没有的是否后来也从您这里受到过教益?您在发现、扶持年轻研究者与作者方面秉持的原则是什么?
您这样不遗余力,为他们“摇旗呐喊”,铺路架桥,是否如陈思和所言:“在学术事业的追求上,撇开个人的得失,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在今天社会可能达到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陈骏涛老师做到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能够做的最好的一面和最好的境界。”陈思和的这些话您也是认可的吧?
陈:我先修正你对我的一个定位:“编辑出版家”。你说我是“编辑家”勉强可以,但“出版家”就不敢当了,因为那些丛书和套书,我的身份只是主编、总主编或者总策划,从不插手出版。你说我还是一名老师,这倒是确切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到你为止,这三十多年的时间,在我名下当研究生、进修生和访问学者的人头是有点数不太清了。在做我的《口述历史》时,陈墨要我报个名单,我就一个一个往下捋,排出来的名单一共是17个人,还不算3名外籍人士,以及在鲁迅文学院兼课期间分到我名下的三四名外地学员。最早的是陈墨和谭湘,那是在1985年,而你是最后一个,到了2014年。你列举的那位栗山千香子,是没有入册但确实在我名下进修过的日籍人士,那是在1995年。
你引述的栗山千香子、毕淑敏、陈思和说的那些话,是10年以前我的一部纪念文集《这一片人文风景》中,他们几位写的忆念文章中的原话,虽然大多是溢美之辞,但当年乃至今日重温这些言辞时,仍然感到一片温馨的暖意,并由此而更加思念当年与他们以及你们相处的那些日子。毫无疑问,他们(也包括你们)都只说了我“最好的一面和最好的境界”。但我有自知之明,我不过是做了我应当做和能够做到的一面,应当做而没有做到的另一面,以及我个人的弱项和缺项,他们(也包括你们)都避讳了。
至于说到我写的那些序跋,32篇可能还不是全部,还有遗漏的,这也是我这30年耕耘的部分成果。这些序跋有的是应书作者本人的邀约写的,有的则是我主编的丛书和套书的分内之事,不管哪一类,我都是认真对待的。说实话,这些文章水平参差不齐,但还不是敷衍潦草、口是心非之作。从这些序跋中,也多多少少能够感觉到这几十年文学行进的脚步和身影。所以,我在这本书中收录了11篇序跋,约占我这30年所写序跋的1/3,自成一辑。
肖:1997年,徐坤在《悼批评时代的终结——〈文坛感应录〉感言》的篇尾说:“批评,还能否作为一种独立品格的象征?还能否作为一种事业的选择?阅尽了昨日的繁华之后,在瑞雪的冷清中轻轻关上书页,不禁掩卷而长叹:骏涛先生,且慢言退休罢!如此之宽厚、睿智的长者,请再送年轻的中国当代文学走一程。”时隔9年,2006年10月,郭小东在《真心守望——陈骏涛印象》中如是说:“当我在深秋依然酷热的南方,写下这些关于陈骏涛先生的文字时,我心头忽然有一种过分沉重的痛楚。那就是陈先生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磨难而依然胸怀坦荡仁爱待人,我们也即将老去,我们能如他们一样,把自己的人生,锻造得如他们一样令人满意令人尊敬吗?”如今又一个10年过去了,转眼已到2016,您依然与您关心、热爱的文学事业执手偕行,不离不弃;依然以您特有的宽厚与严谨为后学指引着学问和人生的门径,让他们在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更一往情深!
陈:徐坤和郭小东这两段话,今天重读,我是既感动又羞愧!尽管这是10年前、甚至近20年前说过的话,但重温这两段话,让我又一次想起了那些激情的岁月,在那些岁月里,我与那些青年朋友之间的关系。很多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桥——记忆和感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说过这样的话:“一些年青朋友说应该感谢我,我说我应该感谢他们。尽管我曾经为他们的出阵擂过鼓,助过威,对他们有过那么一点帮助,但我从他们身上也吸取了许多养分,可以这么说,倘若没有他们的影响和催动,也没有我的今天。人类追求真理的进程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力中延伸的,每一代人都既是起点又是桥梁。”——这也是当年最具有“老桥”意识的青年评论家黄子平曾经说过的话,它还依然是如今迟暮如我的一种心情!
人心依旧,但岁月无情!如今我已进入耄耋之年,你说的“依然与您关心、热爱的文学事业执手偕行,不离不弃”,这倒是事实,也是我生命和精神的一种寄托,但“为后学指引着学问和人生的门径,让他们在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更一往情深”之类,就是一种良好的祝愿和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了!
好了,该说的都说过了,我们的对话就此打住吧,老年人的唠叨,说多了,会讨人嫌的,余下的话,留在以后再叙吧!谢谢你,也谢谢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所有朋友!
2016年1月12—20日,北京—沧州
(责任编辑:王学振)
In Pursuit of a Free and Full Life——On the Telekinesis Dialogue inLunBianShiLing
CHEN Jun-tao1, XIAO Ju-pin2
(1.InstituteofLiteratur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2.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CangzhouNormalUniversity,Cangzhou061001,China)
2016-07-09
陈骏涛(1936-),男,福建福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肖菊蘋(1967-),女,河北南皮人,沧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I206.7
A
1674-5310(2016)-09-0056-04